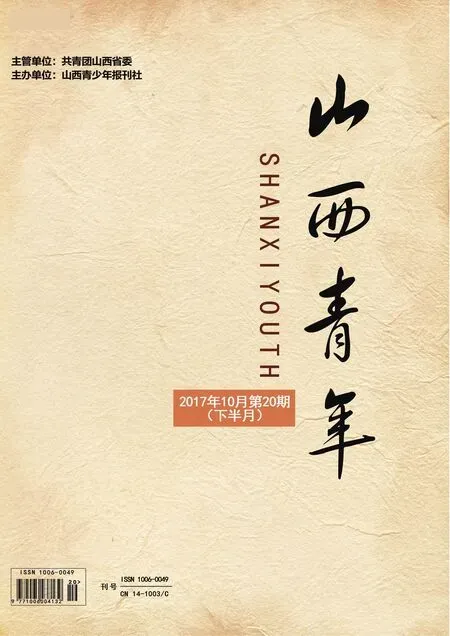关于法官的法理认同与裁判说理的探讨
孙浩骞
长春理工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关于法官的法理认同与裁判说理的探讨
孙浩骞*
长春理工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司法裁判方面通常运用法理来说理,其容易被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接受,同时植入并且提高整个社会的法理意识。要想让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得以体现,依靠国家的权利是主要方法,除此之外,通过裁判的法理也能证实裁判结论的公正性。当法官在裁判说理时,只有运用法学理论分析说明,才能澄清案件的事实和其中的逻辑关系,使裁判符合法律法规、道德准则和逻辑思维,以证明裁判结论的公正性。
法理;裁判;说理;民意
近些年,民意与司法审判之间的冲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中间显示的问题就是司法判决和社会公众认可之间的隔阂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是法官专业的法学思维和群众常识、理性和非理性以及专业和非专业之间的区别造成的结果。从裁判说理这一角度,司法判决和公众舆论之所以会有冲突主要是因为法官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和裁判的结论,更没有对法理说理进行分析。当今这种现状并不能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在裁判中满意。裁判的法理不能被当事人和公众理解,怀疑裁判结果的合理性,进而质疑和误解裁判的公正性。这些现象的源头是法官的自我否定和当事人和公众不满无法理说理的现状所产生的。当事人和公众想要了解裁判理由的愿望是呼唤裁判文书通过法理分析得出的民意。审判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方法,而司法法官用法理说理则能缓解民意与司法审判之间的冲突,这应成为以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一、在裁判说理中缺乏法理
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官都背负着一个恶名:裁判不说理。这种情况在学术界备受批评,可到目前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现在,随着“四五司法改革纲要”的颁布,以往的旧问题再次出现。司法裁判要想具有权威性,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方面就是通过裁判说理来证明裁判结论公正性。因此,裁判文书说的“理”与法理密不可分。当法官在裁判说理时,只有运用法学理论分析说明,才能澄清案件的事实和其中的逻辑关系,使裁判符合法律法规、道德准则和逻辑思维,从而使裁判结论的公正性得以呈现,使得司法制度的公平、透明度以及可接受性能够得到保证。但是,我国的司法裁判现状并不完善,还存在着不以法理说理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裁判文书都不能准确对裁判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引起司法裁判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得裁判的权威和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二、法官在裁判中应如何以法理说理
(一)让法理与解释方法相结合
运用法理和解释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说理可以做如下理解:一是用法理去解释事实所包含的法律意义,二是用理解释、扩展和限制相关模糊的法律。具体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解释:
第一,运用法理解释案件事实纳入法律制度的过程。法官应当利用法律概念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对案件事实所呈现的法律性质进行专业阐述和澄清,从而让当事人、律师以及社会公众对案件事实以及案件所对应的法律关系的权利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把案件事实变成法律事实。
第二,按照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法理被用来解释适用于案件裁判的逻辑思考和裁判过程。法官可以用法律构成要件理论来解释案件事实和法律事实的一致性;使用公平和正义的概念阐述案件事实的价值判断与法律规定相符合,而且其与法律法规的价值判断也相一致,从而根据法律和案件的事实对法官判决的逻辑和思维过程进行推论。通过以上方法证明法官裁判的公平性、公正性以及客观性,从而让当事人接受裁判。
第三,当法律规范不清不楚,与案件的事实不完全相符,不能直接进行采用时,法官应当用法律来阐明,在裁判文书中运用法理对法律法规的扩展的阐述对法律法规进行解释。因此,法官应该运用普遍性原则来解释常识的扩展,避免被误认为是迎合公众舆论的非理性决定,进而提高裁判的说服性。
(二)运用法理来理解价值判断过程
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性和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在案件的审理中会有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可能某些案件事实并不能与相关法律法规完全匹配;第二种情况就是,案件的事实的确符合法律法规,但其逻辑推断出的裁判结果将导致不公正的法律后果。
当发生第一种情况时,法官无法找到与案件事实相匹配的法律规范时,需要对该准则的目的价值进行分析和判断,之后根据部门法学说,将法理具体化,通过逻辑思维来创造适合的裁判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应该在裁判文件中用法律术语来分析价值判断过程,并用法理说明价值判断和选择的缘由。一般情况下,众所周知,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主观性的,我们并不能从法律、教义学或者司法判例中对判决指示完全理解。法官在很多情况下,必须考虑他们判决的结果,从他们的是非意识和涉及到的利益进行决策,这通常和经验、前见等相关。在这一点上,法理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轮廓”——一种不明确的(法官)行为准则。该制度具有辅助法官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功能,实际上指导和决定着法官的判决。
在发生第二种情况的时候,也就是说案件事实与法律法规相一致,但其逻辑做出的裁判将会引起不公正的法律后果,这个时候,法官应该在裁判文书中运用法理监督功能,对价值判断进行分析,分清恶法,为裁判规范提供基础。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司法裁判中运用法理来进行说理时,应该被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所接受,这样才能提高社会的整体的法理意识。首先,我们应该对法官的专业的法学修养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强,使法理成为他们自身精神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法官自身发自内心的对法理进行认同,他们才会用法理来说服大众。与此同时,提高其他法律共同体成员的法学理论知识,而不仅仅是法官。另外,最高法院所颁布的指导案例应尽可能地在法理上进行分析以使其成为法官等专业团体工作人员的直接指导。
[1]凌斌.法官如何说理:中国经验与普遍原理[J].中国法学,2015(05):99-117.
[2]葛天博.存在与选择:基于司法认同的实证分析[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06):3-7+52.
[3]于晓青.法官的法理认同及裁判说理[J].法学,2012(08):76-86.
[4]黄强.增强裁判文书说理功能——从法官法律解释能力的现实构建视角[J].山东审判(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2006(03):100-103.
[5]王申.法官、现代性与法理认同[J].法学杂志,2006(01):94-96+144.
孙浩骞(1992-),男,汉族,吉林长春人,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法理学。
D
A
1006-0049-(2017)20-008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