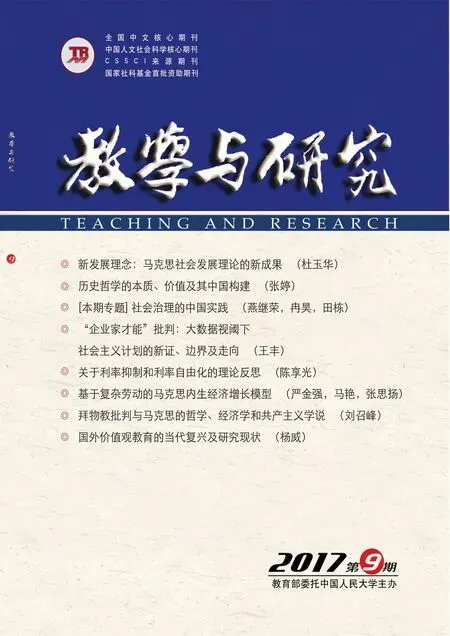关于利率抑制和利率自由化的理论反思
——兼论借贷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之关系
关于利率抑制和利率自由化的理论反思
——兼论借贷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之关系
陈享光
资本利率价格观 ;货币利率价格观;借贷资本;利率自由化
资本利率“价格观”和货币利率“价格观”是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两种利率“价格观”,其他的利率“价格观”不过是这两种价格观的变种或综合。无论是资本利率“价格观”还是货币利率“价格观”都缺乏现实解释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利率看作是与资本商品—借贷资本相联系的价格,但它是一种不合理的价格形式。这种利率“价格观”可以称之为借贷资本利率“价格观”。不同利率“价格观”引申出不同的政策主张,由资本利率“价格观”和货币利率“价格观”引申出的利率政策和改革主张是错误的。只有正确把握作为资本商品价格的利率,厘清利率与货币或货币资本积累、现实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才能对利率政策和利率改革做出正确的选择。
市场经济中,利率常被看作是一种价格形式,同其他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不同的经济学中,对决定利率的供求关系的解释却完全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利率价格观。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着两种典型的利率“价格观”,一种可以称之为资本利率“价格观”,另一种可以称之为货币利率“价格观”。西方经济学中其他形式的利率“价格观”不过是这两种形式“价格观”的综合或变种。资本利率“价格观”把利率看作是由储蓄投资决定并调节储蓄投资使之趋于均衡的价格,而货币利率“价格观”则把利率看作是由货币供求决定并调节货币供求使之均衡的价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也把利率看作是一种价格形式,认为它是由借贷资本供求决定的价格形式,然而它是一种不合理的价格形式,这种价格观可以称之为借贷资本利率“价格观”。本文对不同的利率“价格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西方流行的利率价格观引申出的利率政策和利率改革主张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说明正确理解利率“价格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利率政策和利率改革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资本利率“价格观”和货币利率“价格观”
西方经济学中,利率通常被看作是一种价格,同其他价格一样,也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不过不同经济学流派对决定利率的供求关系的解释却很不相同。古典经济学把利率看作是资本的价格,这种价格取决于资本供求关系。资本的供给来源于储蓄,资本的需求来源于投资,投资是利率的递减函数,储蓄是利率的递增函数。均衡利率取决于投资与储蓄的均衡关系。这种利率价格观没有考虑收入与储蓄关系,这与其关于国民收入的假定有关。古典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相信供给能创造自己的需求,依靠市场力量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充分就业均衡条件下把国民收入排除在储蓄函数之外。同时由于古典经济学把货币看作是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面纱”,因此这种利率价格观没有考虑货币因素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利率仅与储蓄投资等实际经济因素有关,而与货币因素无关,利率取决于储蓄投资,同时也调节储蓄投资,并使二者趋于平衡。
古典的资本利率“价格观”受到凯恩斯的批判。凯恩斯认为,古典利率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经典学派(古典学派)所用二函数,即投资对于利率之反应,以及在定量所得下,储蓄对于利率之反应,不足以构成一利率论。此二函数所能提示者,只是:设从其他方面,知道利率之高低,则所得将定于什么水准;或所得维持于某水准(例如充分就业下之所得水准),则利率将定在什么水准。”[1](P155)凯恩斯认为,利率不可能是储蓄或等待的报酬。因为,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储蓄以现金方式储藏起来,虽然他的储蓄量和不以此方式进行的储蓄量完全相同,他并不能赚取任何利息。凯恩斯认为,古典利率理论“错误之处,乃由于把利息看作是等待本身之报酬,而不看作是不储钱之报酬。”[1](P155)“利率并不是使投资资源之需求量,与目前消费之自愿节约量,趋于均衡之‘价格’。”[1](P143)在凯恩斯看来,“传统分析方法是错误的,乃在其未能正确认明何者为经济体系之自变数。储蓄与投资都是经济体系之被决定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1](P157)由于储蓄和投资都是经济体系中的自变量而非因变量,因而不能决定利率。传统的分析方法虽然知道储蓄决定于所得,“但忽视了一点:即所得定于投资,故当投资改变时,所得必定改变,所得改变之程度,乃使储蓄之改变恰等于投资之改变。”[1](P157)因此,在凯恩斯看来,储蓄供给曲线和投资需求曲线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能产生一个均衡的利率,储蓄和投资不可能通过利率调节实现均衡,而只能通过收入调节而趋于均衡。
古典利率“价格观”也受到罗杰斯(1989)和莱琼霍夫德(1981)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利率价格观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2][3]在他们看来,资本利率“价格观”把存量和流量割裂开来,储蓄曲线和投资曲线代表对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或代表对新证券或债券的需求和供给的流量,均衡利率取决于这些流量。然而,这种分析忽略了存量的影响,似乎前期发行的还未到期的证券或债券不影响利率的决定。他们认为,实际上并非如此,对存量证券需求可能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增加或减少,从而影响这些证券的价格和利率。例如当流动性偏好增强时,对存量证券的需求就会减少,存量证券的价格因此会下降,利率提高,从而偏离由流量决定的所谓均衡利率,新的均衡的建立取决于利率变动产生的影响。另一逻辑上的问题是投资和储蓄在其理论分析上是用价值来定义的,而将资本作为一个价值的量来推导利率将陷入循环论证。从逻辑上看,如果不知道利率,资本的价值就无法确定,没有资本的价值,也就不能推导出利率理论。
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把利率看作是使储蓄投资趋于均衡之“价格”,那么凯恩斯则把利率看作是由货币供求决定并使货币供求趋于均衡之“价格”。凯恩斯用流动性偏好解释利率,他认为利率是货币现象,因此只能用货币供求而不是资本的供求来解释。凯恩斯认为,货币是一种特殊的资产,最具有流动性,利息是放弃这种流动性取得的报酬,而不是储蓄或等待的报酬。因此,利率不是取决于资本的供求,而是取决于货币供求,利率是使货币供求趋于均衡之价格。凯恩斯说:“利率并不是使投资资源之需求量,与目前消费之自愿节约量,趋于均衡之‘价格’。利率乃是一种‘价格’,使得公众愿意用现金形式来持有之财富,恰等于现有现金量。这就蕴含:设利率低于此均衡水准(设把现金脱手所可得之报酬减少),则公众愿意持有之现金量,将超过现有供给量;设利率高于此水准,则有一部分现金会变成多余,没有人愿意持有。假使这种解释是对的,则货币数量与灵活偏好二者,乃是在特定情况下,决定实际利率之两大因素。”[1](P143)凯恩斯认为货币供给由货币当局决定,货币需求即流动性偏好由人们的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决定。交易性货币需求是收入的函数,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预防性货币需求既受收入因素的影响,也受利率变动的影响;投机性货币需求是利率的递减函数。均衡利率取决于货币供求平衡关系。在货币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利率取决于货币供给,利率会随货币供给的增加而降低,但当降低到某一很低水平时,经济中所有的人都预期利率将会迅速上升,从而使货币需求曲线变成水平的,货币需求无限大,这时就形成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在存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不会对利率和物价产生任何影响。显然,在凯恩斯看来,利率是纯粹的货币现象,它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利率的决定与实际变量无关,利率的变动使货币供求而不是使储蓄投资趋于均衡,储蓄投资的均衡主要是由收入而不是利率调节实现的。
显然,资本利率“价格观”把利率看作是由储蓄投资实际经济变量决定而与货币变量无关的价格形式,货币利率“价格观”则把利率看作是由货币变量决定的而与实际经济变量无关的价格形式。这两种形式的利率“价格观”无疑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一些西方学者试图把两种利率“价格观”加以综合。借贷资金利率“价格观”、IS-LM模型中的均衡利率“价格观”等,就是资本利率“价格观”和货币利率“价格观”综合而成的,资本利率“价格观”和货币利率“价格观”存在的问题必然存在于这种综合利率“价格观”中。
二、马克思主义借贷资本利率“价格观”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上述两种形式的利率“价格观”及其变种都是错误的,利率既不是由资本供求决定的价格形式,也不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价格形式,而是一种与特殊的商品——资本商品相联系的特殊价格形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利息、利率范畴必须联系生息资本、借贷资本来解释。生息资本存在于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广泛存在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是货币的各种职能发展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了货币就有货币储藏,虽然货币是货币,不是资本,但通过借贷利息,货币储藏者就可把储藏的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手段,储藏者依靠这种手段占有全部或部分剩余劳动,以及一部分生产条件本身。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购买和支付越来越在时间上相分离。在这种条件下,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基础上产生的高利贷,又进一步扩大了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为高利贷的真正的、广阔的和独有的地盘。[4](P678)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特殊形式,是同小生产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这种情况下,把超过生产者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全部余额以利息的形式被高利贷者所侵吞。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利息,资本主义社会的利息只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息资本变成从属于产业资本的一个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转化为资本,并通过这种转化,由一个一定的价值变成一个自行增殖的价值。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外,又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作为资本的商品,借贷资本的回流采取偿还的形式,因为“它的预付、它的让渡,具有贷放的形式。”[4](P385)“只有这种让渡的行为,才使货币的贷放成为资本的货币的让渡,也就是说,成为作为商品的资本的让渡。”[4](P392)资本本身所以表现为商品,首先是因为资本被提供到市场上来,并且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但它的使用价值是生产利润。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其价值不是由它们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们为自己的所有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来决定。 其次,资本所以表现为商品,是因为利润如何分割为利息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是由供求,从而由竞争来调节的。
借贷资本作为资本商品有一种属性,就是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资本只有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才变成这样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自行增殖的性质有一个固定的价格,这个价格在每一具体场合都表示在利息率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产生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产生出利息率。”[4](P415)货币资本从资本循环运动中独立出来,形成独立于职能资本家的货币资本所有者,从而产生了借贷关系,进而产生了利息和利息率。很显然,如果货币资本所有者和职能资本家不是相独立,货币资本所有者就是职能资本家,职能资本家拥有所需的货币资本,也就不可能产生借贷关系,从而不可能产生利息和利息率。正是货币资本所有者不是职能资本家,职能资本家需要货币资本,从而产生了资本的商品化,就是要把货币作为资本来增殖的货币所有者或货币资本家把货币让渡出去,投入流通,使货币资本成为一种资本商品。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让渡只是暂时由它的所有者占有变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占有,因此它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卖出,而是以偿还为条件的贷放。在借贷资本形式上,同一资本具有双重规定,在贷出者手中,它是借贷资本,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里,它是作为产业或商业资本。资本商品同一般商品是不同的,从而决定了利息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价格。
由于资本商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所以“利息是资本的价格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不合理的。” 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把利息叫作货币资本的价格,那就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与商品价格的概念完全相矛盾。在这里,价格已经归结为它的纯粹抽象的和没有内容的形式,它不过是对某个按某种方式执行使用价值职能的东西所支付的一定货币额”。[4](P396)西方经济学流行的利率“价格观”把利率看作是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的价格,看不到它是一种特殊商品的不合理价格形式,因而难以对利率做出科学的解释。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借贷资本上,由于同一资本具有双重规定,所以平均利润要在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利息只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由于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所以利息率是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马克思指出:“资本所以表现为商品,是因为利润分割为利息和本来意义的利润是由供求,从而由竞争来调节的,这完全和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它们来调节的一样。”[4](P398)但是,商品的价格是以价值或生产价格为基础的,商品供求的变化只影响商品价格对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偏离,如果供求平衡,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和它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相一致,商品供求决定价格对规律的偏离,但货币资本的利息不是这样,竞争并不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相反,除了由竞争决定的分割规律之外,没有别的分割规律,因为并不存在“自然利息率”。尽管利息是平均利润的组成部分,利息率由平均利润率调节,但利息率并不存在“自然界限”。马克思把平均利润率看作是利息的有最后决定作用的最高界限,而“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它可以下降到任何程度。”[4](P401)不过,马克思认为,这个时候出现起反作用的情况,使它提高到这个相对的最低限度以上。显然,利率既受制于一般利润率,又调节着剩余价值的分割。
借贷资本既然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商品,货币资本家供给这种商品,职能资本家购买这种商品,形成对它的需求,市场利息率同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由供求决定。这种供求既不是一般的资本的供求,也不是货币的供求,而是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在一般利润率一定的情况下,市场利率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
要指出的是,随着现代金融化的发展,不同经济部门都卷入普遍的金融活动之中,特别是家庭部门不仅是借贷资本的供给者,而且成为借贷资本的需求者,它们形成的借贷资本的供求成为借贷资本供求的组成部分,借贷关系不仅发生在货币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而且发生在各种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这种情况下,利率不仅受不同部门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的影响,而且影响和调节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利率的这种分配再分配功能由于金融化快速发展而不断加强。
从资本形成过程看,货币金融的存在使得资本积累过程分立为三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过程,即储蓄过程、金融过程和投资过程。借贷资本的供求既与储蓄过程相关联,又与投资过程相关联,储蓄中以债权资本形式提供的部分,就构成了借贷资本的供给部分,投资中以债权资本形式形成的货币资本需求就构成借贷资本的需求部分,利率与储蓄投资中的这两部分相关联,而不是同储蓄投资整体相关联。因此,从储蓄投资过程看,以债权资本形式形成的货币资本的供给和债权资本形式形成的货币资本的需求,决定和影响利率, 而不是储蓄投资流量决定和影响利率。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储蓄投资过程的分离,没有因这种分离产生的资本商品化,就没有利息和利率,把利率看作是储蓄和投资的函数是没有根据的。利率是由借贷资本供求而不是储蓄投资决定的。
由于借贷资本是以货币形式出现的,往往造成借贷资本与货币相混同,把借贷资本的供求归结为货币供求,从而对利率决定做出错误的解释。实际上借贷资本和货币是完全不同的经济范畴,借贷资本虽然是以货币形式出现的,货币形式上贷出的资本量影响利息率,但不能认为利息率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借贷资本不同于货币,借贷资本的量不同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并且不以后者为转移,西方的货币利率“价格观”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把货币与货币资本或借贷资本相混淆,因而不能正确解释利率的决定和利率与实际经济变量、货币变量间的关系。
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利率的变动无疑要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不以一个国家的生产条件为转移而对利息率的确定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比它对利润率的影响大得多。”[4](P412)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情况更是如此。当今世界,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频繁,流动规模愈来愈大,而其中货币资本的流动远比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性更强,各国的利率影响这种资本的流动,同时受这种资本流动的影响。
借贷资本一方面是所有权资本,利息是其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另一方面对职能资本家来说是借入资本,他们利用借入资本进行经济活动,获得的资本果实即利润必须以利息的形式让渡给借贷资本家。利息率直接影响借贷资本供求,而不是货币供求或一般的资本供求。由于借贷资本的双重规定,借贷资本的积累一方面表现为所有权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表现为现实资本的积累。然而所有权资本即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并不等于现实资本的积累,借贷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积累并不一定一致,借贷货币资本可以在没有任何现实积累的情况下增加,甚至是现实产业资本收缩和萎缩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也影响着利率,同时利率也影响借贷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
三、利率抑制与利率自由化的反思
利率能否通过市场自动调整到最优水平或均衡水平,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利率“价格观”给出了不同答案。凯恩斯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者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凯恩斯认为,“利率不会自动调整到一种水准上,最适合于社会利益;反之,利率常有太高之趋势,故贤明当局应当用法令、习惯甚至道义制裁加以抑制。”[1](P302)他提出:“故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续下去。补救商业循环之良方,不在取消繁荣,使我们永远处于半衰退状态;而在取消衰退,使我们永远处于准繁荣情况。”[1](P278)按凯恩斯的观点,储蓄是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利率的函数。因为收入通过乘数依赖于投资,所以储蓄最终是由与利率水平成反比的投资决定的,因此实际利率高就会引起投资和储蓄率的下降,并会与增长和就业发生冲突。凯恩斯认为,“利率变动对实际储蓄量之影响,非常重要,但与一般人所设想的方向相反。即使提高利率确有减低消费倾向之作用,但我们断言:利率增高之结果,乃减少实际储蓄量。盖总储蓄乃定于总投资,而提高利率适足减少投资——除非投资之需求表变动,抵消利率上涨之影响。故利率增高之结果,必定是把所得压低到一个水准,使储蓄减至与投资相等”。[1](P95)在凯恩斯看来,必须把利率控制在一定水平上,使得该利率下的投资量足以维持充分就业量,这样才能使所得和储蓄增加到充分就业水平。
凯恩斯的抑制利率的主张,显然是建立在对投资、储蓄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的。在凯恩斯看来,储蓄是消极行为,投资则不然,它是发起或维持某种生产过程或是保持流动资本等积极行为,资本的增减,取决于投资量而不是储蓄量。储蓄不会使财富总量增加,而只会引起双重的转换。“一方面是消费品从储蓄者转移到消费者整体中去,另一方面则是财富从生产者整体方面转移到储蓄者整体中去,但消费总量和财富总量则保持未变。”“储蓄的结果只是在消费者之间以及有权保有财富的人之间引起变动或转换,它被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家的损失抵消了。”[5](P147)凯恩斯否定了储蓄决定投资的传统观点,认为投资能够自行产生与其适应的储蓄,是投资决定储蓄,而不是相反,高的利率将抑制投资进而抑制收入的增加,并通过收入影响储蓄,利率抑制则能对投资、收入和储蓄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凯恩斯学派继承了凯恩斯的投资决定储蓄的观点,坚持抑制利率的主张。根据他们的分析,把利率抑制在低水平上能够刺激投资增加,从而能够起到调动闲置资源进而增加收入的机制性作用,同时低利率对国民收入做了有利于投资者和借款者以及利润所得者的再分配,从而有助于增加社会储蓄投资流量。市场自发形成的利率难以把利率控制在发挥这种作用的水平上,相反,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形成的利率常有趋高之趋势,从而对投资储蓄和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新凯恩斯主义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引入信贷市场的分析,证明信贷市场形成的所谓均衡利率并不是最优的。斯蒂格利茨等指出,“在理解信贷市场方面,标准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不仅毫无帮助,甚至会产生误导。这种误导性是因为我们倾向于把信贷价格,也即利率,看作和其他价格一样,能够实现市场出清。”[6](P24)他们认识到,利率有别于一般商品价格,信贷市场并不能自发形成实现市场出清的利率。因为信贷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银行实际收益与贷款利率之间并不存在单调的正向关系。按照他们的解释,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利率提高,导致申请借款者的平均质量下降。第二,较高的利率鼓励企业将资金用于高风险的活动,导致道德风险问题。最后还有一个更为直接而简单的原因:即使借款人的行为没有改变,较高的利率也意味着企业拖欠的可能性更高了。如果存在破产成本,投资的社会收益将因此而下降”。[7](P208)这样,市场形成的所谓均衡利率并不是最优的。他们证明了存在一种低于市场均衡利率的利率可以改善相互提供担保的贷款者的整体资产质量,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这种低于市场均衡利率的利率可以与出口鼓励相联系,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在他们看来,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信贷配给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信贷配给并不是低效率的,相反政府可以借助于信贷配给鼓励向一些特殊领域如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促进特殊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抑制利率理论和政策主张为自由主义者特别是金融自由化论者所否定。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利率抑制使得利率这种价格低于市场均衡水平,必然对经济产生严重的扭曲作用,阻碍储蓄投资的增加和合理分配,阻碍经济增长。麦金农(1973,1989)从利率对储蓄投资过程的影响说明了利率抑制的严重后果,他认为,把利率抑制在均衡水平以下,一方面会抑制储蓄的增长,使储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另一方面将使银行更偏好于一些资本收益不高,但资本成本相对较低的投资计划,从而降低投资的效益。同时抑制利率导致信贷配给,而信贷配给必然导致低效率。不仅如此,利率抑制也会导致非正式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由于这种非正式金融市场上信息极不完善,风险管理费用昂贵,交易成本较高,可支配的资本规模又相对较小,限制了发展的空间,因而这类市场也同样没有效率。这样,由于利率的抑制导致各类金融市场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且会造成金融中介的严重机能障碍,因而阻碍经济增长。[8][9]格利、肖等认为抑制利率会减少储蓄投资流量,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他们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的核心就是解除利率管制,提高实际利率,实际利率的提高将产生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因为“反映储蓄稀缺性的价格,会提高储蓄率,改善储蓄配置,促进劳动力对资本设备的替代,并有助于公平的收入分配。”[10](P129)
利率自由化理论体现的利率“价格观”与古典、新古典的利率“价格观”是完全一致的。按照利率自由化理论的解释,利率愈高,人们愈是趋于放弃即时消费,做出有利于将来消费的决定,储蓄投资水平因利率提高而提高,同时利率作为资本价格,影响资本和劳动力的技术组合选择,降低利率意味着资本价格相对下降,因而会导致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而提高实际利率能够防止资本对劳动力的无效替代。按照利率自由化理论的逻辑,取消利率抑制,把实际利率提高到所谓的均衡水平,不仅可以促使储蓄投资流量的增加,而且能够排除效益低的投资项目,促使资源流向效率高的投资领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这反过来又带来储蓄的增长,促进投资增长,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可见,利率自由化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典、新古典的利率“价格观”基础上的,如果说利率抑制论承认了市场失灵,那么利率自由化理论和政策主张则恢复了市场神话。
尽管利率抑制和利率自由化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们都是建立在对利率的错误认识基础上的,他们对利率与相关变量关系的认识以及储蓄投资关系的认识都缺乏科学的根据。如前所述,利率是与特殊的资本商品相联系的价格形式,而资本商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利率是一种不合理的价格形式。利息是借贷资本带来的果实,在借贷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条件下,它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从借贷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关系看,虽然一般利润率构成利息率的上限,但最低界限则是完全无法决定的,完全取决借贷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竞争,并不存在自然利息率,不能把利息率看作是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的价格。
既然利息率是与资本商品的形式——借贷资本相联系的范畴,那么利息率直接影响的是借贷资本的供求。提高或降低利息率可以引起借贷资本的增加或减少,但借贷资本供给增加或减少并不意味着现实积累增加或减少。借贷货币资本积累的构成要素和现实资本积累的构成要素是完全不同的。借贷资本的增加可以在现实积累不变甚至减少的条件下实现,因为借贷资本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性手段如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集中,流通准备金或私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约(这些准备金在短期内就转化为借贷资本)而实现。借贷货币资本具有虚拟性,“即使假定借贷资本存在的形式只是现实货币即金或银的形式,只是以自己的物质充当价值尺度的商品的形式,那么,这个货币资本的相当大的部分也必然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完全像价值符号一样,只是对价值的权利证书。”[3](P576)当货币在循环中转化为借贷资本,并且同一货币反复代表借贷资本时,它只是在一点上作为货币存在,而在其他点上,它只是以资本索取权的形式存在。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由现实积累也就是由商品资本等等的价值转化为货币而产生的,但这种索取权或权利证书本身的积累,既不同于它由以产生的现实积累,也不同于由发放贷款实现的未来积累。借贷货币资本的相对独立性和虚拟性意味着货币资本的积累能够脱离现实积累而实现。事实上即使在产业资本积累主导下,也能够产生脱离积累的过度货币资本积累。在金融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利率的自由化易于导致借贷货币资本的过度积累,而过度积累的借贷货币资本极易投向易于泡沫的资产,不仅强化资本的流动性和投机性,而且可能导致现实积累的障碍,甚至导致职能资本的金融化,因为它强化了金融投资,而不是实际产业投资。利率自由化的理论没有区分货币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把货币资本的积累等于现实资本的积累,假定提高利率必然带来现实积累或储蓄投资流量的增加,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利率抑制理论尽管意识到利率并不直接作用于现实积累,但他们不理解货币与借贷货币资本的区别,因而不理解利息和利息率的实质(如凯恩斯把利息看作是放弃货币流动性的报酬),看不到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进而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之间的联系,利率抑制虽然能够启动投资通过收入产生储蓄机制,然而这不是无条件的,如果不存在闲置资源,或者存在闲置资源但不是由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靠抑制利率刺激投资不仅不能启动这一机制,而且将造成储蓄投资通道的障碍,影响储蓄投资流量的增加和配置效率的提高,因为长期把利率抑制在低水平上,损害了通过借贷资本形式进行资本集中和配置的功能,使资本循环周转过程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反流受阻,从而影响资本的正常循环周转,现实的资本积累由于得不到借贷资本积累的支持而受到影响。
在储蓄投资决策分离的情况下,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假设都是不能成立的。古典经济学假设储蓄能够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相同收益的投资领域,储蓄投资能够在利率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均衡。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者则假定投资能够自行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储蓄,储蓄投资主要是通过收入调节而不是利率调节趋于均衡。然而,他们的假设并不符合实际。
我们知道,现实的资本积累过程由于货币金融因素引入变成储蓄过程、金融过程和投资过程三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并不一定转移到高收益率的投资领域,还可能被投资于金融领域形成金融资本的积累,这种积累并没有现实资本积累的发生,高利率带来的可能是强化金融投资和金融投机,并不一定带来高投资、高效率和高增长。撇开高利率可能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说,高利率本身会造成对投资的抑制,缩小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空间和通道,这在普遍缺乏投资能力的发展中经济会造成严重后果。
凯恩斯及其支持者看到了储蓄过程和投资过程分离条件下,投资具有调动闲置资源的机制性作用,并通过收入效应影响储蓄的形成。不可否认,从动态过程看,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投资活动能够把闲置、半闲置的资源或生产能力调动起来,从而扩大生产能力,这又会对储蓄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应当看到,投资归根到底要受储蓄的制约,投资调动资源的能力也不能不受到储蓄规模及其物质形式的限制。长期把利率抑制在低水平上,必然影响借贷资本积累并通过借贷资本积累影响现实资本积累,过度的抑制必然会影响金融体系在货币资本聚集和分配中的功能。同时,生产能力的形成有一个时滞过程,通过利率抑制刺激投资,从短期看,改变的主要是增加需求,而不是生产能力,从投资到形成生产能力有一个较长的时滞过程,特别是像能源、电力等基础产业部门的投资更是如此。由于时滞过程的存在和产业“瓶颈”的限制,利率抑制引起的投资需求的增加,将直接引起价格的上涨而不是生产能力的增加,且时滞过程越长,“瓶颈”越细,价格上涨就越严重。这种情况下,利率抑制不仅不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储蓄,而且也不可能通过收入机制平衡储蓄投资。
利率自由化理论强调利率对动员、分配储蓄的机制作用,但由于不理解资本商品的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错误地认为高利率就能带来高储蓄从而带来高投资、高增长。实际上,高利率固然能够促进在借贷资本形态上的积累增加,但这种积累的增加并不一定代表储蓄增加,因为这种积累的增加可能是储蓄者因利率提高而对金融资产持有结构改变的结果。即便借贷资本的积累代表着储蓄增加,也并不意味着增加的储蓄能够导入有效投资领域。由于高利率提高了一般利润中利息支付的比重,造成职能资本实际收益的减少,从而造成潜在储蓄和潜在投资渠道沟通的困难,高到一定程度,甚至减少生产资本的投资以增加更多的金融投资,造成生产资本的金融化和对产业资本发展的阻碍。根据前面的分析,利率虽然是一个不合理的价格形式,但它同其他价格形式一样影响收入分配,在利润率一定的条件下,利率提高意味着借贷资本家获得了更高的收入,而职能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相对减少,这对生产和生产资本的积累都是不利的(马克思曾分析了借贷资本同时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的情况),特别是当利润份额降低到一定限度,这无疑会导致更多资本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促进生产资本的金融化,强化金融领域的资本积累。金融化的快速发展,家庭部门成为重要的借贷货币资本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一些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房地产等需要依赖金融支持才能购买,这种情况下,过度积累的借贷货币资本易于流向房地产等领域,导致这些领域的资产泡沫化,甚至引发危机。利率自由化理论过度强调利率对储蓄的作用,而忽略了对积累过程另一端投资的影响,把投资看作是被动性因素,假定增加的储蓄能自然而然地转移到有效的投资领域,在储蓄与投资决策分离的条件下,这种假定是不现实的。利率越高,投资的渠道就越窄,特别是借贷资本的高利贷化,形成对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压榨,不断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因此,从生产和生产者的角度看,借贷资本的高利贷化是极其有害的。
可见,无论是利率抑制理论和政策,还是利率自由化理论和政策,都缺乏科学的根据。从借贷资本利率“价格观”看,利率是通过借贷资本联结储蓄和投资的,借贷资本的积累并不必然等于现实资本的积累,借贷资本的增加或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现实资本的增加或减少,因而并不意味着储蓄投资的增加或减少。既要看到借贷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之间的区别,不能把借贷货币资本形式的资本积累直接等同于现实积累,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看到一定条件下借贷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的一致性。正确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利率政策正确选择的前提。合理的利率政策就是使二者趋于一致,借由借贷货币资本积累促进现实资本的积累。
在存在货币金融的条件下,借助于借贷货币资本进行的资本积累,包含着实物资产的所有权的积累和对实物资产虚拟要求权的积累,后者是通过货币资本或金融资产形式的积累来体现的。那种基于储蓄者从投资者那里购买实物资产的金融所有权,投资者运用所筹集的资金进行现实积累即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假定,而把生产性投资和金融投资相等同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由于金融化快速发展,生产性投资与金融资产积累之间、借贷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它们之间可以发生很大程度的背离。利率政策应根据以借贷货币资本形式进行的资本积累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现实积累的判断来确定,应摒弃那种损害现实积累的利率政策,高利贷化的利率政策就是这样,利率改革应防止高利贷化。
借贷货币资本可能是由货币转化而来的,也可能是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而来的。而货币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是一件比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更简单得多的事情。只有后者才能包含真正的、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相联系的借贷资本的积累。从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的情况看,可能发生和生产积累成反比而同生产积累有联系的借贷资本过多的情况。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其增加甚至是产业资本收缩和萎缩造成的结果。这意味着借贷资本的增加或减少,与产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的增加或减少并不是一回事,利息率由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而不是其他供求关系来决定,它的提高可以直接带来的是借贷资本积累的增加,而不是现实积累的增加,在金融化的条件下,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不仅不能带来产业资本的增加,而且会由于生产资本的金融化导致产业资本的积累的减少。[11]
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显然要比现实资本的积累容易得多。提供借贷资本的资本家进行的积累总是直接以货币形式进行的积累,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通常要由再生产中的资本本身的各种要素的增加来实现。仅仅由于信用事业的发展和货币借贷业务在大银行手中的异常集中,就必然会使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作为一个和现实积累不同的形式能够加速进行。社会上一切收入在一定时间内采取货币收入的形式,因此可以变为存款,并由此变为借贷资本的来源。各种收入,无论是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只要它存在于某种货币形式中,只要它变为存款,它就可以变为借贷资本的要素,但不是生产资本本身。构成借贷资本的要素与构成生产资本的要素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借贷资本转化为再生产中资本的各种要素,才能转化为生产资本。由于借贷资本和生产资本积累的构成要素不同,影响借贷资本积累的因素并不一定影响生产资本积累,促进借贷资本积累的措施如高利率,并不一定促进现实资本积累,甚至可能成为阻碍现实积累的障碍,如利率高到一定程度会使得转化为再生产中资本的要素可能无利可图,从而影响现实资本积累。
显然,借贷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不能把二者相等同,也不能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利率直接影响的是借贷资本积累,而不是现实资本积累。现实资本积累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利率政策的着眼点应放在现实资本积累增加和配置效率的提高上,如果没有现实资本积累的增加,仅有借贷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无疑是毫无意义的。作为一种不合理的价格形式,利率并不能自动确定在现实资本积累所需的最优水平上,应通过有效调节把利率控制在适当水平上,以通过借贷资本的积累促进现实生产资本的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1]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 Rogers, C.Money, Interest and Capital: A Study in the Foundations of Monetary Theor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3] Leijonhufvud,A.“The Wicksell Connection: Variations on a Theme”,In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Essays in Macroeconomic Theor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4]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凯恩斯.货币论(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 斯蒂格利茨等.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7] 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A].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8] McKinnon R. Money and Development[M]. Brooking Institute,Washington,1973.
[9] McKinnon R.Financial Liberlization and Development:a Reassessment of Interest-Rate Policies in Asia and Litina America[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989,Vol.5, No 4.
[10] 爱德华·S·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11] 陈享光.金融化与现代金融资本的积累[J].当代经济研究,2016,(1).
[责任编辑陈翔云]
ATheoreticalReflectiononInterestRateRestraintandInterestRateLiberalization——Also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ccumulationofMonetaryCapitalandtheAccumulationofRealCapital
Chen Xiangguang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rice view of capital interest rate; price view of currency interest rate; loan capital; liberalization of interest rate
The price view of capital interest rate and the price view of currency interest rate are two kinds of “price views” of interest rates, which are popular in Western economics. Other price views of interest rate are merely the synthesis of these two price views. Both the price view of capital interest rate and the price view of currency interest rate lack the ability of realistic explanation. Marxist economics regards interest rates as the price associated with capital goods and loan capital. But it is an irrational price form. This kind “price view” of interest rate can be called “the price view of loan capital interest rate”. Different “price view” of interest rate brings out different policy opinions. Only when we correctly grasp the interest rate of the capital commodity price an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est rate, the accumulation of monetary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reality, can we make the correct choice for our interest rate policy and interest rate reform.
陈享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