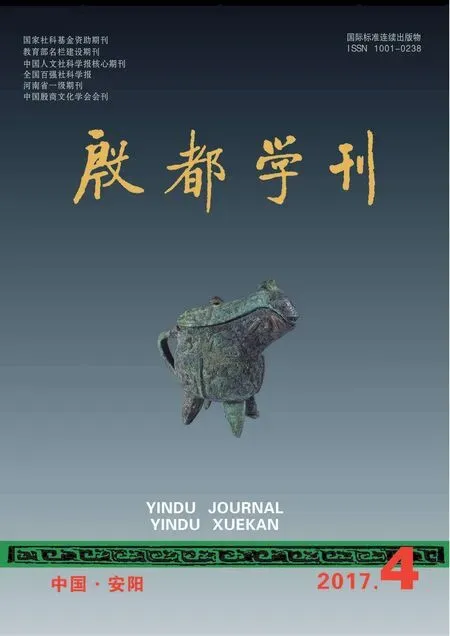“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困境与理论缺陷解析
——“审美意识形态”论合法性问题讨论之三
杨晓新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濮阳 457000)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困境与理论缺陷解析
——“审美意识形态”论合法性问题讨论之三
杨晓新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濮阳 457000)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困境表现为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左右为难,从逻辑上说就是属概念的左右为难,从理论建构上说是理论基础的二元化。这来自论者对本质与性质(属性、特性)、“审美”和“意识形态”模糊不清的认识,同时,“审美意识形态”论又依靠这种模糊不清的认识勉强维持了一种模模糊糊(既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的、仿佛的合法性。
审美意识形态论;理论困境;理论缺陷;理论基础二元化;概念放逐
无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看,还是从“意识形态”一词的当代含义看,将文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都是没有问题的[1],但“审美意识形态”论却存在种种语言和逻辑问题,难以成立[2]。本文进一步对“审美意识形态”论遭遇的理论困境以及相应的理论缺陷进行一些阐释和分析,以进一步弄清“审美意识形态”论究竟能否成立。
一、“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困境
说来简直有些难以置信,单纯从语言层面看,“审美意识形态”论似乎只是差之“毫厘”:如果把“审美意识形态”解释为通常的偏正结构,即“审美”修饰“意识形态”,“审美”表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一种属性或特征(具有审美属性或特征的意识形态),这就没有任何问题①谭好哲先生就是在此意义上肯定“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谭好哲《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网站:http://wenyixue.bnu.edu.cn/html/jiaoshouwenji/tanhaozhe/2006/1121/598.html。,可“审美意识形态”论者却执意“另辟蹊径”:一方面将“审美意识形态”解释为“审美”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又强调它是“审美”与“意识形态”无分高下、谁也不从属于谁的对等融合,这就把自己逼入了逻辑困境。因此,单纯从逻辑上看,“审美意识形态”论者的这种“理论”选择实在令人费解。
反复研读“审美意识形态”论者的有关论述,笔者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困境可能来自对本质与性质(属性、特性)、“审美”与“意识形态”这些概念模糊不清的认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要提出者多次论及如下意思:“审美意识形态论最重要的改变是引入‘审美’这一概念,从而把文学看成是美的价值系统。在80年代初、中期的美学热潮中,它力图摆脱了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单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缚,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地平线上揭示文学自身的特征。”[3](P33)“‘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时代学人根据时代要求提出的集体理论创新②童庆炳先生还进一步论证说,布罗夫虽然讲到审美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他没有完全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并加以论证。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一书出版于1990年,且是一本对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启蒙主义美学著作的评述,与我们所提出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没有多大关系。因此,‘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是当代中国学者的一次理论创新”(童庆炳《怎样理解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载《中国大学教学》2004年第1期)。笔者却觉得,幸亏布罗夫和伊格尔顿没有这样的“理论创新”。。它是对于‘文革’的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和批判。它超越了长期统治文论界的给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带来公式主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它的立场仍然在马克思主义上面”[4](P59)。这位学者甚至反复声称,“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5](P105)[6](P32)。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究竟什么是“审美”,什么是“意识形态”,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有关阐释文本看,“审美意识形态”论者的认识却并不清楚。论者可能以为,要摆脱“文学政治工具”论,就不能径直说文学是意识形态。这恐怕是一种误解。将文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见得就是“文学政治工具”论。问题的症结在于,性质与本质是两个概念、两回事,本质是事物自身的根本性质和最高性质,性质则是事物本质派生的某一方面的特性或功能。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是对文学的一种性质(社会属性、社会本质)的判断,而不是对文学本质的判断,或者说,在这个关于文学性质(社会属性、社会本质)的判断之外,还同时存在关于文学本质的判断*笔者另一篇文章《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文论的定位问题——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合法性问题讨论之四》对此问题有详细讨论,参见《殷都学刊》2012年第4期。,二者并不互相排斥和互相矛盾,亦即承认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排斥对文学自身本性(如人们所谓的“审美”或别的什么本性)的认识。但国内(包括“审美意识形态”论者)普遍把“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视为对文学本质的判断,在此情况下,“审美意识形态”论者自然不肯径直说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单就这一点而言,“审美意识形态”论者是对的。而如果将“审美意识形态”解释为普通的偏正结构,那无论“意识形态”前面加什么定语、加多少定语,都不能改变文学根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样的理论判断。因此,“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要提出者明确提醒人们,不能将“审美意识形态”理解为“审美的意识形态”[4](P60)。
但另一方面,或者出于其固有的理论信念,或者同时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为规避某种政治风险甚或获得政治支持而对“政治正确”的追求?*童庆炳先生在2002年的一次“文艺学教学改革及教材建设研讨会”(武汉)上曾传授过他编写教材的秘诀:“教材编写要考虑六个‘面对’”,其中之一是要“面对领导”,“让领导放心”,称这“是中国特色”。参见童庆炳、王先霈《面向未来的思考——文艺学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二人谈》,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审美意识形态”论者要保证其理论“立场仍然在马克思主义上面”,这在他们看来就是不能抛开“意识形态”,不能干脆径直地说文学就是“审美”。其实,说文学是审美不见得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问题的论述只是他对文学的社会本质的论述,马克思完全可以、事实上也确实发表了大量关于文学自身本质的论述。更何况,“审美”绝不可能是一种没有社会内容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相反,“审美”常常烙印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印记。也就是说,讲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不妨碍同时也讲文学是“审美”(且不论此观点本身的是非)。
这样,“审美意识形态”论者既不能直接说文学是“审美”(这在他们看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直接说文学是意识形态(这在他们看来仍是要竭力摆脱的“文艺为政治服务”那一套),又不愿抛开“审美”和“意识形态”,则唯一的选择就是、也只能往“中间”走:将“审美意识形态”解释为“审美”这种“意识形态”,这至少在字面上既不“得罪” “审美”,也不“得罪” “意识形态”——“审美”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诚可谓用心良苦。但“审美意识形态”论者却忽视了理论内部的逻辑自洽:在本质的意义上,文学怎么能既是“审美”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呢?借用董学文教授的说法,某种东西是“苹果”,“苹果”当然也是一种“水果”,但在本质的意义上,怎么能说这种东西既是“苹果”又是“水果”呢?而说一种东西是“苹果”与“水果”的“混合”,则更让人莫名其妙!即使退一步,即使不谈论文学本质,这两种判断要能同时成立,那它们一定发生在不同的逻辑层次上,但“审美意识形态”论者却执意要把发生在不同逻辑层次上的判断融合为一个东西,结果是生造出一个让人无所适从、也给他们自己带来无边麻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个“第一原理”!多年来,“审美意识形态”论已覆盖大陆高校文论讲坛,“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要提出者作为“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一“理论创新”的代表人物,却不得不三番五次出来摆讲堂,向同行宣讲“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秘意”,这一方面固然见得其“理论”之“地位”,但另一方面,那么多教本(“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要提出者自己主编的就大约有10个版本)那么长时间的宣讲,竟然还有那么多同行“不开窍”,这种不够理想的效率恐怕很难排除其理论自身的“无能”成分“自我作对”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如有论者指出的,他们的具体解说又常常游移不定:“有的阐发给人以审美+意识形态的印象,主次不分;有的阐发过于突出了‘审美’二字中的‘美’字,以至于遮蔽了文艺的其他社会属性和功能;有的阐发对审美的解析过于泛化,导致以审美代替了一切,如此等等”[6](P107)。“主次不分”或许是他们的本意,起码是其主要提出者的本意,而两种“偏致”倒可能是具体阐述中不小心“走了火”,结果是既得罪了“审美”,又得罪了“意识形态”,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理论困境。
从理论层面而不是从逻辑层面看,“审美意识形态”论所陷入的理论困境的实质是:“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一种关于文学的理论建构,陷入了理论基础的二元化的困境,也就是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即逻辑上所谓定义的属概念),它实际上自设了“审美”论和“意识形态”论两个理论基础,从而陷入了二元论的自我分裂的困境——二元论是不可能自圆其说的。但一种理论在实际的展开过程中,会本能地追求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即一元化(如笛卡尔最终搬出“上帝”来调和“物质”与“精神”一样)。“审美意识形态”论由于在不经意之间为自己设置了两个理论基础,这必然使这一理论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面临重重障碍。许多论者都发现,“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阐述过程不顺畅、缺乏学理上的自洽。理论基础的二元化必然使其理论阐述左右为难、左支右拙,论者自然要努力把道理讲通,于是,“左右为难”就成了“左右游移”。“审美意识形态”论主要提出者的“整一”说是企图把“审美”和“意识形态”融合为一个东西,但他自己和其他一些论者又常常不由自主地或者偏向“审美”,或者偏向“意识形态”,这些大概都是论者无意识地受到逻辑规则的支配力求理论基础的一元化、力求理论体系自洽的结果。但实际上,其自设的两个理论基础“审美”论与“艺术形态”论却根本不可能融为一体,二者是从两种不同角度观察文艺的结果。这就好比盖楼房,要把第一层与第二层建成一个统一的平面,或者好比一个人穿了两层衣服,却要把第一层衣服的扣子与第二层衣服的扣子扣在一起,这简直是神的工作。
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缺陷之一:暧昧不明的“审美”
但“审美意识形态”论并未罢手,它还要在困境中“前行”。一个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号称“文艺学第一原理”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却闭口未对“审美”和“意识形态”作出解释,说起来真真不可思议。
如上所述,“审美意识形态”论理论困境的根源在于对“审美”和“意识形态”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这两个概念可是“审美意识形态”论名副其实的核心概念。然而,笔者注意到,这种模糊不清却反过来“成全”了它:试想,要把两个不同意义的判断融为一体,唯一的办法就是模糊这两个判断的含义,从而模糊二者的关系。笔者最初发现“审美意识形态”论竟然没有对“审美”和“意识形态”作出解说时觉得实在让人惊诧莫名:既然叫“审美意识形态”论,理所当然要把“审美”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支柱性概念讲清楚的。但反过来看看就很容易明白了:假如“审美意识形态”论把“审美”和“意识形态”给讲清楚了,那“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这套“理论” 就根本讲不下去了,换句话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摆脱其理论困境的办法就是对“审美”和“意识形态”两个关键概念的放逐——干脆不去解释。这样看来,“审美”和“意识形态”两个关键概念的放逐既是“审美意识形态”论陷入理论困境的原因,也是其企图摆脱理论困境的策略——也许不那么自觉,如此,其理论言说方维持住了一种模模糊糊(既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的、仿佛的合法性,这也证实这一理论的难缠之处。
先说“审美”。在汉语中,“审美”是与“美”纠缠在一起的,而“美”在美学中本来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要说清“审美”当然不容易。这与翻译也有关,也许还与现代汉语的有关语用习惯有关。汉语“审美”对应的英语单词为aesthetic,其本义为感性的,是一个形容词,但汉语“审美”却是一个动词,指人们以特定方式对“美”的事物的一种“对待”(观照),而“美”则是一种肯定性的感性体验与其所涉及的对象的统一。显然,“美”是“审美”的结果。如此,则不应再以“审美”去翻译aesthetic,而应恢复其本来意义——感性,相应的,aesthetics应译为“感性学”*此处参考了高迎刚《艺术、美及审美之间的关系辨析》,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但实际情况是,在大陆文论界和美学界,“审美”一语经常代替“美”的位置被使用。比如,人们常说“文艺具有审美属性”,这当然可以解释为“文艺”是文艺家“审美”这一活动的结果,因此可以称“文艺具有审美属性”。但就这个结果本身来讲,准确的表述应该称文艺具有“美”的属性而不是“审美”属性。大陆学者还常常说某物具有“审美”价值,这可以解释为这个东西可以作为“审美”对象并具有使人产生美感的属性,但就这件东西本身来说,同样应该说是具有“美”的价值而不是“审美”价值。这其中或许有一个深层的无意识原因,即所谓的“美”并非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人以特定态度“对待”的结果,这“对待”即“审美”,也就是说,“美”有赖于“审美”,故在应该使用“美”的地方不由自主地常常以“审美”替代之。除此以外,也可能是现代汉语双音节的构词习惯使得“美”单独作为一个词语使用在音节上不太方便,使得人们在该使用“美”的地方或时候转而以“审美”取而代之。但毕竟“美”与“审美”是两回事:“审美”是一个行为、过程、态度和对待事物的方式,而“美”则是“审美”的结果。
尽管存在上述普遍问题和困难,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建构,人们还是有理由要求“审美意识形态”论对“美”和“审美”作出合理的、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遗憾的是,实际上论者未对“美”或“审美”作任何有效解释。比如,在“审美意识形态”论主要提出者主编的一本《文学概论》教材中,第一编“本质论”之下的第二个大标题“文学的审美特质”之下有“(一)文学的审美性质”和“(二)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两个标题,在“(一)文学的审美性质”之下有三个标题:“1、文学的特殊对象”“2、文学的特殊方式”“3、文学的审美特质”[7](P51)。而所谓“文学的特殊对象”就是“具体的、感性的人”;“文学的特殊方式”就是“现实的感性形式”。人们可以问:为什么以“具体的、感性的人”为对象就是“文学的审美性质”的表现呢?为什么“现实的感性形式”就是“文学的审美性质”的表现呢?而“文学的审美特质”却被具体解释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均“具有美的性质”,这是典型的同义反复:这“美的性质”从何而来?什么是“美的性质”?教材都没有告诉读者。在“(二)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之下讲了三点:“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虚拟性”。为什么这些就是文学的“审美特征”呢?在这一点上,这本教材显然缺乏自明性。
这本教材有时还以“审美”解释“审美”:在讲文学的审美性质时说,与“科学运用概念、判断、推理、分析和综合,以理论的形式掌握世界”不同,“艺术则通过形象、意境和情感,以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7](P53)其中就用“审美感情”解释审美性质,又用“审美态度”解释“审美感情”[7](P64),而“形象、意境和情感”为什么就是“审美”,同样不得而知。后来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仍然如此:讲“生活活动的美学意义”,竟然矢口不解释何谓“美学意义”,却用另一个同样未加任何解释的“诗意情感关系”去解释“美学意义”[8](P31)。在“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一章中讲“文学的审美含义”时,仍然未对“审美”做任何解释,直接去分析作品,然后总结道:品味这篇作品,“完全可以在三幅想象的人生场景中驰骋情怀、流连忘返,领悟到人生体验的丰富画卷与深长意味。由此而言,文学难道不是人生体验的审美表达吗?”并由此得出结论:“文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审美形态。文学是指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行为及其作品,包括诗、散文、小说、剧本等。这正是文学的审美含义。”[8](P51-52)读者不能不问:那样的一种阅读体验何以就是“审美”的呢?文学为什么因此就是一种“审美形态”(这个“审美形态”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什么叫“审美形态”)?“文学的审美含义”究竟是什么?完全让人不知所云。
而到了讲“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表现”这样的核心问题(对这本教材的体系而言)时,同样未对“审美”做任何解释就讲了三条:“无功利与功利”“形象与理性”“情感与认识”[8](57-68),人们完全可以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就是“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表现”呢?这本享有广泛声誉的教材甚至还说:“当艺术真实的创造及其蕴含的情感评价成为‘真’与‘善’的统一时,这统一便构成文学创造追求的审美价值”[8](174),为什么“真”加“善”就等于“美”呢?
此外,明明是讲文学与一般意识形态的区别,举的例子却是自然科学[8](P51-52),那么,“以具体、感性的人为对象来反映现实、反映社会”究竟是文学与一般意识形态的区别还是与自然科学的区别?难道自然科学也是“一般意识形态”吗?这就涉及如何理解“意识形态”的问题。
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缺陷之二:语焉不详的“意识形态”
笔者虽然认为,将文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并未误用“意识形态”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意识形态”论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解释就是正确的。如许多论者已经指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们实在根本未作出明确解说。
在1998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概论》(童庆炳主编)第一编“本质论”中,第一个标题是“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其中未对“意识形态”作任何解释。在此标题下并列讲了“文学的意识性”“文学的社会性”“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关系”(此句不通)三个问题,只在最后一点中直接述及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7](P17-21)。有理由认为,这段论述是把意识形态等同于意识或社会意识(这是国内文论界不少论者的通病)。只是在这本教材的学习辅导材料中才对“意识形态”作了如下解释: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而“文学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即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化,就这一点而言,它如同政治、哲学、科学、宗教、道德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9](P11)。然而这个解释却大成问题:它表达出来的意思是,“意识形态”就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的简称,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就是意识的形态。这十足是一个望文生义的解释,这样的“意识形态”显然也太宽泛了:“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都是意识形态吗?若是,则连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言谈都是意识形态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恐怕与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尤其是,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同义反复,等于没有解释。到了《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童庆炳主编)中,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仍是直接称述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有关论述,仍未对“意识形态”作任何解释。若此处尚可原谅的话,那么在专论“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一章,竟仍然矢口不对“意识形态”作正面和规范的解释,只是在引述过经典著作的一段论述之后,交代(只能叫“交代”)了意识形态的外延(如哲学、宗教、艺术)及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意识形态”本身的定性(内涵)解释仍不见踪影,然后就讲“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表现”:“无功利与功利”“形象与理性”“情感与认识”[8](P57-68)。既未对“美”和“审美”作任何解释,也未对“意识形态”作有效解释,自然使人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三条就是“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表现”呢?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要提出者曾在一次“文艺学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会议上介绍其文艺学教材编写经验,讲到“教材编写要考虑六个‘面对’”,第一条就是“要面对学生。过去我们的有些教材太简单,学生一读就懂,自己读懂了,就不想听老师讲了,不爱上课。我的经验是教材不能太简单太容易,要给学生留下学习的空间,留下思考的空间。我们编写的《文学理论教程》时候,有的地方就故意不下明确的定义,而用描述的语言,使学生读下来基本能懂,但又不能完全弄懂,关键问题要由老师去讲,最后的定义由老师和学生自己去下。就是说,在老师的帮助下,通过思考,才能完全弄清楚”[10](P37)。但遍翻上述两本教材,并未见到任何针对“审美”和“意识形态”的“描述的语言”,难道对“审美”和“意识形态”不作任何解释也是这位论者所说的应当给学生留下的“学习的空间”和“思考的空间”吗?我不相信这样的教材学生“基本能懂”,我的经验是,学生不但“不能完全弄懂”,而是“完全不能弄懂”。不用说学生,就是教师,教材若无一个基本解释,历史上和学术界有那么纷纭的关于“审美”和“意识形态”的解说,而教材却不提供一个基本看法,即使教师也无所适从。
如此重大的缺陷,若是存在于那些为糊弄饭碗而胡乱凑数的教材,或者尚可理解,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文学理论教材,它顶着多项闪亮的桂冠:《文学理论教程》是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百门精品”课程教材。一篇称颂“审美意识形态”论主要提出者“探险者的风范”的文章这样说:“从应用范围看,这些教材涉及本科生、研究生、自考生、函授生和电大生等多种类型,可以说,涵盖了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文学理论教材的几乎方方面面。难怪人们会称童庆炳为‘文学概论教材专家’。”[11](P8)出自如此“专家”之手的如此“规格”的教材却存在如此“量级”的缺陷,笔者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评论① 这些年对童本教材的批评已经很不少了,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如此国家级精品——评〈文学理论教程〉》,载《学术界》2008年第1期。 。其他论者还谈到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在对“意识形态”的解释中存在的其他种种问题,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放逐两个关键概念既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阐释者提供了某种阐释的“自由”,又使(必然!)“审美意识形态”论整个理论阐述难以自明和自洽,虽经多次“开课”解惑,却仍使人恍兮惚兮,甚至是越讲越糊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自我放逐。这想必并非这一“理论创新”所追求的效果吧。
[1]杨晓新.“意识形态”概念再讨论——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合法性问题探讨之一[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3).
[2]杨晓新.漂浮的能指:“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语言与逻辑分析——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合法性问题探讨之二[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6).
[3]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再认识[J].文艺研究,2000,(2).
[4]童庆炳.怎样理解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教程》编著手札[J].中国大学教学,2004,(1).
[5]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J].学术研究,2000,(1).
[6]谭好哲.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EB/OL].(2006-11-06)[2011-03-12].http://wenyixue.bnu.edu.cn/html/jiaoshouwenji/tanhaozhe/2006/1121/598.html.
[7]童庆炳.文学概论(修订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8]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童庆炳.文学概论自学考试指导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10]童庆炳,王先霈.面向未来的思考——文艺学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二人谈[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
[11]王一川.探险者的风范——略说童庆炳的教材工作[J].文艺争鸣,1998,(1).
2017-09-01
杨晓新(1963-),男,河南嵩县人,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美学及文化研究。
I206
A
1001-0238(2017)04-0087-06
[责任编辑:邦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