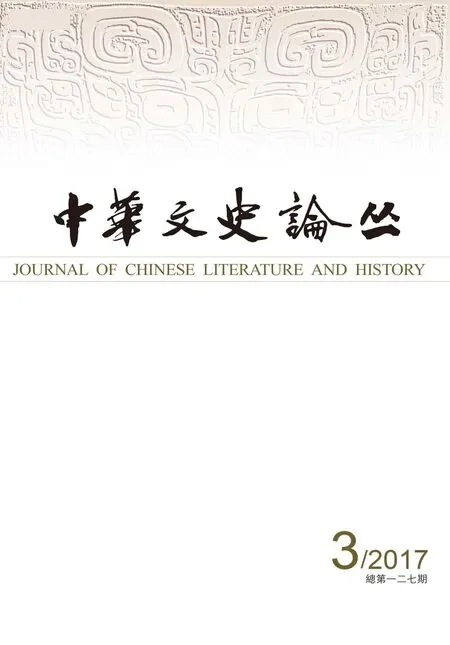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的背景及其政治和文化意涵
朱義群
提要: 王安石在宋英宗朝一直閑居江寧,不肯回朝復職,因爲他和當政的首相韓琦有很深的矛盾。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後,北宋朝廷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神宗很早就對王安石具有深刻的印象,希望將他召回委以重任;另一方面,神宗對長期專政的韓琦産生不滿,希望收回下放已久的權柄。次相曾公亮爲了排擠韓琦,力主再次召用王安石,並與參知政事吴奎産生齟齬,這些矛盾最終在治平四年閏三月的一場御前辯論上集中爆發。嗣後,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這是具有濃厚的政治象徵和文化隱喻意味的任命,在政治上象徵神宗、王安石“君臣合作”的開端,在文化上隱喻王安石“以道進退”與“觀時而動”相結合這一出處哲學的成功實踐。
關鍵詞:宋神宗 王安石 知江寧府 政治象徵 文化隱喻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八月,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因丁母憂而解官居喪江寧,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七月除喪後,朝廷屢次下詔召他回京恢復原職,他都没有應詔,依然閑居江寧。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朝廷又一次召王安石赴闕,但他仍没有應命。直到當年閏三月,神宗起用其知江寧府,王安石方接受任命;同年九月,神宗召王安石回朝擔任翰林學士,王於次年四月赴闕。熙寧二年(1069)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以變法革新,“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陳亮集》(增訂本)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8。宋代歷史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知江寧府是王安石政治生命的新起點,但他在英宗朝“屢召不起”而在神宗朝接受新命的做法,在歷史上曾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而現代學者似對此話題没有予以太多的關注。本文在挖掘現有史料的基礎上,探究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的背景,並闡發事件背後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涵,以豐富我們對王安石變法相關背景的認識。
一 王安石“屢召不起”的緣由及相關爭議
王安石於治平二年七月除喪後没有應命赴闕,《臨川先生文集》卷四收録的兩封《辭赴闕狀》,顯示他不能赴闕的理由是“抱病日久,未任跋涉”、“抱疢不任職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四《辭赴闕狀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435。但這僅僅是他的一面之詞。在當時,關於王安石在英宗朝“屢召不起”的緣由,還有兩種比較通行的説法。一種説法是,仁宗嘉祐年間,王安石在立英宗爲皇子問題上有“異議”,故疑懼不敢入朝。此説源於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三:“時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又據同書卷九:
熙寧二年,韓魏公自永興軍移判北京,過闕上殿。王荆公方用事,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荆公終英宗之世,屢召不至,實自慊也。*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4,95。
韓琦親口承認“安石有異議”這件事,應是邵伯温相關説法的依據。然而,這一記載的真實性相當可疑。首先,韓琦於治平四年十一月判永興軍,*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下簡稱《長編紀事本末》)卷八三《种諤城綏州》治平四年十一月丙戌條,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3年,頁2704。至熙寧元年十二月即移判北京大名府,*《長編紀事本末》卷六三《王安石毁去正臣》熙寧元年十二月乙丑條,頁2056。他“過闕上殿”發生在熙寧元年,並不是王安石“用事”的“熙寧二年”。其次,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簡稱《長編》)卷二四治平二年二月辛丑條記載,在仁宗晚年立英宗爲皇子時,當時傳言“近臣中亦有異議”,英宗親政後追究此事,發現傳言中的那個“異議”之人竟是三司使蔡襄。宰相韓琦等人極力救解,請英宗不要相信那些傳言謗語,而英宗不以爲然,並反問“造謗者因何不及他人”,堅持將蔡襄罷免補外。*李燾《長編》卷二四治平二年二月辛丑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4946—4947。以上兩點分别從正面、側面證明,《邵氏聞見録》所謂“安石有異議”、“不敢入朝”的説法不足憑信。
司馬光《涑水記聞》記載了另外一種説法,即王安石因怨恨當國執政的宰相韓琦而不肯入朝: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簽書判官事,韓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乎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之,以韓公爲輕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爲韓公所沮。會遭母喪,服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六,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311。
以上所記乃是慶曆二年(1042)王安石進士及第之後出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時與時任長官韓琦發生的一段因緣。《邵氏聞見録》卷九亦記載,王安石任揚州簽判時“每讀書達旦”而被韓琦懷疑“夜飲放逸”,王安石於是認爲“韓公非知我者”,*《邵氏聞見録》卷九,頁94。兩人開始有了隔閡。魏泰《東軒筆録》亦認爲:“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時王荆公初及第,爲校書郎、簽書判官廳事,議論多與魏公不合。”可見王安石與韓琦之間的嫌隙由來已久,所以《涑水記聞》説:“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爲韓公所沮。”此事同樣可與《東軒筆録》相互印證:“洎嘉祐末,魏公爲相,荆公知制誥,因論蕭注降官詞頭,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又爲糾察刑獄,駁開封府斷爭鵪鶉公事,而魏公以開封爲直,自是往還文字甚多。”*魏泰《東軒筆録》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64—65。可見王安石爲知制誥時與宰相韓琦之間的嫌隙已經很深了。以上種種説法,是王安石可能因怨恨韓琦而不肯入朝的證據。
綜上而言,關於王安石在英宗朝“累召不起”的緣由,除了王安石所謂“抱病日久”之説外,還有兩種常見的説法: 一種認爲王安石在立英宗爲皇子問題上與韓琦有異議而不敢入朝,但這種説法是不足憑信的;另一種則認爲王安石因怨恨韓琦而不肯入朝,這一説法似乎得到諸多證據的支持。
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召不起,或爲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吴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意以爲韓琦沮抑己,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輔相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臨事迂闊,且護前非,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公亮熒惑聖聽,非臣熒惑聖聽也。”上未審,奎重言之。癸卯,詔王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長編》卷二九治平四年閏三月癸卯條,頁5086—5087。
辯論中的曾公亮是集賢相(次相),吴奎是新任的參知政事(副相),而當時的首相韓琦可能因忙於英宗山陵事務而没有上朝。以上記載顯示,王安石在英宗朝屢次拒絶赴闕,神宗即位後繼續召用,王安石“又不起”,這可以與《臨川先生文集·辭赴闕狀三》相互印證:“臣……當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解職。……緣臣自春以來,抱疢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即所苦滋劇。所以昧冒奏陳,乞且分司。”*《臨川先生文集》卷四,頁435。按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逝世,同年八月王安石母吴氏去世,王安石因母喪解職之時,恰好在繼位的英宗“亮陰”(居喪)之期。他稱英宗爲“大行皇帝”,則此狀奏進日期當如清人沈欽韓所説“在神宗即位之初”,*沈欽韓《王荆公詩文沈氏注》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33。而非蔡上翔所繫的治平二年七月。*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一二,收入《王安石年譜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397。此狀證實了神宗即位之初“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的事實。引文還顯示,王安石的稱疾不起,引起了神宗不滿,懷疑他是否真的有疾抑或故意“要君”。曾公亮保證王“必以疾病,不敢欺罔”,而吴奎卻聲稱王不赴闕乃因“以爲韓琦沮抑己,故不肯入朝”,言外之意是王安石不是“欺罔”就是“要君”。前已提及,種種證據表明王安石可能因怨恨韓琦而不肯入朝,而吴奎的言論則證實了這一説法的部分真實性。
雖然王安石自稱“抱病日久”,但“稱疾”並不足以成爲不能赴闕的理由。在宋代,官員爲了推托朝廷某項任使,往往以疾病爲名,這幾乎是心照不宣的事。曾公亮擔保王安石“必以疾病”,並不意味他真的相信此事,他僅僅是爲了强調王“不敢欺罔”罷了。他希望神宗召王安石回朝予以重用,作爲將來“輔相”的後備人選。因爲王安石與韓琦有矛盾,所以曾公亮的這一立場就被認爲出於“欲以傾韓琦”的目的了。
觀察曾、吴之辯,我們發現,曾公亮力主召王安石回朝,而吴奎强烈反對之,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熒惑聖聽”,處於嚴重對立的狀態。至於辯論的結果,《長編》記載爲:“癸卯,詔王安石知江寧府。”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則表述爲:“上納奎言,於是安石不再召,癸卯,安石知江寧府。”*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卷一三《神宗任用王安石》治平二年十月條附,叢書集成續編本,40册,頁331上。而據《宋史·吴奎傳》,在吴奎説完“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一句後接着敍述:“乃命(王安石)知江寧。”*《宋史》卷三一六,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0320。這體現了彭百川和《宋史》史臣對此事共同的理解: 神宗“采納”了吴奎之言,不再堅持召王安石入朝,改命其知江寧府。
綜觀這場辯論,有許多值得注意的現象。例如,韓琦在英宗朝一直擔任首相,當時朝廷亦曾屢次召王安石赴闕,爲什麽神宗即位後,次相曾公亮力主召王卻被認爲含有“欲以傾韓琦”的動機呢?另外,在辯論中,吴奎和曾公亮在王安石的問題上處於尖銳對立的情形也特别引人注目,爲什麽在神宗即位之初,王安石的起用問題突然成了朝堂議論的焦點呢?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地方,神宗當初召王安石回朝,王没有應命,而當他被改知江寧時卻毅然從命,這其中又有什麽隱情、深意呢?
二 神宗即位後的思想動態及其與韓琦的關係
《長編》所載“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之説可能源自司馬光《涑水記聞》:“曾魯公知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介甫於上,强起之,其意欲以排韓公耳。”*《涑水記聞》卷一六,頁311。這一説法雖得自傳聞,但並非空穴來風,因爲曾公亮與韓琦並不是同心同德的政治盟友。自仁宗嘉祐六年(1061)以來至神宗即位伊始,朝廷中基本形成了首相韓琦、次相曾公亮以及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概的治政格局(嘉祐七年三月孫抃罷參知政事後,由樞密副使趙概接任)。*梁天錫《宋宰輔表新編》,臺北,國立編譯館,1996年,頁85—89。其中韓琦和歐陽修都是所謂“范仲淹集團”的核心成員,*漆俠《“范仲淹集團”與慶曆新政》,原載《歷史研究》1992年第2期,此據氏著《探知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26—247。而曾公亮是賈昌朝、張方平提拔的人,*《蘇軾文集》卷一四《張文定公墓誌銘》内曾公亮、張方平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457。賈、張二人與“范仲淹集團”都有矛盾,*《宋史》二八五《賈昌朝傳》,頁9619;章培恒《〈辯姦論〉非邵伯温僞作》附論二《張方平與韓琦、歐陽修、司馬光的關係》,見氏著《獻疑集》,長沙,嶽麓書社,1993年,頁98—105。故曾公亮雖與韓琦、歐陽修長期共事,但並不與他們同心同德。例如,治平三年(1066)英宗有意命張方平爲翰林學士承旨,歐陽修反對,稱其“挾邪不直”,而“曾公亮以爲不聞其挾邪”,“故卒命之”。*《長編》卷二七治平三年正月辛巳條,頁5022。當時韓琦有權有勢,又有歐陽修從旁協助,曾公亮作爲次相,不敢正面與他們抗衡,只能陽奉陰違,虚與委蛇。
然而,曾、韓政爭的背後隱藏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神宗即位後對韓琦專政的不滿,這是理解神宗即位以來諸多事件深層原因的重要線索。自嘉祐初年韓琦擔任宰相以來,關於他“專權”的爭議一直没有中斷。據説,韓琦爲首相時“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次相曾公亮),該典故則曰問東廳(參知政事趙概),該文學則問西廳(參知政事歐陽修),至於大事則自與決之”。*王得臣《麈史》卷上,《全宋筆記》第一編(10),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8—9。英宗朝御史因“濮議”彈劾韓琦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對其“壅塞言路,意在專政”的不滿。*《長編》卷二六治平二年十二月壬寅條,頁5012。後來,反對韓琦的御史紛紛罷免補外,韓琦事權增重,同時也招致了更多的非議。因此《宋史》説:“帝初臨御,頗不悦執政之專。”*《宋史》卷三二九《王陶傳》,頁10611。我們可以從神宗即位後的相關表現對這一論斷有進一步的了解。
首先是治平四年三月發生的歐陽修“帷薄”事件。御史蔣之奇彈劾歐陽修“帷薄”之罪,雖因“所言曖昧”被貶,*《長編》卷二九治平四年三月條,頁5080。歐陽修卻也黯然去職。在此過程中,神宗的態度頗不尋常。墨本《神宗實録》附《孫思恭傳》稱:“修爲言者所攻,上將誅修,手詔密問思恭,思恭極力救修。”*《長編》卷二九治平四年三月條注,頁5080。《宋史·歐陽修傳》亦説:“神宗初即位,欲深譴修,訪故宫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頁10380。這些記載都顯示神宗有意懲罰歐陽修,經孫思恭勸解後纔讓修體面下臺。又據《長編》卷二九,神宗在參知政事吴奎面前誇蔣之奇“敢言”,*《長編》卷二九治平四年三月,頁5080。要褒獎之奇。這説明蔣之奇攻擊歐陽修是契合神宗意旨的,聯繫到歐陽修是韓琦鐵桿政治盟友這一事實,我們不難得出神宗强烈希望削弱韓琦在朝中勢力的結論。
其次是神宗對“濮議”反對派的態度。我們知道,英宗朝的“濮議”事件導致了御史臺與中書的對立。後來御史如呂誨、呂大防、傅堯俞、郭源明等人雖被罷免,但贏得了人心,而力主“濮議”的韓琦、歐陽修則飽受非議。據《長編》卷二九記載,治平四年三月,神宗與參知政事吴奎討論“追尊濮王事”時,深以吴奎所謂“追尊事誠牽私恩”爲然,認爲“此爲歐陽修所誤”。*《長編》卷二九治平四年三月癸酉條,頁5083。當時神宗命權御史中丞王陶舉薦御史人選,王陶“乞復用呂大防、郭源明,執政以爲意欲逼己,不悦”。*《長編》卷二九治平四年閏三月庚子條,頁5086。神宗手詔王陶説:“呂誨、傅堯俞朕固知其方正可使,止爲先朝所逐,未欲遽用,俟其歲月稍久,任之亦未晚也。”*《長編》卷二九治平四年閏三月己丑條,頁5085。以上諸事表明,爲了打擊韓琦在朝中的勢力,神宗有意爲“濮議”翻案,起用因反對“濮議”而被罷免的御史回朝的計畫自然在進行當中。
最後是王陶發動的“宰相不押班”事件。王陶是神宗的潛邸舊臣,在神宗即位後迅速獲得升遷,於治平四年三月權御史中丞。神宗對他委以心腹,稱“朕與卿一心不可轉也”。*范鎮《王尚書陶墓誌銘》,收入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集》卷二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450册,頁392上。而王陶也志得意滿,自謂“本是儲王羽翼客,今爲天子腹心人”。*呂希哲《呂氏雜記》卷下,《全宋筆記》第一編(10),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287。這年閏三月己丑(十一日),王陶以御史臺名義“以狀申中書”,要求宰相赴文德殿押班,*《宋會要輯稿》儀制四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2014年,頁2363下。没有得到回應,便“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特意將矛頭指向韓琦,“斥韓琦驕主之色過於霍光”。*《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七《宰相不押班》治平四年四月辛酉條,頁1831—1832。王陶的激烈彈文後來迫使韓琦“上表待罪”,居家不出,此事亦成爲導致韓琦最終罷相的重要原因。王陶曾自言當初彈劾韓琦的動機是“誠欲尊獎主威,收還君柄,六卿絶分晉之禍,三家無弱魯之强”,*《呂氏雜記》卷下,頁287。表明他揣摩到神宗“不悦執政之專”的心思,因而策畫了這起以韓琦爲目標的“宰相不押班”事件。
神宗欲盡快收回下放已久的權柄,因此與當政的韓琦有矛盾。但韓琦是有“定策”功的元老重臣,神宗不敢率性而爲,收權行動只能迂回進行。治平四年閏三月的辯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在英宗朝,韓琦深受倚重,地位非常穩固,而王安石與英宗幾乎毫無淵源,召王回京復職根本不會對韓的權力基礎産生影響。而到了神宗朝,在“帝初臨御,頗不悦執政之專”以及各路反韓人士將陸續回朝的背景下,作爲次相的曾公亮主動迎合神宗心意,力主召回與韓琦有矛盾的王安石,因而被懷疑具有“傾韓琦”的動機,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 王安石的兩極評價及其遭遇神宗的契機
在神宗即位之初的那場辯論中,曾公亮盛贊王安石“文學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真輔相之才”;而吴奎則痛斥王“臨事迂闊,且護前非”,“萬一用之,必紊亂紀綱”。可見曾、吴對王的評價存在嚴重分歧,特别是他們對王的執政能力的預估截然相反。
曾公亮對王安石的極高評價可能是含有政爭性質,未必盡然,但司馬光在給王安石的一封信中也説:
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司馬光《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與王介甫書》,四部叢刊縮印本,182册,頁450上。
此信作於熙寧三年(1070)三月,當時司馬光已與王安石從朋友走向對立,因此他對王的評論相對公正,更重要的是,這番評論是司馬光根據平日見聞而做出的。如《温公瑣語》所述:
王安石……好讀書,能强記,雖後進投贄及程試文有美者,讀一周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見者皆伏其精妙。……始爲小官,不汲汲於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爲宰相,薦安石及張瓌、曾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擢用,以激澆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原注: 目睹。)*司馬光《温公瑣語》“王安石不汲汲於仕進”條,《涑水記聞·附録三》,頁386—387。
可見司馬光亦推重王安石卓越的學識和難進易退的行義,從而對他的政治前景抱有很高的期待。
吴奎對王安石的質疑同樣是建立在自身經驗的基礎上的。據《長編》一九二,嘉祐五年七月朝廷“命翰林學士吴奎、户部副使吴中復、判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度牧馬利害以聞”,*《長編》卷一九二嘉祐五年七月壬子條,頁4638。當指吴奎所謂“與安石同領羣牧”之事。然吴對王的印象很不好,認爲他“迂闊”而不切實際,將空言誤國。
對王安石的兩極評價分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體而言,司馬光代表這樣一類士大夫,他們相對重視道德、理想和精神的價值,期待如王安石那樣的“賢者”當政,實現天下太平。這類士大夫不一定當國執政,但對社會輿論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力;而吴奎代表另一類官員(特别是宰相韓琦),*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録》卷三之三《參政吴文肅公》引《魏公别録》:“韓魏公嘗云: 吴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惟長文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必强,性很,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見《朱子全書》(12),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451。强調務實,反對空言,他們很多人當時正掌握實際權力,可以影響王安石在政治上的發展。例如,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擔任三司判官時將他已形成的政治改革方案寫成一篇長達萬言的《言事書》,進獻給仁宗,但没有得到在位的皇帝及宰輔大臣的重視。洪邁《容齋四筆》説:
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四《王荆公上書并詩》,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673。
作爲有豐富政治經驗的官僚,韓琦、富弼等人對王安石的“先王之政”藍圖皆持保留意見。再如《東軒筆録》説: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則第一廳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荆公爲閣老,會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爲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東軒筆録》卷一,頁115。
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雖然在輿論上享有聲望,但在實際政治中並不得志。他在給孫覺的信中談到:“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爲。”*《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六《與孫莘老書》,頁804。王安石執政後自謂“在仁宗朝知制誥,只一次上殿,與大臣又無黨”,*《長編》卷二三四熙寧五年六月辛未條,頁5684。同樣證實了他與當政者的疏離。
《邵氏聞見録》説:
時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世臣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邵氏聞見録》卷三,頁24。
這段話有些問題,特别是説王安石“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一句不足憑信,前已言及。然而,邵伯温指出王安石通過交結世家名宦建立社會關係、積累政治資本,則並不为過。實際上,王安石與英宗幾乎毫無淵源,又與當政的韓琦有矛盾,縱然有經綸天下的理想,奈何没有“結君心”的機會。因此,他只能走另一條路,即利用與世家名宦,特别是儲君親近大臣的關係,進而“結新君”。後來確實成爲王安石遭遇神宗的契機。
臣今日聞除王安石知江寧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誠然者,臣竊以爲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則?安石知道守正,不爲利動,其於出處大節,料已素定於心,必不妄發。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視事,則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爲也。又其精神可以爲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請,從容侍從之地,豈是人情?臣久知安石之不肯爲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諭,臣向所開陳者是也: 若人君始初踐阼,慨然想見賢哲,與圖天下之治,孰不願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則已,若不至此,必幡然而來矣。臣竊恐議者以爲安石可以漸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誘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賢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計取,陛下稽古講道,必於此理粲然不惑,惟在斷而行之,毋以前議爲疑,則天下幸甚!(李燾注: 韓維論王安石,據維奏議具載之,足明安石進退失據也。)*《長編》卷二九治平四年閏三月癸未條,頁5087;參韓維《南陽集》卷二四《議召王安石劄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01册,頁712上—下。
文中提及的韓維,即《邵氏聞見録》所稱“韓、呂二家”中韓氏家族的主要成員,也是王安石在開封“深交”的好友。他長期擔任神宗居東宫時的記室參軍,屬於潛邸舊臣的一員,此時以龍圖閣直學士的身份充當皇帝的顧問。
韓維認爲,放棄召王安石回朝擔任知制誥,而改命其知江寧,可能是出於“以爲安石可以漸致,而不可以猝召”的考慮,然而這不是“致安石”的正確方法。因爲安石是以道自守、以義進退的賢者,對於出處問題早有考慮,而這個方法是一種“利誘”,“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一定不能奏效。如果王安石當初以病爲由不肯回朝擔任從官,可是“除大郡,即起視事”,難免給人以要君和矯情的口實,因此必定不肯接受詔命。
那麽,什麽纔是“致安石”的正確途徑呢?即前引韓維之言,若“人君始初踐阼,慨然想見賢哲,與圖天下之治”,安石必“願效其忠,伸其道”,這是“致安石”的惟一方法,“惟在斷而行之,毋以前議爲疑”。這些話顯示,韓維早前曾與神宗討論過王安石的起用問題,並形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即所謂的“前議”。
在《南陽集》卷一六中有一道題爲《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可舊官服闋》的制詞,可能是韓維替神宗草擬的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的詔書,其文云:
敕: 三年之喪,禄之於家而不敢煩以事,此朝廷所以待近臣而申孝子之情也。若夫既除而從政,則下之所當勉也。具官某,學通經術,行應法義,銜哀服禮,内外竭盡,可謂邦之俊良、民之表儀者矣。朕臨政願治久矣,想聞生之奇論,以佐不逮。其悉朕意,亟復於位。*《南陽集》卷一六《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可舊官服闋》,頁656下。
制詞中“朕臨政願治久矣,想聞生之奇論,以佐不逮”一句似可與前述韓維言論相互呼應,表明神宗即位後確實與韓維達成了召回王安石“與圖天下之治”的“共識”。
那麽,這個“共識”是如何形成的呢?邵伯温説:
先是,治平間,神宗爲潁王,持國(韓維)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某之説,某之友王安石之説。”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邵氏聞見録》卷三,頁25。
這個説法可與鮮于綽《韓維行狀》相印證:
初,公與王荆公素相厚善,公侍神宗潛邸,數稱其經行。授太子左庶子及龍圖閣直學士,皆薦以自代。神宗想見其人。*鮮于綽《韓維行狀》,《南陽集》附録,頁773上。
正因爲韓維經常稱道王安石的學問和爲人,使得神宗對王安石有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一即位就希望將“想見其人”的心願付諸實施。葉夢得《石林燕語》説:
神宗初即位,猶未見羣臣,王樂道、韓持國維等以宫僚先入,慰於殿西廊。既退,獨留維,問:“王安石今在甚處?”維對:“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來乎?”維言:“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於山林者。若陛下以禮致之,安得不來?”上曰:“卿可先作書與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維曰:“若是,則安石必不來。”上問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進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書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臣當自以陛下意語之,彼必能達。”上曰:“善。”於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屬之意。*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01。
現在可以基本確定,韓維與神宗達成過一個共識,即王安石是“有志經世,非甘老於山林者”。只要神宗信任重用,“安得不來”。基於這個共識,韓維通過王安石之子王雱傳達了神宗的意旨,而韓維爲神宗代擬的《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可舊官服闋》同樣也是這個共識發生效力的結果。也正因爲有了這個共識,神宗命王安石知江寧府之詔纔會引起韓維那麽大的反應,並反覆提醒“陛下向所宣諭,臣向所開陳”的“前議”。
爲什麽韓維堅信“若陛下以禮致之”,王安石“安得不來”呢?前引《石林燕語》提到,王雱曾多次造訪韓維,使韓維獲取了王安石的相關資訊。又據《宋登科記考》,治平四年(1067)正月二十五日,神宗下詔任命知貢舉官及考試官;三月四日,禮部貢院放榜,王雱登進士第。*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305,306。王雱應是在治平三年底或四年初爲參加省試赴京,並順道造訪了韓維。那麽,王雱具體何時來京的呢?據王銍《默記》:
先公言: 與閻二丈詢仁同赴省試,遇少年風骨竦秀於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也。是時盛冬,因相與於一小院中擁火。詢仁問荆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不晩且來。雱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爾。”詢仁云:“舍人既來,誰不願賃宅,何必預尋?”元澤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須與司馬君實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擇鄰必須司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兒曹有所觀效焉。’”*王銍《默記》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45。
此處“先公”即王銍父王莘,王元澤即王雱。王莘與閻詢仁同赴京城參加省試時遇王雱,時在“盛冬”,閻詢仁問“荆公出處”,王雱則作出了回應。《宋會要輯稿》禮五五之三記載,“治平四年正月八日,英宗皇帝崩,神宗皇帝即位”,“十七日,始見百官”。*《宋會要輯稿》,頁1963上。而前引葉夢得《石林燕語》説,神宗“即位”之後、“見羣臣”之前,韓維就告訴他“安石子雱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考慮到新君即位資訊傳播及王雱行程所需要的時間,王雱很可能是在英宗去世、神宗即位之前,也就是在治平三年的“盛冬”,已從江寧來到開封了。王雱回應閻詢仁稱,他來京城,“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爾”,因爲王安石“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不晚且來”。王雱既然對閻詢仁、王莘宣揚王安石將要回京復職,很可能亦對韓維宣揚了此事,韓維也許正是得到了這一消息,纔敢在神宗面前保證王安石“若陛下以禮致之,安得不來”。其間的脈絡似乎是有迹可循的。
總之,神宗在即位以前已對王安石有了深刻的印象,即位後不久就向他傳達了“待遇眷屬之意”,並且下詔召其赴闕,但又被安石謝辭了。治平四年閏三月的那場辯論,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發生的。筆者以爲,王安石既然打定主意“不晚且來”,那他謝絶神宗僅僅是一種自謙或自重的表示,他或許希望神宗表現出更足夠的誠意。也就是説,如果神宗堅持繼續召之,必定會有所回應。曾公亮盛贊“安石真輔相之才”,不僅是對神宗心意的迎合,也是對王安石這個未來政治明星的取悦。吴奎無疑深知其中之内情,爲了抵制安石的到來,決定作頑强的努力,從而爲曾、吴之辯的發生埋下了伏筆。
四 王安石知江寧府的政治象徵和文化隱喻
《長編》云:“詔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視事。”*《長編》卷二九治平四年閏三月癸卯條,頁5087。蔡上翔指出,《臨川先生文集》中有《辭知江寧府狀》及《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等表狀,*《臨川先生文集》卷四《辭知江寧府狀》,頁435—436;卷五六《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頁610—611。證明王安石“遜辭之不容,必已辭不允而後受”,*《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一二,頁404。可見李燾之誤。而李燾之説源於《温公日録》,*《三朝名臣言行録》卷六之二《丞相荆國王文公》引《温公日録》:“治平四年,以介甫知江寧府時。介甫方乞分司,衆謂介甫必不肯起,既而詔到,即詣府視事。”頁504。李不注出處,又不加考辨,遂有此誤,從中似隱約反映其對王安石的態度。儘管如此,王安石畢竟接受了此命,確實與其先前的表現不一致。前引韓維曾斷定王必不受命,“安石知道守正,不爲利動”云云,而相關結果卻不如所料,李燾因此論道,“足明安石進退失據也”,對王安石的出處問題提出了質疑,從而表達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傾向性。實際上,韓維似乎没有完全理解王的出處哲學,李燾對王更是存有偏見。
王安石知江寧府具有濃厚的政治象徵和文化隱喻意味,具體而言,在政治上象徵神宗、王安石“君臣合作”的開端,在文化上隱喻王安石“以道進退”和“觀時而動”相結合這一出處哲學的成功實踐。
(一) 政治象徵:“君臣合作”的開端
前已提及,曾公亮力主繼續召用王安石回朝,但遭致吴奎激烈的反對,神宗轉而改命其知江寧,史家認爲這是“采納”吴奎之言。然而,對王安石來説,江寧不僅是他早年隨父遊歷並定居之地,而且是“丘墓所寄之邦”,*《臨川先生文集》卷五七《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頁616。王安石曾兩度居喪於此,因而江寧是他的“鄉郡”、“鄉邦”。徽宗朝有臣僚上言説:“官守鄉邦,著令有禁,陛下待遇勳賢,優恤後裔,……示眷禮也。”*《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八四,頁8328上—下。可見,守鄉郡代表一種優待和特權,王安石知江寧同樣是特殊情況下的政治安排。
據《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九記載,“安石即(既)受命知江寧,上將復召用之。……(吴)奎曰:‘恐迂闊’,上弗信,於是卒召用之”,治平四年九月戊戌(二十三日),詔“王安石爲翰林學士”。*《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治平四年九月戊戌條,頁1908。而據《太平治迹統類》卷一二,此月己丑(十四日),“韓琦數因入對懇求罷相,上察琦不可復留,賜手劄曰:‘……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虚上宰之位以待卿還。’琦亟奏:‘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虚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至辛丑(二十六日),韓琦罷相,以“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太平治迹統類》卷一二《神宗聖政》治平四年九月己丑、辛丑條,頁313下。又據《宋宰輔編年録》,參知政事吴奎亦於同日罷免。*徐自明撰,王瑞來《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65。《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集》卷一四《實録·王荆公安石傳》説:“除安石爲翰林學士,命下數日,(韓)琦罷相,安石始造朝。”*《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集》卷一四,頁773上。而《丁未録》云:“安石聞(韓)琦罷相,甚喜。”*《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七引《丁未録》,頁383。
以上種種迹象表明,王安石知江寧是入朝爲翰林學士的前奏,而任翰林學士與韓琦罷相又有一定的關聯,其中隱含的深意,仍然要從相關背景上索解。治平四年(1067)閏三月辯論中,吴奎表現出對王安石强烈的排斥態度,以及吴奎身後有韓琦支持這一事實,使神宗感覺到朝中反對王安石的勢力還很强大,如果貿然召用,將激化與韓琦集團的矛盾,從而對王安石産生不利影響。所以,爲避免直接衝突,令王安石暫知江寧,同時集中精力解決韓琦的問題,對神宗來説不失爲一個穩妥的辦法。
王安石很早就得知“上待遇眷屬之意”,但他在没有繼續得到召用而被命改守鄉郡的情況下毅然就任,説明他敏銳地覺察到了朝廷的情況,並理解了神宗的用心。或者説,他與神宗之間達成了一種“奇妙的默契”,*仲偉民先生認爲:“神宗命安石知江寧府,很多人以爲安石可能還會像以前那樣拒絶任命,但没想到安石痛快至極,接詔後即上馬赴任。對此我們没有必要作過多的解釋,因爲神宗信任安石是如此的堅決,而安石對神宗任命的接受又是如此的果斷。我們只能認爲神宗與安石君臣二人之間有種奇妙的默契,這是一種能夠相互理解和相互感知的默契。這種解釋可能不是十分圓滿,但可能是最恰當的解釋之一。”參見仲偉民《宋神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頁35。這種“默契”就連韓維也没有想到。然而,正是這種“默契”,象徵着神宗與王安石“合作”的開端,也爲將來的“君臣遇合”定下了基調。
(二) 文化隱喻:“以道進退”和“觀時而動”的結合
余英時先生説:“士的出處問題自先秦以後論者寥寥,直到宋朝纔受到這樣普遍而集中的注意,這在士大夫史上是必須大筆特書的。”又説:“士大夫持‘道’或‘義’爲出處的最高原則並能形成一種風尚,這也是宋代特有的政治現象。”*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自序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頁9,224。在余先生所列舉的宋代士大夫中,王安石是最重視出處問題的一位,他在仁宗朝的“難進易退”以及英宗朝的“屢召不起”,都可視爲這一論斷的注腳。然而,這僅僅是王安石出處哲學中的一個方面;而在另一方面,王安石强調士人在堅持“以道進退”的原則下,還要注意“觀時而動”。康定元年(1040),王安石《上蔣侍郎書》自謂:
某嘗讀《易》,……斯則聖人賾必然之理,寓卦象以示人事,欲人進退以時,不爲妄動。時未可而進謂之躁,躁則事不審而上必疑;時可進而不進謂之緩,緩則事不及而上必違。誠如是,是上之人非無待下之意,由乎在下者動之不以時,干之不以道,不得中行而然耳。……其於進退之理,可以不觀時乎?*《王文公文集》卷二《上蔣侍郎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25—26。繫年參考楊倩描《王安石〈易〉學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6。
在儒家經典中,《周易》往往“推天道以明人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1中。借卦象的變化來顯示吉凶悔吝和進退得失之機,與王安石對士人出處問題的重視相吻合。據研究,王安石曾於嘉祐年間撰寫了《易解》一書,對於其出處哲學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例如,王安石釋《晉·初六》曰:“初六以柔進,君子也,度義以進退者也。常人不見孚,則或急於進,以求有爲;或急於退,則以懟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價者也。’此‘罔孚’而裕於進也。孟子久於齊,此‘罔孚’而裕於退也。”*參〔宋〕 李衡《周易義海撮要》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册,頁390上;楊倩描《荆公易解鉤沉》,氏著《王安石〈易〉學研究》,頁65—66。事實上,王安石正是通過對《周易》的理解來闡述他的出處哲學,認爲士人要將“以道進退”和“觀時而動”結合起來。*參考劉成國《王安石〈易解〉發微》,《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頁44;《荆公新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7—28。
自從嘉祐八年(1063)離開朝廷後,王安石一直閑居江寧,一面授徒講學,一面從事著作。他在此期間對於經學的研究更加精進,逐漸構建了一套富有獨立見解的學術體系,在繼續探討“道德性命之理”的同時,治學的重心越來越向經世方面傾斜。特别是從治平年間所寫的《禮樂論》和《虔州學記》這兩篇文章來看,王安石越發注重“内聖”與“外王”這兩個領域的連結。而從爲學生出的《策問》第十一題可以看出,他關心的都是北宋王朝當時的財政、吏治、軍政、馬政等問題,充分體現了經世致用的取向。*參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79—88;劉成國《荆公新學研究》,頁40—42;楊天保《金陵王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311—335。韓維説:“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於山林者。”可謂至言。
王安石雖然“身在山林”,但一直“心存魏闕”,事實上,他已經爲將來重返政壇做好充分的準備了。在英宗朝,朝中大臣因“濮議”幾乎兩敗俱傷,而對於王安石來説卻是聲望極好的時期,“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馬永卿輯,王崇慶《元城語録解》卷上,叢書集成本,601册,頁9。他一直在等待有利的時機東山再起。或許在治平三年底,有關因英宗“不豫”、“自得疾不能語”、“立皇子潁王頊(神宗)爲皇太子”等消息從宫禁流出,*《長編》卷二八治平三年十月乙酉條,頁5063;十二月辛丑、壬寅條,頁5068,5069。王安石覺得這是一個“結新君”的機會。他借王雱赴開封參加省試之便,與世家名宦聲氣相通,*司馬光時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王安石囑托王雱要與司馬光“擇鄰而居”,則王雱與司馬光應該有所交流。使自己願意赴闕、“不晚且來”的消息散佈開來,成功引起了神宗的注意。這不禁令人想起“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的故事,在王安石身上的重演。*《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七收有一首《浪淘沙令》,原詞云:“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爲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只在談笑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頁401。表達了王安石對伊尹、呂尚(姜子牙)因與湯、武二王“相遇”而建功立業的豔羨之情。這表明王安石可能自比爲伊尹、呂尚,希望得到“明君”的“知遇”,這或許是他積極於“結新君”的心態。王安石《手詔令視事謝表》説:
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寬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即知素願之獲申;睿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秉洪鈞。*《臨川先生文集》卷六《手詔令視事謝表》,頁647。
此表作於熙寧三年(1070)。王安石自謂,最初因不爲當政者所知,深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故“自屏於寬閑”,不願進取。然而後來又因相信“聖人之時不可失”、“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應詔而出,從“鄉郡”、“禁林”直至“忝秉洪鈞”。可見,知江寧府是王安石政治旅程的再出發,也是他所奉行的“以道進退”與“觀時而動”相結合這一出處哲學的成功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