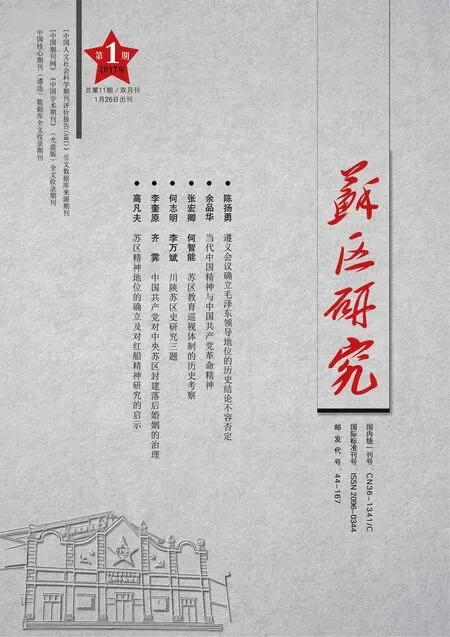论湘鄂边苏区的历史地位
向凤毛
论湘鄂边苏区的历史地位
向凤毛
湘鄂边苏区,是中共中央直接策划,由贺龙、周逸群等领导创建的,是起步最早、斗争时间最长的苏区之一。其大致演变历程为:湘鄂边苏区先发展为湘鄂西苏区,并在土地革命后期成为湘鄂川黔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湘鄂边苏区红四军的诞生和发展,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起到了牵制敌人和策应、配合其他苏区的作用。此外,苏区军民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
湘鄂边苏区;历史地位
湘鄂边苏区以湖南桑植、湖北鹤峰为中心,包括湖南慈利、石门、大庸,湖北五峰、长阳、巴东、建始、宣恩、恩施等县的大部或一部分地区,以及湖南龙山、澧县、安乡,湖北来凤、咸丰、松滋等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从地域范围而论,湘鄂边苏区是湘鄂西苏区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湖北、湖南党史部门和相关高校组织专家学者,对湘鄂西苏区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两本著作,是迄今为止对湘鄂边苏区最完整的反映。
长期以来,对湘鄂边苏区的历史地位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相对较少。20世纪90年代,湘鄂两省少数高校的专家曾就湘鄂边苏区的特点、苏区红军的创建发展、苏区斗争成功的经验等有过专题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涉及的地域空间大多为湘鄂边与湘鄂西苏区范围内,时间段是1928年至1933年。岁月的长河承载历史的沧桑。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必要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对湘鄂边苏区的历史地位进行再认识。今湖南张家界市(辖桑植、慈利、大庸等县区)是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的发源地和中心区域,是贺龙元帅的家乡和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2014年4月至2016年3月,笔者与同事一道,通过“走走党史”的方式,对上述苏区历史进行了再次追寻、思索和记录。结合所思所得,本文从创建湘鄂边苏区的起源,苏区红军创建发展的曲折历程,湘鄂边苏区与湘鄂西苏区、黔东特区根据地、湘鄂川黔苏区的历史关联等方面,就湘鄂边苏区特殊的历史地位加以探讨。
一、中共中央直接策划及创建最早的苏区之一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从1927年8月至1929年,党在城市和农村发动和领导了约达200次大小不等的武装起义。它遍及全国东西南北中12个省、约150个县的广大地区。”“从全国来说,那时最大的苏区有6个,即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边、鄂东北、闽粤赣。”*石仲泉:《湘鄂西苏区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苏区研究》2016年第1期,第7页。
八七会议把发动湘鄂粤赣4省农民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有学者认为,创建湘鄂边苏区是贺龙提议,由中共中央决定的。这有失偏颇。大革命失败后,湘鄂边地区各种武装蜂起。以桑植县为例,当时有近20支武装、3000余人。“对于这一地区的情况,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派贺龙回湘西之前,曾指示中共湖南省委派人去湘鄂边,利用有利条件,尽可能形成一个割据的局面。”*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1927年8月23日,《中央复湖南省委函》指出:“湘西工作也要有相当的准备,如政治上的宣传,军事上的联络和组织土匪农军等,以备如果鄂省那一部队能到湘西时之大暴动。”*《中央复湖南省委函——对暴动计划、政权形式及土地问题的答复》(1927年8月2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湖南省委加强了对湘西特别是湘西北地区的领导。中共湘西特委组建后,1927年11月,特委委员陈协平到桑植县洪家关,与时任小学教员的省二师学友谷佑箴取得联系,迅速组织起700余人、400余枪的桑植农民武装,在洪家关成立了桑植农军总指挥部。12月5日,农军攻占县城,在城内打击土豪,分发浮财给贫民。此次桑植年关暴动,虽未能形成割据的局面,但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为创建湘鄂边苏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
192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制定了《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正在筹划全国第二次武装暴动的中共中央,期望两湖(湖南、湖北)地区能够发动新的武装起义,开创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对举行新的暴动怎样实施才能成功,中共中央曾作过多次专题研究,把暴动的厚望寄托在湘鄂西地区。1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暴动给湖南省委的信》指出:“在湘西党的力量和工农的力量虽然比较薄弱,然而常德以上,沅澧一带,客观的环境——统治者之复杂和内部的冲突,比较别的地方好,贺龙在那一带颇有历史关系……你们应派人去利用这些条件……尽可能形成一个割据局面,并且在澧水一带要与湖北的石首、公安联络”。*《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暴动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12月15日),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省社科院历史所、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党史资料丛书——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3册,1985年12月内部出版,第39-40页。
南昌起义部队南撤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1927年11月,起义总指挥贺龙经香港秘密到达上海,开始谋划新的革命斗争,并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返回家乡重建武装的请求。贺龙的想法与中共中央的意向不谋而合。在上海期间,根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贺龙代两湖省委组织拟定了《湘鄂西暴动计划》。12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派李维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何资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周逸群(贺龙入党介绍人)等与贺龙座谈。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割据湘鄂西,是中共中央在全国各地组织武装暴动,实行分区割据的整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湘鄂西地区分成若干区域实行暴动,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发动在南昌起义后回到湘西的原第二十军的军事骨干的作用。座谈会后,由周恩来将座谈会纪要呈交中央讨论决定。12月28日,中央第十次常委会议讨论贺龙回湘后的行动计划。会议记录写道:“割据问题从哪里发端,我们力量常德要好一点,但何键在那里,在客观上不可能。应以桑植、大庸、石门、慈利四县为根据地。(这一带)地势是很好的。桑植虽无党,但军事上有把握。大庸,过去农民是有斗争的。慈利亦然……”*刘雁声:《桑植起义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93页。这一计划,是对《湘鄂西暴动计划》的进一步完善。192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贺龙返湘,并组建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郭亮,委员为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以加强对暴动的领导。当时,郭亮在武汉,徐特立、柳直荀因中央另作安排,后改由周逸群任特委书记。
1月11日,周逸群、贺龙、卢冬生(中共中央交通员)等,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离开上海,西进武汉,转战荆江,于2月28日夜到达桑植县洪家关。随即,成立中共桑植县委,以桑植年关暴动的队伍作为基础,组建起3700余人、1500余支枪的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清明节前夕,湘西北特委在洪家关宣布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打出湘鄂边第一面红色军旗。4月2日,工农革命军发动桑植起义,攻克桑植县城。4月3日,成立桑植县革命委员会,并颁发《工农革命军布告》。随即接管国民党桑植县政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湘鄂边革命斗争从此拉开序幕。
中共中央一直十分关注湘鄂边地区的武装斗争。桑植起义后,工农革命军处境艰难,由于敌人严密封锁,经常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中央和湖南省委先后派出4批党和军事干部赴湘西寻找贺龙和工农革命军;贺龙派卢冬生赴上海汇报,派张海涛、陈石青到湘西、鄂西寻找党组织;均未如愿。1928年11月,邓小平起草的《中央给贺龙同志信》带到桑鹤边界。“信中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对红四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页。并就游击战争的任务、方针及前途等问题作出明确指示。中共中央在信中担心“贺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地向你们进攻”,“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龙兄即刻起程前来中央是为至要”。*《贺龙传》,第70页。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后来中央同意了贺龙仍留在湘鄂西工作的请求。1929年5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致贺龙和湘鄂西前委《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信带到鹤峰。指示信着重介绍了毛泽东、朱德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对湘鄂边苏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二、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作出重大贡献、提供宝贵经验
湘鄂边苏区诞生了红四军,为党保存了武装力量,锻炼了斗争骨干,积累了斗争经验。湘鄂边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建发展经历了一系列困难和挫折。在异常艰难的时期,贺龙曾主动隐退,秘密指挥。桑植起义后,由于遭到强敌进攻,且部队刚组建,战斗力不强,工农革命军三战未胜,37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400多人。周逸群被迫转移到鄂西开辟根据地。此后,这支部队主要活动在崇山峻岭的桑植、鹤峰边界地区,先后进行多次整编。其中,有过记述且在红四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整编有11次。1929年2月,工农革命军集结到桑鹤边界的杜家村再次整编,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不久,以鹤峰县城为中心的红色割据局面初步形成。5月,红四军主力南进桑植,6月,再次解放桑植县城,部队恢复到1500余人。7月,红四军先后取得桑植南岔、赤溪河两次大捷,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正式形成。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斗争,在湘鄂边建立起一支经过战斗锻炼,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基础的人民武装力量,红四军发展到4000多人;创造了与朱德毛泽东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李文林式(东固革命根据地)、方志敏式(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并列的贺龙式革命根据地模式;培养出贺锦斋、王炳南、贺炳炎、贺英、卢冬生、廖汉生等一大批人民军队的骨干力量。
湘鄂边苏区创建了两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工农红军,进一步扩大了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湘鄂边地处偏僻,是土家族、苗族、白族、汉族聚居的地方,深受官、匪、军阀和土豪劣绅地主的剥削压迫,民生艰难,民风强悍,富于反抗精神和斗争传统。贺龙所率领的北伐军第二十军是南昌起义主力军,“总兵力达到两万人”,*刘达五、刘冠群:《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其中桑植籍指战员3000余人。“人民军队作为武装力量的第一次列队,贺龙及其率领的部队构成了我军最为壮观的阵容。”*陈先义:《贺龙元帅的数千名族亲烈士》,《北京日报》2008年3月31日,第19版。湘西北特委发动桑植起义时,包括参加南昌起义后返回家乡的指战员在内,以桑植县为主的土家、苗、白、汉族3700多人聚集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桑植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中,军、师、团干部中很多人为少数民族,例如贺锦斋、王炳南、贺桂如、李云清等。1928年7月,贺龙在长阳资丘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全军1100多人,其中土家族将士占50%以上,从军长、参谋长,到政治处长、军法处长、军需处长都是土家族人。这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支以军为建制、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工农红军。
湘鄂边苏区孕育了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发展成为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当贺龙领导开辟湘鄂边苏区的同时,周逸群、段德昌等在以洪湖为中心的荆江两岸地区开展河湖港汊地带的游击战争,组建了约7000人的红六军,创立发展了洪湖苏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0年3月,贺龙率红四军东下洪湖。4月12日,中央文件规定贺龙指挥的湘鄂边红四军为“红二军”。从此,按中国工农红军序列,湘鄂边苏区红四军改称红二军。1930年4月,洪湖苏区红六军开始移师西进。7月,红二军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南平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二、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组成以周逸群为书记的红二军团党的前敌委员会,贺龙任红二军团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全军团共万余人。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根据地正式形成。193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军团在长阳枝柘坪改编为红三军。湘鄂边苏区丧失后,1934年夏,贺龙、夏曦、关向应等率红三军开辟黔东特区根据地。10月,来自中央苏区的红六军团和红三军在黔东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的会师,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一个战斗整体,形成策应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强大战略突击力量;直至1936年7月,以红二、六军团为主体组成红二方面军,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
湘鄂边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建发展,为党和人民军队统战政策的成功实践提供典范。贺龙、周逸群回到洪家关时,各种反动武装对桑植构成包围态势,对组织发动桑植起义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此,湘西北特委和中共桑植县委采取了“拉关系”、“挖墙脚”的统战策略。特委以贺龙的名义,向邻近桑植的团防头目送去近百封信函,或规劝他们改变立场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反动派,或动员他们为革命支援粮食和军费,或规劝他们保持中立,或希望他们采取假打真和迂回策略等。这些信件在各地团防中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大多数团防维持中立,不少人还主动献粮,捐枪弹。与此同时,对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胆敢疯狂进犯的反动团防坚决予以打击。贺龙、周逸群还同与当地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名流雅士打交道,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争取他们同情和支持革命。例如谷德桃、邓仁山夫妇,辛亥革命时是桑植“会党”领袖,也是湘西“讨袁护国”的重要骨干。夫妇俩接受贺龙的委托,与慈(利)、桑(植)、鹤(峰)联防办事处主任兼慈利县第五区区长谷岸峭谈判,获得成功。此后,谷岸峭让红军在慈利县官地坪设立秘密联络点,为红军筹集物资、提供情报、购买枪弹,照顾和抚养红军家属和伤病员。官地坪成为湘鄂边苏区的可靠后方。
贺龙是党内较早认识和改造利用神兵组织的领导人。在创建湘鄂边苏区过程中,充分利用盛行于湘鄂川黔边境的神兵组织,采取改造、改编的方法,逐步把神兵的主要力量吸纳到红军队伍中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史上独特的对反政府农民武装利用改造的成功范例。1929年1月,贺龙对鹤峰县邬阳关神兵成功进行收编,将其主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特科大队。12月,贺龙成功收编鄂西地区势力最强的咸丰黑洞神兵武装。1933年7月,贺龙率红三军再次进驻黑洞,9月23日,黑洞700余名神兵加入红军。
三、湘鄂西苏区的策源地和战略大后方
整个湘鄂西苏区,因湘鄂边苏区的创建发展而形成,又因为湘鄂边苏区的最后丧失而结束。湘鄂边苏区的形成与发展,与洪湖苏区相呼应,为形成整个湘鄂西苏区创造了重要条件,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争。1930年7月,湘鄂边苏区和洪湖苏区连成一体,形成湘鄂西苏区,与鄂豫皖、湘鄂赣苏区守望相助、唇齿相依,起到了策应配合作用。“它地跨长江两岸和洞庭湖区,直逼武汉重镇,又为‘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因而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构成了心腹之患的威胁,在土地革命战争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石仲泉:《湘鄂西苏区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苏区研究》2016年第1期,第7页。
红二军团转战湘鄂西苏区期间,在湘鄂边地区的桑植、鹤峰、五峰、长阳等县来回游击,湘鄂边苏区得以巩固和扩大。红二军团多次选择在湘鄂边落脚,又从湘鄂边出发,开辟新的斗争。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红三军军部、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等,都曾经设在鹤峰、桑植等地。1928年2月至1933年6月,贺龙、段德昌等率部曾9次进入湘鄂边的巴东县,5次屯兵巴东金果坪,在此直接指挥湘鄂西革命斗争,将革命推向高潮。因此,湘鄂边苏区成为湘鄂西苏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战略大后方。
1930年9月,中共中央新任命的湘鄂西特委负责人到达洪湖,开始执行“左”倾错误。10月中旬,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红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红一、红三军团第三次攻打长沙。10月21日,红二军团发起南征行动。12月,红二军团在松滋杨林市遭到严重挫折,伤亡2000多人,仅红六军就损失约四分之一。随后,贺龙率红二军团转移到湘鄂边鹤峰休整。期间,收编了国民党甘占元部约3000人,获得大批武器弹药。“1931年3月红三军以此为前进基地,北渡长江,巩固和扩大了巴兴归苏区,开辟了荆当远游击区和鄂西北根据地。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敌人,使洪湖苏区获得了一个暂时稳定的局面。”*胡济民:《湘鄂边苏区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75页。
1932年1月召开的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会,全面确立了王明“左”倾错误对湘鄂西苏区的统治,给苏区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加上湘鄂西中央分局对军事斗争的错误指导,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严重被动局面。8月,洪湖苏区丧失。10月上旬,红三军撤出根据地,历时2个多月,进行横跨鄂豫陕川湘黔6省的7000里“小长征”,部队由1.5万人减少至9000人左右。12月底,贺龙率红三军再一次选择在湘鄂边的鹤峰县境落脚。在一边开展反“围剿”斗争、一边被迫应对“肃反”的情况下,红三军在鹤峰、桑植、永顺、慈利、大庸、石门、巴东等地来回游击。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至1933年6月,湘鄂边苏区基本恢复到1930年时的规模。
四、为其他苏区起到牵制敌人和策应、配合的重要作用
桑植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蒋介石迅速调兵遣将,企图扼杀工农革命军于摇篮之中。1928年4月15日,国民党独立十九师师长陈渠珍配合四十三军龙毓仁旅向工农革命军疯狂反扑。工农革命军奋起迎战,在桑植凉水口、罗峪、白果垭一带与敌周旋。5月初,转移到桑植、鹤峰边界的红土坪、白竹坪等地休整。7月,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矛盾暂趋稳定,从而铺开了全面的“清乡”“围剿”。国民党陈嘉佑的十四军和陈渠珍的独立十九师,加上桑植团防,对桑植形成包围之势,从杜家山、双溪桥、梨树垭、南岔等方向偷袭洪家关。贺龙指挥部队顽强阻击,由于敌众我寡,后转移到桑鹤边界的大山中隐蔽休整。
1928年8月,湖南军阀调集上万兵力向工农革命军进攻。工农革命军在石门两战失利后,转移到桑鹤边界。国民党部队又联络桑植、慈利、石门、鹤峰、宣恩、咸丰等10余县的地方反动武装,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11月2日,敌独立十九师分两路“进剿”红土坪。工农革命军顽强突击,贺龙率部进入桑鹤边界大山中与敌周旋,坚持斗争。
1929年3月,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联合石门、桑植、五峰、恩施、建始、巴东等县团防共1万余人进攻鹤峰。红四军集中主力与敌激战,击毙王文轩,保存了鹤峰的红色割据区域。6月,桑植红色政权的再次建立和红四军力量的恢复壮大,“使湖南省主席兼‘清乡’司令何键为之震惊。蒋介石在武汉得知贺龙指挥的红军在湘鄂边活动的情报,急招何键去武汉密商‘清剿’方案。6月中旬,何键陪蒋介石抵长沙,密电驻辰州(沅陵)独立十九师师长陈渠珍,带领桑植、大庸、永顺、慈利、石门、鹤峰、五峰、宣恩、来凤、咸丰等县地主武装,同国民党正规军吴尚、戴天明等师配合,采取严密封锁的战术,从东、西、南、北向桑植步步进逼,作铁桶式的包围。”*本书编写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7月,贺龙率部先后取得桑植南岔、赤溪河大捷,共歼敌3000余人,巩固和扩大了苏区。
1929年9月底,何键奉蒋介石之命,派吴尚、陈渠珍、李云杰等师,会同地方武装共数万人,集结于常德、石门、桃源、慈利等各战略要地。10月初,吴尚师阎仲儒旅和慈利、桑植、石门等团防2万多人逼进桑植。贺龙率部歼灭阎仲儒旅千余人。1930年1月,红四军歼灭盘踞在恩施、宣恩边境的反动团防赵金轩,继而再克新塘,沉重打击了湘鄂边苏区西线的团防和土豪势力。
1930年11月,湖北第十一军军长徐源泉指挥4个师又7个旅的兵力,在民团武装的配合下,组织对湘鄂西苏区大规模“围剿”。此时,湘鄂边苏区牵制着川军二十六师郭汝栋部及长阳、五峰、宜都等县团防于自己的东北边及长阳一线,在西南边还牵制着湘西陈渠珍师,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苏区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7月,为配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湘鄂之敌以第十九师、新编第十一师、新编第七旅及大批民团,共计30余个团的兵力,向湘鄂西苏区发动“围剿”。期间,石门、慈利团防和湘军第三十四师共9个团的兵力,向湘鄂边苏区围攻,遭到湘鄂边独立团的猛烈阻击。后急调石门、澄州、临澄之敌援,王炳南独立团于石门等地伏击歼敌,连连获胜,有力策应了其他苏区的红军作战,减轻了敌重兵向洪湖苏区推进的压力。
五、开辟了湘鄂川黔苏区的落脚点,并成为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1933年7月,国民党“湘鄂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调动部队,完成对湘鄂边苏区的包围,企图围歼红三军。此时,湘鄂西中央分局仍然坚持“左”倾错误,在苏区推行“肃反”扩大化,由于红三军七、九两师分开行动,难以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被迫到处流动游击,频繁战斗,得不到及时补充和休整。至11月,红三军只剩下3000多人。从1933年底到1934年4月,红三军“在这个时期游击永顺、龙山、桑植、大庸、慈利五县境内,有两个多月陷于无目的的流浪”,*《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9月15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1934年)》,1985年12月编印,第431页。濒临毁灭的边缘。至此,坚持了7年之久的湘鄂西苏区斗争,因湘鄂边苏区的最后丧失而结束。此后,贺龙、夏曦、关向应等率红三军从湘鄂边出发,进入川黔边。至1934年9月,建立起包括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5县地域及秀山部分地区,纵横200里,拥有10万以上人口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所以,湘鄂边成为红三军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出发地。
1934年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县横石等地出发,先遣西征,为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探路,10月24日与红三军在黔东根据地会师。鉴于创建湘鄂边苏区时期的群众基础和工作基础,根据贺龙的建议,28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红二、六军团从酉阳南腰界出发,发动攻势作战;开辟以大庸、永顺、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苏区,有力策应了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长征。所以,湘鄂边又成为红二、六军团的落脚点。“这样,不仅开辟湘鄂西苏区的红二军团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开辟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主要区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支柱,而且湘鄂边苏区的一些地区也成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石仲泉:《湘鄂西苏区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苏区研究》2016年第1期,第6页。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实施战略转移。湘鄂边又成为红二方面军万里长征出发地。
在“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下,全国各苏区原来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打破。在这一大背景下,湘鄂边成为红二、六军团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落脚点和长征出发地,揭示出湘鄂边苏区的重要历史地位。
湘鄂边苏区的创建发展,展现出血与火、泪与笑、红色风暴与白色恐怖交织的一幅幅历史画卷。湘鄂边苏区,是中共中央直接策划创建的,酝酿于1927年八七会议后,起步于1927年底桑植年关暴动和中共湘西北特委的组建,正式形成于1929年7月。湘鄂边苏区是湘鄂西苏区的策源地、有机组成部分和战略大后方。这里诞生了红四军(红二军),孕育了红二军团(红三军)和红二方面军,为全国其他苏区开展武装斗争起到重要的策应和配合作用。贺龙、夏曦、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从湘鄂边出发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又在湘鄂边落脚建立湘鄂川黔苏区,有力策应了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以致湘鄂边又成为湘鄂川黔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一系列的策源地、诞生地、落脚点、出发地、战略大后方,这些特点突显了湘鄂边苏区的历史地位。从湘鄂边这块红色土地上,先后走出168位共和国将帅和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苏区军民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值得永远铭记。
责任编辑:戴利朝
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Hunan-Hubei Border Soviet Area
Xiang Fengmao
The Hunan and Hubei Border Soviet Area was planned directly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nd led by He long and Zhou Yiqun. It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soviet areas which struggled for the longest time. The Hunan and Hubei Border Soviet Area has generally gone through the evolution process as follow: it firstly developed into the Hunan-Hubei western Soviet area and then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viet area in the border area of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d Fourth Army in the Hunan-Hubei Border Soviet Area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s army. It has also played a role in pinning down the enemy, supporting and coordinating with other Soviet areas. Besides, the Soviet soldiers and civilians have made great sacrifices for the revolution.
the Hunan-Hubei Border Soviet Area;historical position
向凤毛,男,中共张家界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编审。(湖南张家界 427000)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1.008
——以传承人向佐绒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