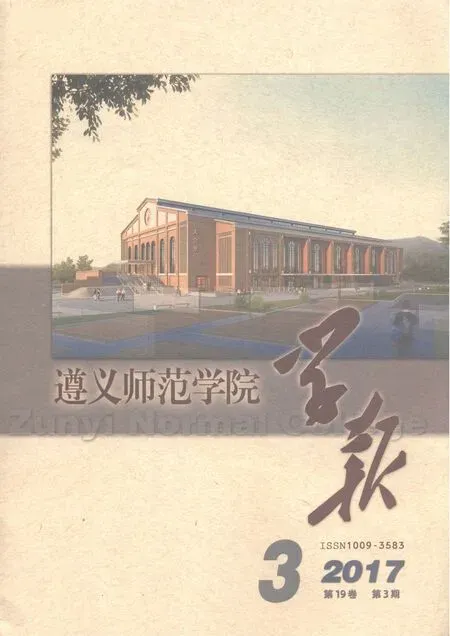元代土官朝贡及其制度化
彭福荣
(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408100)
元代土官朝贡及其制度化
彭福荣
(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408100)
元朝继承政治文化遗产和制度文明,在大一统历史框架和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以强大军政势能为基础,延续羁縻统治传统,地方治理中参用土人为官,允准、接纳和认可西南等地民族首领的主动朝贡,通过引导性朝贡带动元代土官朝贡实现制度化发展,成为元代土司制度的重要方面。但是,元代土官朝贡制度因政治吸附与文化吸引及制度草创而未充分发展,为明清土司制度与中国土司朝贡制度的健全完善留下了空间,相关研究值得深化。
元朝;国家;整合;土司;朝贡;制度
根据朝贡制度,古代中国的藩属国政治归附封建王朝、顺服国家权力,采用王朝年号、年历,按时向宗主国进献礼品、方物并得到奖赐封赏,使边远民族和其他国家感沐天朝恩典。[1]P1因此,朝贡及其制度是封建王朝整合建构统一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方式、手段和保障。元朝是我国古代极具重要影响的封建王朝,续递国家治统,建构整合统一国家政治共同体,延续前代历朝的羁縻统治传统,在国家治理体系能力建构完善中,任用土人世代为官并创造性地纳入王朝职官体系,肇端我国土司制度,对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民众也实现了间接统治,使原本处理边远民族和国家关系的朝贡成为国家王臣的义务,成为元朝与土官、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手段和形式之一,朝贡及其制度成为元代土司制度的重要内涵。在大一统历史框架和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西南等地的民族首领作为元朝的“王臣”和土官,必须履行朝贡纳赋义务,从而使王权干预下的惯例性朝贡在贡期、物品、队伍和程序等方面成为元代土司朝贡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明清土司朝贡制度完备的前提。本文拟就元代土官的朝贡做一初步探讨。
一、元代羁縻统治与土官主动朝贡
羁縻统治是我国封建王朝经略边疆边地的创举,元朝在大一统历史框架内,创造性地实行地方行省管理体制,延续历朝“以夷制夷”、“以蛮治蛮”的羁縻传统,敕授地方民族首领品级不等的职衔,将认同国家治统、顺服国家权力和归附王朝政治的地方民族首领通过“参用土人”为官的方式,纳入国家职官体系,承认其历史影响和地方权威,同意其有限自治,逐步建立、扩大和巩固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统治,确保古代中国在疆域盈缩不定、边疆与邻邦界限不清情况下,能以宽松灵活、务实有效的治理方式,控制和联系边地边疆,促进和增强各民族相互了解,促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向外部辐射影响,[2]体现了“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边疆治理思想与少数民族政策。[3]在此过程中,我国西南等地的民族首领认同元朝续递的国家治统,在强大政治势能下位居“王臣”,保持自身民族和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传统,继续借助朝觐贡纳传统,表其政治归附和体现王臣忠顺,稳固国家与土官、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参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和稳固。
元朝在地方治理中参用土人为官,即设置两条土官,同时敕授其职衔、名号和符信,逐步建立和强化了针对边远地区和民族的国家统治,使按例朝觐皇帝、贡纳方物特产成为维系国家与土官、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流通、利益博弈的手段。云南虎氏傣族首领召依于至元六年(1340)掌控勐卯地方政权,被元朝立为麓川路军民总管府总管,自号思翰法,于至正十五年(1355)遣子莽三赴京朝贡,请求认可其地方统治权力,被国家立为平缅宣慰司,思翰法得职平缅宣慰使。[4]P10《元史·成宗本纪二》记载:大德元年(1297)二月“丙申,蒙阳甸酋长纳款,遣其弟阿不剌等来献方物,且请岁贡银千两及置驿传。诏即其地立通西军民府,秩正四品”。[5]卷19《成宗本纪二》对此,《元史·地理志四》“通西军民总管府”条亦载:“大德元年(1297),蒙阳甸酋领缅吉纳款,遣其弟阿不剌等赴阙进方物,且请岁贡银千两及置郡县驿传。遂立通西军民府。”[5]卷61《地理志四》文献表明:元朝基于边远民族地区首领主动“赴京朝贡”、“来献方物”,诏命设立国家治理机构和任用土人为官,在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建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究其原因,西南等地各民族首领朝贡国家和缴纳赋税,“象征着土官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意味着土官土司地区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6]P39对此,《大定府志·旧事志一》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三月己未,“诏讨罗氏鬼国,以蒙古军六千人、哈剌章军一万人、西海药剌海万军奴军一万人、阿里海牙军一万人,三路并进。六月丁丑,遣吕告蛮部安抚使王阿济,统万户昝坤招谕罗氏鬼国。七月甲子,括蒙古军成丁者敕亦来等率万人入罗氏鬼国。如其不附,则入讨之。九月丁卯,罗氏鬼国阿察及阿里降,安西王相李德辉遣人偕入觐。罗氏鬼国为顺元路宣抚司。十月丁丑,以湖南兵万人伐亦溪不薛。亦溪不薛降。壬辰,亦溪不薛酋病,遣其从子入觐。帝不许。”[7]卷45《旧事志一》元朝凭借军政势能,完成国家政治共同体整合,以数万大军进抵罗氏鬼国,遣发万人军队,不附则讨的态势迫使酋首阿察、阿里降附新朝并朝觐元世祖,完成国家统治秩序建构,使其自身亦得职顺元路宣抚使职。元朝以同样方法将亦溪不薛整合到统一国家,降附元朝的酋首因病“遣其从子入觐”,被元世祖视为不敬顺而“不许”。上述文献显示了元朝整合贵州水西地区到统一国家的军政过程,展示了王权对地方民族首领归附朝贡的干预和影响。
西南等地的地方民族首领慑于元朝强大的军政势能,为获取和保守自身统治地位和利益,认同其续递的国家治统,朝觐皇帝和贡献风物特产,表达顺服国家权力、归附王朝统治的意愿,从而获得敕授的土官职衔,使自己跻身“王臣”,获取元朝认可其地方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对此,《元史·世祖本纪十三》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月丁亥,元中书省臣奏告:“洞蛮请岁进马五十匹,雨毡五十被,刀五十握,丹砂、雌雄黄等物,率二岁一上。”对此,元世祖“有诏,从其所为”。[5]卷16《世祖本纪十三》文献表明:洞蛮等慑于国家强盛,主动提出“请岁进马”并“二岁一上”。元世祖代表国家,认可朝觐贡纳的行为和请求,显示中央政府与地方土酋的政治互动。另外,同年十二月“丙戌,八番洞官吴金叔等以所部二百五十寨民二万有奇内附,诣阙贡方物”。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元朝“从葛蛮军民安抚使宋子贤请,诏谕未附平伐、大甕眼、紫江、皮陵、潭溪、九堡等处诸洞猫蛮”。“八番都元帅刘德禄言:‘新附洞蛮十五寨,请置官府以统之’。诏设陈蒙、烂土军民安抚司”,同年二月甲子,黑蛮等归附入贡元朝,亦表明西南等地的地方民族首领主动归附元朝,显示了国家权威的巨大影响。[5]卷17《世祖本纪十四》对此,《元史·世祖本纪十四》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月丙申,“四川行省以洞蛮酋长向思聪等七人入朝”;同年十一月丙戌,“提省溪、锦州,铜人等洞酋长杨秀朝等六人入见,进方物”。至元三十年(1293)正月丙子,“西番一甸蛮酋三人来觐。各授以蛮夷军民官,仍以招谕人张道明为达鲁花赤”。[5]卷17世祖本纪十四《元史·泰定帝本纪一》亦载:泰定二年(1325)二月丁亥,“平伐苗酋的娘率其户十万来降,土官三百六十人请朝”。[5]卷29《泰定帝本纪一》
非惟慑于国家权威主动归附朝贡,西南等地的民族首领亦出于提高政治威望、品级职衔而朝请贡献。《元史·成宗本纪一》记载: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云南部长适习、四川散毛洞主覃顺等来贡方物。升其洞为府”。[5]卷18《成宗本纪一》地方民族首领通过朝贡,被元朝用提升土官职衔品级的方式予以鼓励,也诱导更多土官认同国家和归附王朝。因此,元代西南等地的民族首领归附元朝,国家不仅确认其地方统治权力的合法性,甚至提升其职衔品级以示笼络奖劝,甚至诱使土官遇重大庆典和喜庆节日等主动赴京朝贡,加强自身与国家的联系,表明尊顺国家权威的意愿,借助国家王权巩固土官政治和保有统治利益,显示了国家权力对地方民族事务的干预和影响。《元史·成宗本纪二》记载:大德二年(1298)九月己丑系“圣诞节”,皇帝于“驻跸阻妫之地,受诸王、百官贺”,有“交趾、爪哇、金齿国各贡方物”。[5]卷19《成宗本纪二》事实上,元朝对西南等地前来朝觐贡纳的民族首领敕授品级不等的职衔,地方事务治理“参用土人”,利用其历史影响逐步建立间接的国家统治。因此,西南等地的地方民族首领认同和归附元朝,主动朝觐贡纳而跻身“王臣”,朝贡成其提高政治威望、巩固地方统治甚至设置土官的前提。《元史·地理志四》“金齿等处宣抚司”条指出:“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朝贡。二年(1261),立安抚司以统之。”[5]卷61《地理志四》正是由于中统初年“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朝贡”,元朝于其“朝贡”次年“立安抚司以统之”,可见金齿等宣抚司的设置前提是地方民族首领先期朝贡国家,表达认同和归附元朝的政治意愿。
作为国家回应,元朝在西南等地的治理中任授土人为官,利用土官政权对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建立间接的国家统治,显示了地方民族首领朝贡皇帝与国家建立土官政权的先后关系,体现了国家与土官、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互动,也揭示了地方民族首领归附国家、朝贡纳赋的原因在于保有统治地位和利益。泰定三年(1326)二月癸丑,“八番岩霞洞蛮来降,愿岁输布二千五百匹。设蛮夷官镇抚之”。同年八月癸亥,“湖广行省太平路总管郭扶、云南行省威楚路秃剌寨长哀培、景东寨长阿只弄男阿吾、大阿哀寨主弟你刀、木罗寨长哀卜利、茫施路土官阿利、镇康路土官泥囊弟陀金客、木粘路土官丘罗、大车里昭哀侄哀用、孟隆甸土官吾仲并奉方物来献。以昭哀地置木朵路一、木来州一、甸三,以吾仲地置孟隆路一、甸一,以哀培地置甸一,并降金符、铜印,仍赐币帛、鞍勒有差。”[5]卷30《泰定本纪二》以上史料表明:元代湖广和云南等行省的地方民族首领先行朝觐皇帝“并奉方物来献”,表达归附国家、输纳方物的意愿,换得国家在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设置土官政权,以建立间接的国家统治,被中央政府以颁赐符信、敕授职衔和奖赏钞物等方式确认土官地方统治权力的合法性。
二、元代土官引导性朝贡与其制度化
古今中外都面临着采用灵活务实的统治方式和创新国家治理制度、将最广大人口和地区整合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问题,而羁縻统治及其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应对边远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策略之一。宋元交替,统治者面临着继承政治文化遗产、续递国家治统及创新国家制度的境况,故承认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民众的发展差别而延续羁縻统治传统、任用土人为官以治理地方事务、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成为务实可行的统治策略。因此,元朝接受、认可和调控土官朝觐皇帝、贡献风物特产的行为,视为是否认同国家治统、顺服国家权力和归附王朝社稷的基本条件并予以鼓励、罢免甚至惩戒。与此对应,土官跻身“王臣”,朝贡往来实即元朝国家整合与治理体系能力建构完善及西南民族首领国家认同与政治归附的产物和重要方面,具有强化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的作用。同时,国家权力的干预,使贡期、物品及规模等方面形成惯制,土官朝贡从“因俗随性”到“定期按例”的转变则标志着元代土官朝贡完成了制度化,体现了元朝的国家整合与王权干预,是国家治理体系能力建构完善的手段和内涵;限制性朝贡成为元代土司制度的重要方面,是元朝创新国家制度,建构统一国家、建立治理体系能力和开发民族地区的产物,对我国土司制度、明清土司朝贡及其制度兴废与西南土司政治等具有重要影响。[2]
(一)额定土官朝贡义务
元朝对顺服王权、认同治统的地方民族首领规定朝贡义务,显示了国家权力对地方治理和民族事务的干预和影响,为元朝强化国家整合和推进地方治理的成果。
宋亡,播州土司归附元朝,被元朝强制额以定期朝贡的义务。《元史·世祖本纪五》指出:至元十二年(1275)十二月己亥,佥书四川行省枢密院事昝顺奏告朝廷:播州安抚杨邦宪等“未知逆顺”需要“降诏”招抚,使之“自新并许世绍封爵”。[5]卷8《世祖本纪五》元世祖对此“从之”,“遣使者诏邦宪内附”。《遵义府志·土官志》记载:在元朝隆州同知赵孟烯“赍诏招谕”下,播州土官邦宪在至元十四年(1277)“愿纳土内附”,“捧诏三日哭,表以播州、珍州、南平军三州之地降”,“遣使纳款”,得元世祖“玺书”,授职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抚使,虽“充质子入侍”,但于至元十八年(1281)升职宣慰使并规定朝贡义务。[8]卷31《土官志》《元史·世祖本纪八》记载:至元十八年(1281)八月丁巳,元世祖“命播州每岁亲贡方物”。[5]卷11《世祖本纪八》播州土官朝贡义务的个案表明:元朝对西南等地的民族首领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力和政治吸引力,在整合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逐步明确规定土官朝贡的义务和时间,表明国家统治秩序得以在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中建立和巩固,显示了国家与土司、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的中心―边缘、主体―客体关系和国家权力对地方民族事务的影响。
由于“厚往薄来”朝贡传统的影响,元朝接受甚至规定土官朝贡。为政治笼络和强化王朝国家与地方民族首领的关系,或提升土官职衔品级,或给予高额奖赐,使西南等地的土官争相朝贡京师,以致出现某些朝贡遭到国家的禁止。《元史·成宗本纪四》记载:大德七年(1303)二月,元朝诏“禁诸人非奉旨,毋得以宝货进献”[5]卷21《成宗本纪四》。这更加突出了王权对土官朝贡的干预和影响。
(二)规定土官朝贡时间
元代土官的朝贡时间逐渐形成一年、二年、三年等的定例,但这样的“例贡”亦“各地土官土司不同,因物因地而异”。如前所述,元代播州土官的朝贡时间是被皇帝诏命“每岁亲贡”。但是,元代土官按期朝觐皇帝、贡纳方物的例贡还有二年一贡、三年一贡的差异,其形成和确定是西南等地的民族首领自我请求和国家确认的结果。《元史·世祖本纪十三》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月丁亥,中书省臣奏告:“洞蛮请岁进马五十匹,雨毡五十被,刀五十握,丹砂、雌雄黄等物,率二岁一上。”元世祖对此“有诏,从其所为”,朝贡时间被确定为二年一贡。[5]卷16《世祖十三》元代土官的朝贡时间可由土官本人提出,奏告皇帝后被确定下来,但也可由元朝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确定。《元史·顺帝本纪二》记载: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十二月戊戌,“立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并总管府。先是,世祖既定缅地,以其处云南极边,就立其酋长为帅,令三年一入贡。至是来贡,故立官府。”[5]卷39《顺帝本纪二》对此,《元史·百官志八》亦载:“邦牙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元四年十二月置。先是,以缅地处云南极边,就立其酋长为帅,三年一贡方物。至是来贡,故改立官府以奖异之。”[5]卷92《百官志八》
另外,新君即位、皇亲生日和国家仪典等都是元朝重要的场合,也是西南等地的民族首领朝觐皇帝以展现国家认同、政治归附的契机,各地势力、职衔较大的土官逢遇重大庆典、节日要赴京朝贡,因时无定准,具有临时加贡的性质,成为特殊的土官朝贡形式,被明清土司朝贡制度固定下来。但是,元朝由于西南民族地区远离京城,为体恤土官朝贡遥远,更兼降低朝贡成本和减少惊扰沿途民众社会,因此要求土官加贡须报请批准,才能进京朝贡。由此可见,元代土官不论诏定或临时自加朝贡,都受到王权的影响,元朝皇帝根本性地决定了国家对地方民族首领的政治态度和朝贡时间。
(三)限制土官朝贡人数
在国家定鼎之初,元朝在统一国家政治共同体建构中,延续历朝以来的羁縻统治传统,接受西南等地民族首领的朝贡,消受土官认同国家治统、顺服国家权力和归附王朝的自豪,朝觐管理宽松,并不限制朝贡人数规模,但为体恤朝贡艰辛和沿途惊扰等禁止过多人数的朝贡。《元史·泰定帝本纪一》记载:平伐苗酋的娘于泰定二年(1325)二月丁亥“率十万户来降附”,“土官三百六十人请朝”结果,“湖广行省请汰其众还部,令的娘等四十六人入觐”,被皇帝应以“从之”。元朝限定土官朝贡人数过多具有示范性,尤其明清等朝落实得更加严格。[5]卷29《泰定帝本纪一》
(四)奖劝土官朝贡行为
朝贡是我国历朝处理自身与周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方式和制度,对土官朝贡延续“厚往薄来”的奖劝传统,体现国家和皇帝对边远民族的恩情和仁爱。
土官朝贡系元朝国家整合与治理体系能力建构完善的产物,皇帝根据不同境况,蠲免西南等地民族首领的贡赋义务,显示了国家恩典。《元史·成宗本纪二》记载:大德元年(1297)六月甲寅,“罢亦奚不薛岁贡马及氈衣”。[5]卷19《成宗本纪二》对此,《大定府志·旧事志一》亦载:大德元年“六月甲寅,罢亦奚不薛贡马及毡衣。”[7]卷45《旧事志一》《大定府志·旧事志一》指出:英宗至治三年(1323)“正月癸巳朔,八番洞蛮酋长遣使入贡……十二月丁亥,免八番顺元差税一年。”[7]卷45《旧事志一》不过,《元史·英宗本纪二》只云“(至治)三年春正月癸巳朔,暹国及八番洞蛮酋长各遣使来贡”,[5]卷28《英宗本纪二》未言免除差税事,个中缘由仍需考证。
我国历朝尊重边远民族地区的物产资源及生产状况,并未强制规定朝贡物品,长期形成并保持“随其所出”的朝贡惯例。元朝继续利用朝贡体制来加强国家和西南等民族地区与各族土民及其首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允准土官朝贡表达国家认同和王朝归附的意愿,接受其方物特产的贡献。文献表明,元代西南等地多有土官利用风物特产朝贡国家,马匹牲畜及副产品和地方性动物成为重要的朝贡物品。水西和播州等地具有悠久的畜牧传统,各民族蓄养羊马牛等大型牲畜,“水西马”、“播州马”等甚至成为国家军马的来源之一,马匹是四川、云南和湖广土官朝贡国家的物品。《元史·成宗本纪三》记载:大德五年(1301)二月己亥,“永宁路总管雄挫来朝,献马三十余匹”。[5]卷20《成宗本纪三》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月甲子,“金竹酋长骚驴贡马、氈各二十有七”,被元朝“从其请,减所部贡马,降诏招谕之”。另外,元朝也要其进贡风物——“精善”的硃砂、雄黄,但宽松地规定“无则止”。[5]卷17《世祖十四》《元史·世祖本纪十三》亦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二月戊寅,“播州安抚使杨汉英进雨毡千”。[5]卷16《世祖本纪十三》云南等地是我国大象等大型动物的生息之地,各民族亦驯育大象贡献国家。《元史·成宗本纪一》记载:至元三十一年(1294)六月,“云南金齿路进驯象三”;同年十二月,曲靖、澂江、普安等路夷官各以“方物”来贡。[5]卷18《成宗本纪一》《元史·仁宗本纪二》记载:延祐二年(1315)十月癸卯,“八百媳妇蛮遣使献驯象二。赐以币帛。”[5]卷25《仁宗本纪二》《元史·文宗本纪四》记载:至顺二年(1331)二月甲戌,“云南景东甸蛮官阿只弄遣子罕旺来朝,献驯象”。[5]卷35《文宗本纪四》对元代土官土司利用其他风物特产朝贡国家,《大定府志·旧事志一》记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九月庚子,“鬼国遣使献方物”。“至大四年(1311)五月戊子,罗鬼蛮献方物。”[7]卷45《旧事志一》另外,元朝鉴于按例奖赐的财政压力、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物产资源状况,干预土官朝贡物品的品种、数量等,不允准随意增减贡物数量,显示了国家权威对地方民族首领朝贡的影响,是土司朝贡制度化的重要方面。《元史·睿宗传》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乌蒙宣抚司进马,逾岁献之额”,被太子晓谕“勿多进马”。[5]卷115《睿宗传》
元朝延续历朝“厚往薄来”的朝贡传统,采取“宜厚其赐,以怀远人”的策略,对土官朝贡予以奖励性的回赐,鼓励和劝导西南等地民族首领朝贡皇帝和认同国家的行为。《元史·世祖本纪九》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二月丁未,“定安洞酋长遣其兄入觐”,被国家“敕给驿马”。[5]卷12《世祖本纪九》《元史·世祖本纪十四》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月,元世祖接受金竹酋长的朝贡,“从其请,减所部贡马”,也“赐新附黑蛮衣袄,遣回”。[5]卷17《世祖本纪十四》《元史·成宗本纪一》记载:元贞元年(1295)三月丙辰,金齿夷洞蛮朝觐皇帝,被“赐衣遣之”。[5]卷18《成宗本纪一》《元史·成宗本纪三》记载:大德五年(1301)二月己亥,“永宁路总管雄挫来朝,献马三十余匹”,被元朝“赐币帛有差”。[5]卷20《成宗本纪三》《元史·仁宗本纪一》记载:至大四年(1311)二月丁卯,“思州军民宣抚司招谕官唐铨以洞蛮杨正思等五人来朝,赐金帛有差”。[5]卷24《仁宗本纪一》《元史·仁宗本纪二》记载:延祐二年(1315)十月癸卯,八百媳妇蛮遣使贡献驯象二匹,被国家“赐以币帛”。[5]卷25《仁宗本纪二》《元史·仁宗本纪三》记载:延祐五年(1318)八月丙寅,“广西两江龙州万户赵清臣、太平路总管李兴隆率土官黄法扶、何凯,并以方物来贡。赐以币帛有差。”[5]卷26《仁宗本纪三》泰定三年(1326)八月癸亥,元朝“赐大车里新附蛮官七十五人裘帽靴服”。“湖广行省太平路总管郭扶、云南行省威楚路秃剌寨长哀培、景东寨长阿只弄男阿吾、大阿哀寨主弟你刀、木罗寨长哀卜利、茫施路土官阿利、镇康路土官泥囊弟陀金客、木粘路土官丘罗、大车里昭哀侄哀用、孟隆甸土官吾仲并奉方物来献。以昭哀地置木朵路一、木来州一、甸三,以吾仲地置孟隆路一、甸一,以哀培地置甸一,并降金符、铜印,仍赐币帛、鞍勒有差。”[5]卷30《泰定本纪二》
元朝根据“厚往薄来”的恩赏原则,还对西南等地的土官给予稀缺物资或其他优厚待遇,以示对地方的肯定和鼓励,以至赏赐朝贡成为土司朝贡制度的内涵之一。《元史·成宗本纪二》大德元年(1297)五月戊辰,元朝“追收诸位下为商者制书、驿券”,但于戊申“给葛蛮安抚司驿券一”。[5]卷19《成宗本纪二》根据元朝驿传制度,驿券是用于乘用驿站车马、使用夫役的凭据,具有调用资源、快速通关的便利,国家给予土官驿券,具有奖劝鼓励的意味。由于“黔地无盐”,水西等地的食盐因获取渠道单一、数量有限而倍加珍贵,国家向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配给食盐成为笼络民族首领的措施。《大定府志·旧事志一》记载:至顺二年(1331)“十一月壬申朔,令四川行省给亦奚不薛官牧盐。”[7]卷45《旧事志一》对其缘由,同书卷47《旧事志三》记载:至顺二年(1331)十一月壬申,云南行省奏称“亦溪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忽叛乱,盐不可到,马多病死”。于是,元朝“诏令四川行省以盐给之”。[7]卷47《旧事志三》食盐是亦溪不薛等地马匹健康的保障性物资,元朝的食盐供给程度关涉水西亦溪不薛等地畜牧业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地方民族首领即土官的统治利益。元朝诏令将战略性物资食盐供给水西等地,充分保障土官的利益,是奖劝地方民族首领朝贡的手段,体现了国家的恩遇宽仁。
三、结语
朝贡制度是我国历朝处理周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重要制度,藩属国按时如例朝贡宗主,表其国家认同与王朝归附的意愿,封建王朝也通过奖励性回赐将恩典泽被四方。元朝续递历朝治统,承认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民众的发展差别,继承政治文化遗产和中华民族制度文明,在大一统历史框架和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以强大军事威慑和政治吸附为基础,延续羁縻统治传统,在地方治理中参用土人世代为官,将更广大民族和地区整合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间接的国家统治。在与元朝的权力互动与利益博弈中,西南等地的民族首领即土官通过朝觐皇帝、贡纳风物特产的方式,表达认同国家治统和归附元朝政治的意愿,但元朝对土官朝贡义务、时间、人数的规定和限制及奖劝等显示了国家权力对民族地区与各族土民的干预并逐渐实现制度化,成为元代土司制度的重要方面,是明清两朝土司制度与西南等地土司朝贡的历史经验,为中国土司朝贡制度的早期形态。由此可见,元代土司朝贡制度的形成背景是元朝军政势能下的国家建构整合,或因制度草创,统一国家的政治吸附与文化吸引尚欠充分,为明清土司制度与土司朝贡制度的健全完善留出了空间。这是我们研究土司朝贡制度必须看到的。
[1]付百臣.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2]方铁.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2):68-80.
[3]彭建英.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略论[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04-108.
[4]中国政协会议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德宏土司专辑[G].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1997.
[5](明)宋濂.元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本,1986.
[6]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7](清)黄宅中.大定府志[M].毕节:贵州省毕节地区档案局,1982.
[8](清)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M].遵义: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出版,1986.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 Tusi Officials’Paying Tribute System during Yuan Dynasty
PENG Fu-rong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ety,Economy and Culture along Wujiang Basin,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8100,China)
Following the previou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Yuan Dynasty,on the basis of its strong military base,continued the Jimi policy towards the ethnic groups,allowed the people from Tusi areas to be officials and approved of the paying tribute system by Tusileaders,forming an integrated part of Tusi system during Yuan Dynasty.However,the Tusioffical’s paying tribute system was not a fully-fledged one because of polical,cultural and systematical reasons at that time,leaving a large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in the period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while its research needs to be deepened in the future.
Yuan Dynasty;country;integration;Tusi;tribute;system
K247
A
1009-3583(2017)-0017-06
2017-3-12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乌江流域历代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10XMZ013)的成果之一;长江师范学院立项建设学科民族学特别委托项目“明清时期土司朝贡制度与国家认同研究”(2017TSW02)的阶段性成果
彭福荣,男,重庆涪陵人,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主要从事民族历史和地域文化研究。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