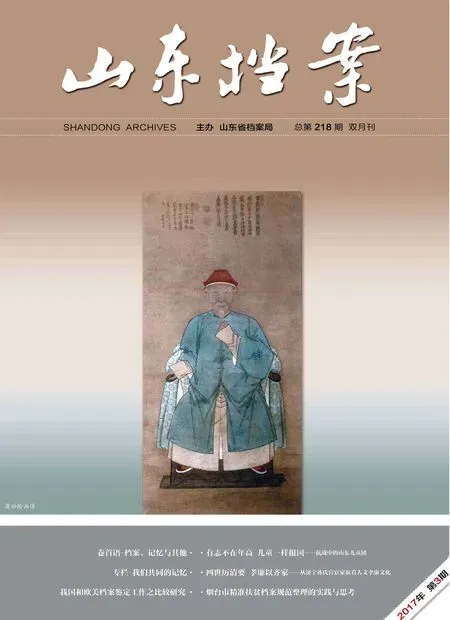管理学视域下的高校人物档案管理与服务
文·刘忠华
管理学视域下的高校人物档案管理与服务
文·刘忠华
随着各高校档案馆信息化与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各高校逐渐将人物档案的管理纳入视野范围之内。高校的“人物档案”是指人物在高校长期教学、科研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保存、利用价值的、不同载体的各种文字、声像材料和实物。包含创作手稿、演讲稿、文章、报告、回忆录、传记、书画、日记、著作、证书、信函、作品、藏品、照片、音频资料等内容,具有私人属性明显、形成时间长、档案价值大等特点。目前,为高校优秀人才建立人物档案,充分开发人物档案信息资源,激发其他教师和学生的学术热情、传承和发扬科学文化成果,维护学校和个人的学术历史地位,已经成为诸高校档案馆建立人物档案的共同诉求。
一、高校人物档案管理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人物档案资料的征集比较困难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物档案的主要来源是“人物”(或者其亲友,统称资料所有人)手中的个人资料。一般采取“移交”“捐赠”“寄存”“征购”“复制”等收集方式。部分档案意识比较强的资料所有人理解并能支持档案馆的工作,愿意采取不同的方式将其资料归入档案馆,由档案馆集中管理;也有部分资料所有人对档案馆的这一举措表示拒绝或者置之不理。
从管理学上讲,资料所有人也是“理性经济人”,行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基本特征,即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有独立的追求目标及采取一切可能的行为与方式追求目标。因此,“所作出的社会选择和社会行动最原初的动力来自于人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和理性追求”[1]。在档案馆向其征集个人资料时,自然会权衡“交”与“不交”所带来的利益得失。他们认为,资料存放在自己手中比较安全放心,今后查找利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再加上部分资料里还可能包含相当大的经济价值和经济利益。将资料交到档案馆多是无偿的,资料所有人看不到明显的“利好”(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即便档案馆是通过“征购”的方式来收集资料,资料所有人的收益也是有限的。部分资料所有人甚至揣测此举虽然对学校有一定利益,但更多的是相关管理者为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而做出的一种决策。
从法律上讲,人物档案是属于资料所有人的个人私有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2]。 资料所有人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将资料交给档案馆,都意味着档案所有权不同程度的分离,要放弃部分权利和利益。再者,通常高校针对人物档案的征集所发布的《人物档案管理办法》没有强制力,更无法对不执行的行为做出处罚性措施,所有权人有权选择不放弃资料所有权。[3]
从情感上讲,人物档案是其劳动与心血的结晶,是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与见证,对资料所有人来说是独一无二、意义特殊、极其珍贵的,的确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
(二)人物档案管理的相关配套制度不够完善
不少高校档案馆都制定了相关的人物档案管理办法,甚至不少省市的档案馆都制定了相关的法规来征集辖区范围内的名人档案。笔者在仔细查阅了这些相关的人物档案的管理法规和规范后,发现虽然法规都对收集范围、征集方式、整理和保管方式、利用、权益责任、奖惩等方面做出了规定,但都是原则性的强调,在具体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特别对于如何具体执行找不到正式的解释与说明。比如“对在人物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或者捐献重要、珍贵档案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给予奖励,并颁发证书”[4]。那么,如何界定“显著成绩”?档案的“重要”或“珍贵”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界定?奖励的金额标准是多少?奖励证书由学校来还是由档案馆来颁发?档案所有人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明白透彻的了解,自然无法理解学校建立人物档案的苦心,更不会消除疑惑与戒心来支持和配合这项工作。
(三)档案管理的文化理念落后
事实上高校人物档案管理存在的大多数问题,最终都可归结为文化问题。绝大多数档案管理者的逻辑出发点是,这是一件对学校、对“人物”个人都有利的事情,我们是替学校来收集、管理人物档案的,因此所采取的手段也是通过行政命令——发文来进行的。他们所关心的是采取何种方式能从个人手中征集到更多的资料,采用何种方式能将资料保管好,并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快捷地提供查询服务,人物档案管理工作到这儿就基本完成了大半。这是一种典型的“管制型”的管理理念,强调的是“管理”。这种传统的档案管理文化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物”上,注重的是档案资料的增量变化,追求的是数量上的增加,以为有变化就是有发展。再加上外界在对高校人物档案管理水平进行评判时,也往往将件数或者卷数,即档案的数量或者规模,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在这种文化理念熏陶下,档案所有人也养成了一种习惯于“服从管制”的理念,即使不赞同管理内容,也不会质疑这种“管制”模式的合理性。
(四)人物档案管理的手段落后
在“信息为王”的社会环境下,建立数字化档案馆是高校档案馆的发展趋势。然而,档案馆作为高校的一个基层组织,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没有明显的话语权,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方面自然不会受到足够的重视。档案资料的征集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比如暂时收集不上来的人物档案,需要采用借出复制、拍照的办法进行收集;对重要的人物档案进行有偿征集,或给持有人适当的物质奖励;通过多种渠道购买与人物相关的已出版发行的部分档案资料。此外,档案馆需要配备足够的基本硬件设施,以确保人物档案的存放安全合理,增加档案所有人对档案馆的信任。大多数高校对人物档案的管理手段比较落后,数字化过程举步维艰。这都阻碍了人物档案管理的健康迅速发展,也不利于档案馆向外界提供优质、全面的服务。
二、高校人物档案管理困境的治理对策
(一)更新档案管理理念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在我国的社会全面转型期,政府正在由“管制型”向“服务型 ”转变,公共管理正在取代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以服务为本,强调以公众为对象,引入竞争机制,以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提高政府的能力与效率,使公众获取更多高质量服务。[5]基于公共管理理念的高校档案馆也应该适时转变职能与角色,强调以公众为本和服务至上。
档案馆要以满足公众的档案需求为目标,提供多种形式的档案服务。根据公众的思想和行为规律去激励、引导他们为档案馆的发展做出贡献。让公众理解,建立人物档案也是档案馆为他们提供的一种服务内容,他们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激发自己,宣传自己,实现自己。
档案馆的管理者要摒弃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认清档案馆存在与发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公众提供服务。同时,也要调动档案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全面提高档案工作者的各方面素质与提供服务的能力。
(二)公众参与是解决人物档案管理困境的关键
新公共服务理念倡导“充分重视民主、公民权和为公共利益服务”,将公众参与引入公共权力机构的管理过程,使之真正成为满足公众需求的服务者。[6]高校建立人物档案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学校、服务师生、服务社会。人物档案的建立不仅仅是档案馆的事,而是与学校相关的每一个人共同利益的聚合。人物档案如何建立,如何利用,档案馆提供何种服务,都应该通过广泛的对话来吸引校内外师生员工与校友的广泛参与,吸收部分相关人员参与到人物档案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形成大家共同参与,共同管理的局面。
奥尔森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一种“选择性激励”来驱使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参加集体行动。[7]即在集体行动中区别对待积极参与和消极不参与的两种人,奖励积极参与者来示范诱导其他人采取相同的行为,促使公众形成强烈的参与意识,从而促进集体行动。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奖励积极参与人物档案管理的那部分公众,从而带动其他人的参与。比如,笔者所在的学校孙长林先生,毕生致力于民间工艺美术和文化的收藏与保护,在书画、陶瓷、民艺等领域收藏颇丰,晚年把自己毕生所藏的4646件藏品无私捐献给了学校,其中不乏国家一级文物,其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难以估量。学校在接受捐赠藏品时为此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宣传赞扬了孙老的义举,并专门成立孙长林艺术收藏馆存放这些实物,供师生、学者、广大社会人士参观与研究。“孙长林艺术收藏馆” 不仅成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学校的文化名片。
(三)提高档案馆的服务与管理能力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档案馆不仅要有优良、安全的资料保管环境,较高素质的工作人员,还必须要有先进的管理手段和多样的服务内容。采用信息管理系统,整合档案信息资源,实现人物档案的数字化管理和网上查阅功能,构建档案利用的平台,建立人物档案数据库,通过网站展示本校名人,也是学校的对外宣传窗口。同时,还要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配合,大力进行网络资源建设,全面实现人物档案资源共享,为高校及社会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最优质的服务。档案工作者还要利用手中的资源,针对公众的需求,进行深层次的开发与编研,提供深层次的文化服务。
(四)扩大档案宣传,增强档案意识是解决问题的重点
社会公众对档案的认识需要有潜移默化的过程,对档案意识的培养也应是循序渐进的。要通过多种渠道和宣传载体加大档案宣传,向公众宣传人物档案的价值,使参与档案管理的观念深入人心,让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生成主动保管档案、移交档案的意识。对捐赠档案资料影响较大的,要举行相应的捐赠仪式并颁发证书,以扩大社会影响。像前面所提到的孙老先生捐赠大仪式,就是一种很好的档案宣传方式。也正如孙长林老先生所说:“我认为,能够以个人的力量,将散落于民间的艺术品挖掘、收集和整理出来,返还于社会,以系统的艺术载体的形式返还于现代设计艺术教育,才是艺术品最好的归宿。”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所体现出人格力量、学术境界、文化精神,在激励与感召师生与社会的同时,也完美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即完成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提到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总而言之,从人物档案的建立到实现数字化管理,是高校档案馆服务和管理水平提高的具体体现。通过人物档案的管理,让更多的公众了解认识到档案的重要性,增强档案意识,使公众认识到建立人物档案是对各方都有利的大事,个人的宝贵财富只有最终交给学校,由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才是个人一生心血的最好归宿,这也是我们进行人物档案管理的价值追求。
●
[1]赵成根.经济人假设在公共领域的适用性论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12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1条
[3]杨立人.档案所有权的保护与限制[J]档案学通讯,2007(3).
[4]《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物档案管理办法》
[5]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6]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7]奥尔森(美).《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