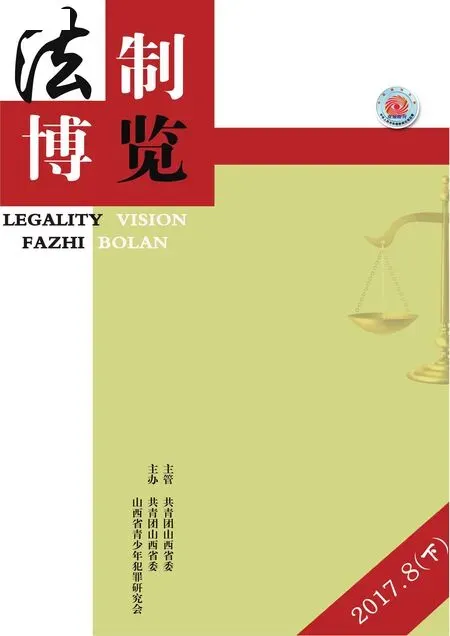宪法的批准
——反联邦党人的权力观——以观念的冲突为视角
王振宇
西北民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30
宪法的批准
——反联邦党人的权力观——以观念的冲突为视角
王振宇
西北民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30
反联邦党人在宪法批准的过程中分别从新政府的性质、权力的混合与制衡、权力的来源及权利法案的缺失等几个方面对于新宪法提出了质疑。其与联邦党人的“冲突”根源于双方权力观念上的差异。反联邦党人认为权力本身即是“恶”,其根本没有为善的可能性。而宪法的支持者们认为只要设计良好,制度可以“驯化”权力。这样,在对权力的制衡和权利的保障问题上,反联邦党人最终诉诸体现着经验主义的“民主”原则,而联邦党人最终诉诸于体现着建构理性的“法治”原则。
反联邦党人;1787年宪法;权力观念
单从“联邦”一词的本意上讲,或许“反联邦党人”才是真正的“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们将州视作保卫人民自由与权利的基础,认为“州”才是真正的“主权体”,而新宪法的内容实际上并不能够被称之为一个“联邦的”宪法。
一、新政府的性质
反联邦党人的第一个批评就是,按照宪法草案成立的“联邦政府”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单一的全国性政府。它将使各州的联盟变成一个大共和国,它享有巨大、广泛且不受有效控制的权力。
首先,在立法方面,国会有着完全的立法自主权。其被授予了创制宪法所赋予的“上述及其他权力”所必要和适当的所有法律的权力,也并不需要考虑州的意见。这样一来,联邦政府实际上可以制定并执行所有法律。
其次,司法权被授予一个最高法院及依照国会颁布的法令设立的若干下级法院。联邦法院系统获得了独立于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巨大的、不受控制的权力。权力天然就具有扩张性,司法权概莫能外。宪法中随处可见的笼统的、模棱两可的条款则无疑赋予了法院通过宪法解释而不当膨胀自身权力的可能,非民选的联邦最高法院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联邦政府”①。
反对者们认为共和国应该限于狭小范围,“单一的大共和国”无法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因为人民只能依靠代表来“代理”自己的意志。这样,政府在进行管理时,要么会因为法律及武力的鞭长莫及而饱受地方战乱与分崩离析之痛,要么就只得借助于常备军队的威严而勉强维持其联邦政府表面上的和谐与统一。这个“共和国”既无法解决代表的代表性问题也根本无法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最终它将会变成自由的牢笼。
二、权力的混合
反联邦党人所质疑的第二点就是各个权力之间的犬牙交错的状态。
首先,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职能上部分的重合了。国会享有宪法所授予的全部立法权。但国会所通过的议案或命令、决议、表决均需要总统予以签署或批准。并且,总统还享有实质意义上的“否决权”。副总统这一职位并无什么必要,但却直接被新宪法指定为参议院议长。虽然其仅仅在表决出现僵局时才有投票权,但这个机制本身就使得行政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渗透到了立法权中。
而根据新宪法的规定,总统在任命合众国的重要官员及驻外使臣时,均需要向参议院咨询并取得其同意。这无疑使得参议院掌握了部分的人事任免权。此外,国会还将其权力的触手伸向了司法权。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独自享有着弹劾权和对弹劾案的排他的审判权也令反联邦党人感到无法接受。
反联邦党人旗帜鲜明的提出:“(有一项原则)任何自由政府没有它就不能存在,那就是政府各个部门的分权”。若是两个部门的权力有了交叉,那二者的利益就会像他们的权力那样也合而为一。
其次,权力的混合将导致责任主体的不明确。有权无责的状态要么使得权力恣意妄为,要么就使得其自身在相互斗争中寸步难行。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自由都将无处容身。
在他们看来,人为地把政府的运作复杂化,将使得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复杂滥用权力、蒙蔽人民,进行权力投机。对此,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使得立法权独立于另外两权,并且通过短暂任期、强制轮换及选举制度使得人民始终掌握着“最终的选择权”。
最后,反联邦党人认为,依靠通过精心设计的复杂政府中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和权力的相互冲突来实现全体的共同利益,实在是太高估人类的理性和智慧了。即使它能被设计出来,在其运行和权力的每一次行使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客观的学识、努力、天分等差异会一点点的打破这个被设计出来的“平衡”,机构之间的差异会逐渐显现并被不断放大和固化。
三、权力受制于人民
在反联邦党人看来,权力制衡的核心在于使得享有权力的人不能滥用而作恶,而这必须依靠人民主权原则来实现。
对立法机关的组成,批评集中在众议员所代表的选民人数和参议院议员的贵族制倾向上。第一,对于新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反联邦党人不无担忧地问道:“…如果有一天…国会让我们每4万所人选出一名代表,难道不也符合宪法吗?②”最终,“众议员将最终被减少到不过13名…这与另一条款的措辞显示的可能性正相契合…③”
第二,参议院的议员任期太长且其缺少有效的轮换机制。依照新宪法,参议员的任期有六年之久。
第三,参议员由州议会而不是人民选出④,这就使得议员与人民隔离开来。不仅如此,参议院还独自享有对弹劾案的审判权。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代表着民主制度的众议院的弹劾权被完全架空。
第四,在授权的范围上,新宪法赋予了参议院以修正由众议院提出的征税议案的权力。而“…英国议会中与之类似的那个院,永远也不会得到这项权力。”
四、权利法案
对此问题,争论集中在通过列举的方式声明权利“是否必要”。联邦党人认为这毫无必要。因为“宪法”本身就是一部“权利法案”。“联邦政府”是由各州所创制的,其所享有的权力均是“授予”的,这种授予直接以列举的方式体现。若再加进权利法案的内容,就无异于是画蛇添足地规定:不得限制表达自由、不得要求过重的保释金、不得课以过高的罚金等等……这难道不是将众多原本未授予政府的权力又“额外”的授权给政府了吗?难道不是为意欲侵犯人民权利的政府大开方便之门吗?
宪法的反对者们对这样的解释和诘问表现出不屑一顾和深深的不信任。首先,宪法并非像其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仅仅包含着授权的规定。例如,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不得中止人身保护令的特权,除非发生叛乱或入侵时公共安全要求中止这项特权…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或溯及既往的法律…合众国不得授予贵族爵位。”他们问道,既然未授权,那么为什么又限制其本就不享有的权力呢?这只能解释为,若不加以限制,则政府将概括的拥有这样的权力⑤。
其次,支持者们口中所谓的“保留的权利”实则仅仅在少数国家确立并被享有,(它们)几乎可以说是“英美法的特殊现象⑥”。由于有例外的规定和兜底性条款的存在,“权利法案”的明确规定可以说是必须的内容了。这比“无凭的口说”要更加可靠、更加能够强化自由所依赖的那些原则。
总的来说,反对者们认为,这一部宪法的架构就决定了其根本无法保障“未与授权即保留”这一原则。不仅如此,州宪法已经成为了“下级法”的一部分,一旦涉及到了权利的争议,即使是州宪法对人民的保护也会被宪法体制本身所摧毁。因为,联邦法院法官及各州的法官均要受本宪法及依照本宪法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的约束,州宪法实际上就无法为自己的人民提供法律上的保护了。
五、权力及权利观念的冲突
通过以上四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反联邦党人们对于权力的观念。
第一,在权力的来源方面。联邦党人认为,依照本宪法,人民主权原则得到了良好的实现,而反对者们则质疑这一论断。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后者成为了州权坚定的支持者。这也解释了这样一对矛盾:为什么联邦党人明明散发着强烈的精英主义气质,却又坚持要将联邦政府的最终权力来源追溯到每一名公民身上;为什么反联邦党人明明是主张卢梭式的“人民主权”,但又不遗余力的维护和保全州的权“利”。
正是因为联邦党人相信这一理性的制度可以真正实现“人民”的意志,所以使得宪法的效力直接来源于每一个公民就可以让新建立的政府强大到足以摆脱州的掣肘;而恰恰因为反联邦党人认为这部宪法无法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所以竭力使得州保有已经享有的相当程度的主体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
第二,在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和分权制衡方面,反联邦党人宣称除非政府的权力范围清晰明确并相互独立且毫无争议,否则其将成为逐步吞噬人们自由的恶魔。但联邦党人认为控制权力的行使与控制其范围同样重要,而在保障权力自身这一层面上,控制权力的行使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反联邦党人坚持认为愈简单的政府形式愈得长久并运行良好,不似赞成者们那样的寄希望于通过“权力对抗权力”“野心对抗野心”以使得人民坐收渔翁之利。
第三,在权力的外部制约及权利的保障上,反对者们坚持权力必须完全受制于财富相对平等而富有美德的人民。在这样的国度,权利的保障就依靠拥有着“纠错权”的人民自身以及其建立的民主制度。这与联邦党人将立法机关本身视为潜在的暴君并注重法治制度本身的“良好设计”的观念格格不入。通过深入思考,我们发现,两方的根本的差异来源于双方对于权力本身性质的不同观念。
联邦党人信奉的是“理性自身的自由以及追求一个好的可能的自由”。他们认为权力本身就包含着为非的可能,不能为恶的,实际上亦不能为善。与反联邦党人将权力看做是彻底的工具不同,联邦党人将权力视为“活物”,它需要保存自身,它也需要抵御其他权力的侵犯。所以,控制权力的重点不在于将权力本身变成完全受人摆布的拉线木偶,而是通过理性的、制度的设计来引导各个权力进行相互的制约和平衡。从而使得自由和权利得以通过这一机制而实现。
而在反联邦党人看来,权力本身即为恶。这样的权力就是一个“利维坦”。要想控制这一个利维坦,就必须依靠权力的来源——人民。但是,不幸的是,即使利维坦成为了我们的工具,它也不过是一个“能保障人民权利”的——利维坦。因为本身为恶的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仍然随时有可能侵犯人民的权利。由此,他们认为保持好现有的自由状态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这些自由和权利是由历史和习惯赋予的,它们已经深入人心,不会被轻易被某一个人或某一届政府所夺走。但如果凭借“设计”出的新制度来保障自由,那么实践中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即使是人民自身“犯错”了也并不可怕,只要能够纠正就行。在这里,反联邦党人们的理念是:选择的自由及民主的“纠错”机制本身比期冀一个永远运行良好的制度要可靠的多。
一言以蔽之,在对自由,权利的保障和权力的控制方面,联邦党人最终诉诸理性建构的“法治”,而反联邦党人则诉诸于偏重经验原则的“民主”。而这也正是二者对于同一宪法文本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体现着二者在权力观念上最为本质的差异。
[ 注 释 ]
①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3.
②姜峰,毕竞悦,编译.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87.
③姜峰,毕竞悦,编译.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80.
④该规定已经由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所改变.
⑤姜峰,毕竞悦编译.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248,255.
⑥同上,第257页.
[1]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美]潘恩.常识[M].李玉冰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2.
[3]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姜峰,毕竞悦编译.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5]
[6][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M].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
[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
D
A
2095-4379-(2017)24-0059-03
王振宇(1993-),男,汉族,湖北十堰人,法学本科,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民族大学,2015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立法法及地方人大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