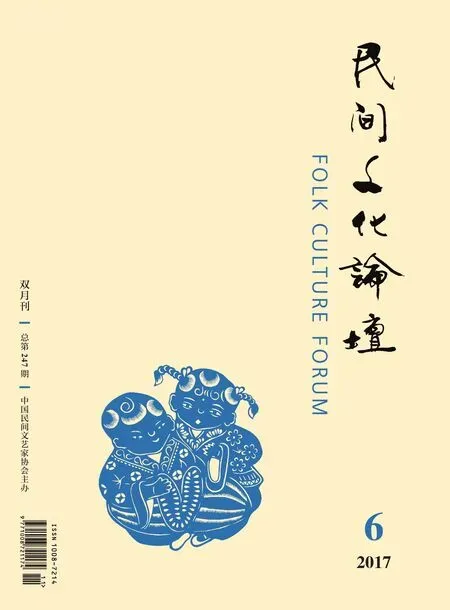昆仑山在先秦中国文学中的象征意义与现实之美
[法 ]雷米 •马修(Rémi Mathieu) 著 卢梦雅 译
昆仑山在先秦中国文学中的象征意义与现实之美
[法 ]雷米 •马修(Rémi Mathieu) 著 卢梦雅 译
昆仑山作为已知海拔最高和位置最西的中国上古高原,神秘莫测,难以接近,却也早为人知。《尚书》应该是第一本让人们注意到昆仑山地表及地下物产的文献①见《尚书•禹贡》。——译者注。正是由于其自然特征,昆仑山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周、汉两代,昆仑山不仅被视为物产名山,还经常在神话传说里出现,最著名的当属周穆王与西王母的奇遇。在后来汉代的诗赋中,昆仑山的神话分量更是越来越重。尽管昆仑山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极其重要,但是西方人却知之甚少。欧洲人很久以前对坐落在丝绸之路上的这一地区一无所知,罗马人自公元1世纪开始知道中国,但并不了解当时汉代的西部疆域,即便是今天,西方人也对这一地区不甚了解。毫无疑问,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将为青海和昆仑山打开世界之窗,让世界认识青海,让世界了解昆仑山。
昆仑山在中国神话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有其历史、地理和宗教的原因。历史上,在中国人认识宇宙的过程中,昆仑山出现得很早;地理上,昆仑山及其周边地区划分了中国西部的边界,人们想象着昆仑山另一边未知世界的神秘莫测。同时,其丰富的土地及地下资源自遥远的周代甚至更早时期便为人所知。因此昆仑山无论在神话还是宗教信仰中均引人注目。诗人和思想家,特别是道家,对昆仑山的象征意义津津乐道:它是太阳落山后的居所,也就意味着暂时的死亡。如今,昆仑山之美在中国家喻户晓,而在国外却鲜为人知。昆仑山的未来何如?人们关注的只是昆仑山的过去吗?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一、先秦文献中描绘的昆仑山
昆仑山缘何为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所知?昆仑山曾是一片极为富饶的广袤地域。据《尚书•禹贡》记载,各国君主都要朝拜大禹。向其进贡皮毛、布料等狩猎和畜牧所得①参见《尚书•禹贡》第六,第150页(《十三经注疏》系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郑玄认为这些人是西戎人。另外,他和其他注疏者都混淆了昆仑山与昆仑地区。据说周穆王西征犬戎时在这里“得四白狼,四白鹿”(《史记》卷一百一十,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881页)。。那个时代,昆仑地区被看做西戎,同样需要向禹帝献贡以获得统治权力的认可。
汉代,汉武帝西征,占据了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土地②见《汉书》卷六十一,第26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经查阅地理学书籍和地图可知,这部官方史书中显示武帝称这些山脉为昆仑(很可能是外语的译文),而这种叫法大概可以追溯到周代,《禹贡》可以证明(见上条注释)。。控制这一地区之于对抗匈奴和月氏民族、保护通往中亚的经商之路有重要意义③见《史记》卷一百一十,第2879页及后。。这一时期的文献显示,昆仑山的宝石与矿产闻名于世。汉代诗人多有赞颂昆仑美玉和奇石之作。人们当时称这些“西北之美”为:“璆琳”与“琅玕”④见《尔雅》卷九, 第2615页 (《十三经注疏》)关于昆仑部分。注释引用了《山海经》卷五,第31页(《山海经笺疏》,《四部备要》,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中亦提及“璆琳”乃仪式扮舞中专用的玉片,“琅玕”(见卷十一,第5页)“似珠”(又见《淮南子》卷四,第6页,《淮南鸿烈集解》,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穆天子传》中反复提到这些地区的玉石与其宗教用途(卷二,第4页,《四部备要》),以及穆王赐予各附庸国的玉石以表彰其美德时表现出的玉石之社会功能。最后,《魏书》卷一百零二,第2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中,将“璆琳”定位在大秦(大夏)。,当然我们不能确定在那时,这些名字所指的玉石是否与现在所指的一样。汉代的大量文献对昆仑山各种玉石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乏溢美之词。但是为何那时的人们热衷于这些种类繁多的玉石?因为那时候玉石不仅作为达官贵人专属的配饰与馈赠,还有重要的宗教功能。人们用玉石制作用于祭祀仪式的各种器皿。我们知道,重要人物死后都有玉器陪葬,玉器象征长久,能够保障魂魄离去之后,躯体仍然长久保存。也许昆仑山与不死之间的联系与其丰富的宝石资源有关——玉正是各种宝石中能够象征永恒的一种⑤周、汉两代有大量作者和著述显示了昆仑山中玉石的存在。其中,《楚辞》第十一,第4页(《四部备要》),或者《淮南子》卷十四,第11页,指出昆仑玉是如此光滑完美无瑕。《吕氏春秋》卷一,第6页(《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局,1986年),卷二十六,第329页,同样赞颂了昆仑的美玉。现在我们在昆仑山下还能看到玉石市场。。
昆仑山的矿产也备受赞誉,文献记载中常见有可以制造兵器的各种金属。比如早期可能用铜制造青铜器,后来用铁制造刀剑。昆仑剑以其坚固闻名。据说能够“切玉如泥”!⑥见《列子》第五,第65页(《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局,1986年)或《尸子》,第一章,第1页(《四部备要》)。这种剑也称“昆吾”(其实是河南一封地名),常与“昆仑”混同⑦见《列子》,第五,第17段, 第65页,或《博物志》,卷三,第4页(《四部备要》)等。昆吾国最初位于河南许昌县。见《诗经》,第22篇, 第627页(《十三经注疏》),第304篇《长发》,以及《左传》,第六十,第2179页第二列(《十三经注疏》),《哀公十七年》(有关一种萨满舞蹈,被发)。。据说此剑是用昆吾山上提取的红铜炼制而成⑧《山海经》卷五,第5页,明确为“赤铜”,而非铁,且昆吾的山当时位于河南。。事实上,秦朝以前,人们似乎把用来造剑的河南昆吾国铜矿与昆仑山用来造剑的铁矿混淆了。昆仑山上不仅有众所周知的动物皮毛、羊毛(还没说到其骏马),有珍石、金属,还生长着著名的水草,在当时(公元前三世纪)用于药材①见《吕氏春秋》卷十四,第142页(《诸子集成》)中写道:“菜之美者,有昆仑之苹”。高诱(196—250)将其比作《山海经》中的薲草(卷二,第18页),认为“其味如葱,食之可以已劳”。。这表明战国末期,昆仑山的植物甚至名扬至中原!还有先秦文献提到了那里大量生长的高大的粮食作物②见《山海经》卷十一,第3页,《穆天子传》卷四,第一页正面以及李善《文选》的注释,卷十五,第8页(《四部丛刊》),关于张衡的《思玄赋》。《楚辞》的一则注释,第十七,第14页,认为那里有很多桂树。。提到昆仑山,古代文献中还经常会出现“流沙”、人们居住的茂密森林、不为中原所知的动物,如骆驼或者其它珍禽异兽。
最后,在周代,昆仑山已经作为黄河——中国北方主要河流的发源地而闻名遐迩③见《山海经》卷三,第5页,或《淮南子》卷四,第3页及卷十六,第13页。。我们都知道黄河在中国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其商业和军事上的交通功能同时为汉室深入中亚提供了极大便利。可以看出,上古时期昆仑山地区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无论在战略、经济还是宗教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神话作品中昆仑山的象征意义
对于昆仑山在什么时代开始在中国神话中作为重要的地理位置出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揣测民间和文人在古代神话中赋予昆仑山崇高地位的若干缘由:地理地位(太阳在西方昆仑山落下)、昆仑山的富饶物产及其象征意义(“天柱”以及与各种宗教崇拜有关)。
最早见证昆仑山神话角色的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小说《穆天子传》——讲述了周穆王西游的奇遇。旅途中,周穆王遇见了西王母,《山海经》描述西王母为“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居住在昆仑山北边山洞里④见《山海经》卷二,第19页;卷十二,第一页(由三青鸟喂食,又写作三足乌(如太阳里的乌鸦));卷十六,第6页。《庄子》卷六,第113页(《诸子集成》)中,将其位于少广山(未确定位置,但注释中提及位于极西方;写作“善笑”而非“善啸”)。。应该没有比《山海经》对昆仑山论及更详尽、更精彩的书了,但是其描述的西王母是头怪兽,而不是位君王。我们当然知道,这段中国君王与西部王后的相遇在道家思想家列子与史学家司马迁那里的有所出入⑤见《列子》卷三,第33页, 及《史记》卷五,第175页及后。。列子关注的是这两个代表了两种文化的主人公,将二人处理为道教神话的两个人物。周穆王摇身一变,成为道教信徒,厌倦了政治生活,意欲去神秘国度探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跟随了老子西游之路。大概在战国时期,西王母则演变成长生不老之女神,直到现在都与寿桃⑥今天,“寿桃”是指一种生日蛋糕。过去,它曾专指西王母的可以让人得到永生的桃子。桃子最初的痕迹是出现在被认为是汉代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之《东荒经》中,卷一第六段,但是“寿桃”一说出现较晚,明代之前未见使用。有趣的是西方的桃子一词来自于拉丁名Prunus persica,意为“波斯的李子“(见老普林尼《自然史》,第十五章第四十四段(又见注释25)),似乎将其命名的西方植物学家认为该物种来自于波斯。古代中国人在将桃子与“西方王母”联系起来的时候难道不也是这样认为的吗?一起出现。无论如何,这些文献讲述的故事引人入胜,展示了中国统治者和蛮族首领的一次和平会面,他们平起平坐,互赠礼物、交换诗作,甚至彼此允诺。
这些文献还讲到昆仑山是上帝或者天帝的居所①比如见《山海经》卷二,第17页及卷十一,第2页。。原因之一就是昆仑山被认为是天柱之一并且位于中央,天空围绕在其周围,就像陶轮的中轴一般;也有人认为这个柱子正是共工与颛顼大战中被撞倒的不周山②见《淮南子》卷三,第1页;《列子》第五第一段, 第52页。。
另一个原因是昆仑山中居住着不为人知的民族,以及众多神明,他们神秘莫测为世人所崇拜。其中,有诛杀怪兽的后羿(这个故事可能来自射日的传说)③见《山海经》卷六,第4页。众多怪物中,见《淮南子》卷十六, 第5页:“神状虎身、条纹皮毛、九尾,乃昆仑之山神。”,还有发明农业的后稷,死后葬于钟山、昆仑山的流沙中④见《山海经》卷十一,第2页。。昆仑山东北方曾建造了观景台以纪念尧舜二帝到此地的巡视⑤见《山海经》,卷十二,第2页及卷十七,第四页。……人们认为昆仑山是天之门户,人们的精神及已故帝王可以通过此处来往于天地之间⑥见《淮南子》卷一,第四页反面。关于众神的出现又见《淮南子》,卷八,第6页。。
因此,诗人们也赋予了昆仑山重要的神话功能,将其写作天门、天柱或者神之所在⑦见《河图》,引自《离骚》注释“天中柱也”(卷一,第33页反面)。据《神异经》之《中荒经》,第九,第一段:“有铜柱焉其上通天,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山海经》卷十一,第3页,中称此地乃“百神之所在”。。以至于汉赋里人们有时称昆仑山为“灵丘”⑧指班昭的诗作《大雀赋》中。。屈原在《离骚》中描写自己将被放逐到这样的地区:“邅吾道夫昆仑兮!”因为他说,在昆仑山之巅,坐落着“悬圃”或“玄圃”⑨见《楚辞》之《天问》,第三章,第6页。在《九章》,第四章, 第34页反面中写到攀登昆仑山以“览云雾”。杜甫在诗作《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第11行)中赞美其友的风景画时,也提到了美丽的“悬圃”。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圃”也是高原及神秘属地上盛产水果的果园,因为其坐落在极西位置(《穆天子传》中描述地名“玄池”的诗行与此处“悬圃”相似,卷二,第5页)。关于昆仑山的悬圃,又见《十洲记》卷一,第10页。。自此,昆仑山与不死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国度不但居住着西王母之类的神明,还居住着掌握长生不老的秘密的圣仙。两汉时期,大量诗作歌颂了昆仑山之伟大和富饶,可能是由于这一时期汉朝攻占此地的缘故。我们可以举出班固、张衡、司马相如、班昭、扬雄、祢衡等等汉代文人关于昆仑山的诗作⑩见班固:《东京赋》,出自《文选》第一,第10页;司马相如:《大人赋》,出自《史记》卷六十七,第3060页;张衡:《思玄赋》,出自《文选》第十五,第8页;班昭(曹大家):《大雀赋》,出自《全汉赋校注》(费振刚、仇仲谦、刘难平出版,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卷一,第558页);扬雄:《羽猎赋》,出自《文选》第八,第24页;祢衡:《鹦鹉赋》,出自《文选》第十三,第29页,等等。。这些文人均是受到屈原启发,将昆仑山视为天地相接的神秘之地,认为可以在那里逃离尘世和烦恼。这些诗人都描写了他们远离城市文明,在群山和众神之间漫步神游的情形。过去的神秘之山,如今成为现实之山。其前景如何?是否已经被其过去所固化和限制?
三、昆仑山的前景
昆仑山的过去如此丰富,其未来如何?在准备此次大会发言的过程中,我重新审视古代文献,令我吃惊的是有那么多作为自然风景而出现的昆仑山,特别是在诗赋作品中往往出现对其各异的形态、缭绕的云雾以及无垠空间的描绘——这是旅行者的视角。留下这些记录的旅行者当然往往是某个中国文人,自远方而来,为其所见的壮丽景象而赞叹。然而在中国之外,还有人了解昆仑山吗?
最早谈及中国的西方著作是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老普林尼的《自然史》(Pline l'Ancien,Histoire Naturelle)。他听说了中国的丝绸制造,当时这种布料已经被引进罗马帝国。他在书中指出,这些丝线生长自一种树上,然后人们收集起来。他肯定这种种植在遥远国度的树就是丝树,并用这个词命名中国人。他详细解释了人们在树林里收集起这些丝绒,将其浸泡在水中,然后罗马妇女将获得的丝线进行纺织。普林尼还指出,这些中国人很友好,但是“完全像野兽一般:他们逃避与外来人群交往,坐等贸易送上门”①见其《自然史》第六章,第54段、55段。由于亚历山大帝的征服活动,对印度有一点认识的托勒密(Ptolémée, 90-168)有类似地理上的看法,但是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对中亚(特别是大夏、大秦)、斯基尔泰人以及托喀尔人(仍然见于甘肃,中国人称之为月氏)并不是不了解的。这是根据老普林尼版的《自然史》(J. André & J. Filliozat,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80, p. 74-75 et 79-80)以及施密特版的« La Pléiade «(《七星诗社》S. Schmitt, Paris, Gallimard, 2013, p. 1792 ,注释 88 及后)之注释所知。该书第十二章,第17和38段也有涉及。。这大概就是他对中国所了解的全部了,当然没听说过昆仑山,尽管可能对中亚有所耳闻。如今,我仍然无法确定西方人对昆仑山的了解有多少长进。
当然,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今昆仑山得以走向世界。遗憾的是,令中国人魂牵梦萦了十几个世纪的这一地区,在渴望来华的外国游客脑海里至今仍然是片空白;同样令人惋惜的是,昆仑山只是停留在中国人神话里那固有的形象上。中国游客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广袤地区的旅游和文化价值,但是外国游客还尚未能探索至此。这一地区难以接近,但是昆仑人民不懈地探索进山的方法以及发展其接待能力。这一切使我有可能对这西王母国度的未来有所展望并怀有信心!
译者按:本文系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法国当代汉学家、前法国国家科学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CRCAO)主任、荣誉研究员雷米•马修(Rémi Mathieu)先生在2014年8月在青海格尔木举办的“昆仑文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学术论坛”大会上的发言。法国汉学的传统治学承袭乾嘉学派,重视文献考据,与北美汉学明显不同。马修先生四十几年如一日研究先秦文学,对中国文献如数家珍,著有《〈穆天子传〉的译注暨批评研究》《关于〈山海经〉的古代中国神话学和人种学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选集》《帝国初期的神话与哲学—— 〈淮南子〉研究》《中国神话学批判》等汉学著作,深谙中国神话学研究。本文梳理和展现了先秦文献中的昆仑形象,同时揭示了昆仑神话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密切联系。
I207.7
A
1008-7214(2017)06-0054-05
[法]雷米•马修(Rémi Mathieu),法国国家科学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CRCAO)主任、荣誉研究员。
[译者简介]卢梦雅,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丁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