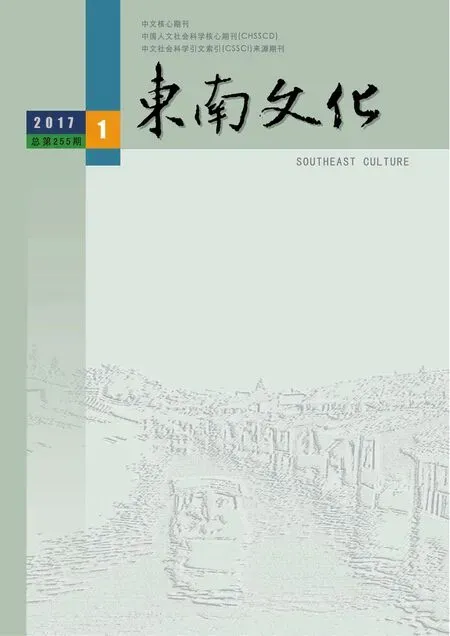真实与重构:博物馆展示本质的思考
徐玲 赵慧君
(郑州大学考古系 河南郑州 450001)
真实与重构:博物馆展示本质的思考
徐玲 赵慧君
(郑州大学考古系 河南郑州 450001)
博物馆一直以中立、客观来宣扬自身对真实情形的表达。作为连接博物馆与公众的桥梁,博物馆展示的本质及过程是探讨博物馆真实性的关键所在。在博物馆场域中,从真实而具体的物件到有意义而抽象的展示,此重构的过程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意义的制造与政治的关切。博物馆展示过程中真实不可避免地被重构,同时博物馆又是权力—知识体系下的一个重要场域,但无论其如何重构,博物馆体现的仍是一种“真实”,是一种可见的、相对的、被社会需要的“真实”。
博物馆展示 真实性 重构
作为收藏展示人类记忆之所,博物馆一直以客观真实的文化场所的面目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究其原因在于博物馆的展示以真实物件(the real object)为依托,并试图以此呈现客观的文化面相。博物馆通过展示将文化以可参观的形式制造出来,同时采用诠释的技巧来改造或重建信息,借此突出基于某类目的或企图而构造的意义。在展示过程中,从藏品到展品的转化,经由解读和诠释的呈现,作为“原材料”的真实物件被制造和生产出意义,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内涵,成为重要而且被重视的东西,由此引起了有关博物馆展示真实性的质疑与思考。博物馆展示与谁有权力、以谁的名义、展示谁的文化及维护谁的利益等密切相关。在权力—知识话语体系下,物件的收藏、展示和诠释均为有明确目的的活动。因此博物馆展示的真实在展示过程中难免被重构,其展示的真实仅是基于某种目的被呈现的一种“真实”。探究博物馆展示的本质实际上是深层次认识博物馆性质的重要途径,遗憾的是,以博物馆展示的真实性为主题的研究并不丰富,相关论著缺乏[1]。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博物馆展示过程中所蕴含的意义制造与政治性话题入手,深入解析博物馆展示真实性的困惑,进而重新思考博物馆展示的本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
一、博物馆展示真实性的困惑
在《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一书中,英国社会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曾明确指出,一直以来,博物馆均被视为专业化、定义严格的文化展示机构[2]。博物馆展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一方面源自其所展物件的稀少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这些物件本身就是富有客观性的历史材料和视觉证据。亨里埃塔·利奇(Henriet⁃ta Lidchi)如此描述博物馆展示中的物件:“来自于过去的物件往往以文献和证据的姿态出现,而且被看作是文化本质的物化,可以超越时间、地点的变迁和历史的偶然性而存在。物件的物质性提供了对稳定性和客观性的一种允诺,暗示了一个稳定的不模糊的世界。”[3]因此博物馆展示被普遍认为是获取客观信息的最可靠的途径之一,是对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忠实反映。这种真实不仅有别于旅游景点的“舞台真实”,而且有别于复制艺术品的“模仿真实”,同时还有别于现今各种高新技术的“虚拟真实”,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真实。真实物件似乎从本质上保证了博物馆的中立、客观,其展示内容不应被质疑,也不可能被质疑[4]。尤其是在这个到处充斥着仿制品的时代,追求真实的博物馆无疑为观众探寻过去提供了最佳场地。美国斯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教授珍妮特·马斯汀(JanetMarstine)也明确表示,博物馆是这个陷于文化健忘症的时代对真实性的需求的一种回应[5]。
除对真实物件的追求之外,在实践中,博物馆还竭力为物件的展示提供真实的场境,如尽可能地将物件置于复原或模拟的原始场景中进行展示,或者直接在物件被发现的原址上建立博物馆进行展示等,甚至还配以身穿相应时代的服饰及从事相应生产活动的表演人员,借此鼓励观众了解“真实的”人类生活与环境面貌。随着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出现与发展,博物馆更加注重改进其展示方式以求达到“真实”的再现,进而讲述背景更宏阔的故事,反映更广大的现实。
通过真实物件本身及物件与原始场景的结合,博物馆试图引导公众相信博物馆内展示的内容是客观的、真实的。遗憾的是,博物馆展示脱离了具体物件的真实层面,不免陷入有关真实性的讨论陷阱之中。一方面,即使物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其原始的形式,但其原始意义的特殊性也永远无法复原。西方许多绘画原本在教堂中安置,当离开其原始场景而在博物馆内集中展示时,其宗教意味已被削弱或消失殆尽,而沦落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另一方面,物件一旦被展示,便成为博物馆叙事的核心——展品,在博物馆场域中便被赋予了特定意义,自动参与了概念、观念和情感的文化生产。这种从普通物件到展品的转化,使所谓的真实得以无限放大,而其他真实则被人为地加以虚化或掩盖。
由此可见,博物馆展示的真实性似乎只是被制造出来的,真实物件在展示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被重构。展示不再是自足的物件个体的集合,而变成了承载各种意义的综合体。从博物馆展示过程的意义制造与政治关切两方面来分别解析,可以对博物馆展示的本质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二、制造意义:博物馆展示的一般策略
物件是沉默的,本身并没有固有价值,并不像博物馆宣称的那样能够“为自己说话”[6]。博物馆展示由物件构成,但并非是物件的简单堆积。物件只有与意义结合起来才具有展示价值。然而,已经消失的真实充满了不可描述性,只要尝试再现就会变成对材料的处理。从这个意义上看,博物馆展示只能是一个个建构的事件,一种复杂的意指系统[7]。换句话说,博物馆展示就是一种制造意义的过程,意义均是通过物件的选择、信息的诠释被建构出来的。
首先,博物馆物件的来源不仅与博物馆本身的性质和目标有关,与管理者的知识和视角有关,同时也与各时代中不同脉络下的审美品味、政治宗教等价值运作有关[8]。博物馆管理者可以决定什么被收藏,什么被展示,什么不被展示,记录什么而又忽视什么。一方面,为了展示主题的需要,管理者会不自觉地对物件进行煞费苦心的挑选,而这主要集中在符合展示主题、器形较为完整、样式相对精美的物件。对物件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展示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任何展示其实都只能反映社会真实文化的很小一部分,而且是社会主流价值所崇尚的精致或精英文化的那一部分。另一方面,从藏品到展品的生产过程,更是一个从“眼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创作过程[9]。彼得·弗格(Peter Vergo)曾对博物馆展品的可能性进行一番论述后认为,“物件被挑选为展品的标准并不是随机或任意的,正相反,它们是根据特定的目的而被选择出来的”[10]。物件一旦被纳入展示体系,便成为展示所要讲述的整个故事的元素之一,被赋予价值,变成特定意义的载体,从而使其在展示中的含义远超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展示的过程即是物件按展示主旨被选择、美化、提高,被赋予一定的观念、情感、倾向,进而变成某种思想或信念的载体。意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主观地制造出来的。
其次,从主旨表达来看,博物馆展示也是一个诠释性的、生产性的过程,是对事实的一种发现与制造。当物件出现在博物馆场域中,并在一定的秩序中进行展示时,新的意义通过解读或诠释的方式被制造出来。美国博物馆学者大卫·迪恩(David Dean)就认为博物馆展示在诠释的过程中含有必然的主观性,“博物馆对展品的诠释,其实就是解释、澄清、转译的一种行动或过程,或是个人对于主题或物件的理解的一种呈现”[11]。展示时,展品被抽离原始的时空背景及功用后,往往会被赋予新的意义,隐含不自觉的利益关系。博物馆展示就是有意建构的,用以向公众展现作品本身无法揭示的东西[12]。
博物馆以中立、无争议、无偏见等标签来标示自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或淡化其在展示过程中所做的选择及有倾向的诠释,从而获得其文化身份的某种权威性。但是,博物馆展示在对展品进行命名、排序、诠释的过程中,所运用的辅助科学技术手段,甚至其线性的、逻辑的元叙事展示模式,已然体现了其对展品的重塑。展示即成了一个“他者化/成为”的过程。因此,博物馆展示已不可能是原始呈现,而仅是对现实所做的某种程度的模仿而已。在没有意图的地方,展示是不成立的[13]。美国艺术理论学者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对此总结道:“正如并没有任何描述艺术原本面貌的中性方式一样,没有一种布展是不凸显一种诠释的。”[14]
再者,博物馆展示中意义的制造还不免受到策展人本身价值观的影响。“真实性和事实本身或现实状况并无关联,而是一种有关于权威的表达。物件本身并没有权威性,但策展人借此展示权威,以此来决定如何讲述过去。”[15]策展人可以从自身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奠定展示的主调。当下多数博物馆展示尝试摆脱原有单调的展品和说明牌的简单形式,倾向于通过讲故事的手段来展示自己的主题。而物件在故事中如何被挑选出来、连贯起来并延续它们之间的关系,则受到策展人的学识、视角、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等左右。策展人作为博物馆文化的生产者,挑选物件并将之融入特定语境中形成一个叙事秩序,操控了物件呈现的意义。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在探讨艺术品背后的本质时指出:“对于艺术品来说,它们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它们是什么样子依赖于我们把它们解释成什么样子”[16]。巫鸿也曾在多篇文章中论述艺术的真实与重构关系,指出以复制真实著称的摄影中每幅取景和角度都必然含有特定的政治、文化取向和拍摄者的目光,甚至最忠实的纪实摄影也不例外。至于描述历史的文字和图画,就更无法摆脱记录者的眼光、风格和判断[17]。如此看来,受策展人思想和其所代表文化的影响,博物馆展示的文化并不能中立地还原其真实性,而是隐含着一种主观的选择和偏见。
通过分析博物馆展示过程中的意义制造,可以发现一种学术思考的反向进路,即质疑隐藏在“可参观性”背后的“不可参观性”。当研究博物馆展示中的物件和文本说明时,需要思索:哪些物件被挑选出来了?什么内容被诠释了?什么内容被排斥在外了?它的主题思想、词汇选择、字里行间显示的是谁的知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博物馆展示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是被主观选择和建构了的。博物馆从神庙(temp le)到公共论坛(forum)的哲学演变,不过是博物馆外在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变化。博物馆依然在表征一种有选择的文化,只是随着多样视角的出现,过去的垄断被打破了而已[18]。博物馆内的每次挑选、剔除、排列、诠释都是展示的一种有目的的策略。
三、政治性:博物馆展示的权力话语
博物馆展示中真实被重构的现象,不仅与展示过程中意义的制造有关,还与展示所蕴含的政治性有关,根本原因在于博物馆本身即是一个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文化展示场所。博物馆展示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代表了一种权力—知识的话语体系,其真实性也在政治环境中被重构了。诚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话语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必须在生产和流通语言的互动情境和结构环境中研究。”[19]从展品来说,博物馆内展品的选择不能忽视其政治性、意识性及审美性偏向[20]。同时,博物馆展示是由那些能够支配展示资源的文化生产者所控制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强调:“不仅要关注博物馆展示了什么,还要看谁参与了展示及展示的过程。”[21]英国博物馆学者沙伦·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同样指出:“博物馆建筑形式和博物馆展示中物件被分类和并置也体现了博物馆政治。”[22]博物馆展示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依据展示主旨及政治意图对其意义的诠释进行了“适度”处理。展示是艺术的政治经济价值的首要交易场所,意义在这里得以建构、维系乃至解构[23]。理解博物馆展示真实性的政治化重构,就必须思考博物馆与多元文化、民族国家、等级秩序的关系,充分认识博物馆展示与权力运作的内在逻辑。
一方面,博物馆是文化展示的重要场所,在文化权利的呼声下博物馆内展示的文化更为多元。不可否认,种族主义依然存在,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者”与“他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界定。但在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尊重不同地区、不同历史传统和不同政治制度下各种文化价值的思想已然成为社会潮流,博物馆也开始着手为以前被排除的文化提供展示空间,期冀通过展示更为多元的文化来消解博物馆权威文化的声音。然而,遗憾的是,多元文化的展示实质上并没有扩大文化范围,只是增加了被展示的文化数量,而继续掩盖了博物馆在调节展示和被展示双方权力关系时所起的作用[24]。博物馆展示依然和权力及博物馆围墙之外的群体之间持续的不平等关系有关,被边缘化的、被抹煞的文化的声音在展示中仍然很少得到表现。
另一方面,博物馆本质上具有按国家划分的自然属性,是国家政治的展示场所,国家的政治身份在博物馆中得到精心诠释和宣传。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文化人类学教授安唐·布洛克(Anton Blok)认为,“制造历史”的建构过程中蕴含着权力的安排,“对于文化展示的研究要关注不同群体在描述或诠释展示物件的意义的不同方式和立场,更要探讨其中的权力安排及物件是如何被再现、建构和符号化”[25]。博物馆是政府和文化关系的中心,是权力展示的媒介,博物馆展示的主旨必然是以国家意志为导向的,并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场所。博物馆展示从根本上说要迎合社会正义、社会道德、社会主流思想,因此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态度倾向和功利色彩。作为社会文化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肩负着塑造正确文化和教育意义的使命,且希冀通过展示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行为,以维护社会的主流标准与价值观。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在考察了“文化生产”这一重要社会文化现象之后指出:“主导文化总是被呈现为文化,透视社会整体的参照点。它试图在它的范式和价值之内界定和包容其他文化。”[26]博物馆展示迎合了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制造了权力下的知识。正如黄光男所言:“博物馆工作的真实性,似乎在社会运动中被政治化了。”[27]
此外,博物馆还是一个体现等级关系的重要场所,通过展示进行知识、身份和文化的等级秩序及发展历程等重要社会概念的宣告。在博物馆这一文化展示场所中,文化整体被学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分成了若干等级,直线进化论式的分类使博物馆把社会排列成了从落后/原始民族到较先进/现代民族的一个连续统一体。在博物馆展示空间内,展品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过去到现在的顺序线性摆放,提供了一条列队前进的路线,暗示了“直线”的历史进化过程。博物馆展示同时还进行身份的表意。如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首都博物馆以女性为主角,从女性视角设计的“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分别展示了妇好的王后、母亲、将军等身份,指意其社会、家庭、历史等多重角色。这一方面迎合了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贤妻良母”的妇女观;另一方面则着重加强了当下女性对个人身份及职责的认知。而当时社会的残忍暴行及其他女性极少见于史料记录的事实在展览中未见任何体现。通过把充满了抗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历史简化成相互连贯、易于同化的秩序,博物馆制造了一种用以使人安睡而非清醒的历史感[28]。
自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者、人类学者、社会学者、新博物馆学者已经开始质疑博物馆展示背后的政治性及其不平等性,质疑某些物件和事实被挑选出来进行展示的依据。从国际层面来看,博物馆一直隐含着西方社会的秩序观念与分类逻辑;从民族国家层面来看,博物馆则扮演着宣扬社会主导意识,压抑有悖于社会主流文化的工具性角色;从身份、等级层面来看,博物馆所裹挟的对于社会参与和文化权利的追求依然受制于僵化意识的束缚。在面对如何消除其隐藏的权力—知识话语体系问题时,博物馆更倾向于采用文化拼图的概念来迷惑观众,而并不去体现展示背后的权力不平衡和结构不平等的问题。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兴起,单线性的传播转向双向性的互动,然而其并非创造真正的互动经历,只是将参观者的注意力转移开,防止他们提出更多的关于博物馆权威性和真实性的问题[29]。
四、余论
博物馆意欲展现真实,展示过程中真实却不可避免地被重构。博物馆展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真实的物件被挑选并呈现为展品时就会被赋予相应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博物馆又是权力—知识体系下的一个重要场域,其展示以符合社会主导意识和主流文化为标准,实现了真实性的政治化重构。而这种被博物馆重构的“真实”,根本无法满足公众渴望了解真实的诉求,也与博物馆所标示的中立、客观等形象相背离。但综观博物馆展示的过程,之所以会造成真实性的错觉,原因在于展示物件的具体化及物质化的真实。人们质疑,展示过程中物件被选择、被诠释及意义被重构之后,还能称之为真实吗?然而,当逆向思考博物馆为什么会选择如此展示时,另一种更为复杂与抽象的真实开始浮现,即被展示所建构的“真实”多数是当下社会所需要的“真实”。博物馆无法呈现完全的历史真实,然而,如果将其放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真实性却似乎变得有迹可循。即博物馆展示所凸显的“真实”是部分的“真实”,是迎合了当下社会意识形态的“真实”。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30],同理,一切展示也都是当代展示。博物馆展示真实性的讨论不仅要置于博物馆展示空间内去探析,而且还应放置在广阔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讨论,还要结合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多角度地思考博物馆展示所蕴含的深意。似乎博物馆展示中信息重构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无论其如何重构,体现的仍是一种“真实”。这是一种可见的、相对的、被需要的“真实”。如此看来,真实抑或是重构已然不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博物馆展示究竟凸显了哪一种可见的“真实”及表达时所用的手段与方式。为全面解构博物馆展示的真实与重构,博物馆甚至可以在展示中呈现出主题和物件选择的视角、诠释的立场及自己的目的和企图。或许,唯有博物馆自身破茧而出,以一种更加开放、客观的态度来解构知识权威的意识形态、检视知识建构的真实面貌,博物馆才可能真正为大众所有,并在社会中永续发展。
[1]目前探讨博物馆展示真实性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陈哲《论历史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浙江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认为博物馆物品的真实、内容的真实和形式的真实构成了展示的真实性;贝拉·迪克斯的《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及大卫·卡里尔的《博物馆怀疑论——公共美术馆中的艺术展览史》(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两书中,均质疑了文化在被展示后如何发生改变,认为真实性在展示中是被重构了的;亨里埃塔·利奇《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和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指出要结合意义和政治来认识展示中文化的表征;许功明《当代博物馆文化之展示再现与价值建构:从现代性谈起》(台北自然科学博物馆2005年)及刘婉珍《透视博物馆剧场:博物馆真实建构的真实世界》(《博物馆、知识建构与现代性》,台北自然科学博物馆2005年)等认为博物馆展示的真实是一种建构的真实。
[2][12][24]〔英〕贝拉·迪克斯著、冯悦译:《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1、172、158页。
[3]〔英〕亨里埃塔·利奇:《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和政治学》,〔英〕斯图尔特·霍尔编、徐亮等译《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5页。
[4]宋向光:《博物馆展陈内容多元构成析》,《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
[5][29]〔美〕珍妮特·马斯汀著、钱春霞等译:《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5、32页。
[6][15]Spencer R.Crew,James E.Sims,Locating Authen⁃ticity:Fragments of a Dialogue,in Ivan Karp,Steven D. Lavine.ed.,Exhibiting Cultures: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Museum Display,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 tution,1991,pp.159,163.
[7]屈雅君、傅美蓉:《博物馆语境下的性别文化表征——以妇女文化博物馆为例》,《南开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2期。
[8]许功明:《当代博物馆文化之展示再现与价值建构:从现代性谈起》,王嵩山主编《博物馆、知识建构与现代性》,台北自然科学博物馆2005年,第393页。
[9]傅美蓉:《论展品:博物馆场域下的知识生产与性别表征》,《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4期。
[10][20]Peter Vergo,The New Museology,London:Reak⁃tion Books Ltd.,1989,p.2.
[11]〔美〕大卫·迪恩著、萧翔鸿译:《展览复合体——博物馆展览的理论与实务》,(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13]〔日〕佐マ木朝登:《博物馆工作手册》,转引自耿凤英《谁的故事?——论博物馆展示诠释》,《博物馆学季刊》第25卷第3期。
[14]〔美〕大卫·卡里尔著、丁宁译:《博物馆怀疑论——公共美术馆中的艺术展览史》,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16]〔美〕阿瑟·丹托著、陈岸瑛译:《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
[17]巫鸿:《“第二历史”:改造历史的历史》,《美术馆》2010年第1期。
[18]尹凯:《变迁之道:试论博物馆历史与功能——兼论〈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东南文化》2015年第3期。
[19]〔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
[21]Tony Bennett,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103.
[22]Sharon Macdonald,The Politics ofDisplay:Museums,Science,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1-21.
[23]Ressa Greenberg,Bruce W.Ferguson,Sandy Nairne,Thinking about Exhibi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2.转引自〔瑞士〕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著、任西娜等译《策展简史》,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5页。
[25]〔荷兰〕安唐·布洛克:《“制作历史”的反思》,〔丹麦〕克斯汀·海斯翠普编、贾士蘅译《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4—139页。
[26]〔美〕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90页。
[27]黄光男:《博物馆新视觉》,(台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75页。
[28]Turner,Evan,Walter Leddy,eds.Object Lessons:Cleve⁃land Createsan ArtMuseum,Cleveland:Cleveland Mu⁃seum of Art,1991,p.217.转引自大卫·卡里尔著、丁宁译《博物馆怀疑论——公共美术馆中的艺术展览史》,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30]〔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页。
(责任编辑:黄洋;校对:王霞)
《东南文化》订阅启事
《东南文化》杂志是由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1985年创刊,20多年来已出版200余期,深受海内外文化界、学术界、收藏界的推崇,被录入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等。
《东南文化》于2009年改版后,定位于中国大陆东南及港、澳、台地区乃至日、韩等东亚诸国文化遗产的探索、研究、保护、展示与利用等,加强了对文化遗产从保护、研究、管理到继承、欣赏、展示诸领域的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的关注,以适应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新内容、新趋势和新要求,凸现文化遗产地位,彰显东南地域特色,并努力打造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从而推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事业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主要栏目有:东南论坛、遗产保护理论、考古探索、地域文明、博物馆新论、专题研究、十竹斋艺谭等,图文并茂、印刷精美。
本刊为大16开本,128页。全年6期。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邮发代号28-236。全年订费165.00元(含邮资),国外订户每年订费为120美元(单价20美元)。凡读者直接向编辑部订购,可获书价8折优惠。我刊在收到订单及书款后,即发杂志。
另外本刊尚有部分过期刊物,欢迎选购。
通信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编辑部
联系人:何刚
邮政编码:210016
电话:(025)84841253
电子邮箱∶dnwh@chinajournal.net.cn
《东南文化》编辑部
Authenticity and Reconstruction:The NatureofM useum Exhibiting
XU Ling ZHAOHui-jun
(DepartmentofArchaeology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450000)
Themuseum has built its image as providing neutral and objective narrative for authenticity. As a bridge linking themuseum and the public,museum exhibiting,with particular regard to its nature and process,is essential in addressing the issues of authenticity and the museum.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the authentic andmaterial objects intomeaningful and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occurringwithin themuseum space concerns two essentials∶themaking ofmeaning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politics.The authenticity is in⁃evitably being reconstructed in exhibiting.Themuseum is an important site of the power-knowledge system. Despite of the reconstruction,what is represented in the museum is“authentic”,which is visible,relative, and socially needed.
museum exhibiting;authenticity;reconstruction
G260
:A
2016-09-30
徐玲(1969—),女,郑州大学考古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赵慧君(1989—),女,郑州大学考古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