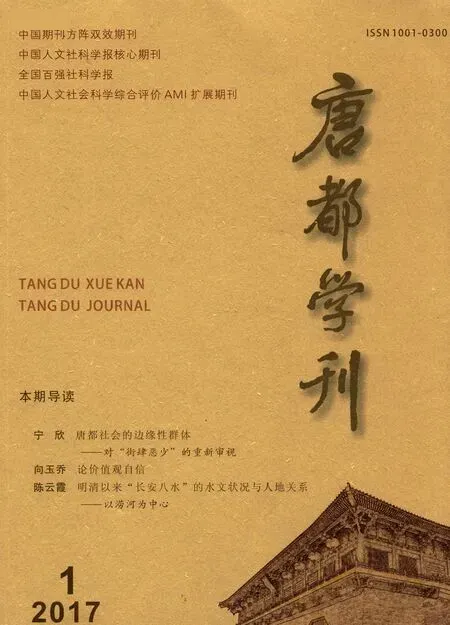法律、社会和公民:法治的三重基础
——基于对柏拉图《克力同》的分析
惠永照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武汉 430074)
【哲学研究】
法律、社会和公民:法治的三重基础
——基于对柏拉图《克力同》的分析
惠永照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武汉 430074)
法治社会的建立和维护依赖于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由法律、社会和公民三者相互作用而共同构建起来的,其中公民对法治的真诚信仰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决定着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和一个秩序良好社会的建立和维护。《克力同》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它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守法的榜样。在对《克力同》的分析以及对古代希腊与现代社会的比较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对于当前法治建设的启示。
柏拉图;《克力同》;法律;社会;公民
法治是我们的时代特征,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维护依赖于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由法律、社会和公民三者相互作用而共同构建起来的。所以法治的实现依赖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一个优良的法律体系和一众愿意服从法律的公民。在这三个因素中,公民因素居于核心,公民对法治的真诚信仰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决定着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和一个秩序良好社会的建立和维护。《克力同》这一古老的文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法治基础的三个方面联系在了一起,它启示着我们去探讨公民对法律服从的限度,指引我们从对两种社会的比较中找寻各自的公民基础。
一、良法
《克力同》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主人公是苏格拉底。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为不敬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判处死刑。之后苏格拉底的一些朋友包括克力同买通了关系准备帮助苏格拉底越狱,只要苏格拉底同意,他就能够很容易逃出雅典。问题是苏格拉底一直不同意越狱,克力同多次劝说无效。《克力同》篇记述了苏格拉底行刑前第三天早上克力同最后一次尝试说服苏格拉底越狱逃走的情形。
苏格拉底整个论证的前提是“不可以恶报恶”。在《克力同》篇中,这个前提并没有得到论证,而是直接作为大前提出现的,它是在苏格拉底和克力同及其他人的日常对话中已经反复讨论并接受下来的一个命题。苏格拉底问克力同,对于“不可以恶报恶”这一原则,是不是平常无事闲谈之时认可,等到事到临头了就要否定它了呢?克力同说当然不能。[1]106-107这就意味着他们都承认“不可以恶报恶”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然而一旦承认了这一点,克力同就已经不可能再说服苏格拉底了,因为他们都会承认用越狱的方式对抗不公正的判决就是以恶报恶,这在他们看来是不正当的。
接下来苏格拉底让法律自己说话。法律说,苏格拉底呀,你未出生时,我生你(通过婚姻制度),出生后,我养你、教育你(通过教育制度),成年后,通过自己的理性判断,你可以自由地选择离开本邦到外邦去,而你在70年内不仅没有离开,甚至连出国参观、旅游的次数都比那些看不见的、腿脚不便的还少。就算是在受审判时,宁可受死也不愿被流放。你的言行说明你对本邦的法律是满意的,“你言语与行为都和我们订下了甘为守法公民的契约。”[1]110而如果你逃走,就践踏了和法律定下的契约。这时候,你就成了法律的破坏者,这种行为是不容于政治修明的城邦的。
看起来苏格拉底像实证法学家那样认为恶法亦法,不公正的判决同样需要被遵守,但实际上苏格拉底的理由更加复杂。在苏格拉底的论证中,既有城邦的实在法,也有一种与实在法联结在一起但又不同于实在法的公民契约,后者并不是一种自然法,因为它并不构成实在法的基础。它更接近于一种社会契约,在这个契约的条款中,“遵守城邦的实在法”赫然在列。而且这个契约是理性的,是公民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存续所必须共同遵守的理性契约。这样,公民的违法行为就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公民的违法行为直接违反了实在法:另一方面,也因为对实在法的违背而违反了理性契约。
越狱的行为既违背了现实的法律,也违背了理性的契约,法律亲口告诉苏格拉底的话不是指出苏格拉底如何违背了现实的法律,而是指出他如何违背了理性的守法契约。这样的一个契约在现实层面上是不存在的,近代契约论传统中的契约也不能从现实层面而只能从理念层面来理解。由于这种理性的契约并没有缔约者现实的明白同意作为条件,所以不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洛克都需要借助“默认的同意”来解释这个契约的签订。[2]定下这个理性契约、做出守法承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存在。对于契约论者而言,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对于古希腊思想家而言,国家(城邦)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利益需要,更重要的是国家是个人道德完善的手段,通过国家个人才能够达到终极的善。所以破坏法律就是毁坏国家,就破坏了个人自我完善的途径,阻断了人通过国家而将自身提升为完善之人的道路。亚里士多德说,不在城邦中的人,要么是神,要么是禽兽。[3]5没有了国家,人将再次与野兽为伍。
所以对于苏格拉底而言,越狱必然是恶的。因为它通过违反现实法律的方式违反了理性的契约。信奉不可以恶报恶的苏格拉底选择服从不公的判决,从容就死。
苏格拉底之死引发了整个思想界的大风暴。它的影响力贯穿哲学、政治学和法学。在法学上,它提出了“恶法是否是法、不公的判决是否要遵守”的问题,开启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论辩的先声。自斯多葛学派和西塞罗开始的自然法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回应。西塞罗认为,在实在法和公民契约之上,有一种更高的自然法,它“是植根于自然的、指挥应然行为并禁止相反行为的最高理性。”[4]158“这种法律的产生远远早于任何曾存在过的成文法和任何曾建立过的国家。”[4]159西塞罗对自然法的理解是斯多葛式的,他从人与宇宙的同构关系中确立了自然法对人的规范意义。自然法源于人与神共有的理性,因为人与神共有理性,所以他们同样共有自然法和正义,因而“我们此刻就必须将这整个宇宙理解为一个共同体,神和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4]161
自然法将人提升到了一种超越的位置之上,在此位置上,人可以对某一具体的实在法进行批判。自然法的超越维度一直保留在西方的法学思想中,虽然人们无法就自然法形成一种共同的认识,但是现实的法律实践需要一种对现行法律的评判,自然法的观点很容易契合这种需要。也正是站在自然法的超越位置上,人们才能够去询问恶法是否是法、不公的判决是否要遵守。如果恶法也是法,那么对于恶法的违背本身也就是一种恶;如果恶法不是法,那么违背恶法不仅不是恶,而是一种善。
西方历史上有悠久的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的传统。罗尔斯把非暴力反抗定义为“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对抗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5]364-365非暴力反抗并不要求违反那个正在被反对的法律,它诉诸的是一个公民政治社会中大家共有的正义观,因而它是一种在公共讲坛上公开表达的和平请愿行为。可以说,“非暴力反抗是在忠诚于法律的范围内(虽然是在外围的边缘上)表达对法律的不服从。”[5]367梭罗、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是倡导非暴力反抗的理论家或践行者。
一个稳固的法治社会不仅需要有一套法律体系,而且还需要这一套法律体系是一个良法体系。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总是存在法律的空白,而已立的法律也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法律自我改良的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包括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对旧法的自我修订,也包括司法部门基于司法实践的反馈和普通公民基于个人权利的合法的吁求途径,还包括在所有合法途径无法奏效时诉诸全体公民的正义观而在公共讲坛上发表的和平请愿。通过法律的改良机制,原本被侵害的个人或群体最终受到了尊重,这既加强了受侵害个人或群体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也为全社会树立了一个尊重公民权利的楷模,加深了全体公民的安全感,这样的国家不是被破坏了,而是更牢固、更有凝聚力了。所以可以说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改良机制本身就是建立完善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秩序良好的社会
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想要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体系,反过来秩序良好的社会体系又依赖于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来维护,所以法律与社会是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
罗尔斯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接受并且知道所有其他人也都接受相同的正义观念和正义原则;(2)公众认为社会的基本结构能够满足这些正义原则;(3)公民具有一种通常情况下起作用的正义感。[6]虽然罗尔斯的说法相当理想化,但它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秩序良好社会的基本轮廓。在罗尔斯的观点中,正义原则居于核心地位,可以说,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正义一方面调节着社会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塑造着公民的正义感。
虽然古希腊人与我们一样重视正义问题,但二者对于“何为正义”的认识却是不同的,这主要是因为建构古代希腊社会和建构现代社会的基础不同,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而古希腊是建立在等级制之上的。
古希腊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存在着自由民、奴隶和外邦人的区别。就连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3]7雅典的民主制只及于公民,其公民范围非常狭窄,奴隶、妇女、儿童和外邦人都不在公民之列。这种不平等影响了希腊的正义观。我们认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种情况同种对待”是公正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正义”概念中内在地蕴涵了“平等”的概念。古希腊人的“正义”概念看起来与我们是一致的,“公正就是平分,法官就是平分者。”[7]138但是由于现实中的希腊人是不平等的,所以公正在人与人之间就意味着一种比例关系,如果两个人是平等的,那么同比例分配是公正的;如果两个人是不平等的,那么同比例分配就是不公正的,只有按照两人之间不平等的比例来分配才是公正的。“所以,公正在于成比例。”[7]135
所以,虽然从表面上看,古代希腊的政治社会与现代政治社会具有一种奇特的相似性:民主制和法治,但是古希腊社会的民主制和法治都带有等级制的特点。与此相对,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民主和法治的基础都是平等,我们的时代虽然能够容忍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分配,但无法接受人们在政治权利和义务上的不平等分配。在当前,“任何政治理论要想看起来合理,都以人人平等的理念作为其内核。”[8]比如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包含着一个更深层也更抽象的平等权利,[9]并且两个原则都是围绕着平等展开的。第一个原则赋予人们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个原则处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
另外与古希腊社会不同的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被罗尔斯称作“理性多元主义”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各种不相容但都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将会长期共存。他认为这种理性多元主义的事实不仅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种永久特征,而且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成果。[10]33每种哲学学说、宗教学说、道德学说都可以在公共领域里面言说自身,这就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多元并不导向相对主义,多元也并不意味着一切意见都是有价值的,不意味着我们丧失了判断是否善恶的标准。我们的多元社会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而从平等中可以衍生出那些我们极其珍视的价值观,比如民主、法治、正义等。所以我们时代的多元是平等之上的多元,我们的社会就是建立在共享基本价值观之上的多元社会。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法律自然成为维系公民的纽带。不论持有什么样的学说,所有人都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言说和行动。所以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必定是一个法治社会,在这个法治社会中,虽然人们各自信奉的哲学学说、宗教学说、道德学说不同,但人们却共享着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比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这种共享基本价值观之上的多元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只要人们能够对这些基本价值观形成共识,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是秩序良好的,也是稳定的。
正如罗尔斯所言,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人们的正义观念是共享的,但是人们对于正义观念的认可的理由不可能是一样的,所有人从自身所信奉的学说出发,出于各自的理由而支持正义观念,这样全社会就在正义观念上形成了一个重叠共识。[10]123也就是说,大家是有共识的,大家都相信什么是正义的,然而大家认可它的理由可能是不一样的。多元社会意义上的法治以及其他基本价值观也可以理解为这种意义上的重叠共识。有些人支持法治是出于一种共和的理想,有些人可能仅仅是出于害怕遭受不平等的对待,有些人想要生活在一个实质上人人平等的社会里,而有些人仅仅是厌恶官员的特权。不管你持有什么观念,最终这些人共同地想要一个法治的社会,有依法治国的政治诉求。
三、守法公民
良好的法律体系和秩序良好的社会从宏观上为法治打下了制度和文化的基础,而这两者的实现又有赖于愿意服从良法的公民,不被服从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没有法律有效调节的社会也只能是一片混乱。所以整个法治的基础最终建立在公民之上,与法治相适应的合格公民构成了法治的微观基础。
法治社会下的公民既包括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也包括普通公民。但出于理性能力、利害关系和参与意识的差异,公民会发生分化。仍以《克力同》为例,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出场的人物可以分为以下七类:一类是像苏格拉底那样完全服从理智的人,一类是像克力同那样虽然受大众意见左右但可以被理性说服的人,前两类人不论是在政治参与中还是在司法活动中,都更愿意运用理性说服的方式来影响他人。第三类是可以被利益收买而愿意徇私舞弊的人。被克力同收买的狱卒就是这类人。这类人可以是公职人员,也可以只是普通公民,他们在没有公职时只是一个潜在的徇私舞弊者,一旦有条件就会表现出来。第四类是能够利用法律的人,他们将法律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那些诬告苏格拉底的人就是这类人。第五类人与第四类人一样,都能够利用法律来达到一定的目的,然而第五类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被法律保护的正当目的,那些个人权利被侵害而向司法机关提出诉求的人就是这类人。第六类不是作为案件的当事人而参与到司法活动中,这些人构成了审判苏格拉底的时候500名陪审团的成员。他们或者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者总是被大众意见左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普通人,有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热情。第七类实际上没有出场,是那些不关心政治也不参与政治的人。这类人主要是奴隶和外国人,没有公民权。所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是沉默的,他们人数众多,但被制度性地排除在政治之外。
在现代社会中也存在苏格拉底或克力同那类人,他们是因为理性而服从法律,并且也能够被理性说服,然而他们服从法律的理性理由无法被所有人接受。多数人是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或者是出于对违法所受惩罚的恐惧而选择服从法律的,这时候他们就把守法当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当法律有利于自身时,他们会倾向于遵从法律;当法律不利于自身时,他们就倾向于逃避法律。在我们的社会同样有投机分子,他们的参与并非是为了维护法治,而是想要借制度获利。也有像赫拉克利特一样的避世者,他们不关注政治。不同类型的公民对于法治拥有不同的认识和意愿,社会的任务并不是使他们的认识完全一致,而是努力把他们的多种认识和意愿协调起来,使它们在法治之上形成一种重叠共识,从而构成对法治的支持。
为了实现这一重叠共识,就需要培养出与法治相适应的公民,这些公民虽然最关注自身的利益,但他们却愿意在法律的框架内用与他人利益相容的方式来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们的正义感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对于自身的违法行为能够给予良心上的拒绝;并且他们不把遵守法律当作权宜之计以待合适时机用违法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是把个人的自尊和价值感建立在由法律所规定的正义的实现之上,这种实现既体现为被公正对待,又体现为公正待人。以上的三个方面,即对自身利益的合法追求、对违法获利的良心拒绝和建立在正义之上的自尊和价值感,共同构成了与法治相容的公民的道德心理学。
为了培养这种与法治相适应的公民,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外在的方面就是建立完善的法治体系。用制度来管理人,将所有不同认识和意愿的人纳入一个完善的法治体系之内,这样个人守法与否就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取决于这个法治体系。这个法治体系需要良好的法律、公正的司法和严格而无差别地执法,只有如此,才能树立起法律本身的权威。“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律本身都力促对其自身神圣性的信念。”[11]18而法律的神圣性可以通过其内在的权威建立起来。然而只有制度是不够的,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人愿意被制度约束,所以第一位的仍然是意愿问题。大家普遍都愿意被法律约束,那么制度本身才会有约束力。这种愿意不是口头的愿意,而是内心实质的愿意。当然不需要所有人愿意,只需要一定比例的人有这种实质的意愿,这些人既分布在普通公民之中,又分布在执法者之中。所以在建立好制度的同时,在内在方面还要培养公民守法的意愿,这就需要进行公民教育,培育公民意识。公民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也包括公民的法律实践和实质的政治参与。只有具有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公民实质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法治才有公民基础,才会牢固地树立起来。
通过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最终使公民不仅知法,同时拥有法治精神,愿意守法,愿意把法律作为个人行为的规范。而最终的目标是要培养起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从内心中尊重法律,敬畏法律。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1]3卢梭也说,最重要的一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12]
在建设法治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守法的榜样,苏格拉底正是一个守法的榜样,但很难说他是个好榜样,不是榜样本身不好,而是这个榜样难以学习,难以模仿。像苏格拉底一样的人在现实中可能有,但一定很少。与苏格拉底相比,克力同更有现实意义。他是一个同样受大众意见左右,关注个人利益的普通人,但他却是一个可以被理性说服的人。在公共领域,我们借助公共理性言说、说服和被说服,我们的利益诉求可以在理性范围内讨论、辩驳和确认。像克力同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公共领域里的合格公民。而我们公民教育的目标也不是培养像圣人一样的苏格拉底,而是普通人克力同。
[1] 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M].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洛克.政府论(下)[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4.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M].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003重印).
[6] 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6.
[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8]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M].刘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4.
[9] 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吴玉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236-237.
[10]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1]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2]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70.
[责任编辑 王银娥]
On the Three Foundations of Rule of Law-Law, Society and Citizen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lato’sCrito
XI Yong-zhao
(DepartmentofPhilosophy,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430074,China)
It depends on a solid foundation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socie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foundation is built up by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parties: law, society and its citizens. S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depends on a well-ordered society, an excellent legal system and the citizens, who are willing to obey the law.Critois an early Plato’s dialogue, which has set an example for law-abiding. We can get some inspirations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from the analysis ofCrito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ncient Greek and the modern society.
Plato;Crito; law; society; citizen
B502.232
A
1001-0300(2017)01-0047-05
2016-09-16
惠永照,男,河南南阳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和康德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