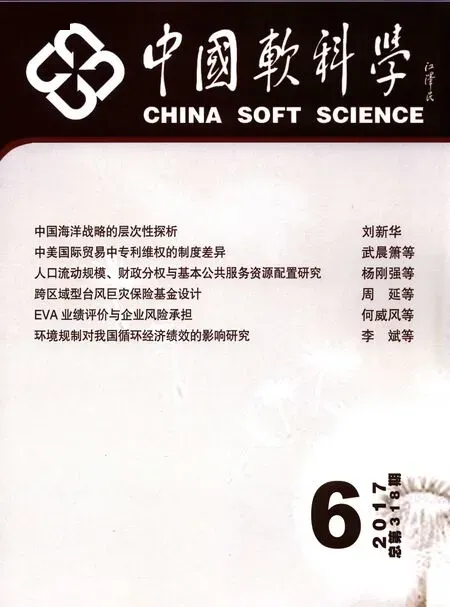中美国际贸易中专利维权的制度差异:基于案例的比较研究
武晨箫,李正风
(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
中美国际贸易中专利维权的制度差异:基于案例的比较研究
武晨箫,李正风
(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
本文以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美国断路器企业的知识产权纠纷为案例,分析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专利保护制度差异。研究发现美国在进口环节设置的337调查作为一种准司法制度,有效弥补了专利司法保护国际贸易领域的缺点,其实质是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具有“防火墙”的功能。比较而言,中国针对专利侵权的行政保护力度弱,未能真正发挥对司法制度的补充作用,同时本土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缺少有针对性并行之有效的专利维权渠道。本文认为,在整体上提高我国专利行政保护力度的前提下,有必要针对国内和国际贸易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特点,构建有差异的专利行政保护体系。
专利保护;国际贸易;337调查;案例研究;制度差异
一、引言
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仅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且要在国际竞争中有效地维护自主知识产权,同时要有效地利用市场这一战略资源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的创新战略和政策,比较强调知识产权的创造,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在全球竞争中专利维权的关注严重不足,如何合理利用市场资源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全球贸易市场中,知识产权维权问题一直存在。这对于目前正努力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的中国来说,更是不可避免的挑战。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一方面,我国企业研发出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由此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涉外专利维权风险;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我国企业也与国外企业发生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纠纷。
在已经发生的国际贸易专利侵权纠纷中,国内一些企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我国企业遭遇国际贸易知识产权纠纷的原因,学术界多有探讨。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产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经济、制度等大环境影响[1],如中外贸易持续顺差[2]、外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3]。另一方面,国内企业[4]、行业[5]和政策制度[6]确实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2-3],如我国企业技术能力弱,知识产权储备和运用不足;各主体不熟悉外国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和规则等。以美国337调查为例,337调查是对在美国进口贸易中知识产权侵权或其他形式的不公平竞争等行为展开的准司法调查。人们发现,近年来涉及我国企业和产品的337调查数量逐年上升,调查诉由以专利侵权为主,涉案产业高技术化趋势明显[7]。有学者对涉及到中国企业的337调查案件进行回顾,通过案例分析我国在应对337调查存在的问题[3],也有人试图针对调查的不同阶段[8]或调查涉及到的各个参与主体,在应对策略方面提出建议和对策[9-10]。
但在这些分析中,人们对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专利维权制度的差异的探讨尚不深入。而认识这种制度设计上的差异,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体系和知识产权政策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选择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领公司”)和美国企业在美国、中国发生的专利纠纷的案例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中美两国专利维权的制度差异,反思我国专利维权体系存在的问题。选择该案例的原因如下:第一,中国企业在美国337调查中多以和解或败诉告终,而通领公司海外维权案是“中国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完胜第一案”[9],并且“首次起诉美政府机构获胜”[10],其维权过程具有典型性。第二,自2004年起,通领公司遭到美国断路器企业巨头轮番提起的多次专利侵权诉讼与337调查。在应诉的六年时间里,通领公司经历了败诉、上诉、反诉等,可系统展现美国专利维权制度体系的特点。第三,在此案例中,美国断路器企业在美国制度体系内诉通领公司侵权,同时,通领公司在中国制度体系中诉美国企业的中国子公司侵权,是对中美两国专利维权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恰当案例。
通过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维权制度存在哪些差异?我国应如何处理专利司法保护与专利行政保护的关系,进而通过维权机制设计促进我国产业的发展并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
二、案例:通领公司与美国企业的专利纠纷
通领公司是我国一家生产断路器的民营企业。
断路器是一种漏电保护器,其工作原理是当设备探测到带电导体和回路导体间电流不平衡时自动断开电路,防止漏电事故发生。《美国国家电气法规》*《美国国家电气法规》最早于1879年由保险公司、机电业者、建筑业者和其他机构联合制定。1911年,由美国国家消防协会(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简称NFPA)接管,成为美国国家消防系列文件中的一部分(NFPA 70),是美国电气安全领域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每三年修订一次,现最新版本为2017版。(National Electrical Code,简称NEC)[11]规定,一套住宅必须至少安装八只断路器,且每两年必须更换一次。由于NEC在全美50个州适用,因此,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自20世纪80年代起,莱伏顿(Leviton)、库珀(Cooper)、帕西西姆(Pass & Seymour)、哈卜(Hubbell)等多家企业垄断了美国断路器市场。它们生产的接地故障断路器(Ground Fault Circuit Interrupter,简称GFCI)产品采用机电一体化漏电保护技术,并申请了大量专利,形成了密集而立体的知识产权高坝和陷阱。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接地故障断路器产品是以零功耗永磁式电磁脱扣和电磁复位原理实现自动控制的漏电保护技术,突破了传统技术局限[12],实现了自动复位、通讯控制和网络系统控制,提高了产品的安全性和检测灵敏度。
在进入美国市场前,为规避知识产权诉讼风险,通领公司委托两家美国律师事务所进行了产品侵权评估。在拿到两份不侵权司法意见书后,通领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凭借新颖的技术和较高的性价比,通领公司2004年在美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美元,占据了美国约10%的市场份额[13]。通领公司产品的迅速扩张引起美国断路器寡头的恐慌。自2004年起,美国莱伏顿公司、帕西西姆公司多次通过专利侵权诉讼、337调查等手段对通领公司发起进攻,试图将通领公司的产品挤出美国市场。从2004年到2010年,通领公司经历了艰苦的国际知识产权维权之路。在此过程中,通领公司也在国内提出了针对莱伏顿公司、帕西西姆公司中国子公司或生产商的专利侵权诉讼。
2004年,拥有60%美国断路器市场份额的莱伏顿公司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先后在美国三个州四个不同地方法院起诉通领公司的美国经销商专利侵权[11]。通领公司主动以第二被告身份介入此案。经过3年多的对抗与较量,通领公司两次拿到不侵权的马克曼命令(Markman Order)*马克曼命令(Markman Order)是美国法官根据马克曼程序做出的审理专利侵权纠纷、解释专利权利要求、确定保护范围的司法裁决,对侵权判决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2006年5月23日,通领公司拿到针对558专利不侵权的马克曼命令。根据美国法律,在马克曼程序中败诉的当事人不能提起上诉。但莱伏顿公司隐瞒了正与通领公司打官司的事实,用766专利再次起诉。2007年3月5日,通领公司再次拿到针对766专利不侵权的马克曼命令。。最终,2007年11月,莱伏顿公司以不上诉为条件与通领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这场备受中外媒体关注的“中美知识产权官司第一案”[14]是我国企业在美国知识产权纠纷案中第一次被判完全不侵权。
2007年,美国帕西西姆公司以专利侵权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USITC)提起通领公司等多家企业侵犯其美国知识产权的337调查(案件号为337-TA-615)。同时,帕西西姆向美国纽约联邦北部分区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2009年,USITC下达337调查终裁判决,裁定通领公司侵犯帕西西姆公司的美国专利,对中国企业产品实行有限排除令。2010年8月,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通领公司不侵权,撤销对通领公司的有限排除令。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彻底推翻USITC的337调查。
2010年,莱伏顿向USITC提起针对通领公司等企业的337调查(案件号为337-TA-739)。由于莱伏顿与通领公司曾达成和解协议,通领公司主动向美国新墨西哥州联邦地方法院提出诉讼。2010年12月,美国新墨西哥州联邦地方法院判令莱伏顿在一周内撤销针对通领公司的337调查。至此,通领公司跨国维权之路终于告一段落。
在应对美国企业发起的专利诉讼与337调查的同时,通领公司采取反制策略,在中国先后两次起诉美国企业中国子公司侵犯通领的中国专利。
2006年,在莱伏顿公司通过美国联邦法院专利诉讼起诉通领侵权的同时,通领公司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美国莱伏顿公司中国的子公司立维腾电子(东莞)有限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侵犯了通领外观设计专利。立维腾公司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判定通领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无效。2007年3月,立维腾公司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维持通领公司专利有效的决定[15],转而在北京法院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和通领公司。在经过一审、二审[16]后,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发布终审判决,裁定通领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17]。立维腾公司采用专利无效策略成功地应对了通领公司在中国发起的第一次反击。
2008年,在通领公司全力应诉帕西西姆337调查的同时,发现帕西西姆在华制造的GFCI产品侵犯了其子公司希珂尔电气有限公司的中国发明专利,随即向国家海关总署提出海关保护申请。2008年7月,希珂尔公司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美国帕西西姆公司在华生产企业东莞长安讯诚电业制品厂告上法庭。与立维腾的策略相同,长安讯诚提出涉案专利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经审查判定希珂尔专利权利要求10无效,在权利1-9的基础上继续维持专利有效[18]。然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0日判定长安迅诚的产品未落入希珂尔专利权利要求范围内,因此未构成侵权[19]。至此,通领公司在中国发起的两场以反制为目的的维权官司均以失败告终。
三、美国337调查的制度设计及其实质
通领公司知识产权维权的案例不仅涉及到涉案的国内外企业,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维权制度上的差异。对该案例的分析表明,在美国的国际贸易中专利维权体系中,337调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337调查是独立于美国联邦法院体系的准司法调查。更为重要的是,337调查仅适用于美国进口知识产权纠纷。通过比较分析337调查与美国专利司法保护的关系及其差异,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美国337调查这种制度设计的目的。
(一)337调查的历史演变
美国337调查的法律依据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1922年关税法》,其中第316条规定,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行为属于非法行为,总统有权对相关产品增加关税或禁止其进入美国。这是一条总摄性条款,立法者的目的是通过提高关税或禁止相关产品入境来限制不公平竞争。1929年,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为在大萧条中保护本国利益,美国国会将《1922年关税法》第316条纳入《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对在美国进口贸易中知识产权侵权或其他形式的不公平竞争等非法行为进行337调查[20]。
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本国企业产品,美国大力宣扬自由贸易,要求各国开放市场,在此期间几乎无人提起337条款。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滞涨为337条款的复兴提供了机会。首先,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国造成冲击,1971年美国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其次,知识产权逐步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美国产业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在动力愈发强烈。最后,由于司法程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存在不足,尤其在国际贸易中,司法程序往往缺乏效率、取证困难,侵权人可以通过变更美国进口商轻易规避法律制裁。因此,美国产业界建立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337条款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21世纪后,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低迷,337调查数量不断增长。
337条款作为337调查的法律依据,经过《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多次修改。一方面,美国国内产业界不断游说政府保护国内企业的利益,降低美国企业提起337调查的门槛,使申诉人能够更为轻易地证明进口产品侵犯了其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企业在337调查中受到打压,来自国际产业界的压力迫使美国对337条款进行了局部修改[3]。可以说,促使337调查规则不断演变的动力源于美国产业界与国际产业界的博弈、美国对国内企业的贸易保护与国际市场自由竞争原则之间的张力。
(二)337调查与美国专利诉讼的比较
由于337调查仅适用于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纠纷,比较该调查与美国专利诉讼的差异可以更好地揭示其制度设计的目的。
从337调查的程序看,在申诉人提出337调查申请后30日内由USITC下设的不公平进口调查办公室审核并给出是否启动调查的建议,在立案后的45日内提出结束调查的目标日期,由行政法官进行取证、审理并给出对初裁结果和救济措施的建议,之后由USITC委员对337调查案件进行裁决。在337调查中,美国联邦法院体系的作用包括:(1)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受理337调查中的反诉及平行诉讼;(2)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不服USITC最终裁决的上诉进行一审判决;(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337调查上诉进行终审判决[3]。
实际上,从337调查开始至USITC终判,一直是准司法程序。如果被告不服USITC的终裁判决,可向联邦法院上诉,案件才真正进入司法审查程序。337调查与司法调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案条件和成本。美国337调查立案条件极低。申诉企业不需缴纳诉讼费用,只需递交申诉书即可。在立案材料方面,在1988年对《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的337条款进行修订后规定,337调查中的知识产权案件立案时,只需要申诉方提供行为要件和产业要件,而不需提供损害要件。在申诉人方面,337调查对申诉人或企业的国籍或注册地不做限制,只要申诉人认为其在美登记注册的知识产权受到进口产品侵犯,或认为进口产品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并证明美国国内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相关产业,即可向USITC提起337调查申请[3,21]。
比较而言,美国司法体系需要申诉人证明损害的存在,即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相对于普通民事诉讼,专利侵权案件的取证更为困难[28]。首先,专利侵权具有行为隐蔽性。侵犯专利权不是对有形财产的直接占有,而是以同样的专利技术方案制造产品或实施方法。第二,专利具有公开性,专利权人难以获得侵权人复制其专利产品的翔实证据。尤其是如果侵权事实发生在境外,侵权的证据更无从查起。第三,司法制度对专利侵权证据的要求非常严格。因此,通过美国专利司法保护体系,专利权人在立案前的取证工作上就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和精力。
在前述案例中,作为申诉企业,莱伏顿公司或帕西西姆公司只需向USITC提出我国接地断路器产品侵犯了其美国知识产权且美国国内存在断路器产业,无需费力收集证据证明我国产品究竟如何侵权,也无需证明我国产品给企业或产业带来多大损失,即可提出337调查,调查立案成本极低。
第二,案件管辖权。337调查对案件管辖权的要求较为宽松。在涉及到通领公司的两起337调查案件中,涉案的中国企业并没有在美国直接设立分公司,而是通过中间商将产品销往美国,但也被列为被申诉人[3,23]。宽松的管辖权为美国专利权人维权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在美国司法体系内,对管辖权的限制较为严格,要求被告必须能够以法律规定的方式被送达、必须在美国境内拥有可执行的资产[3]。在进口产品环节,外国制造商在美国境内一般没有工厂或经营场所,如发生侵权行为,美国专利权人只能起诉该产品的进口商。国外的生产商可以轻易地通过更换美国进口商规避司法制裁,继续由其他美国进口商进口侵权产品。特别地,由于外国制造商不是案件当事人,法院难以要求他们提供专利诉讼所需的材料,进而无法调查取证。
第三,救济措施。专利司法诉讼判定被告存在侵权行为后,只能针对有限的被告执行惩处措施、裁定金钱赔偿,但不能向非被告颁发禁令。而在337调查中,虽然无法使申诉企业直接得到经济赔偿,但USITC除可以发布针对特定当事人产品的有限排除令之外,还有权发布普遍排除令,即不分进口产品来源地或生产商,禁止所有同类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甚至可以将侵权产品的上下游产品全部排除在外[3]。这样一来,通过337调查,胜诉的美国企业可以有效地阻止竞争产品进入美国。
在通领公司经历的两起337调查案中,USITC终裁分别发布了有限排除令和普遍排除令。如果中国企业不再向联邦巡回法院上诉,USITC普遍排除令成立,那么我国漏电保护行业将重蹈VCD行业的覆辙,我国自主生产的接地断路器将失去美国市场,国内漏电保护产业将面临停产倒闭甚至消失的风险。
除了立案门槛低、管辖权限定宽松、救济措施严厉外,与美国联邦法院司法体系的专利侵权诉讼相比,337调查还具有审理周期短、被告应诉成本高等特点。一般地,337调查时间不超过12个月,较为复杂的案件也须在18个月内结束[3]。与美国司法体系专利诉讼审判周期相比,337调查的时间缩短了约一半以上,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的明显优势。此外,337调查是无赔偿诉讼,即使最终判定被申诉人不侵犯申诉人权利,被申诉人也得不到任何赔偿[3]。且由于案件涉及美国企业商业机密,中美两国语言、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律师通常很难发挥直接作用,被诉企业必须聘请美国律师。这就导致很多被诉企业由于无力承担巨额费用而不得不寻求和解、甚至直接放弃美国市场。
(三)337调查的目的与实质
从以上关于337调查的历史变迁,以及对337调查与美国司法调查差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337调查从一开始就有保护美国市场和美国产业发展的动机,只是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与贸易相关的国际规则的变化,以及知识产权重要性的提升,这种目的或动机在“反对不公平竞争”或“促进对知识产权的有效和充分的保护”等制度理念下有了更大的解释空间。事实上,在国际贸易中,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自由主义的原则有利于消除贸易壁垒和促进公平竞争,但全球竞争中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也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保护主义。这种张力在337调查中有突出的体现。
如果从专利保护的行政执法的角度理解337调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该调查的两种功能及其冲突。一方面,337调查有通过行政执法来弥补司法保护不足这方面的功能。Marisa A Pagnattaro等人[22]的研究认为:“在进口产品知识产权侵权方面,由于司法保护耗时长、过程具有不确定性,美国企业通常提起337调查作为最后的补救措施。”Jack Q Lever[23]也指出:“337调查是打击外国产品不公平竞争的有力武器,为美国产业提供了阻挡外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途径。在很多情况下,337调查是法院司法系统的重要替代与补充。”
但另一方面,337调查制度在确实为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有效渠道的同时,“337调查可能被用作抵制进口产品的贸易保护工具:在国际竞争中利益受到威胁的美国企业提起337调查是为了寻求贸易保护,而不是捍卫其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创新,但337调查制度可能损害创新、对研发投资产生负面影响:美国企业可能会发现从保护已有知识产权上获得的利润已经足够‘多’。因而337调查可能会被滥用为贸易保护工具,而非知识产权维权工具。”[24]有学者更加明确地指出:“USITC是一个拥有重要权力的强势机构,其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目的有时甚至会伤害专利体系的目标。”[25]
如果准确把握337调查在制度设计上的特点,可以更加清晰地发现该调查的实质。337调查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337调查仅针对进口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纠纷;其二,该调查明显有利于申诉人而不利于被申诉人。这种制度设计反映了337调查的根本目的,是要有效地维护美国知识产权、美国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通领公司的案例看,不论是美国企业直接发起的专利司法侵权诉讼,还是由通领公司不服337调查终裁上诉至司法体系,均以美国企业败诉或和解告终。可见,在美国司法体系下,美国国内企业并不能在以“公正”为宗旨的司法制度下“讨到便宜”。但是,这些美国企业却可以在以“保护”为根本指向的337调查中获得多方面的庇护,即便通领公司在最终的司法诉讼中获胜,但已经在多次337调查和漫长的司法诉讼中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丧失了发展的良机。可以说,美国在商品进口环节建立的337调查制度发挥了“防火墙”功能,通过专利行政保护,打压具有强劲竞争力的外国产品,阻碍其瓜分美国市场,从而为美国企业的利益提供了保护。
四、中国专利维权制度的特征与问题
在通领公司的案例中,通领公司也在中国对美国公司的专利侵权进行维权。但通领公司不是通过专利行政保护,而是通过司法诉讼来寻求保护。选择这种策略与中国专利维权制度的特点有关。
对比美国337调查及其与美国司法体系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专利维权在制度设计上涉及两方面问题:第一,从手段上看,专利的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关系;第二,从对象上看,不同的保护手段是否同等地应用于国内的专利纠纷和国际的专利纠纷。总体上看,美国专利维权制度的特点:第一,存在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两种互补的制度设计;第二,有区别地对待国内、国际的专利纠纷。具有行政保护和“准司法”特征的337调查仅适用于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纠纷。
下面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国专利维权制度的特点。
第一,专利行政保护是否成为专利司法保护的有效补充?专利司法保护是依据相关法律,为保护与恢复专利权人被破坏或侵害的利益,而对侵权人实施强制性的法律措施。专利行政执法则是政府机关或委托单位依法处理专利侵权行为、调节专利纠纷及查处假冒专利或专利侵权的具体行政行为。1994年,专利行政保护得到国际条约的认可。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规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采用行政手段,由此形成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轨制”方式。
司法审判的出发点在于执行法律,侧重于保护权利人的权益。专利司法保护具有力度大、权威性高、规则明确等优势,但由于遵循“不告不理”的听审原则,司法保护无法对侵害行为进行预防。同时,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侵权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成本收集证据。加之专利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取证难度大。司法程序也导致审判时间过长,一旦侵权人提出专利无效抗辩,即使严格按照各个阶段的审限,至少也需要三年时间才能结案[26]。以上因素导致可能存在司法保护失灵情况:“在调查取证不能、发现侵害人不能、制止侵害行为继续不能、畏惧诉讼程序繁琐、预期获赔数额低于诉讼成本,以及大规模、群体性侵权等情况下,都会出现民事司法救济‘失灵’的现象”[27]。
相比较而言,专利行政保护作为专利司法制度的有效补充,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正”[28]。专利行政执法注重效率,执法程序便捷,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与灵活性,有利于及时解决矛盾,维护专利权人合法权益。在处理侵权纠纷的过程中,专利权人可请求专利管理部门调查取证,相较于司法诉讼,专利权人付出的成本较低。同时专利行政执法人员调查取证也具有专业性优势。
我国自1984年建立专利制度起,就施行专利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两条途径,协调运作”[28]的策略。特别是在我国专利制度建立之初,司法救济调处社会纠纷的力量不足[29],行政保护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此后《专利法》修改的过程中,行政保护的执法力度被明显弱化。2000年《专利法》第二次修改[30],明确了行政保护的地位在司法保护之后,取消了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最终决定权;同时弱化了专利行政机关对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理,取消了专利行政机关责令赔偿的职权。这样一来专利行政执法部门只能调解或责令停止侵权,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侵权行为人的主动配合。针对专利侵权案件,专利行政执法部门无法使用暂扣、查封、没收、赔偿等行政执法手段或措施,仅拥有行政调处权。2011年开始施行的《专利行政执法办法》[31-32],明确了专利行政执法的原则与制度、主体与职权以及执法程序等,但并未对针对专利侵权的行政执法权力做出修改。
在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或调解中,专利行政执法部门对侵权人不具任何威慑或约束作用。若当事人不服行政部门做出的处理决定,反过来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部门的权力和责任严重不对等,这一方面导致专利行政执法力度弱,专利权人往往不愿寻求专利行政保护,被申诉人也可以通过上诉轻松地使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执法部门因担心发生行政诉讼影响绩效考核而不愿处理专利侵权纠纷[33]。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保护对专利维权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可以认为我国专利行政保护并没有成为专利司法保护的有效补充。
从通领公司的案例看,在面对两家美国企业在华子公司进出口环节出现的专利侵权问题时,通领公司选择提出专利侵权诉讼,走司法保护程序,而没有选择行政保护程序,固然与我国没有专门针对国际贸易中专利侵权的行政保护有关,但也是因为我国现行的行政保护制度作用相当有限。
第二,是否应有区别地对待国内专利侵权纠纷与国际贸易中的专利侵权纠纷?美国对专利行政保护或“准司法”体系的执行范围进行了限定,专利行政保护仅适用于国际贸易中的专利侵权纠纷,在美国国内并无针对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保护体系。对此,有学者认为,美国产业竞争秩序较为稳定、规范,企业专利意识较强,鲜有大规模、群体性的侵权案件,因此国内专利侵权的处置为法院诉讼。但在国际贸易中,涉及到复杂多样的主体,通过司法诉讼解决专利侵权纠纷非常困难,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建立了行政保护制度[29]。我们此前的分析表明,以337调查为代表的美国专利行政执法手段只用于进口贸易,其实质是要保护美国市场、产业和企业,维护美国国家经济权益、美国专利权人在国际贸易中的权益,其制度设计目的与功能与司法体系有很大不同。
实际上,我国有与美国337调查类似的专门针对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摩擦的法律规定。2004年4月6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增加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专章,该法第29条规定:“国家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保护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进口货物侵犯知识产权,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侵权人生产、销售的有关货物进口等措施”[34]。该法条对进口贸易中知识产权侵权的行政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我国至今尚未在该法律规定下形成专门针对进出口产品的、可操作的调查和维权制度体系。换言之,就维权体系看,我国的行政专利保护和司法专利保护在实际操作上仍然未对国内专利侵权、国际贸易中的专利侵权做出区分。
从理论上看,把专利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种手段运用于国内专利侵权及国际贸易中的专利侵权,在把司法保护作为必须手段并保持其一致性的前提下,我们的制度设计可以有四种选项。(1)不论是国内专利侵权,还是国际贸易中的专利侵权,均采用统一的司法保护,而不使用行政保护的手段;(2)对国内专利侵权运用司法保护;对国际贸易中的专利侵权运用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种手段;(3)对国内专利侵权、国际贸易中的专利侵权,均运用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种手段,并使用统一的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4)对国内专利侵权、国际贸易中的专利侵权,均运用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种手段,但在司法保护保持一致性的情况下,在行政保护方面有所差异。
第一种制度设计难以避免司法保护的不足,专利保护的力度有限,维权的成本较高。第二种制度设计大体与美国相似;第三种制度设计与目前中国制度设计的实际运行情况相近。但如果行政保护的力度不大,被侵权人不愿意提请行政保护,这种制度设计实质上将与第一种制度设计类同。因此要想使这种制度设计真正发挥作用,加强行政保护力度,使之真正成为司法保护的必要补充是一个必要条件。第四种制度设计涉及到针对国内专利侵权、国际贸易中专利侵权行为的不同,充分考虑国际贸易中专利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专利维权的需求和目标的差异,制定有区别的行政保护措施。
从目前我国专利保护制度设计及其实际运行状况看,一方面,我国和美国的专利司法保护体系较为相似,在国际贸易中的专利维权不具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行政保护不能作为司法保护的必要补充,被侵权者往往不得不主要依赖司法保护。从通领公司的案例看,其在国内起诉美国公司侵权时,最终选择司法途径,立案之前原告付出大量时间精力收集侵权证据、被诉企业提出管辖权异议拖延审理时间[35]、在被告交足担保金后海关放行了扣押的疑似侵权产品,其结果是本土企业维权的成本很高。
从我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看,随着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不仅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将面临越来越多的专利纠纷,在国内市场也将面临越来越多的产品专利维权问题。而且这种国际贸易中的专利维权不仅涉及到涉案企业,也关系到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关系到国家利益。考虑到国际贸易中的专利侵权,往往存在涉案国外企业差异性大、多样性强,取证复杂、难度大,以及调查和处置涉及到法院、知识产权局、商务部、海关等多个部门的协同,我们认为,有必要针对国内和国际贸易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特点,构建有差异的专利行政保护体系。
因此,通过以上关于中美国际贸易中专利维权的制度对比和分析,我们更倾向于第四种制度设计,即对国内专利侵权和国际贸易专利侵权,均运用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种手段,但在司法保护保持一致性的情况下,在行政保护方面针对其特点而有所差异。一方面要从总体上提高行政保护的力度,赋予行政保护更大的管辖权,允许专利行政执法部门在专利侵权案件中使用暂扣、查封、没收、赔偿、责令赔偿等实权,以提高执法的权威性、有效性和操作性,使行政保护真正成为司法保护的必要补充。另一方面,要针对国际贸易中的专利维权特点和目标,形成更能够整合知识产权局、商务部、海关等多个机构职能的专利维权体系,改变各部门职责不明、分工不清、协调不力的状况,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保持司法体系公平、正义与行政保护快速、灵活的张力,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为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保护国家利益提供保障。
[1]冉瑞雪. 337调查突围:写给中国企业的应诉指南[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2]何培育. 中欧国际贸易知识产权纠纷与对策[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8(5): 109-113.
[3]张 平,黄贤涛. 产业利益的博弈——美国337调查[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4]刘梦兰. 发展企业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浅论[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8 (6): 26-29.
[5]杨丹丹. 由“337调查”引发对行业协会作用的思考[J]. 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6 (5): 31-32.
[6]卢海君, 王 飞.“走出去”企业知识产权风险研究[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27(2): 40-46.
[7]常 雁, 毛雅君. 浅析我国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基于中美知识产权贸易争端中“337条款”的思考[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 67-70.
[8]牟 燕. 美国337条款调查应对策略之实证研究[D]. 福建: 厦门大学, 2007.
[9]张 君. “以夷制夷”中国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完胜第一案——记浙江通领科技集团海外维权路[J]. 中国经贸, 2011 (9): 50-53.
[10]新浪财经. 中国企业首次起诉美政府机构获胜[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917/07588673723.shtml, 2010-09-17/ 2016-12-01.
[11]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NFPS70: National Electrical Code[EB/OL].http://www.nfpa.org/codes-and-standards/document-information-pages?mode=code&code=70&tab=about, 2016-12-01.
[12]通领科技. 企业概况[EB/OL]. http://www.chgpg.com/aboutus1.htm, 2016-12-02.
[13]范 炜. “走出去”企业海外维权问题——对浙江通领科技集团知识产权海外维权的深度调查[J]. 浙江经济, 2011 (10): 23-25.
[14]新华网.“中美知识产权第一案”胜诉后的反思[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10/10/content_6856953.htm, 2007-10-10/2016-03-02.
[15]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插座(接地故障断路器GFCI)[EB/OL]. http://app.sipo-reexam.gov.cn/reexam_out/searchdoc/decidedetail.jsp?jdh=WX9268&lx=wx, 2016-09-23.
[16]北京法院网. 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等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EB/OL]. http://bjgy.chinacourt.org/paper/detail/2010/07/id/270874.shtml, 2010-07-06/2016-09-23.
[17]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 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立维腾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再审行政判决书[EB/OL]. http://ipr.court.gov.cn/zgrmfy/zlq/201310/t20131022_159554.html, 2013-10-22/2016-12-03.
[18]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避免压敏电阻失效的装置及方法以及接地故障断路器[EB/OL]. http://app.sipo-reexam.gov.cn/reexam_out/searchdoc/decidedetail.jsp?jdh=WX13262&lx=wx〗, 2016-11-23.
[19]北大法宝. 希珂尔电气有限公司与东莞长安迅诚电业制品厂等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EB/OL]. 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rwt/160/http/P75YPLURNN4XZZLYF3SXP/case/pfnl_1970324837862629.html?keywords=%E5%B8%8C%E7%8F%82%E5%B0%94&match=Exact, 2016-11-03.
[20] Unti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337 Info-Unfair Import Investigations Information System[EB/OL].http://pubapps2.usitc.gov/337external/, 2016-12-02.
[21]钟 山. 美国337调查规则, 实务与案例[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22] Marisa A Pagnattaro, Stephen K Park. The long arm of section 337: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s a global business remedy[J].American Business Law Journal, 2015, 52(4): 621-671.
[23] Jack Q Lever.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import trade: action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J].The Business Lawyer, 1986, 41(4): 1165-1186.
[24] Catherine Y Co. How valuable are the patent behind section 337 cases?[J].World Economy, 2004, 27(4): 525-539.
[25]Bruno G Simões. What’s the deference? why the federal circuit's treatment of itc section 337 cases raises agency-specific precedent concerns[J].The Kansas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2013, 23(1): 104-119.
[26]王志刚. 论行政保护框架下的专利侵权救济[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3):131-134.
[27]董 涛. 专利权保护网之漏洞及其弥补手段研究[J]. 现代法学,2016(2):43-60.
[28]刘银良. 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的弊端:历史的选择与再选择[J]. 知识产权,2016(3): 33-44.
[29]万里鹏. 我国专利行政执法制度实证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2015(9):119-123.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法第二次修改的说明[EB/OL]. http://www.sipo.gov.cn/zxft/zlfdscxg/bjzl/200804/t20080419_383844.html, 2006-12-28/2017-03-30.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60号) [EB/OL]. http://www.sipo.gov.cn/zcfg/flfg/zl/bmgz/201310/t20131025_861844.html, 2011-01-13/2017-03-30.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修改<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的决定》(第71号) [EB/OL]. http://www.sipo.gov.cn/zcfg/flfg/zl/bmgz/201310/t20131025_861844.html, 2015-06-01/2017-03-30.
[33]冀 瑜,李建民. 试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及其完善[J]. 知识产权,2011(7):97-99.
[3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EB/OL].http://www.gov.cn/flfg/2005-06/27/content_9851.htm, 2005-06-27/2017-03-16.
[35]北大法宝. 东莞长安迅诚电业制品厂等与希珂尔电气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EB/OL]. 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rwt/160/http/P75YPLURNN4XZZLYF3SXP/case/pfnl_19703248390
83128.html?keywords=%E5%B8%8C%E7%8F%82%E5%B0%94&match=Exact. 2017-03-04.
(本文责编:王延芳)
The Differences of Patent Protection Syste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ase-based Comparative Study
WU Chen-xiao, LI Zheng-feng
(Instituteof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 among China’s Tollea Group 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circuit breaker enterprises, we analyzed two countries’ patent protection syste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e found that the 337 investigation, which is a special quasi-judicial institution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ort and export links, acts as a great supplement to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essence of 337 investigations is to protect the domestic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the function of the “fire wall”. However, comparatively speaking, the power of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aimed at patent infringements in China’s is quite weak, so that is not qualified enough to make a complementation to the judicial system. As a result, the China’s domestic enterprise cannot find an effective way to protect their patent right and is in an inferior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refore, we suggest China establish different patent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systems applied respectively in inland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the premise of generally improving the patent administration protection in our country.
patent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trade;337 investigations; comparative study;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2016-12-14
2017-04-28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中国重大科技创新的社会研究:案例分析与理论探索”(20141081191)。
武晨箫(1991-),女,北京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政策。通讯作者:李正风。
G306.3
A
1002-9753(2017)06-0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