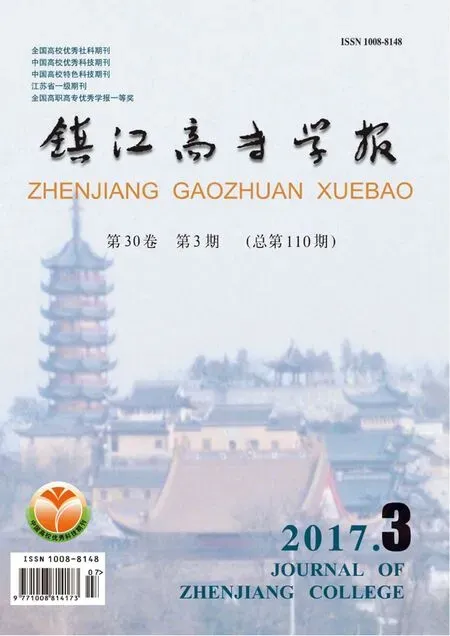借鉴与创化
——《万寿寺》《暗店街》比较论析
高 强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借鉴与创化
——《万寿寺》《暗店街》比较论析
高 强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王小波的《万寿寺》与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对侦探模式有着不同的处理,结构相似,主题形同而异质。莫迪亚诺对王小波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特别是其代表作《暗店街》,不仅被王小波在《万寿寺》中多次提及,而且对《万寿寺》的整体结构和深层意蕴产生了较大影响。
王小波;莫迪亚诺;《万寿寺》;《暗店街》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得益于对众多外国作家的借鉴与吸收,其兄王小平曾谈到:“有人说,他是从古典文学,从那里面探索出来的。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知道的最清楚,他那时思考的形成,和前人不一样,都是从外国的东西里面来的”[1]99。王小波本人亦曾多次著文谈到他的师承,谈那些让他敬仰的作家。其中既有如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乔治·奥威尔这样名扬海内外的文学巨星,也有卡尔维诺、尤瑟纳尔、杜拉斯、图尼埃尔这样知名度相对较小的作家,而法国作家莫迪亚诺(一译为莫狄阿诺)无疑属于后者,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王小波的推荐,莫迪亚诺才开始慢慢被中国读者所熟知。作为王小波口中体现了“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的那类作家,莫迪亚诺对王小波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特别是其代表作《暗店街》不仅被王小波在《万寿寺》中多次提及,而且对《万寿寺》的整体结构和深层意蕴产生了较大影响。将王小波的《万寿寺》与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并置一处,考同辨异,有助于我们在更深的层面理解王小波和他的文学创作。
1 对侦探模式的不同处理:化用与戏谑
借用侦探小说的手法和结构,这是莫迪亚诺《暗店街》一个比较突出的特色。作者在借用的同时,又作了个性化处理,使侦探模式与小说的严肃主题相得益彰。首先,主人公侦探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至于“凶手”这一侦探小说中常设角色,莫迪亚诺小说中却不存在。其次,莫迪亚诺对悬念的处理,与柯南道尔、克里斯蒂这些侦探小说大师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悬念的设置不同。《暗店街》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悬念——“我到底是谁”,但这个悬念不像一般侦探小说那样关乎一个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某个行为的真相,很具体;在《暗店街》、在莫迪亚诺那里,悬念往往是巨大的、笼统的、形而上的,“我”的真实身份这一问题,关乎一个人整整一段生活,属于生存论意义上的悬念。其次,对悬念结局的处理不同。在侦探小说中,悬念到最后一般都会揭晓,这个答案往往还相当出人意料。但在莫迪亚诺那里,要么直至小说结束疑问还仍然存在,要么导向悬念结果的,“总是一个个平常的细节、淡化的场景”[2]294,绝不会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发生。《暗店街》即是如此,那个困扰主人公的巨大疑问在小说结束时,依旧无解。居伊不远万里前去寻找那个唯一能够揭开自己身份谜团的人——他的昔日好友弗雷迪,然而弗雷迪已在不久前一次事故中不幸罹难。怅然若失的居伊决定到罗马暗店街2号即他的出生地去进行最后的尝试……小说便在一片浓重压抑的阴霾中结束了。这种对悬念结局的处理,使我们在读完《暗店街》后,没有像读完一部其他侦探小说那样有种释然的感觉,反而更为揪心,而这种延续不休的疑问背后往往大有深意,“他更具有使你在掩卷之后又情不自禁要加以深思的魅力,一种寓意的魅力”[2]295。
莫迪亚诺在《暗店街》中娴熟地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手法,有条不紊地驾驭着情节的演进,并使情节与主人公心理的波荡起伏相互映衬,从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与此同时,莫迪亚诺并未仅仅停留于表面的侦探小说技巧的运用,而是把侦探小说化为他自己小说的骨髓,成为其小说探查生存真相与表达深层意蕴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柳鸣九所言:他小说中的人物往往都置身于某种“恐慌感与危机感”之中,为了摆脱这一处境,他们都在苦苦寻找自己的根、自己的归依、自己的支撑点,这些寻找和探查,“正是他们的存在感与存在意识所促使出来的生存行为”[2]308。
在王小波《万寿寺》中,同样存在侦探小说的痕迹,不过与莫迪亚诺的处理方式判然有别,在王小波那里,侦探模式成为他拆解和戏谑的对象,这种戏谑化处理表现为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现实世界中,失忆后的“我”对过往似乎避之惟恐不及,于是,“我”并没有像《暗店街》里的居伊那样,想方设法去寻回记忆,“我”的寻找行为自始至终都是消极被动的。而且在《暗店街》中,德尼兹、弗雷迪这类与过去的“我”有着亲密交集的人物,在居伊四处奔走的寻访下也没有出现,他们都是隐匿的,这让小说情节更为曲折离奇,整体氛围愈加神秘朦胧。但在《万寿寺》里,“我”过去的见证者——无论是白衣女人还是表弟——都不请自到,并且他们还帮助我顺利轻松地恢复记忆。《暗店街》中处心积虑、千辛万苦的寻觅行为,到了《万寿寺》中则变得如此简单,以至“我”颇为无奈地调侃道:“在《暗店街》里,主人公花了毕生的精力去寻找记忆,直到小说结束时还没有找到。而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把很多事情想了起来,这件事使我惭愧”[3]228。侦探模式被王小波予以了戏谑化处理,一切都显得那么滑稽、不值得:别人劳神费心的行为在“我”这里变得不堪一提,别人朝思暮想的过去在“我”这里又是那么索然无味。“莫迪阿诺没有写到的那种记忆必定是十分激动人心,所以拼老命也想不起来。而我的记忆则令人倒胃,所以不用回想,它就自己往脑子里钻。”[3]228在这里,作者对于侦探小说模式的肆意捉弄指向了对乏味、庸俗的现实生活的背离和否定。另外,在想象世界里,作者也对侦探小说模式进行了戏谑化处理。尤其是写到薛嵩遇刺后,“我”对刺杀行为进行的一系列假想,每一次假设都建立在对前一种设想予以推翻的基础上,如此便衍生出了多种解释、多种故事版本。
这种戏谑化处理与王小波的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他在《万寿寺》中借助王二之口说到:“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可以是任何人。我又可以拒绝任一时间、任一地点,拒绝任何人。假如不是这样,又何必要有小说呢?”[3]225。这里所表达的是王小波对于创作上教条化准则的反抗、对于写作自由的追求、还有对于作品有趣轻松的肯定。王小波说:“我自身的体会是,写起东西来还是应该……举重若轻。”[1]221“举重若轻”是要以“艺术之轻”去化解、抵抗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重压,去表达思想层面的“重量”。
2 结构相似:复合文本、双重时空与双重主人公
莫迪亚诺的《暗店街》讲述了私家侦探居伊·罗朗不幸在一次事故中丧失了记忆,只能以伪造的身份生活于世,为了摆脱失忆造成的痛苦和迷惘,他决心追查自己的过去。在追查、寻觅过往的故事中,出现了大量他人的讲述、往来信件、年鉴、电话通讯簿、调查材料、身份证明、文书档案以及历史遗迹之类的东西,它们经常独立成章,成为小说另一个叙事者,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凡此种种,“都是‘我’藉以顺藤摸瓜的阿里阿德涅线团”[4]143。正是因为这些零零碎碎材料的“讲述”,“我”的过去才徐徐展开——尽管旋即又被怀疑与遗弃。某种意义上,上述材料组成了一个“次文本”,它们与居伊的寻找故事一道构成了《暗店街》这一“复合型文本”。
《万寿寺》中同样存在类似的“次文本”结构:即与“我”此时此刻经历相对照的“我”在失忆前创作的手稿。手稿讲述的是在晚唐时,一个名叫薛嵩的纨绔子弟买得湘西节度使一职,率领随手招募的亲兵和两个随营妓女来到湘西凤凰寨。在这里,他遇到了苗女红线,并抢她为妻。后来,他遭到行刺,并与刺客展开了周旋……失忆的“我”在阅读手稿过程中,觉得现在这个写法很是无趣,“就像一张或是一叠白纸,像纸一样单调、肃穆、了无生气”[3]22,而里面的主人公薛嵩“虚伪、做作”,让人不满,于是“我”便对其进行了反复改写,同一个故事被以多种手法予以讲述,从而变得枝节横生。由此,《万寿寺》产生了两个叙事层面:一方面是失忆后的“我”在现实中寻找回忆,阅读、更改手稿和吃饭、工作、做爱的故事;另一方面是在“我”的虚构删改下形成的充满嘉年华色彩的故事。“我”不断穿梭往返于“万寿寺”与想象中的凤凰寨和长安城,“我把故事和真实发生的事夹在一起来写”[3]208,如此,“一个真实的自我渐渐面目清晰地凸显在‘我’的想象之域”[5]。
在莫迪亚诺那里,相较于现在和未来,过去更为根本、更加重要,恰如居伊所言“生活里重在过去,而非未来”[4]121。《暗店街》便是以寻找“过去”为中心的小说,而“现在”反而退居边缘,这是以重要性而言。但若以着笔多寡来衡量,“现在”在《暗店街》中又处于显性状态,“过去”则隐藏在“现在”的讲述、寻找和主人公支离破碎的假想性记忆当中。现在与过去的交织缠绕无疑是《暗店街》比较明显的一个结构方式,其中现在的故事以主人公的寻找记忆为核心内容,而过去则模模糊糊地上演着上世纪40年代一群寄居巴黎的外籍人的坎坷经历。
在《暗店街》里,现在是犹如暗夜笼罩一般一片朦胧,“周围一片寂寥死寂”[4]46,记忆出现了许多空洞,普遍的精神失落与身份失序使人们无所适从,焦虑不安。由于丧失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周围的一切与他毫无瓜葛,自己被抛离于生活之外,因此对居伊而言,现在是一种无根、茫然、痛苦乃至荒诞的存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我飘飘无所适,不过幽幽一身影”[4]5。与之相反,过去则是他所经历过的一段难忘的、充满瑰丽色彩的美好岁月。“我”在寻找记忆的过程中,时时回忆往昔,想象中的过去生活和当下世界交替呈现,致使主人公的身份在私家侦探居伊·罗朗和外籍人彼得罗·麦克沃伊两者之间游移往复,居伊一次又一次试图证实自己的确就是彼得罗,而彼得罗又一次次“远离”居伊,直至最后对疑问的查询以弗雷迪的葬身大海而更加杳无踪影。简言之,《暗店街》的情节可以视为现在的“我”向过去的“我”靠近、弥合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最终宣告失败,由于探询到的记忆无法得到印证,主人公便只能在真实与幻觉之间游走徘徊,对自我真实性的怀疑使他堕入现实的迷宫不能自拔。
王小波的《万寿寺》同样存在由现在和过去(准确的说是想象世界)组成的双重结构,不过与《暗店街》相比,《万寿寺》的双重结构更为复杂。在整体上《万寿寺》可分为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两大板块,而在局部又可以进一步细分出若干次级层次:现实世界往复穿梭于当下(失忆后)与过去(失忆前)之间,想象世界分别在虚构的凤凰寨和长安城依次展开,加上作者叙述行为的介入和多头平行叙事,整部小说令人目不暇接。《万寿寺》的现实世界中,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充满着种种钳制和体制化色彩,就连厕所堵住了,粪水四处漫延,也无人清理,“我”要去把壅塞的大粪捅开还被拒斥,一切都是那样的令人感到不快、压抑。因而“我”便逃往书稿里,在想象世界的长安城中虚构一片绚烂的诗意世界。在作者的叙述中,那里纯净、优美,充满智慧和乐趣,而想象中的主人公薛嵩也从一个内心阴暗、满脑子建功立业恶俗念头的“学院派”,变成了不甘为现实秩序所束缚的、自由酣畅的“自由派”,“我的故事重新开始的时候,薛嵩已经不是个纨绔子弟了,成了一位能工巧匠”[3]100。从万寿寺到凤凰寨,再到长安城,“我”不断改写手稿,不断排斥“屎一样的”现实,不断提炼出理想中的童话世界,从个人的想象和虚构之中提炼出诗意和美。
与《暗店街》相似,《万寿寺》中同样存在两个“我”:现实中的“我”与想象中的“我”。想象的“我”在《暗店街》中变幻不定,在《万寿寺》中则定格为“薛嵩”。“我”与薛嵩是一种互补、同化关系,就像“我”表白的那样:“在长安城里我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薛嵩。薛嵩也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我”[3]228。但是与《暗店街》里“我”费心尽力地向想象中的“我”靠拢不同,《万寿寺》中的弥合方向变成了想象中的“我”(薛嵩)向现实中的“我”(王二)靠拢、叠合。在《万寿寺》的现实世界里,“我”不光丧失了记忆,还处处遭受拘囿、束缚,毫无乐趣可言,于是“我”便在想象中虚构出一个越来越有趣、不流于俗的薛嵩,某种意义上,薛嵩就是真实的“我”、理想的“我”,是“我”的价值观念的化身。也就是说,薛嵩在慢慢变作“我”所喜爱的模样,在渐渐向“我”、向“我””的理想靠拢。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作者对呆板无趣的现实的拒绝,以及对自己所持人生价值的坚定信守。
3 形同而异质的主题:真实自我的不同定义与寻求
对于自我身份的疑虑,一直困扰着《暗店街》和《万寿寺》主人公,对于过往的寻找是两部作品的共同主题。但是两位主人公所追寻的自我显然完全不同:一个寻求的是自身的往昔,从而确认自我、寻回完整的个体;另一个追寻的则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诗意世界。两部作品对真实自我的不同定义导致了形同而异质的主题表现。
在《暗店街》里,居伊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真实姓名、生平经历、职业工作、社会关系……一句话,他成为了一个没有本质、没有联系的,类似孤魂野鬼的存在。不仅居伊的身份出现了危机,其他人物也陷入一种无根无底、漂荡无依的境遇:彼得罗是没有合法护照、没有正当身份的“黑人”;费雷迪、盖伊、维尔德梅尔是持假护照者,只能躲在边境上,伺机逃往中立国。在此情况下,寻找自我、寻找往昔便成为他们寻求解脱、寻求慰藉,重新确立人生支撑点与栖息处的唯一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居伊寻求的便不单单是自己的记忆和过去,而是自身存在的根据和意义。米兰·昆德拉曾说:“忘,这是人的一个重大的个人问题,自我丧失似的死亡。但这个自我是什么呢?它是我们所记得的一切的总和。因此,我们对死亡感到恐怖的不是丧失未来,而是丧失过去。遗忘是与生俱来的死亡形式。”[6]遗忘意味着死亡,而记忆则是一种还魂丹与安抚剂。“我们的此在其实一无所有,只能凭借过去的经验、阅历、回忆这些既往的东西确定,此在的我拥有的现在时间只能是永远在流逝的瞬间,因此,只有过去的失去的时间才成为我们唯一感到切实的东西。”[7]66因而,居伊的寻找行为才超越了形而下的冲动,抵达了形而上的存在论意义,类似于一种精神救赎。“这一行为既是向过去的沉溺,找回过去的自己,更是对现在的自我确证和救赎,是建构‘此在’的方式。”[7]64
但是,要在浩瀚无边的人海中,在久远的历史中寻找过往的蛛丝马迹,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何况在这过程中“人都经受着自我泯灭与自我消失”[2]302,个体在大千世界中如此微不足道,如此易于消散和被遗忘,正像居伊和于特谈到的那种“海滩人”:这类人转瞬即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沙子上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4]49-50。居伊、于特以及现代的芸芸众生,其实都是“海滩人”。这是莫迪亚诺在小说中反复阐发的寓意:“也许,我根本就不是那个彼得罗·麦克沃伊,也许我什么也不是,仅仅时弱时强的声波透过我的躯体,漂浮空间,渐渐聚散,这便是我。”[4]87“有谁知道呢?也许我们最终会烟消云散,或者,我们完全变成一层汽水,牢牢附在车窗玻璃上,用手怎么擦也擦不掉。”[4]148直到小说结束,居伊凝视着照片上一个正在哭泣的女孩的面影,还在不无哀婉地感叹道:“薄暮时分,小姑娘随母亲从海滩回来,她无缘无故就哭了,因为她还想再玩一会儿。她走远了,到路口已经拐了弯;我们的一生,不是跟孩子的这种伤心一样,悠忽间在暝色中消失吗?”[4]171这正是现代人的常态:生存茫然无根后的慌张,以及寻求精神救赎的艰巨与虚妄。在这个意义上,“莫狄阿诺创造了一部现代人寻找自我的悲怆史诗”[2]302。
《万寿寺》中的“我”虽然不像居伊那样苦苦寻求失忆前自己的真实情况,但他同样在追寻着真实的自我,只不过,王小波与莫迪亚诺对真实自我有不同的定义,从而导致王小波和莫迪阿诺对记忆的见解很不一样。对居伊或者说对莫迪亚诺而言,真实自我指的是个体处于一种完满、连贯、有序、有根的精神安定状态,莫迪亚诺把记忆当作正面的东西,让主人公苦苦追寻它;而对王二或者王小波来说,真实自我则意味着不庸俗、不乏味、不被拘束,是自由自在、诗意满满的图景,因而王小波把记忆当成可厌的东西,像服苦药一样接受着,“我的记忆尚未完全恢复,但我已经觉得够多的,恨不得忘掉一些”[3]230。正是由于现实世界太过远离真实自我的设想,真实与想象存在着巨大反差,所以《万寿寺》中的“我”刻意逃避往日的记忆,但他并没有放缓对真实自我追寻的步伐,他之所以在想象世界里对手稿进行不厌其烦的改写,就是为了在那里创建一个属己的、永远不会被异化的“诗意的世界”。
其实,在两部小说的名字中就蕴含着各自的深意。“暗店街”是居伊的旧居,是隐藏着他真实过往的所在,小说结尾,居伊还声称“再者,我还要奔走,最后尝试一次,去我在罗马的旧居,暗店街2号”[4]171。“暗店街”是居伊的希望,象征着他的真实自我。而“万寿寺”在“我”眼里则是一个了无生气、压抑沉沉的体制化单位,它是“我”的精神梦靥。于是,无论如何“我”得逃离,既然摆脱不了记忆,因为“没有记忆的生活虽然美好,但我需要记忆”[3]233,但“我”可以建构自己的梦幻世界。回到“暗店街”,意味着走投无路的最后曙光;回到“万寿寺”,则意味着亘古不变、别无选择的人生宿命。同样是追寻真实的自我,居伊选择的是在此岸世界中捕捉着稍纵即逝的蛛丝马迹,但一切都是那么混乱而又零散,因而《暗店街》的追寻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而王二却选择了在彼岸世界中恣肆、浪漫地图绘真实的自我,尽管他显得那么孤独,尽管“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3]259,但他不仅“拥有此生此世”,更重要的是他还“拥有诗意的世界”[3]259,正是因为这个精神家园的存在,王二便得以抵抗鄙俗的扰攘尘世。因而,与《暗店街》相比,《万寿寺》的寻找更为浪漫和乐观。
4 结束语
学者戴锦华认为《暗店街》之于《万寿寺》不过如《红线》一样,只是一个“噱头”[8]。但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王小波在《万寿寺》中多次提及《暗店街》,其用意不仅是拿来装点门面或者游戏之笔,而是在《暗店街》的启发下,王小波才在《万寿寺》中思索记忆与遗忘、灰暗现实与诗意世界、残缺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关系。但王小波在接触、借鉴莫迪亚诺《暗店街》的基础上,又不断以民族的文化意识和个人主体的想象力作出阐发和理解,然后予以创造性地发挥。于是,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探索和书写就打上了鲜明的王小波烙印——这便表现为上文分析到的《万寿寺》一反《暗店街》那样在现实世界中苦苦挣扎的沉痛感,而是在想象天地里尽兴地建构充盈着浪漫和希望的诗意世界。这种不被现实所拘囿,能够摆脱钳制,依靠思想、依靠写作营造属于自己的永恒精神家园的行为,正是李银河盛赞王小波为“浪漫骑士”的原因。
总而言之,王小波创作《万寿寺》一方面受到《暗店街》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自己的写作促成了《暗店街》提及的相关问题的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是为对方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另一方面,本文化也可能因此得到生长和更新”[9]14。《暗店街》成为阅读、解析《万寿寺》的参照,在这两者的“互识、互证、互补”[9]14过程中,我们对作品的人物、结构与主题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
[1] 艾晓明,李银河.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2] 柳鸣九.凯旋门前的桐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 王小波.青铜时代[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4] 莫狄阿诺.暗店街[M].李玉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5] 程鸿彬.通往沉思和想象的陷阱:论王小波小说《万寿寺》中的“戏仿”[J].理论与创作,2006(4):77-82.
[6] 李凤亮,李艳.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525.
[7]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8] 戴锦华.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J].当代作家评论,1998(2):21-34.
[9] 乐黛云.跨文化之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刘 蓓〕
Transplantandcreation—ComparativeanalysisofWanshouTempleandMissingPerson
GAO Q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There are different treatments of the detective mode in Wang Xiaobao’s Wanshou Temple and Patrick Modiano’s Missing Person in spite of similar structure and theme. Modiano’s influence on Wang Xiaobao is comprehensive, especially Modiano’s masterpiece Missing Person, which is referred to many times in Wanshou Temple by Wang Xiaobo, and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whole structure and deep implication of Wanshou Temple.
Wang Xiaobo; Patrick Modiano;Wanshou Temple; Missing Person
2017-01-20
高 强(1994— ),男,重庆彭水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25
: A
:1008-8148(2017)03-0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