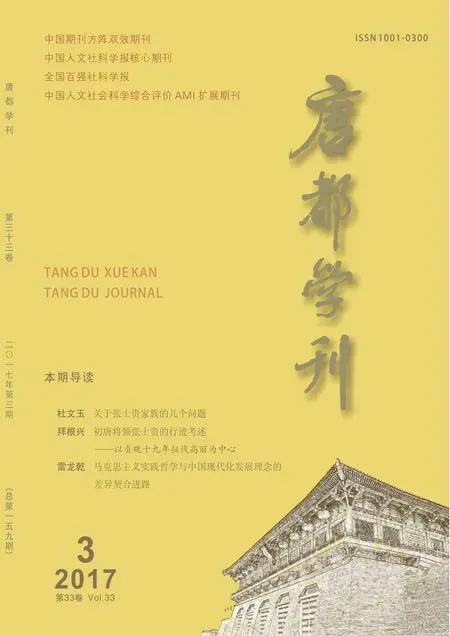孟子“可欲之谓善”命题析论
朱小娟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伦理学研究】
孟子“可欲之谓善”命题析论
朱小娟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可欲之谓善”是孟子性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理解孟子人性善思想的关键。对这一命题的全面把握要从“可欲”一词的内涵着手。结合孟子性命思想来看,“可欲之谓善”中的“可”应取之意是“能够”,“可欲”即是“能够探求到”,“可欲”的内容则是“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端”及其所表征的“仁义礼智”诸德。由于这些是人唯一能够经由自身力量而无需求于外就可做到的事情,且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自然而然地指向于“善”,所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孟子的“可欲之谓善”命题有其合理性,与他的人性善思想刚好契合;但就一般意义而言,它也有不妥当之处。
可欲;善;性命;四端;诸德
“可欲之谓善”是理解孟子“善”观念及其性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出自《孟子·尽心下》。孟子在回答浩生不害关于“何谓善?何谓信?”的发问时说道:“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由此观之,这段话是具有内在因果关联性的一串判断语句,首句“可欲之谓善”是理解自“有诸己之谓信”以下五个判断的关键。所以,弄清楚“可欲之谓善”这一命题的思想内涵,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孟子上述那段话,而且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把握孟子的“善”观念及其性命思想。
一、孟子语义中的“可欲”之涵义
学界关于“可欲之谓善”这一命题的解读,可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毋庸置疑,“可欲”是理解这一命题的关键词和突破口。孟子以“可欲”来规定“善”,那么究竟如何厘清“可欲”一词的内涵呢?
“可欲”由“可”和“欲”组成,正确理解“可欲”一词的含义,需要从字形和字义上分别对二者进行解读。相对来说,“欲”比较好理解,有贪、求、想要等意思,是人们内在的情感体验与心理活动。“可”的引申义则较多。“可”源于甲骨文,从字形上看,它的左下部是“口”,本指发声器官,这里表示“许可”;右上部是“丂”,表声。《说文》中解释道:“可,肎也。从口、丂。”但“可欲之谓善”中的“可”显然不取“许可”之意,而是作为助动词使用,常见的解释有“可以”“能够”“应当”“值得”。其中,“值得”和“应当”是目前学者选用比较多的两种解读。比如,有人在译注《孟子》时将“可欲之谓善”翻译成“那人值得喜欢便叫做‘好’”[1]264。还有人认为,“孟子的‘可欲’,指的是价值之应当”[2]24。当然,也有人从“能够”的含义上去解读“可”,指出“‘可欲’即能够满足人们的欲望、需要,能引起人们喜欢、快乐、满意等积极情感体验的价值”[3]54。对比这三种观点,最后一种把“可”理解为“能够”,强调内在力量的发挥,是比较恰当的。但这种解读所强调的“能够”力量的主体是“价值”,而非人本身,这与孟子的意旨又是背道而驰的。那么,能否将“可欲”之“可”作“值得”解呢?这需要从孟子关于性命思想的论述中寻找答案。
《孟子·尽心下》有云:“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在孟子看来,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的天性,但人的这些欲望能否得到满足,则有命的作用;仁、义、礼、智、圣诸道德规定,都由命决定,但人能否得到它们,其中也有天性的作用。所以,孟子认为,性命是一体的,人所得自于天者,皆可称之为“性”,亦可称之为“命”。然而,孟子在性与命之间又做出了一种内在区分。“这个区分的根据在于:人在对二者的取之之道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4]45
孟子在《尽心上》中说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将“性”视为能够通过主观努力取得的一种东西,它所指向的是内部力量,它的实现要靠“我”来完成。“命”的实现则不同,它受外界各种复杂因素的限制、约束,对它的决定权在“外”而不在“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孟子才对人的口、目、耳、鼻、四肢及其欲望言“命”而“不谓性”,是因为这些并非人心所直接“可欲”者;同样,孟子单称“仁、义、礼、智、圣”诸德为“性”而非“命”,则是因为这些是人心能够直接欲求到的。由此可推断出,孟子所说的“可欲”应当是不被“命”所限定的东西。而倘若将“可欲之谓善”中的“可”理解为“值得”就会曲解孟子的原意。因为“值得”通常是对比两种或多种可能结果,而倾向于做出何种选择,多用于表示经济价值、审美价值等价值选择上的意向。以这种“可欲”来概括和规定“善”明显不符合孟子之意。这样只会因评价主客体的纷繁复杂而造成“善”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所以,“可欲”之“可”不能作“值得”解,同样也不能作“应当”解。因为,“应当”是伦理学范畴,是道德价值中的“值得”。
结合孟子性命思想来看,“可欲之谓善”中的“可”应取之意是“可以”“能够”。但比较而言,“可以”更多强调没有外在因素的限制,“可不可以”终究要受“命”的影响;而“能否”则主要靠“我”的内在力量之强弱。古人考虑问题不是从外在束缚考虑,而是从人本身出发,所以“可欲之谓善”只能向内,不能向外。因此,孟子语义下的“可欲”之“可”更准确的解释是“能够”,“可欲”即是“能够探求到”,而“可欲之谓善”则是在说,人能够依靠自身主观力量探求到的才是“善”。
二、对孟子“可欲之谓善”内容的整体把握
明确孟子语义下“可欲”一词的含义是全面理解“可欲之谓善”命题的基本前提。孟子以“可欲”来界定“善”,并认为此“可欲”者,所指即“性”,是向内的。那么,向内的东西中又有哪些是“可欲”的呢?
宋儒张栻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在《癸巳孟子说》卷7中说道:“可欲者,动之端也。盖人具天地之性,仁义礼智之所存,其发见,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所谓可欲也。”按照张栻的解释,孟子“可欲之谓善”的内容就是“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端”及其所表征的“仁义礼智”四德,这与孟子的意旨十分切合。
孟子在《告子上》篇中回应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观点时,说过:“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由此可以看出,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这“性”乃显诸“四端”之情,即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而“四端”表征的则是“仁义礼智”诸道德规定。所以,这“四德”不是外界赠给“我”的,而是“我”本来就具有的,是人保持“常性”的结果。而现实中有些人不能坚守“仁义礼智”诸德,或者他们与其他人相比,坚守的程度不够,只是因为他们的天性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的缘故。孟子通过这样的论述想要表明,“四端”虽是上天赋予,但亦是人本身所具有的,而且人处于自觉自知的状态,能够意识到这种“赋予”,能够通过自身力量的发挥保存、巩固这种“赋予”,并由于保持了这种天性而产生“仁义礼智”诸德。当然,这些道德规定也要人去主动探求、追寻,否则便会丢失。所以,孟子说“求则得之”与前面引述的“求有益于得”“求在我者”所指皆为人心之“可求”“可欲”者。这与张栻的解读趋于一致。即以“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端”及“仁义礼智”诸德来规定“可欲之谓善”的内容。这样一来,开篇引用的“有诸己之谓信”和之后四个判断的主辞就都是这“可欲”的“四端”及“四德”。
孟子之所以把“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端”及“仁义礼智”诸德规定为“可欲”的内容,不仅因为这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显著特征,还在于它们是人唯一能够经由自身力量而无需求于外就可做到的事情,其内在依据归根结底在孟子的性命思想那里。从前可知,孟子既主张性、命分立,又坚持性、命合一。“性、命分立”主要体现在各自的实现途径之根本差异上。这里要重新去品味我们之前引用过的孟子的一段话:“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段话中的“性也”是说,口、目、耳、鼻、四肢之欲皆为人与生俱来的,但是,味、色、声、臭、安佚对人来说是有待于外的,这些欲望满足与否并非人自己所能决定,所以孟子才说“有命焉”。而“仁、义、礼、智、圣”这五者与前五者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它们虽然也要在父子、君臣等关系中求得实现,但终究要体现在人的道德实践中,要发自本心,这恰好展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自我价值,因而孟子说“君子不谓命也”。正是基于此,孟子得出结论,人之为人就在于保存和无限扩充此“四德”之性。那么,这“四德”的内在根据又在哪儿呢?孟子认为在于人的道德心性,即前面屡次提及的“四端”,尤其是不忍人之心。《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当齐宣王问及孟子“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孟子将“保民”之德直接归于“不忍人之心”,亦即恻隐之心。可见,“四端”的核心是“情”,是“不忍恻隐”之情。这也正好印证了朱子论“四端”之关系时所作的比喻。他说:“恻隐是个脑子,羞恶、辞逊、是非须从这里发来……恻隐之心,通贯此三者。”[5]1289因此,“四端”心性乃是“仁义礼智”诸德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
在孟子看来,性、命又是合一的。《孟子·尽心上》首章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由此可以明晰,孟子说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修身以“事天”,重在强调天人合一。“这个合一,不是一种静态的理论设定,它表现为一个人的存在超越性价值实现的动态历程。”[4]46亦指人通过主体自觉感知和道德践履,觉悟到自己的本性,以确证“天之所以为天”,进而求得对天命的领悟。然而,知天的目的并不在于知晓有“天”这一外在对象性的存在,而是要“立命”。这就要靠人无限扩充自己内在的道德心性。所以,不论是从性、命分立的角度,还是从性、命合一的视角来看,“四端”“四德”都应当是孟子“可欲之谓善”的具体内容。
三、“可欲之谓善”命题的合理性及不妥之处
综观目前学界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孟子“可欲之谓善”命题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有之,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亦有之。正确评判一个命题的合理性,决不能囿于“一刀切”的狭隘眼光,而要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全面理性的分析。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孟子“可欲之谓善”命题的合理性主要在于:
第一,它以孟子的性命思想为依据,探寻到了人的道德自律的根源性,这是对前人的超越。事实上,以“仁义”诸道德规定为人心之“可欲”“可求”并不是孟子的发明,而是孔子首先发现的。孔子曾经说过:“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乎?我未见力不足者。”[6]47“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6]90“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6]141这几则材料显示,在孔子看来,“仁”是人天生的本性,实行仁德也全在于自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自己努力争取,就可以达到。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孔子提出自省的修养方法,强调人进行道德修养的自觉能动性,既揭示出道德修养必须依靠主体自觉,不能依赖外力,又表明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教育和修养,才能摆脱禽兽的劣性,成为道德高尚的“仁者”。孔子的这些发现,颠覆了以前世代对人主体性的淹没、对“天”等神秘力量的盲目推崇,促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仁义”乃是人唯一能够直接欲求到的,“为仁”则是人唯一有能力可以不必借助外力做到的事情。孟子在此基础上,更前进了一步。他将孔子发明的“仁义”诸德理解为人性的内在规定,并以“可欲”与否对性、命做了区分,为人的道德行为选择找到了内在根据。
第二,孟子揭露的“可欲”之内容,其发端恰好是类似于人的本能性的自然表现,由此回应了他的“人性善”论断。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诸德是人心之“可欲”的内容,是人的天性,而这“性”又显诸“四端”之情。何为“四端”之情?在孟子那里,它们是人生而就有的,是人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孟子·公孙丑上》说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可见,在孟子看来,以“恻隐之心”为首的“四端”之情不是人出于交际、荣誉、喜好等功利目的考虑的结果,而是临事不假思索的本能显现,就像人先天就具有“四体”一样自然。如此一来,就将人“可欲”的“四端”及其表现出来的“四德”自然本然地指向于“善”,这刚好证明了孟子人性善思想的正确。由于“人性善”,所以人通过自身力量欲求的东西也是“善”的,由此推导出“可欲之谓善”命题的正确,最终实现了“自圆其说”。
但是,“可欲之谓善”这一命题也有欠妥之处。一方面,孟子以自己的人性善思想为前提,层层推理,结果推导出“可欲之谓善”,但这一前提本身就是有待商榷的。众所周知,关于人性善恶之争论,历来从未停歇过,至今没有取得共识。所以,至多能说“人性善”是有关人性善恶论战中的一种代表性观点,而不能当作绝对真理加以对待。实际上,善、恶只有在涉及主体之间的关系时才会产生,因而讲善恶要与主体相联系,与人的自由意志相联系。另一方面,“可欲”的不一定是善的。人可以凭借自身力量,辅以外在助力,谋取自己想要的各种功名利禄,满足众多情欲,甚至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种“可欲”显然不是孟子所说的作为“善”的“可欲”。退一步说,假设“可欲之谓善”在一般意义上也是成立的,那么,这意味着“善是正价值”。随之而来的就有几个问题:其一,谁来评判这“价值”;其二,拿什么标准来评判;其三,在什么条件下进行评价;其四,对谁有正价值。当评判主体、评判标准、评判条件不同或发生变化的时候,评价的结果也会不一样,价值是正或负也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心之“可欲”“可求”的也不一定是“善”的。所以,对孟子的“可欲之谓善”这一命题,要结合他的性命思想来理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看到它的合理性,又正视它的不妥之处。
[1] 杨伯峻.孟子译注(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 崔宜明.“可欲之谓善”论析[J].学术月刊,2001(1):23-27.
[3] 张奇伟.道德价值是“可欲”的——孟子“可欲之谓善”命题发微[J].人文杂志,1992(6):53-55.
[4] 李景林.论“可欲之谓善”[J].人文杂志,2006(1):43-47.
[5]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钱逊.《论语》读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
[责任编辑 王银娥]
Analysis of Mencius’ Proposition “Goodness is the Satisfaction of Desires”
ZHU Xiao-juan
(SchoolofMarxism,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Goodness is the satisfaction of desires”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Mencius, which is also the key to understand Mencius’ good thought of human nature.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desire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master this proposition. From the point of Mencius’ life thought, being desirable should be explained as possibility, what can be desired is equal to what is able to be explored. Its contents contain the four terminals: compassion, shame, modesty, right and wrong and all kinds of the four cardinal virtues: humanity, justice, propriety and wisdom. These people were born with the ability to do it by nature with their own efforts rather than others’ help, naturally reaching the realm of goodness. Therefore, from the positive point of view, Mencius’ proposition makes some sense, which conforms to his thought of kind human nature. But in a more general sense, it has its own defects.
desires; goodness; life; four-terminal theory; all kinds of morality
B222.5
A
1001-0300(2017)03-0054-04
2016-08-10
朱小娟,女,安徽灵璧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集体主义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