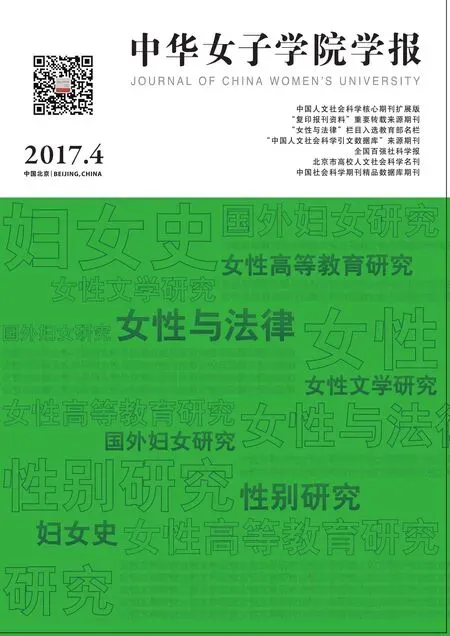民族文化语境与中日“郑成功文学”郑母形象的变迁
寇淑婷
民族文化语境与中日“郑成功文学”郑母形象的变迁
寇淑婷
郑成功作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母也备受中日学界关注。以中日“郑成功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在民族文化语境影响下,中日两国对郑母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实像与虚像交织的特点,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变迁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差异。其中,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为日本“郑成功文学”所特有,而自立的女性形象和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则是中日“郑成功文学”共有的形象特征。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形成体现了明显的时代、政治及文化印记。
郑成功;“郑成功文学”;郑成功之母;女性形象;民族文化语境
郑成功作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郑成功之母(以下简称“郑母”)也受到中日学界的关注与研究。①日本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山久四郎:「国姓爺鄭成功の母」,载于『歴史教育』1958年第10号;黒石陽子:『「国性爺合戦」考――3段目の老母像を中心に』,载于『言語と文芸』1988年第102号;平田澄子:『近松浄瑠璃の「女性」――底意をあらはす女たち』载于『日本文学』1997年第10号;小森洋一、内藤千珠子:『「国性爺合戦」と伝説の記憶』,载于『シリーズ言語態6間文化の言語態』,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第79—94页。然而,日本学者围绕郑母的研究多局限于近松门左卫门《国性爷合战》②本文中出现的“国性爷”并非笔误,因为日本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在《国性爷合战》中将国姓爷郑成功写成了“国性爷”,以突出其主观创作意图,所以后世出现了国姓爷“性”与“姓”的不同称呼方式。中“和藤内”(郑成功)的母亲上,对一以贯之的日本“郑成功文学”③笔者在日本“国姓爷文学”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将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定义为“郑成功文学”。参见寇淑婷、岛村辉:《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载于《东疆学刊》2017年第3期。中的郑母形象缺乏整体认识。中国关于郑母的研究成果,也大多是从历史角度展开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以中日“郑成功文学”的代表作作为考察对象,对郑母形象进行整体研究,试图呈现出在民族文化语境下郑母形象变迁的特征,以及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差异与民族文化语境的关联。
一、民族文化语境下郑母身份认同的实像与虚像
郑母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厘清民族文化语境下郑母的身份认同是认识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前提。对于郑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有“田川氏”和“翁氏”两种说法。在中国,关于郑母是田川氏的说法,匪石在《郑成功传》中写过曾到郑成功出生地平户探访,“居者告余:‘昔吾国有义侠女曰田川氏,实为平户士人之女,年十七八婚于明人郑七官芝龙为妻。’”[1]72关于郑母为田川氏的说法,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也持认同态度,“(芝龙)居无何,落魄之日本,娶平户士人女田川氏,生成功。”[2]546而关于郑母是“翁氏”的说法,《台湾外志》记载:“郑芝龙,字飞黄,福建泉州府南安県石井人。在日本国娶翁氏,生森。”[3]1对此,陈三井的《郑成功全传》叙述较为详细,“成功母之出身,世人不甚清楚。据一些资料记载,或说她是日本长崎王族女;或说是日本肥前平戸士人田川氏之女;或说是倭妇翁氏……笔者以为,成功母既生于日本,又在日本长大,因此,不管她姓翁或姓田川,她总算是日本人。因此称她为‘日人翁氏’大概是最恰当不过的了。”[4]37
在日本,则主要认为郑母为“田川氏”,即使有“翁氏”之说,也因受到了江日升《台湾外志》的影响。朝川善庵的《郑将军成功传记碑》中关于郑母有如下描写:“(郑芝龙)乃娶田川氏,宽永元年七月二十三日,生成功,后又生七左卫門。”[5]473-474幸田露伴在《郑成功》中的观点与朝川善庵一致,“郑成功是南安县石井巡司人。父亲芝龙,字飞黄,母田川氏,日本平户人”。[6]1137而河村哲夫在《龍王の海:国姓爺·鄭成功》中针对郑母是翁氏的说法指出:“《台湾外志》等中国文献,多数认为郑母为‘翁氏’。相传翁氏(指郑成功外祖父)为福建省泉州人,因经商到达日本,后与日本女性结婚,将与‘翁’发音相近的‘用’拆分成两个字‘田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翁’是‘王族’,是一位叫做‘翁翌皇’的皇族出身的人。”[7]48
另外,关于郑母的出身,也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出生于“日本王族”,也有的认为是“日本娼妇”。染崎延房在《台湾外記:一名国性爷》中写道:“(郑成功)其父为中国大豪杰,其母为我朝一娼妇。”[8]3稻垣孙兵卫在《郑成功》中指出:“根据某些记载,田川氏为日本平户的娼妇,说田川氏在生了郑成功后又改嫁生了七左卫门,后又陪伴芝龙到中国。还有的说田川氏既不是娼妇也不是艺伎,而是出生于平户的名门望族。”[9]4-5关于田川氏为“娼妇”的说法,江日升的《台湾外志》描写较为详细,“昔之日本,最敬唐人。……所以抵日本者,老诚亦被迷堕,况一官(郑芝龙——笔者注)正在方刚之年乎?亦是天数该然,赤绳紧足,本街有倭妇翁氏,年十七,娇艳绝俗,美丽非常。见一官魁梧奇伟,彼此神交,第不得即为双栖并一耳。一官遂聘之,合巹后,隔冬往下。”[3]3-4
同时,对于郑母之死,也有不同观点。在中国,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写道:“俄而贝勒博洛及韩固山猝至,乃走。田川氏不去,伏剑死。成功大号,悲不自胜。”[2]549陈三井在《郑成功全传》中描写道:“翌年十一月芝龙向清军投降。被挟往北京,清军突至安平,成功母受淫辱,于十一月三十日毅然自杀殉国。”[4]39在日本,朝川善庵关于郑母之死这样写道:“俄而清兵至,芝豹兵溃,芝豹奔回安平,成功母田川氏在泉州城,独不退曰:‘事既至此,何爱一死。’登城楼自刭,投水死。”[5]475可见,中日两国对郑母之死的细节描写不尽相同,但大多是因清兵而死。然而,陈舜臣在《风云儿郑成功》中所描写的郑母,却是为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不影响郑成功的前途,自杀而死。显而易见,陈舜臣对郑母自杀而死的文学叙事,与历史事实产生了极大的偏离。
1987年,福住信邦的小说《国姓爷郑成功之母》问世,这是一部以郑母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作者福住信邦,原名郑邦夫,是郑成功在日本的同母弟弟田川七左卫门的第十一代子孙。福住信邦在撰写该书时,与其他日文小说用文章体的表达方式不同,该书通篇使用了日语的敬体表达形式,足见作者本人对郑氏祖先的由衷敬意。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是一部权威性著作。《国姓爷郑成功之母》出版后,福住信邦又创作了《新国姓爷合战物语》,这两部著作被认为是亲子书。福住信邦在该书后记中表明了出版《国姓爷郑成功之母》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大陆存在诸多对郑母的误解、误传,因而希望通过该书澄清一些历史事实。
关于郑母的出身,福住信邦在《国姓爷郑成功之母》中指出,郑母为田川氏,名松。田川松的母亲在她出生的时候,因患产褥而死。关于田川松的父亲,福住信邦指出,田川松的父亲“田川七左卫门”,号“松庵”,是一位汉方医,后来辗转经营自己的诊疗所,而田川松则成为父亲的助手。该书详细描写了田川松被指名到平户藩主府邸做侍女,之后被藩主姐姐松东院收为养女嫁给了郑芝龙的经过。这也可以解释前述田川氏为“日本长崎王族女”的说法了。
另外,关于郑母为翁氏的说法,日本学者中山久四郎指出,在平户的风俗中,喜欢尊称年长的老父为“翁”,因为郑芝龙经常称田川松的父亲田川七左卫门为“翁公”,于是这种说法传到了中国,因此中国称田川松的父亲为“翁公”,田川松也被称为“翁氏”,误以为是中国人的后裔。[10]
可以说,中日两国围绕郑母身份认同的诸多质疑,呈现出了实像与虚像交织的特点。虽然在民族文化语境下,中日两国某些观点不一致,但是却可以相互印证,使某些历史问题越辩越明。郑母扑朔迷离的身份,也为中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从而使中日“郑成功文学”中的郑母形象呈现出各种样貌。
二、民族文化语境下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变迁
以中日“郑成功文学”的代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日本“郑成功文学”中的郑母形象呈现出三个不同特征,其中,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具有独特性,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特有的郑母形象,而自立的女性形象和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在中国“郑成功文学”中也有所体现。
(一)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以《国性爷合战》及其翻案剧为中心
日本“郑成功文学”中关于郑母的描写,最早出现在《明清斗记》卷三第八节“郑芝龙陷于北军,芝龙之妻自杀”中,然而最具特点的女性形象,还是近松《国性爷合战》中所塑造的郑母形象。1715年近松的《国性爷合战》在大阪竹本座上演,大获成功。后世作家以《国性爷合战》为原典,创作了一系列翻案剧。主要有1929年小山内薰的《国性爷合战》、1949年久保荣的《史剧国姓爷新说》、1958年矢代静一的《国姓爷》。《国性爷合战》所塑造的作为日本代言人的郑母形象,在翻案剧中得到了艺术生命的延续。
在《国性爷合战》中,郑母以“和藤内母亲”的身份出现,之所以称其为日本代言人,是因为以《国性爷合战》为代表的这些戏剧所塑造的郑母形象,体现了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国性爷合战》第三幕,在狮子城下,和藤内母亲主动要求将自己用绳子捆绑,入城面见甘辉,请求甘辉助和藤内完成复兴明朝的大业。当看到郑芝龙的女儿、也是甘辉妻子锦祥女欲自杀时,和藤内母亲说道:“你今天死在这里,那一定会被认为是我这位继母从日本远渡三千里来到中国,因憎恨你而杀死了你。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耻辱,若是别人知道我是日本人,那一定会成为日本国的耻辱。照耀中国的阳光也在照耀着日本,日本也有仁义五常,出生于日本这个慈爱之神国的母亲,怎会眼睁睁看着女儿去死?这个绳子是来自日本众神的注连绳,就用它来绞死我吧,让它将我的灵魂带回日本。”[11]222-223锦祥女的自杀打动了甘辉,和藤内母亲果真也以自杀结束了生命,“母亲大笑道:‘太好了!终于实现了愿望!锦祥女,你看到了吧,你舍弃生命完成了父子的愿望,父子的愿望就是这天下的愿望,这把九寸五分的剑,是你为了整个中国而自杀的剑。母亲不会妄言,不会给日本带来耻辱。’于是拿起剑刺向自己的咽喉……‘甘辉、国姓爷,不要悲伤,你们的敌人是鞑靼王。’”[11]227-228和藤内母亲为了光复明朝而“英勇就义”,和藤内带着国恨家仇,驱逐了鞑靼王,占领了南京城,完成了母亲及天下人的夙愿。这位和藤内母亲,处处以“日本的耻辱”自省,诉说着、践行着日本的仁义五常,俨然一副日本代言人的姿态。这种描写在《国性爷合战》翻案剧中表现得也尤其突出。对比中国的戏剧作品,笔者发现,中国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戏剧,如阿英的《海国英雄》(1941年)、郭沫若的《郑成功》(1979年)等,均未出现对郑母的描写。由此可见,中日两国文人们的关注点并不相同。
另外,小山内薰的翻案剧《国性爷合战》以及矢代静一的《国姓爷》所塑造的郑母形象,与近松所塑造的和藤内母亲无异,只是语言的现代感更强。在矢代静一的《国姓爷》中郑母被称为“阿圆”,人物的主体性增强。然而,久保荣的《史剧国姓爷新说》的风格却与近松的剧作迥异。
在久保荣的《史剧国姓爷新说》中,郑母被称为“田川菊女”,她时时拥有一颗“日本耻辱”之心,经常告诫森舍(郑成功),中国一直视日本为东夷,作为日本人一定不要做有损国威之事。为了稳固森舍地位,田川菊女深夜跑到唐王殿下寝殿,威胁殿下为森舍赐国姓。“殿下,请求您,无论如何为森舍赐名!……请赐名!赐明朝的朱姓!”[12]70日本女子田川菊女,威胁大明朝皇帝为自己的儿子赐国姓,这种文本与历史的错位书写,使作者的国家主义意识跃然纸上。
在郑母殉死情节的设计上,该剧也与近松的原作相去甚远。田川菊女“(一边逃跑)饶了我吧,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如发狂般,摘下首饰)这个,给你!这是昆仑白玉,(扔了过去)”[12]99,可以看出,田川菊女并非自愿殉死,该情节虽与原作迥异,但却体现了田川菊女对死亡的恐怖,以及作为女人的人性化表现。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近松《国性爷合战》及其翻案剧所塑造的郑母形象,时刻拥有一颗“日本耻辱”之心,为了光复明朝,为了天下,不惜牺牲生命。在这一系列剧作中,郑母被赋予和藤内母亲、“阿圆”、“田川菊女”的名字,使这些剧作的虚构色彩逐渐增强。这些被塑造的作为日本代言人的郑母形象,体现了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与此不同的是,郑母形象并非中国剧作家的关注焦点,在中国戏剧中笔者并未发现对郑母形象的描写,这也映衬出《国性爷合战》及其翻案剧所塑造的作为日本代言人的郑母形象的独特性。
(二)自立的女性形象——以《国姓爷郑成功之母》为中心
福住信邦在《国姓爷郑成功之母》中所塑造的郑母形象,与前述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不同,这里所塑造的郑母形象表现出了自立的女性形象特征。
首先,郑母田川松自幼独立,并逐渐掌握了自立女性的生存技能。作为父亲诊疗所的得力助手,田川松十四五岁就能够独自往返于诊疗所和平户之间采购药材。当时平户是日本幕府开放的一个对外贸易港口,来自中国、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地的海商集结于此进行贸易,是一座极其繁荣的城市。田川松父亲的诊疗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田川松逐渐可以使用这些患者国家的语言与他们进行简单的对话,这项语言技能为田川松创造了与外宾接触的机会。在荷兰商馆举办的答谢宴会上,田川松被邀请去帮忙。“田川松小姐懂得当天来宾的话,所以,看客人需要什么,将意思传达给其他来帮忙的女孩就可以。”田川松也是在这次宴会上,遇到了对她一见倾心的郑芝龙。可以看出,在《国姓爷郑成功之母》中,郑母田川松是父亲田川七左卫门医师的得力助手,并且懂外语,具有作为自立女性的独立生存的技能。笔者认为福住信邦的这种描写意在否定郑母为日本“一娼妇”的说法。
其次,田川松自立的女性形象还体现在她做侍女的经历上。这次经历使她完成了从一位庶民女子到大家闺秀的蜕变。田川松在藩主府邸期间,从举手投足至一般教养,都接受了严格训练,从而变成了一位更具教养、更具女人味的女人。田川松因聪慧、行事得体,受到藩主姐姐松东院的赏识,被松东院留在身边,在她嫁给郑芝龙时,是“以松东院养女的身份出嫁的”。[13]46在藩主府邸,田川松接受了松东院的教育,“凡三从四德、茶道、花道、歌道等可以陶冶心性的活动,皆会教给姑娘们,……为了防身,也习长刀、短剑等武术。”[13]35-37可以说,在藩主府邸的经历改变了田川松的人生。
再次,田川松自立的女性形象,还表现在对家庭的经营上。田川松在经过松东院的调教后,拥有了作为日本传统女性的妇道与教养,她很快融入中国家庭,开始了新生活,与丈夫相敬如宾。作为郑芝龙的妻子,田川松生了两个儿子,一位是众所周知的郑成功,另外一位是后来继承了外祖父名字的田川七左卫门。郑成功七岁回到明朝,后被隆武帝赐国姓,被称为国姓爷。田川七左卫门则一直留在日本,后来成为在日“一官党”①在日文文献中,一般称郑芝龙为“一官”,“一官党”是指以郑芝龙为首的郑氏在日本的海外贸易集团,在郑成功时期被改为“国姓爷党”。的首领,负责郑氏集团的日本贸易,并不断出资支持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这些都凝聚着郑母田川松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在郑芝龙回到明朝后,因当时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渡海到国外,因此,田川松独自留在日本抚养幼子长大成人。与丈夫多年分居异国,待到团聚时,已从一位二十七岁的少妇变成四十四岁的妇人。
其实,德川幕府之所以迟迟不放走郑芝龙的家人,除了由于日本实行的锁国政策外,还因为郑芝龙的家人是获得郑芝龙海外贸易集团利益的保证。田川松与田川七左卫门的存在,相当于郑芝龙在日本的“人质”,德川幕府能够通过此种手段控制郑芝龙,保证德川幕府的利益。所以,直到最后,郑成功的弟弟田川七左卫门也没有能够离开日本。然而,田川松的两个儿子,郑成功和田川七左卫门成为郑氏集团在中国和日本的真正继承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的“郑成功文学”中,对于郑母自立形象的描写,也表现在对家庭的经营上。陈墨峰《海外扶余》中郑母以“芝龙娘子”的称呼出现,且“芝龙的娘子又极其能干,把一份大家私拿在手里,盘得一点也不漏,而且只有多出来,再没有少了的。所以这一份家私越挣越大”。[14]46虽然笔墨不多,但能够对郑母有所涉及已属难得。
总之,在福住信邦的《国姓爷郑成功之母》中,田川松自幼就具有自立自强的性格,而且具有能够自立的生存技能,在与郑芝龙结婚后,对家庭的经营也表现出自立的女性形象的特点。同时,自立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的“郑成功文学”中也有所体现。自立是女性独立的保障,也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郑母生活的时代,日本正处于江户时期,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男尊女卑的观念是禁锢女性思想的牢笼,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没有自主权。中日文人所塑造的郑母自立的女性形象,体现了郑母独立的人格。可以说,郑母自立的形象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
(三)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以《国姓爷郑成功之母》《海外扶余》为中心
福住信邦的《国姓爷郑成功之母》在塑造郑母自立自强的女性形象的同时,还表现出郑母作为贤妻良母的一面。而且,中国的“郑成功文学”也表现出了这一特点,陈墨峰的《海外扶余》就是其中一部。
在《国姓爷郑成功之母》中,郑母的贤妻良母形象,首先表现在郑芝龙与田川松的恩爱之情上。福住信邦在描写郑芝龙与田川松的相识、相爱的细节时,字里行间充满了浪漫笔墨。郑芝龙用本命星的传说试图打动田川松父亲松庵,并承诺一定要让田川松成为“正室”。“如果不能和她结合的话,我想我这辈子大概不会设正室吧!”[13]21作者多次强调“正室”,体现出日本对于正室身份的重视。其实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在古代,正室始终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在中国“郑成功文学”中,关于郑芝龙与田川松成为夫妻的描写,陈墨峰在《海外扶余》中只是一带而过,“却说郑芝龙有一回做贸易到日本,却逢着一个同伙的朋友也在日本,问起芝龙年纪,很觉得敬慕,便替芝龙作媒,娶了一个日本女子。芝龙完婚后,便把她带了回来,一家团聚。”[14]6
其次,田川松的贤妻良母形象还表现在对儿子的教育上。郑芝龙夫妇对郑成功的期望是状元及第,因此这也成为对郑成功的教育目标。据该书描写,郑成功五岁之前的教育都是由田川松负责的。田川松对郑成功的教育方针,首先是“稳固幼儿的身体健康,其次陶冶情操,使其具有爱心”。[13]69田川松对郑成功的教育非常全面,甚至访遍平户岛,请求精通乐器的乐师为其演奏音乐陶冶情操。这种以幼儿为本的教育理念,虽带有虚构性,却充分体现了田川松对郑成功教育的用心良苦。在郑成功五岁时,父亲郑芝龙从福建家乡请来一位名叫鼓继德的秀才,从千字文开始传授郑成功中国古典文化,“于是田川松便和爱儿成为同学,共同上课。学习之后,她觉得能接触到丈夫祖国的文化,实在太幸福了。”[13]76田川松一直以母爱温暖着儿子郑成功的心,支持着郑成功为国家去战斗。
再次,郑母的贤妻良母形象还表现在其对名利、对生死的淡然态度上。国姓爷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松,在回到明朝不久后被授予“国夫人”的称号。然而,田川松被封为“国夫人”虽表面荣光,背后却遭到周围妻妾的排挤。即便如此,田川松依然心地坦然。她的一生中多次与亲人生离死别,对人生早已有所参悟,有种宿命论似的人生观。所以,当死亡果真降临到她头上时,田川松表现出了无比淡然的态度。当清军攻打安平城时,将领都逃跑了,田川松没有选择逃跑。当清军攻破城池,为了不受凌辱,田川松选择了自杀,“她一点也不把这些狼群野兽放在眼里,只是冷静地从怀中取出剑,往胸口插下,踉跄地走到墙边,闭目纵身而下……是不是自己在无意识中领悟到了自己的命运?”[13]215
关于郑母之死,《海外扶余》的描写截然不同。“‘清兵要来抢了,我们快走吧。’芝龙娘子听了,吓得浑身乱抖,话都说不出来了”,当芝龙娘子被赎出来的时候,“只见满面泪痕,和着血痕一条条的铺满,虽然众人一齐被虏,倒是她最苦了……到得晚上,乘众人都睡了,不防备着她却独自走到舱面,把蓬索拉了一根打了个圈,竟自缢死了。”[14]50中日两国关于郑母之死的描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然而最大的不同是,“受凌辱”后自杀这一细节自始至终在日本“郑成功文学”中没有出现。
以上对郑母的贤妻良母形象以《国姓爷郑成功之母》和《海外扶余》为中心,从对丈夫的支持、对儿子的教育、对人生及生死的观念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可以看出,中日“郑成功文学”中关于郑母贤妻良母形象的描写具有强烈反差。贤妻良母是对女性优秀品德的赞美,江户时期的女性因为受到家制度的制约,所以要求女性必须为家庭无私奉献,成为贤妻良母。中日“郑成功文学”所体现的郑母贤妻良母的形象,符合江户时期女性的身份特点。近代以降,日本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要求更加迫切。1899年2月,日本颁布了《高等女子学校令》,将培养贤妻良母视为女子教育的目标,目的是让女子在家庭中发挥妻子和母亲的作用,间接为国家做贡献。可见,日本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这一品行的重视。
三、民族文化语境与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形成
追溯郑母形象形成的源头,还是要回到民族文化语境中去认识。首先,对于郑母的身份认同,中日两国存在诸多差异,对此,福住信邦[15]397曾指出,也许是因为中华民族思想的原因,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母亲为倭妇是从心理上抗拒的,所以将她说成是翁氏,是在日华侨的女儿;还有的说成是倭王之女;最为甚者是被认为是丸山游女,而且即使在最后被杀害的时候还遭受了凌辱。即使现在,一听说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很多中国人都会大吃一惊。福住信邦不仅指出了中日两国之间对于郑母身份认同的差异,同时还指出了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那就是在中华思想的影响下,郑母的身份认同或被误解为在日华侨,或对其日本人身份从心理上抗拒而遭到抵触。福住信邦所述的中华思想,可以理解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郑母身份认同的差异。在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特征与差异也受到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家对郑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才会产生差异,从而使郑母形象特征体现了明显的时代的、政治的及文化的印记。
首先,就时代特点而言,郑母的形象特点不仅体现了日本江户时代女性的优良品德,还体现了对时代的超越。日本江户时期,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森严,日本社会是以武家社会的主从关系为基础构建的社会,在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夫妇关系等也被视为主从关系,女性以家庭为中心,被排斥在社会主导地位之外。当时对女性的教育,也与男性进行区别对待。关于女性的训诫书籍有多种,知名的女训,例如《女大学》《女论语》《女训孝经》《女今川》《女实语教》等,是女性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生存状况以及社会地位。其中,《女大学》是江户中期日本普及的女训,按照儒教传统观念,其中对于女性的教育理念以及女性结婚后的实际生活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女大学》规定女性一旦嫁人,对丈夫就要像对天一样彻底服从,并且详细规定了十九条女性必须遵守的要求,其中包括女性要心地善良,要顺从丈夫,要严守贞操,要万事勤俭节约,要勤勉,甚至包括女性不能嫉妒,不能多言等要求,体现了强烈的男尊女卑观念,成为禁锢女性的道德理念。从《女大学》对女性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女训受到了中国儒家男尊女卑等观念的影响,女性被认为是次于男性的存在,这也反映了当时日本女性的生存现状,那就是女性结婚后必须要成为贤妻良母,但是女性要想获得自立,具有独立的人格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中日“郑成功文学”所塑造的郑母的形象特点,例如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以及自立的女性形象,则超越了当时的时代,而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是与江户时代女性的身份特征相吻合的。
其次,就政治特点而言,最突出的表现是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郑母形象也随之变化。日本学者认为,“可称之为国姓爷热潮的时代,在日本至今曾出现过三次。第一次以近松的《国性爷合战》为开端,出现在享保期(日本年号,1716年至1735年)前后;第二次出现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第三次则出现在日本侵华战争之后。而且,每次‘国姓爷’热潮的出现都与中日关系的变化相一致。”[16]2作为日本代言人的郑母形象,发端于《国性爷合战》,是江户时期社会潜伏着的国家主义意识的反映,郑母形象的这种特征一直延伸到1958年矢代静一的翻案剧《国姓爷》,也就是说,郑母这一形象特点贯穿着日本出现的三次“国姓爷”热潮,一直持续到“二战”后。而在1987年福住信邦的《国姓爷郑成功之母》中,郑母形象却以自尊、自立的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出现,与上述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由此,伴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日本“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再次,郑母形象还深受中日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日本“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具有明显的武士道印记。事实上,武士道可以说是异文化融合的产物,因为武士道的起源除了来自日本的神道外,还来源于佛教和中国的孔孟之道。孔子思想中关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以及孟子的民本思想都被融入了武士道精神,甚至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也对武士道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江户时期是武士道的形成时期,同一时期近松的《国性爷合战》受其影响也是理所当然的。
郑母形象在《国性爷合战》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和藤内母亲为实现父子愿望不惜舍弃了生命。在武士道中,“女子为丈夫、家庭以及家族而牺牲自己,与男子为主君和国家而牺牲自己是一样的。”[17]120可以看出,和藤内母亲的牺牲,体现了武士道“忠”的精神。但是由于和藤内母亲复杂的身份,她的殉死体现了以下几层意思:一是,作为郑芝龙的妻子,她的牺牲直接原因是为了忠于丈夫;二是,按照武士道体系,忠于丈夫、为丈夫牺牲与为国家牺牲是一样的,所以她的牺牲是了国家,但是这里的“国家”,应该指日本,是为了不给日本带来耻辱而牺牲;三是,她的牺牲是为实现郑芝龙复兴大明的愿望,所以,她也是为复兴大明而牺牲。从以上三点可以推断出,和藤内母亲作为日本人,为了忠于丈夫郑芝龙,为实现复兴明朝的伟业而牺牲,实际上就是日本人为了拯救中国而牺牲了生命。而且,和藤内母亲死得毅然决然,这也是武士精神中“勇”的一种体现。同时,和藤内母亲用于自杀的怀剑,有九寸五分,是标准的日本女性用于防身的短剑,“对日本妇女而言,不知如何自杀是一种耻辱。一位女子虽未学过解剖学,却必须清楚哪里是割喉的正确部位。”[17]117在《国性爷合战》中,和藤内母亲就是割喉而死。而且,在《国姓爷郑成功之母》中,郑母田川松在赴死那一刹那对死亡早已有所领悟,可以“清楚看到阳光下她的脸上浮现的一丝微笑”。[13]216这种生死观,也是武士精神的体现。武士道最为赞赏的女子,就是要能够从女性的柔弱中解放自己,展现出足以与男性相媲美的刚毅。
另外,在《国性爷合战》及其翻案剧中,郑母慷慨激昂的演说中“个人耻辱”、“日本耻辱”曾反复出现,郑母形象的这一特点体现了武士道对“名誉”的重视。在武士道中,名誉被认为是人不朽的构成部分,任何对个人名誉清白的玷污都是莫大的耻辱。另外,对于女武士而言,她们一生要为了维护家庭的名誉和体面而任劳任怨,甘于奉献,“作为女儿,她们为父亲牺牲自己;作为妻子,她们为丈夫牺牲自己;作为母亲,她们为儿女牺牲自己。”[17]119所以,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她们要能够支撑起家庭的重担,具有自立精神,成为贤妻良母。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受凌辱”这一细节的差异,即在日本“郑成功文学”中这一细节没有出现。那是因为“对女武士来说,贞操是最重要的德行,比生命还重”。[17]117郑母田川松在松浦藩藩主府邸曾习过短剑用于防身,这就为后来田川松的殉死做了铺垫。所以,当清军攻破城池,田川松没有选择逃走,而是在遭受凌辱之前英勇自杀,从而形成了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差异。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郑母形象所体现的日本文化的武士道印记,如女子为家庭的无私奉献、视贞操为生命等均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儒家文化被武士道吸收融合后所呈现出的武士道印记。同时,郑母形象在日本“郑成功文学”中的特征,或多或少也表现出日本作家对郑母这一日本女性所持有的特殊的“文化成见”[18]239,即对郑母这个“自己人”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
综上所述,中日“郑成功文学”中的郑母形象,在民族文化语境影响下郑母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实像与虚像交织的特点。以《国性爷合战》及其翻案剧、《国姓爷郑成功之母》等一系列日本“郑成功文学”的代表作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日本“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变迁体现了三个特征,分别是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自立的女性形象、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在与中国“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比较后发现,作为日本代言人的郑母形象具有独特性,是日本“郑成功文学”所特有的形象特征。而且,郑母形象并未成为中国戏剧家关注的焦点。自立的女性形象与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则是中日“郑成功文学”所共有的特点。受到民族文化语境的影响,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特征与差异,体现了明显的时代、政治及文化印记。从时代特点来看,郑母形象特点不仅体现了日本江户时代女性的优良品德,还体现了对时代的超越;从政治特点来看,表现为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郑母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文化特点而言,日本“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体现了明显的武士道印记,这些武士道印记有些来源于中国儒家思想对武士道的影响,因此,郑母形象在体现出日本特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与中国“郑成功文学”郑母形象的共性特点。而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下,中国“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上对郑母身份认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文化人出于民族感情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母亲为日本人这一事实的抵触。
[1]匪石.郑成功传[M].台北:台湾银行,1960.
[2]连横.台湾通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江日升.台湾外志[M].济南:齐鲁书社,2004.
[4]陈三井.郑成功全传[M].台北:台湾史迹研究中心,1979.
[5]朝川善庵.鄭将軍成功伝記碑[A].日本随筆大成[C].東京:吉川弘文館,1975.
[6]幸田露伴.鄭成功[A].露伴叢書(下)[C].東京:博文館,1902.
[7]河村哲夫.龍王の海:国姓爺·鄭成功[M].福岡:海鳥社,2010.
[8]染崎延房.台湾外記 (一名国性爺)[M].東京:永保堂,1874.
[9]稲垣孫兵衛.鄭成功[M].台北:台湾経世新報社,1929.
[10]中山久四郎.国姓爺鄭成功の母[J].歴史教育,1958,(10).
[11]近松門左衛門.国性爺合戦[A].近松門左衛門集[C].東京:新潮社,1986.
[12]久保栄.史劇国姓爺新説[A].久保栄選集Ⅰ(中国湖南省)[C].東京:中央公論社,1949.
[13]福住信邦.国姓爺鄭成功の母[M].東京:講談社,1987.
[14]陈墨峰.海外扶余[M].孙菊园,孙逊校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15]福住信邦.新国姓爺合戦物語り(下)[M].東京:講談社,1992.
[16]油屋亮太郎.新国性爺合戦物語り序[A].新国性爺合戦物語り(上)[C].東京:講談社,1988.
[17]新渡戸稲造.武士道[M].東京:岩波書店,2006.
[18]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杨 春
Changing Image of Zheng’s Mother in Sino-Japanese“Zheng Chenggong Literature”and the National Cultural Contexts
KOUShuting
Zheng Chenggong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 relationship,whose mother was one ofthe focuses ofthe academic circle in the twocountries.Taking“ZhengChenggongliterature”in China and Japan as the object of study,it can be found that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identity of Zheng’s mother was interwoven by facts and fictions,and the changing image of Zheng’s mother has shown different features in the two countries.The image of Zheng’s mother as a Japanese female specially belong to Japan’s“Zheng Chenggong literature”.But the image of Zheng’s mother as a self-independent and virtuous wife and mother was commonly shared by China and Japan’s“Zheng Chenggong literature”.The obvious imprint of time,politics and culture has helped to form the image of Zheng’s mother in“ZhengChenggongliterature”in the twocounties.
ZhengChenggong;ZhengChenggongliterature;Zheng’s mother;female image;national cultural context
10.13277/j.cnki.jcwu.2017.04.008
2017-05-10
I313.06
A
1007-3698(2017)04-0063-08
寇淑婷,女,满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女性文学。100875
本文获得2016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编号:留金发[2016]3100号)的资助,亦系国家重大项目 “‘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14ZB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