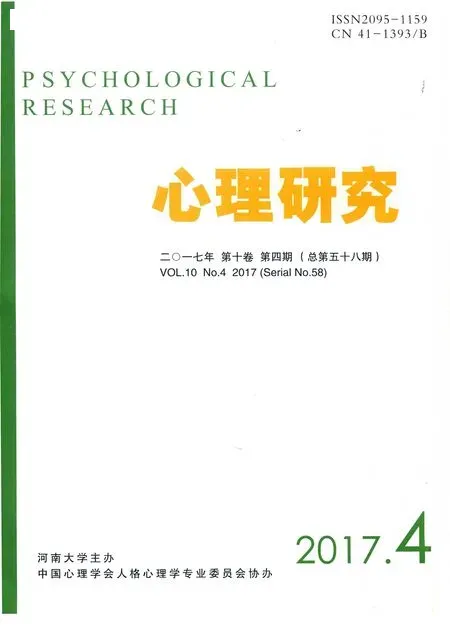由认识论真理向本体论预设的回归
——笛卡尔心—身困境的逻辑追踪
李莉莉 高申春
(1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乌鲁木齐830017;2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长春130012)
由认识论真理向本体论预设的回归
——笛卡尔心—身困境的逻辑追踪
李莉莉1高申春2
(1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乌鲁木齐830017;2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长春130012)
作为近代哲学始祖的笛卡尔,通过系统怀疑的方法找到了唯一毋庸置疑的真理——“我存在”,然而古典哲学对世界的本体论探寻形成了人们关于“存在”的客观化理解模式,这种客观化理解模式限制了笛卡尔,使其无法对“思维或精神存在”的认识论意义进行充分地揭示。因此,“我作为一个思维的东西、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心灵存在”就由一条认识论真理回归成一个本体论预设。在此前提下,心灵与身体成为两个平行的实体分属于精神和物理的世界。在处理心灵为什么能够感受到身体的状态的问题时,笛卡尔陷入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一心—身困境造成了心灵哲学长期以来无休止的争论和困惑,甚至成为现代心理学不断变革的元凶。
笛卡尔;认识论;本体论;心—身困境
笛卡尔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思想日趋深入人心,神学逐渐失去支配力的历史转换时期。通常,人们认为17世纪是这一转换的时间节点[1],代表了近代的开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没一个会让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感觉不可解;路德会吓坏托马斯·阿奎那,但是阿奎那要理解路德总不是难事。”[2]而此后,科学的发展对于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处在近代开端的人们而言,神学在其精神思想领域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学的进步和神学的退却不是无限的。这一时期的科学家几乎都同时又是教徒:哥白尼是宗教法博士,当过教士;伽利略既是科学家,也是天主教徒;就连缔造了整个自然物理主义的牛顿也将那些暂时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帝的安排。笛卡尔自视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沉思录》是为促进教会神学的说服力以及维护人们对上帝和灵魂的信仰而著,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16、17世纪的人们在情感上仍然坚定地相信灵魂与上帝的存在,在这种态度下,很多科学家因同时具有教徒的身份而着意将科学与神学划分开来。如伽利略深信,科学的任务是探索自然规律,而神学的职能是管理人们的灵魂,二者不应互相侵犯。
对于拥有科学精神同时又善于沉思的笛卡尔而言,科学与神学的这种划江而治并不能让他满意。因为在他心中有着一种忧虑,这种忧虑既包括对科学无神论威胁的担心,也有来自他自己的矛盾,即在追求真理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在《沉思录》的卷首,笛卡尔在“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院长和圣师们”中说:尽管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教的人来说,光凭信仰就足以使我们相信有一个上帝,相信人的灵魂是不随肉体一起死亡的,可是对于什么宗教都不信,甚至什么道德都不信的人,如果不首先用自然的理由来证明这两个东西,我们就肯定说服不了他们[3]。从表面来看,笛卡尔似乎作为教徒坚定地相信上帝和灵魂,但实际上,与其说他在用“自然的理由”来向无神论者证明,不如说他在努力说服自己,因为他无法仅凭信仰将上帝和灵魂作为先在条件接纳下来,而必须以一种系统的、逻辑一贯的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它们的存在,更为主要的是通过这种方法,他能够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因此,笛卡尔意欲抛弃一切传统观念,建立一种拥有坚固基础的系统哲学,即“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衰的东西”。
1 毋庸置疑的“我存在”
笛卡尔通过系统的怀疑来寻找坚定可靠、经久不衰的东西。笛卡尔说,感官有时会在很小的事物和远距离的事物之间糊弄我们,因此不值得完全相信,而且就连诸如此刻“我坐在炉火旁,穿着冬天的睡袍,手里拿着一张纸[3]”这样清楚明白的事也没有什么确定无疑的标记和相当可靠的迹象来使人分辨出清醒和睡梦。但是即便如此,睡梦中所虚幻的假象也总在模仿某种真实的东西,而即便这些假象荒诞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也总有某些更简单、更一般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的,以构成这样荒诞的形象。在笛卡尔看来,这些真实存在的、更简单更一般的东西就是物体的一般性质和外延:具有广延性事物的形状;事物的量,即大小和数目;以及事物所处的地点,所持续的时间,诸如此类。也就是说,我看到的某个事物有可能是一个虚幻的假象,也可能是我在睡梦中的所见,但是对于事物的一般性质无论是清醒还是睡梦中都是不变的,是确定无疑的,比如2+3恒等于5,正方形总有四个边等。因此,数学、几何学就比物理学、天文学、医学更为可靠,因为前者所对待的是一些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东西,而后者由于对待的是一些复合的(composite)事物因而是可疑的。
然而,对于更一般的、更简单的这类认识总还可以进行怀疑,因为倘若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奸诈狡猾的恶魔来使我总是这样计算,并总是让我认为正方形有四个边,那么我岂不是就轻信了他的诡计?但是,所有这些可怀疑的点都指向了一个确定无疑的事件,那就是“我”的存在!我的所见可能是虚幻的或梦境中的,但如果没有“我”,哪里来的假象呢?我可能会按照某个神灵的安排进行计算,但这恰恰说明了作为欺骗对象的“我”的存在,“有我、我存在”(I am,I exist)[3]这个命题是确定无疑的。
那么,“我”又是什么呢?笛卡尔说,从以往的一些观念来看,我想起我曾经认为自己有脸、手、胳臂,这些都是我的“身体”(body)部件,“身体”和其他物体一样,具有一定形状,位于某处,排他性地占据一个空间,能通过触摸、观看、聆听、品尝或鼻嗅加以认识,能够进行移动,但身体的这些性质和“我”有着本质的区别。我还记得自己吃饭、走路,感觉并思考各种事物,这些活动可归于灵魂。灵魂诸事项中是否有我之为“我”的内容呢?由于“我”不同于“身体”,那么,吃饭、走路这些能力对于“我”的本质而言当然也只是虚妄。那么感觉呢?显然感觉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生,而且有时我梦见自己感受到了很多事物,但之后发现什么也没发生。那么思维呢?笛卡尔发现只有思维是真实的,是不能与我分开的,是我之为“我”的根本,我可以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思想持续一秒,我便存在一秒,思维停滞,我亦不复存在。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
2 作为一个精神或心灵的存在的“我”与物体或身体的关系
既然,“我”在本质上等同于一个思考的东西,一个精神、理智或心灵,“我存在”是唯一毋庸置疑的真理,那么还有什么其它的东西存在吗?由于“我”作为一个思维的东西,一个理智或理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至善的、完满的上帝,是这个无限的、永恒的、常驻不变的、不依存于其他东西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一切东西由之创造和产生的实存,将某些认识能力和真理放在“我”之中。因此,上帝必然存在。同时,可以得出一条一般原理:凡是我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因为正是上帝给了我这样尽善的认识能力。那么,我们清楚分明地领会到了什么呢?笛卡尔说,“我”的确认识到物质性的东西可以存在,因为我清楚而分明地觉察到了它们[1]。
2.1 论物质性身体的存在
我如此清楚分明地通过感官觉察到了很多事物。我感觉到我有一个头、两只手、一双脚等等,它们构成了身体的组织。我感到我的身体处于其他很多物体之中,并受到它们各种有益或有害的影响。愉悦感和痛苦感使我衡量出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的。除了快乐和痛苦之外,我还感觉到内部的饥饿、口渴以及其他感受的质。我也能感到光、颜色、气味、味道以及声音,以此为基础我识别出天空、大地、海洋以及其他物体,并把它们相互区分开来。现在,既然所有关于这些性质的观念向我的思维呈现了它们自己,而且这些性质全都是我恰当而直接地感知到的,那么就不无理由说我感觉到了明显不同于我的思维的事物,也即,那些观念赖以产生的物体。借助经验我知道这些观念在未经我许可的情况下就向我全然呈现出来,它们的呈现不受我的意愿左右。并且,由于通过感觉觉察到的观念比我有意地通过沉思形成的观念抑或印在我的记忆中的观念更为生动、清晰,甚至更为独特,因此它们似乎不可能来自于我自己,只可能来自于其他事物。另外,我发现我会使用想象的能力来应对物质性的事物,而想象就是认识功能在某个直接呈现的物体(body)上的应用,因此该物体是存在的。为了进行想象,我需要心灵的一种特殊的努力,这种努力是理解和领悟所不需要的。这种努力也将想象与纯粹理智活动区别开来。因此,就其区别于理解力而言,想象力并非我的本质(也即我心灵的本质)之必须,因为即使我缺少想象力,我也仍旧是现在的我。这样一来似乎可以推论出,想象力有赖于某种不同于“我”的东西。
这种想象力所依赖的不同于我的东西就是身体(body)。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首先使用“body”这个语词来意指外在物体。在论述外在物体存在之后才借助对想象能力的分析推论出身体的存在。他说,我很容易理解到,可能有一个身体存在着,正是借助这个身体,我才能想象实体事物。想象这种思维形式与纯粹理智区别开来是在如下这个意义上说的,即当进行理解时,心灵就在一定意义上转向它自己,并省察在它内部的某个观念;而当它想象时,它就转向身体,并在身体中直觉到某个与观念相符合的事物,而这个观念要么由心灵的理解而来,要么由感官的觉察而来。诚然,如果身体确实存在的话,想象就能够以这种方式实现。并且我想不到还有其他恰当的方式来解释想象,所以我做了一个可能的猜想,即身体是存在的。
2.2 作为一个精神或心灵的“我”与物质的身体的区别
笛卡尔哲学具有如下几个要点:唯一毋庸置疑的真理和逻辑基础——我存在;一个一般性原理——凡是我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以及一个推论——外物和身体的存在。那么,“我”、外物、身体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呢?“我”在本质上是一个理智、精神(spirit)或心灵(mind),在笛卡尔看来,这个理智、精神或心灵显然是不同于外部事物的,那么身体呢?“我”这个精神存在与这个身体又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笛卡尔认为心灵与身体截然有别。他说,我清楚分明地将心灵和身体领会为不同的实体(substances),那么根据一般性原理可知,心灵和身体一定相互有别。在笛卡尔看来,身体和外在物体一样都是物质性(materialistic)的,具有某种形态、位于某个位置、排他性地占据一定的空间,可以统称为“body”。那么就身体仅仅是一个外在之物而不是一个思维之物而言,就可以确定我与我的身体截然有别。并且笛卡尔认为,纵然没有身体,心灵也会一如现状。心灵和身体的差异还在于身体就其本性而言常常是可分的,而心灵则完全是不可分的。因为当我考虑心灵时,即当我考虑我自己时,我在我之中区分不出什么部分来,即我将我自己理解为一个浑然一体的完整的东西。尽管整个心灵似乎与整个身体结合在一起,但如果一只脚或一条胳臂或任何其他身体部分被截去,也不会有什么东西从心灵中被拿走。也不能将意愿、感觉、理解等功能称为心灵的“部分”,因为正是这整个的、同一的心灵在意愿着、感受着和理解着。而在我能够想到的任何实体的或广延的事物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不能在思维里划分成各个部分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可分的。人的身体是由更多的偶然性构成的,而心灵则具有更多的一般性,心灵能够理解不同的事物,能够想要不同的事物,能够感受不同的事物,但心灵本身却从未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肉体很容易死灭,但精神或心灵就其本性而言是不灭的。此外,不仅心灵可以独立于身体而存在,而且由于人的身体是某种由骨骼、神经、肌肉、血管、血液以及皮肤等零件装配构造而成的机器,即使没有心灵存在于其中,仍然会展现所有它现在具有的运动,除了那些受意志或者因此也可以说受心灵支配发起的运动外。因此,心灵与身体不仅是彼此有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彼此对立的。
2.3 心灵与身体的联系
心灵与身体虽然截然不同,但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身体,出于某种特殊的权利被称为“我的”,要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属于我,因为我永远不可能像与其他物体那样与它分离。在我的身体之中,我能感觉到所有的饮食之欲和情感。我注意到来自这个身体而不是别的外在物体的疼痛和愉悦感。而且我的天性(nature)也使我明白,我出现在我的身体中,就像一名舵手出现在船只上,不仅如此,我最为紧密地与之相联,也就是说,与之混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与身体构成了一个东西。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作为仅仅是思维之物的那个存在,当身体受伤时,将不会感觉到疼痛;或者毋宁说,我将通过纯理智手段来觉察伤口,就像舵手通过观察来判断他的船只是否有损坏。当身体需要食物或饮料时,我会明确地对此加以理解,而不会困惑于饥饿和口渴的感觉。因为显然这些口渴、饥饿、疼痛等模糊的思维形式不是来自于别的,正是发自于那个由心灵和身体混合而成的整体。
那么,为什么“我”在本质上不同于身体,但却能够感受到来自身体的疼痛呢,或者说心灵和身体这两个完全独立的平行的实体是如何实现交流的呢?显然,“我”出现在我的身体中,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发现身体的需要,帮助它做出判断。因为在身体周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物体,它们对身体存在着或有益的或有害的影响,心灵需要判断哪些事物是要接近的,哪些事物需要躲避。在这个过程中,身体的状况会通过脑作用于心灵,而且这种作用是一一对应的,即脑中的任一特定运动都只引起心灵中的一个感觉。比如当喉咙发干时,会引起脑中的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反映到心灵中就产生“渴”的感觉,这时心灵就判断应该喝水了。同样,笛卡尔认为,当脚部受伤时,经过神经的传导,也会引起脑中的一种运动(当然有别于喉咙发干的运动),这种脑部运动会在心灵中映射出“疼痛”的感觉。后来笛卡尔主义者们将这种对应关系解释为:身体和精神好似两个钟,每当一个钟指示出“干”,另一个钟就指示出“渴”。这种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进一步说明在感觉之后发生的由心灵向身体的回转,当心灵感觉到渴之后它会做出一个判断,指引身体趋向于水,这个指引也同样会映射为脑中的某种运动吗?如果是,是否可以说心灵在控制身体呢?这不是明显地与身体完全受物理定律支配相抵触吗?而且这样的影响不也恰恰违反了心灵和身体分属于不同世界互不干扰的总体主张吗?
3 笛卡尔心—身困境的逻辑追踪
3.1 “我存在”由认识论断回归为本体论预设的逻辑分析
笛卡尔普遍怀疑方法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一方面其认识论的动机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即通过普遍的怀疑寻找确凿的认识基础,并通过严格的逻辑论证来确定认识原理,取得一般性结论,这对于以神学为主导的中世纪哲学而言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另一方面,笛卡尔通过向内省思而使主观存在上升为认识论的基础,这极大地鼓舞了人类理性和意识主体的自觉性和自信性。自笛卡尔以后,理性主义富有生命力地成长为近代哲学的重要形式之一,而在自然科学极具膨胀力的现代,这种自觉性和自信性又给予了现象学以生命。
然而,笛卡尔对于自己通过普遍怀疑寻找到的毋庸置疑的真理“我存在”所具有的认识论意义的理解是不彻底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在笛卡尔所处的时代,人们对于“精神实在”的认识尚未完全脱离本体论的束缚。古典哲学对世界的本体论探寻形成了人们关于“存在”的客观化理解模式,即将存在理解为像物理的东西那样的实体,人们关于灵魂的观念就是这样的。当然,这是由认识本身的类比习惯导致的。由此,本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论断的“我存在”,就在不知不觉中回归成一个本体论预设,“我”作为一个精神或心灵与身体并列起来,成为两个无法沟通的实体。“我存在”是笛卡尔二元论的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症结,而且,在后世很多以心灵为主题的哲学中,“我”变成了“笛卡尔式幽灵”令人困惑不解。
实际上,如果笛卡尔能够进一步彻底地贯彻其认识论初衷,就会达成一种与实体二元论完全不一样的认识二元性理论[4]。他将看到“我存在”这一结论的得出来自于认识主体的向内省思,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对外部物理世界进行认识的方式,因为后者是主体作为外在于认识对象的第三人称实现的认识,与此不同的是,前者是主体内在地包含在认识对象之中,或者说是和认识对象相同一的自我认识。前者是内在的洞察,后者是外在的观察。如果在笛卡尔沉思之时,有另外一个沉思者对笛卡尔进行身体解剖(这正是现代脑神经科学所实现的研究模式),那么笛卡尔的“我存在”就会失效,因为这另外的认识者除了看到笛卡尔的脑及神经系统的一系列活动外,将一无所获,精神或心灵的实在性除了笛卡尔这个主体的自我省思外决不能由除他以外的另一个人通过观察得到,即便是主体间的移情式思维也只是在推论的意义上承认他者存在。因此,“精神的存在”与“物质的存在”来自于人类的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它并不能构成两个相互平行的实体,或者说精神和物质并不属于同一个范畴体系[5]。由于笛卡尔没能把握到这一点,他把素朴实在论意义上的身体(包括脑)归属于物理的世界,把他由普遍怀疑得到的“精神存在”在区分的意义上与其并列起来,之后再来解释这个由他人为地搭建起来的二元论世界中心灵和肉体的关系,所以除了自相矛盾外,笛卡尔未能提供心身关系的有价值的解答。在这个意义上,心身关系实为一个伪命题。
由于笛卡尔这种认识论的不彻底性所造成的心灵与身体作为实体的对立,最为突出地影响了现代实验心理学的发展进程[6]。现代实验心理学从其建立到每一次危机的出现和应对都集中体现了笛卡尔实体二元论的范畴错误。如前所述,笛卡尔提出“我存在”这一论断给了心灵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合法性,因为既然心灵是与物质、与身体相对立的截然不同的一个实体,而自然科学已经对物质对身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那么心灵不仅应该是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被广泛地视为人类理智的重大成功,将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用于研究心灵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在19世纪,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被用来研究心灵,该尝试导致了实验心理科学这个产物。随后,美国机能心理学从德国心理学那里承袭了整个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从其性质来说是笛卡尔式的,即将意识视为某种独立于身体而自足的实体存在的那种理解方式[7]。这一概念体系与美国心理学所信奉的实用主义精神相矛盾,从而导致了机能主义的危机以及作为对这一危机的应对的行为主义运动的兴起。行为主义运动所奉行的对意识和心灵的取缔最为明显地违背了心灵存在这一认识论基础,也与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前提相抵触,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学再次陷入危机[8],继而兴起的认知心理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对心灵实在的关注,但是已经失去自身理性优势的心理学无力重新揭示自身的逻辑矛盾,从而遭遇到当代具身认知研究的冲击。这是另外的主题,这里不再多言。
3.2 实体二元论的心—身困境
从前面对笛卡尔实体二元论的介绍可知,由于笛卡尔仍然受限于素朴实在论[9]意义上的存在观念,而未能彻底发掘“我存在”的认识论意义,从而使“我”或“心灵”获得了与物质一样的实体意义,心灵与身体成为同一个范畴中的两个相互平行又完全不同的实体。于是,对于外物如何通过身体引起心灵上的感觉的问题笛卡尔表现出了逻辑上的矛盾。实际上,笛卡尔意义上的心身关系问题是一个伪问题。从本质上说,“我”或心灵作为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的对立不是本体论或素朴实在论意义上的对立,而是人类作为认识主体的两种认识途径的对立,这两种认识途径就是向内的洞察与向外的观察。对于心灵而言,唯有这个心灵主体的向内省思才能获得其自身存在的证明,任何来自外部的观察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心灵。因此,这种精神实在是如此不同于任何物质,因为所有物质性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外在的观察来认识,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唯有精神或心灵不能被观察。换句话说,任何来自外部的认识都绝不会找到心灵,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心灵没有进行向内的省思,“我”的心灵便不存在。因此,把心灵和身体或脑并列起来去寻找二者沟通的方式显然是无效的伪问题。
很多现代人都能轻易地拒绝笛卡尔的二元论,但在具体说明心灵或意识问题时,仍然会陷入心身二元的思维方式。如心灵剧院的比喻[10],有人将意识的发生过程作这样的描述。在身体内部(特别是在头部)仿佛有一个小人,他坐在一个屏幕前,屏幕上是感官从外界获取来的一系列形象。那个小人就是真正的“我”。“我”好像就是寄居在身体中的一个幽灵,从大脑的某个地方往外看,或者在脑海里想象某些事物,然后指挥身体做出各种行为。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曾经误导很多神经科学家去寻找与意识相对应的脑区,并企图在那里发现心灵存在的证据[11],但事实已经证明他们失败了。
笛卡尔二元论造成了持久而深远的困惑,其心身关系问题在现代衍生出一个新的表达方式——代表精神属性的心灵与代表物理属性的脑或神经系统的关系。当然这个问题不再是对二者之间如何沟通的追问,而是致力于理解心灵和脑的本体论性质。在笛卡尔的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心灵与脑密切相关,但出于与笛卡尔一样的认识局限,心灵与脑的关系并未被完全揭示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在神经科学所代表的自然科学态度如日中天之时,心灵曾一度被还原为脑的活动,心灵的存在几乎成为一种谬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意识的主观性质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心灵或意识与脑的关系问题也成为心灵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心灵与脑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心灵是脑构建出来的自我概念,心灵存在只能由这个脑所属的个体通过自我洞察的方式获得,而脑作为一个物质的东西是外部观察(外部认识)的对象。心灵与脑在性质上的对立与任何我们已知的其他对立关系都不同,任何将心灵与脑在类比的意义上进行的理解都将歪曲二者的关系。心灵与脑的对立源于人的两种认识途径的矛盾,一个人不能既向内省思获得“我存在”的心灵体验,又同时从脑中“跳出来”外在地观看自己的脑。换言之,心灵与脑二者在同一种认识方式下只能存在一个。如果是个体进行自省,那么这个人就内在地体验到自己的心灵,如果他被另外一个个体外在地观看时,就只能看到脑,绝看不到被观看对象的心灵。我们关于他者心灵的设定完全来自于一种同理心,这种同理心容易使两种认识途径叠加起来,造成笛卡尔式的困境。正因如此,物理主义才会从根本上否认心灵的存在,因为物理主义所采用的全部方法都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看待被研究对象,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物理主义坚称世界只有物质别无其他。但是脑恰恰是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物质,它能构建出一个心灵的体验并为自己所把握,在这种向内的体验中衍生出了一个精神的维度,而这个维度才是人存在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心灵存在着。
1斯潘根贝格,戴安娜·莫.科学的旅程.郭奕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1.
2Russell B.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Simon&Schuster,inc.,1945:525.
3Descartes R.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Translated by Donald A.Cres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1998:47.
4BuckhamJW.Dualismorduality?The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1913,6(2):156-171.
5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3.
6Wright H W.Dualism in psycholog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940,53(1):121-128.
7高申春.心理学危机的根源与革命的性质——论冯特对后冯特心理学的关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45(5):150-155.
8黧黑.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刘恩久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421.
9孙正聿.哲学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207.
10布莱克摩尔.意识新探.薛贵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160.
11Dennett D C.Consciousness explained.Little,Brown and Co.,1991:21-42.
Regression from an Epistemology Truth to an Ontological Preset:The Logical Track of Descartes’Mind-body Dilemma
Li Lili1,Gao Shenchun2
(1 College of Educational,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Science,Urumuqi 830017;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
As the ancestor of modern philosophy,Descartes found the only undoubted truth that‘I exist’by the universal doubt.However,the ontological groping for world in classic philosophy made an objective comprehension to the‘exist’,so that Descartes was restricted in revealing the epistemology meaning of‘I exist’or‘the thought exist’adequately.Consequently,the judgment that‘I am a thinking thing,a spirit,an intelligence or a mind’regressed from an epistemology truth to an ontological preset.On this premise,mind and body became two parallel substances which respectively belongs to spirit and material world.On the problem of how the mind feels the body’s state,Descartes made a logical contradiction.Such a mind-body dilemma not only led to the endless argument and confusion in mind philosophy,but also caused the ceaseless revolution in modern psychology.
descartes;epistemology;ontology;mind-body dilemma
高申春,男,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schgao@sina.com
①为方便起见,以下将直接用笛卡尔的第一人称“我”来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