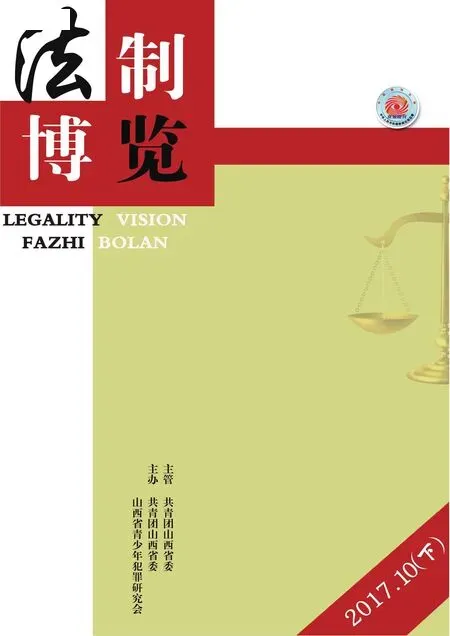实现领土分离的全民公决之法理刍议
——兼论救济性分离理论和内部自决理论
应弘毅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实现领土分离的全民公决之法理刍议
——兼论救济性分离理论和内部自决理论
应弘毅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在所有殖民地基本都实现独立的当代社会,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使领土分离的情形却依旧屡见不鲜。这其中涉及到的实质问题是尊重一国内部某一地区的居民的集体意志与维护该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之间的矛盾。曾有学者提出救济性分离权和内部自决权的理论,但二者都在法理上存在缺陷,难以自洽;而作为频繁出现的全民公决,其实现路径需要有更为充分的法理进行阐述。将主权让渡理论扩展到全民公决的问题之中,以综合考量分离地居民的集体意志和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更为适宜的解释路径。
全民公决;领土分离;救济性分离;内部自决;主权让渡
全民公决是指国际法承认在特定条件下,由某一领土上的居民通过投票来决定该领土的归属①。被殖民的民族争取殖民地的独立和原战败国试图收复被占领土均可以采取全民公决的方式,前者如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通过全民公决独立,后者如1935年萨尔区通过全民投票重与德国合并。而随着殖民时代的终结,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国家领土变更的情形并未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这主要是因为一国内部某一地区的居民也试图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领土是否分离,比如魁北克省曾在1980年和1998年两次举行全民公投试图从加拿大中分离,而在2014年又分别出现了苏格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与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的公投。与魁北克省和苏格兰公投不同,克里米亚的脱乌公投并不为乌克兰政府所承认,可见有些全民公投本身存在合法性的争议。因此,我们必须以国际法为依据,厘清全民公决的实现路径,以确认其合法状态。
对于一国国内居民是否有权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该地区的领土分离,学界曾提出救济性分离理论和内部自决理论,而这二者在法理上均存在缺陷。为弥补二者在法理上造成的缺陷,本文旨在运用主权让渡理论,探究通过全民公决实现领土分离的合法路径。
一、救济性分离理论的缺陷
救济性分离理论的出现与民族自决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第5项原则第7段规定:“以上各项不得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破坏或损害在行为上符合上述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原则并因之具有代表领土内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之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这一段本旨在尊重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救济性分离理论则认为通过反向解释可以得出:如果一个主权国家以种族、信仰或肤色为由拒绝某部分人民参加政府(即内部自决权被否定),将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作为最后的救济,这部分人民可以以分离的方式行使自决权(即救济性分离)。②然而,救济性分离权本身就存在法理上的诸多缺陷。
首先,救济性分离权不是民族自决权的衍生与发展。行使民族自决权导致领土变更的结果是殖民地独立,而行使救济性分离权则可能导致国家分离,即一国国内的部分领土脱离母国而成立一个或几个新国家。这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母国是否将这一部分领土视为与本国其他领土(特别是本土)无异,而非该部分领土之上的居民是否享有与本国其他地区的居民的同等权利。因为殖民地独立不涉及宗主国的主权问题,而国家的分离则必然地牵扯到母国的领土和主权问题。因为殖民地和其他被外国占领或统治的领土,从来就没有被它们的宗主国视为其领土的组成部分,而是作为它们的海外属地对待的。③
此外,即使一国内某一地区的居民的政治权利与本国其他地区居民的政治权利不相同,也不能必然推出前者享有民族自决权,遑论救济性分离权。这是因为针对民族、宗教信仰等不同的居民,国家可能会颁布适应不同族群的国内法,导致不同族群的权利的差异,但这并不一定就是歧视,因为有时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反而会使社会达到平衡。比如,由于弱势族群的参政议政能力弱或弱势族群所在地远离本国政治中心,而存在削减其政治权利的可能。比如,关岛、美属萨摩亚和北马里亚纳群岛邦等美国的海外领土,其居民都具有美国国籍,却没有选举总统的权利。
再退一步而言,即使存在对少数族群的实质性的法律权利的缺失,少数族群是否可以依据救济性分离权使国家分离呢?从国际公法的法理看,一国对其国内某一区域的居民行使不法行为原则上不适用国际责任法的调整范围,而应适用其国内法;若一国对其国内某一区域的族群进行诸如大肆屠杀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时,这种行为虽然属于国际罪行,但国际责任法中也并未将国家领土的分离作为国家责任的形式。
二、内部自决理论的瑕疵
内部自决权主要是现存国家的整个人民不受外来干涉地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决定其政府的形式;作为一国整个人民一部分的种族团体在不受歧视的基础上平等参政的权利;以及少数者取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利。④从实质上而言,内部自决理论和救济性分离理论存在逻辑的一致性。正是由于人民存在内部自决的权利,当其权利受到侵犯时,人民有权通过领土分离的方式以保障其人权。
从内部自决理论看来,人民平等参政和少数者享有一定自主权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人民不能平等参政或者少数者没有一定自主权,则人民可以决定国家是否存在,甚至将领土分离。内部自决理论强调一国内居民的政治权利的平等性和自主性,这看上去与人民主权理论和社会契约理论一脉相承,但其实已经完全跨越了这二者的理论界限,成为谬误。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言:“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⑤可见,卢梭认为国家主权只能存在一种意志,而这种意志应当是国内全体人民的公意。而内部自决理论忽视了普遍性的公意,仅强调了某一地区居民或是某一族群的“独意”。这种逻辑显得荒诞可笑:如果一国内有无数族群,那么这国内将存在无数的“独意”。这种“独意”若不能转化成公意,则与卢梭主张的单一意志相违背;如果“独意”能转化成公意,那么内部自决则不应局限于某一地区居民或某一族群的自决,而应当是一国内全体人民的共同自决,也就是说,一国内某一地区居民若想实现领土分离,应当由国内全体人民投票公决,而非囿于这一区域的居民。
三、主权让渡下的全民公决
由于救济性分离理论和内部自决理论本身存在法理上的缺陷,难以证明全民公投的合法实现路径,因此其合法路径需要有新理论的支持。归根到底,救济性分离理论和内部自决理论难以自洽是因为二者都试图从公民权利的角度去解释国家分离的问题,而忽视了从国家主权本身去审视这个问题。
因为一国很少存在单一的种族或民族,各民族间往往存在杂居的情况,在少数族群的聚居地,在国内占多数的族群则又成了少数。假设同一民族间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会在全民公决中投一致票,那么就会出现区域内部出现源源不断的全民公决,可能会不断出现新分离出的国家又继续被分离的可笑情形。因此,仅凭民众的权利配置不公和利益诉求需要就进行全民公决显然是不符合国际法逻辑的。
而在国际实践中,尽管有可能出现民众为寻求领土分离的抗争,但其全民公决的合法性,也往往最终依赖于当事国的承认。如果全民公决结果是同意进行领土分离,而当事国又承认全民公决的合法性,则其实质是母国的主权让渡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说的主权让渡与欧盟成员国对欧盟的主权让渡不同。后者指的是主权让渡是指主权国家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将国家的部分主权权力转让给他国或国际组织行使的一种主权行使方式。⑥而本文主张将主权让渡理论扩展到全民公决的问题上,所说的“主权让渡”,是指母国将分离地的主权完全地交给分离国。其中有两点主要差别:一是让渡的对象由国际组织变成分离地;二是让渡的主权是完全性的,而不是部分的。
再次,主权让渡理论不仅本身着眼于国家主权问题,而且也能体现公民集体意志,因为主权让渡理论的依据是相对主权理论。相对主权论认为国家主权受国内宪法和国际法的双重限制,因而国家主权是有限的,这就兼顾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和人民集体意志的体现。由此看来,全民公决实现领土分离的合法路径的条件有两个:第一是当事国承认全民公决的合法性,第二个是全民公决的结果是支持领土分离。
四、结语
全民公决作为一个民主决策方式,本身并无不妥之处。但在国际社会中,尤其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时,其常常产生争议,这主要是因为对全民公决实现领土分离的合法路径不仅缺乏国际公法中的实体法的规范,其在法理上也亟需厘清。由于国家分离涉及尊重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的基本原则,而救济性分离理论和内部自决理论的法理过分关注某一地区弱势族群的权利,而忽视了国家的共同意志,回避了国家主权问题,其逻辑难以自洽。回答国家主权与领土变更的问题应着眼其本身,全民公决实现领土分离的合法路径不能离开当事国的承认。
[注释]
①邵津主编.国际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3.
②杨承甫.救济性分离权的追溯性思考——以“保障条款”的解释为研究进路[J].法制与社会,2016(13):10.
③王英津.有关“分离权”问题的法理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12):26.
④白桂梅.论内部与外部自决[J].法学研究,1997(3):116.
⑤林英峻.国家主权理论的新变化[D].山东大学,2008.
⑥高凛.从欧洲一体化评述国家主权让渡理论[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6):96.
[1]邵津.国际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3.
[2]杨承甫.救济性分离权的追溯性思考——以“保障条款”的解释为研究进路[J].法制与社会,2016(13):10-12.
[3]王英津.有关“分离权”问题的法理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12):19-37+155-156.
[4]白桂梅.论内部与外部自决[J].法学研究,1997(03):104-115.
[5]林英峻.国家主权理论的新变化[D].山东大学,2008.
[6]高凛.从欧洲一体化评述国家主权让渡理论[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06):91-98.
D99
A
2095-4379-(2017)30-01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