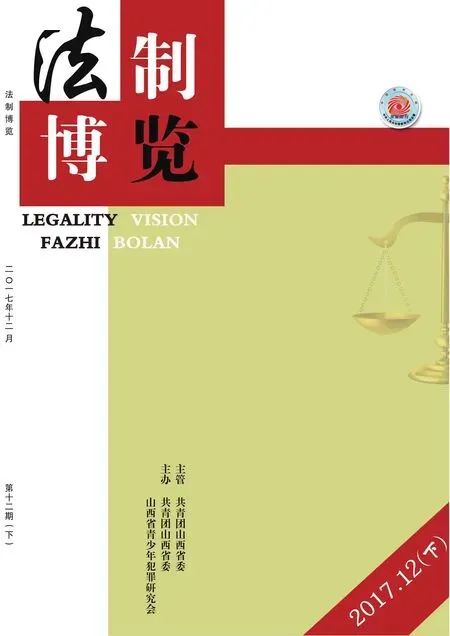《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与中国的选择
叶雅冰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与中国的选择
叶雅冰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对于保护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然而,联合国粮农机构发布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却让发达国家踌躇,发展中国家彷徨,包括我国在内的英美日等大国仍持观望态度。基于条约在农民权益保护、粮农植物遗传资源流通、分享粮农遗传资源所生惠益等方面的相关规定,面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特性和法制现状,综合而言,我国加入条约,利大于弊。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农民权;资源流通;中国选择
在世代农民的农耕实践和专业育种者的科学培育下,作为众人劳动与智慧的结晶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对于保护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显然,联合国粮农组织很早就意识到了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历经七年的修订,2001年11月3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第31届大会正式通过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一反过去无法律约束力的象征性条约管束,这份新条约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
截至2016年1月26目,条约的缔约方已达137个国家,条约覆盖的物种已包括水稻、玉米、大麦、谷类、高粱等3508个具有抗性的新品种,16个新社区种子库建成,1120个作物品种得以保存,受益者达13万人次,其中农民11.4万人。[1]
然而,我国仍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持观望态度。基于条约内容和发展前景,结合我国的主要顾虑,综合而言,我国加入条约利大于弊。
一、农民权益保护问题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第5/89号决议》,农民权是指源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农民在保存、改良和取得遗传资源特别是原产地中心和多样性中心的遗传资源中所做出的贡献被保护的权利。[2]
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农民权既不属于单一农民个人,也不属于农民集体。它被联合国授予国际社会,由国际社会作为当前及未来世代农民的托管人对农民的权利加以保护,并通过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基金加以实施。
诚然,这种由国际社会居高临下远距离操作的保护方式,极易导致保护主体模糊化,使保护措施难以具体化,不具针对性。同时,国际社会也很难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对各国农民的权利加以干涉,使得保护初衷难以实现。
此外,大量发达国家的专业育种者,在发展中国家农民通过世代农耕获得的良种培育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培育出转基因、抗病虫种子。他们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为其研制的新种子获得专利保护,再将这些升级后的种子高价回销给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专业育种者的知识产权和非专业育种者基于多年劳作的经验所应享有的权利难以平衡。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恰恰有效解决了农民权保护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它通过将农民权主体国家化和农民权内容具体化的方式,在肯定知识产权制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农民的权利。
首先,条约将农民权的实现从国际层面转入国家层面。条约规定各缔约国有保护农民权的义务,要求各缔约国切实建立法律框架,在本国法上强调并保护农民权利。同时,条约还通过“根据其需要和重点”、“酌情”、“依其国家法律”等限制性修饰短语,强调缔约国的自主选择权和与他国的协商权[2],使得农民权的保护因国而异,使得各缔约国都可以针对自身的实际国情对农民权进行有效的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保护。因此,在条约的保护下,农民权不再是国际社会手中攥着的虚权,而是真正被写进各缔约国本国法的实权。
其次,条约将农民权具体化为三个层面的权利,分别是:传统知识的保护,参与分享惠益的权利和参与决策的权利。
在传统知识保护方面,条约建立了特殊权利制度,即通过控制他人对传统知识的使用,对农民权加以积极保护和不当利用制度,即通过阻止他人对传统知识的使用,对农民权进行消极保护。在两种制度的保护下,条约最大程度地在承认现有知识产权体制的基础上,实现农民与专业育种者利益的再平衡。
在参与分享惠益的权利和参与决策的权利方面,条约9.2条(b)款和(c)款明确表示要保护农民“公平参与分享因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而产生的利益的权利”和“参与在国家一级就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有关事项决策的权利”。条约将农民作为实行主体,缔约国作为第三方,通过将农民的权利具体化的方式,对农民权进行保护,完美符合各国的保护诉求。
二、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流通问题
与其他遗传资源相比,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具有显著的独特性。首先,它属于人造的生物多样性形式,需要通过持续的人工保存和特殊养护才能保留;其次,它的散布具有集中性,多集中于“栽培植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原产地和多样性中心”,使得针对原生境的保护尤为关键[3];其三,国家间对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不论是拥有丰富专业育种者资源,掌握新基因种存的发达国家,还是在世代农民的辛勤劳作下拥有丰富农地原生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对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无障碍稳定共享,都有极高的需求。
基于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特殊性,能否实现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无障碍稳定流通,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正有效地解决了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流通问题。
诚然,在条约订立后,2010年10月30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条约第10届缔约国会议通过的《名古屋议定书》也对生物遗传资源利用及其利益分配问题加以约束,我国也于2016年加入成为缔约国。《名古屋议定书》确立的双边路径虽然对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流通和保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也存在诸如谈判成本过高,谈判地位不对等,资源共享无法源源不断[4],后续转让无法实现等问题。建立多边体制,确立缔约国向其他缔约国提供获取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义务,刻不容缓。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作为一份基于各国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重要性一致高度认同的多边协议,将保证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稳定与无障碍流通作为各缔约国最主要的义务加以强调。
根据条约规定,各缔约方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鼓励在其管辖下持有条约附件一所列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自然人和法人将这些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纳入多边系统;同时,条约的管理机构会在两年内对未将以上资源纳入边系统的机构采取必要措施。条约强调各缔约国“应迅速提供获取机会,无需跟踪单份收集品,并应无偿提供;如收取费用,则不得超过所涉及的最低成本”。
无疑,条约在尊重知识产权和各国主权的基础上为各缔约国提供了有利于其粮农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副完美图景,并通过《材料转让协定》有效解决后续转让的问题。
三、分享粮农遗传资源所生惠益的问题
虽然条约所建立的惠益体制在实际操作中惠益尚微,但就其构成而言,条约的惠益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已趋完善。
条约的惠益体制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信息交流、技术获取和转让、能力建设与分享商业化的货币惠益。
在信息交流方面,条约虽然对信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加以明确的肯定,但也通过“这些信息凡非机密性的均应提供,但须遵循适用的法律并依国家能力而定”,加以限定,使得条约在实践中更宜被各缔约国所接受。在技术获取和转让方面,条约按照承认并符合充分、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条件进行,提供了建立课题组或建立稳定的商业合作伙伴的方式,推进技术获取和转让的稳定性,切实保护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利益。在能力建设方面,条约提出了制订或加强科技教育和培训计划,开发并加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的设施,与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的机构合作,在这些国家开展科学研究,并在所需要的领域发展这类研究的能力等切实方案。虽均属于建议性条款,无强制性和法律约束力,但也可见条约良好的发展预期。
四、中国的选择
我国作为粮农遗传资源大国,基于我国对粮农遗传资源的保护现状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未来发展趋向,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对我国而言,利大于弊。
首先,从我国对粮农遗传资源的保护现状而言,我国目前尚无一部统一的法律对植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加以规制,只是任相关制度散见于各单行法、行政法规和规章中;与分散的立法状况相应,我国也无单一机构集中行使对于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职权。此外,我国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专利保护制度,但就目前运行现状而言,授权品种的所有者以公共科研教学单位为主,品种权转化利用率低,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单薄,植物新品种流失严重。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窄,申请程序复杂,审查速度缓慢,维权困难。
其次,就条约本身而言,条约从根本上肯定了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稳定与无障碍流通的根本目标与农民权益的保护,根据如上三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对于条约的未来发展与预期前景均可持一个乐观态度。此外,条约也肯定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帮助,并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个世界范围的粮农资源共享库。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条约尚有些许不足和模糊之处,但加入条约,也是对我国国际话语权的进一步确立,更有利于维护我国的权益。综上,建议我国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1]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介绍近期工作进展[J].世界农业,2016-03-10:193.
[2]张小勇.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保障——<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评析[J].法商研究,2009(1):14.
[3]于燕波,王群亮,Shelagh Kell,Nigel Maxted,Brian Ford-Lloyd,魏伟,康定明,马克平.中国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及其保护对策[J].生物多样性,2013,21(6):750.
[4]徐靖,银森录,李俊生.<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与<名古屋议定书>比较研究[J].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3,14(6):1099.
D922.6
A
2095-4379-(2017)36-0059-02
叶雅冰(1997-),女,浙江温州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2015级法学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国际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