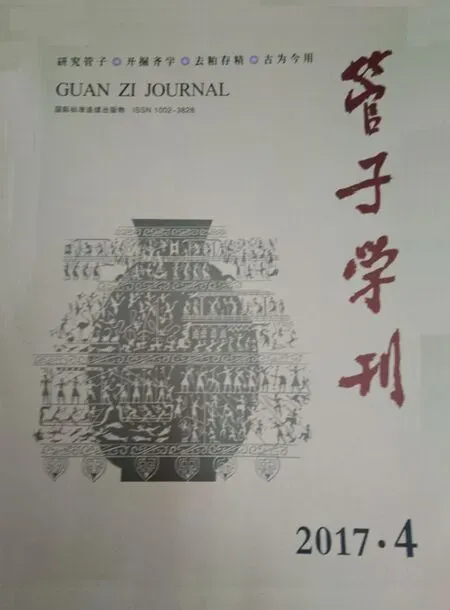浅议天下主义与华夏帝国的初成
史少秦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古今论坛
浅议天下主义与华夏帝国的初成
史少秦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每个时代都会面临建构并描述人类共同体的问题,鉴于先辈思想家已经使用“天下”的概念来描述他们视野所能触及的人类生存世界,后世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增量性诠释,使“天下体系”内容不断丰富,框架更为清晰,形成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理解中国的“天下体系”,必然要从其萌芽时代入手,探究“天下体系”同华夏政治共同体的初成之间的关系,才能彰显“天下体系”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历史意义。
天下主义;华夏帝国;宗法封建;王霸政治
现存与可考的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中,“天下”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也就是东周时期的文献之中,《尚书》《礼记》《周礼》《论语》《孟子》《老子》等文献中都有提到“天下”概念,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认为这一时期的天下观念主要有两种类型:古文经学系统中将天下理解为包含中国与夷狄在内的复合型政治社会(帝国),以及今文经学系统中将天下理解为统一语言圈、同一交通圈、同一文化圈所构成的九州(即中国)这样的单一政治社会;古文经学系统中的世界,是以天子统治的王城为世界中心,按照九州——四海(天下)——四荒——四极的顺序重叠展开,以及今文经学系统中将昆仑山作为世界中心,主张方五千里的天下在其东南①详见[日]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5-62页。此外,该书认为《礼记·王制》将领域方三千里的九州(即中国)作为天下;《尚书》今文经学将方五千里的九州(即中国)作为天下;《周礼》《尚书》古文经学则构想了由九州与四海(中国与夷狄)所组成的方万里的天下。。
在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系统中,天下都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天下不等于古人所理解和想象的世界全部。古文经学系统中,以天子所在王城为世界中心(这并不是地理意义的中心,而是文化意义的中心),通过文化的凝聚联合诸夏与夷狄在内而成九州(诸夏)而御四海(夷狄)的多元政治社会,然而四海之外仍有四荒,四极等“化外之地”,因此天下存在模糊边界,天下为世界的部分而非全部。今文经学系统中,划定了昆仑山为世界的地理中心,“天下”位于其东南,且明确了天下的疆域——方五千里,为同一文化与语言的单一政治社会,将夷狄划于天下之外,故而将“天下”限定于指称华夏帝国。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深刻一致性在于:都认定天下是有限性概念,存在有边界;都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主体和文明中心。两者的不同在于对于“天下”的边疆或周边的“夷狄”的认识。
观念必然兴起于问题历史逻辑发展的中端:向前它要回应问题的产生以及总结问题的前半段发展;向后它要预测问题的未来走向以及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天下”观念是对于西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共同体的体系建构与历史安置,一方面回应宗周(西周)政权的政治体系建构以及成周(东周)虚位政权下政治共同体的历史状况;另一方面预测成周后期诸国纷争的未来趋势以及探讨混乱政治局面解决的终极真理。前者进行了华夏政治共同体的理论建构,后者为华夏帝国的初步形成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基础。“天下”观念的有限性既是对西周政治权威一元性的描述,也是对后世华夏政权单一性的要求:号称“天下”的政权只能是单一的,具有排它性,这成为了“天下”体系的重要内容“大一统”论与“正统”论的滥觞。
“天下”观念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薄变厚的过程。作为“薄”的“天下”观念,是以华夏中心区(即政治控制与文化核心区,也可称之为“中国”)为中心的政治与文化控制和影响的同心环状结构。
华夏中心区是“天下”的核心,即“诸夏”或“中国”的所在,边疆区即所谓“夷狄”所在的地区,华夷可以互变,因此此地区同华夏中心区一起组成“天下”的基本区域;势力范围区属于“天下”的不稳定边界,而影响区仅为“天下”的影响力所触,不为天下控制力所及。“薄”的“天下”观念侧重“天下”的政治地理意涵。
作为“厚”的“天下”观念,是包括“霸道”论、“王道”论、“天命”论、“大一统”论、以及“正统”论等理论在内的政治理论体系,其中每一个政治概念的提出都伴随着政治历史的变化与对于“天下”体系的时代诠释。“厚”的“天下”观念关注“天下”的政治哲学建构。
“天下”观念体系兴起于西周末年,臻成于西汉初年,这一时段剧烈的政治历史变革成为孕育“天下”体系的肥沃土壤。探寻“天下”体系的观念源流需要回到先秦,对这一阶段的政治历史变革进行系统的考察。
一、从宗法封建到霸王政治
限于史料的缺失,商政权的精确边界已不可考,其势力范围大致在今河南地区(商的多个都城位于河南境内),殷(今河南安阳)在盘庚迁都之后成为商朝政权的政治中心,可以推断商直接控制的地区在殷周围,而像周等诸侯国基本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仅向商王表示臣服。《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1]1252“纣克东夷,而陨其身。”[1]1323从这两条材料记录了商纣王曾出师讨伐东夷①考虑到商政权是势力范围可能不及东夷地区,以及春秋笔法的修饰,“叛”理解为作乱为佳。,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或军队大伤元气,以至于牧野之战时以奴隶充兵源而导致灭亡。可以推断商朝时期势力范围不及东夷。
西周之时齐鲁两国负责周东方疆域的开拓:齐祖太公望就国伊始就开始了同莱夷之间的土地争夺战,到齐景公时代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齐国的疆域大大扩展,将莱夷(东夷之一支)的活动范围缩小到山东半岛的最东部;鲁祖周公平定殷地三监同淮夷(东夷之一支)的叛乱,兵锋东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后二年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奠定鲁国根基,并大大扩展了周的东部和南部边疆。
周灭商之后,并没有将政权中心设立在商都殷,而是在周成王之时,在周公领导下将殷人顽民(也就是商部落遗民)迁至雒邑,并在附近筑王城,迁周人来居住,作为周的陪都。并按置八个师(即殷八师)的军事力量,一方面来镇压殷遗民,一方面以此为基地,扩大周的版图并控制东方的诸侯。“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2]423周公东征为西周划定了基本疆域,大致东到山东半岛,北到今辽宁附近,南到淮水和汉水流域,西到西安附近,基本形成以宗周(丰、镐)为扇心,面向东方展开的扇形形状。这个扇形区域形成西周初年“天下”观念的基本政治地理范围,即华夏中心区之所在。西周广大的东部疆域由雒邑为控制中心,而周天子开中国历史中天子戍边的先河,其所在的丰和镐京成为西部边境的守卫重镇,这为西周的政治安全埋下了隐患,周幽王时期的犬戎之乱伏笔于此。丰、镐为周天子所在的王都,因此称之为“宗周”,意即各诸侯国都要以周作为宗主,由周六师卫戍;雒邑为周成王时所修筑的东方陪都,西周东方领土的政治中心,安置着象征“天下”的九鼎,也是西周金文所指“中国”的所在地,有殷八师驻扎。西周分建之诸侯主要有三个类型:宗法封建,指周天子同族的姬姓诸侯国,例如鲁国、卫国;军功封建,指凭借伐商军功而受封,例如齐国、纪国;遗贵封建,指前朝遗贵,主要指殷商后人,以及皇帝、帝尧等先王后人,例如宋国、陈国等。宗法封建诸侯国占压倒性的多数,是西周“以藩屏周”策略的具体实施。宗法制在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构政治关系,天下诸侯以周王室为天下之大宗,各诸侯国内以世子为大宗,家族以嫡长子为大宗,层层形成树状结构,进而形成西周的家国天下体系建构。西周政权基本上是统而不治:周天子的直接控制区域集中在宗周与成周这两座王城所在京畿,各诸侯国各自行使其行政权,而奉周天子权威的一统。李峰认为,天子戍边的军事紧张以及对于淮夷军事集团的镇压逐渐蚕食着周天子的军事力量,加之周天子“恩宠换忠诚”的土地赠与政策,以及封建制度下诸侯高度自治权的制度性缺陷,使得西周王室政权在内忧外患下陷入持续衰落的困境①详见李峰:《西周的灭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2-163页。。周最终发展到春秋战国的乱世,天下进入分裂的格局。“天下”的疆域虽已分裂,“天下”的最高权威仍然保持独一且排他,由“天命”唯一的继承者天子来代表,周公提出的“天命合法性”的政治伦理架构依然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天命且唯一,天下最高权威且唯一,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且唯一,成为“天下一体”的政治哲学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宗法封建保留了天下一统的种子:“天下”最高权威不可分裂与“天下”实际疆域分崩离析之间的张力成为各诸侯国追求天下一统的动力。
平王迁洛,放弃宗周而坚守成周政治中心,成为“中国”观念的现实投射。“国”在春秋时期代指诸侯的都城,也即封地之所在,天子的所在的“国”(王城)在春秋时期被认为是居于中心和中央,因此被称之为中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3]413然而,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已经不再具有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军事力量,而同一时代的东方诸侯国正在渐渐崛起,政治中心力量的衰落和诸夏力量的强大改变着东周政治共同体的历史面貌。缺乏政治动员能力和足够军事力量的周王室对外不能够担负起对于疆域之外蛮夷政权的抵御,对内部不能够以超越性权威来解决诸侯之间的纷争,东周王室政权难以承继西周祖先留下来的“天下”政局,制度性崩溃和兼并性战争如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复回。“天下”面临体系的重构与制度的重建,“霸权”和“王权”是这一过程中有益的尝试。
争取霸权的建立是春秋时期主要强大诸侯国的政治生活。
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4]176。
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5]153。
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②这里的五霸是指昆吾氏(夏)、大彭氏(殷)、豕韦氏(殷)、齐桓公、晋文公。[6]61-62。
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故圣人与之。非明王之张法。霸犹迫也,把也,迫胁诸侯,把持王政[6]62-63。
战国及其秦汉初年的思想家们将霸主置于天子之下,诸侯之上,行“方伯”大权,代行天子的部分行政职能。强者必尊其位,霸权的争夺是西周弱中央政权状态发展的必然,王权之下身份地位平等的诸侯国单位之间实力的不均衡变化导致了彼此之间关系的变化,具有较强实力的诸侯寻求建构新秩序以结束弱政府状态下的旧有存在,霸权③霸权来源于方伯,西周先祖周文王领“西伯”之尊,统帅殷商西部各诸侯国,春秋之时这一职官设置成为虚衔,惟存荣誉。即是一种寻找新政治秩序建构的积极尝试。然而春秋之时的霸主亦不具备足够的力量而实现对其他诸侯国的吞并,进而一统天下,仅能在尊奉周天子为最高统治者的前提下,以诸邦国领导者的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即“友诸侯者霸”;战国之时追求雄图霸业的王国则以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而且各强国已经具备相应的国家力量,所以统一天下被认为是王者之治,即“臣诸侯者王”。
对抗四面夷狄的侵扰和调解各诸侯之间的纷争是霸主代行周天子所行使的职权。春秋首霸齐桓公以“尊王攘夷”而著称,自行自发帮助“诸夏”盟友抵御边境夷狄部落政权的侵扰,而周王室已然没有力量护卫边疆;周王室亦无力处理诸侯国的现实政治纷争,春秋时期兼并战争不断,灭国无数,霸主也只能着眼于协调主要诸侯之间的矛盾,无法做到对所有诸侯的完全政治掌控。“尊王攘夷”以“华夷之辨”作为政治哲学基础,华夷之辨着眼于“诸夏”与“夷狄”的分离和融合,明确区分华夏与夷狄差异性的同时,又认为两者存在有融合的基础,即正方向上的“以夏变夷”和负方向上的“以夷变夏”,华夷之辨通过构建华夏文化的对立面——“蛮族”来实现华夏文化的一体性和诸夏身份认同的包容性。各诸侯国,尤其是同宗同姓诸侯国之间血缘联系的日益疏离,促成了宗法分封体制的没落,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周的统治基础,新的政治统治秩序的建立成为政治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在此之前需经历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尝试,这将经历一个动荡的过程。
战国时代同春秋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各强势诸侯国已经不再谋求霸权的建立,而是去追求整个天下王权的实现,各诸侯强国纷纷称王,周王室丧失了最后一丝权威:“一匡天下”的抱负由“一统天下”的雄心所代替。《孟子》中有这样的记载:“(梁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孟子)对曰:‘定于一。’”[4]71战国中期的孟子系统地建构了王道政治哲学,宣扬“仁政”“性善”“民本”等观念,基本上对于霸道予以否定,将解决天下定于一的问题寄托在王道身上,并身体力行在各个诸侯国宣传其王道思想。霸道给予周王以形式上的尊敬,在名分上霸者居于周王之下;王道彰显诸侯统一乱世的决心,预判了战国时代的最终走向。战国后期的荀子细致总结了王霸与礼法,“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5]470。在荀子这里,虽然王道仍优于霸道,但王与霸之间的差别已较孟子为少,都被视为王统治天下的策略。战国时代新政治形势下,“霸主”政治已经随着周王室的名亡实亡①战国之时周王室的地位完全下降为一般诸侯小国。而成为历史,王道一统成为强势诸侯国追求的未来。孟子的王道更具理想性,荀子的王道更具现实性,荀子学生韩非、李斯等法家中人,更是在实践层面促成了秦王朝将“天下”真正在现实中“定于一”。伟大的思想是站在过去的肩膀上看向未来,思想诞生于旧制度并摧毁旧制度。
秦国最终完成了“天下”在权威和实际疆域上的统一,将破碎的诸夏地区——华夏文明核心圈重新凝结于一体。
二、周秦之变与“天下”秩序的重构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宗法分封的终结。法家入主秦国政权之后,实行军功授勋而强力镇压了国内的贵族势力,瓦解了秦国境内的血亲分封体系;秦始皇血腥灭亡东方六国,翦灭了分封贵族的有生力量,破坏了六国遗老反扑的最后希望。分封建制在秦朝彻底奔溃,郡县秩序兴起并成为天下体系的核心治理秩序。“王道”政治是何未来?分裂危机何以结束?建构国家与重构天下成为秦需要面对的“现代性”问题,在统一权威的同时秦也在进行诸夏疆域统治权的归一,周之政令不出王畿,管理“天下”的政治历史新局需要由秦来开创。秦所要建构“国家”,基本的疆域是周之时诸夏共同体的集合,即秦整合诸夏为一体,在此之上秦扩土充疆,奠基华夏帝国的最初,也是最为核心的疆域,奠定“天下”体系的核心范围,“天下”之视域以此向外扩展。“天下”定于一,帝王臣诸侯,法统行郡县,秦王朝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王道”政治理想,然而其成就方式(血腥吞并和残酷统治)和结果(二世而亡)为后世所诟病,以“暴秦”称之。新秩序的建构无法完全避免失败的洗礼,成熟的制度总是经由不断损益磨砺而成,很明显,这是一次不成功但有益的尝试。周时代“天下”的秩序随着周的终结而终结,因此“天下”秩序在秦开始重构。
两周“天下”的政治关切是“一统”,秦汉之后“天下”的政治关切是“统一”。“一统”在“天下”范围内尊奉周王室权威的至上无二,以周统为尊而实现文化上的认同:政权上尊“中国”②西周之时诸侯的都城称之为“国”,天子的“国”称之为王城,诸侯拱卫处于“天下”中心的天子所在的王城,所以天子所在的王畿也被称为“中国”,这是狭义意义上的中国;广义的“中国”是指周天子为中心的诸夏政治共同体,位居中土,四面临夷,故称中国。,文化上辨“华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312周天子在权威上至上独尊,名义上享有天下的全部土地,然而周天子的政令却难越王畿,诸侯各自于其国行使自治,李峰考证西周厉王时期周天子对于非王畿土地的处理直接导致了“国人暴动”,厉王出奔③详见李峰:《西周的灭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3-156页。。周朝“一统”尊权威与文化,周天子得“天下”之名,各诸侯得“天下”之实。“华夷之辨”以树立文化对立面的方式促成“诸夏”集团的内部集体认同,华夷的区分更多强调的是文化的区异而非种族的不同,吴楚祖荆蛮,终为中土以夏称;“华夷可变”论建构了“天下”的模糊边界,中土政治共同体可以认同蛮夷入夏,成为“诸夏”一员,而诸夏之众习用文化风俗,也就成为夷狄。周“天下”以诸夏共同体为中心,以夷狄为“模糊边界”,夷狄地区之外,为“天下”的视野尽头,以幻想存置而不做现实考虑。
秦汉“统一”的内容除了至高权威的至上无二外,还包括政权、军事力量、社会制度、文化和疆域土地的统而为一,即由一个中央政权来总领“天下”,形成政治身份上的单一认同,变诸夏政治共同体为单一华夏政治体:共有的“天下”发展为集权的“天下”。周尊“一统”,先有“天下”的“一”,即文化的华夏认同,而后由周王室来承此“统”;秦汉的“统一”则是建立在“天下”政权与版图的多元化历史条件上,一元文化认同下多元政权的并立是秦汉“统一”中破碎的“一”,秦汉正是要“统”而为“一”。周时代“天下”主义中文化的华夏认同留存了华夏帝国政权与疆域统一的种子:这是强有力的文化向心力。秦汉“天下”体系的重新建构是华夏帝国初步建成的政治与文化根基,华夏政权得以绵延至今,实现整体性历史延续亦有赖于此。
政治思想与政治历史的关系缠绵悱恻,政治思想在回应反思政治历史的同时又希冀引领政治历史的发展方向,然而政治思想在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命运:既不为其提出者所架构的体系所束缚,也不可能全然按照自身的逻辑而展开,因为它在未来必然要同政治现实发生碰撞。
《周礼》《礼记》《仪礼》中所记载的制度是周制度的理想化设计,现存史料和考古材料都不能证明三礼中的制度设计是政治历史现实,《礼记·礼运》篇对于“大同”的设想是周“一统”思想的理想极致,孔子提倡亲亲尊尊,所维护的一统是周天子权威的一统,周天子的意义在于作为天下诸侯的领导者而非统治者,因此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7]331
孟子之时已经主张以新的王而不是周天子来统一天下,原因在于周王室已经沦为普通诸侯国而权威丧尽,不再居于领导地位,孟子承认周王室“一统”局面已然崩溃,天下混乱分裂,期待王者规制动荡。荀子时代,统一已成为战国乱世的共同诉求,荀子礼法并重而将王霸相统一,比及孟子“王道”以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荀子“王霸统一”的政治策略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孟子绘制蓝图,荀子寻求实策,荀门弟子韩非、李斯兼申不害、慎到、商鞅法家之术以影响和塑造秦政治策略,促成“天下”统一局面的政治现实最终诞生。无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先秦儒学都没能跳出宗法分封的建国模式制度窠臼,对于先圣言行和经学文本的过分推崇,限制了视野,造成在回应战国“现代性”问题时总是希冀从先圣以及经书中去寻找解法;法家对于制度的建构着眼于政治现实而非远古理想,并非远古理想不可取,而问题在于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面对周秦之际建构国家与建构天下的双重政治形势,法家无疑更具优势。然而政治合法性建立的策略并不能成为政治合法性延续的依靠,单纯依赖法家的政策措施无法巩固统治的道德伦理基础。
秦亡于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不健全,新的政治道德伦理基础尚未建构,两周宗法封建的残余影响就不能完全肃清,天下之人以暴秦称,缺乏对秦帝国的政治认同和道德伦理认同。秦的政治合法性建构不是来自“革命”,东周王室政权衰弱而非残暴;也非来源于“禅让”,东周王室早已失去其“天下”之宗的权威,“天命”早已不在。秦建构国家的同时重构天下,重构天下的同时需要论证新的“天命”所降,然而尚法传统的秦王朝更重现实国家力量建设而冷落道德文化,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的任务到汉时方完成。《史记》中记载:“秦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离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将兵出塞攻梁,梁破则周危矣。”[8]111司马迁将秦得以顺利统一天下视为得“天命”之助,即“天命”在战国末年已降临赢秦。强大的军事力量暂时遮掩了政治道德伦理的虚弱,秦军兵锋所指,扫六合而一宇内,薄海东南,收编东夷南蛮于中土;筑墙东北,实体化了同北方游牧民族的边界;西线边陲已临大漠高原,达致当时国力人力所能及之顶点。统一时代的华夷之辨被国内民族和地域融合的形势所取代,有西戎背景的赢秦没有中土诸侯强烈的诸夏情结;对于“客卿”的重视使得赢秦虽偏居西陲,仍能得到中土丰富和先进的政治资源。秦国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其帝国气质在始皇之前已然孕育。长城的完善划定了秦的北部边界,防御意味着固守,秦汉及之后的华夷问题集中在了华夏农耕帝国与北方游牧政权对于北方领土的争夺之上,而华夏帝国境内的地方少数民族则不包括在“夷”的政治论域之内,“华夷之辨”存在于对立政权的相互争夺中,关切的是政治正当性与政治合法性的构建。周以权威凝聚天下,秦以郡县统治天下,对全部疆域实现了划一的直接统治,值得注意的是秦开拓了华夏帝国疆域的基本版图,成为之后华夏诸政权的统治核心,并以此为基础向外扩张,此为华夏帝国的“根本”,后世所谓收复“故土”,还我“山河”即指此片地域,此片地域属于“天下”体系中所不可更易的地区。之后华夏世界历经分裂与统一,也多是围绕这一地区的政治争夺,保有中土华夏世界旧地被视为捍卫祖先留下的基业,完成统一者为人所称颂,裂疆割土以献夷狄者成为千古罪人。
秦对于“天下”体系的重构和华夏帝国疆域与制度的建构之贡献可称伟大,然而却由于自身政治合法性建构的缺陷与政权纯粹法家化统治的失败尝试而迅速灭亡,留下的经验教训成为后世华夏帝国统治者的宝贵遗产。汉朝天命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秦暴政之上,以儒家思想弥补政权道德伦理合法性基础,以“大一统”予宗法封建以最后一击。汉武帝之时,华夏帝国初步形成。
三、汉承秦制与华夏帝国的初成
宗法分封虽已崩溃,但惯性仍存。项羽灭亡秦朝之后,佯尊楚怀王为“义帝”而自称西楚霸王,以“天下霸主”的实际政治身份促成了“天下”的“二次分封”,除确立六国遗贵的身份外,还分封灭秦将领与亡秦降将。楚汉战争之前的军功分封和遗贵分封是周宗法分封的残余影响,项羽军功集团和六国遗贵对于国家构建的模式仍停留在分封建制制度之上,暴秦亡国与桀纣亡国不存在大的区别,“革命”之后必然要将革命果实进行瓜分。汤武率领诸邦诸侯一起讨伐不义,故而汤武之“天下”乃公有之天下,非汤武一人之“天下”,汤武行领导天下之权,众人掌各邦国政治之实;而今项羽灭亡暴秦也非一己之功,赖得各支军事力量之合力:(项羽)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8]217。项羽亦不具备对于其他军事力量的压倒性优势,仅能凭“霸主”之位而胁迫傀儡最高权威楚怀王以领导众人,因此“二次分封”也乃形势使然,项羽楚国遗贵的身份是其对于分封建国制度有更多的政治认同的原因所在,“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8]217浓烈的乡土观念和贵族对于荣耀的追求造成了项羽的短视,楚汉战争之前的项羽难察其对于“天下”的雄心。“二次分封”只是对秦亡后破碎国家的简单归置,原本有希望统一山河的西楚政权却偏居一隅享受秦亡革命果实之一角。相比之下,刘汉政权正在一步步实施着恢复秦时河山的计划,刘汉政权的“天下”视野在这个乱世中显得独一无二:六国遗贵集团热衷于故土的恢复,没有野心也没有力量去构思天下的蓝图;军功分封集团要么不具实权,要么只存裂土分封之智,乏有“天下”之观念。
起于贫微的刘汉政治集团不会同情贵族政权及其政治制度,汉家天下的建立是现存可靠史料中第一次以贫民政治集团最终建立王朝,统一天下,成汤、周武、以致秦皇都是以高级贵族身份得享大宝,刘汉比嬴秦同宗法封建有更为彻底的身份决裂,因此以宗法分封为基础的古典贵族政治彻底亡于天汉王朝。政治历史在旧时代的彻底落幕中迎来新时代的曙光。
黄老思想与兵家谋略是汉政权最终统一天下的理论基础,秦暴政是汉承受天命的政治合法性之源,汉朝继续着秦在新“天下”秩序中的国家建构,并提供了新“天下”体系的伦理框架———“大一统”,促成了以“天下”为基本视域和论域的华夏帝国的初步形成。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9]1。“大”作重视、尊崇讲,一统则指天下总系于一,总摄于一。《春秋公羊传》是“大一统”思想的理论之源,将“王正月”解读为孔子面对春秋之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僭礼,陪臣执国命,正朔分行,战乱不断的政治现实,强调以“王正月”来统一正朔(历法),“大一统”来重尊周天子的“一统”,行王道政治于天下。“尊王攘夷”是《春秋公羊传》的另一个核心思想,通过区分华夷,论证了华夏一统的正当性。诸夏统一于周天子而成“天下”,天下的领域包括“四国多方”,天下的统治核心所在“宗周”亦成为“中国”,乃周天子王城之所在,诸夏是“天下”的主要区域,四国多方处于“天下”的不稳定边疆,多方不必属于华夏国家。西汉的“大一统”问题已经超越春秋,由“文一统而实不一统”发展为“文一统而实一统”,因此,“尊王攘夷”亦发展为单纯的华夷之辨。“大一统”的西汉关切集中在疆域复土秦时规模与政权收归中央集权:前者解决的是统一“天下”的问题;后者处理的是封建制的残余。“尊王攘夷”在西周的现实诉求成为农耕帝国同北方游牧政权对于领土的正当性争夺:“尊王”由于中央集权的实现而不再提及,攘夷成为华夏帝国同游牧部落①汉代主要是北方匈奴游牧政权。的外交理论基础。汉帝国以黄老之术建国并于高祖、文景二帝之时为主要统治思想,是出于当时孱弱的国力考虑,思想的兴起必然有其时代的诉求,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在国力昌盛的汉武帝时繁荣并非现象性问题那么简单。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10]2523颜师古注解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10]2523“一统”与“统一”在汉初之时概念含义已经相互包含融合。董仲舒所倡“大一统”问题不只是建国的问题,其深远诉求在于重构天下。董仲舒政治哲学的主体是“天”,“一统”乃天地古今的常经通义,因此国家的建构也要依循此“天道”,实行“一统”,不只是在政权与思想上,而且在文化上也要“一统”。前者迎合汉帝国统一天下的大势,以及为文景二帝到汉武帝一直实行的削藩政策提供政治哲学基础;后者同汉武帝在认识上达成了共识,赢秦法术成就了秦朝也葬送了秦朝,黄老思想只是蓄势时期的产物而不能满足大一统帝国的天下雄心,儒家思想更有助于庞大帝国的建设、稳定与存续,故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建构国家的同时,先秦法家借助秦朝以雷霆之力实现了新“天下”体系的版图基础,黄老之术奠定了新“天下”体系主体帝国的强盛之基,儒家在此基础之上完成了新“天下”体系的基本建构,促成了绵延至今的华夏帝国的早期形态。
秦皇开始的建构国家的工程起于将周时松散的多元政权共同体向单一集权的帝国形态规制,周时周王室政令不出王畿,以王城内政治事务为施政对象,各诸侯各自于自己封地行使政权,周王室起到的是政治垂范的作用。各诸侯在周礼的规定下以次级政权单位仿照周王室的政权结构来建构自己的封地政权,侯国同王畿在政治地位上有等级差别,但在实际政治现实中都为某特定区域的单一政权,周王室只是在名义上享有“天下”,实际上“天下”掌有在不同的封地诸侯手中。周王室的“国家经验”可能并不比秦皇从其王国前辈处所积累的要高明,也就是说,面对疆域广阔的帝国形态的新型国家,秦皇并没有已经成熟而参照的政治经验可循。推行已经在秦国普及的郡县制于全国范围,以及在郡县制基础之上收归地方权力于中央而集权,是秦皇建构国家的有益尝试。这两项举措也是“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在现实层面的实现。然而秦还未曾巩固便二世而亡,建国之大业也承接到汉高祖之手,然而由于分封制度的惯性和汉初中央集权力量的弱小,郡县制并未如秦朝实施的那么彻底而兼以分封制,此可认为是分封制的惯性所致,而中央集权的力量在加强,中央集权与分封制的尖锐矛盾在文景二帝之时愈演愈烈,最终而起“七国之乱”。刘汉建基之初,限于形势与历史惯性不得不分封诸多异姓诸侯王,而在基业稳定之后又大肆削藩以维护中央集权;然而同时却错将未行分封制而使国危之时无人勤王作为秦灭的原因之一,进而又大肆分封同姓诸侯。然而灭亡夏商者亦是夏商周之诸侯。
刘姓分封就国者误将此时之分封比于西周之分封,“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8]2148欲与中央政权共享“天下”而裂土封疆。革命的果实面临瓜分的危机,郡县制与分封制具有制度的天然矛盾性,中央集权也必不能包容地方离心,帝国的统治者必将不能容忍任何割裂“天下”权力的挑衅。文景行黄老积蓄力量,汉武帝终以“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决了这一制度性难题。分封制在实体层面的消灭是秦汉“建国”大业的最终完成,华夏帝国实现了在政权、疆域、文化上的“大一统”,华夏中土成为铁板一块,以帝国的形态完成了“天下”体系中心区的构筑。
此刻,汉武帝基本完成建构国家与重构“天下”的双重工程,绵延至今的华夏帝国形态初步形成。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4.[3]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陈立.白虎通义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4.
[7]朱彬.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9]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D092
A
1002-3828(2017)04-0061-07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4.10
2017-09-28
史少秦(1988—),男,山西阳泉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政治哲学。
张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