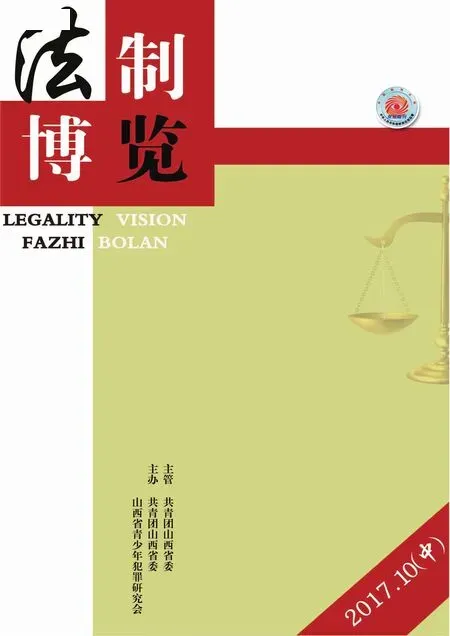“一带一路”框架下投资争端多边解决机制新思路
张天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2
“一带一路”框架下投资争端多边解决机制新思路
张天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本质上是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利益的博弈,均以期获得对己方有利的裁判结果,各种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国际投资法领域若存在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不仅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公开透明高效的利益保障机制,也可以有效化解一些发展中国家勉为其难地将争端解决诉诸国际仲裁的困局。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多边解决机制
关于外国投资者与国家之间投资争端的解决方式,主要分为政治实力导向型或法律规则导向型(power-oriented or rule-oriented)。前者又称为外交解决方式,包括谈判、咨商及外交保护等;后者又称为法律解决方式,包括寻求东道国国内司法救济途径以及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纵观国际之间较为通行的双边或区域性投资协议,通常兼具有诉诸外交或政治渠道(如咨商)与法律途径(如仲裁)的争端解决方式,即当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发生投资争端后,应首先寻求当地救济,当当地救济失败或称卡尔沃主义枯竭后,外国投资者再向母国寻求外交保护或诉诸国际仲裁。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外国投资者采取传统的救济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不理想的。随着“一带一路”活动推广,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持续增长及中国对外双边投资协定(BIT)数量的增加和仲裁范围的逐步扩大,未来将有更多的机会被诉至ICSID等国际仲裁争端解决机制,但ICSID规则制定者的出发点、ICSID在程序正义、透明度、自由裁量权、个案一致性、仲裁员资格以及仲裁上诉机制缺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促使国际社会需要积极探索新的“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一、从双边投资协定看中国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演变
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BIT构成全球双边投资条约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对外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的发展趋势看,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谨慎保守到逐步放权,对于ICSID等国际仲裁机制逐步接受的过程。
(一)中国BIT争端解决机制现状
通观中国不同时期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其中的争端解决机制不尽相同,比较庞杂。归纳起来,其差异主要有:
1.有关当地救济的规定不一。目前,中国对外签订的BIT对当地救济的规定主要有如下几种:(1)没有规定磋商的要求,投资争端可直接提交于国际仲裁;(2)争议无法通过双边协商解决的,外国投资者可以提请国际仲裁,不需要事先寻求当地救济;(3)外国投资者在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之前,可选择东道国的当地救济;(4)外国投资者可选择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和国际仲裁。而就岔路条款而言,有些BIT没有作出规定;一些规则允许争议由东道国法院或仲裁管辖,但选择是终局的;有些规定已诉诸东道国法院的,可依东道国法律撤回诉讼并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
2.有关同意仲裁的规则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1)“可以”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从字面上看,只是“意向性”地同意;(2)“应当”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从字面上看,属于“强制性”同意;(3)基于双方同意,投资者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有权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这属于契约型同意。
3.关于仲裁管辖范围的规定不同:(1)早期BIT规定可以提交国际仲裁的事项仅限于征收补偿金额相关争议;(2)有些BIT规定可仲裁事项范围不仅仅是征收补偿额争议,也包括“与本协议有关的其他问题的争端”,或者是征收补偿额之外的其他争端事项;(3)后来一些BIT规定可以提交国际仲裁的可以是因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或任何法律纠纷;(4)另一些BIT则将可仲裁事项为“因履行本协议项下与投资有关的义务所产生的争端”。
4.有关仲裁类型的规定各异:(1)有的规定特设临时仲裁机构;(2)有的明确为ICSID仲裁;(3)有的规定可选择特定仲裁机构或仲裁规则,如ICSID仲裁机制或联合国贸发会仲裁规则;(4)有的规定限定为反向选择,即除非双方明确同意设定特设仲裁庭,否则应提交ICSID;(5)有的规定不同争议事项可提交不同仲裁机构,如关于征收补偿额的争议可提交ICSID,其他争议事项则可采取特设仲裁机制的方式解决;(6)有的则泛泛地规定争议可提交国际仲裁。
5.有关提交仲裁的时间要求规定不一:有规定3个月的;有规定5个月的;有规定6个月的;还有规定9个月的。
(二)中国对ICSID争端解决机制态度及挑战
中国于1992年2月签署华盛顿公约,并于1993年1月7日递交了批准文件,成为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对参与国际司法和仲裁活动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对待ICSID投资仲裁的态度上也是如此,通常仅允许将与征收补偿有关的争议提交中心仲裁。然而,近年来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议解决实践中的仲裁庭管辖权范围呈扩大趋势,中国的这种谨慎态度正逐步受到挑战。
在主要作为资本输入国(东道国)时期,中国更注重“留权在手”,一方面,仅允许特定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相应地,中国早期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允许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可仲裁的范围和程序提交均有较为严格的限制,①即仅允许将征收补偿争议提交ICSID仲裁,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可仲裁事项的保留。另一方面,中国坚持“个案同意”原则,即未经中国同意或批准,外国投资者不得将有关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中国在1998之前签订的89个BIT中,仅有13个同意ICSID管辖,其余76个未接受ICSID管辖权。而且该同意ICSID仲裁的13个BIT中也只是同意双方在6个月内仍不能友好协商解决的才允许将有关的征收补偿额争议提交国际仲裁;而其他争议只能交由东道国国内法院解决或根据仲裁协议提交国际仲裁。因此,作为资本输入国时期的中国在实践中对ICSID的态度是“有限同意”而且大部分采用限制性的争议解决条款。故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BIT称之为“第一代BIT”。
1998年之后的BIT在可提交仲裁的事项上有明显的扩展。尤其是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实施,中国对外投资增长越来越快,2015年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吸引的外国投资成为资本输入国,2016年累计实现投资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②但中国很多的对外投资流向了投资环境价差或法治状况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此外,2016年中国为全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中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1.3%、16.3%和1.4%。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海外投资利益保护方面也逐渐放宽了对ICSID等国际仲裁的限制,包括可提交仲裁的事项也逐渐扩大至有关投资的任何法律争议,而且也逐步开始放弃“用尽当地救济”并接受国际仲裁的强制性同意。反映在中国1998年之后签订的20来个双边投资协定中,只有8个未接受ICSID管辖,1个部分接受,其余17个全面接受,中国对国际仲裁也从“有限同意”的模式转变为“全面同意”的模式。故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BIT称之为“第二代BIT”。③
二、“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多边化”尝试与新思路
近3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已经超过500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在显著提升,如中缅密松大坝工程和中缅莱比塘铜矿项目被叫停、中缅铁路工程计划被取消、墨西哥政府无限期搁置高铁招标计划及坎昆龙城项目停工、德国叫停中国三安光电对欧司朗灯泡部门的收购,均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阻或失败的典型案例。毫无疑问,“一带一路”的跨国投资及投资争端将不断上升,基于“一带一路”框架构建多变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亦宜作长远规划。
(一)WTO多边体制下的“多边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缺失
相较于WTO下多边贸易体制,多边国际投资条约谈判的努力也均以失败告终,国际投资法领域仍以双边条约为主。1948年《哈瓦那宪章》是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框架的第一次尝试,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保护投资者和维护主权方面不可协调的矛盾,最终因美国拒绝签字而胎死腹中。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5年倡导“多边投资协议”(MAI),但成员国之间因国家主权、劳工保护、环境保护与文化保护等各项议题上的分歧于1998年中止谈判。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和相互妥协,“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最终被纳入WTO框架协议中,整个WTO协议与国际投资法或多或少或直接或者间接地相互联系,从而为国际投资多边立法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来说,WTO协议充其量只是达成了一些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算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边投资协议。④
(二)双边或诸边投资协定下的“多边化”投资争端解决新尝试
在缺乏统一的多边投资协议的情况下,双边互惠主导的众多BIT、RTA投资条约形成了一个现实国际投资法制网,但这个国际投资法制具有典型的“碎片化”特征,即每个投资协定都需要单独谈判,无论是条款还是权利和义务方面都可能出现反复重合或规定不一致,不仅给投资者造成了条约适用的困惑,也给投资者选择合适的投资法律造成困难,国际投资法制的混乱、法律冲突与不稳定性也就在所难免。通过在这种情况下,最惠国待遇条款实际上承担了投资法制的“多边化”功能。首先,因不同双边投资条约签约主体的不断重复可使“双边承诺”转化为“多边承诺”,其次,最惠国待遇条款可将投资条约的缔约国在与第三方的投资条约中所承诺的更高标准的投资保护义务自动地适用于与其他缔约国的投资者,进而使不同投资条约下的投资保护标准达到基本相互协调或相对统一。我们应注意到,欧盟执委会在2015年9月16日提出了投资法院体系(ICS)提案,新的ICS包含第一审法庭(Tribunal of First Instance)与上诉法庭(Appeal Tribunal),新的上诉法庭采取WTO上诉机构运作原则。如果此提案能够最终实现,就能解决ICSID饱受诟病的仲裁判断不一致、平衡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规制权、用尽当地救济等的问题无疑是对多边或诸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全新尝试。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投资争端“多边化”解决机制新思路——OIIC方案
中国经济总量早已跃居世界第二,现为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吸收外资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二大对外投资来自于香港,2015年我国(不包括香港)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根据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角色应当有相应调整和转变,而且正处在“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历史时期,具备适时向国际社会输出多边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之国际公共品的时机和实力。
首先,现有的ICSID是一套以发达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制定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一方面,由于ICSID的规定制定者的出发点倾向于保护来自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另一方面,ICSID在程序正义、透明度、自由裁量权、个案一致性、仲裁员资格以及仲裁上诉机制缺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并导致抵制ICSID的“反向运动”和多个国家退出ICSID等事件,因此世界亟需改革甚至构建新的ISDS。
其次,TTIP框架下的ICS方案为构建新型多边化ISDS提供了可以实践的蓝本。欧委会为TTIP提出的设立新的、透明的ICS提案为替代ICSID为代表的传统ISDS客观上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创设全新的ISDS提供可供实践的蓝本。
最后,亚投行可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新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多边解决机制的诞生母体。借鉴ICSID设立于世界银行框架之下的实践,亚投行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型投资者与国家争端多边解决机制——“OBOR国际投资法庭”(OB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urt,简称OIIC)诞生的母体。
三、“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多边化”的限度
(一)投资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国家同意不得被推定
在国际法体系下,并不存在高于国家的强制性争端解决、第三方管辖机制及执行机制,因此,没有国家的同意,投资者亦无权将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投资条约赋予外国投资者一般是投资准入和投资待遇等实体保护权利,可诉诸国际仲裁的程序权利并不当然随之获得。只有当缔约国明确放弃国内诉讼管辖或同意接受国际仲裁管辖时,投资者才可将其实体权利的救济诉诸国际仲裁机制。属人、属物、属时管辖权不得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予以规避,只有当投资条约缔约国明确表明最惠国待遇条款可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等程序性权利时,投资者才可依据该条款将第三方条约中更为优惠的争端解决条款予以引入,从而实现投资争端解决的“多边化”。
(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多边化”的主导者系缔约国而非仲裁庭
Maffezini v.Spain案⑤开启了将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程序性权利主张的先河。尽管最惠国待遇已成为国际投资条约的核心条款,但是其并非一项习惯法义务。最惠国待遇义务仅为缔约国之间的条约义务,而且最惠国待遇的“多边化”功能也依赖于缔约国之间的协商合意。在当下投资实体权利保护或投资遇标准趋于一致的背景下,投资条约限定保护范围及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限制投资自由化的主要体现。在最惠国待遇条款不适用的情况下,国家之间可基于双边互惠机制扩大投资条约的保护范围或减少甚至取消将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限制条件,而不用担心这样的互惠安排是否会被第三国投资者“搭便车”;在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的情况下,国家推动投资自由化的积极性将会受到抑制,因为其对任何特定国家作出的任何优惠承诺都将无条件地适用于第三国,而第三国确并未向该国提供相应的优惠承诺。⑥如此一来,为了达到通过保护程序权利来更好地实现实体权利、为投资者提供非歧视性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更好的途径不是通过仲裁庭扩大解释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而是通过国家主导来实现国际投资法制的多边化,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或是在现有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完善或重构投资者与国家投资争端“多边”解决机制。
[注释]
①Vesel S.Clearing a Path through a Tangled Jurisprudence:Most-Favored-Nation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Yale J.Int'l L.,2007,32:125.
②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j/2017/01-16/8125984.shtml,2017-7-6.
③卢进勇等.新一代双边投资协定与中美和中欧BIT谈判[J].国际贸易,2014(05):18-19.
④金学凌,赵红梅.论国际投资法制的多边化发展趋势[J].南昌大学学报,2010,11,41(6):41-42.
⑤ICSID Case No.ARB/97/7.
⑥徐树.最惠国待遇条款失控了吗?——论国际投资条约保护的双边主义与多边化[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3,16(1):276.
D996.4
A
2095-4379-(2017)29-0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