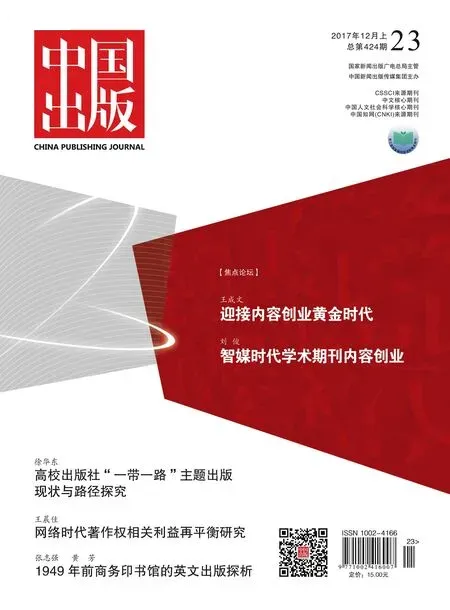“互联网+”形态下版权创造、传播与交易转型研究*
□文│张祥志 安雪芬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确立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为“创新改变生活”(Innovation-Improving Lives),并重点讨论知识产权体系如何通过吸引投资、奖励创造者、鼓励创意开发等方式支持创新,并保证创造出的新知识能被免费获取用以让未来的创新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进步。“互联网+”所催生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主题之一,其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互联网+”这一创新形态,科学研判、系统梳理并理性考察版权创造、传播和交易之嬗变是完善版权体系的前置性任务,也是版权体系真正支持互联网创新的前瞻性工作。基于此,本文拟沿着“新型技术—版权转型”的思路,科学系统地剖析、梳理并总结归纳“互联网+”形态下的版权变革之内涵,以期为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和《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提供可供参考的素材。
一、“互联网+”形态下经济关系之变革
“互联网+”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新形态,突破了以往“+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和理念,强调从联合转向融合,体现为“以互联网为主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与深度融合的过程”。[1]“互联网+”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着强烈的关联关系,包括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国家经济的转型等。针对具体的产业发展,国务院于201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重点强调了互联网与创业创新、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金融、公共服务、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融合,以推动“互联网+”新经济形态的形成,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互联网+”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具体体现在经济关系层面,即互联网+基于其自身特性对经济关系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均产生深度影响。
首先,“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和技术性改变了传统经济关系中的生产环节。互联网使参与生产尤其是知识生产的门槛降低,知识生产所需的信息、数据、知识等“操作性资源”广泛存在且边际成本为零,互联网的扁平化联接方式为个体参与生产提供了空间,这些互联网带来的开放性和互动性特征“使得以知识生产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型,基于公地资源的大众生产模式成为主流”。[2]在大众生产模式之下,“网络使用者在互联网媒介上进行创作性活动成为普遍现象”,[3]人们通过社会互动即可创造全新的知识,由此给传统经济关系的生产环节带来的影响表征为企业的生产主导角色从价值创造主导者转变为价值创造和生产的协助者。另外,从企业生产成本控制的维度分析,互联网的技术性和由此带来的技术信息应用能力能够促使企业克服“机构困境”,“即通过改变传统生产组织方式继而克服企业因追逐利益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的管理成本上升的弊端”,[4]在利润获取和成本控制上表现的更为优异。
其次,“互联网+”的交流性、渗透性和复杂性改变了传统经济关系中的流通环节。连接一切、万物互联的“互联网+”所隐含的交流性特征,以及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及时流动而产生的‘流动空间’使得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在地理上获得延伸”的渗透性,[5]使得传统经济关系在资源流动与配置、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经济活动流通的中间媒介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从经济学角度,互联网创新之本质乃是达成了全球信息资源的重新配置及流通,企业在资源配置和流通中的信息汇集能力愈发凸显。“互联网+”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生的经济效果不同于传统方式,网络平台成为“互联网+”时代经济流通的最关键媒介和渠道。
最后,“互联网+”的多元性、自主性和隐蔽性改变了传统经济关系中的消费环节。“互联网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偏好伪装和同质分类机制”充分显现了互联网的多元性、自主性和隐蔽性。[6]在此背景下,经营者的商业模式不再局限和依赖于传统经济关系中消费者的直接购买行为,而更多地采取免费获取模式通过“访问”或“流量”控制方式让消费者与商家之间产生“黏性”以获得后续的商业利润。“互联网+”对传统经济关系中的消费行为带来的转变主要体现为消费行为、商业模式、消费动机等维度。在互联网2.0时代下,消费者的行为能够被培育和塑造。[7]“移动互联网让企业走向‘微市场模式’”,[8]传统大众顾客因其消费特征而被区分为属性各异的小众。而消费者参与网络互动背后的动机基于消费者的多元化和自主性及网络的隐蔽性使其完全异于传统的消费行为。
二、版权创造的“去职业化”及其转变
“互联网+”环境下版权创造的“去职业化”,转变了版权创造模式、版权创造主体、版权创造形式以及版权创造内容。在版权创造模式层面,缘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和交流性等趋势和特性,使得版权创造不再是专业从业人员的“专利”,互联网上成千上万用户对创作的参与以及专业创作人员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创作成为可能并逐步成为版权创造的主要模式。比如,电视剧的生产创作、网络小说的创作等不再是传统的制作人决定电视剧和小说内容,而更多依据观众和用户的反应和意见来决定作品的内容,此种“内容生产的互动性”和“用户/读者决定内容”模式改变了以往“媒体决定内容”的模式,“使得传统意义上内容生产的专业生成内容(PGC)专业生产模式转化为用户生成内容(UGC)用户自创+PGC专业生产相结合的模式”。[9]在版权创造主体方面,正是基于版权创造模式的非职业化和大众化,使得互联网的参与者与创作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限在网络创作中变得模糊,且版权创造主体逐步泛化。价值共创理论——即“顾客参与到价值链的每个环节,消费者与企业来共同创造价值”——在版权创造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版权的创造及价值链过程相比于传统方式对参与者(消费者)的依赖程度逐步深化。
在版权创造形式维度,版权创造的变革体现在:以碎片化、微型化为特征的微创作逐步兴起,以编辑、加工、演绎、戏仿等行为进行的二次创作逐渐增加,以社交媒体、电子出版、网络平台等为载体的创作行为也日渐盛行。互联网环境下版权创造的形式趋于多样化、丰富化。在版权创造内容方面,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对经济关系中生产活动的影响带来的创造模式、主体和形式的变革,驱使版权内容更加个性化、更具针对性,传统的大众化的作品逐步被小众化的带有强烈个性的作品所取代。共享经济的产生以及基于大数据预测分析的商业模式的兴起即是版权内容个性化的最佳佐证。另一方面,互联网形态下的版权内容创造的动机亦发生了质的变化,创造者的创造动机不再局限于单方面的经济利润或精神价值的追求,分享带来的愉悦感、自身能力的显示、网络地位的单纯获取、互惠互利的追求等动机日益增多。现有相关研究已然证明,程序员参加开源软件的持续开发和创作的动机既包括“基于能力显示的信号机制”,也涵盖了“基于互惠行为的礼物文化”。正是缘于创作动机的多元,使得版权内容趋于多元多样,更具创造性和个性。
三、版权传播的去中心化及其变革
“互联网+”环境下版权传播的“去中心化”,变革了版权传播的介质、版权传播的效率、版权传播的模式和版权传播的枢纽。“互联网+”对于经济关系中流通之资源配置、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和流通媒介的影响在版权传播视域显现为典型的去中心化特性,即版权传播摆脱了以往媒介中心的桎梏向着多元、自由、交互方向逐步发展。
首先,“互联网+”促使版权传播介质由单一转向多元,传统版权传播的“一个内容,一种介质”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变革为“一个内容,多种形态,多元介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微信、微博、搜索引擎、社交平台、游戏社区、流媒体等传播介质不断涌现,版权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多。而且从互联网1.0到互联网2.0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版权传播的介质还在不断延伸和创新。
其次,“互联网+”使得版权传播效率进一步高效便捷,正是基于版权传播介质和渠道的多元,使得版权传播效率得以提升,为版权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和交易提供了便捷。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传播效率得以提高,数字技术使信息与有形载体完全分离,实现了传播的无时间差和无地域性。[10]数字技术携带的版权传播的高效性和便捷性不仅仅发生在互联网产业,传统产业的版权传播效率也得到质的升华,博物馆藏品的版权数字化、传统纸媒出版产业版权的数字出版和优先数字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的可视化和数字化、图书馆版权的电子化等都为文化版权资源的公开、传播和交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再次,“互联网+”孕育了交互融合式的版权传播模式。与传统单向式的传播模式不同,互联网参与者的核心动机和心理需求表征为社交上的满意和提升,通过与其他成员建立互动和联系而获得效益或精神满足,无论是以猫扑、天涯、知乎等为例的社交平台还是以微信朋友圈、微博发布、弹幕电影为例的网络平台均充分印证了互联网的交互性,这种交互既包括商业机构掌握的媒介平台与私人之间的交互还涵盖了私人与私人之间的交互,交互式的版权传播模式逐步成为主流方式。在交互的基础上,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种不同类型传播媒介和渠道之间的联接汇集,促成了融合式的版权传播模式。以电信传输网、广播电视传输网、计算机互联网相互通融为代表的三网融合技术使问题进一步加剧,形成“一个传播终端、六类传播行为、三种法律定性”的复杂局面,其直接原因变现为传播技术的发展融合。[11]
最后,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平台成为版权传播的枢纽和核心。不同于传统的出版社、报社、期刊社等媒介掌握着绝大多数版权内容,互联网环境下的网络平台成为信息传输的中心,也使得网络平台成为版权创造、传播和运用的关键连接点,“互联网+”推动版权传播枢纽由传统媒介转向网络平台。信息获取类、商务交易类、交流沟通类和休闲娱乐类四大互联网应用方式均以网络平台为中心,“网络平台是网络信息传播和版权传播的中心”。[12]
四、版权交易的“去单一化”及其变更
“互联网+”环境下版权运用的“去单一化”,变更了作品利用形态、版权许可方式、市场主体角色和版权商业模式。作品利用形态的“去单一化”体现在“互联网+”背景下作品在市场中的形态由一元转换为多元:一方面,以作品为基石的版权价值链不断延伸,优质版权的开发不断深入,使得作品的形态在市场需求中不断拓展;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影响下的传统作品在向数字作品转型进程中,作品本身的形态也随之由单一转向综合,即作品本身包含了多种技术、形态和要素。
以动漫作品为例,其利用形态的多元化和作品本身的综合性在互联网背景下得以凸显,“中国动漫企业更注重动漫衍生品的研发,在当前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下,动漫产业已成为科学与艺术高度融合的多学科综合的新领域,其产品更多地兼容了高新技术因素”。[13]再有,以互联网环境下的舞蹈作品为例,“舞蹈的作品著作权人通常有编导(大型舞剧又分: 总编导、执行编导、编导等)、编剧、服装、音乐、灯光、舞美等,舞蹈作品的邻接权人通常有出品人、表演者、录制者、视频网站经营者等”。[14]
版权许可方式的“去单一化”表现为:大规模授权许可取代小范围许可成为市场主要需求,便捷高效授权许可取代低效许可成为市场基本特征,基于共享免费观念的许可与基于产权化观念的许可并存成为市场基本格局。随着文化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张和互联网的逐步普及,以版权为核心内容的“IP热”在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领域不断发酵,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版权授权许可的大规模需求,无论是电影产业、音乐产业还是电视剧产业、动漫产业,版权授权许可的数量均呈现高速上升的趋势。
除此之外,在强大的市场驱动之下,版权授权许可的交易成本成为版权交易的关键节点,便捷、高效、简明成为互联网环境下版权授权许可的共性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诞生和发展正是源于这一考量。虽然以产权化观念为本源的版权授权许可模式仍是现今文化交易市场最为主流的模式,但是随着互联网开放性所裹挟的文化自由理念的扩展,以“知识共享”“开发存取运动”为代表的共享免费观念下的公共许可亦是愈演愈烈,从而形成了产权化许可与公共许可并存的版权市场许可局面。
市场主体角色的“去单一化”显现为在版权消费链中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角色的模糊,版权消费中读者、作者和传播者单一身份的消失。在价值共创理论的视域下,版权消费链中的消费者、传播者和参与者等主体均是与创作者互动的价值共创者,或者是版权消费者进入创作领域来帮助、互动和合作创造价值从而形成多赢的效应,或者消费者主导消费领域引导创作者基于消费兴趣和动机来获得更好的体验价值,角色互换、界限模糊成为主要特征。版权商业模式的“去单一化”呈现为传统契约式的“有偿提供-利润获取”商业模式被互联网下的公益式的“免费提供-后向收费”模式所逐步取代。如前文所述,互联网技术下经营者的商业模式不再仅仅依赖于消费者的直接购买行为而更多通过“访问”或“流量”等控制方式来吸引用户从而形成后向收费模式,这一商业模式的蜕变在版权领域表现得尤为典型。与传统契约式的商业模式不同,互联网下的版权商业模式在前端对于普通消费者更趋向于公益式的模式,主要通过后端的后向收费模式来获得利润,“目前市场上比较主流的后向收费包括广告发布、竞价排名、网络游戏、冠名赞助等”。[15]
五、结语
科学系统地掌握“互联网+”在发展历程中对社会关系的改造,是社科科学研究的使命和责任。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以版权为基石的相关产业和社会关系的改造无疑是巨大的。以作者、传播者和读者等主体为主线构成的版权创造、传播和交易之版权消费链在“互联网+”形态下发生了深刻的蜕变。“互联网+”对于经济关系之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影响恰好映射至版权领域的创造、传播和交易端点。版权价值链的“去职业化”“去中心化”和“去单一化”携卷的版权转型和嬗变为版权法律关系之变更、版权权利之确权授权和侵权规范革新以及版权产业之发展都带来了新的命题。
(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宁家骏.“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背景、内涵及主要内容[J].电子政务,2015(6)
[2]Benkler Y.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J].Information Economics & Policy, 2006, 19(2)
[3]Schradie J. The Digital Production Gap: The Digital Divide and Web 2.0 Collide[J]. Poetics, 2011, 39(2)
[4]Shirky,?C. Here?Comes?Everybody: The?Power?of?Organizing?without?Organizations[M]. New York:The?Penguin?Press, 2008
[5]Castells M.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London: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6]Farrell H.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Politics[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2,15(1)
[7]赵振.“互联网+”跨界经营:创造性破坏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10)
[8]Manish Goyal,Maryanne Q Hancock,Homayoun Hatami.Selling into Micro-markets[J].Harvard Business, 2012,7/8
[9]郝婷、黄先蓉.论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版权交易制度的完善[J].数字图书馆论坛,2016(7)
[10]熊琦.互联网产业驱动下的著作权规则变革[J].中国法学,2013(6)
[11]焦和平.三网融合下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构——兼析〈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前两稿的相关规定[J].法律科学,2013(1)
[12]王利明.论互联网立法的重点问题[J].法律科学,2016(5)
[13]张颖露、刘华.中国典型动漫企业专利分析及启示[J].情报杂志,2017(3)
[14]李超.论网络传播中舞蹈作品著作权的保护[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6(6)
[15]张新雯、陈丹.微版权概念生成的语境分析及其商业模式探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