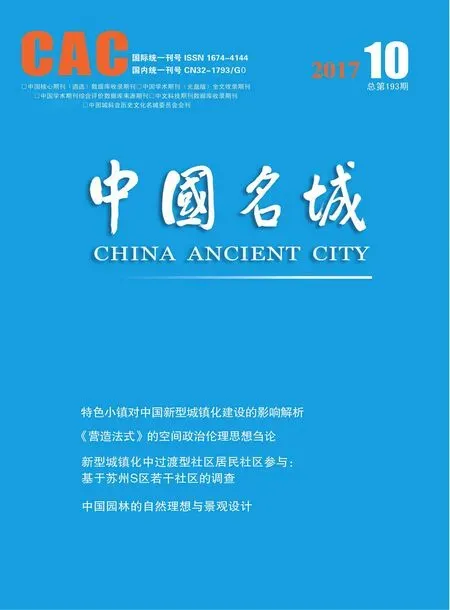浅析上海老城厢的角色演进与文化特质
王 娟 万 勇 李 娇
浅析上海老城厢的角色演进与文化特质
王 娟 万 勇 李 娇
上海老城厢地区是上海“城市之根”。随着租界在老城厢外的兴起和 繁荣,人们渐渐忽视了上海老城厢之于上海的重要意义,甚至视其为包袱和累赘。 通过分析上海老城厢在上海各个时期的角色演进,找到贯穿老城厢始终的文化特质,客观审视上海老城厢在上海城市史中的重要地位,最后提出关于老城厢文化发展的一些思考和建议,以期对上海老城厢的未来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上海 ;老城厢 ;演进 ;文化特质 ;建议
1 老城厢的文化角色演进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上海老城厢的文化角色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因此,本部分将老城厢的演进划分为发展期、没落期、追赶期、沉寂期、复兴期、彷徨期,分别阐释老城厢在各个时期所扮演的文化角色。
1.1 发展期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发展期,是指南宋末年上海设镇到开埠前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阶段,政治上,上海老城厢扮演着一个政治中心的角色。从1292年上海建县以来,就在老城厢内设立了县衙,知县总理一县政务、户籍、赋役、税收、缉捕、诉讼、文教、农桑等事务。1730年,上海道移设老城厢内,知县遇事向道台请告,道台直接参与上海治理,加强了上海县的城市管理。
经济上,上海老城厢日趋繁荣,尤其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沙船业的繁盛,水上航线的开辟。沙船业的兴起主要为漕粮北运,后来逐步扩展为海运贸易,盛时开辟北洋、南洋、长江、内河和远洋五条航线,吞吐量达百万吨。二是棉纺织业的繁荣。江南地区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宜棉花种植。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在明代晚期的棉布产量达到1420万匹,清嘉庆年间增加到2475万匹左右,而可供外销的棉布数量则分别为1150万匹和2075万①。三是小商品贸易的繁荣。包括服装成衣类、医药类、副食类等,形成了一定的集聚,达到了一定的规模。1817年,以商贸行业命名的街道数量大约占总街道的14%,从中也可见一斑。另外,上海老城厢各类公所、会馆林立,说明各行各业的发展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比较规范的组织。
社会上,上海老城厢日渐发展。1291年建县时约有三十万余人(明正德《松江府志》),1816年人口增至四十一万余人(清嘉庆《上海县志》)。②1832年,上海县还设立了“采访节孝公局”,聘用专门的乡绅整理乡民们贞节、孝顺的案例,并告示乡民,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组织的完善,城市人口的增加,社会关系的祥和,等等,推动了上海老城厢的社会发展,使其在大部分历史进程中走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
文化教育上,老城厢也独领风骚。一方面,以豫园、露香园、日涉园、也是园等为代表的园林精妙雅致、建筑艺术高超;以李延敬、蒋宝龄、吴历等人为代表的海上画派独树一帜;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天主教徒促进了天主教在老城厢的传播。另一方面,上海建县后,官办的镇学就改为了县学(也称为学宫),与县学同时并举的还有由过去的儒学者自办的学习机构“书院”,以及由地方绅士集资创办的“义塾”。学习机构林立,由此也可看出当时老城厢教育的完善。
1.2 没落期
开埠后至民国初,由于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等的建立;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起义对老城厢的巨大破坏,导致老城厢的发展逐步走向没落,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削弱。
一是经济上的衰落。曾经称霸一时,承担老城厢经济之龙头的沙船业,由于轮船业的兴起而逐渐衰落;棉纺织等产业由于租界地区大量工厂的兴办,也逐步退出老城厢;此前遍布的钱庄、鳞次栉比的商铺、林立的码头,由于沙船业的衰落、棉纺织等产业的转移、老城厢商业地位的下降,也逐渐向经济比较发达的租界地区转移。最终,老城厢原有的经济中心地位向租界地区漂移,老城厢传统的商贸中心地位受到极大冲击。
二是市政设施和管理上的落后。一方面,老城厢没有公共照明、自来水和正式的消防、保洁机构。另一方面,老城厢地区没有规范的城市建设和治理方案,很多事务依旧是约定俗成,无组织,无体系;三是环境的逐步恶化,等等。密布的河汊逐渐干涸,曾经舟水桥相衬的泽国面貌已逐渐消逝;原来的水系已经无法行船,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倾倒的生活垃圾和生活废水。从视觉上来看,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从嗅觉上来说,到处是废品、排泄物和污水,臭气熏天,气味难闻甚至让人窒息。
1.3 追赶期
民国建立前后,上海华界当局和居民对租界地区的繁华、进步非常羡慕,萌生出学习、追赶的意识,作为华界的老城厢一度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尽管闸北华界自治发展开始新探索,尽管民国政府于1930年代提出大都市计划欲拓展城市空间、转移发展重心,尽管老城厢在全市的地位日渐式微,但老城厢自我救赎的步伐毫不动摇、一直向前。士绅群体集体上书要求拆除城墙。辛亥革命后,上海老城厢开始逐步拆城拓路、填浜筑路、学习租界地区先进的城市治理机制、引进先进的生产制度技术和人才等等,这些举措为老城厢的复兴带来了契机。
首先是拆城拓路、填浜筑路。从1914年之后,上海老城厢开始拆除城墙、填平河浜、筑造道路。随后老城厢开始和租界、华界地区接轨,互通有无,从原本围城封闭发展的旧模式,走向开放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其次是完善市政设施。1917年,南市电灯厂的电灯点亮在上海老城厢内的大街小巷。使得老城厢摆脱了煤油灯时代。自来水厂的建成,使得老城厢地区的居民在1920年后逐渐开始使用自来水。警钟楼的建设,救火联合会的成立,使老城厢的消防工作进一步接近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上海公共体育场的建成,为市民提供了大型公共空间,市民生活更加丰富。
第三是改善卫生环境。一方面,1910年,老城厢正式设立清洁所,并且对清洁人员、清洁时间做了严格的规定。另一方面,拆城拓路、填浜筑路之后,老城厢的路网系统逐渐系统化,路面环境卫生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另外,还统一发展慈善事业。开埠前老城厢地区经济较为繁荣,善堂林立,各项慈善事业已经萌生。但直到1912年3月,出于统一施行慈善事业的考虑,同仁辅元堂与育婴堂、普育堂、清节堂等其它慈善机构联合组成了上海慈善团。慈善堂由各堂负责人领导,遇事共同协商解决。③
1.4 沉寂期
上海老城厢的沉寂期大约在1956年至1990年之间,这与彼时全国和上海的发展条件、发展策略息息相关。在这个阶段,老城厢已不再存在历史上曾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地位(哪怕日渐式微的弱中心地位),与全市面上各地区一样,也没有太大的发展与改观,甚至与那个年代更受待见的工业区、商业区、办公区和中高档居住区相比,处于一定的劣势地位。老城厢居民在本就薄弱的生活、生产、生态基础上,承受着更多的艰难与付出。
在计划经济期间,曾经繁盛的沙船业和棉纺织业早已退出老城厢的历史舞台;繁荣的小商品贸易也因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发展受到束缚;再加上大量农村人口移民上海和上海本身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这一时期老城厢内人口密度急剧升高。居住条件极差、充满消防隐患的棚户简屋连绵成片,老城厢居民生活水平很低。在大跃进期间,全国上下主张“先生产,后生活”,上海也不例外,上海这一时期的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工业生产跃居前位,但基础设施,如住房、交通、道路等却并未进行改善和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老城厢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在很多方面处于停滞状态。老城厢依旧是昔日拥挤的弄堂和一些小型手工业在艰难的维持生存,老百姓在挣扎中期待老城厢的复兴。
1.5 复兴期
上海老城厢的复兴期大约在1990年至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上海老城厢全面崛起,在经济、文化、市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均颇有进益。
豫园城隍庙等重要历史地段得到改建,精致的飞檐、雅致的白墙红瓦、小巧的翘顶、林立的商铺,带动了老城厢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老城厢地区的经济繁荣。市场经济体制的施行,使老城厢的街巷再次出现林立的商铺,小商品贸易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老城厢的历史文化价值逐步显现并受到重视,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文物单位的宣传推介都有很大进展。
同时,在土地批租开始之后,房地产业兴起,本土居民无论是购买商品房,还是动迁安置到其他新建房屋,都实质性地改善了老城厢的环境面貌、分流了老城厢的人口、促进了市政基础设施的完善,棚户区大量减少,绿化、道路、设施大量改观,人口密度逐渐降低。
近年来,黄浦区成立了老城厢指挥部,征集了城市设计方案,编制了发展规划和计划,开展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老城厢似乎迎来了新一轮发展的契机。
1.6 彷徨期
然而,不管如何奋起,当老城厢所在的南市区与黄浦区合并进而又与卢湾区合并后,当老城厢的定位与发展被放置于更大的空间后,当老城厢因其他地区的充分发展而成为相对来说更难啃的硬骨头后,当发展成本更高昂、风貌保护更关注、利益纠缠更激烈、社会关系更敏感后,政策完善与机制创新工作小步渐进(甚至浅尝辄止),发展商望而生畏,老城厢复兴的节奏开始变慢。特别是老城厢南部地区,懵懂一片、饱经风雨的旧民居,不知何时才能迎来新气象。
在受到各种力量挤压的情况下,老城厢发展面临诸多矛盾和纠结,俨然处于一个发展的彷徨期。一是文化坚守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2002年前,土地批租、招商引资、旧区改造等等,老城厢一度大刀阔斧,拆旧建新为一时风尚;2002年,老城厢地区被确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历史建筑拆与留的天平开始倾斜;近年来,在“拆改留”到“留改拆”的城市更新大环境下,老城厢历史建筑在拆与留之间徘徊。但是老城厢东临浦江,北依人民广场,西接新天地,南靠世博园,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明显,是经济发展热点地区。如何做到发展老城厢地区经济又不产生对人文遗产的破坏,是当前老城厢发展的一大矛盾。第二,高昂的动迁成本和窘迫的生存条件之间的矛盾。老城厢地区多为沉淀了上千年的老建筑,消防隐患高,安全性能差,居住条件比较差,是更新改造的重点地区。但该地区人口密集,住宅密度高,动迁成本高昂,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矛盾。第三,旧区改造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利益纠缠,关系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使相关工作难以推进。若不能处理好各个利益体之间的关系,将会导致各利益群体之间产生矛盾纠纷,甚至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
2 老城厢的文化特质
文化特质是在漫漫历史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上海老城厢在其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内敛、深厚、繁盛、平实、互助的文化特质。
2.1 内敛
上海老城厢的内敛首先体现在城市形态的围合性上。嘉靖三十二年,因倭寇袭击而促使四通八达的老城厢筑起了城墙。老城厢也被围在了几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辛亥革命后,拆除城墙,就地筑路,新的路网并未改造成笔直大道,而是保留了原有的围合结构,凸显着昔日老城厢本色。其次,老城厢的内敛体现在住宅建筑的围合性上。老城厢地区的住宅大多为合院式,从外部形态来看,关上大门,整个房子便与世隔绝;从内部形态看,四周围合,仅中间的天井与外界相通,抬头所见即是整个世界。另外,老城厢的内敛还体现在道路空间的私密性上。老城厢的道路依旧保持着较窄的尺度,且丁字路、交错路、曲折路众多,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很少,相对于租界地区而言,开放性特征很不明显。除了主要的街道以外,其余依旧为小巷,仅仅适合人的行走。深入老城厢内部,两侧高高的墙壁、羊肠小道,私密性极强,低调内敛,与老城厢外的宽阔、笔直形成鲜明的对比。
2.2 深厚
上海老城厢虽然建县至今只有七百多年的历史,由于开埠前该地区商贸发达,使得本区重视教育,人才辈出,底蕴深厚。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一是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精英荟萃。上至科学巨匠徐光启、政界领袖李平书、棉纺先祖黄道婆、秦观后代秦裕伯、一代武将乔一琦、海派画家王一亭、沙船霸主郁泰峰、实业精英陆伯鸿等人,下至顾家女眷顾缪氏、韩希孟、面筋能手薛二倌等,不论哪个领域,均有行业巨匠从这里脱颖而出。二是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纵观老城厢上千年的发展中,曾经有过的寺庙庵观不计其数,例如大境道观、白云观、城隍庙、小桃园清真寺等。直到现在,每逢重要节日,人们都还会到城隍庙烧香,期望城隍能够保卫家人平安幸福,保卫上海生生不息。三是优质的学堂书院。开埠前上海最著名的四大书院(龙门、蕊珠、敬业、梅溪)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其中梅溪书院(现在的蓬莱区第一中心小学)最先开办小学教育,开启了历史上近代学堂的先锋。除蕊珠书院在民国期间停办以外,龙门书院、敬业书院都持续发展,成为现在的上海中学和敬业中学。此外,“深厚”这一文化特质还深刻的体现在上海老城厢的建筑艺术、园林艺术、地名文化、民俗文化等方方面面。
2.3 繁盛
老城厢地区历经百年沧桑,曲折发展。但是总体来说,不论是经济上盛极一时的沙船业、城隍庙豫园商业中心;还是曾经作为政治中心的上海县城;抑或文化上独树一帜的海上画派、顾氏刺绣、学堂书院等等,都体现了老城厢的繁盛。例如持续繁荣的城隍庙豫园一带的商业。城隍庙本为烧香敬神的庙宇,由于开埠前老城厢经济繁荣,来城隍庙拜神的香客众多,于是沿庙宇两旁就形成了林立的店铺,经营物品主要为烧香用品。此后,随着上海商界精英、社会士绅等兴起建造园林之风,城隍庙旁边建起了精致的园林,以潘家的豫园为代表。历经辗转,城隍庙成为庙、市、园林三维一体的城市空间。这样的城市空间不仅成了平民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场所,同时雅致园林也吸引了文人墨客的聚集。即使是在开埠后,城厢经济中心向租界北移之时,这里仍然是文人墨客雅集的好去处。近代以来,各相关政府部门不断对城隍庙地区进行维护和管理,逐步将其商业规范化,经营范围鲜明化,从而使得城隍庙成为了上海名片,获得了外地人和上海本土人的双重青睐。如今,城隍庙豫园商业中心已成为中外游客来上海观光的必去景点之一。
2.4 平实
老城厢地区整体的城市风貌始终保持一种平实的本色,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老城厢整体建筑风貌的平实。低矮的建筑、狭窄的弄堂、曲径通幽的街巷,与外滩地区的富丽堂皇、陆家嘴地区的鳞次栉比、衡复等风貌区的优雅居住、其他新建城区的整洁有序相比,老城厢基本上还呈现为原有的本色和调性,成为整个大都市里与众不同的一个地区。二是市民生活的平实。对老城厢地区的居民来说,拥挤的住宅、嘈杂的街市、摩肩接踵的人群、曲折的小道、朴素的三餐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无力改善现在的生存条件,只是平淡、踏实的过着原有的日子。三是生活信仰的平实。这一点在上海老城厢地区的路名命名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如永兴街、永宁街、安平街、福佑街、安宁街、贻庆街、如意衖、万安街等等,直至今日,这些路名中的一部分仍在使用,从这些路名中,我们能够体会到隐藏于路名背后且渗透在老百姓骨子里的平实信仰。
2.5 互助
互助作为上海老城厢的文化特质之一,映射着老城厢市民生活的祥和风貌,推动着老城厢的发展。首先是族内互助,包括家族互助和宗族互助,是老城厢最早的互助形式。宋元时期,以农业经济为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依赖于血缘和地域,于是同姓家庭组成家族,同血缘按亲疏远近组成宗族,选举家长和族长管理族内事务,救济孤寡、调解纠纷、维护秩序等。其次是行业互助和地域互助,是开埠前同老城厢经济繁荣同时并生的社会互助。行业互助是指同一行业内人员的互相帮助,如因沙船业的繁盛而兴起的商船会馆;地域互助多指移民而来的外乡人聚在一起建立会馆,形成互助,如泉漳会馆、潮惠会馆等。再次是宗教互助和社会互助,是促进市民正常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互助形式。宗教互助主要是指信奉同一宗教的人之间的互助。社会互助主要是指一些慈善机构,如同仁辅元堂、新普育堂、上海育婴堂等对有难市民的帮助。二者的存在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满足了市民的基本生存需求、给社会带来了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最后是随着老城厢的发展而兴起的新型协会互助。例如1907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和万家公益会总董毛子及等人联合发起建立的救火联合会④等等。总之,以上所有互助机构的建立,推动了老城厢的发展,凸显了老城厢市民间的互助精神。
3 未来老城厢未来发展的思考
从古到今,上海老城厢的角色虽然在不断演进,但是它的文化特质和内涵却始终流动在这块面积不大的空间里。因此,老城厢的未来保护和发展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3.1 保护老城厢的文化遗产
老城厢地区历史积淀深厚,名人宅第、宗教建筑、私家园林众多,道路系统完善,文化遗产十分丰富。通过这些物理空间,老城厢储存了人们对上海漫长的城市史的记忆。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和城市记忆的载体,失去文化遗产,人们对于一座城市的认识会逐渐模糊,对于生息于斯的记忆会慢慢消失。因此,要抓紧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加强对老城厢地区人文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抓紧抢救和修缮那些破损严重的人文遗产;开发商要严格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开发建设,确保老城厢的人文遗产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受到破坏;市民要提高自身修养,树立主人翁意识、责任意识、公德意识,自觉保护老城厢的人文遗产。
3.2 挖掘老城厢的文化特质
老城厢的文化特质是在上千年历史中积淀而成的,是老城厢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特质深藏于老城厢的表象之下,加上年代久远、档案缺失,使得人们对老城厢的认识比较肤浅,记忆比较模糊,甚至开始被人们淡忘。因此,需要深度挖掘老城厢的文化特质。在老城厢和老城厢以外地区的双向互动中发现老城厢的古老魅力、找到新旧对比中的文化张力、直面未来发展中的巨大压力。让老城厢尽快变压力为动力,体现文化的张力,展现古城的魅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让老城厢形象更加鲜明、立体、丰满的展现在人们面前。
3.3 寻找老城厢发展的突破点
老城厢是昔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中心,现在已经逐步演变成上海众多地标中的一个,且只有豫园城隍庙地区发挥着它的商业、旅游和文化街区作用,其它地方的带动作用并未充分展现。因此,可以借助这些文化资源,发展特色城厢文化,振兴老城厢。具体突破方法如:建立老城厢文化博物馆;和相关旅游机构合作开辟老城厢一日游的主题线路;相关部门可以筹资拍摄老城厢历史文化纪录片,扩大上海老城厢知名度;甚至把老城厢的历史文化名人事迹编入沪上学校学生的课外读物中,从“城市之根”的高度予以普及等等。
3.4 破解老城厢发展的瓶颈
老城厢地区存在着诸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破解发展的瓶颈关键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完善老城厢地区的发展战略规划,制定出符合老城厢特色、展现老城厢魅力的规划方案,以引领老城厢的未来发展;二是完善老城厢发展的政策,让老城厢的发展更有法可依、有根可循、有文可引;三是创新老城厢的发展机制,通过客观评估老城厢现状,找到适合上海老城厢的发展机制,尤其是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四是创新老城厢的发展模式,明确老城厢的发展定位,采用与时代贴合更紧密、更有利于社会参与的发展模式,让老城厢尽快破解发展的瓶颈。
3.5 走出老城厢发展的彷徨期
如前文所述,老城厢存在文化坚守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高昂的动迁成本和恶劣的生存条件之间的矛盾,以及旧区改造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导致政府工作难以推进的问题,因此导致老城厢的发展陷入了彷徨期。在此,一方面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尽快对老城厢进行专业评估和明确定位,制定老城厢的发展方案;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居民、企业、专家等社会各界人士加强对老城厢发展的关注,献言献策,争取在汇集民智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老城厢实际需要、有利老城厢特色彰显的老城厢发展方案,使老城厢尽快走出发展的彷徨期,最终重振老城厢。
上海老城厢地区是上海“城市之根”。随着租界在老城厢北侧和西侧的兴起和繁荣、新区新城在上海城市外围呈圈层状的建设与发展,人们渐渐忽视了上海老城厢之于上海的重要意义,甚至视其为包袱和累赘。当然,上海老城厢曾经辉煌与繁盛,也曾衰落与沉寂,曾经追赶与复兴,也曾彷徨与纠缠,在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老城厢一直处于起起落落的角色转换之中。
然而,在实际上,老城厢改变的是其在上海历史上的角色和地位,不变的是贯穿始终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有些特质甚至是上海文化瑰宝、上海城市财富、上海精神之源。上海应高度关注与重视老城厢,研究老城厢的城市功能演进、城市形态变迁、城市文化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影响老城厢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对历史负责任、对当下负责任、对未来负责任的高度,提出老城厢发展方略,努力使老城厢带着历史文化基因和千年上海记忆,走出现实的羁绊,走向光明的未来。
注释:
①李伏明.《制度、伦理与经济发展——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研究(1500—1840)》[D].上海:复旦大学,2004.
②潘君祥.陶治.刘平.陆菁.《上海700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92页.
③许国兴,祖建平.《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第53页.
④潘君祥.陶治.刘平.陆菁.《上海700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233页.
[1]陈业伟.上海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J].城市规划汇刊,2004(05):50-58.
[2]乐涛.上海老城厢风貌特色及其保护价值[J].上海城市发展,2004(04):31-34.
[3]杨云.吴岱茜.龙头上的一颗明珠:豫园老街[J].上海商业,2013(14):65-67.
[4]何益忠.从中心到边缘—上海老城厢研究(1843—1914)[D].上海:复旦大学,2006.
[5]李伏明.制度、伦理与经济发展——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研究(1500—1840)[D].上海:复旦大学,2004.
[6]许国兴,祖建平.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
[7]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8]李天纲.文化上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9]熊月之.上海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0]潘君祥.陶治.刘平.陆菁.上海700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1]何益忠.老城厢晚清上海的一个窗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2]薛理勇.上海老城厢史话[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13]忻平.城市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4]苏智良.上海城区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15]陈业伟.旧城改建与文化传承[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16]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17]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Shanghai Old Town is the root of Shanghai City.With the rise and prosperity of concessions outside the Old Town,people gradually ignored the significance of Old Town to Shanghai,and even regarded it as an encumbrance.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role evolution of the Old Town in all periods of Shanghai,fou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out the Old Town,objectively observe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Old Town in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City,and finally put forward some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to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Old Town,expect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Old Town.
Shanghai ; Old Town ; Evolution ;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 Suggestion
C912
A
1674-4144(2017)-10-73(6)
王 娟,上海市黄浦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馆员。
万 勇,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城市记忆空间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
李 娇,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学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蒋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