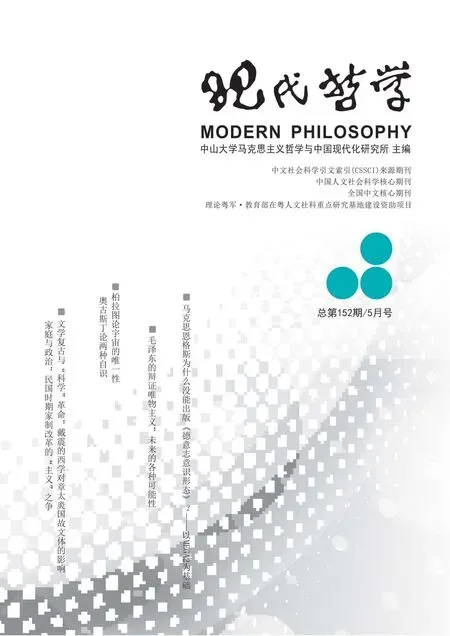张元济与《正统道藏》重版
黄 剑
张元济与《正统道藏》重版
黄 剑
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对《正统道藏》进行的影印,是商务重心由出版教科书为主向影印善本古籍、出版学术书籍转变中一大事件,这不仅是整理国故中的重要一环,而且这一相对系统基本材料的重版,对后世研究的兴起居功至伟。通过对商务出版《道藏》过程的梳理及研究,显现出张元济在晚清民国延展人脉的具体方式与思路,进而检视、发现由此展开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标签化历史认知的差异。
张元济;傅增湘;徐世昌;商务印书馆;《道藏》重版;人脉
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在1923至1926年间以北京白云观所藏《正统道藏》为底本进行影印。虽先后仅印150部,但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极大研究便利,直接促进了近代道教研究的兴起。著名如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正基于此而展开,对《道藏》乃至道教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然过往研究对《正统道藏》民国年间印行一事尚显薄弱*陈晓维:《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好书之徒》,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46—158页。除陈晓维一文外,鲜见相关研究。。
在商务大规模翻印包括《正统道藏》在内的经典善本及学术书籍之前,商务的崛起主要是依靠出版教科书*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35页。。但对于一个不断壮大的商业帝国来说,在人脉急剧扩张的情形之下,如何突破企业发展瓶颈的问题摆在了以张元济为首的决策层面前。在多方人脉的鼎力支持下,商务完成了从出版教科书到翻印经典善本、出版学术著作为主的策略转变,在带来了可观经济利益之时,亦为其赢得了南方学术重镇的美誉,进而又促进了商务决策层与主流政学商三界人脉的匹配。*商务对外部政学商界的联络,从以张元济为首转变为以张元济、王云五为共同核心进行。。
一、义利双赢
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代开始大规模影印包括《道藏》在内的经典善本及出版学术书籍,不仅将企业打造成远东地区顶级出版巨擘,更被时人目为极重要之学术机关,在近代文化史上创造了一个义利双赢、难以逾越的高度。而这一局面的出现,要从商务自出版教科书向影印善本、出版学术书籍的经营策略转换谈起。
自清末以来出版教科书利润颇为可观,故而大量民营资本注入出版行业。随时间推移,教科书市场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当中编辑人员的招募和培养,成为教科书出版的重中之重。1920年2月3日,张元济午后出席商务印书馆第237次董事会议。他提出:“现在各省自编教科书,又新思潮激进,已有《新妇女》《新学生》《新教育》出版。本馆不能一切迎合,故今年书籍不免减退。应当注重印刷,力求进步。现在成绩不宜视为止境,即再进为八百万、千万均非难事,但人才实在缺乏,极宜留意。”商务印书馆董事长郑孝胥提出:“可特提十万,以备储养之用。试办三个月,如不适用,即行辞去。”张元济认为:“此策甚为紧要,但初办不必过宽,至欲办理此事,应有人担任。”*《张元济全集·日记》第7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83页。
各省自编教科书,加上其他出版社的竞争,使得人才储备显得尤为重要。张元济通过网罗人才来延展人脉是其一生工作的重心。当时,教科书竞争已经达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程度,由商务重要干部成立的中华书局已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对教科书投入巨资也不可能获得以往惊人的商业利润。如何调整商业结构,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这个问题摆在了商务领导人面前。
此时张元济作为商务的全盘规划人物审时度势,提出了翻印经典善本与出版学术书籍这一对策,被事实证明是极富远见之举。1926年1月19日,商务总务处第696次会议上,张元济就收购密韵楼藏书发言:“……在本馆则因影印旧书为营业之一种。如《四部丛刊》、《续藏》、《道藏》、《学津讨原》、《学海类编》、《百衲本资治通鉴》、《廿四史》、《续古逸丛书》等,有数种均已售完,虽有数种销数无多,然未有不销因而亏本者。”*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34页。后来重印《四部丛刊》也与中华出版《四部备要》与商务竞争有关*1926年9月16日:“……近中华发售《四部备要》,大张旗鼓。本馆因重印《四部丛刊》,以相抵制……”(《张元济全集·书信》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14页)同年10月17日致傅增湘书也提到此事:“重印《四部丛刊》原为同业竞争而发,初意不过仅印续编,后见同业有《四部备要》,不能不并行,以期招徕。”(《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31页)。在保存文化的同时,商务影印大量古籍获得了巨额利润,仅《四部丛刊》这一种书,张元济在一次股东会上公然承认:“此书发行两次预约,共销二千四百余部,收入有一百余万元。”*《张菊生口中之买书案》,《晶报》1927年5月3日,第2版。这种义利双赢的局面实为商务印书馆史上的黄金时期。
商务印书馆此时出版的学术专著及杂志,不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也涵盖了自然科学领域;不仅自身坚持这个方向,而且扶助后进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当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支持中华学艺社继续发行一份综合性学术刊物——《学艺》杂志。《学艺》在发刊词中批评我国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不能和社会科学齐头并进,故而导致了18世纪后学术故步不前*君毅:《发刊词》,《学艺》1917年第1期,第1页。。所以这份杂志定位办成不分文理的一个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既刊载广义相对论等自然科学理论,也介绍社会科学,内容极为丰富多彩。
商务这种无论中西、文理、新旧的学术发展理念最终获得极大的成功,并通过提携后进的方式促进了人才合理的双向流动。丙辰学社,后来之中华学艺社不少重要骨干服务于商务,并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如学艺社总干事郑贞文、副总干事周昌寿、编辑干事范寿康;商务也有重要干部来到学艺社担负重任,如何炳松。
中华学艺社(丙辰学社)是1916年创立以留日归国学生为主的学术团体,中华学艺社侧重文理结合。当时,总干事郑贞文、副总干事周昌寿、编辑干事范寿康、郭沫若四人中就有三人在中华学艺社供职,《学艺》杂志在商务能够出版,一方面是商务拓展业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商务印书馆对中华学艺社学术水准的肯定。
学艺社的灵魂人物郑贞文1918年7月2日入馆*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第508页。,他回忆:“1918年秋,我由日本毕业回国,张元济聘我在编译所理化部当编辑。”*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01页。张元济早在5月22日的日记有载:“日本留学理科郑君贞文,汉文极佳。与梦商,拟俟伊来沪时约与面谈,再定聘用否。”*《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61页。不久郑贞文被张元济延请入馆,与其他输入的新鲜血液一道,共同见证了商务历史上的高峰。
其他如支持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创办《史地学报》等*胡焕庸:《竺可桢先生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328—329页。,也使得商务印书馆的人脉,通过翻印善本、编撰学术著作逐步渗透到国家重要的学术、教育、经济、政治部门。商务印书馆在重视社会科学方面传统的同时,亦关注到自然科学的昌明,以振兴传统文化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不仅在张元济执掌的时代表现明显,甚至延续到了王云五执掌时期*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除影印善本、流通古籍的工作仍由张元济主持外,其他书稿的出版规划,由王主管。编译所从1922年到1924年,进用职工达266人,他延续了“五四”以来张元济、高梦旦所实行的新方针——从注重教学用书转向并重一般图书,着力介绍学术名著。唐锦泉:《回忆王云五在商务的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56页。。
由此观之,商务印书馆在当时不仅仅是一印刷企业,也不仅是一商业机构,在张元济主导的年代俨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文化机关,这不单是商务当权者的自我认同,也是社会上对商务的一种期许。如胡适1926年写信给张元济就说道:“……所以我极盼先生再支撑几年的辛苦,使这一个极重要的教育机关平稳地渡过这风浪的时期。”*《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39页。就商务这种性质的教育机关而言,肯定不只是简单发行教科书,而在于企业在乱世之中勇于担当,通过翻印经典善本与出版学术书籍促进文明传播与社会进步。《道藏》的印行正是企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二、印行《道藏》与维系人脉
民初北京政府时期,各派军阀轮流执政,社会动乱、思潮激荡,形势瞬息万变。张元济及其执掌的商务印书馆适时把握住机遇,利用当时动乱的政治形势和自身在政学商三界的强大人脉,在夹缝中求生存,以文化出版事业为桥梁,从五四运动到整理国故运动,无分新旧左右、禹内域外,汇集一时之俊彦,既出版新知如汉译名著发行,又整理国故如出版《道藏》,将各方力量活成一片,获得了各方均赢的欢喜局面。张元济执掌下的商务印书馆也迎来历史上义利双赢的黄金时代。
受日本印行《大正藏》的刺激,加之风传日本还有印行《道藏》的打算,国内有识之士加速了印行《道藏》的步骤,以免在文化领域再受其辱。1918年6月13日,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在北京购地建馆及印行《道藏》等事北上。6月20日抵京,6月22日晨起访伍光建、高子益、蔡元培、王宠惠、林纾,下午访陈筱庄、王峄山、郑际堂*《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73页。当日张元济拜会多为教育家。在此及后文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将张元济访京行程逐日的作了一个轮廓性描述,就是试图通过张元济入京后与政界、学界相关人等开始频繁会晤,除商务的运营业务和出版事项进行跟进,与同道联合出版《道藏》的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外,将政局动荡下、新旧中西各方势力庞杂相处的局面中,张元济为求生存、谋发展,不得不与上下左右、内外新旧的各方关系同时交往,以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的真实状态尽可能的还原,从而了解《道藏》等国故影印所处之背景情况。。6月23日上午访丁澄如、汪大燮、朱小汀、金兆蕃、孙宝琦、夏循垍、董康、宝熙、力胜、张君劢等;午后访卢涧泉、孙荫庭、夏曾佑、邵伯絅、蒋维乔、王搏沙、熊希龄、严复、钱能训、冯公度与史履晋、蒋式惺等人*《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73—374页。冯公度与史履晋、蒋式惺三人于1905年共同创办北京第一家民用电灯公司,即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本日多见有功名出身、知识分子型政客。。6月24日午后见汤尔和、林绍年、汪建斋、沈曾桐、方甘士、陈仲骞、曾刚甫等。6月25日一早出门见傅增湘、谷钟秀、王云阁、张一麐、徐子璋、张仲叔、方惟;午后见伍连德、叶瀚等人*《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74页。。 6月26日访叶叔衡、章士钊、蔡元培、屠寄等人。6月27日唔李盛铎、沈东绿、金巩伯、沈尹默、刘崇杰、李石曾、庄思缄、陈独秀、余阶青、吴菊农等人*《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75页。。与沈尹默谈小学国文教科书,沈向张建议全用白话文,论修身材料不合儿童心理,数学画实物不宜诸事*《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76页。沈尹默亦顺应历史潮流而向张元济建议教材改用白话文。。6月28日访林长民、吴尚之、钱恂、王叔鲁、袁观澜等人。6月29日访戴螺舲、董懋堂、沈钧儒、马叙伦、徐新六、许溯伊等人*《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76页。。6月30日午前与曾刚甫、汪大燮、林长民、贾果伯、朱小汀来谈;上午十时和傅增湘同往方家胡同图书馆看书;晤邓邦述、叶恭绰、江天铎、徐建侯、钱恂,午后三时散;后去拜见徐世昌、蒋百里、陈汉第、朱希祖、郭小麓等人*《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77页。。
1918年7月1日,拜访曾叔度、魏冲叔、高阆仙、郭春榆。午后访邓邦述、金仍珠、孙宇晴、钱阶平等人*《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77页。。7月2日上午见许吕肖、熊希龄、林万里、丁佛言、严璩、蒋维乔、胡石城、王搏沙、萧秋恕、林宰平等;午后晤胡文甫、汪大燮、伍光建、陈汉第、胡适、晚饭后冒广生来访*《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77—378页。。7月3日高子益、汪大燮、林长民、张元济四人出游。张元济直至7月5日回城*《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78—379页。,7月6日与伍光建游。7月7日赴陈汉第宅,见俞涤烦*《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80页。。张元济与相关人等马不停蹄的会面为商务即将开展的业务及拓展人脉起了明显的作用。在其挚友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关照下,商务既在计划之外又在计划之内接下个大订单。
1918年7月8日与蔡元培谈:“大学教员及兼任外边教授者,拟就现有教科书先行改良。问本馆能否接受照改。余云,极所欣盼,即酬报一层,将来亦应致送,虽不能丰,亦应尽所当为。鹤谓,此可后来再说。此时可否各送书一份,以便着手。余云可以照送。”*《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81页。7月9日,由于蔡元培先行提出,北大教授们改编教材后交付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张元济午后“二点三刻赴北京大学晤鹤庼、陈独秀、马幼渔、胡适之、陈仲骞、沈尹默、朱逖先、李石曾、钱念劬之弟,号秣陵。又管图书馆某君,谈三事:一、世界图书馆事,二、编辑教育书事,三、改订本版教科书事”*《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81页。。7月10日由于李拔可病重,和夏曾佑谈续编《中国历史》事后,张元济折返上海*《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83页。。
张元济此次北京之行,拜会了大量政、学、商界的头面人物,计有大总统、各部部长、大学校长、教授及大公司董事,继续了他执掌商务后游走三界的路数。张元济与印行《道藏》的关键人物,如傅增湘、徐世昌不断会面,虽无具体材料遗存,然此议题当在讨论之列。加之出版《道藏》并不仅是个简单出版问题,已上升到传承民族文化的层面,所以《道藏》的印行虽不如其他大型丛书印行那般利润丰厚,但由此巩固了他在北洋一系中与科举出身的大知识分子的友谊。且在蔡元培关照之下,让北大教授参与编写教育书及改编商务版大学教科书,既提高了教科书本身的质量,使得商务版的教材得以攻占最高学府,又使得编书的教授们增加了收入、扩大了影响,进而替蔡元培收买不少人心。同时,商务印书馆通过张元济的频繁拜访,与京中无论是趋新、还是相对保守的学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而发现新旧壁垒从来是相对而言,并无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如当时被目为老派的沈尹默也建议张元济应该采取白话文教科书。
张元济回到上海不久,7月19日启程再度折返北京。7月22日在北京饭店膳室遇见辜鸿铭*《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86—387页。。7月23日在北京分馆看书,偕孙壮、傅增湘在中央公园茗谈片刻,即返旅馆。7月26日致信高凤谦、孙毓修,请将《四部举要》未有各书标出寄来,以便采购。午后访福开森。7月27日致信蔡元培,还越缦书目。并开去书单,皆评校之书,请转商每种各选首尾二册,于一个月后寄沪。访史康侯、蒋性甫、王克敏,王许诺可借书给商务影印。7月28日午后访那桐、宝熙、徐桐等人,均未晤。致外交部拜客,适星期一,无人在*《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88页。。从张元济的日记记载来看,除人名之外,多记访书之事,而且不仅是为《道藏》做前期准备,也为《四部举要》即后来改名的《四部丛刊》的相关事宜做前期的积极准备。
8月6日访夏润枝、聂献廷、沈曾桐、方甘士、林青生、林宰平、汪大燮。午后与傅增湘见白云观陈道人,谈印行《道藏》事。“拟告以沪观一部,拟抽给津贴,亦无允意。陈甚难商。京观一部可否商一变通办法,运至上海可以向两部立案,沿途饬官保护,作为官事办理。或由观派人同往监看,均无不可。道人云,已于廿日前去信与陈。再侯十日,如有回信不允,拟再追一信去。余言,如有办法,可再函商。如系空言,似不必再渎,不如就在此商定办。道人亦无言。”*《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90页。从这段日记中,可以发现当时商务与北京政府及江浙沪等地方势力交情甚深,不仅可以调动包括教育部在内的两部总长为其将《道藏》搬运至上海影印背书,还可以号令各省长官下令沿途保护。张元济长期在政界深耕之关系可见一斑。
8月7日访蔡元培、庄思缄*《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91页。。致傅增湘书,谈昨日与陈道人会晤后的看法,催促傅增湘加紧办理*《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290—291页。。8月8日王亮来访,说他父亲有道光三十年至光绪廿八年档案,问可否印行。张元济留两次先看。访林琴南。又至外交部访唐宝恒等人。8月9日拜会魏麟阁、梁伯祥、冯公度等人*《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91页。。8月10日拜会孙宝琦、夏循垍、董康、陈汉第、陈钧侯、陈懋鼎等人。8月12日访钱恂、叶恭绰。8月13日,致信王克敏,商借七种碑帖影印*《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92页。。8月14日白云观陈毓坤道人来谈影印《道藏》之事。8月15日访王芸阁。又访张一麐、徐子璋、谷九峰、马振五、蒋梦麟等人*《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93页。。8月19日午后三时,张元济与通艺学堂学生在中央公园茶叙,并照相。到者林胥生、郑沅、姚大雄、黄敏仲、林朗溪、夏循垍、雷曼卿、毛艾孙、戴芦舲、曾孟海、陈均候、陈懋鼎、郭啸麓、王书衡、吴鞠农、范赞臣、夏虎臣。8月20日访雷曼卿、汤尔和、黄敏仲、沈曾桐、方甘士、林胥生等人,并辞行。8月21日徐森玉来访,谈京沪两白云观借印《道藏》事。同日,拟成《道藏》契约,送傅增湘处。午后,偕孙壮、俞涤烦访福开森,观其所藏字画。午后拜会高子益、邓邦述、林彪、朱小汀、金兆藩、徐新六,并辞行*《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94页。。8月22日至24日,往访刘崇杰、伍连德、张君劢、蔡元培、董康、孙宝琦、辜鸿铭、庄思缄、宝熙、王宠惠、林长民、蒋性甫、史康侯、冯公度及北京大学陈独秀、胡适、夏浮筼、秦景阳、沈尹默、朱希祖、曾霁生、王克敏、叶恭绰、袁观澜、陈宝琛、蒋维乔等人,并辞行*《张元济全集·日记》第6卷,第395页。。8月25日离京返沪。
张元济这次大费周章的往返于京沪两地,除有影印《道藏》等既定之事外,会晤北京政学两界人物更是他两次北京之行的重点。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安排,基本达到了张元济的目的: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商务在我国出版业的地位,更是扩展及巩固了他本来极其良好的人脉,为商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应潮流而动铺下了坚实基础。甚至在不到一年之后的五四运动中,在最初应对失措的情况下,依然稳坐山头,巍然不动,这些都和张元济平时游走政、学、商三界上层是有莫大关系*参阅黄剑:《从消极到顺应:五四时期的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19—125页。。
北京政府时期军阀间混战不休导致政局混乱,商务印书馆虽受一定影响,但商务利用其庞大人脉圈,通过影印善本、出版大量学术书籍,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实力。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吴佩孚获胜后迫使徐世昌辞去总统一职。被迫下台的徐世昌与张元济一道,开始了他可传之名山的另一伟业。1922年12月14日,赵尔巽、康有为、李盛铎、张謇、田文烈、董康、熊希龄、钱能训、江朝宗、梁启超、黄炎培、张元济和傅增湘共13人,发起重印明版(道藏),撰发《重印正统〈道藏〉缘起》。卸任的总统徐世昌,因信奉道教,“概出俸钱,成斯宏举”,并请时任教育总长傅增湘总理其事。所用底本为北京白云观藏(道藏)原本,除将原本缩为石印六开小本,还将梵夹本改为线装本。自1923年10月至1925年6月,每四月出书一次,分六次出齐*《重印正统道藏》,《申报》1922年12月14日,第2版。。。张元济在这个时候接受徐世昌的资金印行《道藏》,也颇能说明他平日行事风格。张元济一直都喜欢与有同好的科班文人为友,无论其厕身于政、学亦或商界;也无论其党派、所谓新旧;更不管其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这也是张元济与袁世凯、蒋介石等既非功名也非高等学府出身的领袖始终不能融洽的缘故之一。
三、投资或助资
关于退位总统徐世昌捐出一年俸禄资助《正统道藏》印行的佳话自印行起流传至今。但随着近年商务印书馆散出大量档案,有人收集后提出不同意见,主要依据为傅增湘致张元济谈《道藏》印行信。全信内容如下:
敬启者:昔年增湘创议影印《正统道藏》,历时四载,奔走南北,譬解疏通,乃得定议,允假出照片。旋由东海助资,贵馆协力,卒以告成。惟当时事属创始,初无把握,故原预约只一百部。嗣目期满截止,已售去九十余部。深恐不敷分布,乃议加印五十部,然此后五十部系重制版,又多费矣。出版后三年,存书已全数售罄。近来中外人士及边远省份向敝处询问者日日不绝。肆间悬千金以求亦不可得,近且有出千五百金者,而在沪平两馆来购者亦复甚多。盖此百余部流布后,当世颇知此书之宏富深玄。西洋人尤重之,购求更亟。鄙意为时势之需要及学术之宣扬,此书宜早为重版印行,以副海内之望。拟请贵馆查取昔日合同,急议重印办法。其部数以二百部为限,仍发行预约。其价应酌增若干,以现时工价物料为准可也。至制版,则以原书重照,较初办,自可轻减若干。用款一节,初次由东海垫出二万五千元,目前如再请东海出资,恐亦非易。以彼高年,或不愿分神及此。目前假定开办之始需费三万元,拟由仆与贵馆各认其半。俟预约截止,款项收齐,或赢或绌,彼时再计分担之法或分任拆息亦可。至分配余利,则酌前次合同行之。以鄙意揣之,其有赢无绌,可以断言。缘此次再版,知此书之重要者必多,其订购踊跃必较上次为甚。若加以宣传之力,百余部可以坐致。此等良机,似不可失。敬祈台端会商决定,早日施行。如有未尽事宜或须面议者,鄙人可以来沪陈述,更为妥协也。此上菊生 拔可 云五 先生 傅增湘拜启 九月二十日*陈晓维:《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好书之徒》,第147—148页。
信件收藏者据此判断,徐世昌不是道藏印行的捐助者,而是投资人。为加强这一观点,还特意写到:
《道藏》印成之后,徐世昌和张元济为此书闹得颇不愉快。原因之一是徐世昌作为出版《道藏》的大股东,嫌张元济拖拉,多次通过傅增湘,催促其结算赢利,并分配余书。另一件事则是“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被焚毁。次年,商务打算重建东方图书馆,张元济给徐世昌写信,恳请其为新图书馆捐赠一部《正统道藏》。徐世昌却通过傅增湘转达了自己的意思:愿意捐赠一部自己编印的清人诗集《晚晴簃诗汇》,《正统道藏》则只能按照市场售价一千元出让。张元济对此大感意外,他当然不肯低头,就让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孙伯恒设法弄了一部。并特意写信告诉傅增湘“费银八百数十元”。比从徐世昌手里买,省了一百多元。*陈晓维:《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第153—154页。
其实根据《重印正统〈道藏〉缘起》当中说述“经东海徐公概出俸钱,成斯宏举。特与商务印书馆订约,专承印事。合并梵夹,改为线装。摹影校勘,三载克毕。海内宏达,尚垂察焉”*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第665页。,说的很明白,就是道藏的印行是徐世昌出钱,商务印书馆出力,到底是捐助还是投资,并不重要。而且徐世昌虽已退位,要专门通过印行区区一百五十部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书籍来牟利,似乎也大费周章。加上所发现的新材料中也只有两处提到“垫出”和“出资”两词,并未说明是投资还是捐助。至于结算盈利、分配余书,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行为。当时商务出版的研究著作,不仅要给付版税,即分配余利,也要分配给作者部分书籍。何况开初张元济对发行《道藏》前景并不看好,本来就希望徐世昌自己能够多收几套以解负担。
1923年4月15日,张元济致信傅增湘,云:“再《道藏》结算,共售出三十一部。希望尚有数部。但欲印百部,必须售出六十部,否则尚须垫本。尊处发出信件,务祈设法进行。今之阔人费去数百元真不过沧海之一粟,想此事总不至无希望也。”*《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314页。5月23日又云:“《道藏》已经开印,现又定出五部。印数壹百,售数总可望五十部。仍乞鼎力吹嘘。抽印单行本务乞代为一选,能得与精于此学者商之,尤妙。”*《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314页。8月1日,有信至“昨日孙伯恒兄寄来尊处代招购买《道藏》名单一纸。查单内已经购定者五户,尚未接各分馆报告者八户,业已专函往查。如尚未来买,除由分馆前往接洽外,再函达京馆。恳尊处设法催询,缘潭潭府第,分馆或未必能得门而入也。敝处实销,连尊处代招已购各户在内,共得六十部。私冀全书告成之日可望售去八十部。如此时局,如此书,可谓有成绩矣。今年十月出第一期,希望不致失约”*《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315—316页。。10月23日,“《道藏》预约共售出六十三部,后半印价当可足用”*《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317页。。
由此可见,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对发行《道藏》是否能够收回成本,一直都极为担心。张元济不得不频繁致信傅增湘,希望其以教育总长之尊为《道藏》推销。订下之后,还要催促傅增湘进一步落实到实处。直至真正销售出去,张元济才放下心来。当然,日后《道藏》大卖,出现了需要加印的局面,这是主事者始料不及的。但因为费用问题,在印行一百五十部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再度加印。
徐世昌出资出版《道藏》的意义在于,首先可以看出四民界限划分在民初已经不那么壁垒森严,仔细审视重印《道藏》的发起人,社会身份不是高官就是鸿儒,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士人从官场退出后转入商界的比比皆是,如张元济、张謇;以商界为跳板伺机再回政坛担任高官的就更多,商务内部就有王云五、朱经农等人。而且,一定要说徐世昌出资印行《道藏》是一种投资的话,不如可以看成是由于信仰使然或是保存文化的自觉。诸人在《申报》高调发表声明的原因,也是在于认为印行《道藏》此举重点不在于如何盈利,而是“宗教学术,所系重已”。以此书印行的数量及张元济一直担心这个项目能否收支平衡来看,印行此书本意在于赚钱的说法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根据前引用材料,张元济估算《道藏》要销出六十部才能保本,剩余四十部,以售价几百元来说,商务分文不取,徐世昌所得数目也不巨大。所以投资一说,显得颇为武断。。加之预订《道藏》能够拿到较低的折扣,1926年出齐之后,一般才按定价一千元发售。第一次印行一百部,后又加印五十部,一共一百五十部。这种情况也再度说明,当每部按照几百元预订,无论是否徐世昌出资,通过出版《道藏》而获利的层面都很小。如果明知极有可能亏本还注入资金的话,捐助的意味自然就比投资的说法要更站得住脚。
有关徐世昌与张元济因为《道藏》一事闹得不愉快一事,在《徐世昌日记》《张元济日记》及《张元济书信》中均未见有记载。1927年5月10日,张元济致书傅增湘,道:“承示近来纸张头尾厚薄不匀,《道藏》、《困学纪闻》两种订本尾低头高,一尺书差至两寸许,堆案既不耐观,插架更难齐整。此等弊病自不仅两书为然。幸荷指教,得以及早改良,感慨无既。”*《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341—342页。1927年6月30日,傅增湘有信致张元济,云:“东海印《道藏》总账重开已办好否?”*《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347页。张元济在此处有批注:“请梦翁带去面交,更易结束。”*《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347页。同年8月7日,张元济复信傅增湘时,也谈及此事:“《道藏》总账已催梦旦速办,带京面谈。”*《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348页。上述信件可以表明,至少直至1927年5月前不久,还在加印《道藏》,所以两人才会探讨装订美观的问题。8月,张元济已经指示高梦旦到北京与傅增湘面谈《道藏》总账一事。办事拖拉这种说法自是无从谈起。而且,直至国民政府正式上台之前,徐世昌在袁世凯死后,是北洋政府中担任总统时间最长的一位,平时素与张元济相友善。
张元济延展人脉的能力,非常人可比。他执掌下的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个商业与文化机构,也是个政治场所。从里面出来及收罗的政治人物,不知凡几,为人所熟知的有蔡元培、郑孝胥、王云五、陈叔通等人。所以在刚进入商务的茅盾眼中,商务印书馆本身也是个变相官场,以至于年轻时的他,不知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为何养那么多闲人*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前后》,《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45—146页。。陈叔通回忆他离开商务两年后,张元济等人一次就给他送了六千银元*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39页。。由此观之,无论是茅盾还是陈叔通,社会地位不知低徐世昌多少,张元济尚礼遇有加,更不会因少许资金开罪这北洋首脑。
张元济也是一个极为尊重学者及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人物。如1927年2月18日,张元济就《四部丛刊》再度发行时,沿用了初版本中采用傅增湘所藏底本一事,去信傅增湘,希望得到授权。当中有云:“敝馆印行《四部丛刊》初版之时,曾承台端慨借善本,至为感荷。此次再版,业已发售预约,次第开印。中有《颜氏家训》等八种,当时借自邺架,今拟仍以原本付照,俾免转展失真之弊。叨辱爱末,辄再奉商。别附目单,敬祈赐察。”*《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338页。由此可见,以张元济小心谨慎的性格,断不至于就少许金钱拖拖拉拉。
其后一事也可为此做个注脚。1930年4月10日,张元济与任鸿隽、江瀚、朱希祖、李宗侗、李四光、易培基、胡适、容庚、陈寅恪、陈垣、傅斯年、蔡元培、蒋梦麟、罗家伦、袁同礼、傅增湘等三十人联署刊发《国立北平图书馆刊行珍本经籍招股章程》,章程总共七条。当中第二条为:“开办费暂定为一万元。除由该馆筹拨一部分作垫款外,余由发起人先行认股,并求助于海内外之赞成者。”第三条为:“此项开办费共分二百股,每股五十元。同人及赞成者或认一股致数十股,均听人个人自便。”第四条为:“书籍印成后,其发行权及版权均归该馆。认股者均得按定价核析分书。如有认股而不愿分书者,尤拜高谊。”第五条:“前十集发售后,如有盈余,当再拟目续印他书,并续招新股,一如前例。”*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63页。这个章程中就明确了股东的股份只是分书,而没有收益,就算有盈余,又投入到再续印他书当中。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傅增湘与张元济解释,这次不太好让徐世昌出资的原因是:“用款一节,初次由东海垫出二万五千元,目前如再请东海出资,恐亦非易。以彼高年,或不愿分神及此。”可见股东分书确已坐实,但投资分钱或在其外。
虽然《道藏》的垫资人徐世昌笃信道家,但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印行此书的目的,在《重印正统〈道藏〉缘起》中已明确说明是“宗教学术所系重”。后来张元济在1929年12月15日复孙玉仙书时也再度解释:“影印《道藏》却为弟在商务印书馆时所主张,然意在存古,而不在于布教。”*《张元济全集·书信》第1卷,第516页。而且,由于在筹备印行《道藏》其间,日本人也已经着手做收集整理《大藏经》的准备工作,这对于中国学人来说,无疑是个刺激,加紧印行《道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道藏》的印行也直接促成了近代道教研究的兴起。
张元济以影印诸如《道藏》等经典善本、出版学术书籍为桥梁,邀请性质不一的政学商头面人物加入,一方面反映出作为出版人夹缝中求生存,不得不和各方势力都要有所交往的真实状况;一方面也显示了人脉圈子的庞杂高端,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商务得以长期垄断国内出版业的缘由。
四、结 语
王云五总结自1912年至1925年间商务成就时,有如下表述:“本馆印刷与编译各方面日益发展,出版图书多于前十年五倍,除继续编译中小学师范职业各科用书外,如世界丛书及各大学机关各科丛书之编译,为介绍新学理,供研究新文化者之参考材料;如四部丛刊、道藏、续藏之汇印,为流通精本或孤本古书,供整理国故者之参考材料。”*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27页。并总结:“民十五年前之革新运动,为中国旧文化之批判。民十五年后之革新运动,为中国新文化之发展。”*同上,第328页。王云五在这里说对中国旧文化之批判,应该是指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对固有文化的批判继承。
著名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张舜徽对张元济领导下的商务转型意见如下:“当张氏最初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时,着重译印政史技艺新书和编辑小学适用的最新教科书,后又大量辑印汉译世界名著和自然科学小丛书,大大推动了当时科学研究和科技事业的发展。这时,他在馆内已培养了一批组织和领导这些工作的后起之秀,可渐渐接替自己的任务。他感到整理古代文献,至为切要,非有旧学基础,不能动手,于是自己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这方面来。”*张舜徽:《中国文献学》,许昌: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305页。
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代经营重点开始转移,从发行教科书为主的单一型企业向既出版新知、又保存国故的新型现代化企业转变。作为转变过程中,尤其是整理国故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对《道藏》重版印行的梳理研究可以发现张元济与民国时期的政学商界各方势力的交往历程,这不是一个单独的案例,反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从中可以检视、发现由此展开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标签化历史认知的差异。
(责任编辑 杨海文)
B26
A
1000-7660(2017)03-0139-09
黄 剑,江西大余人,历史学博士,(广州510631)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