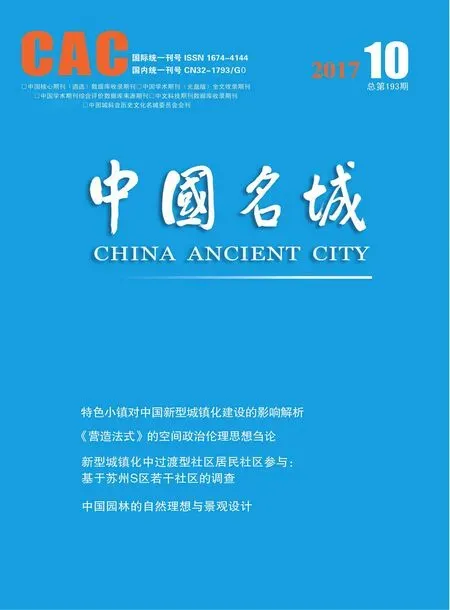略论文化景观与我国名城保护
赵献超
略论文化景观与我国名城保护
赵献超
将文化景观置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之下考察,指出文化景观是遗产保护观念扩展的产物,作为一种“遗产观”,它是认识和研究文化遗产的新的视角。同时,梳理了文化景观的重要类型——城市历史景观产生和发展的国际动态与趋势,指出城市历史景观在“方法论”层面的意义。结合我国城市遗产保护的现状,展望了未来城市历史景观的研究与实践。
文化遗产;文化景观;城市历史景观;城市遗产;历史文化名城
近年来,“景观”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词汇。如果从1992年“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算起,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一个特殊类型已经存在二十余年。而1996年庐山作为文化景观被世界遗产专家认可,“第一次将‘文化景观’这个词汇带入了中国遗产界”[1],中国遗产界对于该种类型文化遗产的争论也持续了将近二十年。2011年11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采纳了《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以下简称《建议书》),试图将城市历史景观(HUL)作为认识城市遗产的“遗产观”和处理遗产保护问题的“方法论”推向全世界。
《建议书》的采纳“标志着文化景观在遗产保护领域首次进入城市历史遗产保护领域”[2],尽管并未解决文化景观一词“概念不清晰、目的不明确、外延多交叉”[3]的弊端,而历史城市景观这一术语更是“有歧义甚至是误导性的,如果用它来实现交流的目标,其效果是无法令人满意的”。[4]但是回顾文化景观这一概念进入遗产保护领域以及近几十年的发展,审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新变化与新趋势,对我们的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都是有益的启示。
1 从历史纪念物到文化景观
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经历了从对单个建筑或建筑群的保护,到对历史建筑、建筑群及周边环境的保护,再到历史街区、历史城镇的保护的转变,并经历了从对静态的物质实体的保护到人与环境相结合的动态的保护的转变。遗产的内涵被扩展的同时,保护手段也逐步更新,文化景观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国际遗产界景观运动的蓬勃发展,是遗产观念发展的结果。
1.1 从“历史纪念物”到“建筑群”
1931年,第一届历史纪念物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雅典通过了《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The Athens Charter for the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Monuments,简称《雅典宪章》),在这份“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份重要的国际文献”①中,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保护历史性纪念物(Historic Monuments)的“共识”②。
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种国际共识的同时,保护观念也在不断发展。在二战后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文物建筑及其周边环境受到破坏的形势下,“一些已经并在继续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问题已越来越受到注意,并展开了紧急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简称《威尼斯宪章》)于1964年应运而生,《威尼斯宪章》开篇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这不仅适用于伟大的艺术作品,而且亦适用于随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过去一些较为朴实的艺术品”,至此,保护的范围从单个的纪念性建筑扩大到对周边环境的保护,文物古迹的概念也从具有纪念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伟大”的艺术品扩展到具有“文化意义”和“历史见证”的“较为朴实的艺术品”,遗产涵盖的范围更加多元化。
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义中提出了“建筑群”的分类,在同时通过的《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古迹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由时间和人类所建立起来的和谐极为重要,通常不应受到干扰和毁坏,不应允许通过破坏其周围环境而孤立该古迹”,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意义;同时建议对建筑群的保护、保存、展示和修复应制定计划,“包括边缘保护地带、规定土地使用条件并说明需要保护的建筑物及其保护条件”。
1987年修订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简称《操作指南》)中,“城镇建筑群”(Group of Urban Buildings)成为新的世界遗产类型。该版《操作指南》进一步将其分为三类:无人居住的城镇、有人居住的历史城镇、二十世纪建设的新镇,从对具体类型的阐释来看,所谓城镇建筑群的重点不在“建筑群”而在“城镇”,故而2005版的《操作指南》将之替换为“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Historic Towns and Town Centers),尽管只是名称上的改变,对“建筑群”的相关保护观念影响之深刻可见一斑。
1.2 从“建筑群”到“历史城镇”
自《世界遗产公约》将“建筑群”作为世界遗产的一个重要类型,并强调“修复地区与城市周围发展之间有何关系”以来,对城市遗产的保护也经历了从狭义的建筑群到广义的城市遗产的转变。
1975年召开的欧洲建筑遗产大会通过了《阿姆斯特丹宣言》,认为“建筑遗产不仅包括品质超群的单体建筑及其周边环境,而且包括城镇乡村的所有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地区”,故而将“历史城镇、城市老的街区、具有传统特性的城镇和村庄以及历史性公园和园林”纳入建筑遗产的范畴,认为这种整体性保护的思路“是对单独保护个体纪念性建筑和场地的一个必要补充”③。
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内罗毕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afeguarding and Contemporary Role of Historic Areas,简称《内罗毕建议》),将历史地区及其环境(Historic areas and their environment)视为不可替代的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内罗毕建议》所谓的历史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以“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应的古迹群”为主要构成内容。《内罗毕建议》指出,“每一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应从整体上视为一个互相联系的统一体,其协调及特性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联合,这些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因此一切有效的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对整体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该建议不仅要求积极保护历史地区及其环境,而且要求“其所在国政府和公民应把保护该遗产并使之与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作为自己的义务”。《内罗毕建议》将保护的对象进一步拓展到“区域”的范畴,保护的对象也不再是冷冰冰的物质躯壳,而是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各有效组成部分互相联系的统一体;同时强调“保护与修复工作应与振兴活动齐头并进”,以满足居民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需要,强调了保护的“当代作用”。
为应对因工业化而导致的历史城镇与城区遭到的“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Towns and Urban areas,即《华盛顿宪章》),该宪章涉及的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而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意味着这种城镇和城区的保护、保存和修复及其发展并和谐地适应现代生活所需的各种步骤”。《华盛顿宪章》“提出了现在学术界通常使用的历史地段和历史城区的概念”[5],并进一步明确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的方法与手段,明确指出“为了更加卓有成效,对历史城镇和其它历史城区的保护应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完整组成部分,并应当列入各级城市和地区规划。”
1.3 文化景观所体现的“遗产观”
遗产界文化景观的概念源自“乡村景观”(Rural Landscape)④,是对西方遗产领域“遗产的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相互孤立这一现象”[6]的一种反思和回应。经过近十年的探讨,世界遗产委员会从地理学领域借用了“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s)这一概念指代一类代表着“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的文化遗产。1992年在美国圣菲(Santa Fe)召开的第1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意将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在1994年及以后版本的《操作指南》中,明确了文化景观的定义与类型⑤。
但是由于景观这个词本身“确切含义的不确定性使对这一概念的误解存在至今”[7],而《操作指南》中对文化景观的定义和分类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对文化景观的定义、分类、标准非但没有渐趋统一,其争论反而日趋白热化。”[8]200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简称《会安草案》)中,与会专家就文化景观的定义做了调整⑥,并在“框架性概念”下指出“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会安草案》同时指出,“一处文化景观可以包括纪念物。但无论是否包含纪念物,文化景观本身都是需要加以保护的基本因素。”
通过对文化景观相关官方表述的解读,笔者认为,文化景观概念的引入,不仅是对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分离进行的弥合尝试,更是将遗产观念扩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作为历史见证的单体建筑、建筑群、历史城镇和城镇区域固然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多种要素(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动态演进的区域、有人居住或劳动其间的活态空间也被纳入了遗产的范畴,文化景观的概念体现了物质空间和非物质要素(以及场所精神?)的结合。在文化景观的视野下,发展的地位和作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 城市历史景观
文化景观的活态的、物质空间与非物质要素结合的、动态演进的、注重发展特点,使得人的活动最集中、包含要素最多样、正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且发展的诉求最为强烈的城市空间成为国际遗产界景观运动的重要阵地。
2.1 城市遗产保护领域对文化景观的采纳
2005年5月,为响应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上的要求,一场名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会上讨论了一整套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重要准则和方针,形成了《维也纳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Vienna Memorandum on “World Heritage and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 Managing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即《维也纳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近十年来,文化遗产的含义有所扩展,其解释更为广泛,引导人们认识到人与土地的共生共息以及人在社会中的作用。这就要求在所辖范围内采取新的方式方法来保护城市,发展城市。”(第十条)而城市历史景观⑦“植根于当代和历史上在这个地点上出现的各种社会表现形式和发展过程”(第八条),是“自然和生态环境内任何建筑群、结构和开放空间的整体组合”(第七条),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和保存既包括保护区内的单独古迹,也包括建筑群及其与历史地貌和地形之间的在实体、功能、视觉、材料和联想等方面的重要关联和整体效果”(第十二条)。城市历史景观将城市区域内的“功能用途、社会结构、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持续变化”(第十三条)作为城市传统的一部分,着眼于城市整体,“通过高质量的干预措施使文化得以延续”作为最终目标。可以看出,城市历史景观是文化景观在城市领域的再现,是文化景观视野下对城市遗产的重新认识与解读。
随后,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导下,举办了一些列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会议、论坛和讨论⑧。经过6年的讨论与完善,终于在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以下简称《建议书》)⑨,将城市历史景观“作为一种保存遗产和管理历史名城的创新方式”推向全世界。
2.2 不仅是遗产观,更是方法论
城市历史景观作为认识城市遗产的新视角、保护城市遗产的新方式,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2.2.1 保护的对象是更全面的“城市遗产”
在城市范围内,以前强调对“历史城镇”、“历史街区”或“历史地区”的保护,对“历史性”过分关注,保护对象往往是城市的局部。甚至2005年的《备忘录》主要针对的还是“已列入或者申报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历史城市,以及在市区范围内有世界遗产古迹遗址的较大城市”(第六条)。而《建议书》将适用对象扩展到所有的“城市遗产”(Urban Heritage),在官方表述中,“城市遗产”包括以下三类:1.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遗迹;2.并不独特但以协调的方式大量出现的遗产要素;3.应考虑的新的城市要素(例如:城市建成结构;空地、街道、公共空地;城市基础设施、重要网络和装备)。这样的扩展,不仅对于价值不突出的历史城区、或未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历史城区具有重要意义[9],而且将“新的城市要素”纳入保护框架之下,是文化景观“活态”与“发展”理念的体现。
2.2.2 城市历史景观方法
《建议书》明确了城市历史景观的定义:“是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其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第八条)⑩从该定义可以看出对相关学术领域——尤其是城市形态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10],较之此前出现的任何关于文化景观的定义或概括都更为精准。
城市历史景观的要素涵盖了城市中所有相互作用的要素,包括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历史与当代、有形与无形,各要素在城市空间内多层次地积累变化,是“活的城市的动态性质”的体现,也体现了“从主要强调建筑遗迹向更广泛地承认社会、文化和经济进程在维护城市价值中的重要性这一重要观念的转变”。
城市历史景观的提出是为了应对因人口迁徙、全球市场的自由化和分散化、大规模旅游、对遗产的市场开发、气候变化、大规模城市化和失控的城市发展等对城市造成的压力,也是对过去所采取的“主题公园”式的保护方式造成的保护区域与整个城市割裂的反思[11],力图“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内以全面综合的方式识别、评估、保护和管理城市历史景观打下基础”(第十条)。
城市历史景观“作为一个整合建成环境保护政策与实践的工具……目标在于确立一系列的操作原则,保证城市保护模式能够尊重城市不同历史文化脉络的价值、传统及其环境,帮助重新定义城市遗产在空间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12]
3 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启示
正如景峰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面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新动向,如何在城市建设中充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景观,以体现历史名城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风貌,这是我们每一个爱护、关心人类家园的人都应该深深思考的问题。”[13]
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等,呈现一种“粗放型”的城镇化模式[14]。具体到历史城市领域,保护与发展仍是需要协调的一对矛盾:保护对象往往是局部,与城市整体的联系较弱;试图将保护对象凝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保护与社区发展、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仍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
自1982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开始,后经多年的增补合并,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数目前已达131座,并逐步形成了名城保护体系。这一体系“由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三个部分组成”[15]。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保护的三个层次即为:文物的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前两个层次相对较易实现,而名城的总体保护则鲜见成功的案例。针对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大多数地方只是被动地保护一些孤立的建筑或建筑群的现象,徐苹芳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上要保护中国特有的古代城市规划的遗址遗痕,才能体现出中国古代城市的格局和风貌。历史街区只是局部。我们不能捡芝麻丢西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舍整体保局部是片面的做法,在中国历史文化名称保护中是不可取的。”[16]另外,一些地方在城市开发过程中,肆意破坏旧城格局,使一些很有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变成“毫无特色的普通城市”[17],从而造成“千城一面”的悲剧。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在对待历史文化名城时存在急功近利的心理,打着“旧城改造”的口号进行了不少“建设性破坏”;另一方面是由于基础研究的不充分,不能正确认识古城的格局和在城市建设史上的地位。城市历史景观(HUL)注意到城市区域内“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的层层积淀”的特点,强调“以全面综合的方式”对其进行识别与评估、“针对城市住区复杂的层积现象进行研究”,这和相关学术领域强调在保护过程中加强古代城市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对每个历史文化名城本身的历史和古代城市规划特点的研究,减少在保护管理工作中的失误和盲目性”[18]的要求是相契合的。城市考古领域对古今重叠型城址的个案研究以及与方法论问题相关的阐述对相关城市的基础研究是有益的启示,“我们需要将古今重叠型城市从动态发展的角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注意与城市发展有关联的所有遗迹现象”[19]的同时,还应该扩大文物部门在古城保护与发展中的作用。
另外,城市历史景观在诠释保护战略时采用了宽视角的方法来分析历史聚落和城市,“这一方法促进了更广泛的学科融合,如对地貌学、自然环境和对非物质方面的考虑,这种融合将引导对城市历史价值多样性的更综合、更包容的理解,并对其加以保护”[20]。在城市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多学科的互相借鉴与合作越来越成为发展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机制的建立绝非朝夕之功,《世界遗产公约》即强调将遗产保护整合到综合发展规划之中,城市历史景观是这种理念的延续与发展,如国际遗产专家指出的那样:“未来的挑战是发展这种新工具,使之成为历史城市整体管理方法的有效基础,并且适用于全球不同的地理文化环境”[21],如何使之真正成为行之有效的工具仍处于探索实践之中,希望更多学人能够积极投身城市遗产保护领域中来,在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中贡献自己的才智。
注释:
①本文如无特殊说明,相关保护文件的内容皆引自国家文物局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②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曾指出:《雅典宪章》规定的“古代建筑的保护与修复指导原则在国际上得到公认……为一个国际运动的广泛发展做出了贡献”。
③《阿姆斯特丹宣言》原文见:http://www.icomos.org/en/charters-and-texts/179-articles-en-francais/ressources/charters-andstandards/169-the-declaration-of-amsterdam,译文见:http://www.iicc.org.cn/Info.aspx?ModelId=1&Id=283。
④乡村景观的曾出现于1988和1992年版的《操作指南》中,反映了1992年以前对景观的界定还处于讨论阶段,这两个版本的《操作指南》认为:With respect to rural landscapes,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the Committee has recommended further study so as to help develop Guidelines for determining which properties in these categories may be considered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操作指南》的历次版本参见 http://whc.unesco.org/en/guidelineshistorical.
⑤文化景观的定义和分类自1994年在《操作指南》中被明确以后,一直延续至今,只是在《操作指南》的出现方式有所调整。2005年以后的《操作指南》在附件中对文化景观的定义与分类如下:……6.文化景观属于文化遗产,正如《公约》第一条所述,它们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共同杰作”。文化景观见证了人类社会和居住地在自然限制或自然环境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进化,也展示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外部和内部的发展力量。7.文化景观选择的依据包括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在特定地理文化区域中的代表性,以及体现这些地区核心和独特文化元素的能力。8.“文化景观”一词包含了人类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之间互动的多种表现。9.考虑到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局限性和特点,文化景观通常能够反映可持续性土地利用的特殊技术,反映与大自然特定的精神关系。保护文化景观有利于将可持续性土地使用技术现代化保持或提升景观的自然价值。传统土地使用形式的持续存在支持了世界大多数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因此,对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也有益于保持生物多样性。10.文化景观主要可以被分为以下三类:(i)最易识别的一种是明确定义的人类刻意设计及创造的景观。其中包含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不总是)与宗教或其它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相结合。(ii)第二种是有机演进的景观。它们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这种景观反映了其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的进化过程。它们又可分为两类:-残遗(或化石)景观,它代表过去某一时间内已经完成的进化过程,它的结束或为突发性的和渐进式的。然而,它的显著特点在实物上仍清晰可见。另外一种是持续性景观,它在当今社会与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密切交融中持续扮演着一种积极的社会角色,演变过程仍在其中,而同时,它又是历史演变发展的重要物证。(iii)最后一种景观是关联性文化景观。将这一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因为这类景观体现了强烈的与自然因素、宗教、艺术或文化的关联,而不仅是实体的文化物证,后者对它来说并不重要,甚至是可以缺失的。中文译文摘自《操作指南》2013版:http://www.icomoschina.org.cn/pics.php?class=22 。
⑥《会安草案》中对文化景观的定义和分类如下: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
文化景观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可能彼此重合:其中最容易界定的就是由人类有意识设计和创造的有明确定义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目的而建造的园林景观。这些景观一般(但并非绝对)与宗教建筑和建筑群有关。
第二类文化景观是指有机演变而成的景观、遗迹或生活景观。该景观源自某一社会、经济、行政或宗教动机,通过与自然环境的联系及对其所做出的反应发展成为当前的形态。这一类景观在其形态和组成特征上反应出了其演变过程。
最后一类文化景观是关联性文化景观。此类景观的价值在于与其自然因素有关的强大的宗教、艺术或文化内涵,而不是在于其实质性的文化迹象。后者可能微乎其微,或者根本不存在。
⑦即Historic Urban Landscape(HUL),对其有“历史性城市景观”(《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历史城市景观”(《中国历史城市景观保护发展报告(2013)》)、“历史名城景观”(郭旃.遗产保护新热点:管理历史名城景观[J].中华遗产,2005(4):13.)、“历史性城镇景观”、“城市历史景观”等多种翻译,本文采用其官方译法“城市历史景观”。
⑧ Francesco Bandarin,Ron van Oers,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Managing Heritage in an Urban Century,Wiley-Blackwell,2012.P63
⑨ 中英文建议书见: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48857&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⑩上述更广泛的背景主要包括遗址的地形、地貌、水文和自然特征;其建成环境,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其地上地下的基础设施;其空地和花园;其土地使用模式和空间安排;感觉和视觉联系,以及城市结构的所有其他要素。背景还包括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做法和价值观、经济进程以及与多样性和特性有关的遗产的无形方面。(第九条)
[1]韩锋.探索前行中的文化景观[J].中国园林,2012(5):5-9.
[2]韩锋.城市历史景观——概念、视野及机遇[C]//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世界遗产保护杭州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城市景观保护发展报告(2013).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14-19.
[3]孙华,杨爱英.“文化景观”遗产的有关问题——兼论历史城镇和传统村落的保护[C]//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华构重彩——纪念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80周年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技术国际研讨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65-81.
[4]彼得·H·古德柴尔德.历史城市景观的实际应用:基本原则[C]//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世界遗产保护杭州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城市景观保护发展报告(2013).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20-36.
[5]赵中枢.从文物保护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概念的扩大与保护方法的多样化[J].城市规划,2001(10):33-36.
[6]史艳慧,代莹,谢凝高.文化景观:学术溯源与遗产保护实践[J].中国园林,2014(11):78-81.
[7]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 地理学思想史[M].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3.
[8]韩锋.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及其国际新动向[J].中国园林,2007(11):18-21.
[9]郑颖,杨昌鸣.城市历史景观的启示——从“历史城区保护”到“城市发展框架下的城市遗产保护”[J].城市建筑,2012(8):41-44.
[10]怀特汉德,宋峰,邓洁.城市形态区域化与城镇历史景观[J].中国园林,2010(9):53-58.
[11]罗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城市历史景观保护计划”负责人吴瑞梵:城市保护要为城市的未来发展作贡献[N].文汇报,2014-4-28(9).
[12]罗·范·奥尔斯,韩锋,王溪.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及其与文化景观的联系[J].中国园林,2012(5):16-18.
[13]景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稿)及其意义[J].中国园林,2008(3):77-81.
[14]国家发改委.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5]赵中枢.从文物保护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概念的扩大与保护方法的多样化[J].城市规划,2001(10):33-36.
[16]徐苹芳.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古代城市规划及其保护[J].文物,2001(1):64-73.
[17]佚名.徐苹芳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N].中国文物报,2003-6-1.
[18]徐苹芳.要废除“旧城改造”的思路[J].建筑创作,2003(11):160-161.
[19]杭侃.古今重叠型地方城址的考古方法刍议[C]//中国考古学会,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20]罗·范·奥尔斯,韩锋,王溪.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及其与文化景观的联系[J].中国园林,2012(5):16-18.
[21]莫妮卡·卢思戈,韩锋,李辰.文化景观之热点议题[J].中国园林,2012(5):10-15.
Through examining the conception development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during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ultural landscape is the outcome of the evolution of heritage preservation,and that cultural landscap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study.In the meantime,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new trends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HUL) in the world and to make a point that HUL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actice of heritage protection.Through a discussion of the situation of historic cities in China,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HUL should be studied and practiced more in the future.
Cultural Heritage ; Cultural Landscape ;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 Urban Heritage ; Historic City
C912
A
1674-4144(2017)-10-14(6)
赵献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蒋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