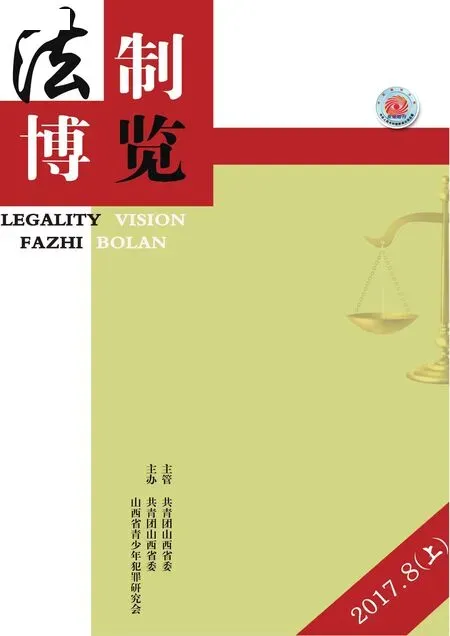探讨洞穴奇案背后的法律困境
孟丽敏
江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探讨洞穴奇案背后的法律困境
孟丽敏
江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洞穴奇案暴露了人类理性的局限,在此之前,人类在理性与感性相矛盾之时,往往能够在法律推理与期待的正义中找到某个中和点,冲突的利益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某种妥协。而在洞穴奇案中,其复杂情形使得无论是有罪判决还是无罪判决甚至是拒绝裁判都具有可被诟病之处,穷尽14个不同法官的选择与观点也无法达成一个完全合理完善的结果,其中所展现的缜密逻辑、精确叙述和蕴含的不同的对于法律价值与思想的探讨,都值得我们深思。
洞穴奇案;法律困境
富勒的洞穴奇案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例,其笔下的五个最高法院法官从不同的纬度精确叙述了复杂的案件事实及多样的法律推理,在此基础上,彼得·萨伯探索了关于此案的九个新观点,环环相扣、逻辑严密,九位法官在论证上同样有力且都忠于法律,却展现了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现了思维的逻辑性与多元性。我想,读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最后第六个涉案者的结局,或是哪一种观点是更为正确的,而应是其中所体现的法律困境与迥异却卓越严密的不同法理方向,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取舍、权利与功利之间的权衡、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博弈,公平正义、道德人情,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难题。
一、案情回顾
纪元4299年5月上旬,5名洞穴探险者受困山洞,食物供给断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在得知十天内救援队伍无法成功进入山洞后,探险者们决定抽签杀死一人,吃掉他的血肉以维持另外4个人的生命。威特莫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他4人仍执意抽签,恰好选中了威特莫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4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院判处绞刑。后4人上诉至纽卡斯国最高法院。富勒在1949年的原始版本故事中,虚构了4300年5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五份判决意见:两票有罪,两票无罪,另一位大法官退出裁判,结果是维持原判。
富勒去世半个世纪后,美国叶尔汉姆学院哲学教授彼得·萨伯以富勒的原始版本为基础,假设50年后洞穴探险者案因遗漏的第5名罪犯归案被审判(假设实际上有6名洞穴探险者)而有机会翻案,虚构了4350年另外9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9份判决意见:4票有罪,4票无罪,另一位大法官回避裁判,结果仍然是维持原判。
二、洞穴奇案背后的法律困境
(一)为了多数人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否道德
在洞穴奇案中,体现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权利与功利之间的取舍,四个人的生命权利与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孰轻孰重。塔利法官认为一命换多命是一项划算的“交易”,并且举了一个例子:假定杀一个人是为了避免一百万人的死亡,情况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改变,至少对大多数人的直觉来说,会毫不迟疑地让志愿者们为了就一百万人而牺牲自己。这样的观点中蕴含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论,即提倡效益主义,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在这个例子里,牺牲的志愿者是英雄,是高尚的行为,甚至是被世人追寻的“英雄”标签和道德高地的压迫而做出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应该”的合理行为,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要求别人做出这个牺牲。如特朗派特法官所说,杀人永远不是划算的交易。
哈佛公开课的教授曾描述过这样一个情境:如果你是一列火车的驾驶员,在驾驶的过程中,你发现有三个小孩在火车道上玩耍,两个小孩在标有“此处危险,严禁逗留!”的火车道上,而第三个孩子则是在没有任何标识、废弃的火车道上玩耍,而火车正在向第一个道上行驶,火车无法停止,如果你可以勇操纵杆把火车选择变化轨道驶向那条废弃的轨道,你会怎么抉择?此时大多数人选择了去撞向那一个小孩,因为人们惯性以数量来衡量和比较,就如同洞穴奇案中塔利法官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然而,因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严重时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如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曾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施行恐怖统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纳粹犯下种种罪行时也是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口号。
那么假设这样一种情境,如果这五个人中,威特莫尔是学术极其成功的科学家,能够为社会带来极大的贡献和价值,而其他四个人是街边的流浪汉甚至是穷凶极恶的罪犯呢,人们的天平是否又会倾向于不应该让威特莫尔来做那个牺牲者?如若宣扬这样的功利比较价值观,那是否校园群体霸凌时应当坐视不理、具有更高社会价值的人拥有侵犯他人人权的权利?无论以粗暴的生命存活数量,还是以个体的社会价值来衡量一个人生命权利的消亡,都是忽略了人权的平等性。桑德尔说,首先人权,是连你自己都不能侵犯、交易的。在我们成为社会人、被贴上种种标签之前,我们首先拥有的是人权,这是作为一切社会人的前提和基础,而人权是无法进行比较与交易的。
(二)即使以自然法来评判也不应是无罪
在洞穴奇案中,福斯特法官提出了自然法的观点,他认为,各个法律分支追求的所有目标的根本指向都在于促进和改善人的共存状态,调节共存状态下相互之间关系的公正和平等,当人可以共存的这一状态不复存在,支撑我们整个法律秩序的基本前提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作用,当威特莫尔的生命被剥夺时,他们并非处在“文明社会的状态”,而是处在“自然状态”,因此应当遵照他们所建立的新的契约来裁判。
然而,在他们建立这一契约之前,他们依旧与外界有着联系,甚至之后的失联也是他们自愿选择了拒绝与外界联系,何况如唐丁法官所说,如果这些人超出了我们法律的约束到达了“自然法”的管辖范围,那这种超越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当洞口被封住的时候还是饥饿的威胁大到某种难以确定的程度,抑或是掷筛子的协定达成之时?这些不确定性使得这个自然法的状态能否得到承认成为了一个问题。
然而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即使此时他们的状态应按照自然法来判断,以新的政府宪章即掷色子这一契约来衡量,那么这个契约是否达成了呢?威特莫尔在掷色子之前是沉默的,但是被同伴强行代为投掷,对于此处的沉默是否可以足以征表威特莫尔的态度,即特莫尔明白无误得收回了他的同意行为,是不赞同的,至少并不赞同在那个时间点上以投掷色子来决定哪一个人应当被牺牲,花费大量时间讨论抽签公平的数学问题本身即表明这项程序必须是公平的而且必须为每一个人所赞同,那么即使另外四个人强制投掷骰子,契约也依旧没有达成,被告便需对自身的杀人行为进行负责。
(三)理性与情感之间的斟酌
法律与道德、情感、伦理、生命之间的牵绊困扰着人们中的判断。吴经熊先生有一段关于律法与爱的阐述:“平等胜于严法,精神胜于文字,仁慈胜于正义。没有人比我更欣赏罗马人的格言了:‘最高的正义也是最大的不义。’”如果法律失去了平等、仁慈,只是机械的遵循它的文字而忽略了内在精神,那么法律可能是冷酷的甚至是残暴的。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法律的平等和仁慈应体现在量刑中,而不是罪与非罪的区分上,但是这个案件的设置并没有给予我们考虑量刑的空间。
在这个案件中,困扰阻挠人们的,是身处绝境下的艰难使人心生同情,从而模糊了事件的本质。就像去年六一儿童节的一条新闻:妈妈为给孩子过一个儿童节而去超市偷鸡腿,群众的目光聚集在母爱的伟大和生活的艰难而纷纷捐款,而忽略了这位母亲本身的偷窃行为,人们往往以并没有主观恶性来为犯罪者开脱,他们主张的理由往往是那个看起来非常公平的抽签办法以及绝境下不得不求生的人类本能。但是这并不能就此忽视了无辜的受害者,并不能忽视法律人思考法律的严肃性和生命的价值。罪刑法定的原则应该被严格遵守,生命的价值应受到最高的尊重。因此,我同情被告,也许是他们的不走运,好像恰巧被禁锢在“一定会犯罪”的怪圈中,但我的理性依然坚持他们的确是故意杀人。
D
A
2095-4379-(2017)22-0150-02
孟丽敏(1996-),女,汉族,江苏苏州人,江南大学法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