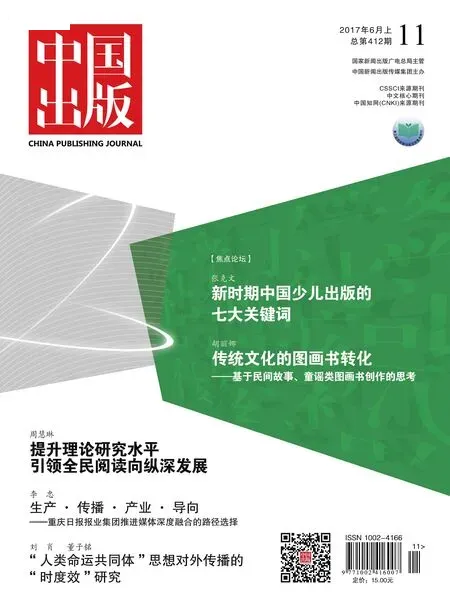均等化视域下流动儿童阅读推广障碍与对策研究*
□文│倪 妍
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加速,大量的乡镇、农村人口为了建设城市、完成城市梦进城打工。而经济发展、信息发达等带来的交通便捷,更让城市与村镇之间的人员流动逐年增速。随着人口流动不断增速,随迁子女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2016年教育部发布的《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明确定义,流动儿童是指户籍记录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的乡村,随务工父母到流入地的城区、镇区(同住)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1]
根据《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数据显示,流动、留守儿童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已接近1亿人,让公共服务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2]为使流动儿童享有与城市儿童均等的生活和教育条件,2006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陆续发起的“圆梦行动、快乐阅读、希望厨房”、2007年南都公益基金成立的“新公民计划”、2017年3月28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新公民计划发布的“流动儿童蓝皮书”等一系列流动儿童阅读推广活动旨在改进流动儿童生活学习环境,让他们享受均等、优质、健康的教育与阅读环境。
一、流动儿童阅读均等化服务现实意义
联合国关注我国流动儿童近况:“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在2010年城镇地区每4个孩子有1个是流动儿童。到2013年,比例上升为每3个孩子有1个是流动儿童。”[3]作为未成年人的流动儿童,正处于身心成长、知识储备、道德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需要家庭、学校、政府、社区、公益组织给予更多的关爱。均等化地进行流动儿童阅读推广,不仅可以促进流动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关系着国民素质的提高、教育公平的实现、城市化的推进以及社会的长期稳定。[4]
1.均等化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保障
均等化的本质是要平等、公平地实现教育。当代均等化研究专家约翰·罗尔斯说过公平三原则:“同等自由原则、机遇均等原则、差别原则。”[5]他提出发展机会应向所有人开放,不应只给某一部分人,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保障大众公平、平等的利益和权利。
我国的专家也提出均等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李国新指出,阅读推广应以普遍均等、惠及全民为目的,以均等化体现公平正义。[6]蒯大申认为,均等化的政策目标旨在均等城乡、区域之间的配置,缩短地区、城乡、群体之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差距,保证全部社会成员拥有平等、均等的文化服务。[7]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民阅读”列入其中,从2014~2017年连续4年将其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由原来的“倡导”发展为“大力推进”。作为我国推广阅读均等、推进阅读公平、提高群众素质的文化强国工程,足以可见政府倡导均等化阅读推广的努力和决心。2017年3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规划中指出要以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为要求,加速提高大众的精神文化素养。[8]
2.均等化促进流动儿童阅读推广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期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平均每年增长600万人左右,2014年末达2.53亿,2020年预计将增长到2.91亿人。[9]伴随加速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人口流动数据更将连年攀升,流动儿童势必成为极其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何实现平等、公正的全民教育,让流动儿童能共享阅读推广的均等教育权利是业内专家一直关注的焦点。
在全国各省市的积极努力下,流动儿童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有了显著的改善,均等化进行流动儿童阅读推广,能有效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公正地发展。2017年3月15日云南省发布的《云南省2017年全民阅读工作实施方案》提出,有效地保障流动儿童的基本阅读权利。早在2012年,浙江省嘉兴市着力打造城乡一体、均等公平的服务体系,用“文化绿卡”让流动儿童与本地居民之间实现身份与机遇均等平等。针对流动儿童群体组织的阅读推广活动,活动设计要契合他们,让他们享受阅读的乐趣和知识的力量,形成自发的阅读活动,养成较好的阅读习惯。
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流动儿童教育、阅读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我们需要加快阅读推广的步伐,切实做到均等、平等、公正的社会服务,为建设文化强国和社会文明发展提供积极的保障。
二、流动儿童阅读推广障碍因素分析
阅读推广的重要对象是儿童和青少年。而儿童、青少年阅读习惯的培养要从小养成。热爱阅读,能够让他们憧憬未来,同时具备自主、有益、终身的学习能力。
1.阅读推广主体对流动儿童的忽视
我国的儿童阅读仍存在人均阅读资源有限、城乡差距明显、阅读目的性较强、阅读推广不平均等问题。其中,流动儿童中存在的问题更突出。这不仅影响阅读推广的成效,更会阻碍流动儿童阅读权利均等的实现。
均等化视域下的阅读推广主体呈现协同合作的多元趋势,从国际阅读协会(IRA)、各国政府等到出版发行界、民间公益组织、图书馆、学校等陆续推出阅读推广活动。作为活动策划机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推广主体,在进行阅读推广时,为了推广效果较好呈现,会选择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氛围较好的公办或私立学校开展活动,而流动儿童学校及社区开展的活动较少。流动儿童的父母工作辛苦,孩子普遍交给老人照顾,或经常随父母工作地迁移流动,孩子对知识、阅读的渴求被忽视,导致了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间的信息差距越来越明显。
2.流动儿童父母缺乏对阅读的认知
在进行流动儿童阅读推广时,我们强调国家政策法规、学校学习教育、社会公益力量的同时,要注重流动儿童父母对流动儿童阅读的关心和警悟,重视家庭教育的正面影响和引导成效。
从农村迁移城市的流动人口,对教育的认知虽受到了城市文化的浸染,但整体的家庭生活习惯和行为仍保持着农村的传统模式。流动儿童家长因为工作的压力等因素,往往只关注孩子的学校教育,而忽视了阅读对孩子身心成长的积极引导作用,缺乏对阅读的认知。另外大部分流动儿童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自身文化素养不高、鲜少阅读,家庭阅读氛围无法营造,这些都导致了流动儿童阅读推广活动难以有效开展。
3.公共阅读空间未被流动儿童有效利用
大部分的流动儿童受家庭等因素的影响,他们重视课内课程,而鲜少进入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当然公共阅读空间也存在自身宣传不足等问题,大部分流动儿童的父母是从乡镇、农村来到城市的,生活圈子窄小,日常沟通的话题也多与工作有关,对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基本没时间、没精力投入参与,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导致他们社会信息获取有限。而传统公共阅读空间主要的服务方式是阵地为主,缺乏对外服务和宣传,这些都限制了流动儿童对公共阅读空间的了解。
三、流动儿童阅读推广服务策略探析
目前,在全民阅读活动已举国推进的大环境下,流动儿童阅读推广活动还不够丰富。阅读推广要真正关注流动儿童,发挥其效能,必须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才能真正均等化地开展流动儿童阅读推广活动,让流动儿童养成恒久的阅读兴趣和习惯。
1.协同政府、学校、社区推广流动儿童阅读
一般来说,政府、学校、出版商、图书馆、社区组织、公益组织是阅读推广的重要参与者,相关部门需要协同合作,将阅读推广活动举办得有声有色,以拓展居民视野、传承阅读文化、提升国民素质,同时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智力保障。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举办的“浙江首届书香城镇阅读推广系列活动”于2017年3月20日正式启动,其中有一条候选要求提到,“申请‘书香城镇’的地区要保障流动儿童对阅读的渴求”。[10]
2.推广亲子阅读更新流动儿童父母观念
培养孩子从小爱阅读的习惯,首先要让家长意识到阅读的乐趣和意义,流动儿童的父母,阅读兴趣不高、阅读习惯不良的现象较普遍。若要有成效地开展流动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必须转变其父母旧有的观念,让流动儿童父母与孩子共同阅读,营造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切实解决流动儿童阅读中的问题。
从2012年开始,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妇联与区图书馆进行多元合作、多方互动,共同整合社区、民间绘本馆等资源,全方位、多元化地开展亲子阅读推广,并且有了一群活跃在各个学校、社区和幼儿园的“故事妈妈志愿者”,致力于推广亲子阅读,传播阅读理念。截至2015年6月已有2万多户家庭受益,并于同年8月成立了流动绘本馆。北仑区的霞浦新浦社区地理位置处于城乡结合部,属于农居混住型社区。随着周边临港大工业园的快速建设和发展,辖区内的流动儿童也日益增多。新浦社区在关注流动儿童生活、生理、学习的健康成长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解决流动儿童尽快融入新环境。社区协同周边学校、公益组织、图书馆等单位,开展“牵手筑巢 幸福家园”流动儿童的成长关爱活动,通过开展“熟悉霞浦、父母讲堂、团队拓展、亲子共读”等活动,促进流动儿童的融合发展。
3.创立多元化活动为阅读推广服务
近年来我国各类幼儿园、学校、公共服务机构,一直致力于培养儿童阅读能力,而处于弱势群体的流动儿童尤其需要大众的关心。目前,各地都开始尝试整合社会资源,全方位、多元化地为流动儿童创造良好的阅读条件。
安徽省合肥市图书馆协同街道创立的合肥民工子弟图书馆从2006年6月服务至今,孩子们既可以免费领取图书证借阅书册,也可以凭证件到市少儿图书馆借书及参加活动。深圳市南天社区发起流动儿童社会融合活动“亲子活动 义工体验”,为同学、家长介绍图书馆的工作范畴,在整理图书的过程中加深与社区的融合。云南省玉溪市聂耳图书馆从2015年开始开展“随迁子女走进聂耳图书馆读书活动”,吸引玉溪地区8所流动儿童小学师生1000多名,在活动中介绍图书馆的历史沿革,同时教会流动儿童如何利用图书馆,并介绍阅读对未来人生的重要作用。聂耳图书馆平时每周末、寒暑假放映儿童影视,在内容上选择具有正能量的少儿动画片、科教片、纪录片。另外,开放“青少年绿色上网基地”针对流动儿童用电脑难、上网更难的现状,全年免费开放网络。图书馆将不良、不健康的网络信息进行干预,保障传输给孩子们的网络内容都是健康的。
四、结语
阅读是人类掌握知识、增长智慧、规范行为的重要方式。均等化的流动儿童阅读推广需要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积极引导流动儿童父母更新观念,加大图书馆、学校等的推广教育,发掘优秀的阅读产品为流动儿童提供服务,进而补偿流动儿童教育、阅读的缺失,推广均等公正、机会平等、优质规范、健康共享的教育与阅读环境。
(作者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