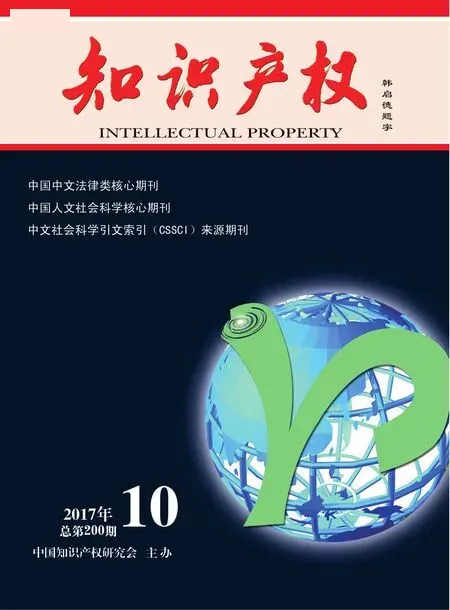专利视角下中医药传统知识现有技术评介及制度启示
陈 庆
专利视角下中医药传统知识现有技术评介及制度启示
陈 庆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价值在于以传统知识形式披露的医药用途信息,在专利视角下,应以出版物公开发行的群体来界定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是否构成“现有技术”,在使用公开上更应以是否涉及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实质性用途的公开使用为准则,探索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新颖性标准。
中医药传统知识 医药用途信息 现有技术 新颖性
一、问题的提出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价值在于以传统知识形式披露的医药用途信息,蕴含着巨大的产业药用开发价值,2015年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用于治疗疟疾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再次证明了中医药作为我国原创科技资源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所在。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发展,我国的传统中药逐渐成为各国发展生物科技,尤其是生物制药的重点目标,也成为培育“生物海盗”的温床,而由传统中药所蕴涵折射的传统知识也同样遭到侵蚀。
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属于传统知识一部分,是相对于现代知识的另一类知识体系,这种医药用途信息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不断实践发展而来,传统性是其区别于现代知识体系的根本特征。其所谓的“传统”,意味着该传统知识的获得与使用方式属于特定民族或地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这种传统是历经了数代以家庭为单位的不断尝试所建立起来的,具有稳定的信仰体系、准则和实践,并通过口授而世代相传下来,具有传统群体的文化特质,反映特定群体的传统生活方式。
这种基于“传统”的特性使得我们常陷入一种误区,既然焊上传统的烙印,而且历经数代传承、发展,那么其所创知识不可能是“新”的,属于我们常为信奉的“古法”知识,更不可能符合专利法上的“新颖性”标准。对于大多数知识产权来说,其受保护都有一定的期限,然而,传统知识却是古老的并且是跨年代的存在,我们无法清楚地划定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如果一个事物在时间维度上没有任何可作判断界点的东西,那么这一事物就无所谓“新”或“旧”,因为新颖性也是有相对的时间界点作为参考系,如专利的新颖性以专利申请日,有优先权的以优先权日为界点。
对于此观点,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其认为传统知识虽然源于过去,但是却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是对传统的超越,是对传统的一种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知识也是当代知识。①WIPO.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 including expressions of folklore[Z]. WIPO/IPTK/MCT/02/INF . 4.传统知识在代代相传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地传承交替,对于大多数传统药物而言,经历数代的不断尝试,传统部族、社区对其药性的每一次探索、挖掘,都使得传统药物在治疗理论上更加趋于稳定,治疗效果更加精确。因此,对于这种传统药物医药用途信息的探索也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创新之中,不断改变和丰富着自己的内容。诸如中国的汉医学、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学,以及日本、韩国的传统医疗体系都是建立在古代医学体系之上的,但这些体系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获得突破和革新。中国大量的传统药方的改良被授予专利权,就证实了这一点。②GRAHAM DUTFIE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 Trade and Biodiversity : Seeds and Plant Varieties[M] . Earth scan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 2002.P95.
上述观点和解释对于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的“传统”本质特征给予了较好的描述,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并不是墨守成规,“传统”一词反映了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基于传统”的起源背景,突出的是代代相传,为某个特定民族或其居住地域所固有,并随着环境改变而不断演进。故有学者提出应采用类似《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中的新颖性规定,将是否为“首次公开”(first disclosure)转变为“商业新颖性”(commercial novelty)以解决“传统”在时间界点混沌不清的问题。③杨明:《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9页。
专利法上的“新颖性”要求我们所保护的对象必须是前所未有的、未曾出现过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那么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是否符合这种“新颖性”标准,有待我们深入研究。
二、“现有技术”的对接及存在的问题
一件发明要获得专利权,要求这件发明必须是新的,即其不能是在先技术或者已经为公众所知晓,这是由专利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
《TRIPS协议》仅仅以新的(newness)作为可专利性的基本标准,并没有采用统一的或普遍性的新颖性标准(novelty standard),亦没有对新颖性的问题做出详细的规定,简而言之,不属于技术现状之发明即具有新颖性。各国对专利新颖性的审查标准不一,但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一说法,即申请专利的技术应不属于现有技术或不为公众所知晓,两者意思大致相同,一般如果属于现有技术则已为公众所知晓,如我国专利法对现有技术的定义即是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者专利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在其申请日之前已经为公众所知。
现有技术又称在先技术,是指在申请日前已经为公众所知的技术,这种知识在专利申请之前或在优先权日之前即可整体地从公共领域获得。④WIPO/GRTKF/IC/2/6, July 1,2001.现有技术是各国专利法和专利审查指南中评判专利新颖性最为常用的术语,已经成为一个用来衡量发明创造是否具有新颖性的客观参照物。⑤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如《欧洲专利公约》规定一项发明如果不构成现有技术的一部分(not form a part of the state of the art),则具备新颖性;韩国、印度、俄罗斯则采用“一项发明如果未被现有技术所预期(not anticipated by the prior art),则具备新颖性”,not anticipated的用法更指明了现有技术对发明的指引和启示作用;还有如瑞士、秘鲁等国家采用“一项发明如果未被现有技术所包含(not included in the state of the art)”,则具备新颖性,其与《欧洲专利公约》术语如出一辙,我国专利法采用的表述方法也基本一致。⑥2008年修法之前的我国《专利法》,虽未直接使用现有技术一词,将新颖性直接表述为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但该表述却仍然隐含了现有技术的含义。
无疑,评价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的“新颖性”离不开对现有技术的解读。而作为“技术”,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所包含的传统治疗方法和药用价值,尽管是以传统知识方式呈现,但并不妨碍其作为技术而存在。因为这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和药用价值信息并不单纯是一种知识,里面还涉及到具体对药物的操作和处理的过程,这些治疗是以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展现传统中医药对于人体疾病的药物机理,是一种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理应属于“技术”范畴。⑦陈庆:《传统植物药可专利创造性研究》,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2期,第47页。
对于落入现有技术的一切发明创造都不得获得专利授权,评价一项发明创造是否是现有技术,通常会从三个方面判断,即时间因素、地域界限和公开的程度。而各国对此的判断基准也较为不同,由此导致不同的国家对专利新颖性的要求不同。于纯理论上来说,现有技术应涵盖申请日之前(不包括申请日当日)所有能为公众所知(available to the public)的信息,并不限于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语言或任何形式,例如书籍、电子、网络、口头、任何展示或使用等。⑧蔡瑟珍著:《专利发明实体审查基准(一)》,我国台湾地区“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出版,国立台湾大学科技整合法律学研究所编印,2006年版,第105页。
于时间因素上来说,各国基本上接受了以“申请日”为时间界点,除了仍然采用先发明制度的少数几个国家,即申请日以前公开的技术内容都属于现有技术。而于地域界限来说,依据国内公开和世界范围的公开为标准分为相对新颖性、混合新颖性和绝对新颖性。
为公众所知一般包括任何形式的公开使用、销售或出版物公开,各国对公开的方式基本一致,但却并未设定一个标准,只要达到足以为公众所知的公开程度即推定为该技术为公众所知,属于现有技术。
从专利视角来看,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的为公众所知的公开形式,包括口头公开、使用公开和书面公开等方式。那么这些公开方式是否影响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新颖性的标准,由于现在绝大多数国家基本采用的都是绝对新颖性标准,那么我们对于这种公开形式也以全世界为限,对公开的程度和模式进行一番探讨。
三、“现有技术”为公众所知的理论误区
专利制度以“现有技术”为基石,以“出版物公开、使用公开”确定“现有技术”范围,打造专利制度新颖性审查标准。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的新颖性判断上,对“现有技术”标准的评判,应严格遵行出版物公开及使用公开的规则,避免陷入“现有技术”为公众所知的理论误区。
(一)出版物公开
日本特许法采用“刊行物”,美国法则用“publication”,均系指一切出版物。我国台湾地区则采用“刊物”一词,三者相比较仍然存有差异。我国台湾地区的“刊物”一词似乎语义过于狭隘,因为刊物与书刊或出版物含义还是存在不同,原指杂志之类出版物,而刊行物应指一切公开出版发行之印刷物,以公开散布为目的所复制的资讯传达媒体。有学者认为,我国台湾地区“刊物”用法似有仿效日本之故,应与“刊行物”同义,均指一切出版物。⑨杨崇森著:《专利法理论与应用》,台湾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94页。通常以印刷或其他机械的方法发行,但即使是使用手抄、打字、复印纸书写等,亦应包括在内。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社会资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各种媒体的使用也极为普遍,传统旧法所规定的刊行物也已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活字印刷物。这一点似乎也得到国际公认,如美国判例并不全以出版物形式出现,其专利申请采用电子申请或记录在移动存储器上,亦属出版物。我国出版物公开一般是指以书面方式披露技术信息,但出版物并不限于印刷的,也包括打字、手写、用光、电、磁、照相等方式复制的,其载体不限于纸张,也包括各种其他的类型的信息载体,如缩微胶片、影片、磁带、光盘、照相底片等。⑩吴汉东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三版,第174页。
出版物突破原有传统印刷复制方式,将其扩大到一切可予以记录并传播的媒介,包括缩微胶片、影片、磁带、光盘、照相底片、手写和网络。出版物形式的突破极大地提高了发明创造的新颖性审查标准,同时也成倍地提高了对于新颖性审查的难度和授权后权利的不确定性。传统印刷出版物的公开发行判断新颖性是否成立是以全球范围为界,出版物不论在国内出版还是在国外出版,不论是其公开日期在近期还是在久远的古代,也不论其采用的语言是中文还是其他国家的任何语言文字,只要公开发表,使公众能够获知,其内容就足以构成现有技术。对于审查员来说尚难以穷尽所有的出版物资料来审查其新颖性,更何况新型传播媒介的介入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为审查增添不可预知的难度,如对于如缩微胶片、影片、磁带、光盘、照相底片等方式的公开,那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种公众可以获知的状态。对于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来说,公开出版物披露的内容范围及公开的途径和方法是否足以达到使他人获知的程度是直接关系到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是否成立现有技术最为重要的两个问题。
根据专利法相关理论,何种已经被披露的知识信息可以成为现有技术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该知识信息能够为公众所获知,二是公众能够从披露的知识信息里得知实质性技术知识的内容。
第一,对于传统出版印刷物而言,排除私人或秘密的文件或者属于某个组织内部流通的文件,对于存放于公众场合的,如图书馆、公共场所等视为可以获知。当然这种可以获知仅仅只是一种“可能”,并不一定构成一种事实,法律采用推定方式强调公众想要知道就能知道的状态,而不是公众已经实际获得的状态。对于如缩微胶片、影片、磁带、光盘、照相底片等方式的公开,那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种公众可以获知的状态。传统出版印刷物一般以发行方式界定公开的状态,而对于缩微胶片、影片、磁带、光盘、照相底片的获取则更多的应该考虑以公开传播、销售为界,始能证明被传播的技术信息处于公众可以获得的状态。传播方式及媒介的不同,可能也会导致出版物的方式的突破与使用之间的重叠。
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的文献化是其所维系的传统医药理论体系得以存续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世界范围内具有独特理论的传统医药基本上都以文献化形式加以记载,如印度的阿育吠陀植物医学、普遍盛行于印度-巴基斯坦半岛及其他部分穆斯林国家的尤那尼(Unani)传统医学[11]P.N.V.Kurup,“Medical Astrology”in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Coverage, 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83:64.及中国的传统民族医药等。而对一些尚未形成其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在其部族长期实践下所形成的独特的治疗体系和方法则欠缺完整的文献记载,如美洲印第安部的纳瓦霍人所掌握的独特的传统知识医药治疗方法[12]William Morgan, “Navaho Treatment of Sickness: diagnosticians” in David Landy, ed., Culture disease and Healing: Studies in Medical Anthropology(New York,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77)165 ,p167-169.、拉美国家的体液治疗(Humoral therapy)[13]Carmel Goldwater,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Latin America”in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Coverage, Halfdan Mahler, in a foreword to Robert H.Bannerman, John Burton & Ch’en Wen-Chieh, eds.,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Coverage:A Reader For Health Administrators and Practitioners(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83,p43.等。对于文献化的方式披露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我们仍应区别对待,法律上应严格以是否构成公开出版物为考量。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文献化方式以印刷出版的居多,然而也存在大量古籍手抄本(一般称为“孤本”)的形式,通常手抄本形式为了保存方便在日后的文献整理中也会以印刷出版的形式再现。根据前述分析,此类型的文献化都应归为出版物。然而其是否构成公开,即达到可以使公众获知的程度,则应具体分析。本文认为公开性的程度应取决于此类文献所掌握及出版发行的群体,如果是以国家、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名义发行的出版物及其文献化则应认定为可以使公众所获知,而以私人名义所持有的文献,这一类文献主要包括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孤本”、祖传下来的内部印刷本等,及具有一定社区封闭性的传统部族,特别是涉及一些少数民族医药所保有的文献,则应以排除在公开出版物之外。
另外,公众能够从披露的知识信息里得知实质性技术知识的内容,应是指同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不用发挥创造性劳动就能根据所披露的知识信息直接知晓该发明内容并制造出来。日本旧法原定为“记载须至容易实施之程度”,即有关发明之记载,须达到该领域从业者,不必特别思考,就能实现该发明的程度。[14]吉藤幸朔著:《特许法概说》,有斐阁1997年版,第83页。即只要记载其发明构成要件即可,不须连发明的目的与作用效果一并记载。而欧洲专利局审查指南中对此却提出了应当“充分披露(enabling disclouse)”的要求,其认为判断是否构成现有技术应该以所披露的信息是否足够,可以使得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实现其技术启示。
那么一些仅提供提示却并未详细说明具体实质内容的知识信息是否构成现有技术?这种提示是否又可以理解成是某种技术启示?如果结论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技术启示是否也会影响现有技术的成立?对于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而言,如果只是单纯揭示其医药用途信息,即某种传统中医药具有治疗某种疾病的用途,而没有更多其他的信息,如采集的时间、地点、使用记录、如何加工处理才能发挥其治疗效果,有何副作用等,是否代表该种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已公布了其实质内容,属于现有技术?
有学者认为中医药的药物用途并不是偶然被发现的,而是中华民族在千百年来世代反复尝试、实践而得来的,这种药物用途的发现是建立在我国独有的古代朴素哲学思想之上,有其一定的理论根基作支撑,才导致中医药形成较为稳定的药用价值。而且中医药治疗效果的发挥有赖于其独特的处理方法,包括使用的时间、施药的环境等因素,其共同构成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
本文以为,如果单纯的只是揭示其医药用途信息也应该属于实质内容的公开,属于现有技术。对于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而言,一方面,其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对这种治疗用途的发现,才使得传统中药,特别是中草药区别于普通的植物,而这种治疗用途的发现也是经过长期实践经验而获得的,对于中医药传统知识体系来说,将某种植物用于治疗某种疾病才是其最终目的。另一方面,正是这种药用价值的揭示为进一步研究开发和提取其有效物质成分提供了研究方向和技术启示,如印度的姜黄案、亚马逊的死藤水案都是以当地对这种药物用途的长期使用而认为其属于现有技术而否定其新颖性,不予授权。如果将其药用效果作用和治疗目的也一并记载,似乎超出了现有技术对“便于容易实施”之程度。如果认为单纯的只是揭示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不构成现有技术,那么发达国家跨国制药集团更可以肆无忌惮地据其将中医药进行萃取提取有效成分,以申请专利。对此,尹新天教授做了呼应,其认为《欧洲专利局审查指南》的“充分披露”规则在实际中并没有必要,其相当于提出了类似于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说明书应当充分公开的要求……就单独一项现有技术而言,有的内容十分翔实,有的内容十分宽泛,这都不影响其构成现有技术……现有技术是否披露了足够的技术信息的问题在判断新颖性、创造性时自然会予以考虑,不必在判断是否构成现有技术时予以考虑”。[15]尹新天著:《中国专利法详解(缩编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页。一种治疗某种疾病的某种中草药本身所披露的药物用途信息足以构成对后期针对该种中草药提取的有效物质所开发出的新药物的技术启示,因此构成实质性的公开。
(二)使用公开
使用公开是现有技术成立的又一条件因素,然而这种使用,须能通过使用行为而达到揭露技术内容,使该技术能够处于为公众所知的状态,并不以公众实际上已经使用或已真正得知该技术的内容为必要。对于那些须通过拆解或破坏方能揭示其内部隐蔽结构的发明创造,仅仅为外界所展示使用不构成现有技术,除非在公开销售、提供产品的情况下,方可构成现有技术的公开使用,因为购买者购买之后有权对其进行拆分、破坏研究其内部具体构造。欧洲专利局的立场也是基于此点理由,认为如果某一对象被置于公众中不负有保密义务的成员能看见的地方,同行业的技术人员单纯从外部即能获知其内部的所有技术特征或者需要通过拆卸或破坏就能知道其内部技术特征,则被认为是为公众所知。
然而如何理解“公众”一词,其评判标准如何又是一个问题。日本学者认为所谓公开使用乃公然实施,即公然得知之状态,亦即处在可被不特定多数人知悉的状态下实施之意。故少数人虽知悉,但在不能期待保密场合乃公知,反之,虽多数人知悉,但彼等如系居于应将发明保密之关系之人,例如被仰赖出资之人、共同研究人员、经营者、家属等时,则非公知。[16][日]中川善之助、兼子一监修:《特许•商标•著作权(实务法律大系10)》,第41页。转引自祭瑟珍著《专利发明实体审查基准(一)》,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出版,国立台湾大学科技整合法律学研究所编印,2006年版,第103页。
由上可知,为公众所知的状态并不在于人数多寡,而在于是否是针对不特定人而言,对于某个团体、社区、部族来说其针对的是特定的人,具有传播的相对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封闭性。然而,针对特定的人之间的公开传播,保密性固然是可以成立不为公众所知的状态,如果特定人之间如某个团体、社区或部族之间因为共同的宗教信仰、人文环境、地缘关系而结成较为固定封闭的组织,那么在这种组织内部相互公开传播和使用但没有签署或口头约定等任何其他形式的共同保密协议,是否仍可被认为不构成为公众所知之状态?
这种观点在其他国家法律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支撑依据,日本判例认为只有家属在家里见到制作与持有发明物时,并非公知。[17]杨崇森著:《专利法理论与应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2006年版,第94页。中医药传统知识中,民族医药所在的传统社区是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共同的人文社会环境而组成的封闭性社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属于一种广义上家庭的范畴,而成立非公知状态。至于社区各成员之间是否需要有口头或书面签署的保密协议,自可依社会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因素等被认定为应当承担保密义务,此种情形称为默示的保密义务,所以,即使社区以外的人知晓了该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也应该由于用途来源获知途径的非法性而排除其构成现有技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孕育并产生传统知识的传统社区与发达国家创造现代知识的大型实验室是相似的。[18]严永和著:《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任何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都是在前人智慧劳动的基础上而获得,即使是利用了公共知识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实验室对这种发明创造也拥有权利。而传统社区由于封闭性,其他地方的社区并不确切地了解或掌握该社区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因此仅仅在某一团体或社区内为其部族所知,该种传统知识应被认为具有新颖性。
另一方面,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的本土性及封闭性是导致其边缘化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上也契合专利法上新颖性的要求。传统知识主要是集体和跨代的创作,它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基础之上并不断反复地发展,通常,当一个“创新”或者“发明”出现在这传统环境下也不会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19]Noami Roht-Arriaza, of seeds and Shaman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1997,17,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p936.
对于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而言,公开的方式以口头公开和使用为其最常见的形式,中医药独特的治疗用途和方法知识通常以以下几种方式呈现:第一,对于民族医药而言,特定区域民族、社区的人们对其治疗用途和方法都非常熟悉并知道如何具体使用,这种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对于整个民族区域来说是公知的;第二,对于某类中医药,人们都知道其治疗用途,即知道这种中医药可以治疗什么疾病,但只有少部分人知道具体的使用方法并能熟练的操作;第三,对于某类中医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其具体用途和使用方法,只有少部分知悉该药用用途及使用方法。
对于第一种方式,该医药用途和使用方法都为本民族、社区所掌握,包括与此相关的所有传统医学理论、人文宗教、历史文化因素等。对少数民族集聚区、社区内部这属于一种公共知识,人人皆知。如江瑶族人民利用九万大山上的“藤藤草草”,开创出神奇的浴药配方,该配方对于瑶族村寨来说,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但对于外界其仍然处于一种非公知的状态。对于第二种方式,该医药用途为本民族、社区所公知,但其使用方法只为少数人所掌握,如上述江瑶族浴药剂型的具体制作方法及使用方法,并非所有江瑶族人都知道。那么,这种由某类特殊人群所掌握的制备方法则不属于公开使用。对于第三种一般不构成公开使用,鉴于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的特性,这种方式其实较难成立,因为中草药作为单株植物不像几种植物药配合所组成的组方或复方,人们可以直接通过观察知道该种中草药可以用于治疗哪类疾病,除非其一直是以加工处理的方式(如使其变成颗粒状、直接熬制成汤药或膏状物等)予以使用,使得外人无法从外观上推导出其具体属于哪种中草药。对于这种情况,自然成立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状态,无讨论研究之必要。
结 语
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以传统医药信息为保护客体,以传统知识为披露形式,在“现有技术”设计上,应严格遵循出版物公开及使用公开的规则,以出版物公开发行的群体来作为界定是否构成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文献公开化的判断依据,在使用公开上更应以是否涉及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实质性用途的使用为准则,探索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的新颖性标准。
传统中药特别是中草药通常是使用整株的生态性植物所披露的传统药物用途信息来治疗某种疾病,其重点在于识别特殊的植物药而不是确切的活性物质,但是,在使用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的过程中,其发挥药效的往往与西医方式提取的有效物质是同一成分。根据现在各国专利法的规定,即使这种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是已知的,但是从这种植物药中分离和萃取的物质可以获得专利权,因为人们并不知道该准确的活性物质。既然两者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分离出来的物质因为该物质未被传统部族所揭示而具有新颖性,那么从技术上来讲,这种披露未知治疗物质自然某种医药用途信息也具有新颖性。那种认为一定要明确具体的物质,达到西方社会形式主义所认可的知识水平才具有新颖性,才能获得专利保护是不成立的。[20]Diamond v. Charkrabarty, 447 U.S. 303,309(1980).See Sheldon W. Halpern,Craig A.Nard, Kenneth L. Port, Fundamentals of United States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Copyright, Patent and Trademark,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9,p227.
我们有理由相信,专利法对于新颖性的规定也并非完全不适用于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更应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探索适合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用途信息的新颖性标准路径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加合理的权利保护模式,避免“生物海盗”行为的进一步泛滥。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es in the disclosure of the information on drug usage in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ent, the group should define the constitution of prior art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at publicly publishes the publications. In making public the drug usage, the standard should be whether there is substantial public us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meanwhile trying to establish the novelty standard for drug usage in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drug usage information; prior art; novelty
陈庆,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法学教研室主任、讲师,法学博士
2 0 1 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医药传统知识医药信息专用权研究”(项目编号:1 7 F F X 0 2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