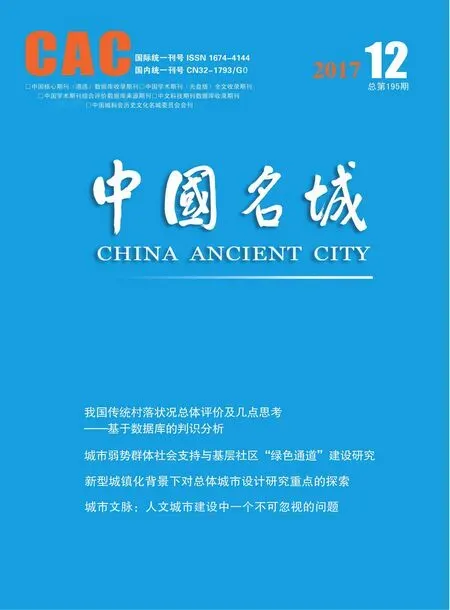城市文脉:人文城市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刘 涛 钱 钰
城市文脉:人文城市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刘 涛 钱 钰
“城市文脉”在当下已经成为学术探讨、政府文件及新闻报道中的流行词汇。通过梳理影响城市文脉话语形成、流行的主要因素,参照“文脉”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使用习惯,可以将城市文脉定义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在特定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反映。城市文脉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反映了城市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合力,也代表了城市历史的深厚积淀和城市文化记忆的提炼浓缩。对现实的城市文化建设来说,延续城市文脉与塑造城市文化形象之间的关系应该最为紧密,而整理城市文脉则需要重视城市文化重心的演进。
城市文脉;城市建筑;城市文化形象;文化重心
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聚集的中心,城市不但在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结构变革和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引擎”。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文脉”一词本来多用于文学理论和堪舆风水,可能并没有出现过将“城市”和“文脉”两个语词连用的情形。但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中夷平城市自然和文化个性、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等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文脉不仅在与城市发展有关的学术探讨、政府文件及新闻报道中出现频率明显增加,还被赋予了城市建设必须参考的根本、文化发展必须依托的资源之类的重要职能。
1999年6月,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由吴良镛起草的《北京宪章》提出了文化是城市和建筑之魂,建筑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解释着地方文脉;伴随地域文化多样性和特色的衰微,“城市和建筑物的标准化、商品化致使建筑特色逐渐隐退,建筑文化和城市文化出现趋同现象和特色危机。”[1]2014年2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北京玉河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工作展览及河堤遗址时指出,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城市建设应该贯彻“人文城市”的建设理念,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彰显城市文化形象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要建设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防止千城一面。至于以城市名称加文脉之方式命名的城市形象宣传片、系列报道、文物展、书画展、图片展、研讨会,其数量之多更是难以准确统计。
1 关于城市文脉的不同言说
与所有涉及文化的词汇一样,对城市文脉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说,它们所包罗的具体内容、涉及城市工作的特定方面也存在层次和范围上的显著差异。如吴良镛在上个世纪末就明确表达过城市建筑是城市历史文脉延续传承的有形的、具体的表现,他还指出,与个体建筑相比较,城乡聚落更像是一面能够系统反映某一国家、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变迁过程的“镜子”。[2]类似的说法流传甚广,在城建规划和文物保护方面影响很大。2011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专家座谈会上就说过:“历史文化街区既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场所,更是城市发展的文脉所在。”[3]2016年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即有要通过保护古遗址、古建筑、近现代历史建筑和保护传承、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来更好地延续历史文脉、展现城市风貌的表述,还要求用5年左右时间,完成所有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
另外,超越具体形式,从重新评价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关系的高度,把延续城市文脉作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文化持久繁荣的重要动力,使它与当代文化生产、消费、社会变革发生关联的趋势也在持续壮大。如冯骥才曾以巴黎为例说明城市文脉不只“确凿而冰冷”地存在于博物馆的陈列品和古老建筑中,更应从整个城市里居民的生活文化中得到“生动又真实”的反映,“在文物中历史是死的,在这文化中历史却仍然活着。从深远的过去到无限的未来,它血缘相连,一脉相承,形成一种强大和进展的文化与精神”。[4]又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在倡导建设有文脉传承的人文城市时,强调促进功能提升与文化文物保护相结合、整体保护文化生态、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而根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2015)的精神,为了在城市发展中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不仅应该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的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也需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
2 城市文脉话语的历史渊源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当人们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还是经常需要向历史传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去寻求支持和帮助。[5]p.585对城市文脉的研究、讨论同样也是如此。现实中,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改造、开发的案例提醒我们:一方面,坚持将城市文脉等同于城市的建筑风格、规划格局,将延续城市文脉等同于保持城市建筑的历史风貌、传统格局,这样的作法显然不能体现城市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关键性作用。不但容易在拆旧建新、拆真建假中陷入千城一面的尴尬境地,难以充分展示文化遗产“活化”、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的特殊魅力,而且不能合理解释、有效指导各种旨在接续、保护城市文脉的社会活动——如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徽州市更名为黄山市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明确的主要方面和足够的具体事项作为实际“支撑”,只是把城市文脉与文化资源、文化生态、文化形象等词汇捏合在一起,很可能会引起城市文脉概念的空洞化和形式化,削弱甚至消解它对城市文化变迁、发展问题的解释力。尽管在古汉语中可能并没有出现过将“城市”和“文脉”两个语词连用的情形,但为了使有关城市文脉的学术研究、公开讨论可以有一个相对清晰和统一的范围,能够在政策制定及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建设性作用,还是应该从影响城市文脉话语形成、流行的主要因素着手,对城市文脉话语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进行廓清和梳理。
首先,“文脉”一词并非由国外传来,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风水典籍中早有“文脉”出现。明代王文禄著《文脉》三卷以论说古今诗文。在他看来,文脉即“一代人文之精神命脉”。秉持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立场,王文禄指出“文之脉蕴于冲穆之密,行于法象之昭,根心之灵,宰气之机,先天无始,后天无终”。文脉与山水(源于昆仑)、星宿(反射太阳的光辉)、经络(受心统摄)类似,虽然有盛衰否泰、起伏无定,其聚合的形式常常变化,如“圣学息而变纵横,纵横变为经术,经术变为名节,名节变为清谈,清谈变为诗赋,诗赋变为学究明经,又变为道学”,但其源于心、载以道的传承却是生生不息、永难断绝。文脉聚合又有大聚、小聚之分,前者“脉以贯道、道原于心”的名家名作辈出,后者则多见“心溺气漓”、华而无实的粗劣、轻薄之文。[6]
在堪舆风水中,文脉主要是指有利于当地居民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或者说“文运昌隆”的山川形势及聚落格局。北斗七星中的文曲星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是主文运、科甲的星宿。著名的堪舆典籍《撼龙经》中说“龙脉”发源于须弥山,其分支聚合不仅与城市分布关系极为密切,而且和天上的星宿相对应,即:“分枝劈脉纵横去,气血钩连逢水住。大为都邑帝王州,小为郡县君公侯。其次偏方小镇市,亦有富贵居其中。大率行龙自有真,星峰磊落是龙身。高山须认星峰起,平地龙行别有名。峰以星名取其类,星辰下照山成形。”龙脉如与文曲星配合适宜可以促使当地文运昌盛,多出秀才、举人、进士,也就是“若得尊星生一峰,便使柔星为长雄。男人端貌取科第,女人主家权胜翁”。[7]古代中国城镇周围往往建有文峰塔、文昌塔、文兴塔,命名有文笔峰、笔架山的原因就在于此。而民间流传“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的俗语、笔记小说中常见葬吉穴后子孙高中进士、状元的故事也都是社会重视风水文脉的生动写照。
其次,城市文脉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确实是受到西方建筑理论界的影响。英文中的“CONTEXT”原是语言学中的术语,既指有助于确定词汇、句子真实意义的上下文关系,又表示事件发生的背景及条件,在中文中也可以被翻译为文脉。20世纪中叶,CONTEXT被引入建筑领域成为西方建筑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相关学者主要用它批判当时建筑设计中无视环境、场所的存在,只是把单体建筑当作独特问题看待的不良风气,并力图通过在设计中和谐地结合传统来达到新旧建筑的视觉连续、城市景观的和谐共生。20世纪80年代,这种思潮传入中国,短时间内就形成了建筑学界的“文脉热”,又称为“文脉主义”。
大体上,西方建筑理论界虽然对文脉有着不同的解读,但在把城市文脉看作设计上的某种静态风格(或历史参照)方面却是高度一致。正如布罗林所说:“对早期建筑形式的再解释是尊重文脉真正的和有机的方法”。一幢新建筑要与其毗邻的老建筑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必然会从文脉中汲取灵感,通过完全照搬已有的建筑形式、采用基本相似的形式,但对它们重新进行组织、创造与老形式有同样视觉效果的新形式、将原来的形式抽象化等途径来达到视觉上的连续性。[8]而当进入中国建筑学界之后,文脉则有了动态发展的新含义。就像吴良镛认为的,相较于城市的旧有部分,新的部分不仅数量更多还在与日俱增,“如果说历史文物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永恒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那么新时代的建筑美当是更有活力的建筑,它应当是继往开来,既满足新的生活要求,又是对历史文脉的继承,反映着新时代对建筑文化艺术的新追求,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时代之美”。[9]
第三,中华文化复兴理念的传播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城市风貌、城市个性的重视,极大推动了城市文脉话语的流行和内涵的扩大。总体上,“文脉热”在中国建筑学界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尽管《北京宪章》中强调文化是城市和建筑之魂,“建筑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解释着地方文脉”,但除了简单套用于具体项目中的空间整合及文化符号等设计元素的运用,关于文脉的理论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已经很少出现。这种情况直至本世纪初才恢复。2000年以后,由于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之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之重要因素的地位及作用日渐凸显,中华文化复兴的理念开始在中国社会迅速传播,以复兴特色鲜明、魅力独特、传承不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得到社会各界、各阶层的广泛认同。习近平用“讲清楚”概括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即:“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0]受中华文化复兴理念的影响,被赋予了文化①发展脉络新内涵、尤其聚焦于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文脉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在日常用语中,作为承载文脉的空间载体之一和文化活动最为集中的场所,城市自然也会更加频繁地与文脉连接在一起。
在城市文脉话语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来自中央高层的示范和倡导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如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长期关注、思考城市文脉的延续与城市个性的保持问题,公开发表过许多有关城市文脉的重要论述。2003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中提出,作为省会城市,杭州应在保护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弘扬历史文化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做得更好。2006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遗产日”调研时说,城市化过程中隐藏着对文化遗产进行破坏的危险,在现实中就存在着城市文化个性的轻视甚至埋没,造成文脉的断裂,造成‘千城一面’的现象”。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指出: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既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和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3 城市文脉的内涵与整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5]p.88综合前面两节的分析,可以发现:“文脉”一词在传统文化中的长期使用对城市文脉话语的流行有着难以否认的重要影响,如堪舆风水中文脉发达预示科举事业兴旺的观念与当下将城市文脉与文化繁荣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做法相类似,古代文论中文脉源于心、载以道、生生不息的理念与当下延续文脉才能留住“城市之魂”的说法相类似。但文脉在当下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实际内涵确实与古代和由西方传入的相关理论存在巨大差异,并不应该将古人和西方学者的言说简单套用于今天对城市文脉的阐释提炼、传承延续。
从广义上说,除了受本能的驱使以外,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也正是因为“文化”具有包含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学科门类极其广阔的属性,才使确立一种可以被广泛认同(包括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城市文脉”概念显得特别困难和复杂。顺应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需求,参照文脉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使用习惯,将城市文脉定义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如文明进步、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包容和谐等)在特定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反映;认为它体现在道德伦理、价值观、宗教、文学、艺术、习俗、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心理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阐释可能比较适合反映城市文脉是浓缩城市历史的深厚积淀、提炼城市文化的多彩记忆的最终成果。既显示了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发展中的综合作用,体现出城市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也容易被大众知晓、理解、记忆和使用,还为从时代、阶层和各个学科等不同的视角、侧面研究城市文脉的传承延续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城市有兴亡存废,各个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精华、长处、优点在不同国家、地区有极其多样化的具体表达,它们千差万别的组合方式导致了城市文脉在公众视野中的聚散离合、盛衰否泰、起伏无定,也必然使不同城市的文脉传承状况和延续城市文脉的路径方式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由上述对城市文脉概念的阐释出发,结合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实施和人文城市建设的实际,未来对城市文脉的研究可能特别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现实的城市文化建设中,延续城市文脉与塑造城市文化形象之间的关系应该最为紧密。本质上,城市文化形象是公众对特定城市文化传承、发展的总体印象或综合评价,它的塑造不可能脱离对城市文脉的探究。如果将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的目标定位于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传承、利用、开发中与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时代新风尚、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在联系和互动中彰显城市的个性和特色,那么延续这些城市的文脉与常说的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可以说就是一回事情。对城市文化形象的研究现已有许多成果公开发表,而关于城市文脉概念、内涵、特征、延续问题的深入讨论当然可以从中找到有益的参考和借鉴。第二,对城市文脉的认真发掘、细致整理是延续城市文脉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延续城市文脉并不是要保持城市的各种传统文化样式长期不变,而是要根据时代主题转换的需求和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原则,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混合、扬弃更替中生长出城市特有的文化吸引力。②在这方面,陈序经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的“文化重心”理论极具现实意义。从物理学的视角,重心的有无、重心位置的变化对于维持特定物体形状、位置的稳定以及认识物体运动规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在特定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文化重心始终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发生或快速或缓慢的变迁,也为整理城市文化脉络、保存城市历史记忆提供了一条相对清晰的主线。
陈序经认为,“文化重心”是某个区域文化、某个时代文化、某个文化系统的主要内容、主体成分,它对文化的其他方面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与支配。在空间分布上,每个文化区域都必定有中心、边缘的分界;而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识别文化重心及其变迁轨迹的最大价值却是在于了解某个地区、某个社会、某个时代文化的特点,“不但可以明白文化发展的程序与趋向,而且可以当作改造文化的张本”。[11]横的方向(或者说空间维度)上,城市所聚集的文化要素、文化活动、文化样式往往会特别偏重于文化的若干方面,如与现实政治的关联、与经济运行的互动、教育考试、文学艺术、宗教伦理、科学技术等等。纵的方向(时间维度)上,受政治格局、经济形势、交通条件、人口构成等变动的影响,特定城市的文化重心也会随之发生转换,以往处于边缘地位的非“重心”方面(要素)可以上升为重心方面(要素),曾经辉煌的“重心”方面(要素)则或许逐渐被弱化为非重心方面(要素)。因为具有文化遗产丰富、文化资源厚积、城市沿革连续未断的特殊优势,中国为数众多的著名古都,像西安、北京、南京、开封、洛阳、安阳等理应在人文城市建设扮演先导、示范的重要角色,同时也可以为在横向或纵向的维度上建构城市文脉整理的模式、提炼城市文化的特色提供许多典型案例。[12]
如北宋之后,开封由帝国首都衰退为河南的地方性中心城市,屡次经受黄河水患和战乱。虽然每次都能从废墟上得以重建,城市中轴线和基本格局也一直未变,但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进程被强行中断,珍贵的历史遗存和文物大多数被埋藏于十多米深地下的事实使得文化累积的脉络不能很好延续,也难以使参观者对宋代文明发展的巅峰进行深度体验。2010年,描绘北宋东京盛世荣华的《清明上河图》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中以动态版的形式重现,不仅激活了中国人关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历史记忆,使到开封清明上河园风景区体验宋代城市风情的游客数量猛增,也极大促进了以往少有人关注的,有关宋代东京城规划、建设、管理的研究成果通过新媒体在民间的普及和传播。③又如在殷商古都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和诸多青铜重器举世闻名,但它们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却较少为民众所知。李济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中说安阳是“青铜时代中期东方的一个极其独特的世界性城市”;殷商时代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其背景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这种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筑了一种伟大的青铜文化。而青铜文化本身却有它复杂的来源。这些来源中,有一部分,我认为是与两河流域——中央亚细亚有密切关系的。”[13]这些观点本身其实就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所倡导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极佳注解。
4 结语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已经明确,在建设和谐宜居城市的过程中要“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延续历史文脉,建设人文城市”。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的倡导,当下,“人文城市”的建设理念已经走出城建规划研究、文化研究的小圈子,成为许多城市提高城市的美誉度和持续发展能力的现实选择。同时,城市文脉延续和人文城市建设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开始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代需求,对城市历史文脉的研究和讨论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展开。它的延续不应该是对文脉在文学理论或风水之学层面的简单承袭,也不会是对建筑学所提出的“文脉主义”层面的简单借鉴,而是要将城市的现实发展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主流趋势相对接,将其体现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从人到物,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等。应该重视的还有,为了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对城市文脉的阐释提炼、城市形象的塑造提升还都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无论是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之下对特定城市的文脉变迁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爬梳整理,还是在对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都需要将增强特定城市居民及社会公众对城市文脉认同、理解放在首位,不断丰富人们心目中城市文化记忆的内容,持续拓宽保留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的现实路径。
注释:
①在这里,文化所指涉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文学和风水,包括建筑、服饰、饮食、语言、宗教、民族、节庆、风俗、民间工艺、(区域)名称、世界观、价值观、秩序观、审美情趣、社会心理等十分丰富的内容。
②如:在古代,程序复杂、耗费不菲的传统葬俗、婚俗和家族的同居共财曾被认定是文明的的生活方式,反映出中国人对祖先、家族的高度重视,现在却因为不符合文明社会的要求而很难完全恢复、大面积推广。还有年节时举办的庙会和社火,尽管时间上可能与几百年前保持一致,但活动的方式和内容、参与者的动机和来源构成却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③专注时政与思想的互联网平台澎湃新闻网曾在其“城市史话”和“私家历史”专栏,以《最大的城市,最多的人》《百万人口的北宋东京汴梁,与千万规模的北上广,哪个更拥挤?》等为题,发表过十多篇与宋代东京规划、建设、管理、饮食、民俗有关的文章。根据专业研究者的考证,1000多年前的北宋东京城人口密度与今天的北上广大致相当,但其空间规划、景观营造、市政管理的水平却并不一定就比现在差。化报,2011-01-19.
[4]冯骥才.对城市而言文物不等于文化[N].北京青年报,2000-07-2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王水照.历代文选: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690-1711.
[7]钦定四库全书:子部:撼龙经[M].文津阁藏本.
[8]布罗林.建筑与文脉:新老建筑的配合[M].翁致祥,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118.
[8]吴良镛.广义建筑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10]习近平.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N].人民日报,2013-08-21(01).
[11]陈序经.文化学概观:第三册[M].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20-37.
[12]刘涛,甘桂芬,钱钰.论古都文化形象的内涵、特征与塑造[J].中国名城 ,2010(10):11-29.
[13]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89,105.
In recent years, the urban context has became a popular word in academic discussion,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news reports.This article sorts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urban context’s formation and popularization,reviews its idiomatic usage in Ancient Chinese and Modern Chinese. Then, the urban context can be defined as reflection of the main trend of human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specific cities. The urban context is reflected in every aspect of social activities.This definition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resultant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many elements such as materail city life,cultural tradition,geographical environment,etc .It also represents profound accumulation of city histor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of city cultrcal memor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cultu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inuation of the urban context and shaping of the city cultural image should be the most close, and it’s finishing should follow the evolution of city cultural focus.
urban context ; city architecture ; city cultural image ; cultural focus
C912
A
1674-4144(2017)-12-59(6)
刘 涛,河南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博士。
钱 钰,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于向凤
[1]吴良镛 .北京宪章 [J].时代建筑 ,1999(3):88-91.
[2]吴良镛.广义建筑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49,67.
[3]单霁翔.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延续城市发展文脉[N].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