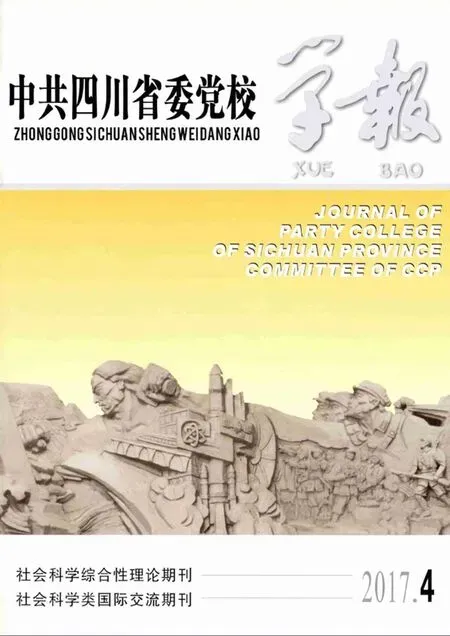“党内政治文化”命题基本特征的分析
毕瑛涛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四川达州 635000)
将“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的首次表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讲的一段话:“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习近平同志还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加以确认:“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1]他还提出“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2]著名学者李忠杰认为:“通常所说的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的文化,而政治文化就是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别和重要方面。它是社会的政治关系、政治过程、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等在人们精神领域的反映,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对于政治问题的认识、态度和价值取向,主要由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等构成。”[3]还有学者认为:“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文化,实质上就是指现代政党秉持和奉为圭臬的普遍价值。”[4]“党内政治文化”命题,应当包含着这样一些基本性的特征。
一、从历史发展轨迹和当前中国社会实践活动观察,党内政治文化自然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要求的核心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政治报告使用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5]P16与“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5]P34两次分开表达的表述方式,提出了“四个自信”问题。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阐释:“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6]习近平将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一起使用,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一种高度自觉。同理,执政党对自身政治文化的自信,也是极其特殊和重要的。通过文化自觉来促进实现文化自信的战略目标,体现出自身强烈的使命感。习近平论及的文化自信,无疑是从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的维度出发的,具有很高很远的战略视野和思考维度。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的执政党,其政治文化(或者政党文化),必然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的核心构成和必要构件,必然在文化自信中占有相当的权重。很难设想,在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两种乃至多种话语指导体系或者文化价值观指导体系,中国社会不会出现思想混乱或者浑浊的状态,其后果十分危险。同时必须预见到,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自信,实质上就是执政党历史使命的自然需要和发展结果。执政党不能依托自身文化自信来支撑和鼎托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与执政的历史合法性、法理合法性,其后果也是十分危险的。与此同时,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自信还是国家民族文化自信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是统一关系、相辅相成关系、优势互补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辉映的关系。囿于此,执政党政治文化既是国家民族文化自信的构成,更是国家民族文化自信的自然延伸、自然发展、自然传承。科学确认和明晰二者的关系,无疑对随意讨论“文化中心论”、“文化核心论”、“文化决定论”和“文化支撑论”等等现实问题,澄清在国家治理中指导思想上存在的许多模糊认识,具有特别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是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自然归宿
《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自然而然,执政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也必须如此依皈。习近平认为,党内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笔者看来,党内政治文化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最终归靠地。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不仅是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出发点、主导力,还必然是归宿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最核心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组织起来的。这个最先进的理论,在当代世界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正如李忠杰指出的:“所谓先进的党、革命的党,必然也是在思想文化上进步的党。只有在先进文化的指导下,在代表先进文化的情况下,这个党才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进步作用。相反,如果一个党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甚至已经腐朽、没落,那它就绝不可能对社会历史进步起推动作用。”[3]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立场、基本方法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都必然是执政党政治文化的主导力、出发点、指导思想和最终归宿。因此,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著作,还要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既要精心研读原文原著,字斟句酌,读懂学透,还要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经验与制度成果,将理论思想与实践需要密切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着新的高度发展,推动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依赖性借鉴性特征
中国近代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日本、苏俄的影响最为关键。同盟会元老朱执信是最早通过日本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朱氏的这种传播属于零星性质,非系统性传播。随着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中国具有了整体性和爆炸性。甚至当时还属于十分偏远的四川乃至四川盆地内的川东川南地区,都受到了其深远影响。著名学者彭明在其扛鼎之作《五四运动史》一书中考证认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囿于四川“据不完全统计,在五月四日至六月三日期间,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的地区,有……成都、重庆、绥定(今达州)、叙州(今宜宾)”[7]P356。众所周知,苏俄十月革命与中国五四运动的发生、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特殊的联系和影响。因为如此,才有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8]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条历史必然规律被中国共产党人所解读所解构所掌握,是付出了艰苦的探索和巨大的代价才取得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就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必然就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中国作为执政党,其政治文化必然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依赖、相借鉴、相融合、相承继的鲜明特征。尤其是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进程数千年,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民族的基因中,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中,也深深地浸淫着儒家文化的因子。不可否认,许多观点或者观念至今还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苏武牧羊几十年痴心不改的报国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功名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观;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怀和气度;于谦“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清廉追求;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结等等,无不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时代价值。不可否认,这些历史精神财富,与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白求恩“四个人”的情怀,雷锋“永做革命螺丝钉”的精神,焦裕禄的公仆精神,谷文昌的清正廉洁作风等等,具有很大的相似甚至相同之处。
在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自然需要大胆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无疑也是重要选项之一。为此,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促进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真正形成。
四、党内政治文化体现着执政党的本质属性与执政党的价值追求
任何文化,不论其是什么文化形态或者以何种方式展示,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追求和价值体现,这是文化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的执政党,其党内政治文化,无疑也要体现或者昭示自身的本质属性和价值追求。这种本质属性和价值追求,也常常被表述或者称为“党性”。《中国共产党党章》就是这些本质属性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党章》对执政党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9]P63为此,执政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充分体现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和约束。从实践活动来考察,执政党在党的建设的长期探索和努力中,已经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建设总格局。各个建设部分既有基本的任务和要求的约定,又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则深深地蕴含于渗透于各项建设之具体实践活动中,体现着执政党的本质属性。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路线纲领、制度规范、思考维度、价值追求、精神状态、工作作风等等方面都时时处处体现和传递着执政党的价值追求,都深刻地受到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否有意识,是否主动,执政党在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赖以遵循的制度纪律时,每个党员和领导干部在从事党内外的公务甚至进行一部分个人活动时,都必然受到一定的执政党政治文化观念支配,体现着一定的文化思想和文化风格,展现出浓浓的执政党政治文化的烙印。同样,执政党党的建设总格局中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每一种建设都蕴含着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因素,都受到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深度制约。总而言之,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充分体现执政党本质属性和价值追求是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内在属性,也是历史的必然归宿。
五、执政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内政治生态具有良好的正面涵养功能
政治生态(又称政治土壤),实质上是党内政治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或者制度安排)整体对党员个体的关系和影响的问题。这种整体与个体的政治文化,是辩证统一关系。执政党整体的政治文化,指导、规范和决定着每一个党员个体的政治文化,每一个党员个体的政治文化也必然反过来影响、制约整体的政治文化。一旦某些地方发生塌方式腐败,则必然表明其局部的政治文化出了问题。个体的政治文化也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会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甚至相互干扰,促使和决定着局部乃至全局整体的政治文化或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或向消极落后的方向演变。如果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在政治文化上出了问题,不仅会导致党员和领导干部本人滑向错误的方面,而且会对党的整体形象乃至党的先进性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客观地讲,曾经一段时间党内的政治生态的确受到了各种文化思潮的严重冲击,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政治生态事实上出现了恶化的状态,因此反映在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文化中也出现了不少消极腐败现象。曲青山分析指出:“有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政治观念糊涂。有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在一些地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又如,一些落后的‘官场文化’一度滋生蔓延。有些人不是潜心工作、立足于干事创业,而是千方百计拉关系、找靠山。有些人小人得志,一旦掌权,就把主管的部门或单位当成‘家天下’,专横跋扈、颐指气使。有些人以我划线,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有些人自己没本事,就搞‘逆淘汰’,千方百计打击有本事的人,以此树立自己的‘权威’。有些人权欲熏心,整天琢磨着向上爬,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有些人迎合上司所好,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阿谀逢迎,失去了党的干部应有的气节和风骨。”[2]上述现象,有些需要制度设计来解决,有些需要党内法规来规范,但是更多的还是在制定执行制度、法规的同时,运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来解决。因为执政党政治文化具有其他文化难以企及、无法替代的功能。西汉时期,著名学者刘向在《说苑·指武》中,首次将“文”与“化”合成一个整词,谓之“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说。晋朝束皙在《文选·补之诗》中,已将文与武、内与外区分开来相对而论:“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由此可见,“文化”最原始的意义就是有“以文教化”的意蕴。因此有学者认为,“以文教化”、文化重在“化”。[10]党内政治文化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一样,应当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持久的过程加以确认,让党内政治文化保持其强大的影响力,绝对不可以追求短平快式的效应。尤其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化”,实际上就是政治生态的良性涵养问题,只能付出艰巨的、长期的努力,别无选择。
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无疑会大大的助推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及其发展。
[1]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原载求是).新华网,2017-01-01.
[2]曲青山.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J]. 北京: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01-12.
[3]李忠杰.建设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J].北京:人民日报,2017-01-25.
[4]毕英涛.从政党文化透视坚持党员主体地位的意义[J]. 北京. 学习时报(教育导刊),2008-01-15.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北京:光明日报, 2016-07-02.
[7]彭明.五四运动史[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陈先达.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J]. 北京:光明日报, 2016-03-02.
[9]中国共产党党章[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20]毕英涛.文化重在“化”[N]. 四川:达州日报,201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