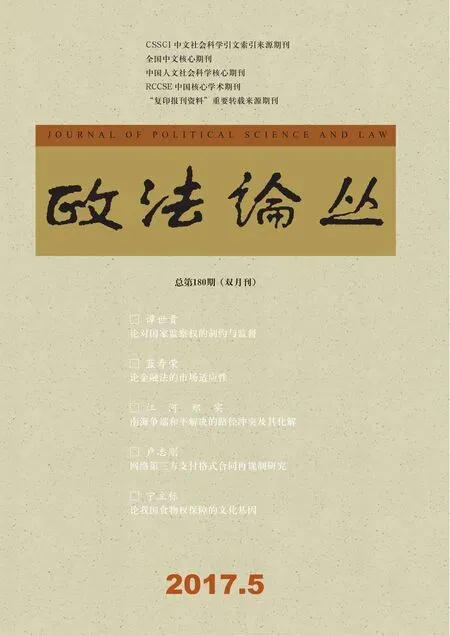诉讼机制不能解决行政权限争议问题之分析*
张显伟
(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诉讼机制不能解决行政权限争议问题之分析*
张显伟
(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行政权限争议问题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的阻碍。经由诉讼机制不能解决行政权限争议问题:从实定法视角论,经由诉讼机制解决行政权限争议既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又无可资操作的针对性程序;从产生的原因分析,行政权限争议并不具备诉讼解决的基础条件;从裁判主体方面考量,我国法院当下还不具备对行政权限争议问题施以司法裁判的资格,我国法官目前也没有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足够能力。行政权限争议问题的解决须仰仗立法,由国家权力机关作为解纷主体。
行政权限争议 公共利益 诉讼机制 行政诉讼
引言
行政权限争议亦称行政机关间权限争议、行政权限冲突,意指不同行政机关间因行政权力的积极行使或消极不行使而引发的行政权抵触现象。逻辑上可以将行政权限争议界分为“积极的行政权限争议”和“消极的行政权限争议”两类。“积极的行政权限争议”是指不同行政机关对同一个行政管理事项争抢管辖权,出现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或者重复处置现象,行政执法实践中“执法扰民”、“多顶大盖帽对付一顶小草帽”情形的发生是“积极的行政权限争议”的不良后果和形象表现;“消极的行政权限争议”是指没有哪一个行政机关对某一具体行政管理事项行使管辖权,不同行政机关间相互推诿,致使行政相对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投诉无门、控告无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行政机关上下级的关系类似一种“命令——执行”系统,自上而下单向运行特点明显,上下级行政机关间不可能存在行政权限争议,虽然同级行政机关数量众多,块块管辖不同的行政事务,但是,下级行政机关几乎没有太多的自主权、主动性,需要均仰仗上级行政机关的指令、命令具体运行行政权力,同级行政机关间权限争议现象也鲜有出现,至少在公开媒体上未能觅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开始逐渐向地方放权、分权,以调动和发展地方的积极性、能动性。随着分权式行政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各行政机关在自身职权范围内对所管辖的行政管理和服务事项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判断权、决定权和自主权。但是,由于行政管理和服务事务的复杂、交叉、分割,再加上现行行政机关组织法的疏漏、粗燥与不尽理性,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权限的交叉、重叠、冲突在所难免。2000年以来,行政权限争议问题大有普遍化发展态势。①行政权限争议问题的出现实质上是行政权力之间功力互耗,是不同行政机关间分工与合作关系出现不和谐的明显体现,而行政机关间的不协调乃至相互抵触,显然有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正是通过行政权力在不同层级政府单位之间的分配,使得庞杂的公共事务的治理成为可能,纵向与横向的权力分割不仅缩小了治理的距离,而且提高了治理的效率”,[1]P413行政权限争议无疑将阻碍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近年来,行政权限争议的现实反映出其不仅损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且因为不同行政机关间相互抵触、公权力之间内耗互损,致使公共秩序处于混乱状态,政府在社会民众中的公信力也因此受到极大贬损。总之,行政权限争议的出现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极大地阻碍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
客观说,行政权限争议在市场经济条件和分权式行政体制改革背景下是不可绝对避免的。现实的作法是:一者通过行政机关组织法的完善,极力明晰不同行政机关间的权、责边界;再者建构行政权限争议解决法律机制,对一旦发生的行政权限争议纠纷案件进行裁断,判定诉争权力性质和归属,讯及且科学理性地定纷止争。为顺畅解决行政权限争议纠纷案件,近年来国内有学者提出经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该类争议的理论建议(对这些学者以下简称“肯定派”),并就行政权限争议行政诉讼解决机制的具体建构等展开学术分析。②勿容置疑,通过行政诉讼机制解决行政权限争议具有一定优势:该机制的设置及运行符合司法最终解决原理,有助于彰显现代法治理念,若果该机制能妥当运行必将利于行政权限争议的理性解决和极大减少该现象的出现等等。笔者认为在正确回答“行政权限争议可否经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这一问题之前一定要解决以下几个基础问题:一是将行政权限争议纳入行政诉讼机制解决在当下中国有无现行法律依据;二是目前我国法院有无资格对行政权限争议案件进行解决?从事行政审判活动的法官能否胜任行政权限争议案件的审理并作出客观、正确裁判;三是行政权限争议案件是否具备诉讼解决的基础条件。这几个问题是判断可否将行政权限争议纳入行政诉讼机制解决的前提和根据。
一、缺乏明确法律依据
“肯定派”学者多从应然法角度展开分析,他们认为从现行《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目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和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等的规定出发,可以推理出经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行政权限争议是“可以的”或者是“应该的”这一逻辑结论: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一条明确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核心目的。“积极的行政权限争议”意味着不同行政机关间相互争抢管辖权,对同一个行政管理事项都进行处置,当然会出现重复处置、多头执法、一事再罚、执法扰民现象,这显然是严重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消极的行政权限争议”则意味着没有哪个行政机关愿意对某一具体的行政管理事务行使管辖权,各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投诉均不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控告、申诉长期得不到解决,无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保护。总之,行政权限争议的出现是不利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保护的”,而将该类争议交由专门解决行政纠纷案件的行政诉讼机制解决是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所以,肯定派学者认为将行政权限争议交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是契合行政诉讼目的。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六条明确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规定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该原则也是行政诉讼区别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而且也是行政诉讼之“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一诉讼目的实现的具体载体。行政权限争议是因为行政权力的积极行使或者消极不行使造成的,在权力法定和行政法治前提下,理论上论,每一例行政权限争议案件的背后一定存在着行政违法现象,或者说行政权限争议往往意味着有行政违法情形存在,因此,对行政权限争议案件的诉讼解决亦即可以查明行政违法。因此,“肯定派”认为将行政权限争议交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是“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这一行政诉讼特有原则实现的应然举措和必然要求,同时也利于实现行政诉讼目的。正如有学者所言:“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实现离不开对行政机关权属争端的诉讼解决”[2]
“基于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规定,完全可以将行政权限争议纳入到行政诉讼机制解决”。[3]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法律依据是《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该条规定并非是本案的原告、被告,但是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或者同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可以通过申请或者由法院通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行政诉讼。行政权限争议实质上受损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司法实践中不少行政权限争议案件是因为行政诉讼的提起而引起社会关注的,假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将行政权限争议的一方作为被告推向法院,毫无疑问,与被告发生行政权限争议的另一方行政机关是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行政权限争议的处理将成为行政诉讼案件解决不可回避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肯定派”认为,现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中内涵了“可以经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行政权限争议”这一结论。对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
第一,从实在法视角分析。“法律”绝对不可以是一种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应然”,其必须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法律文本、判例和具体的法律规则。马克思法学基本原理认为,“法律由规则、原则和概念三种要素构成,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都是客观存在的实在物”,[4]P92恰恰是依靠具体、明确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法律”才具有了指引性、可操作性、和预测性,才可以对社会关系起到现实、有效的调整作用。如果“法律”是虚无缥缈的、不可捉摸的“应然”或者是“理想”,那么就根本无法对社会生活进行具体的指引,人们也根本无法依靠理想的“应然法”对社会关系的发展进行预判,应然法将丧失法规则的一切优势,泯灭法规则的所有特色。从《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目的、基本原则、第三人制度等的立法规定中我们的确可以推理出“行政权限争议可以纳入行政诉讼机制解决”或者“将行政权限争议纳入行政诉讼机制解决是应该的”结论,但是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却没有任一条款明确规定行政权限争议案件经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所以,从实在法视角分析,行政权限争议经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是不可以的。
第二,从政治体制上推演。我国宪法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有明确规定,《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该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已经得到历史和现实的确凿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意味着各级人民法院是权力机关所立法律、法规的司法机关,人民法院无权创造法律,只能以权力机关颁行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受理并审理纠纷案件。综观我国权力机关所立的法律、法规,均无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与审理行政权限争议案件的明确规定。所以,从政治体制上推演,行政权限争议经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是不可以的。
第三,从法律适用原则角度展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法律适用原则,该原则既是“人民大表大会制”政治体制对司法工作的具体要求,也是“人民大表大会制”政治体制在司法工作中得以保障的准则依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要求我国的人民法院受理哪些案件、对已经受理的案件如何具体审理、审理之后应该作出哪几种类型的裁判、每一种类型的裁判应该在何种情形下作出等等,均必须以现行“法律”为准绳,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人民法院不得僭越。我国现行立法包括《行政诉讼法》,均无“行政权限争议经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的明确规定。相反,《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关于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规则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并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人民法院决不得仅仅评籍对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扩张性解释与合情理推演而从事行政诉讼活动。所以,从法律适用原则角度展开,行政权限争议经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是不可以的。
二、无可资操作的针对性程序
法律程序是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得以具体实现的依仗,法院对争议案件的处理必须通过法定诉讼程序完成。诉讼程序作为法院处理所受理案件的方式、方法、步骤、顺序、时限等方面的立法规定,蕴含着诸多价值理念,在此不作展开论述。不可否认,诉讼程序作为十分具体的操作性规程,可以为法院和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指引,依据诉讼程序的导向,法院和法官就可以顺畅地对案件施以审理并作出法定的裁判。没有诉讼程序的明确指引,法院和法官将不知如何指挥当事人对所收集、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质证,也无法确定对何种证据材料作以认证、对何种证据材料予以否定,无法评判业已认证的证据是否达到诉讼证明标准的基本要求,更无法知晓应该作出何种类型的裁判。总之,法院和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与裁判绝不可须臾缺乏诉讼程序的具体指引。
我国对行政纠纷案件诉讼审理最初适用的是民事诉讼程序。事实上,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是两种区别明显的纠纷解决机制,它们分别解决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纠纷案件,二者在受案范围制度、当事人制度、证据制度、裁判类型制度等方面均存在着截然差异。适用民事诉讼的方式、方法、步骤审理行政纠纷案件显然是非科学、不理性的,是行政法治发展初级阶段的暂时之举和权宜之计。随着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1990年《行政诉讼法》正式颁行,但该法在诉讼程序的安排上深受民事诉讼程序立法规定的影响,毫无自身特色,仅设计了一套行政诉讼一审程序,即一审普通程序,而且行政诉讼一审普通程序的具体运行极类似于民事诉讼一审普通程序,各类不同行政纠纷案件的诉讼审理毫无差异地均适用统一的、类似于民事诉讼一审普通程序的程序,致使实际审理中问题很多。我国有学者对当时行政诉讼程序运行的问题进行了形象描绘:“行政诉讼程序设置的无特色和没有针对性很大程度地造成了行政纠纷案件审理不畅,行政审判实践障碍重重和步履维艰。[5]P107”2014年新修正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一审程序进行了一定完善,在一审普通程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审简易程序,这大大提升了行政诉讼程序的法治化水准,但是却远未能实现行政诉讼程序的精细化和针对性。
“程序相称”是现代诉讼程序原理之一,“程序相称是指诉讼所设置的程序要与处理的案件类型和当事人利益满足相适应”,[6]P107当今世界法治先行国家和地区在诉讼程序上不仅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三大不同类型诉讼制度建构了不同的诉讼程序,既便是在每一个诉讼制度内部也在现代法治理念的指导下设置了精细的处理专门特定类型纠纷案件的针对性诉讼程序。具体在行政诉讼上就是针对行政纠纷案件的不同类型,一一设计了有别的专门化审理该类行政纠纷案件的程序,在审理的具体步骤、方式、方法和原告资格的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起诉期限的长短要求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异性设计。日本现行《行政案件诉讼法》将行政诉讼分为抗告诉讼、民众诉讼、当事人诉讼和机关诉讼四种类型, 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当事人制度、起诉的条件、举证责任等的规定上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分别设置具体的、针对性审理程序;“根据法官审判权的大小,法国的行政诉讼区分为完全管辖权之诉、撤销之诉、解释及审查行政决定的意义和合法性之诉以及处罚之诉四类”,[7]四类不同的行政诉讼也分别设置了不同的诉讼程序;“美国存在着政府诉讼类型,当地方政府与州之间或者地方政府之间就其权限、利益发生冲突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有点类似于英国的特权令,不同的特权令其申请的条件和法院处理的程序各不一样”;[8]我国台湾地区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四条至第八条将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界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三种类型,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行政纠纷案件一一设置了不同的审理程序。正如有学者所言:“各国的行政诉讼,习惯上仍循一定之方式、形式或类型,原告始得就其所受侵害,请求行政法院提供救济,而行政法院亦得仅就法定之诉讼种类所相应得以救济之方法为裁判”[9]P169,“行政诉讼的类型化设计及其诉讼程序的针对性安排,既有利于全方位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又有利于司法机关有效、公正地行使行政审判权解决行政纠纷”。[10]
行政权限争议不同于一般类型行政纠纷,该类纠纷的主体双方均为行政机关,该类纠纷在性质上不是主观权益的争议,而是对某一具体行政公权力归属的判定,是典型的客观诉讼。我国《行政诉讼法》设置的审理程序针对的均是“官、民”之间的行政纠纷,是“民”为了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而诉请法院对“官”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该类案件属于典型的客观诉讼。泾渭分明、截然有别的两类不同类型纠纷案件,适用同样的程序进行审理,显然是无法奏效和极不科学的。源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能针对行政权限争议案件的诉讼解决设置针对性程序,所以,经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行政权限争议案件是不可以的。
三、不具备诉讼解决的基础条件
诉讼虽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最重要、最权威、最公正、最公开的机制,但是,正如世间万物一样,法规则统治下的诉讼机制也绝非是完美无瑕的,诉讼机制也具有天生固有的局限性。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各国的诉讼机制都或多或少地显示出危机的迹象,③我国研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著名学者范愉教授认为:“诉讼具有纠纷解决的特定性和新型纠纷的局限性、判决结果不符合情理、诉讼成本高昂、积案及迟延、诉讼与审判的公开性等一些固有的局限性”。[11]P22-24笔者同样认为纠纷解决的诉讼机制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且这种局限性也一定具体体现在多个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源于诉讼机制与法律规则的须臾不可分离关系,诉讼机制只能适用于解决法律纠纷,在法规则的指引下解决依照有效法规则规定解决纠纷。诉讼被当今社会公认为是法治的明显表征,因此诉讼应该在法规则的主导下运行。正如有学者所谓:“在法律主治的视野下,诉讼要求努力做到凡事皆有法式”,[12]美国法学家富勒也曾经指出:“法院难以审理非法律性质的和多极的纠纷”,[13]那些法律规则不清、专业性强、当事人之间地位不平等特征的社会纠纷,因为法律规则和公共政策的不确定使得法官难以下判,判决的形式合理性及程序公正取向难以达到实质公正,社会效果不佳。总之,纠纷付诸于诉讼机制解决的基础条件是该类纠纷应该是法律纠纷,非法律性质或者法律规则不清引发的纠纷不具备纠纷诉讼解决的基础条件。
正如医生治病必须首先探究病因一样,为理性地解决行政权限争议,我国学者对该特殊类型争议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和客观分析,黄显雄教授认为:“权限争议即行政主体之间由于行政权限所引发的争议,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由于立法的缺陷或者其他复杂原因,而与另一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冲突或重叠而产生的法律争议”;[14]张忠军教授将行政权限争议产生的原因归纳为:“法制不健全、体制方面、转轨的现实、经济社会事务的复杂性和关联性等四个方面的原因”。[15]行政权限争议产生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学者们一致认为立法缺陷一定是该特殊类型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深层次原因。如果现行立法对不同行政机关权力的纵向边界和横向边界都作以清晰界定、科学划分和理性配置,各个不同行政机关依据科学理性的立法界定各司其责,就不会有行政权限争议这一不尽人意现象的出现,行政权限争议产生的背后一定存在着立法对某一行政管理事项缺乏安排或者立法对某一行政管理事项规定得不科学。[16]P205既然立法原因是行政权限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深层次原因,那么,行政权限争议实质上就是法律规则不清的社会纠纷或者是非法律性质的纠纷,因此,该特定类型争议也就不具备诉讼解决的基础条件。
既然行政权限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深层次原因是立法缺陷,那么,从产生的原因角度对症下药,必须经由立法解决行政权限争议,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也因而就是行政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关。在我国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亦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在我国解决行政权限争议的国家机关只能是国家权力机关,而不可以是专司法律的法院。笔者认为,经由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弥补立法的漏洞或者完善立法的缺陷,制定完备、科学、理性的行政机关组织法是行政权限争议力避最重要、最现实可行的举措。
四、尚无适格的裁判主体
裁判主体具有一定裁判的资格、能力、资质是确保裁判客观、公正和具有说服力,进而达到裁判社会效果的要求。尚无适格的裁判主体,此处特指在目前情况下法院尚不具备资格,同时法官也不具备能力对行政权力的归属进行断定并作出理性裁判。虽然行政权限争议具体表现为不同国家行政机关间对某类行政权力的争执,要么是积极地争抢对某事项的行政管理职权,要么是消极地推诿对某事项的行政管理职责,源于行政的公益性与公共性,行政权力所掌管的事务实为公共事务,公共事务背后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因此,行政权限争议的实质是不同公共利益间的冲突、抵触。法院和法官对诉争权限归属的判定活动在逻辑路径上可以界分为三个密切联系、前后相继的阶段:第一阶段,需要对诉争的利益是否为“公共利益”进行判定;第二阶段,需要在明确判定为“公共利益”,亦即需要纳入行政管理范围的基础上,再对不同的“公共利益”进行权衡、考量进而作出协调或者具体割舍与处分;第三阶段,对诉争的公共事务管辖权作出由哪个行政机关具体行使的权威裁判。很显然,法院和法官对诉争利益是否为“公共利益”以及对不同“公共利益”进行权衡、考量和协调、处分继而作出判定的前提和基础是法院有资格和法官有能力。让没有资格和能力的主体去评判诉争的利益是否为“公共利益”同时作出权衡、考量、协调、处分继而作出裁判显然是非理性的,如果这样作,法院和法官所作出的裁判也不可能是客观、公正和具有社会公信力的。笔者认为,我国目前情况下法院尚不具备资格,同时法官也不具备能力对行政权限争议案件施以裁判,理由是:
第一,法院没有资格对行政权限争议案件施以裁判。即我国的法院并不具有对该类特殊类型争议案件进行受理、审理和作出司法裁判的资格和资质。因为:
其一,“公共利益”是一个难以在法律上明确的概念,让法院判定公共利益不合适。正如文上所述,对行政权限争议案件的裁判首先需要判定诉争事项所代表的利益是否为“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虽然现实存在,但却是一个十分宽泛而且极易变动的概念,正如有学者所言:“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概念,至今尚未形成被广泛认可的定义,法律对公共利益的涵义和覆盖范围一直缺乏清晰界定”,[17]P103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立法明晰“公共利益”的内涵,同时厘定“公共利益”的外延,为法院的判定活动提供准绳?实际上,通过立法对“公共利益”进行确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公共利益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术语,现实世界各国立法均无从觅到对公共利益的立法界定,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却并非是一个可以在法律上明确其内涵的概念,即便对公共利益的内涵通过反面排除的方法来加以定义,在现行域内外各国的法律文件中也无法觅到”。[18]笔者以为,让专司法律法院去评判一个非法律可资界定的概念,再对之进行权衡、取舍,作出裁判,显然有悖于司法认知法律活动基本规律的要求,④。亦即法院没有资格对行政权限争议案件进行解决。
其二,法院并非是“公共利益”代表的主体,让法院权衡、取舍、协调、处分公共利益不合适。法院是中立的裁判机关,法院所从事的基本工作是对孰是孰非进行事实判定,并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进行裁判,司法工作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好恶和情感倾向,“就司法机关和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来说,司法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表现为一种刻板的、保守的机械性活动”,[19]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如果允许法官创制法律,制定法就会失去普遍效力,只要法官不采用制定法而自行确定法律,他的决定就因世界观和国家观念的差异而难免主观,这样法律的安全、司法的统一、判决的可预见性都将受到严重危害”。[20]P110司法工作的中立特点决定了法院不可以成为某个利益的代表者,不可以对利益进行价值倾向权衡。当今时代是民主法治大发展的时代,民主制政治体制诉求大家的事情由大家说了算,由大家表决,最后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进行裁断。很明显,公共利益是大家的利益,亦即是大家的事情,当然理应由大家作主。如今,代议制民主是世界最普遍、最理性的民主形式,因此,有资格代表公共利益的也只能是选民选举所产生的代议制机关,而非是对事实进行客观判断、中立裁判的法院。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法院并不具备作公共利益代表人、代言人的资格。因此,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宪政格局下,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的只能是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现实中国法院和行政审判法官没有资格对行政权限争议案件施以裁判。
第二,法官没有能力对行政权限争议案件施以裁判。案件的裁判是由法官具体作出的,法官具有作出相应裁判的能力是裁判客观、正确和具有公信力的基本要求。行政诉讼是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诉讼,行政诉讼的标的是行政行为,行政审判实际上就是对行政机关业已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评判。行政权限争议案件的审理离不开对诉争权力所实施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判定这一基础,亦即,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判定是行政权限争议案件审理所无法回避的,只有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客观断定,才可以对行政权限的归属作出正确、理性的裁判。而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客观断定的确需要裁判者具有相应的能力。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法国针对行政纠纷案件的诉讼解决单独设立了行政法院,对行政法院的行政审判法官具有特定从业条件的特别要求。法国行政法院的行政审判法官任职条件里有行政经验和法律知识的双重要求,并通过一系列人事、组织方面的制度安排使得该条件得以落地,“法国对行政法官的选拔相当严格,如最高法院的法官初级成员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优秀毕业生,高级成员主要是由内部晋升,极少部分是由外界高级行政官和专家中选任”。[21]同时,“为保证行政裁决尽可能地适应行政实际,确保行政裁判的客观、正确,大力增长行政审判法官的行政知识和经验,法国还确立了行政审判法官的兼职和外调制度”。[22]P373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英国和美国源于法律适用平等的司法理念,虽没有单设行政法院,行政审判的法官也是普通法官,并无特别任职条件的刻意要求,但是,“英国、美国等法治先行国家尊奉行政救济穷尽原则,亦即所有的行政纠纷案件必须历经行政渠道,由专门设立的解决行政纠纷的中立性机关率先解决”。[23]英国设立了行政裁判所,美国设立了独立管制机构,并且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和美国的独立管制机构数量众多,往往因应行政纠纷性质的不同而分别设立,这一因事专设的机构也较大程度地确保了这些机构对该特定行政纠纷案件解决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机构的工作人员往往具备足够的解纷能力。而在我国,并没有专门审理行政案件的行政法院,我们实行的是普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行政审判体制。在法官方面,现实中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并没有区别于民事、刑事审判法官的特别技能、知识、阅历、职业操守等方面的另行要求和专门规定,只要具备一般的司法资格,同时在政治上、思想道德上过关,经过遴选就可以从事对行政纠纷案件的审理。如此的行政审判法官准入条件,意味着从事行政诉讼案件审理的法官可以没有基本的行政职业能力训练,可以不具备丝毫的行政执法经验,而让这样的人员来评判专业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显然十分牵强,特别是针对那些专业性很强、技术性要求较高的行政行为,让外行去评判该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其作出的程序是否合法,根本是不可能的。现行法律对法官从业资格的要求绝对无法确保从事行政审判工作的法官具有审理行政权限争议案件的基本能力和起码条件。
展望
为加速推进并尽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权限争议问题亟待高效、理性解决,行政权限争议问题的解决需要基于本国的法治传统和现实国情,尤其是本国的政治体制。在实行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比如美国、德国等,国家机关间的权力义务之争是由法院通过违宪机制解决的,[24]P648只是源于法治传统的不同,美国的违宪审查由普通法院行使,而德国的违宪审查由联邦宪法法院行使;日本基于其自身法治传统和现实国情,在现行《行政案件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了中机关诉讼类型,机关诉讼专司解决国家公共团体相互间是否存在权限或者与行使该权限有关的纠纷的诉讼。[25]P152我国法治传统上从没实行过真正意义的违宪审查,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除了通过宪法的条文肯定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了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机构外,还在第二十七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当下中国的现实国情也决定了行政权限争议问题经由行政诉讼机制解决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从源头论,我国不同行政机关间分工、合作关系的明确,权力边界的清晰,需要依靠科学、理性、民主的立法,尤其是行政组织法,行政组织法是力避行政机关权限争议问题的法治基础和可靠保障。科学完善的行政组织法体系,可以从应然角度对整个行政组织法律作一个宏观建构,所制定的行政组织法律规范对象明确、疏密有致,行政组织法规范层级结构自治,从而保障法制统一,克服行政组织无序,避免行政组织结构不合理与规模膨胀,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权力交叉,事前预防或者尽量避免行政权限争议问题的出现。当然,缘于法律语言天生的模糊性与抽象性,缘于立法活动固有的滞后性,再加上行政权力本性上持有的扩张性以及社会公众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期待的逐日提高等多重因素,可以预见,一国的行政机关组织法不论如何完善、如何具有理性,行政机关间权限争议案件的出现仍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在现行法律制度体系内建构一套科学理性的行政权限争议解决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在我国,行政权限争议解决机制的掌控者应该是国家权力机关。不可以是法院或其他别的国家机关,为确保国家权力机关高效、理性解决行政权限争议问题,应该为国家权力机关裁断行政机关间权限争议建构相匹配机制,构建具体的针对性操作程序,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和规则支撑。
注释:
① 比如:2001年四川广元交警部门与广元农机部门间的权限之争,参见华君:《部门之争若煞无辜百姓》,载《山东农机化》2002年第13期;2001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与国家质检总局就天津“小站稻”地理标志认证权限之争,参见嵇哲:《工商质检不统一,天津“小站稻”内战何时休》,http://www.enorth.com.cn,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5月3日;2003年河北某集市建设局和晋州市运管部门的权限之争,参见赵永兵、刘波:《两地政府部门争议未决道路运输证苦了辛集“的哥”》,载《燕赵都市报》2003年3月3日;2003年湖北襄樊市市、区两级检疫部门为争夺肉类检疫权权限之争,参见胡杰:《争夺检疫权:襄樊市市、区两级检疫部门大打出手》,载《北京青年报》2003年12月8日;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与水利部就淮河流域水域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总量评定权限之争,参见覃爱玲:《环保总局与水利部之争,两大部委针锋相对之谜》,载《瞭望周刊》2005年4月20日;2006年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围绕小额贷款公司改革主导权之争,参见杜艳:《银行业两监管部门斗法,小额贷款公司处境尴尬》,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1月14日;2007年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就手机电视主导权权限之争,参见焦立坤:《广电总局强调手机电视归属权,必须纳入媒体管理》,载《北京晨报》2007年8月22日;2009年7月河南桐柏县交通局与湖北省随州市公路管理局关于淮河大桥修缮的权限纠葛,参见2010年6月9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管不了的危桥”;2009年下半年来,文化部与新闻出版总署围绕“魔兽争霸”网游监管权归属而发生的一系列明争暗斗,参见厉尽国:《法治视野下的行政权限争议及其解决——从“魔兽争霸”网游监管权之争谈起》,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② 详见王太高:《论机关诉讼——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一个思路》,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9期;黄显雄:《论我国行政机关权限争议的法律规制——从几例部门之争说开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邓可祝:《机关诉讼研究》,载《行政与法》2007年第4期;吴卫军、张峰:《行政权限争议的司法解决——论我国机关诉讼的构建》,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高艳、刘大中、金玲:《论行政权限冲突的化解路径——基于冲突理论的探讨》,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③ 参见[英]阿德里安.A.S.朱克曼主编,傅郁林等译:《危机中的民事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④ 规范法学派创始人美籍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认知法律的活动是一种“概念性”法学,而不是别的什么,我们不可能离开概念进行构思”。参见Kelsen, Juristischer Formalismus and reine kechtslehre ,58 Juristischewochenschrift(1929).1724.cited from The Jurisprudence of Interests, trans. and ed.by M. Magdalena schoch, Harvard university,1948,p.54.
[1] Robert Agranoff.JPART Symposium Introduction: Re—searching Intergovenmengtal Relations.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4,14(4):443-446.
[2] 胡肖华,徐靖.论行政权限争议的宪法解决[J].行政法学研究,2006,4.
[3] 于博.略论中国行政机关权属争端之解决进路——以行政诉讼为主轴的多元主义视角[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7.
[4]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5] 杨伟东.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行政审判权纵向范围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
[6] 张艳丽.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结构的类型化[J].政法论丛,2015,3.
[7] 马怀德.完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诉讼类型化[J].江苏社会科学,2010,5.
[8] 孔繁桦.论作为客观诉讼之机关诉讼[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9] 蔡志方.行政救济法新论[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0.
[10] 邓可祝.机关诉讼研究[J].行政与法,2007,4.
[11] 范愉.非诉讼程序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2] 张志铭,于浩.现代法治释义[J].政法论丛,2015,1.
[13] Lon.I.Fuller,“The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92 Harv.L.Rev.353.转引自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9,3.
[14] 黄显雄.论我国行政机关权限争议的法律规制——从几例“部门之争说开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2.
[15] 张忠军.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及其解决途径[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3.
[16] [德] 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M].林明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7]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18] 侯淑雯.司法衡平艺术与司法能动主义[J].法学研究,2007,1.
[19] 金国坤.行政权限冲突解决机制研究:部门协调的法制化路径探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0]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1] 张显伟.行政诉讼对行政审判体制的诉求[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2.
[22]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3] 谢维雁.中国宪法诉讼存在论[J].现代法学,2009,1.
[24] 莫纪宏.实践中的宪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5] 薛刚凌主编.外国及港澳台行政诉讼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TheAdministrativeLitigationMechanismCannotSolvetheDisputeofAdministrative
ZhangXian-wei
(Law and Politics School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08)
Administrative dispute has become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to promote obstac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aw,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mechanism to resolve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is still lack of clear legal basis, there is no operational procedures for the 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qualification and ability of the subject of the referee, at present, the courts of our country do not have the qualification of judicial adjudication in the case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trial judge has no ability to carry out judicial review on the legitimacy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In our country, the power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dispute should avoid relying on legislation, its rational solution depends on the state power organs.
the administrative right disputes; public interest; litigant mechanism;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1002—6274(2017)05—082—08
DF74
A
(责任编辑:唐艳秋)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与发展的行政法问题研究”(GD16CFX07)、广东海洋大学2017年“创新强校工程”省财政资金支持项目“地方立法科学化实践的思考”(GDOU2017052617)的阶段性成果。
张显伟(1969-),男,山东微山人,法学博士,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广东省地方立法研究评估与咨询服务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立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