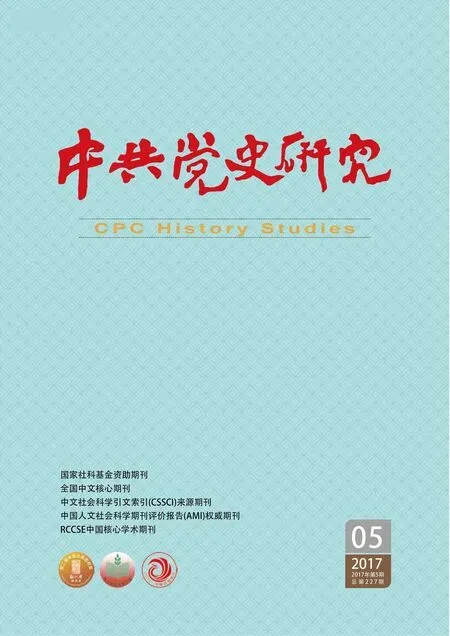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内部日常权力关系的再探讨*
〔美〕李怀印 张一平 张春龙
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内部日常权力关系的再探讨*
〔美〕李怀印 张一平 张春龙
本文利用对不同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访谈,重新考察改革前30年国营企业内部的政治生活,重点探讨工厂车间干部与群众之间以及积极分子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日常关系。本文质疑“新传统主义”理论在解释改革以前中国国营企业内部微观政治生活的有效性,认为干部与工人之间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存在不同程度的庇护与依赖关系,但强调当时车间内部的日常权力关系也受到诸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的制约。文章最后提出“单位社群主义”的概念,用来解读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日常治理实践。
国营企业;权力关系;“庇护—依附”关系;单位社群主义
导 论
长期以来,西方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微观政治研究,一直受到源自社会科学诸学科和区域研究的各种解释模式及概念架构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庇护—依附关系网络”(patron- client network)。始自20世纪60年代,一些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便开始运用此概念来研究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的乡村社会①参见Eric R.Wolf, “Kinship, Friendship and 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Complex Societies,” in Michael Banton, ed.,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Complex Societies, New York: Praeger, 1966, pp.1-22; John D.Power, “Peasant Society and Clientelist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2 (1970): 411-425;Arnold Strickon and Sidney M.Greenfield.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Latin America: Patronage, Clientelage, and Power System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ao Press, 1972;S.N.Eisenstadt and Luis Roniger, Patrons, Clients and Friend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ructures of Trust i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与所谓极权主义政权运用纯粹的高压手段不同,“庇护—依附”关系的运行涉及权力拥有者和追随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和互利互惠;权力拥有者为其追随者提供保护和利益,而后者则有效忠于前者的义务。正如James Scott在分析东南亚社会时所言,“庇护—依附”关系网络的流行,是因为“在控制财富、地位和权力方面一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以及“在人身安全、地位和职位或者财富方面相对缺乏有力的、非私人化的保障”*James Scott,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1 (1972): 91-113.。而对较为发达的社会的研究,则揭示了一种新型的“庇护—依附”形态,例证之一便是群众性政党与其选民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更加非私人化、更为对称的、官僚化的、工具理性的且短暂的关系,它不同于传统社会中旧的“庇护—依附”关系,后者的运作乃是基于面对面的互动、无所不在的道德责任以及持久的情感纽带*参见Alex Weingrod, “Patrons, Patronage, and Political Par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0.4 (1968): 377-400;Mario Caciagli and Frank Belloni, “The ‘New’ Clientelism in Southern Italy: 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in Catania,” in S.N.Eisenstadt and Rene Lamarchand, eds., Political Clientelism, Patronage and Development,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1., pp.35-56;Jonathan Hopkin and Alfio Mastropaolo, “From Patronage to Clientelism: Comparing the Italian and Spanish Experiences,” in Simona Piattoni, ed., Clientelism, Interests,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52-171.。
Andrew Walder对中国改革前后的工业企业的分析,即是运用“庇护—依附”关系模型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最佳例证。他认为,与凭借高压政策或者意识形态手段不同的是,工厂车间层面的领导通过运用“有原则的区别对待”(principled particularism)来确保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顺从。所谓“有原则的区别对待”,即是说,那些“积极分子”亦即忠于领导的工人会有更多的机会晋升、涨工资、发奖金、入党,或是在分房和工作安排方面享有优先权,从而导致工人们在组织上依附于车间领导。这种情况由于当时工人们没有跳槽机会、生计上全面依靠本单位,因而显得尤为突出。Walder发现,工人群体的分化,并非基于教育、资历或是技能的不同,而是主要取决于他们和车间领导的关系,大体可分为忠于领导的少数积极分子和占工人群体绝大多数的非积极分子。他进一步认为, 普通工人尽管对那些享受特权的积极分子心怀不满,对他们跟领导之间“正式的庇护—依附网络关系”抱有敌意,但在供应短缺的年代,为了生计还是会跟厂领导私下拉关系,从而形成“工具化的私人关系”(instrumental-personal ties)。所有这些现象,构成了Walder所谓的“共产党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之所以“新”,是因为它不同于旧的“传统”概念,后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依附、顺从关系和任人唯亲现象,与现代社会注重独立、契约、平等之类的观念截然对立。而新传统主义所指的是中国工厂内部高度制度化的庇护—依赖网络,亦即党所提供的系统性的利益刺激(即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用自己对党的忠诚,换取职务上的提升和其他方面的奖励),以及干部与工人之间不稳定的、较为实用化的私人关系。所有这些都不同于以往从所谓极权主义视角所理解的共产党社会,以为那里只靠意识形态、精神动员加上严密监视所带来的恐惧来维持统治,排斥任何私人关系的空间,也拒绝新传统主义所体现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结合。*Andrew G.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尽管新传统主义论对当代中国领域的研究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学术界也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解释。一些批评者认为,总体而言,在中国社会包括工厂生活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庇护—依附”关系网络,但是他们质疑这种关系在车间层面流行的程度,质疑运用这种模式来分析整个工厂系统的适用性,还质疑在工厂政治中存在的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的分化*Deborah Davis, “Patrons and Clients in Chinese Industry,” Modern China, 14.4 (1988): 487-497; Elizabeth, J.Perry,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World Politics, 41.4 (1989): 579-591; Marc Blech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th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ook review), Pacific Affairs, 60.4 (1987): 657-659; Brantly Womack,. “Transfigured Community: Neo-Traditionalism and Work Unit Socialism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26 (1991): 313-332.。遗憾的是,这些批评主要是基于评论者大而化之的观察和推论,很少有人运用从实地调查获得的确凿证据来证实他们的批评。
鉴于此,本文以笔者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对全国各地97位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访谈结果为依据,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这97位退休人员分别来自上海(19位)、北京(11位)、江苏(14位,主要来自南京)、湖北(28位,主要来自武汉)、浙江(5位,均来自宁波)、辽宁(5位)、广东(3位,均来自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本合作课题的参与者包括研究人员、大学教师以及来自上述城市的研究生,受访者来自其家庭成员、亲戚、朋友或熟人。所有受访者均曾于1949—1976年间一度在国有企业当工人或任干部。在这97位受访者当中,39位曾担任国有企业某个级别的干部(5位工厂领导、7位车间领导、11位小组领导、1位党支部书记、1位工会主席、2位工程师、3位技术员、2位质检员、6位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1位教师),剩下的均是普通工人。这些人来自不同领域(18位在机械工业、15位在纺织工业、8位在冶金工业、7位在电力行业、9位在石油行业、4位在化工工业、4位在矿业、5位在建筑业、5位在交通业、6位在食品加工业、3位在化肥制造业、3位在工具行业、2位在橡胶业、1位在医药行业、1位在印刷行业、1位在塑料产品行业、1位在灯具制造业,还有4位在不同的后勤服务部门)。对这97位退休人员的访谈基于一份标准问卷,包含了43个问题,涵盖他们在工厂生产方面以及不同年代政治活动的个人经历。每次访谈都留有一份3000字至1万字左右的书面报告。*本研究所使用的访谈记录编号由一个大写字母和一个阿拉伯数字组成,其中字母B指在北京的访谈(黄英伟负责)、C指在南京的访谈(张春龙负责)、H指湖北武汉等城市(江满情负责)、L指南京(勇素华负责)、S指上海(张一平负责)、N指宁波和广州(胡光霁负责)、W指武汉(狄金华负责)、Y指山东以及华北其他地方(王克霞负责),阿拉伯数字表示访谈记录文档的序号。
本文首先对毛泽东时代的工厂领导结构进行总体分析,然后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是干部与工人之间的总的关系,重点是他们在日常生产和政治活动中的互动情形,尤其是影响领导决策及其与工人关系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约束机制。第二是那些影响物质利益分配和政治激励的各种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核心问题在于,这些利益和机会是仅仅因为一些工人忠于领导而会分配给这群少数的特定人群,还是会根据公开的规章制度而分配给所有的合格工人,而干部在分配过程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偏袒那些忠于他们的工人。第三是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关系,核心问题在于,这两群人之间是否形成了明显的分化以及相互敌视。文章最后还将讨论此项研究对于重新认识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日常社会政治关系之含义的意义和价值。
一、干部与工人的关系:一个总的评估
(一)工厂领导的三个层级
厂长和党委书记是国营企业的最高领导。厂长负责具体执行企业的生产任务,书记则负责本单位的人事安排、大政方针以及政治思想工作。通常来讲,厂长和书记不会和普通工人直接接触,特别是在那些拥有数千或上万人的大厂,“厂长根本不下来”(S8),普通工人“可能只知道我们领导是谁,在橱窗里看到,平时看不到的”(S7)。即使在那些仅有数百名工人的小厂里,工厂领导也可能同样“和工人不搭界”(W5;另见W1)。
仅次于厂长和书记的是车间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他们多来自基层,从普通工人干起,因为“肯吃苦、技术好、表现好” 而获提拔(L5;另见L6,H4,W2)。车间领导的任务是确保按时完成或超额完成本车间的生产任务,也负责工人在车间之外的表现。遇有工人因生病或其他原因而缺勤时,车间领导要负责换上替补工人,以便完成生产任务(W5)。如果有人迟到或是缺勤,但又找不到备用工,车间主任就得亲自顶班(N1,W3)。如果车间遇有紧急任务,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车间主任及其他行政人员都须上阵,这在上海某食品加工厂屡见不鲜。为了避免原料腐烂,工厂会在收获季节动员所有人力,日夜不停地加工西红柿和蘑菇之类的作物(S8)。
但是,车间主任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本车间各生产小组中间起协调作用,给每个小组分配任务,监督各项生产活动。因此,除非另有要事(比如开会或是和厂领导协商问题),车间主任必须一直在场(H4)。另外,车间主任还得花费很多精力,用来处理诸如疾病、家暴、离婚等本车间工人的各种个人事务,以及生产小组组长无法处理的其他各种问题(B8)。
每个车间有若干生产小组,每位组长负责几十名工人。很多企业的生产是一天24小时三班倒,每班工作8小时,因此在组长上面,还有值班长;有些厂矿把生产任务分割成数个工段,每个工段只负责整个生产过程某阶段的任务,因此在组长之上还会设工段长。生产组长的基本职责是将具体任务分配给小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组长还要在开工前组织15分钟到30分钟的政治学习。在完成8小时工作之后,组长通常还要组织工人开一个碰头会,一般不会超过10分钟。例如在广州华侨糖厂的碰头会上,组长要和大家进行讲评,“今天我们的生产怎么样,生产了多少糖,出现了什么问题,哪些好人好事,明天大家再来上班要注意什么什么”(N10)。
(二)当干部的代价和特权
组长除履行上述职责之外,承担和普通工人一样的生产任务。因此,在工厂的所有干部中,组长的权力最小却是“最苦的”(S1,S6)。遇有最困难、最危险的任务,比如发生事故或其他紧急情况时,组长需“身先士卒”(S4,W1,W2),否则会在工人中失去声望,工人因而会对组长表示“不服”(N7)。当生产任务结束,工人都下班回家之后,组长需留下来打扫地面,检查小组成员完成的工作。如果有人早退、缺勤,组长还得顶班。因此,组长通常是所有工人当中“最能干、最吃亏”的(S8),但工资跟其他工人差不多(S2,S5)。在讨论奖金发放的时候,组长还得把自己的机会让给别人(N7)。正如上海冶金局的一位普通矿工所说的:“你只有这样吃一点儿亏,以后干活才能把大家动员起来,大家干活才能积极。这个时候当干部是享受在后头,吃亏在前头的。如果你享受在前头,人家早就会对你有看法了。”(N2)难怪当时不少人觉得当一个基层干部就意味着“吃亏”(W1,N1)。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车间领导在某种程度上享有特权,因为不必亲自参加日常生产活动。然而,当车间遇有紧急任务或发生事故时,他们也需要和小组长一起“冲锋在前”。用上海第十七棉纺厂的一位前小组长的话说:“你做干部,不带头,完成不了任务,肯定位置坐不牢的。你到下面要摆平人家,肯定要先自己干出来。你要说服别人,得自己带头。另外,待人也要真诚。”(S7;另见N1)
遇有工资升级、发放奖金、分房或评选先进的机会,车间领导还得表现出无私、高尚的姿态。人们期待车间领导会把这些机会让给那些最合格的工人,“不能和群众去争”(S10;另见L8,N2,S20)。如在南京电信设备厂,一位退休会计称,该厂干部通常只会分到“最差”的公寓(L5)。而在南京某房管单位,一位车间主任的妻子曾经跟丈夫争吵不休,原因是该主任一再放弃自己的分房机会,结果单位不得不给他分房了事(L3)。
当工资调整时,干部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如在宁波港某机械厂,1971年普调时,全厂工人的工资涨5元,而干部的工资只涨2元至3元,这也是为什么来自该厂的受访者当时不愿意做车间主任的原因所在(N4)。在武汉钢铁厂机械制造总厂,情形亦复如此,“调工资时比较透明,工人涨得多,干部反而涨得少”(H12)。在发放奖金时,干部们同样得把机会让给别人。南京星火纺织厂的一个退休工人回忆说:“那时的干部要吃亏的,如拿奖金,如果车间内部不够分配的,领导一般自动降级。还有年终,厂里评奖,都要张榜公布的,工人拿一等奖的机会高于领导,而干部干得突出,一般拿二等奖或三等奖。”(L6)上海压缩机厂的一位原车间领导确认,在“大跃进”之后最困难的那几年,单位领导都得带头把自己的布票、肉票以及粮票退给政府部门,以缓解市面上供应紧缺的局面(S11)。而提拔为车间领导或是其他任何“脱产干部”,也意味着粮食配额从普通工人的标准(每月31斤)降低到干部标准(每月26斤)(H7)。在国营矿场,矿工的粮食配额标准是每月46斤,而干部则是32斤(H13)。因此,当时干部中间流行一句话:“升官不发财,粮食减下来。”(H6)当然,对干部来说,最艰难的日子应该是政治运动期间。每当运动到来,普通工人一般都“没事”,而干部通常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靶子(H11)。在“文化大革命”头几年,干部的日子最为艰困,其中大多数不得不“靠边站”甚至成为批斗对象(H14)。
毛泽东时代力图限制干部特权,缩小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这一作法部分地源自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在1949年前,中共干部提倡艰苦奋斗,与群众保持平等关系,同时鼓励群众自愿参与革命,发扬首创精神*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a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NY: Sharpe, 1995.。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对唯意志论的偏好,对于群众动员的着迷,以及对精英主义和官僚等级制度的厌恶,都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50年代早期短暂试验精英主义路线后随即加以放弃*Stuart Schram,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这种精英主义借自苏联,一度允许干部和技术工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从而导致干部和工人之间以及不同技术和工资级别的工人之间形成明显差别。然而,毛泽东时代限制干部特权以及提倡干部和群众平等的另一层更加根本的原因,则与下列两个因素的交织作用有关:一方面,国家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而不得不最大限度地抽取资源、扩大投资;另一方面,有限的资源又使得国家不得不优先考虑通过保证城市人口的充分就业来确保其生计,这便意味着国家必须避免特权官僚以及工人精英的产生, 否则他们会与国家及其他人口争夺有限的资源。为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国家只能重视运用政治激励或其他非物质手段,而不是运用物质奖励;在生产和收入分配过程中,亦只能致力于缩小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差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形塑干部和工人之间关系的各种制度安排。
(三)与工人的关系
在毛泽东时代,工厂领导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群众关系”“与群众打成一片”(H20)。我们的受访者一般都认为,除个别比较孤僻的干部之外,“那个时候领导还比较积极地关心下面的人”(S8),“当时干部很注重与普通工人的关系”(H3;另见L3)。宁波和丰纺织厂的一名退休人员这样描述她的车间:“厂里的车间主任都是参加劳动的,那是比较艰苦的,你如果自己不带头的话,那下面的工人都会不认真干活的。比如说,车间主任会经常来车间,一方面是和工人接近,一方面看看大家工作做得怎么样。那我们在车间主任下面有班长,在班长下面还有组长。车间主任有指标任务的压力。比如说天气热了,车间主任会送洗脸水来,那是关心工人嘛!夏天的时候车间很热的,我们就会想,你们坐科室的真舒服,我们累死累活的!这个就是说,车间主任跟工人的关系要融合,不然你生产要搞上去,是非常困难的。”(N1)
由于在工厂生产和管理的过程中,工人的合作极其重要,所以各级干部都想方设法赢得工人的支持和配合,因为后者能够在执行命令、完成任务方面起带头作用。对于那些新提拔上来的干部或从厂外调来的干部来说,有一批听话的工人显得尤为重要。这些领导特别喜欢从新招的工人里寻找支持者,因为这些新人不像那些有资历的工人动辄摆老资格,或是依靠他们与其他领导之间的关系(N5)。那些得到关照的工人也会注意与上级保持良好关系。然而,我们的受访者也都认为,那些故意阿谀奉承、给领导送礼行贿的工人,还是非常少的(W1,N1,N2)。用南京电信设备制造厂的一位退休人员的话来说,就是“那时不需要讨好领导”;来自上海一家服务性企业的受访者也称,在他们那里,工人“用不着讨好”领导(S9;另见H10,H13,H15,L3)。
至于为什么大多数国有企业中的工人不必讨好干部,受访者给出了不同解释。有些人认为这与个性有关(H1,H4,S10,S18,W4)。更多的则是强调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因素。比如,一名武汉钢铁厂机械制造总厂的退休人员解释道,他们厂的工人之所以很少去巴结干部,是因为那时的“社会风气比较好”,这跟改革以来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H10)。另一些退休人员强调,他们厂领导的个人品质较好,其中大多数是从普通群众中提拔上来的,肯吃苦耐劳,“跟现在完全不一样”(L3)。从工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跟干部之间要么“关系比较一般”,要么“关系蛮好”,要么“关系非常融洽”(L3);他们尊重干部,但没有必要去巴结干部(H13,H15)。
大部分受访者都强调,在当时的国有企业中,与领导的私人关系之所以不那么重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干部和普通工人在总体上处在“平等”的状态。在谈到他们与干部的关系时,受访者使用最多的是“平等”(S10,S18,Y1,Y4)、“比较平等”(S8,S11)、“一律平等”(S11)、“平起平坐”(L2)、“还不错”(B9,L4,N4)之类的描述。但是,不同的受访者对“平等”有不同的理解。对一些人来说,平等基本上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只有下班后他们才会有平等的感觉,而在上班时,工人们“还是要服从领导的,因为当时认为服从领导就是服从毛主席,就是服从国家安排”(B2;另见S4)。另一些受访者则从经济角度加以解释。用南京中兴源丝绸纺织厂退休工人范先生的话说,当时工人和领导之间是平等的,因为他们的工资都差不多,主要取决于工龄和资历;无论干部还是工人,工龄长、表现好的,工资就高些(L2;另见Y1,B9)。
然而,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大体上平等,关键在于当时工人的生计有制度保障,干部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例见L2,S11,S18,Y1,Y4)。 因此工人们平时也没有觉得有必要给领导拍马屁,用宁波港的一名退休职工的话说:“不会去拍的,最多就是打声招呼,叫声厂长,有的理都不理睬的。领导权力你说大也大,因为他讲了算的。但是拍马屁的人很少。因为领导能管的事情其实也不多,粮食有定额是粮食部门负责的,小菜发菜票是居委会负责的,发工资是国家规定的,领导也没有权力克扣。没有辞退工人的权力,需要上级单位批准。”(N4)石油工业部下属的南京第二分公司的一名退休医生安某也说:“那时候大家一般都不拍马屁的,但是也有极少数的个别人拍马屁。大多数人都是实实在在干活的,那时候的领导权力没有现在的领导权力大的。”(L4)
简而言之,国营企业内部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受两种制度安排的制约:其一,工人事实上的就业终身制(所谓“铁饭碗”)以及国家所规定的一套涵盖从生到死的福利保障措施,使得大多数工人没有必要从个别干部那里寻求保护,也没有必要效忠干部个人,后者在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其二,与工人们在生计上无求于干部的状态相反,干部们在缺乏物质手段以激励工人的情况下,不得不有赖于工人的配合,以按时完成生产目标。这两种制度安排是将借自苏联的一套工厂管理方式与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相结合的结果。中国人力资源充沛,但就业岗位有限,这使得工人没有太多机会在不同企业之间自由跳槽,这与苏联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短缺,工人的流动率非常高,因此不得不靠物质手段留住工人,刺激其生产积极性。*Donald A.Filtzer, Soviet Workers and De-Stalinizatio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Soviet Production Relations, 1953-19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Martin K.Whyte, “The Changing Role of Worker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73-196.与之相反,中国工业化的资金和资源十分有限,因此在激励工人的积极性方面,无法主要依靠物质手段(经常性的涨工资、发奖金或是分房子等等),只能通过缩小干部与工人在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差距,提倡工人的“主人翁”精神,以非物质手段为主,激励其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均与苏联社会所存在的严重不平等和等级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David Lane, Soviet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77-194; Donald A.Filtzer, Soviet Workers and Stalinist Industrializatio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oviet Production Relations, 1928-1941, London: Pluto, 1986,101-102.
二、工资调整和住房分配
工人与干部之间是否如大多数受访者所说,存在着大体平等的关系,工人队伍本身到底有没有产生如新传统主义论者所假设的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分裂。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车间干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运用个人的权力,决定工人的物质福利和政治地位。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干部在工人的工资调整、奖金发放、职位晋升、工种分派和授予各种政治荣誉等方面,其决定权受到何种制约,工厂里是否因此形成了Walder所说的工人对上级的人身依附以及裙带关系的盛行。*Andrew G.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pp.96, 97, 160, 163, 166.据称,由于干部们大权独揽,他们“在惩罚工人时可以肆意妄为,使那些在工作中表现好而本应加薪和得奖金的人,失去了机会”*Andrew G.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p.100.。为说明干部们的个人专断,Walder引用了关于布达佩斯拖拉机厂某工头的一段描述,以佐证中国工厂的情况:“在这里,他们就是皇帝,他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会将好处‘施舍’给他们看起来顺眼的人……工头们不仅仅管我们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管人。工头们决定我们的薪酬,我们的工种,我们的加班时间,我们的奖金,以及工作失误的罚金。”*Andrew G.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p.102.中国的车间干部是否真的如匈牙利布达佩斯工头那样强权和专断?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中国企业的工资升级和住房分配。
(一)工资调整
毛泽东时代很少涨工资。自从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标准的工资体系之后,仅有三次工资上调:第一次是在1959年和1960年,当时涨工资仅限于国有企业中50%的职工(1959年为30%,1960年为20%),优先考虑的是在生产和技术革新中取得成绩的人;第二次涨工资是在1963年,占工人的40%,受益者是多年来的低工资职工;第三次是在1971年,依然是低工资职工优先,其中包括1966年底前进厂的所有一级工、1960年底前进厂的二级工和1957年底前进厂的三级工。在1977年,进行了一次类似的全国普调,涨工资的对象主要是1971年底前进厂的一级工和1966年底前进厂的二级工。由此可见,在毛泽东时代工资升级仅有寥寥数次,每次涨工资,都是针对绝大多数工人或工龄相同的全体职工,即所谓“赶鸭子过河”(H13)。
工龄是决定工人工资调整的最重要因素,这在1963年、1971年、1977年的国家政策中有明确规定,我们的受访者也再三证实了这一点(见H15,N5,N10,W1)。据宁波机械厂的一位退休工人回忆:“工资评定也是按照积分的,劳动态度、工作量、工龄、群众评定,这样评定的。所以还是比较合理的。当时评定主要还是以工龄为准,如果别人工龄30年,你15年,工资评定起来肯定是30年的那个人多。工龄是主要的一条,然后再参考其他各项。最后还有一项就是群众评定,那么群众评定是有差别的。如果我对你好,我就同意,我对你不好,我就不同意。那么作为评委会的领导来讲,首先一条是工龄,这个条件已经把你限制了。所以说,当时基本上还是合理的,当然要绝对合理是不大可能的。中央文件、省里面文件、局里面文件都是以工龄为准的,所以我们工厂也是以工龄为准的。”(N5)原在华侨糖厂工作的一位技术员,回忆起厂里的工资升级,也觉得是“很民主的,没有关起门来搞的,是比较公开透明的。首先上面给方案,然后厂里面讨论,一般考虑这些因素:工龄、考勤、劳动态度、工作成绩、群众关系、政治表现。那个时候讲政治,如果政治上落后,你就靠边了。五级工资以下就是主要按工龄,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就按照这工龄套上去。上了六级、七级、八级就是主要看你表现了”(N10)。
我们的受访者大多同意,当时他们厂中工资调整的资格审定“比较公开透明”“很民主”(N10;另见 H15,L6,N4)。通常,这一过程会有几轮讨论,并会对结果进行公示。在宁波港机械厂,加薪由工资委员会来定,该委员会由厂领导和几位积极分子组成。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在个别工人中间走访,听取意见,“这个群众都有发言权的,如果某人明显不符合条件,群众会把他拉下来的。因为有三上三下的制度,上面的结论交群众讨论,然后反馈,这样来回三次”(N4)。在南京星火棉花纺织厂,每轮讨论结果都会张榜公布。来自该厂的受访者称:“职工工资等级是按照政策公开透明地进行,用大红纸张榜公布,有意见大家讨论。包庇、舞弊行为不是没有,但是很少,是极个别的现象。”(L6)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仅不会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和亲近的人加薪,相反都会把机会让给工厂里那些工资最低和工龄最长的工人(B7,L8)。上海压缩机厂的某车间主任回忆说,当时所有干部都得“谦让”,他自己也主动降了半级。在另一轮加薪中,所有干部都不得参加(S11)。广州金笔厂原副厂长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一项政策,即干部的平均工资不得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资,他自己当副厂长的工资是65.2元,仅相当于四级工的水平(N9)。
厂领导的意见在工资调整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在全国普调政策并不适用的地方更是如此。例如在上海,相当一批在1960年后进厂的工人,并没有采用全国通用的八级工资制。所有在1968年后进厂的工人,均没有固定的工资级别,这些人到1983年已经多达170万。他们的工资有不同的标准体系,每级相差3元,即所谓的“一条龙”工资制度*《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87、291、293页。。工资升级时,领导有权决定给职工加3块、6块还是9块。益民食品加工厂的一位退休工人杨女士因此抱怨,值班长有可能“就把这个9块给了他认为好的人,不一定是大家认为好的人”。她进一步解释说:“还有种人呢,打个比方说,很能干,什么都能上,但是他老是迟到早退。你说他能拿什么,领导和你关系好的就是6块,不好的就是3块。我就说领导有权力的吧,就有这个权力。这个东西也是很复杂的,要说清楚很难。”(S8)
可是,如果某些干部果真“有小动作”,一旦被发现,“老百姓就会造反,也敢吵的”(S6),会有工人站出来“打抱个不平”(W5)。例如在宁波的一家棉纺厂,据回忆,“评工资的时候,给人评得好或坏,车间主任是参与的。这个时候工人里面骂得很多的。如果谁没加上,那有些人会骂的。总有人没加上的,不是百分之一百能加上的。(问:会当面骂吗?)当面也会骂的。工人有的时候,是什么都不管的。她要提意见了呀,都是直来直去的。如果她跟你有意见了呀,你有什么坏事,她都会给你挖出来的。(问:什么坏事呀?)家里的事呀,什么的。(问:和工作没什么关系的事情呀?)嗯,是的,和工作没关系的事情。她就是把你挖出来了。比如,你老公怎么样,怎么样;你之前的什么什么事情。车间主任或班组长的大人小孩都会被骂进的,工人是什么都不管的”(N1)。
(二)住房分配
毛泽东时代也很少分房。即使有房源可分,也不像工资调整那样要论资排辈。分房主要考虑的是人均住房面积。住房条件最差、人均面积最小的工人排名优先。这一点容易理解。从50年代起,国家的经济战略是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住房建设很少。大多数国营企业从来没有在全单位范围内大面积分过房。工人及其家属要么靠私宅生活,要么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没收的富人院落里,未成家的工人则住单位宿舍。到70年代时,三代甚至四代人同堂屡见不鲜,新婚夫妇谈不上私人空间。到70年代后期尤其在80年代,国营企业纷纷自建公寓,住房困难程度成为分房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至于是不是积极分子、党员或干部,并不影响排名。分房时单位领导也不能滥用权力,包庇现象受到限制。在广州金笔厂,1979年分房时,工人们得先填申请表,再按住房困难程度排名。“分配标准都是按谁最困难谁排最前面的,看你人口、租赁面积、位置,具体讨论”,排名由“分房小组”来定,分房小组由九人组成,每人代表一个车间,排名出来后将进行公示,没有争议后才开始分房(N9;另见L4,L5,N4,S7,Y2)。
因此,我们的受访者大多认可,他们单位的分房是公平的,都经过了几轮审核和公示(如N7,N15,S3);当描述这一过程时,通常都说是“透明的”(S6),“公开透明的”(N5,N7),“比较公开透明”(L5),“很透明,没有包庇舞弊的空间”(H15),“比较公正,没有包庇舞弊的行为”(L3),“没有包庇行为”(H17),“基本上没有什么后门可开”(S3)。由于房源有限,公众舆论会形成巨大压力,干部们即使想舞弊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相反,他们不得不拿出大公无私的姿态,和工资升级时一样,放弃自己的分房机会,让给那些最需要的工人。
当然,这些并不能说明私人关系在分房中不起作用或者领导完全没有偏袒行为。来自上海普陀区的一位受访者承认:“这个人情肯定是会有的,那是不为人知的。就是我们都能接受得了的。哦,比如这个人困难点儿、这个人关系好一点,先分给他,这个很正常,肯定会有点人情的嘛。”(S9)不过,一旦发现领导干部在住房分配时滥用职权,工人们绝不会袖手旁观。在北京青云航空仪器厂,据退休职工杨某回忆:“领导分别人房子时也不敢偏的,偏了下面的人不干的,大家都看着呢,都住在一起谁不知道谁呀。群众感觉不合适就直接写大字报了,往上捅,上面总会管的。”(B1)特别是当他们认为领导干部的后台交易威胁到自己的分房机会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去闹去吵”,“你吵得理想就拿到了,吵得不理想就拿不到”,益民食品加工厂杨女士作如是说(S8)。上海冶金局下属的镇江煤矿发生的抗议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来自该矿的受访者回忆,有两三位不够格的矿工为分房跟领导闹得很厉害。领导为了“摆平”下面的人,只得让步,结果却压缩了其他符合分房标准的工人的住房面积(N2)。此外,如果抗议不起作用,走正常程序自己又不够资格,个别工人就会在未经厂方批准的情况下,强行“占房”(H18)。 在黄冈地区缫丝厂,我们的受访者也强调分房靠“闹”,“分房子以男方为主,当然,女的如果非常狠也会分。分房子的时候,狠一点儿的,就分的好一点儿,老实一点儿的,就分得差一点儿”(H1)。
因此,面对厂领导可能存在的滥权行为,工人们的抗争便显得十分重要。不管是否得当,他们的抗争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信念,即自己是本单位正式职工,有权享有最起码的生存权利。所以,只要不太“出格”,不管闹到何种程度,他们的行动都是“正义的”(righteous),尽管按照政府条文的规定不一定是“正当的”(rightful)。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选择叫骂、占房这样的方式。而领导干部迫于普通工人的压力,也往往不得不让步,以求息事宁人,也保全自己的脸面。不同于上下级之间纪律严明、不带个人色彩的关系,这里领导干部与普通工人更像是生活于同一社区的成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双方都要顾全彼此的生存需求和脸面。
三、积极分子与政治激励
如前所述,在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年份,工资上调和奖金发放之类的物质激励几乎不存在,因此企业不得不依靠非物质手段来激励工人,例如评选积极分子、颁发各种荣誉称号(“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升职称以及入党。根据新传统主义论者的解释,厂领导评选积极分子的标准,与工人在生产中的实际表现和道德素质并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看当事人对领导是否有“具体的忠心”或“私人的效忠”*Andrew G.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pp.100, 124, 131.。因此,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评选积极分子和授予政治奖励的实际过程到底如何,评选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对领导干部的忠心抑或个人能力和生产劳动中的实际表现,积极分子与干部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积极分子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
(一)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
先进生产者(又称“先进个人”)的评选,通常是在每个生产小组内部进行,从本组几十名工人中选出几位候选人。获胜者通常是那些“劳动积极性高、生产质量好、生产数量多的人能获得先进个人,都是由工人选举出来的”(L1)。颁给他们的物质奖励微乎其微,仅具象征意义,通常包括一张奖状再加上一件日用品,例如水杯、毛巾、面盆或笔记本(例见W3,Y1)。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一种新的激励措施,先进生产者可获得一笔奖金(L4)。相对于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的名额更少,评选也更严,一家工厂通常只有几个名额。获选者在申请入党、入团以及提干时,都会得到优先考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进生产者和劳模还有机会加入工宣队,这意味着可以免费到外地休假,或参加一两个月的脱产培训(N6)。70年代末之后,在一些国有企业,劳动模范还可上调一级工资(H15,N6,W4)。
在谈到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的具体评选过程时,我们的受访者几乎都一致强调,这些人是凭自己的辛勤工作和献身精神而被工友们提名评上的。用辽宁省锦州第六炼油厂一位退休女工的话说,厂里的这些积极分子“都是干出来的,真干!”(C6)从南京通信设备厂退休的范女士这样描述被选上的工人,称他们“一年365天满勤不请假、有病不请假、把假条放口袋里继续工作、节约能耗、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八小时干十小时的活”(L5)。宁波和丰棉纺织厂的一名退休职工称,被评选上的工人“工作上比较突出,不计时间,有病装无病,身体不舒服还硬撑着工作,有些还做些调解工作,调解工人互相之间的争吵。一般这些人都是和群众关系不错,与领导关系也不错的人”(N6)。而在武汉橡胶厂,这些优胜者据称“平时做事,你不调皮捣蛋,不迟到早退,这些人就可以,多做点好事。来得早抢着做啊。吃得苦,来得早”,还要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开会时踊跃发言等等(W3)。那些为数不多的劳动模范工作异常卖力。武汉制药厂的一位退休职工这样描述厂里的女劳模:“那她就不是八个小时了,她是我们车间里一个大组长。她中午在那里做,从早晨要做到中午之外,她一天要做两个班,她晚上做。那真是做出来的劳模。我们原来的劳模和现在的劳模,那是死做。”(W4)武汉被服厂一位叫张祥文的工人,曾在1959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12年以83岁高龄去世。“他怎样评上的?”我们的受访者说,“靠生产质量,他当时的成绩是19万件无一废品。1982年,他又创下了22万件无一废品的成绩,被评为武汉市劳模。他这是干出来的,他的手指都变形了”(H6)。在和丰棉纺织厂工作了十多年的陈芳芳是市级劳模,后来成了市总工会主席,据说,“那她这个技术是好的,别人是做不过她的。比如说,我们是接纱头。纱纺出来断掉了要把它接起来,接得不好的话,那个接头就会很粗,布织出来,布面就很不平。那么技术好的人,头接起来看不出的,非常光滑。这个是硬功夫,那这个练是练得很厉害的,业余时间也去练习的。那个时候生产积极性的确是蛮高的,跟现在不能比,不讲报酬的”(N1)。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的王佳芳同样有着出色的技术,“操作技术好、产量质量比人家好,无次品”(S7)。同样,湖北黄冈缫丝厂的叶桂英,曾先后获得厂级和省级劳模称号。她的工作是煮茧,然后将其运往缫丝机,据说她每天上班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H4)。河北省石家庄化肥厂的退休工人崔师傅谈起厂里的劳模,称他们“确实有真本事,确实干得不错”,与如今那些靠“拉关系走后门”选上的劳模截然不同(B2)。
(二)与车间同伴的关系
要做先进分子和劳动模范,除在生产上必须表现优异外,“群众关系好”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们的访谈对象通常形容他们“工作好,人缘好”(S19),“工作积极,群众基础好”(Y1)。上面提到的武汉制药厂那位受访者特别强调群众基础好对于获选的重要性:“说老实话,那时候劳模跟工人,他都是靠工人选出来的,他不是领导选出来的,领导他是不敢选的,那都是一层层的。首先是小组里选,选了再在大组里选,选了再到车间,那是一层层来定的。那不是说哪个领导指定哪个,就是哪个了,那是不可能的。那都是选、比出来的,哪个比她条件优先,就是哪个。”(W4)山东胜利油田的一位退休电焊工也有同样的看法:“先进个人是群众选举的,关系不好能当吗?”(Y1)上海益民食品厂的杨女士说得更为直接,那些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一般来说工作上肯定是能手,和群众关系应该说还过得去,过不去也没人选你”(S8)。同样,在宁波港口机械厂,积极分子“往往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否则是评不上去的,如果大家对某人都很有意见,即使评上去了,也会被轰下来的。那个时候大家讲话的权力还是比较大的”(N4)。
因此,积极分子产生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是从生产小组到车间、全厂各级的评比。候选人必须在同伴们面前展示其技能(L6,N1),胜出者“都是比出来的”,是“靠工人选出来的”(W4)。那些当选劳模的,“要有拿得出的数据”(S7)。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获得其他工人的尊重。我们的受访者在描述普通工人对积极分子的态度时,往往用的是“心服口服”(L5),“都很服气”(S3),“都是服帖的”(N1),“都很佩服他们”(L4,S4)之类字眼。
所以,一旦当选先进个人或劳动模范,获胜者往往会买些糖果或其他零食,分给小组里的同伴们,对他们的支持表达谢意(S8)。用北京768工厂一位退休职工的话说:“不能名和利都得呀!”(B9)获得荣誉之后,积极分子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保持低调,在生产劳动中起带头作用,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积极参加打扫公厕之类的义务劳动(参见L4,L5,L6,L8,S19)。
当然,普通工人中也会有人对获选者心怀不满或嫉妒。西安仪表厂的退休职工方某表示,那些对积极分子“不服气、看不起”的确实存在,但属于少数(S10)。在上海艺术品雕刻厂,评选结果公布之后,总会有些“冷言冷语”(S6)。同样,益民食品厂的杨女士也认为:“佩服的人肯定有,嫉妒的人也肯定有,这个很正常的。但是嫉妒的人肯定也少。以前的人不像现在这么争。”她还指出为什么积极分子不可能取悦所有人:“因为你很会做的人总会嫌弃人家很不会做的人。被嫌弃的人肯定对你有意见。”但是杨女士否认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之间存在严重隔阂,彼此有敌对情绪,毕竟“以前的人真的心眼不怎么坏,不会这样的”(S8)。落选的工人怀有怨气,还可能因为他们与获选者之间实力相当,差距很小(W5),正如北京768工厂退休职工郭先生所言:“这人群当中,有人就特别计较这个,这一年下来,如果他不落点什么他心里不舒服。如果假如今年评不上他,他开春到春节一年都不顺当。找这个毛病,找那个毛病,不是说觉悟有多高。评的时候就一张奖状。”(B7)确实,有些工人落选并非因为生产成绩不如获胜者,而仅仅因为“他们出身不好”,或是因为“没有和领导搞好关系”(H15)。我们的受访者指出,也确有少数人是“拍马屁上去的”(L1),或是“靠关系上去的”(W1),对于这种人,工人们会“有些看法,就不大愿意支持你的工作,这种情况是有的”(W1)。不过,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个例就加以推论,认为工人群众对积极分子普遍存在敌意,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工厂里广泛存在普通职工与少数积极分子之间的分裂*Andrew G.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pp.26, 164-170.,无疑夸大了历史事实。
(三)与干部的关系
我们的受访者几乎都否认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是靠关系获得荣誉的,相反,他们都强调生产中的实际表现才是获选的决定性因素(S4,L4,L5,N2,W2,W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在积极分子的评选中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受访者强调了领导在确定最终名单时的关键作用。葛店化工厂的退休职工说,要想被选上,必须“领导看重你”,“你做得再好,领导不重视你,不睬你,你也得不了标兵”。谈到如何受到领导重视,他补充道:“你要拿出成果来,做出来的标兵,”“你一定要做得出来,做得好。最重要的是要做得好,领导看重你”(W2)。上海硅钢厂的退休工人王先生也有类似看法:“首先要领导看得上,就算你再努力,就算领导看不上,那怎么也没办法,三分努力,七分机遇。”要想得到领导的重视,当上积极分子,候选人必须“起带头作用,什么都在前面,这才能当上啊,没有突出贡献,是当不上的,和我们一样的,都是流水线的,普通人都是服气的”(S2)。湖北大冶石头嘴矿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军事化管理,谈到当时的积极分子评选,退休职工乐先生认为:“大家都差不多,所以评选主要还是靠最后领导决定,靠的是连长对你的印象,虽然有班组开会的程序,但是最后的决定权是在连长那里,基本是由上级指定。一般来说,评上的人都还是能起带头作用,普通职工和他们也很融洽,因为都是一起来的人,天天一起干活,平时关系就很好。”(H11)这里,积极分子和领导关系好,首先是因为他们工作出色,并非仅靠拍马屁或者行贿与领导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正如一名曾在江西省新干县电子仪器厂工作过的上海退休工人所言:“领导看着你肯做,肯定喜欢啊,东西拿得出来,领导肯定喜欢啊。”(S5;另见W4)
当然,前面说过,确有“少数”“极个别”“少部分”积极分子的荣誉是靠逢迎领导而取得的,因此在车间里处境尴尬(L1,S18,W1)。这种情况在改革开始之后更为常见(B1,B2)。然而,许多受访者很快指出,尽管个人和领导的关系在积极分子的评选过程中十分重要,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因素,但是想要获得荣誉,仅仅靠和领导的私人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比领导的赏识更为重要的是得到同一小组职工们的“公认”。上海益民食品厂的杨女士说:“如果大家不公认,光领导是上不去的,那样要造反的,上面他不能做主。”她补充道,如果单位领导仅凭个人喜好,否决某个能力出色、符合资格的候选者,“群众要有意见”。因此,总的来说,那些最终获选的大都是凭实力上去的。用杨女士的话说:“那个时候的领导总归还是可以的,还是能在台面上见见光。”(S8)上海一家服务公司的退休干部陈女士也认为,这些先进分子“和领导关系不一定是很好的,但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工作好的话肯定听领导话的,他要是不听领导的话,会好好工作吗……如果是因为和领导关系特别好而评为先进工作者的话,宣布下来大家都不会服气的”(S9)。和丰棉纺织厂的一名退休工人的看法相近,要评上积极分子,“当时领导这关也是非过不可的,如果领导这关没过,你也是评不上去的。但是,单单和领导关系好,也是不行的,领导会考虑的,这个人推上去没有代表性,没有基础”(N1)。
从工人群众中提拔干部,与评选积极分子有些差异。积极分子的评选主要是看个人在生产劳动中的表现,而要被选为干部,仅仅靠工作努力是不够的,候选人必须具备必要的学历和文化程度以胜任领导工作。最重要的是,正如上海解放塑料制品厂的原厂长、党委书记所言,候选人必须具备领导才能(S3)。车间一级的领导岗位尤为如此。前面曾提及,车间的领导干部除负责所有生产小组的日常生产活动之外,还要管理工人们的个人问题,例如结婚、离婚、家庭暴力以及所谓“男女关系”问题,当然也包括工人们可能介入的各种犯罪活动(B8)。有些合格的工人被上级提名为车间主任后,主动拒绝这一职务,便不足为奇。上海冶金局镇江矿场的一名机修工即是其中一例,据其回忆:“本来厂里面想让我当车间主任,我就不愿意当,我只会协助协助,主要我不太会说话。干活我是干得不错的,但是去管别人,我就不太愿意,总觉得为什么要去管别人呢?这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想法就是爬上去,等爬上去了,自己就可以舒服一点儿。但是像我们这样上去,只会更加辛苦的,只会吃亏。”(N2)
厂领导在选拔各级干部时也必须首先考察候选人的能力。他们不能光看候选人与自己的私人交情,而不考虑对方的能力就作出任命。正如前面提到的和丰棉纺织厂那位退休工人所说的:“提拔要看本事的,不然提上去也是要被人家说的,那人啥本事呀?又不会干活!要被别人说的!”(N1)担心工人们有不满情绪仅仅是厂领导在选拔干部时注重个人能力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工厂的中下层干部,车间主任和生产组长是否具有协调和监管日常生产活动以及与工人沟通的能力,这是维持生产效率的关键所在,而生产成绩又直接关系到工厂领导自己的业绩和晋升。因此,厂领导在选拔中下层干部时,首重候选人的能力。用上海益民食品厂原生产组长杨女士的话说,这些候选人“要能撑得起来的”。她补充道:“撑不起来就没有用了。你要是叫不动别人干活,又不懂技术,自己水平又不行,这怎么做啊!这个倒不能马虎的,还是要凭实力上去的。反正还是要有一些能力,不说百分之百,但百分之六七十总是要有的。”(S8)北京768工厂原副厂长韩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工作要拿得起来,你说你再走上层路线,工作上你要拿得起来呀,你是个笨蛋不行呀,让你干的时候那就得上,撸胳膊挽袖子就得上,而且要镇得住下面的工人。尤其车间主任,你不找硬的不行。”(B8)因此,在前面提到的个例中,即便候选人是凭借与厂领导的私人关系而获提拔,但当上干部之后,自己也不得不加倍努力工作(H18),“自己也还要过得去,要有比较好的表现”(H16)。
概言之,提干不同于积极分子的评选,并非仅看工人是否赞成、生产劳动是否出色。在选拔干部的过程中,厂领导有更大的机动权,因为提干无须工人们的提名和投票。候选人与领导之间的私人关系和忠诚程度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起到一定作用。然而,厂领导在行使自己的机动权时,依然受到某些约束,包括对候选人家庭背景或个人领导才能的基本要求。只有当候选人满足了这些前提条件时,与上级之间的私人关系才会发挥作用。厂领导不可能完全无视候选人的资格和能力,仅仅因为后者对自己忠诚就给予晋升。
四、结论:毛泽东时代的“单位社群主义”
关于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工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工厂或者车间不仅是工人一天工作八小时的地方,而且是他们赖以生存、求得生计保障的场所。因此,他们对工作单位所产生的认同,与1949年之前中国农民对所在村落或宗族产生的认同并无二致。一如村民认为他们的生计安全权高于村落内外任何其他制度安排和权力关系,工人们也把工厂或是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视为理所当然。在工人们看来,干部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上级的任命,而且有赖于他们能够做到公正无私地分配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利益,并确保工人们的生计。干部们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们不仅要在生产和劳动管理上履行职责,而且还要关心工人们下班之后的日常生活需要。简而言之,单位不只是一个从事生产的地方,也是一个干部和工人朝夕相处、共同工作和生活的群体。一旦遇有干部滥用权力、威胁自身利益的情形,工人们会毫不迟疑地加以抗拒,这不仅是基于他们拥有作为本单位成员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这一基本信念,而且受到国营企业两项制度安排的支撑。这两项制度安排对于工人们形成自我身份认同及其对于干部的态度来说至关重要。其一是毛泽东时代的官方话语将工人视作有着正确的政治意识的领导阶级,不同于那些易于贪污腐败以及成为“走资派”的干部。工人们在话语上的领导地位,使他们相信自己有着与生俱来的政治权利,可以向滥用权力的干部作斗争,揭发其错误。其二是作为国营企业职工,工人在就业和各种生活福利方面获得国家在制度上的保障,他们没有必要非得从干部那里寻求私人庇护;如果不得不跟干部较量的话,他们也无须担心自己的生计安全会受到损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干部在政治上和话语上都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总是会成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目标,诸如50年代的“三反”运动、反右派斗争,60年代早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紧随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以及70年代初的“一打三反”运动,等等。所以,毫不奇怪的是,那些一再受政治运动冲击的干部会形成“怕群众”的心理。这是因为,只要有什么政治运动,工人们就会揭发干部们的所谓“错误”。因此,对于干部来说,与大多数工人群众保持良好的关系是他们在历次运动中生存下去的最好方式。从行政上来说,干部也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力能够要求工人完全服从自己,因为后者享有国家保障的终身制和固定工资;而与此完全相反的是,干部要指望着工人的合作以确保生产任务及时完成,这一点对于干部保住自己的职位以及升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经济上来说,干部的生活并不比工人好多少,尤其是与那些资深工人相比,这是因为干部和工人在生活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大。
因此,如果考虑到以上所有政治、意识形态、行政以及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话,干部和工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是对称的。这种对称关系折射出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内部的劳动管理以及基层政治的独特取向,即把群众动员、政治激励以及财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放在第一位。工人作为企业的终身职工,虽然全面依赖自己的工作单位,但是很少会与干部个人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相反,每当工人们怀疑干部徇私舞弊时,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工人就会站出来,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抗拒。他们的抗议可能以一种非正式的传统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讥讽、吵闹、谩骂甚至拳脚相加,也可能以一种合法正当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体现“主人翁”的地位,并行使其所享有的监督和批评干部的天然权利。依附主义的解释模型之所以不适用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国营企业内部的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些企业缺少“庇护—依附”网络的盛行所必需的两个前提条件,即在财富和权力的控制方面存在“持久的明显的不平等”,以及在生计和地位方面“稳定的、非私人的保障”之相对缺乏。
然而,所有这些不应该使人们认为毛泽东时代干部和工人的关系就像宣传话语中的那样是完全平等的,也不应该否认在个别干部和少数工人之间存在的私人化的“庇护—依附”关系,因为的确有某些工人善于算计,通过拉关系,寻求干部的私人保护,从而由普通工人提拔为干部或当选为积极分子。然而,这种情况不应等同于新传统主义论者的夸大解释。新传统主义论者认为,干部在决定工人的工种、工资、奖金和升迁方面可谓大权在握,工人不得不全面依赖于干部,从而导致“庇护—依附”关系的盛行,乃至工人队伍分化为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两个敌对阵营。事实上,“庇护—依附”关系的流行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即工厂或车间干部真正拥有自主决定聘用或者解雇工人的权力,真正拥有自主决定工人的工种、工资和升职的权力。但所有这些条件都要等到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之后才逐渐成为现实。改革进程开始以后,由于厂长经理负责制、合同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的次第引入,工厂领导终于拥有了上述权力,可以自行决定工人的去留、工资以及奖金数额,还能按照本单位的能力和需求,依照单位领导的意志自行建房、分房。与此同时,工人在有能力自由跳槽而不失去福利保障之前,对所在单位的依赖程度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工厂管理层和普通职工之间的“庇护—依附”关系才可能成为常见现象。而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私人化的主从效忠关系只可能个别存在,不会在干部与工人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因为产生这种关系的制度环境和物质条件并不存在。国营企业中的工人群体,也不可能像新传统主义论者所宣称的那样,由于“庇护—依附”关系的盛行而普遍产生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分化和对抗。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日常政治视为某种独特的社群主义(communalism)。包括工人和干部在内的企业所有人员均在生计上仰赖所在单位,并对本单位产生高度认同感。但是,工人对工作单位的依赖,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中世纪世界各地一度流行的农奴对所在采邑的个人依附关系,这是因为工人的生活保障不是基于他们对干部个人的忠诚,干部对于工人的影响力从未达到封建主对于家奴的那种个人控制水平。毕竟,干部们对于所领导的企业并没有所有权,他们本身也受制于上面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厂内的各种非正式规则。一方面,干部在招聘和工资调整方面权力有限,且需在生产方面依靠工人;另一方面,工人的生计获得国家的制度保障。这两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国营企业中干部和工人的关系,相较于毛泽东时代之前和之后私营企业老板与员工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显得更为对称。然而,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国有企业,都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运营的。企业的生产、用人、工资、福利分配完全由中央或各省、市政府相应的管理部门来决定,虽然工人依附于所在单位,单位本身却缺少自主权。因此,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内部的日常权力关系,可以视作一种“单位社群主义”(work-unit communalism)。它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塑造国营企业运营机制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工人对单位的全面依赖,同一单位或单位内部同一部门的所有个人之间形成的认同,而最为核心的则是其中干部与工人之间大体上对称的相互合作、相互依靠的关系。
这种国家主导下的单位结合体至少可以从1949年之前的三项社会和政治遗产中找到源头。其一是传统中国以家庭、宗族或者更大的合作组织为中心的地方习俗和惯例。按照这些习俗或惯例,宗族或社区内的每家每户为了公共利益均需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合作活动中,以确保他们的集体生存,他们亦因此对自己的家族或村社产生依赖和认同。1949年以后的国营企业干部的家长式领导风格,以及他们在生产上对工人的依赖,使人联想到传统村社领袖无所不在的弥散型权威,以及村社成员的集体认可对于这些当权人物建立自身威望和信誉的重要性。*Huaiyin Li, 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5-193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其二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部分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中一度施行的新式福利制度(诸如职工宿舍、退休金等),这些企业于1949年后被新政权接管或改造,而它们的福利制度也部分存留下来*参见Wen-Hsin Yeh, “The Republican Origins of the Danwei: The Case of Shanghai’s Bank of China,” in Xiaobo Lu and Elizabeth J.Perry,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Y: Sharpe, 1997, pp.60-88; Mark W. 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orris L.Bian, The Making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其三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遗产。由于革命年代的物质困乏,中共始终强调运用政治激励手段,并且依靠培养积极分子,来达到动员群众的目的。这三项历史遗产均有助于1949年后国营企业运营机制的形成。但是,在形塑国营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还是1949年后这些企业自身独具特色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制度。作为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媒介,工厂的各级干部确实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可以直接影响到工人们的各种机会;在工人中培养积极分子,对于干部保持企业的正常运转来说,也确是一件有效的工具。然而,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借用“庇护—依附”关系网络的分析模型,断定当时积极分子的选择和培养,仅仅基于他们对干部个人的效忠,也不应该断定当时的干部仅仅给私人圈内的支持者提供涨工资、发奖金、升职等机会。总而言之,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中工人和干部的关系,尽管也存在很多问题,但也绝不是某些论者所形容的“极端的依赖和专制”。*Martin K.Whyte, “The Changing Role of Worker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73-196.就政治、行政以及经济各层面的综括而言,当时的干部和工人之间在总体上保持着一种对称的关系,而这种对称关系本身,又是基于他们所共享的对单位的认同以及对国家的依附。
(本文作者 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教授 奥斯汀 78750;张一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240;张春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南京 210004)
(责任编辑 吴志军)
Everyday Power Relation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Maoist China: A Reexamination
Li Huaiyin & Zhang Yiping & Zhang Chunlong
Drawing on interviews with nearly 100 retired workers from different cities,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political life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three decades prior to the reform era, focusing on daily interactions between factory cadres and workers and between model and ordinary workers.It questions the validity of the thesis of “neo-traditionalism” in interpreting factory politics in the pre-reform era.While acknowledging the existence of patron-client relations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is article underscores the constraints, formal or informal, on everyday power relations on the workshop floor.It suggests “danwei communalism” as an alternative construct to underst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uring the Mao era.
* 本研究课题由三位作者合作承担。除三位作者之外,主持本课题访谈的学者,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黄英伟副研究员、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狄金华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满情副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勇素华副教授、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克霞副教授,以及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博士生胡光霁。本文英文原稿由李怀印执笔。
D232;K271
A
1003-3815(2017)-05-005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