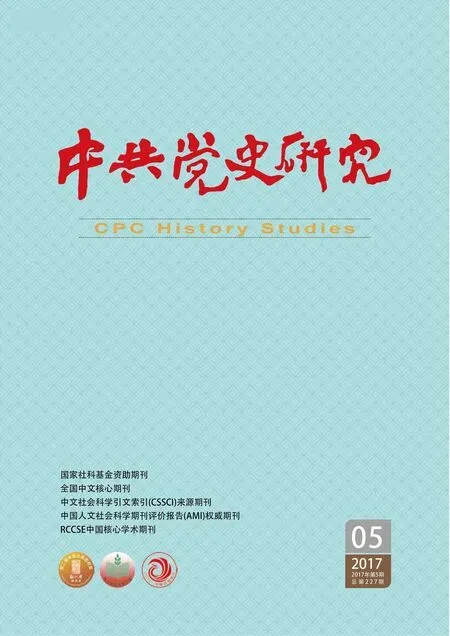概念史视野下的红军长征
——兼论中共在革命道路中的实践表达
杨 东
概念史视野下的红军长征
——兼论中共在革命道路中的实践表达
杨 东
红军长征既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一个超越时空且具有极强“语义承载能力”的独特概念。在红军长征的概念意涵中,既包含着“跑”与“追”这样的具象话语,也含括着“苦”与“乐”这样的叙述话语;既有“对”和“错”这样的路线话语,也有“胜”与“败”这样的辩证话语,同时也内在地包含着“危”和“安”这一转折话语。中共话语中的“长征”是一个“行动”概念。中共一方面突破“长征”概念的意义空间,拓展它的“语义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赋予其新的历史语境,形成新的概念话语和实践表达,并最终成为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资源。
长征;概念史;历史语境;话语
在中共革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演绎形成了不少超越历史时空的特定概念,“长征”就是其中之一。绝境逢生的长途跋涉和史诗一般的传奇经历,不仅凸显着红军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面貌,而且蕴含着强大的“语义承载能力”。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共革命每前进一步,便以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政治功能加以诠释。职是之故,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学术研究,红军长征向来都是人们关注和论述的重大题材。但是检索已有的论著,关涉“红军长征”本身的概念话语,却缺乏厚实的学术探究*管见所及,高华曾对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进行过细致研究,认为“长征”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如果没有“长征”这一段,不仅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的叙述就褪色许多(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149页);石仲泉在《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了红军长征的三个内涵。另有一些论者也对“长征”称谓的提出进行过勾陈。但这些论述因研究旨趣不同,并未对“长征”概念作过细致的演绎和阐释。。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概念史研究,为我们考察红军长征的概念演绎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工具。本文拟以此为视角,细致研究红军长征的概念演绎及中共革命道路话语中的实践表达。
一、从词语到概念——“长征”概念的炼就
“词语”与“概念”虽非等同,但“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在特定的词语中并被表象出来后,词语就成为概念”*孙江、刘建辉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 2013年,第259页。。探究“长征”这一概念,自当从“词语”入手。这既是概念史研究的题中之意,也是历史记录的客观存在。
就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观之,“长征”并非是一开始就有的概念,起初是以“转移”名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鉴于当时面临日益严峻的困境,中央决定红军主力“离开现有地区转移至更加广大与有自由机动可能的地区作战,并创造新的苏区”*《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13页。。尽管此时并非正式开始长征,但是“转移”已成为较为普遍的陈述之词。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84页。。以此为起点,“长途行军”成为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表述。红军到达遵义后,中共中央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又将这次行军称之为“突围的行动”,认为红军的“突围”是“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80页。。红军从决定战略转移到开始长征,以“转移”“长途行军”“突围”等词作其称谓,表明红军此时仍在意图寻求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换言之,当时的红军多半还没有想到要走如此之远的路,更没有想到最终要去往陕北。因此,当时一切准备工作的立足点,在张闻天看来,几乎还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2—23页。。1935年2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指出:“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消灭了贵州军阀侯之担白军全部,推翻了国民党军阀绅粮的封建统治,解放了黔北的工农及一切干人,建立了许多县区的临时工农政权,革命委员会。这样我们实际的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没收了所有军阀官僚绅粮的米谷衣物来分发给工人农民及一切干人。”*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4页。
就现有资料来看,该布告是较早出现“长征”这一词语的重要史料。随后不久,“长征”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其时,红11团政委张爱萍在庆祝娄山关、遵义城两次大捷时赋词庆贺:“长征首获大胜,转战历数艰辛。”在另一首悼念红军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的诗词中,也有“长征转战肩重担”的表述。*解放军红叶诗社选编:《长征诗词选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6、67页。1935年5月,红军进入四川冕宁县,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六言格律诗的形式发布了一个布告,在阐释工农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时明确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红军长征·文献》,第346页。相关史料表明,自红军转战遵义以来,“长征”一词已然频繁出现。不过仍需指出的是,尽管此时已经出现“长征”之称,但尚未成为一个专门概念,因为就在同一时期,在中共相关文件中还有另一种称谓——“西征”。1935年二三月间,在陈云拟定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提纲中,就多次出现“西征”之称,后来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刊发的文章也称“红军英勇的西征,是在最艰难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施平:《英勇的西征》,《党史资料》1954年第3期,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24页。。1935年6月,当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徐向前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依然将中央红军称为“西征军”,称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一报告中,红四方面军称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5册,1986年,第455页。应该说,这份报告已初步关涉“长征”的基本内涵。1935年7月《红星报》刊发的社论,当可认为是炼就“长征”这一概念的重要文献。社论指出:
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在数量上大大的增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而且使我们所进行的国内战争在质量上也起了新的变化。这一伟大的胜利使我们结束了过去的战略方针,开辟了新的形势,要求我们以新的战略方针来代替老的战略方针……我们当前的任务,就不是为着到达一定的地区而进行长途的行军了。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用进攻的战斗争取与敌人决战的胜利,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在今天,我们可能遇到的是粮食的缺乏,雪山与隘路,河流与草原,气候的比较寒冷,有时或者要露营。这些困难,都需要我们去克服,需要我们发扬野战军万里长征和四方面军在雪山顶上与敌人对持[峙]的精神,发扬工农红军固有的克[刻]苦耐劳的特点……我们只有一个意志,就是要争取决战的胜利。*《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红星报》1935年7月10日。
这篇社论不仅涵括了“长征”的基本内涵,而且基本反映出“长征”的“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根据石仲泉对长征内涵的界定,长征“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其次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有尖锐斗争;再次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峻考验”,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构成了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石仲泉:《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5期。。很显然,《红星报》这篇社论大抵具备了这一内涵的基本要素。另外,从概念史的视角观之,特定的概念是历史的沉淀,是以特定的词语进行阐释和表述。当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在特定的词语中并被表象出来后,这个词语就演变为一个概念。这样的理论诉求在该篇社论中同样得到了体现,尤其是社论强调红军发扬“万里长征”的精神,可谓是这一概念形成的“点睛之笔”。此后,“长征”不仅成为中共话语中的固定称谓,更在言说和阐论中演绎而成一个经典的概念表述话语。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沙窝会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红军长征·文献》,第611页。9月,毛泽东在哈达铺“用洪亮的声音号召,经过两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够以自己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红军到达陕北之后,“长征”的概念话语逐渐趋向于标准化和经典化的表述。毛泽东在与肖锋的谈话中说:“我们长征十二个月零两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我们完成了空前伟大的远征,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只有我们红军才有这个气魄,才有这个决心!长征苦是苦,可作用大。它是宣言书,向全世界宣传红军是英雄好汉,蒋介石反动派是没有用的。它又是宣传队,向十一个省的广大老百姓宣传了共产党、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的解放道路。它又是播种机,在十一个省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的。”*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1、131页。12月1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150页。至此,“长征”练就了其最为经典的概念话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表达。
“长征”这一概念一经炼就,就比“词语”本身拥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当一个词语“进入到一种可欲的、多样性意涵的含混之中”,词语“也因之成为一个具有生命的实体”*〔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而一个“有生命的实体”概念的重要表征就在于,它所涵括的意指既有共时性的陈述表达,也有历时性的语义迁衍。由是言之,概念视野中的“长征”,已然成为人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构筑某种政治意蕴和思想张力的重要载体。
二、长征的概念意指——话语表达与精神积淀
历史沉淀于特定的概念。当特定概念成为一种象征符号,自然会成为“历史现实中的经验和期待、观点和阐释模式的聚合体”*黄兴涛主编:《新史学·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年,第12页。。如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还只是针对长征作用的初期表象之称,那么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长征”则以其强大的“语义承载能力”,形成了具有广泛意义的多重话语。
(一)“追”与“跑”:“长征”概念的具象话语
长征是国民党的长途围追堵截与红军辗转突围的殊死较量。因此,在陈述长征的具象话语中,“追”与“跑”构成了长征概念的基本表达。这样的话语表达,既体现在国民党方面,也体现在共产党方面。
在国民党的话语表述中,红军长征就是“溃退”“西窜”,恰如蒋介石之谓:“过去赤匪盘踞赣南、闽西,纯靠根据地以生存。今远离赤化区域,长途跋涉……在大军追堵下,殊非容易。自古以来,未有流寇能成事者。”*《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8页。尤需一提的是,在国民党的陈述话语中,也将国民党军的长途追击称之为“长征”。例如,蒋介石讲道,“中国有史以来,军队长征,未有徒步二万余里者”,诸将士在各纵队司令官领导之下,“忠勇奋发,或者壮烈牺牲,或者裹剑再进,或者不避危难,争为先锋,扑灭赤焰,取得无尚光荣,诚不愧为三民主义之军队”*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上册,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80页。。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语境,在国民党人看来,中共长征不过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强大国军截、堵、追击之下东逃西窜的一次严重失败与溃退的历史纪录而已”*蔡孝乾:《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
在中共的具象话语中,万里长征就是“万里长跑长追”。陈毅即说:“过去蒋介石对付我们长征的队伍是前截后堵,拦腰一棒,全国统一‘围剿’我们;万里长征是万里长跑长追,追得你屁滚尿流,那是敌人胜利的‘围剿’。”*《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473页。毛泽东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的大会上,更是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以“欢送”和“欢迎”阐释了长征概念的具象话语。他指出,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国民党话语中的“追”与中共话语中的“跑”,以至于最终形成的“万里长追”与“万里长征”,尽管体现着各自不同的历史语境,但是这一对话语范畴形成了“长征”概念的具象陈述。正如有人所说,中共“多年来把这一长途流窜命名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迫使共匪二万五千里长征者,乃由国军在后面跟踪追击,使匪无喘息余暇”,“这一段为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追,是剿匪战史上最艰苦卓绝的一页”*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1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3年,第59—60页。。不过,在中共的话语陈述中,以“二万五千里”来指称“长征”,无论是政治意向还是情感取向,都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苦”与“乐”:“长征”概念的叙事话语
所谓“叙事”话语,实际就是一种“谈论(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的方式”,一言以蔽之,就是“将了解(knowing)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telling)的东西”*〔美〕海登·怀特著,董立河译:《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2页。。爬梳相关文献资料,“苦”与“乐”不仅是叙述者表达“长征”概念的核心词汇,而且在特定语境下重构了“长征”的叙事话语。
长征之艰辛举世罕见,长征中的苦难自然“需要说说”*《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46页。。1936年陈云刊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即指出,长征中的红军“上至首领下至兵伕具有刻苦耐劳与其他各种优点,而这些都为国民党军所不及者”*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红旗出版社,1985年,第10页。。红军到达陕北后,叙述长征之“苦”的话语更为集中。毛泽东说,红军长征“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可以说,在“长征”概念的叙事话语中,艰苦之状几乎是长征概念的另一个代名词。故此,只要遇到困难,就要“想一想红军长征嘛!”长征中有多少人倒下,但“他们只要还有一点呼吸,都还要挣扎站起来,继续前进,在敌人面前,在困难面前,表现了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1页。。
长征虽苦,但红军在长征中“并不是愁眉苦脸,而且歌笑欢腾;他们看到的前途不是暗淡,而是光辉;他们不是受失败的威胁,而是前仆后继的打仗,做群众工作、做经济生产工作,积累丰富无穷的经验,为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谢觉哉文集》,第944页。。在这样的叙事语境下,长征已然成为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符号和象征。因此,即便在翻越雪山草地的艰难时刻,红军也会“在鼓乐声中,宣传队忍着饥饿,不顾寒冷,在泥泞的烂草滩上表演起来。尽管唇舌被冻得发僵,说起话来不大利索,浑身无力,唱的声音不大,可是,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乐。歌声像篝火,漫延在无垠的茫茫草地;歌声像火焰,升腾跳跃,温暖着人们的心。在歌声中,红军战士送走了寒夜,迎来了东方的曙光;在歌声中,英雄的部队又踏上了新的征程”*《星火燎原·丛书之二》,战士出版社,1986年,第160页。。
在一些经历过长征的人看来,长征之“艰苦是有味道的”,“艰苦与快乐是一事的两面,也常常在同一时间空间存在;快乐是从艰苦中来的,只有经过劳作、经过奋斗得来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快乐也常常不是要等到艰苦过去之后,而是即在艰苦之中”*《谢觉哉文集》,第946—947页。。如果说叙事是将经历过的事情转变为“可讲述的东西”,那么“长征”话语中的“苦”与“乐”,因其独具鲜明的历史语境,从而成为表达这一概念的生动话语和叙事方式。
(三)“对”与“错”:“长征”概念的路线话语
长征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被迫转移的一次长途行军。长征虽然体现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主义精神,“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51页。。因此,长征概念中的路线话语,是构成这一概念的重要意涵。
就军事路线而言,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原本应该“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结果“此计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丧失了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 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 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既然长征因军事路线的错误而起,在“长征”概念的陈述话语中,以军事路线指称这一概念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5—516、481、477、510页。
长征不仅关涉军事路线,而且关涉政治路线。故而,在“长征”的路线话语中,自然涵括着政治路线这一概念话语。邓小平就指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8页。因此,从长征一开始,就有人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长征途中“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由于改变了错误路线,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没有被消灭,保存了部分力量,继续搞革命,最后取得胜利”*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52—53页。。
综上可见,“长征”这一概念深刻地蕴含着特定语境下的路线话语和陈述表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长征就是“路线斗争”,正所谓“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564页。。这一论述,可谓是“长征”路线话语的生动阐释。
(四)“败”与“胜”:“长征”概念的辩证话语
长征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起,原有的根据地丧失殆尽。红军在被迫长征的途中,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中国革命也陷入前所未有的绝境之中。但是红军绝境逢生,经过长途跋涉落脚陕北,又成为中国革命的起点。因此,在长征概念的话语陈述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败”“胜”辩证法。
长征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失败了,在另一方面来说却是胜利了。红军“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是事实。但是就此认为红军失败了,“这不是事实”,因为“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魏建国主编:《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上册,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从革命力量来看,红军在长征途中遭到挫折,曾经发展到30万人的革命力量缩小到2万多人,尽管到陕北以后又补充了一点,但还是不到3万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红军力量的确遭到了重创。但是从另一层面来看,“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因为“人虽少了,但质量不同了”*《邓小平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4页。,“经过长征考验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是我们党和军队最可宝贵的财富,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治党治军治国的骨干”*《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88页。。
在革命战略的历史语境中,同样体现着长征概念的辩证话语。“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4页。。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给了红军“许多痛苦与许多困难”,但长征的教训告诉我们:“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红军还能克服一切的困难,最终的胜利的到达了自己的目的,那末在目前新的有利的形势之下,他一定能够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以开辟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新局面。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的不是吓怕了我们,而是锻炼了我们,坚强了我们的自信心与敢作敢为的勇气。”*魏建国主编:《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上册,第177—178页。因此,红军长征尽管痛楚,但是从中国革命的长远战略来看,“长征是播种机和宣传队,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从哲学维度观之,长征本身就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艾思奇说:“过去反对国民党五次‘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失败之后又走向单纯防御以至于退却逃跑主义的方面,这也是‘否定一切’的片面观点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和这相反的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了长征,长征在‘左’倾冒险主义失败之后,使革命力量转移阵地,这也是否定,但不是退却逃跑的消极否定,而是通过转移阵地这个否定过程,积极创造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终于在陕北找到了再一次对敌前进的阵地。”*《艾思奇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45页。毛泽东也明确指出,长征尽管“吃过那样大的苦头”,经历过失败,但是“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红旗》1978年第7期。。
可见,“长征”概念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话语,这些辩证话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长征的理论基础,也是阐释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一些论文和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包括长征在内的“胜”“败”经验基础上的总结。正是这些经验总结,才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长征”。
(五)“危”与“转”:“长征”概念的转折话语
长征是在革命力量遭受到极大摧残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导致我们多数革命根据地受挫折,使三十万革命军队减少到三万。我们为什么要长征? 长征是被迫进行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4页。。红军因危机四伏被迫长征到最终胜利入陕,转危为安的格局自然成为长征概念的一个重要转折话语。
在陈述长征的转折话语中,以“挫折”引出“长征”,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是构成长征这一转折话语的基本表达方式。1948年1月,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即指出:“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挫折,来了一个长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3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47页。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军事、政治、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冒险主义,结果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只好两条腿走路”。红军被迫长征,而长征期间的遵义会议成为转危为安的一个转折点。正是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51、58页。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也指出,由于“左”的错误,“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有了遵义会议,虽然长征中受了损失,又遇到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战胜了狂风巨浪,克服了党内的危机”*《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690页。。正是由于长征中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六中全会文件》,新华日报馆,1939年,第78页。。一言以蔽之,“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踏上胜利道路,转折点是遵义会议”*《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26页。。
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中共革命任务的不断变化,“长征”概念的转折话语所指涉的范围更为广泛。它一方面成为开拓中共革命新局面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又将其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结起来。毛泽东在瓦窑堡的一次会议上即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魏建国主编:《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上册,第107页。红军奠基西北之后,毛泽东又以更宽泛的视野说:“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5页。实际上,从红军入陕之后起,红军长征的转折话语已然突破了单纯指涉“长征”本身这一概念,而是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折转联系起来。胡乔木所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 2012年,第36页。这一话语,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转折话语的陈述逐步成为一种固定的表达方式*如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红军“以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迎来了新的曙光,开辟了光明前景”,“红军长征向世界宣告的革命理想已经变为现实,红军长征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并将继续开出更加鲜艳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25、733页。。
综观红军长征的陈述话语,尽管以其强大的“语义承载能力”,形成了具有广泛意义的多重表达,但是仔细分析则有一条清晰的逻辑,即所有的话语陈述最终都可归集于一种独特的精神积淀——长征精神。无论是“共时性”话语还是“历时性”的陈述,聚合在“长征”这一概念中的精神价值,通过人们的话语表达,使得这一概念已然超出了时空范畴,突破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活动史上树立起一座重要的丰碑。尽管从时间范畴上来看,长征只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两个年头,但历久弥新的概念陈述以及与时俱进的精神发掘,却体现在长征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从地域上讲,尽管长征涉及的是当时数个省份,但其影响不仅是全国性的,而是超越了国度的界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概念话语;在文化与哲学的概念话语中,长征话语所阐释的坚定革命信念、不怕艰难险阻的牺牲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由败而胜的辩证话语、纪律严明和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在这一概念话语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质而言之,在长征概念的多重话语中,所蕴蓄的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较量、曲折与前进的转折、光明与黑暗的搏斗、思想路线的尖锐斗争、转危为安的历史承接、承前启后的道路开辟,既是“长征”概念的核心表达,也是长征精神的具体体现。
概念对于“现代世界的语言构造”是至关重要的,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各种政治派别,正是通过“概念”表达他们的“经验、预期和行动”*〔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9页。。由是言之,长征精神的积淀,必将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长征”概念演变成为一种“行动的语言”。在随后的革命与建设道路上,中共通过运用“长征”这一概念,在“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的话语逻辑中,来建构和表达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定指涉,推动中国革命与建设达到预期的目标。
三、“行动”的概念——“长征”概念的运用
概念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行为形式”,概念话语要“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59—60页。。“长征”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话语,同样在中共革命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建构”作用。由此体现的“长征”意涵,因赋予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特定意图而演变为一种“行动”的概念。
“长征”作为行动的概念,并以此建构特定的历史意图,从红军入陕不久即已开始。1936年8月,毛泽东与杨尚昆要求参加长征的“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编辑《长征记》,意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同时“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6页。。中共认为此时出版《长征记》是“极好机会”*《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1234页。,固然是由于长征刚刚结束,许多事情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长征记》“编成后给那洋人带出去印售”,这样好的机会,“真是难得极了,既可以拿去进行国际宣传,又可以募捐,确是一举两得”*童小鹏:《军中日记(1933—1936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230—231页。。考虑到红军入陕后的客观情况,通过“长征”开展宣传和募捐活动,更为重要的意图则在于化解和摆脱中共及红军所面临的生存危机。红军长征入陕,尽管摆脱了国民党的长途“追剿”,但是陕北社会生态环境之复杂,与瑞金时期相比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之国共内战形成的血海深仇依然根深蒂固,国民党“围剿”红军的行动还在积极部署当中。就军事力量而言,尽管数路红军会合于陕北,但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而红军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90%以上的部队损失殆尽。这也就意味着当时中共所面临的首先是生存问题,“如果不能生存, 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金冲及:《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正是在这一情形之下,“长征”就成为扩大中共及红军影响的重要载体。
随后毛泽东欢迎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实地采访,同样是出于红军的出路和生存考虑。其时周恩来见到斯诺后,明确地告诉他“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美〕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页。。在斯诺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毛泽东的主要意图是希望斯诺“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些被国民党称为‘共匪’的人,使外界同情红军,帮助红军”。尽管斯诺也对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传奇故事“感到新奇,兴奋不已”,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极大兴趣,希望毛泽东讲述他本人的故事,而“毛泽东在与斯诺的长谈中讲述了中共的成长历史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但很少谈及自己和其他个人”。*〔美〕斯诺等著,刘统编译:《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479页。斯诺笔下的长征,恰恰是他所报道内容的高潮部分。他以冒险家的笔法,通过一个个充满传奇、历险和可歌可泣的事迹,讲述着红军长征史诗般的经历。特别是他用不少笔墨描述红军强渡大渡河,既紧张动人又充满英雄主义气概。在美国,当时“差不多每一位评论家都选出斯诺对长征的描述加以评论”*〔美〕肯尼思·休梅克著,郑志宁等译:《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9页。。可以说,斯诺的报道不仅成就了他个人,而且极大地宣传了红军长征。他对红军长征的热情讴歌,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震撼了世界。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斯诺的著作,其功劳堪与大禹治水相媲美。”*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Jonathan Cape, 2005,pp.198-199.仅就此而言,不难看出毛泽东欢迎斯诺实地采访并报道长征的历史意图。“长征”也因此成为建构中共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行动”概念。
红军长征入陕之际,正值日军逐步拉开全面侵华序幕之时。因而,以“长征”促抗战,也就成为抗战语境下另一个特定的“行动”概念。斯诺说,红军长征“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美〕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160页。。
实际事实正如斯诺所说,还在长征期间,中共即组织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通过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是唯一抗日反帝的武装”“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要勇敢作战,驱逐日本帝国出中国”等口号,将长征与反蒋抗日联系起来,凸显着“长征”的抗战语境和“行动”概念。红军入陕后,以“长征”促抗战的“行动”概念更为突出。毛泽东在谈及红军长征与一二九运动的关系时,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由于“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所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253页。。由此可见,从红军入陕之后开始,中共将“长征”与“抗战”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不仅转化了“长征”本身的历史语境,拓展了这一概念的意义空间,而且赋予这一概念以新的意指。
实际上,就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张闻天就及时指出,“长途行军中间所决定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页。。林伯渠则指出:“如果说过去的工作中心是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打仗,口号是‘一切服从战争’,那么现在是迅速准备充实快要到来的抗日战争的力量,一切带着国防的性质,工作中心已转到国防建设方面来了。”*《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第51页。由是言之,“长征”的历史语境势必要发生转换,通过“长征”的概念转换以推动抗日战争的展开,也就构成新时期的一个“行动”概念。有关这一论述最为经典的阐释,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落脚点”与“出发点”:“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你们等两天就要走,将来中央也要走。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5页。长征在陕北落脚,抗战从这里出发,“伟大的红军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红军长征“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鼓舞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红军长征胜利,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26页。。这样的阐述既是红军“长征”概念在抗战时期的历史语境意义,也是推动抗战顺利展开并实现最终胜利的“行动”逻辑。
概念话语的关键是“识别”,“如果你把语言、行为、交流、评价、信仰、符号、工具和地点等综合在一起,使别人能够识别出你是特定的谁(身份)在此时此地从事一种特定的什么(活动),那么你就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话语”*〔美〕詹姆斯·保罗·吉著,杨炳钧译:《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页。。“长征”这一概念的表达和运用,由于其内在地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因此,“长征”概念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构成了它的另一个“行动”维度。
长征因其史诗般的传奇经历,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因此,“长征”的概念话语自然成为“识别”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符号。毛泽东说:“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邓小平也指出:“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够经得住十年的血腥恐怖,百万大军的‘围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7页。长征绝处逢生是由于中共的领导,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的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6页。。一言以蔽之,“长征,用它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刘伯承军事文选》,第565页。。
与此同时,鉴于毛泽东在长征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在“长征”的“行动”话语维度中,也内在地蕴蓄着“毛泽东”的符号和象征。长征是被迫进行的,红军之所以被迫长征是因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及至到了遵义,毛泽东“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7、338—339页。。实际上,将长征与毛泽东联系起来,不仅是历史的逻辑,也是行动的逻辑。有人甚或径直称“长征是毛泽东的长征”。尽管许多知名的中国人参加了长征,并为此作出杰出贡献,但事实证明“长征是毛泽东的长征。毛泽东在长征期间为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获得活力而做出的努力是卓越不凡的。如果没有长征,中国今天就不是共产党的天下”*I.G.Edmonds: Mao’s Long March: an Epic of Human Courage.Macrae Smith Company,Philadelphia,1973,pp.1-4.。
将“长征”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联系起来,不仅大大突破了原初的概念意涵,而且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概念的思想张力,并使之演绎成为“建构性”的陈述话语和“行动化”的概念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将二者联系起来,也使“长征”概念的意识形态色彩尤为浓烈。而“长征”的意识形态化,又在随后的话语陈述中体现着极为重要的“建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征程中,“长征”概念的意义维度自然会演变为一种“语言行动”,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开拓新局面的重要精神资源。
四、余 论
“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长征原本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鉴于它史诗般的传奇经历,在中共及社会舆论的话语陈述中,使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演绎而成独特的符号语言,进而演绎成为一个具有极强“语义承载能力”的概念。综观中共革命道路中的“长征”概念,并非是一个僵化的语词,而是一个“行动”的概念。不同的历史任务会赋予其特定的历史语境,由此形成一个特定的行动逻辑,以期实现特定的意图和预期的目标。可以说,中共话语中的“长征”概念,绝非是“被动”的反映现实,而是能动的“制造”现实,并在这一框架内凸显着它的“行动维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共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它的“行动维度”的:一是复原和突破 “长征”概念的意义空间,来拓展它的“语义承载能力”;二是通过赋予这一概念以新的历史语境,形成新的概念话语和实践表达。由于“长征”概念始终都在凸显着它的“行动维度”,故而关联“长征”的概念史也在相应地发生迁衍。不同历史语境赋予了这一概念不同的使用标准和指涉范围,进而体现着不同的诠释功能。由于概念史不是以其语言功能来诠释,而是以社会政治功能来加以诠释,由此形成的陈述话语,“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在话语里实现着渗透了社会交际的所有方面的无数意识形态的联系”*〔苏〕巴赫金著,李辉凡等译:《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59页。。而“长征”概念正是在中共的陈述话语中,将“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联系起来,建构了这一概念的意识形态化色彩,最终成为中共诠释历史、开拓进取的精神资源。
(本文作者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天津 300134)
(责任编辑 吴志军)
《党的文献》2017年第 3期要目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学习座谈会发言选登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
认识和体会(冷 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成效和主要
经验(陈扬勇)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陈 理)
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几点思考(戴焰军)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跳出“历史周期率” (齐 彪)坚持和推进党内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尹韵公)
全面从严治党是民心所向(孙秀民)
把握规律,自觉践行全面从严治党(姚 桓)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规治党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 (蔡文华)
再谈毛泽东为什么编《六大以来》(徐建国)
毛泽东与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季春芳)
任弼时与民主革命时期团的教育训练工作 (汤 涛)
邓小平“中央要有权威”论述解析(王 桢)
邓小平、陈云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高广景)
中共二大与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原则的初步形成 (杨 俊)
20世纪30 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探析 (林 红)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动员与互助合作 (贺文乐)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公安保卫工作论析 (陈 静 孟令择)
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多层革命意义 (陈和平)
1949—1953 年中苏领导人磋商天然橡胶合作的
历史考察(李 华)
1933 年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召开时间考(王 进)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东北部队武器来源考(郭永学)
革命时期的读书会(樊宪雷)
“和生活打成一片”
——艾思奇是怎样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李 勰)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 History of the Red Army Long March——and on the CPC’s Practice express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Road
Yang Dong
The red army long march was not only a major historical event, but also a unique concept with a strong unique concept of “semantic carrying capacity” beyond time and space. In the concept meaning of the Red Army Long March, it contained both the “running” and “chasing” figurative words, also included the “bitter” and “pleasure” narrative discourse; there were Both the “right” and “wrong” words, also had “victory” and “loss” dialectical words, simultaneously inherently contained the “danger” and “security” this transition discourse. The “long march” word also was an “action” concep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one hand broken concept space through its semantic carrying capacity; On the other hand gave its new historical context to form new concep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expression, and eventually became precious spirit resources in the pioneering process.
K03; K061; K264.4
A
1003-3815(2017)-05-004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