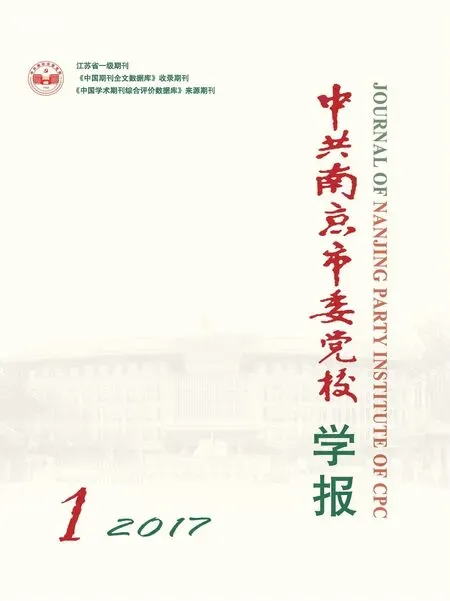论政治领导过程中的非制度性约束*
夏庆宇
(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 上海 杨浦 200433)
论政治领导过程中的非制度性约束*
夏庆宇
(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 上海 杨浦 200433)
既往的政治学研究较为关注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的监督、制约作用,并未对行政主体在领导过程中受到的非制度性约束进行集中的理论表述。这种研究现状反映了一种认识盲区,即未曾注意到任何政治领导者都会受到并未成为明确的制度设计的制约因素的约束。这些非制度性的约束因素可分为主观因素(如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的“天命观”、“仁政观”)、客观因素。客观的非制度性约束因素主要包括:客观现实对政治领导者所构成的约束、被领导者对政治领导者所构成的约束。这些非制度性的约束因素在现实政治中发挥着切实而巨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政治治理趋于“善治”而非“虐政”。研究政治现象时应注意到这些因素及其作用。因此在衡量不同政治体制的“法治”化水平时,不能仅仅以制度性约束的指标的高低为衡量标准,而应将非制度性约束的强度纳入指标体系之中。
约束;制约;制衡;制度;领导
一、引言:本论文的研究意义
美国社会科学界对社会科学论文的意义的一般理解是:论文必须揭示前人并未阐明的、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即提出某种理论)。然而,属于人文学科的历史学科则一般不要求论文必须对社会现象背后的运行机理进行解释,而只要求论文对前人未曾厘清的历史事实进行陈述。也就是说,社会科学论文以提供“理论”为宗旨,人文学科论文以提供“知识”为宗旨。
综合以上两种论文写作规范,似可以将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论文的共同的意义作这样一个比喻:论者看到了其他人未看到的事物并将其告诉给其他人的过程,便是写作论文的过程。所谓“其他人未看到的事物”,既包括现象、也包括现象背后的机制。
本文的写作主题,即是迄今为止其他人并未充分阐述过的、关于政治领导过程的一些现象——即:在任何政治领导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对政治领导者的制度性约束,而且存在着大量的非制度性约束;从古至今,非制度性的约束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政治领导者的行为,使政治领导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善治并使所有政治领导行为都呈现出某些跨时空的共性。
例如,传统上人们认为法治诞生于近代西方社会。法治的本质含义是:政治机构、政治过程受到成文的(即明确的)规定(即宪法、行政法等关于政权设置、运作的法律)的制约、约束。(一般而言,“法”包括民法、商法、刑法、国际法等法律,而“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机构、政治过程受到“法”的约束而不是非政府行为如民事行为受到“法”的约束,因此本文认为用“宪政”来代替“法治”能够更恰当地体现中文中“法治”一词的本义。)但是在近代之前,不论在东方、西方,政治领导者历来均受到多种束缚,这些束缚虽然并一定来自明文的规定、明确的制度,但的确发挥着不可否认的现实约束力。
例如在中世纪时期的西欧,日耳曼人实行封建制度,各级封建领主之间实际存在着“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契约关系,上级封建主将封地封给封臣之后,封臣有义务忠于封建主,在战时派兵随封建主作战,但是封建主一般不能也不会干预封臣领地内部的事务。日耳曼民族在政治上的这种传统习惯约束了日耳曼族领导人,使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因此西欧国家在中世纪呈现出各地封建割据严重、一盘散沙、王权衰落、治权不断下移的局面。
又如中国古代并未出现西方的“三权分立”思想——“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让三种不同的权力相互制约,因此在三权分立制度下,实际上一个国家并无最高掌权者(例如美国总统只是最高行政长官,而不是最高司法长官或立法长官),这种思路与中国古代主流的大一统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如此,中国古代也有“制约与平衡”的观念,例如《元史·列传·卷六十三》记载:“右丞相帖木迭儿传旨:廉访司权太重,故按事失实,自今不许专决六品以下官。”由此可见中国的先人们明白:一个部门的权力过大则会出问题,因此要通过合理权力分工限制某个部门权力过大、滥用权力。又如朱元璋曾明确指出各衙门之间要实行制约与平衡:“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1]
尽管中国古代的主流政治文化认为只有一个最高领导者将更有利于国家,但是中国古代的最高领导者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他的行为至少要符合当时人们的是否观念。例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指出:“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与这种观念相似,《北史·本纪·卷二》描述北魏世祖拓跋焘“明于刑赏。功者赏不遗贱,罪者刑不避亲,虽宠爱之,终不亏法”。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针对统治者的不成文但又切实存在的评价标准,如果皇帝的行为背离这种标准也会遭到臣民的非议。
中国古代的许多皇帝甚至自觉地形成了法治观念。拓跋焘就“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另外《元史·列传·卷六十三》记载谢让的事迹:“让上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律以辅治。堂堂圣朝,讵可无法以准之,使吏任其情、民罹其毒乎!’帝嘉纳之。乃命中书省纂集典章,以让精律学,使为校正官”。朱元璋也指出:“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2]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不是不存在法治——至少存在法治因素。
另外,中国古代也有分权的思想——例如六部各司其职,权限分明。尽管刑部须要受皇帝管理,但“刑部,天下持平”(《元史·列传·卷七》)的理念难道不是“司法权独立”的理念吗?因此,认为“司法权独立”的概念是孟德斯鸠首先提出来的,似乎并不准确。
由此,本文认为,在古今中外任何政治领导过程中都存在不成文的、非制度性的对领导者的制约因素。随便翻翻历史书就会发现: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们很不自由。不论是居于“至尊”之位的皇帝还是手握兵权的枭雄,不论是国王还是苏丹,在执政过程中都在事实上受到许多掣肘。尽管中国古代尚没有后来从西方舶来的“三权分立”的观念,但是掌权者也不是为所欲为的,都是在一定的“规范”内活动。有些“规范”形成了明确的制度设计或成文的规定,例如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史官、言官、谏官制度,历朝历代的“祖宗之法”;有些规范则未成为明确的制度设计但却现实地存在着。非制度性的规范、制约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主观的约束因素、客观的约束因素两类。
二、政治领导过程中的主观的非制度性约束因素
这类因素包括两类:第一,能够起到约束政治领导者的行为的作用的物议性、社会舆论性因素。例如,周厉王之所以令人民道路以目,是因为人民的物议在一定程度上对周王起着制约作用。最终周厉王因为人民暴动而被流放,这显示了人心是能够对封建统治者构成强力的约束的。又如,中国古代的“德治”、“以正治国”、“天命”、“天道”、“德配天地”观念自周初以来就成为了君、臣、民都认可的政治共识,这种共识使统治者的“失德”的政治行为受到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否定,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统治者的行为。第二,能够约束政治领导者的思想、进而能够约束政治领导者的行为的因素(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会影响其行为)。例如,中国古代统治者一般相信天人感应,天子代表天统治人民,因此天子的行为必须符合天的意志,例如不能骄奢淫逸、要爱民如子。这种思想会对封建帝王形成约束,例如当大旱、蝗灾等天灾发生时,封建帝王一般会反躬自省、考虑自己的行为有哪些失德的地方、下“罪己诏”、改变失德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封建帝王在行为时也会有所顾忌。
从形式上说,上述两类制约因素是主观的,从有关制约因素的客观存在和其发挥的现实作用方面来说,上述制约因素又是客观的。下面以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念对统治者所产生的约束作用为例进行剖析。
中国古代的“天命观”指的是一个王朝的兴替是由天意所决定的,而天决定让一个王朝兴、亡的标准是统治者的行为是否符合天的意志、是否符合德治的标准。如朱元璋就明确指出:“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为心,则能永受天之眷顾。若生怠慢,祸必加焉,可不畏哉?”[3]其实,这类“天命观”的具体内容是封建王朝对客观现实进行认识、总结之后形成的产物。往往在实行暴政的王朝灭亡之后,新兴的朝代会看到前朝的经验教训,这时统治集团内部的“天命”意识会最为强烈。因此,“天命”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对治国理政进行的经验总结、是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反映社会的客观需要的一种观念,它事实上反映的是人民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统治者过于残暴,人民将推翻统治者,从而统治者便失去了“天命”。按照上述理解,“天命观”也不是中国独有的,西方的“自然法(natural law)”观念与“天命观”相通,都是人对自身所受到的客观世界的现实约束的一种认识——但是“天命观”带有浓厚的道德观念和神秘主义色彩,这是“自然法”观念所不具备的。
所谓“天命”必然是某种高尚的东西,因此“天命观”内含着统治者必须推崇道德的含义,这就意味着统治者不能“无道”、不能“缺德”,要仁民爱物、克己复礼、修齐治平。“天命观”中的“以德配天”、“天命不常”思想主要是对统治者提出的道德、行为要求。因此可以说,“天命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法治观念。“天命观”要求任何人——特别是统治者——都不能违背“天命”,这也就意味着天子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政治权力要受到约束。因此,“天命观”无疑会对中国古代统治者形成约束。道德、法律都能够约束人的行为,“天命观”本身体现了对统治者的约束,本身就发挥了行政法的作用。尽管“天命观”在约束执政者的行为方面属于一种软约束,但有时也能变成硬约束。例如意识里深植了“德治”观念的大臣直言进谏、面折廷争、以死明志,有时候是能够对皇帝构成很强的约束的,这类令皇帝收回成命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俯拾皆是。
“天命观”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的思维之中,连最底层的庶民都有这样的观念:皇帝是“有道”还是“无道”,官员“为不为民做主”。这无疑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都认为皇帝必须“循道而行”,官员必须“为民父母”,这种观念乃是一种洋溢于全社会的正能量,形成了一种制约政权的社会文化氛围。至于进入统治阶层的、受到这种思想熏陶的、有良知、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在维护善治方面发挥的作用会更大,因为他们更接近权力、更能够直接约束统治者的不良行为。与其它传统社会相比,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义”与“非义”的观念非常强烈,成为中国传统官僚的一种显著特点。
三、政治领导过程中的客观的非制度性约束因素
这类因素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领导者受到客观现实的约束。例如不论是奴隶主阶级统治者还是封建主阶级担任国家的统治者,只要国家发生了水灾,都必须组织救灾,这是因为:有了被统治者,统治者的存在才有意义;如果被统治者出现了生存危机,那么统治者的好日子也不会长久。而后,在治理水灾的过程中,领导者的行动还必须符合水利工程的原理——不论谁当领导者,最终所能采取的行动都必须是符合水利原理的而不能违背有关客观规律,不论谁当统治者都必须遵循有关水利原理、最终做出相同的决策。由此就可以看出客观现实、客观世界的现实规定性对领导者的行为所构成的约束。
可以说,客观现实决定了所有政权都必须遵守一些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又真实存在的规范。这种规范意味着统治者在行动时必须避免一些禁忌、必须完成一些工作、必须照顾到一些情况、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否则政权的统治或治理就会出现问题。
阅读历史可以看出,不论何人“坐天下”,有些“规范”是必须遵守的。比如不能搞得民不聊生,否则就是自取灭亡;相反还要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因为政权的经费来源于民间,来源于人民创造财富。政府必须承担起一些公共职能、提供一些公共产品,比如敌国来犯不能不应对、社会秩序不能不维护、生产不能不予以鼓励、统治机构自身的稳定不能不维持、在文化教育领域政府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发生天灾不能不管,等等。如朱元璋曾告诫子孙:“四方有水旱等灾,当验国之所积,于被灾去处优免税粮。”[4]
统治其实也是一种重担,统治也不能只取不予,统治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要想统治得越久,须要承担的责任、完成的事业就越多,统治者就越不自由。对自己负责任的掌权者、明智的掌权者会活得非常累——累了一辈子的康熙、“累死”了的雍正就是典型例子(雍正长年勤于政事、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吃了术士炼的丹药而暴毙)。例如朱元璋如此自述勤政的情况:“察情观变,虑患防危,如履渊冰,心胆为之不宁。晚朝毕而入,清朝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时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国家所由兴也。”[5]
在面对“天下”时,统治者须要处理许多涉及人民生计的事情;在管理统治集团时,统治者则要付出更多的辛劳。最危险的敌人往往就在身边,统治者不仅要防范统治集团内部的阴谋家,也要注重统治集团内部的平衡。例如皇帝要想任命一名官员,通常也要考虑某官吏的资历能不能降服下属、其他官员会不会有意见等情况再作出任命;要想册封一名嫔妃,也不能不考虑其它嫔妃背后的势力会有什么反应、该决定是否会对统治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可以说,现实中就客观地存在着一些针对统治者的不成文的“规范”,明智的统治者能感受到它们并会顺从它们。即便是统治者也不能打破这种天然存在的“规范”,否则统治集团内部、外部就会出问题。这些就是本文所谓的“客观环境对政治领导者的行为的规范”。这是一种普世性的约束,一切政权只要顾及到相应的利害,都会遵守这些规范。这类规范永远存在、永恒发挥作用,这是因为“统治”本身就不是自由的,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人是完全自由的,最高封建统治者亦不例外。这些规范也决定:不论是何种政权,都不能过度侵害被统治者的利益,否则这个政权必然垮塌。因此,古今中外都不可能出现暴政长期维持的状况。
值得指出,客观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行为,但是也有例外,例外之一是政治领导者不一定能够意识到客观环境决定他应当做的、对他来说最有利的行为是什么;例外之二是政治领导者有时可能会做违背自己利益的事。与客观环境相比,更加直接地决定人的行为的是人的思想、想法。如果客观环境决定了一个领导者采取一种行动会对自己有利、反之就有害,但是这个领导者认识不到这种客观现实或者执意不按照这种客观要求去做,那么他就有可能不沿着客观现实所规定的道路行事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最终自取灭亡。因此非制度性约束因素并不总是能够约束政治领导者的行为,但如果政治领导者执意不受非制度性约束因素(如民意)的约束,那么其政治领导就有可能很快结束——例如在民不聊生时爆发农民起义。由此可见,社会本身具有对暴政的约束机制,当暴政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灭亡,因此任何政府的行为都面临着潜在的限制。
第二,领导者受到被领导者的约束。可以说,领导者领导被领导者的过程,其实也是被领导者“领导”领导者的过程。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一个领导者的位置都不是天然能够维持下去的,从根本上说,领导者必须符合被领导者的期望,才能成为领导者并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因此,不论是否实行民主政体,领导者一定会受到被领导者的束缚,只不过在民主制下,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束缚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已。但在君主制等制度下,被领导者会对领导者构成不那么明显但同样强大的约束。
被领导者往往有摆脱被领导地位、自己成为领导者的意图。因此领导者必须防范被领导者闹独立或暗地里架空自己。例如有著作对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其领导力难以贯彻到地方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由于那时地方政府中传统的回避制度被彻底地破坏了,全国各省差不多都被当地的军头所盘踞,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通统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6]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尚无法对地方实行真正的领导,可想而知中央政府要想如臂使指地领导地方其难度有多大了。
广义的被领导者中还包括除最高领导人之外的领导人。领导集团内部往往也会形成相互之间的强烈制约关系,而且拥有权力的领导集团中的成员往往比普通被领导者能够对其他领导者形成更强烈的制约。例如赵匡胤取代柴宗训、赵光义又取代赵匡胤成为皇帝,中国古代经常出现外戚及宦官的干政等等,就表现出领导集团中的人会对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领导者形成强力的制约。如果最高领导者无德无能,很容易被其他人取代。
四、领导者的素质与非制度性约束因素的关系
成为领导者并不须要具备相同的素质,但是担任领导者则须要具备一些相同的素质,其原因在于在担任领导者的过程中要受到基本类似的非制度性约束因素的束缚。
(一)成为领导者所须具备的素质
无论古今中外,都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现象。人群中存在领导者这一现象,虽然不像猴群中要有一位猴王、羊群中要有一个领头羊之类的现象表现得那样明显,但是在任何人群中,不同的人在群体中发挥的作用很难保持绝对相同:往往自然地会有些人在人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些人则较少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发挥更大影响力的人,虽然可能并不具备领导者的名义,但事实上就是领导者。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成为领导者?须指出,在这里讨论的是自然地出现的领导者,而非已经有了行政机构、由有关机构任命的领导者(或者更笼统地说,由既有的产生领导者的机制产生的领导者,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法理型领导者)。自然出现的领导者与法理型领导者的产生过程是存在差异的:后者有整套的行政机构、强力机关作为被任命的领导者开展领导活动的后盾;而自然地出现的领导者则是依靠自身的素质、自身的素质和自身的活动对群体中的其他人产生的影响而成为领导者的。
在讨论一个潜在的领导者所应具备的素质之前,应看到的一个现象是“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会要求领导者具备不同的素质,因此,在一个非领导者成为领导者的过程中,并不须要有关人员具备相同的素质。可举简单的例子对此进行说明: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贺龙曾经凭借两把菜刀闹革命,由此成为革命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贺龙具备的素质是拥有比一般人更强烈的革命精神;而诸葛亮成为刘备的重要助手、蜀军的领导者之一,则主要是因为其谋略过人。因此,成为领导者的人,并不须要具备相同的素质。
但是能够凭自己的素质成为领导者的人具备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至少其某一方面的素质超过一般人,二是其所具备的素质适合了时代(或者说客观形势)的需要。
与上述自然形成的领导人不同,一些人是在已经形成了一套产生领导人的机制的情况下成为领导者的。相对而言,这些人自身的素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外界的因素、非领导者个人素质的因素会在这些人成为领导者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君主制下,要想成为君主,重要是天生的血统;在今天的美国要想成为总统,必须拥有大笔资金开展竞选活动。
(二)担任领导者所须具备的素质
前已述及,要想成为领导者,有关人员所须具备的素质并不一定相同,但是担任领导者的人须要相同的素质,这是因为领导的过程带有一定的共性,领导者往往须要处理相同的事务。在此处,主要讨论在政治领导现象中领导者所须具备的素质。
第一,处事公允。在领导过程中,往往须要分配利益。在分配利益时,领导者要能够服众。被领导者之所以不会对领导者作出的分配决定提出质疑,主要是因为被领导者能够感到领导者的分配大体符合公平原则。(当然,有时领导者在自己领导的团体内部所进行的分配并不公平,例如封建主把获得的主要的财富分给骑士,依靠骑士的忠诚来维持对普通百姓的统治。但是在骑士集团内部,封建主的分配也要做到公平,不能使骑士因分配不公而起来反对自己。)而且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往往须要对下属进行激励或约束,因此领导者在赏罚过程中更要注意做到处事公允。因此可以说,任何人担任领导,在进行分配、赏罚时都不是自由的,他必须按照下属心目中普遍认同的公平原则行事。任何一个团体、国家所制定的分配、赏罚机制必然要体现、符合这个团体、国家的人民心目中所认可的公平原则。例如,《元史》对元成宗皇后卜鲁罕的最重要评价是:“大德之政,人称平允”,可见即使是在古代为政的客观标准之一也是平允,要想做到平允统治者就不能随意作为。又如慈禧太后之所以能长期统治清政府,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她能够处事公允,让满族宗室成员、汉族大员基本上能够对她的行事感到心服。
要做到处事公允,就须要领导者具备一定的智慧,能够对下属的功过作出正确的评价并作出相应的赏罚,领导者还要掌握下属的心理、对赏罚的决定所能引发的反应有所判断。例如由于项羽未封田荣为王,田荣大为不满并起兵反对项羽,这一事件在刘邦击败项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如果是一名合格的领导者,即使不能使田荣感到自己受到了公平对待,项羽也应当预见到封王的决定可能引起的田荣的反应,从而提前采取措施防止田荣反叛事件的发生。
第二,决策高明。任何一个团体往往是因为某一或某些原因而存在的,因此团体往往会有自己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领导者要带领团体采取行动。在此过程中,领导者要及时给团体指明方向。一般情况下,团体内部围绕团体所应采取的行动这一问题经常会出现不同的意见,这个时候领导者必须能够对不同的意见进行辨析、明确哪种意见更高明并作出取舍。在此过程中,领导者不仅要有果断作出决策的能力,还要有听取不同意见的习惯(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更要有对不同意见进行科学判断的智慧。总之,领导者要能够作出最高明的决策——如果领导者的决策不如团体中的其他人的意见高明,那么这个领导者的位置是难以长期维持的。例如,毛泽东曾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7]也就是说,在太平天国发展过程中,杨秀清的决策能力逐渐显得比洪秀全高明,因此许多将领开始拥护杨的领导,洪秀全的领导地位已经动摇了。
领导者决策高明这一点可以体现为两种情况:一是领导者本人具备最高的智慧(例如毛泽东在红军反围剿和长征过程中显示出了比其他领导人更高超的军事才能,由此中央其他领导人才认可他的领导地位);二是领导者能够采纳其他聪明人的建议,从而作出高明的决策(例如刘邦)。
由于正确的决策必然是符合客观需要的决策,因此领导者在作出决策时也是不自由的,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符合客观现实。
第三,严于律己。领导者受到的有形的约束似乎要比普通人小,但事实上领导者注定受到许多无形的约束,这类约束突出表现在:如果领导者的决策不符合客观要求,集体的事业就会遭遇失败,从而动摇领导者的地位;同样地,如果领导者恣意妄为,会严重影响被领导者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例如历史上著名的“止谤”的周厉王最终遭遇民变:“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因此,领导者要想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必须有很强的自制力,能够自行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其自制力要比普通人更大,这是因为手中握有权力的领导者要比没有权力的普通人更有条件恣意妄为。
第四,善于服众。领导过程中,最根本的是要能够得到下属的服从。有的领导者善于得到下属的爱戴,有的领导者善于维护自己的权威,但在多数情况下领导者都要做到恩威并施。此外,领导者的位置往往是众人所觊觎的,因此领导者要足够机警且能够采取措施消除他人对自己的地位的威胁。
正是由于任何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均须面临基本类似的、非制度性制约因素,因此所有领导者才都须要具备上述四种素质。
总之,任何政治领导者都会受到客观的、主观的非制度性约束的束缚。这些约束因素表现得没有制度性约束因素那样明显,但在研究政治现象时必须注意到这些无形的约束力量所发挥的实际作用。由此,政治学研究就可以摆脱仅仅关注政治构架中的正式的制约性制度设计的狭隘做法,更全面地认识不同的政治体制在不同的社会中所受到的制约,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价不同政治体制的优劣。
此外,任何政治体制都处在具体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中,有关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会对政治体制构成某些非制度性的约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本身不能决定政府的治理绩效,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结合在一起才共同决定政治绩效。例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倡仁政,由此营造出的社会氛围对王朝政权的行为构成了明显的约束,因此不能因为中国古代实行皇族统治就认为古代王朝在任何时候都在推行暴政。又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强大,因此尽管教会本不应该属于政治机构,但教权在当时还是对王权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因此,政治学的研究要避免仅仅关注正式制度而忽视其它现实影响因素、非制度性影响因素的倾向。
[1][2][3][4][5] 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第三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784、783、785、786、788.
[6] 唐德刚.袁氏当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09.
[7] 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70.
(责任编辑: 育 东)
本文为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后期资助基金项目“东欧诸国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研究”(16JHQ025)阶段成果。
2016-12-15
夏庆宇(1981—),男,辽宁鞍山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D0
A
1672-1071(2017)01-00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