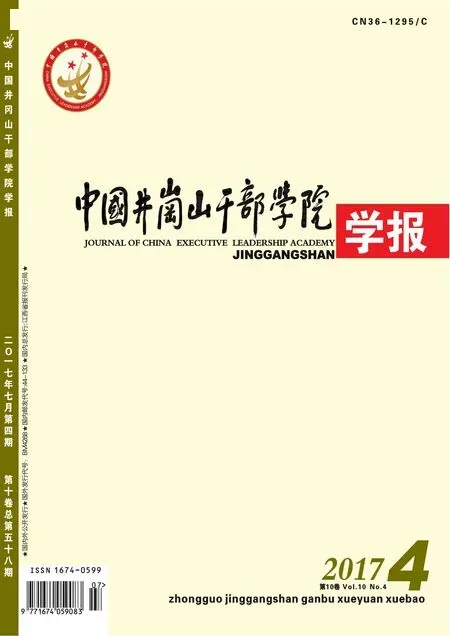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的转折
□张秋实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 武汉 43002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的转折
□张秋实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 武汉 430022)
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中共领导开展的革命其内涵由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转到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政权”的土地革命,是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战略方针的激进化促成了这一历史转折,中共五大是这一转折过程的开始,而八七会议则是这一转折过程的完成。中共五大对八七会议的召开、对蒋汪相继叛变后革命顺利实现历史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是对五大会议精神的继承、贯彻和深化。中共从五大到八七会议转折的完成,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功过互存。
联共(布);共产国际;中共五大;八七会议;革命转折
1927年中共在大革命的中心城市武汉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中共五大,一次是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两次会议相隔时间不长,却伴随着中国革命历程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从五大到八七会议,在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领导开展的革命其内涵由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转到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政权”的土地革命。两次会议恰好处在大革命后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转折阶段。任何历史转折都有一个过程,并不是瞬间发生和完成的。五大应该是这一转折过程的开始,而八七会议则是这一转折过程的完成。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这次转折有着密切关系。
一、联共(布)、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激进战略方针并成为指导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的根本遵循
(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提出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激进战略方针
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召开以前,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在革命前途指向上不是太清楚,也不是很激进。“以前国际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案,不是抽象的指示一点东方民族运动的一般倾向,便是分析中国眼前较琐屑的事象以及目前一些工作方针。”但是,这次“所议决的中国问题提案,则不然了”[1]P12。因为它明确提出“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战略方针”。相比于1923年8月斯大林对派驻中国工作的鲍罗廷提出“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言,这个战略方针是明确而激进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围绕中国革命新的战略方针,还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组织任务作出决定,即做好增加党员数量、巩固和改进支部工作、教育和培养革命骨干、建立结构合理并能迅速收缩和转移的党的领导机关、建立与国民党的正确关系、千方百计加强工会工作、认真对待农村工作、重视军事工作及工农青年工作和国际联络等10个方面的工作,并要求中共创新自己的工作方法[2]P76-88。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两个文件于1927年1月底传达到中共中央。对于这一新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立即看出“国际此提案之执行,影响到我们党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由于不同寻常,中央政治局不敢怠慢,开会进行了讨论,2月发布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对此前在理论和实践指导上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以往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认识不清,“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把这两个革命“截然划分为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致使“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或“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此,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反省过去的“二次革命”的思维和理念,明确表示“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并决定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同时,要求“各区委各地委各特支”,围绕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独裁制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农民政纲等“几个特殊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其目的是“要全党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义”[1]P14-15。
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战略目标的提出,以及为贯彻落实激进战略方针而提出的“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开展土地革命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2]P4等重大理论原则,既意味着中国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国民革命存在着潜在的转折性(这种潜在转折性的最大一点就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国民革命因两党的革命目标不同而导致分裂),又为此后在武汉相继召开的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提供了明确而激进的指导思想。
(二)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激进战略方针成为指导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的根本遵循
为了贯彻落实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革命的激进战略方针,1927年1月,共产国际决定派出一个三人代表团,专门指导中共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维经斯基、多里奥和罗易(4月7日又增补鲍罗廷)。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专门为参加指导中共五大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和多里奥作出指示,对大会的日程安排、需要讨论的问题提出具体规定,其中特别明确两条原则性的指令:一是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二是中共五大的组织决定则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当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为依据[2]P91-92。
由于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革命激进战略方针的提出以及共产国际专门代表团的具体指导,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共五大,相较于四大在理论建树、组织建设和制度创建等方面有很大的提升,所制定的革命政策和措施也比以往要激进许多。资料显示,在五大召开过程中,维经斯基、罗易多次发表讲话,内容涵盖了大会涉及到的所有重要问题,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建立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革命专政等几个要害问题进行了重点阐述,他们的讲话对五大贯彻实施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精神、制定中国革命新方针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五大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等6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目标,提出了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土地革命、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基本任务。五大的亲历者蔡和森说:“五次大会一切决议案的精神都是根据国际决议的,所以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
中共五大闭幕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二楼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的召开使五大提出的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等曾因顾及维持国共合作而耽搁或放弃的激进政策,终于无保留地被付诸实施,成为革命历史实践,并发展到将土地革命与武装暴动相结合的阶段。因此,八七会议是对五大会议精神的继承、贯彻和深化,是从五大到八七会议历史转折的关键环节。
由此可见,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都是以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激进战略方针为根本遵循的。也就是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所制定的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激进战略方针,以及土地革命、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民主专政、武装斗争等重大理论原则的提出和确立,使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有了指导思想上的一致,遵循的都是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激进革命战略方针。
二、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激进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经历了搁置一边、部分实施和整体实施的过程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强调,是在坚持国共合作的前提下作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需要在何等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P619。那么,中共这时面临的“难以置信的矛盾”局面是什么呢?就是按照联共(布)、共产国际的要求,既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发展工农运动,开展土地革命,将革命引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又要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诸多激进政策要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指导下实施,这就造成了一个两难的局面:推行革命的激进政策,势必要冲击到统一战线内右翼势力的既得利益,最终导致统一战线破裂。这种局面导致莫斯科围绕激进战略方针为中共所提供的一系列具体的激进政策和策略,在国共合作的框架内并不能立即被执行,因而从五大到八七会议的转折是随着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推进并最终实现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笔者分三个阶段来叙述这一转折过程。
(一)五大以后到7月12日以前,五大制定的诸多激进政策以及莫斯科的“五月紧急指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大打折扣,或曰被搁置一边
中共五大结束后,武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日益恶化。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在宜昌叛变,兵锋直逼武汉。5月21日,许克祥率部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发起进攻,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万余人,湖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声称要查办许克祥的同时,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过火”问题。这个历史事实说明:按照五大制定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等土地革命的措施还没有开始实行,北伐战争时期兴起的工农运动反遭“查办”。
马日事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召开(1927年5月18日-30日)期间,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结束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5月30日给鲍罗廷、罗易、柳克斯(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普利切)三人发了一封内容激进的电报,通常被人们称为莫斯科“五月紧急指示”[2]P298-300。其要点是通过武汉国民政府,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通过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武装党员群众,组建七万革命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6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给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发来4条补充指示[2]P306-307,6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电示鲍罗廷和陈独秀,指出:“阻止进行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2]P307在接连收到莫斯科三封电报之后,6月7日,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鲍罗廷、罗易等召开联席会议,专门讨论“紧急指示”和补充指示。但是讨论结果是:衷心赞同指示,但未必能够贯彻执行[2]P308-310。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对五月紧急指示的消极态度,是由于指示本身存在着自相矛盾导致的。莫斯科既要求武装工农、开展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中央,又要求这些都应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在汪精卫的国民党点头同意下进行和实施。这就使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陷于两难的困境:要拉住已经日益右转的汪精卫集团,通过他们领导的武汉政府来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显然难以做到;而要撇开武汉政府独立开展土地革命,组建革命武装,又必然会使已濒临解体的国共合作立即破裂。同时,在当时情况下,中共是否有力量改变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的人员结构?是否有能力组织军事法庭来审判夏斗寅、许克祥等反动军官?是否有足够的武器把勇敢奋斗的工农群众武装起来?这些都是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由于“五月紧急指示”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所以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还有鲍罗廷等都认为难以执行。罗易虽然口头上强调应该执行,但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主意。
不仅如此,为了拉住汪精卫集团,6月30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会议决定,瞿秋白受命起草《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并在决议案中提出国共合作的11条政纲。主要内容有:重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声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分割政权的意义”,并向国民党保证: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他们的要求必须符合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政府的法令;工会不得干涉店员的解雇、店铺的管理,更不得惩罚店主;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越店主的经济能力;工会和纠察队等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除非政府允许,不得行使警察职权,如逮捕、审判和巡逻[1]P292-293。这是一个对国民党全面退却的纲领。但是,它既无法拖住汪精卫集团急剧右驶的车轮,又使中共中央成为革命风浪中一艘迷途的航船。
由此可见,在五大以后到7月12日以前这一阶段,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并没有将五大制定的诸如开展土地革命、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工农联盟的民主专政等正确理论原则与激进革命措施付诸实践,相反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形成了压制工农运动、搁置土地革命、放弃争取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取消农民暴动、解散工人纠察队等实际错误。
(二)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新五人常委开始在实际中撇开汪精卫的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将中共五大制定的激进革命政策部分付诸实施,使革命转折在实际中发生
6月底7月初,联共(布)、共产国际下决心调整鲍罗廷和陈独秀,指令改组中共中央。7月12日,根据莫斯科的指示,鲍罗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陈独秀辞职,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中央改组虽说晚了一些,但它是从五大到八七转折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以张国焘为首的中共中央新五人常委临危受命,开始了从此时到八七会议召开的紧急过渡。
首先,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7月13日公开发表《对政局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努力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更将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将继续解放农民之斗争、亦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为兵士的利益而斗争。对于一直处于妥协退让、又遭反动势力打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来说,这篇《宣言》可谓充满激情,读来令人荡气回肠。7月13日宣言,是个界碑,表明五大制定的激进政策将开始付诸实施。其次,7月中下旬,五人常委率领中共中央部署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党在武汉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以保存党的组织。再次,新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并且直接决定和领导了南昌武装暴动。南昌起义不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且诞生了中共独立领导创建的革命军队。总之,新的中共中央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烈火,开始了中国革命的转变。
(三)八七会议召开及其精神的贯彻落实,使五大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激进政策和策略被整体付诸实施,中国革命第一次转折完成
大革命失败后,罗明纳兹受莫斯科委派,接替鲍罗廷、罗易和维经斯基等人,成为共产国际驻华全权特使。他到中国武汉的主要使命是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纠正过去工作中所犯的种种错误,部署实施此前已经制定的所有激进政策和策略,以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由于环境险恶,会议从早开到晚,一天结束。会议深刻反思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指出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我们党武装工农的实际力量如何,党应当把力量建立在工农群众的身上;会议总结了党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推行右倾妥协政策的教训,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所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实际上是将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的精神在实际斗争中贯彻落实;会议深刻检讨了党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认识到武装工农的必要性,没有想到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会议向全党提出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秋收时期,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从而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
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中央领导机关此前的种种妥协退让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结束后,以瞿秋白为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和途径向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会议精神及新的斗争策略,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的斗志,此后各地武装起义“群雄四起”,开展游击战争,进而建立农村割据和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临时中央政治局命令各级党组织建立秘密工作机关,及时确立党在秘密状况下的组织管理方式和各项秘密工作原则及措施,建立严密有序的地下交通网络,确保党的地下组织散而不乱;出版地下党刊,向敌人展开新的斗争。
由此可见,八七会议在7月12日新中央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将五大以来被搁置的激进政策整体付诸实施,并通过在斗争方式、革命途径、革命内容等方面的转变,把中国共产党从严重的政治困局中解救出来,把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而完成了从五大到八七会议的革命转折。
我们回顾从五大到八七会议的转折过程,可以得到这样一些结论:从五大结束到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其间五大制定的诸多激进政策,以及共产国际八大召开后莫斯科给中共发来的“五月紧急指示”,绝大多数被束之高阁,没有贯彻执行,既有“不想执行”的畏难情绪,也有“没法执行”的客观原因;从7月12日新的五人常委会成立到八七会议召开前,因国共合作的框架解体,以五人常委为核心的新中央,为了应对时局的转变,开始积极地将五大以来的诸多激进政策部分地付诸实施,实施的结果使革命转折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八七会议召开及其贯彻执行时期,尽管联共(布)、共产国际仍然指示中共“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却“不退出国民党”,但毕竟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中共可以单独地全面整体地贯彻执行自五大以来莫斯科给予的一系列激进政策和策略,从而使八七会议成为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发生的第一次转折完成的主要标志。
三、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共从五大到八七会议转折完成的指导功过互存
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大革命形势进入波澜壮阔、波谲云诡的变幻莫测时期,特别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五大到八七会议阶段,革命既在原有的轨道上向前,同时又潜伏和孕育着诸多革命转折的因素。而贯穿这一过程始终不变的则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挥动的指挥棒。在这期间,莫斯科指导和影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派遣共产国际代表,让他们坐镇武汉,直接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转折,如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罗明纳兹、纽曼等;二是通过共产国际召开会议、发布领导人讲话和会议决议指导中国革命,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文件精神,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讲话;三是通过直接发给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的电报、电令、指示信等进行遥控。联共(布)、共产国际通过上述途径指导中国革命完成了从五大到八七会议的革命转折。
毛泽东曾对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功过有一个言简意赅的评价,就是“两头好,中间坏”。如果说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是“两头好”的先头阶段,而抗日战争时期是“两头好”的后头阶段,那么本文所论及的内容刚好处于“两头好”时的先头阶段。但正如周恩来所言“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评价可以遵循这一思路进行。笔者认为,评价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从五大到八七转折的影响和作用,既不能夸大其所犯的错误,以至于全盘否定其正面的积极的一面;也不能像斯大林所宣称的那样,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人都找不出哪一个指示和决议是有错误的,对自身所犯的错误完全忽略不计,一好到底,而应以尊重历史的态度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客观地说,联共(布)、共产国际在指导完成中国革命从五大到八七会议的历史转折过程中是功过互存,但功绩是主要的。
“功”的方面主要有下列几点:
一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对中国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强调都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全会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形势迫使帝国主义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新策略,大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脱离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当前民族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中国革命的前途应该是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方向,无产阶级应竭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极其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优势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全会所提出和确立的上述重大理论原则,以及制定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激进战略方针,对顺利实现从五大到八七会议的革命转折具有积极的旗帜引领作用。
二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使中共五大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建树。五大党章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五大党章制定了许多组织建设的新规章制度,比如,对党的纵向组织体系进行了适应发展形势要求的系统建构,自上而下地划为中央、省委、县委(市委)、区委、支部五级,并确定了各级组织名称,打破了地域、行业以及全国范围内党员数量不大对组织发展造成的限制,使中共的组织发展能够延伸到全国的四面八方和各行各业,为中共此后的组织发展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大系统;还有对党的高层领导机构的横向布局进行规范,首次将中央决策机构从日常工作机关中剥离,首次建立中央和省级监察委员会,使纪检工作和监察制度开始产生。这一切使党的领导机构更加科学化,为中共此后的自身发展以及在革命逆境中能够顺利实现革命转折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是联共(布)、共产国际给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发来的“五月紧急指示”虽然没有立即被贯彻执行,但是它提出的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动员两万共产党员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等主张[2]P298-300,富于革命性和激进性,抓住了克服革命危局的要害。虽然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它们显得有些不切实际,也没有及时发挥出积极的指导作用,但是在国共合作破裂后,这些激进措施立马成为中共逆势而行的首选动作,使革命的转折具有实际的转折意义。
四是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的召开,在从五大到八七会议的革命转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充分证明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在这一转折过程中给予中共的指导是积极的、比较正确的,是有贡献的。
“过”的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实现转折的过程中,高估了国民党的革命性,低估了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将革命向前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蒋介石、汪精卫这些假左派身上,在强调中共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同时,又在大革命后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紧急关头和关键时刻,表面上给予中共的政策和策略越来越激进,实际上又要求“联合战线高于一切”,其结果等于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以至最终导致全面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二是1927年4月以后,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国民革命的形势迅速恶化,在中共和中国革命面临着激烈而严峻的挑战之时,身负指导中国大革命重任的莫斯科驻华代表之间却分歧密布、矛盾重重,他们在工农运动、土地革命、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策等问题的决策上一再地发生争论。蔡和森说:新国际代表罗易一到武汉(4月6日)即与鲍罗廷同志政见冲突。罗易自己也说:“在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军事行动方向问题、西北方针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问题、共产国际代表机构问题)上同鲍有分歧。”[2]P242-243莫斯科驻华代表在贯彻落实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的主观意图之间的差异,以及主观意图与客观实践的非耦合性,并由此导致的意见分歧和摩擦,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政局变化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使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夹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之间,在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历史转折的过程中显得被动摇摆,因而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3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姚金果)
Soviet Communist Party(Bolshevik),Communist International,and the CPC’s Transition from 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to the August Seventh Conference
ZHANG Qiu-shi
(Party School of CPC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Wuhan,Hubei 430022,China)
From 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to the August Seventh Conference of the CPC,the connotation of the revolution carried by the Party shifted from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of“fighting the western powers and eliminating warlords”to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of“establishing workers and peasants’armed independentregimes”.This shift was facilitated by 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guidelin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Bolshevik)an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guide over Chinese revolution.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shift and the August Seventh Conference of the CPC was the completion of the turn.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vening the August Seventh Conference and the success of the historical turn of revolution after Chiang Kai Shek and Wang Jingwei;the August Seventh Conference was the heritage,implementa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to the August Seventh Conference,the guidance of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has both merits and demerits.
Soviet Communist Party(Bolshevik);Communist International;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August Seventh Conference;revolutionary turn
2017-06-02
张秋实(1960—),女,湖北罗田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D231
A
1674-0599(2017)04-006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