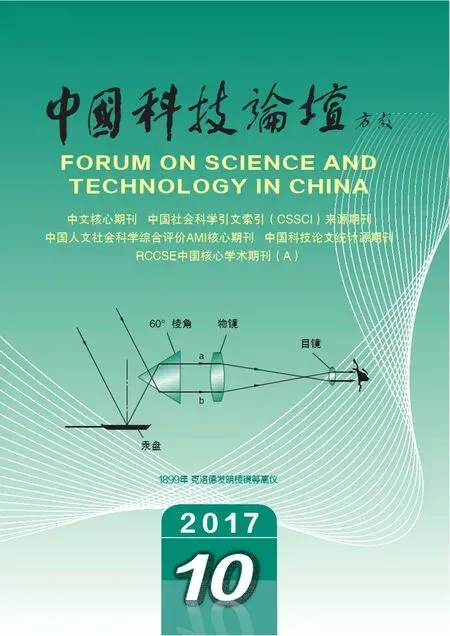纯电动乘用车选择性产业政策成效分析
——对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启示
薛 澜,蒋凌飞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纯电动乘用车选择性产业政策成效分析
——对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启示
薛 澜,蒋凌飞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近年来,学术界和政策界关于产业政策的成效利弊开展了激烈讨论,但对产业政策的讨论只有放到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与具体的制定和实施背景下才有参考意义。中国2009年以来采用选择性产业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就为这样的讨论提供了鲜活案例。国家产业政策制定者通过一系列选择性较强的产业政策来影响纯电动乘用车的技术选择和市场路径。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纯电动乘用车这个关键的细分技术领域中,国家政策支持的产业路径经过曲折过程才逐渐得到市场认可,同时其限制的路径也发展出了庞大规模。实证分析发现这个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①资金投入的加大并不能有效缩短技术性能由低到高的改进过程,在技术发展应用初期设置过高的性能指标,可能需要以牺牲新技术的经济性为代价来实现;②政策对部分市场主体的歧视,反而会为其创造出不受政策约束的“执行真空”,这虽然有助于包容不同于传统技术的经济特性,同时有可能也纵容了市场的无序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性产业政策;纯电动乘用车
1 引言
新能源汽车作为中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自2009年以来一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点关注和扶持对象。国家围绕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和推广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希望用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燃油汽车,解决汽车使用所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同时,也希望通过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中国汽车产业的振兴、在国际竞争中“弯道超车”[1]。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为中国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产业政策在发挥必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其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如何?怎样使产业政策的成效更为理想?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不但可以为改进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相关产业政策提出有益的建议,还将对目前国内关于产业政策的学术讨论做出贡献。
根据政策的作用范畴,可以将推动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政策是通用性产业政策,主要着眼于改进产业的框架性环境[2],可以适用于不同的产业领域,如反垄断政策,各类保障产业的生产、消费和交易过程中的安全、健康和环保等方面的政策;另一类政策是适用于特定产业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政府通过对具体的企业、产品、技术甚至客户市场进行直接的选择和干预,鼓励或限制特定产业路径的发展。
中国的纯电动乘用车产业政策以第二类政策为主。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关键分支,纯电动乘用车指的是“完全用电力驱动、9座以下的四轮载客机动车”,主要包含两种类型:一类完全按照常规燃油汽车标准设计和制造,被称为“常规电动车”;另一类因时速较低在部分指标方面不完全符合常规燃油汽车检验标准,被称为“低速电动车”。
中国纯电动乘用车产业政策的选择性,在生产主体、技术和市场等多个方面均有体现。中央政府不仅依据燃油车生产资质为不同企业设定差异化的准入门槛,而且优先和重点鼓励特定产品、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例如,国家按照传统燃油车的行驶速度为纯电动乘用车设定强制性标准;国家和地方政府按照电池容量和续航里程为车企提供补贴;“十城千辆”工程几乎只适用于公共服务领域等。简言之,国家鼓励常规电动车的发展,限制低速电动车的发展。
然而结果却颇令人感到意外。一方面,在由政府所鼓励的常规电动车路径上,尽管有许多企业较好地执行了政策,但经历了颇为漫长和曲折的过程才逐步得到市场的认可;另一方面,许多违背国家政策而生产低速电动车的企业得到了市场的青睐而蓬勃发展起来。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什么启示?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3],来梳理和分析相关政策实施的初衷、方式、结果和机制。所有与中国纯电动乘用车相关的产业政策均是本研究的关注对象,其中既包括为促进纯电动乘用车应用所提供的央地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优惠和差异化的交通管理措施,也包括为规范纯电动乘用车应用而实施的企业和产品准入、登记上牌和路权管理制度等。主要数据来源于与产业相关的会议论坛、档案资料、与业内人士的访谈等,访谈对象涵盖了汽车领域的专家学者、技术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等。
2 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依据与利弊
选择性产业政策是一种狭义的产业政策,最早由日本所倡导和实践,并且在中国广泛存在。以往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指政府要对产业进行扶持时,对要扶持的企业、产品和技术有强烈的选择性[4]。
本研究从两方面拓展了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外延。第一,这种选择性不仅体现在带有强烈的主动干预意义的扶持性政策中,还存在于旨在规范产业发展的管制性政策中;第二,选择性不仅体现供给侧的企业、产品和技术等方面,还体现在需求侧的消费者类型、区域等方面。
选择性产业政策因带有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的特征而备受争议,但在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应用中似乎又不可或缺。已有的创新理论从市场需求侧和技术供给侧两个方面,为产业政策的选择性提供了依据。
对市场选择的依据是新技术发展初期所面临的传统技术的“锁定效应”,即成本和性能竞争力差的新兴技术与成熟技术在市场上竞争时,前者可能面临成本居高不下和市场扩张困难的恶性循环[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培养一部分“领先用户”[6],并集中性地解决基础设施和其他互补性产品所带来的牵制,从而带动更大规模的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对领先用户的培育可以通过公共采购、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等多种方式来实现。提倡公共采购的研究者认为,在破碎的市场中,用于从事或购买新产品的信息严重缺乏,且存在较强的不对称性。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用户往往都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充分意识到市场将提供和能提供什么样的新产品或服务给他们,而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供应商也不了解客户未来有什么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和企业的互动和沟通存在较大的问题,零散的需求不足以被充分表达,企业难以理解其传递的信号并将其转化为创新。这同样是因为对创新及对相应的需求缺乏信任,同样也没有足够的技术来使用和利用创新。所有这些为供应者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公共采购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达到临界规模。这或者是通过单个采购的庞大规模实现的,或者是通过将多样化的公共机构的需求绑定实现的。这样的公共需求能够为制造商创造明确的激励、降低其市场风险和实现初步的规模经济和学习。公共采购还能够降低适应新产品的转换成本,这或者通过及时的、大规模使用新产品来实现,或者是通过示范来实现,后者指的是公共领域的使用向私人市场传递了一个信号,论证了新产品的功能性,并引起私人市场更早的关注。
除公共采购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来优先和重点地扶持一部分用户,从而新兴技术的发展应用提供利基市场,保护其在不成熟的阶段免于和已有技术体系的正面竞争[7]。在领先市场中,政策可以通过补贴新技术来降低成本,进而促进市场扩张和成本下降,由此打破传统技术的锁定效应。
对技术选择的依据是技术演化理论所强调的“锁定悖论”,即需求拉动型政策在破除传统技术的“锁定效应”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新兴产业的发展锁定于技术成熟度更高的“次优”技术路径中[8]。例如光伏产业中的晶硅技术因为技术成熟度比薄膜技术更高、产业化条件更成熟,因而在政策驱动需求增长时率先得到应用,然而从长远来看薄膜技术的发电成本相较于传统发电方式更有优势,这种“次优锁定”限制了光伏技术在更大范围的市场应用以及在常规的电力市场上难以摆脱对政策的依赖。这些结论带来两点政策启示:一是利用政策驱动新技术的市场需求要注意时机,不可操之过急;二是政策应对具备长远潜力的技术给予更多“关照”,促使政策优先拉动符合特定要求的新技术。
选择性产业政策理论上能够更好地促进新兴技术的应用、实现技术提升、改善传统技术问题等多重的政策目标。然而,这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以政府的选择和判断代替市场机制,其有效实施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理性、知识和信息完备的基础之上,但这在现实中可能是难以达到的高要求[9]。中国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具体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产业政策部门不仅要在某个产业领域进行决策,还要面对数十个、甚至数百个细分产业。要对如此繁多的产业的技术和市场的前景进行预判,并从中准确挑选出先进的技术、产品和工艺予以扶持,产业政策部门需要更加的谨慎[10]。
即使是针对某个细分的产业领域制定政策,新兴产业的不确定性也为决策带来了不可预知的挑战和风险。制定合理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必须对供给侧的生产成本、技术可行性以及市场侧的消费者偏好有完全的了解,而相关的知识只有在实际的市场过程中才能够认识学习。实际参与了竞争过程的市场主体对这些知识往往更为敏感,其发现和利用这些知识的过程也更为高效[11]。产业政策部门的有限理性和知识不完备的问题,可能会制约产业政策取得理想的成效。
3 2009年后中国纯电动乘用车产业政策及其效果:整车企业
3.1 基本政策描述
中国传统燃油汽车领域中,生产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受到国家产业部门的严格控制,有法定整车生产资格的企业被称为“整车企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体系沿用了传统汽车“严格把关准入”的管理思路,考虑到整车企业在传统汽车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生产经验,政策制定者期望依旧依托于这类企业来引入新兴技术振兴国家汽车工业。整车企业可以参照中国汽车分类管理办法,生产同类别的新能源汽车。也就是说,过去有燃油乘用车资质的企业才可以生产新能源乘用车。
政府不仅给整车企业生产纯电动乘用车提供许可,还通过扶持性的政策为其创造产业化条件,其中包括2009—2012年的“示范推广工程”和2013—2015年的“推广应用工程”,主要依靠对传统产品消费和使用较多的市场,来刺激纯电动乘用车的应用。国家一方面优先扶持传统市场,在“示范工程”阶段,政府优先对大中城市的公共服务领域提供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在传统市场上限制传统产品应用,国家不仅对公共服务领域新采购的新能源汽车比例提出“不低于30%”的硬性要求,还要求大型限行限购城市为新能源汽车开“绿灯”。
国家政策还针对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性能设定了标准。一方面对传统主流性能更好的产品给予了更大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直接限制性能较低的产品。续航里程方面,企业每销售一辆纯电动乘用车可获得不高于6万元的中央财政补贴,具体补贴数额根据产品的电池容量或续航里程确定,例如在“示范推广工程”中,产品被补贴的基本电量要求是15kWh,在此基础上电量每提高1kWh、每辆车的补贴增加3000元;“推广应用工程”中,国家改按续航里程补贴企业,产品被补贴的基本里程要求是80km,在此基础上划分出80~150km、150~250km及250km以上等三个层级,对应补贴数额分别为3.5万元、5万元和6万元。时速方面,国家沿用了在传统乘用车领域适用的路权管理和产品检测方式,例如纯电动乘用车与传统乘用车一样有高速公路路权,因而最高设计时速要在70km/h以上,要能够实施50km/h的正面和侧面碰撞试验以保障产品的使用安全。2012年和2015年,国家相继针对纯电动乘用车出台了续航里程和时速“双80”的产品准入标准和“双100”的补贴标准。
3.2 政策实施情况
国家引导和迫使整车企业在已有的政策条件约束下进行技术和市场的决策,促使其向传统燃油车看齐、提升其产品的时速和里程,并且以人均汽车保有量高的大中城市,尤其是限购城市为推广纯电动乘用车的关键市场。七年间,国家和地方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整车企业发展常规电动车。
巨额的财政补贴和中央摊派给地方的销量指标,在某种意义上成功驱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战略转型。整车企业在两轮气魄宏大的示范推广应用工程中都进行了较大的投入,从2012年开始已经有接近一半的整车企业开发纯电动乘用车车型,平均每年都有30款新的车型进入国家机动车公告。
在实际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围绕技术和市场的相关政策要求得到了严格的贯彻执行。技术性能方面,由整车企业所开发的纯电动乘用车车型的最高设计时速不断向燃油车靠近,整体上逐步提高至115km/h以上,电池容量多数在20kWh以上,续航里程基本都高于150km;市场定位方面,整车企业在第一阶段基本集中于出租车和省级公务用车两大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推广,在第二阶段则主要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等限购城市进行销售。
3.3 实际效果
尽管受扶持的整车企业严格执行政策要求、发展常规电动车,但市场推广情况在政策实施后的前四年十分不理想。在2013年前的示范推广阶段,国家提出的目标是“公共服务领域5万辆、私人领域10万辆”,实际上公共服务领域仅完成推广目标的60%,私人领域推广数量不足目标的10%。从推广车型来看,在实际完成的3万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中,有2万辆是以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和非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为代表的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总数不到1万辆,包括纯电动公交车、纯电动乘用车和纯电动专用车。整体而言,可谓“政策热,市场冷”。
在2013年开始的推广应用阶段,补贴范围的扩张和补贴力度的加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一阶段产业“起步难”的局面。2014年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开始高速增长,2015年中国甚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如果没有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的支持,很难想象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整车和零部件的技术和市场发展方面能够取得今日的成绩。然而,“骗补和违规谋补”、依赖补贴和限购政策的问题提醒着我们,新能源汽车成本过高、使用不便等问题,从长远看依旧是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潜在阻力。
4 2009年后中国纯电动乘用车产业政策及其效果:低速电动车企业
4.1 基本政策描述
在中国纯电动乘用车行业中,还有另一类生产纯电动乘用车、却没有整车生产资质的企业。这类企业多以生产低速电动车起家,本文将其称为“低速电动车企业”来和整车企业相区分。理论上而言,中央政府围绕新能源汽车所制定的准入和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和相关规则,既适用于整车企业,也适用于低速电动车企业。但实际上,后者因为不具备燃油车生产资质,面临了更高的、甚至是难以跨越的行政准入门槛。与整车企业通过“备案”获得同类型的新能源汽车资质不同,低速电动车企业要获得同样的资质,不仅面临了近乎苛刻的投资总额和生产规模要求,而且需要经过程序繁琐且通过概率极低的核准过程。
生产资质的缺失,使得低速电动车企业的产品即使达到国家标准,也无法进入国家补贴的目录。更重要的是,交通管理部门需要依据企业和产品的合法资质为其登记上牌,消费这类产品的用户才能够拥有合法的机动车路权。简言之,缺乏新能源乘用车的“整车资质”,也就意味着其产品不能被生产、销售和上路。
4.2 政策实施情况
国家对低速电动车企业的限制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这些企业通过两类渠道绕开了严格的核准过程。一类渠道是说服地方政府容许其发展。在一些本地没有整车企业的地区,当地的低速电动车企业借助国家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契机,向地方政府申请“边生产边申请资质”,成功获得了地方暂行管理办法的保护。另一类渠道是与整车企业合作“挂牌生产”。低速电动车企业借助整车企业的资质进入国家目录,但实际的开发生产过程几乎全部由前者来完成。第二种渠道不仅可以获得合法的路权,还能够得到国家和地方的双重补贴。
低速电动车企业不仅没有遵循国家准入规定,在技术性能的设计上也偏离了国家政策要求,甚至与其截然相反。一些企业虽然进入目录,但仅按照最基本的“双80”标准进行设计生产,实际上没法在高速上行驶;没进目录的企业生产的则是时速不足70km/h的低速电动车,多数不能达到常规汽车检验项目的时速要求,电池基本以能量密度较低的铅酸电池为主,里程在100km以内。
市场用户的选择与政策导向的差异也十分显著。低速电动车企业始终服务于私人用户,且主要满足对传统燃油车消费更少、使用强度更低的边缘市场的需求。起初,这类用户主要集中在乡镇地区和农村,以老年人为主;后来其市场范围逐步向城乡结合部和三四线城市扩张,用户也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仍以满足日常的短途代步类需求为主。
4.3 实际效果
在这条另辟蹊径的低速电动车路径中,国家产业政策没有得到执行,甚至是完全的违背,但低速电动车企业却成功在农村和小城市发展起来。低速电动车并没有因为没有政策补贴和合法“身份”的缺失而销声匿迹,反而呈现出逆势生长的态势,规模远超常规电动车。同样是起步于2009年,仅山东省的低速电动车累计销量已经达到80万辆,大约是全国常规电动车的6倍,骨干企业如时风、比德文在2015年销量均超过6万辆。浙江两家低速电动车企业在2014年前后借助“挂牌生产”分别进入国家目录后,也迅速得到市场认可,在“挂牌”电动车中取得了领先的销量表现。
5 分析及启示
5.1技术演进和组织学习的客观规律难以被高强度产业政策所改变
政策制定者按照传统技术的主流性能和应用市场来对新技术的发展应用路径进行选择性的扶持时,这条路径经过了较为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才逐步得到市场的认可。一定程度上,这正是纯电动乘用车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中“苛刻”的政策要求所造成的。业内不少人士认为,国家在纯电动乘用车的里程和时速等方面提出了过高的标准,导致企业不得不牺牲经济性来迎合国家要求;在市场的选择方面,大城市的用户、出租车和省级公务用车用户对里程的要求过高,按照当前的电池水平,企业在这些用户可接受的价格之下,难以生产出能够满足其需求的产品。
当然,传统主流性能和应用市场在新技术中并非不重要,政策制定者对这些要素的重视并非没有道理。从长期的趋势来看,随着新型储能介质的开发和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纯电动乘用车与传统燃油汽车的里程和时速差距将会逐渐缩减,有利于降低当下还普遍存在的“里程焦虑症”;纯电动乘用车对燃油汽车的替代也会逐渐成为常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初衷,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和市场对新技术的要求能否与其技术经济性的提升相匹配?当前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政策建立在一个隐含的假设之上,即资金投入对技术性能改善的边际效益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技术性能改善所需要的时间可以通过资金投入来压缩,希望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来大幅甚至无限地缩减该目标所实现的周期。
然而,技术性能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尤其对于新兴技术而言,从技术投入到技术产出的过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该过程所需要相关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企业的组织学习,需要通过用户的使用发现问题……这一切都需要耗费时间!这个过程不会随着政策和企业资金投入力度的加大而大幅缩减;该过程所带来的结果,也无法简单地按照传统技术的发展规律来理解和预测。
同时,在纯电动乘用车产业中,由政策所设定的性能指标和受政策扶持的用户的实际需求,诱导和迫使企业设计和生产里程和速度更高的产品,但是作为纯电动乘用车的关键零部件的电池性能的改善速度是有限的。为此造车的企业常苛责其电池供应商“拖后腿”,而后者则抱怨前者“不懂电池”和“片面地用机械制造的思维要求化学电源发展”,汽车界和电池界的相互抱怨被业内形象地称为“隔空喊话”。追根究底,这反映出国家为产业界设定了较高的性能指标后,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所追加的技术资金投入并不能足够有效地缩减电池技术的性能改善周期。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能力相对于2009年前确实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产业政策当然功不可没。然而从横向的比较来看,中国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补贴强度高达美国的9倍[12],但中国产业整体的研发投入力度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旧有很大的差距[13],因此很难说这些政策取得了理想的成绩。更为糟糕的是,为了更快地达到政策要求,许多企业不惜牺牲产品的经济性,而巨额的财政补贴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方式所带来的成本高昂的缺陷,促进了这种设计生产思路的扩散。具体而言,政策对传统的主流性能和主流市场的侧重,诱导了企业不计成本地增加电池数量,装载20~60kWh的电量,更快地实现了200~300km的续航能力。由此所带来的代价也十分明显,即使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双重财政补贴之下,这样设计生产的纯电动乘用车依旧比传统燃油车价格更加高昂。
因此,虽然对传统主流性能的要求看起来无可厚非,但核心问题在于指标设计过高,忽略了新技术由“粗糙”到成熟的学习过程。同样,将纯电动乘用车放在对里程、速度较高的传统主流市场中经受检验,所存在的问题也是类似的。技术性能由低到高的改善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当政策制定者尝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来压缩这个过程时,这些政策并不能足够有效地提升技术改善的速度,反而促使企业采用了技术门槛更低的方式——在车上装载过多的电池和电量——最终牺牲了纯电动乘用车的经济性。
5.2边缘市场与“政策执行真空”孕育了低速电动车的高速发展
国家在扶持整车企业的同时,对低速电动车企业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并非“一刀切”式的禁止,而是以一种歧视性的政策安排的形式存在。在行业准入和路权管理方面,这类企业因为缺乏生产资质无法登记上牌,用户购买其产品不具备在机动车上行驶的合法权利;在产业扶持方面,这些企业无法像整车企业一样获得大幅的财政补贴,无法进军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但这种带有歧视性又未完全禁止的政策安排,实质上为这类企业创造了一个新的细分市场,这就是城乡结合部、乡镇和农村等传统汽车没有普及的地域。这些地方由于路况较差,本来就无法高速行驶。同时,由于使用范围有限,对于续航里程要求不高。
此外,这些边缘市场的政策执行历来就是难题,形成了一个“政策执行真空”,国家针对整车企业制定的技术性能要求对这些企业无法形成约束。这样一个巨大的边缘市场对于低速电动车企业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们过去长期受到市场准入的限制,一直在城乡结合部、乡镇和农村等传统汽车没有普及的市场区域,为其提供农用车、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等产品,对这类边缘市场的需求特点更为熟悉和了解。国家纯电动乘用车政策对大中型城市的青睐和对低速电动车企业的歧视,进一步加强了这类企业立足于边缘市场、发展补充性产品的理念。低速电动车就是在边缘市场和“政策执行真空”双重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当然,这样生产出的产品难以被传统的机动车管理体系所包容。这类市场的道路条件较差、用户活动半径小、加油站少,本就不适合传统汽车的应用。企业没有资格获得国家补贴,只能完全按照市场需求来设计产品的时速和里程,由此制造出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过去传统汽车的设计理念和标准,具有准入资格的企业由于有现成的政策法规要遵守,要开发类似产品反而难度更大。可见,正是歧视性的政策安排所创造出的“执行真空”,包容了低速电动车由低到高的技术发展过程,有利于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
然而,“执行真空”对市场的有利作用也有其安全风险。在缺乏强制性的管理规范的情况下,低速电动车产业中良莠不齐的问题严重。除了部分企业严格遵照四大工艺生产外,还有许多工艺简单、产品粗制滥造的小作坊企业,后者以牺牲产品安全性为代价降低产品成本。在低速电动车的销售和使用中,部分经销商甚至以“无需驾照、牌照、上税”为卖点吸引客户,由于没有规范可依,用户违反交通规则的现象也十分常见。
这些问题并非因为地方政府在刻意纵容产业的无序发展。目前为低速电动车放行的14个省份,都出台了地方暂行管理办法,通过发放特殊牌照的方式对低速电动车进行管理。然而,由于牌照管理属于国家事权,在国家不允许的情况下,地方交管部门无法强制用户给低速电动车上牌,这使得与低速电动车相适应的产品标准、市场准入、路权管理、车辆注册登记、驾驶证和保险要求也都无法执行。
5.3 政策启示
在技术日新月异且不确定性极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促进产业的发展?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选择性产业政策虽然在理论上有助于破除传统技术的锁定效应和次级技术路径的锁定,但市场的复杂多变和政府的有限理性可能会延缓或制约政策取得预期的成效。在中国纯电动乘用车产业中,常规电动车和低速电动车均不可或缺,它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本研究认可产业政策对于整车和零部件的技术和市场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强调政府对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使用应抱以更为谨慎的态度,这对于常规电动车和低速电动车的长远、健康的发展均有意义。基于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分析,本研究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启示:
第一,市场的复杂和技术变革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府无法替代企业做出有效的技术决策。在多个维度的技术属性中,对某一维度的侧重不可避免地以牺牲其他维度的属性为代价。对于不确定性极高的新技术而言,重视哪些维度的属性更符合市场要求,本来就难以事先预测。即便我们认同某些属性对于新技术的长远应用不可或缺,但政府也难以制定出与技术改善速度相匹配的指标水平。更何况,市场需求本是多元的,对于市场而言究竟多高的指标水平合适,可能本就没有唯一的答案。在主导设计不清晰的新兴产业初期,政府应当尽可能少地采用具体的技术标准[14],包容多元化的技术属性组合相互竞争,等待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组合脱颖而出。
第二,新兴产业的潜在市场只有在市场上打拼的企业最清楚,政府越俎代庖可能会妨碍市场的开发和产业的发展。通过动用财政和行政资源,政府固然有能力去引导和强迫一些用户成为领先用户,但并非所有领先用户都能最终转化为大规模市场[15]。事实上,许多新兴产业的成长在初期都需要借助于过去不存在的新兴市场,从而避免与传统产业的正面竞争。然而,新兴市场的规模相对较小、用户偏好信息稀缺,寻找和利用这类市场所需要的学习成本相对更高,寄希望于政策制定者来发现这样的新兴市场是不切实际的。企业尤其是新进入者,对这类市场的敏感程度往往更高。在新兴产业中,政府应当在准入方面降低对新企业的限制,甚至通过反垄断等方式对其予以照顾,这将有利于对新兴市场的发现和利用。
第三,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复杂性,相关的产业政策制定应该更多地遵循适应性治理的思路,允许相关政策根据情况变化进行调整。这不仅有助于促进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还有助于合理地规范产业秩序,降低其应用风险。具体而言,当现行政策体系难以适应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时,政府可以先在政策调整积极性较高的地区,容许当地企业、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不完全受现行政策体系约束,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的治理方式,再逐步将这种适应性的治理方式向更大范围推广。
[1]赵福全,刘宗巍,郝瀚,等.中国实现汽车强国的战略分析和实施路径[J].中国科技论坛,2016(8):45-51.
[2]POLT W,RAMMER C,SCHARTINGER D,et al.Benchmarking industry-science relations in Europe-the role of framework conditions[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2001,28(4):247-258.
[3]EISENHARDT K M.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14(4):532-550.
[4]江飞涛,李晓萍.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J].中国工业经济,2010.
[5]SANDéN B A.The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e of PV subsidies[J].Solar energy,2005,78(2):137-146.
[6]VON HIPPEL E.Lead users:a source of novel product concepts[J].Management science,1986,32(7):791-805.
[7]FABER A,FRENKEN K.Model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Towards an evolutionary environmental economic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09,76(4):462-470.
[8]NEMET G F.Demand-pull,technology-push,and government-led incentives for non-incremental technical change[J].Research policy,2009,38(5):700-709.
[9]王廷惠.微观规制理论研究:基于对正统理论的批判和将市场作为一个过程的理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0]李平,江飞涛,王宏伟.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评价与政策取向探讨[J].宏观经济研究,2010(10):3-12.
[11]LAVOIE D.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12]补贴额度是美国的9倍:新能源车企却懒于搞研发[OL].21财经搜索,2016-09-29.http://news.21so.com/2016/qqb21news_929/39960.html.
[13]李华晶,郑娟,和雅娴.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J].中国科技论坛,2017(1):76-81.
[14]LEE J,VELOSO F M,HOUNSHELL D A.Linking induced technological change,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Evidence from patenting in the US auto industry[J].Research policy,2011,40(9):1240-1252.
[15]ASCHHOFF B,SOFKA W.Innovation on demand—Can public procurement drive market success of innovations?[J].Research policy,2009,38(8):1235-1247.
(责任编辑 刘传忠)
TheEffectandImplicationofChineseIndustrialPoliciesonthePureElectricPassengerVehicle
Xue Lan,Jiang Lingfe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Recently,some heated debates are held among academic experts and policy maker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ndustrial policy.However,only if the discussions are put in specific economic-social backgrounds and the concrete contexts of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s,can they bring us implications.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used selective industrial policies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since 2009,which is a fresh case for these kinds of policy debates.Using a serie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with strong selectivity,the national policy makers has shaped the technological choices and market path.This study reflects that in the domain of pure passenger electric vehicle,which is a key subdivision of the new-energy vehicle,the path supported by the policies did not get recognized by the market until it went through a tortuous process,while the path constrained by governments unexpectedly expanded,which were caused by two reasons.Firstly,more capital could not shorten the period of technology improvement effectively.The performance standard set by the governments was too high for the whole industry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which might induce or force firms to sacrifice the economy of the product to satisfy the request from the governments.Secondly,the discrimination caused by policies created an implementation void without constraints of the governments,which accepted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on one hand and resulted in the disorder of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Strategic new emerging industry;Selective industrial policy;Pure electric passenger vehicle
国家发改委咨询研究课题 :新时期我国国家竞争战略研究。
2017-01-24
薛澜(1959-),男,北京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科技创新与教育政策、危机管理、全球治理等。
F424.3
A
- 中国科技论坛的其它文章
- 思维改变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
- 司法保护对专利权经济价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