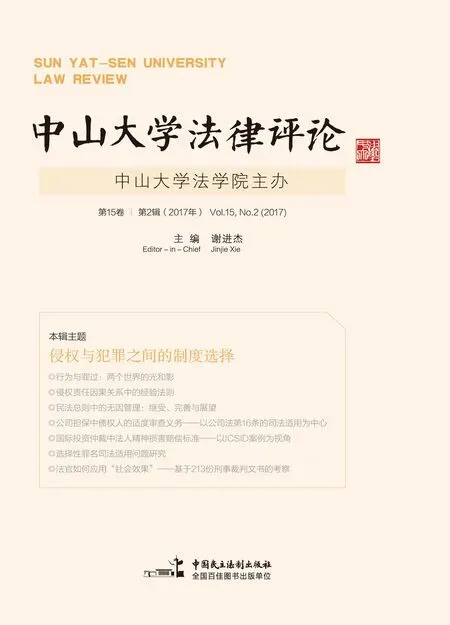行为与罪过:两个世界的光和影
李瑞杰
【提 要】 既往的刑法学理与审判实践,在运用规范逻辑考察行为成立与否与行为个数认定的同时,还保留着简单套用生活意义上相关概念与标准的残余,从而在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光与影中迷失了方向。既然刑法学是规范之学,那么应当树立规范意识,区分事实与规范,遵循刑法体系的内在条理,以行为刑法理论与罪责刑法理论为基点,厘定行为的概念内涵、行为个数的判断标准,检讨概括故意的概念、犯罪参与的基本原理,反思想象竞合犯与牵连犯的刑罚处断、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区分标准。
引言
刑法体系明显存在于两个维度,一个是外在体系,即对刑法规范和构成要件所进行的概念上的梳理、解释和阐明,另一个是内在体系,即贯通和支配整个刑法的精神理念、价值旨归、基本原则各自的以及它们之间的实质联系。彼此之间不相抵牾,应当是刑法体系的固有品格,对此,德国刑法学鼻祖费尔巴哈即认为,“任何混乱以及不协调都是对理性的侮辱,理性的最高使命是协调与统一”。〔1〕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刑法的体系构成》,黄笑岩译,载梁根林、[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主编《刑法体系与客观归责: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立足于规范逻辑的刑法立场,观察行为成立与否与行为个数,是科学适用刑法、准确认定犯罪的应有之义。遗憾的是,既往的刑法学理与审判实践,在推进刑法体系规范化的同时,还保留着简单套用生活意义上的行为概念与行为个数认定的标准的残余,并由此导致了犯罪论体系诸多问题的混乱不堪。
对此种现象,德国法学家卡尔·拉伦茨指出,“要选择何种要素以定义抽象概念,其主要取决于该学术形成概念时所拟追求的目的。因此,描述某类客体的法学概念,与其他学科乃至日常生活用语中的相应概念所指涉者,未必相同”〔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18页。。英国学者塞尔登也表示,“律法的字面意义与精神意义之间存在着人人皆知的区别”,这使人认识到,法律中的概念与生活中的概念不能简单置换。〔2〕参见[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6页。
在这个意义上,深入分析行为的结构与个数标准,使之区别于生活意义上的相关概念范畴,对于准确认定犯罪,建构犯罪论体系,大有裨益。有鉴于此,本文秉此立场和命意,兼采描述、解释与建构的三种进路,聚焦于行为理论与罪责理论,审视当下刑法体系中较为突出的“异质因素”,不时与各种观念见解对话交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以求实现理论与命意的审慎周密,并借此希望我们在耕耘学坛、沟通东西中,多一些反思性检讨的研究、多一些反躬自省的学者。
一、重新架构行为理论
(一)重视行为理论的原因
“于刑法理论史上,类似行为概念般,其内容之如此不明确、使命之如此暧昧、争论之如此尖锐,却迄未出现一令多数人共通接受见解之现象,恐前所未见。”〔3〕陈友锋:《刑法上行为概念与行为之探索》,新北:辅仁大学法律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32页。行为概念不仅是犯罪论,而且是整个刑法学体系的基石,有关犯罪与刑罚的一切问题都应从行为理论来解释。“无行为即无犯罪”,现代刑法是行为刑法,其只以行为作为刑法的判断对象——而不是行为以外的其他因素。行为本身不会成为犯罪,必须经由一定的评价标准才能确定其为犯罪。一方面,行为作为界定刑法判断犯罪的基础。既然犯罪论体系的核心是犯罪,判断犯罪的规范对象的是人的行为,行为必须该当于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时,使能成立犯罪,由此足可看出行为在形成犯罪概念的基础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确认刑法规范的对象与属性是行为与行为规范。“行为刑法原则是刑法作为适用对象的认定原则。任何法律规定,都有其明确的规范对象,刑法更是如此。”〔1〕柯耀程:《通识刑法——基础入门十六讲》,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4页。
在德国学者麦兹格看来,行为理论在刑法体系上具有二重意义。“一为分类之意义,认为行为为刑法上一切现象之最高统一体,非行为,即非犯罪。故行为成为刑法上一切现象之最外围,举凡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之单纯反射运动或意思、思想,自始即置于犯罪概念之外。一为界限之意义,认为行为为一切犯罪要素之形容词或附加语所修饰之名词。故行为乃为刑法评价以前之事实要素,惟非单纯之事实概念,乃为价值关系之概念。”〔2〕甘添贵:《刑法总论讲义》,台北: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49页;亦可参见陈子平《刑法总论》(2008年增修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4页。
这些都是经典之论,但是笔者以为尚不圆满,更为根本的是,“行为者,乃指人类内部意思活动,而表现于身体上之一切动作,并引起外界之变化,称之为行为”〔3〕张灏:《中国刑法理论及实用》,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89页。。能够引起一定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发生变化的活动,是行为的重要属性。〔4〕参见陈忠林《中、德、日现行犯罪论体系的重构》,载梁根林主编《犯罪论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页。因此,基于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法律的评价对象只限于行为。“每一个犯罪行为,无论它表现的作为或不作为,永远是侵犯一定的客体的行为。不侵犯任何东西的犯罪行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5〕[苏联]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王作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101页。任何一个行为必须侵害了法益,才可能认定为犯罪,也才可能对其科以刑罚,而侵害必须通过外界状态的改变来实现,思想活动也因此被排除在刑法的评价体系之外。“我只是由于表现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17页。这也就是说,坚守行为刑法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从传统自由主义的观点,惩罚一个人,是因为其具体侵害了某些人的法益,而不是因为其可能破坏某种抽象的机制、某些想象出来的利益。〔1〕参见林东茂《危险犯与经济刑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第712页。
与此相关,上述文字还涉及行为与结果的关系。可惜的是,我国刑法学界晚近以来浸淫其中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以及有些学者为了合理解释刑事不法的类型,苦心孤诣的提出的三种并列的模式——结果导向的不法模式、行为导向的不法模式(如未遂犯)、主观导向的不法模式(如过失犯)〔2〕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8页。,都存在一些迷误。
诚然,行为与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区分,但是有行为必然有结果,行为必然会改变外在存在的人或物的状态,这是结构主义的必然推论。〔3〕结构关系区别于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平时所说的因果关系,本身存在概念混乱。因为刑法中研究因果关系,其实是在确认这个“结果”是不是某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说某行为造成的“结果”要不要让某人负责。日本学者高桥则夫即指出,在“犯罪是行为”这一场合的行为里包含着狭义的行为和广义的行为,必须注意后者也包含着结果的概念。如果不考虑结果,就不能理解行为的社会意义。〔4〕参见[日]高桥则夫《规范论和刑法解释论》,戴波、李世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而且,行为的性质是由其结果体现出来的,如果“杀人”的行为绝对不可能导致一个人死亡,那么行为也不是杀人的行为。简言之,杀人的行为必然有致人死亡的可能性,行为与结果的无价值性要么一起被肯定,要么一起被否定。结合刑法机能性思考,人力以外事物造成的“社会危害”或“法益侵害”,也不能称其为“社会危害”或“法益侵害”。不法必然是与行为人相关联的人的行为的不法,刑法之所以只可能将人所能够控制的范围内的事项归责于他,正是考虑了避免可能性,惩罚他能够实现预防犯罪。并且,前述不法模式论述,除了重复既往的错误外,还有一个更为明显的破绽——不法的标准只能有一个,多重标准划分概念的外延时难免混乱。〔5〕例如,过失行为中也存在未遂的情况,我们不能以实害结果出现有无认定有无过失,事实是先有过失行为后有实害结果,只是说由于过失犯的罪责较小,不处罚未遂犯。
(二)行为概念的重新理解
从历史上看,因果行为论,无法说明不作为犯,因为不作为时常没有身体动作,尤其是无法说明无认识过失,例如忘却犯,忘却犯并非基于意思而为身体动静,欠缺有意性。目的行为论,认为行为乃人类有目的性的活动,亦即是人为实现其所预先设定的目的所谓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动作,但其对于过失犯及不作为犯也无法论证,行为人并未预见行为所发生的结果;不作为犯无法经由目的意识而支配因果流程,也欠缺目的性。人格行为论,人格是难于把握的概念,如果依此概念来解释行为,很难掌握具体的行为概念;倘若认为将反规范的人格态度加以现实化的表现就是行为的话,那么杀人的犯意流露就是杀人行为了;“主体性”为哲学用语,“行为”则为事实的基础概念,不仅不明确,而且由于其具有多种意义,反而将刑法上的主体概念予以混淆。社会行为论,针对过失不作为犯等情形,虽可以克服目的行为论的缺陷,统一的说明行为的概念,但是舍弃行为实质内容,忽视行为要素的主观面向,也是一大缺陷。是否具有“社会重要性”,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标准;将“社会重要性”解释为具备刑法上可归责的判断意义者,会造成循环论证的情形。一个人的态度必须经过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后,才能清楚知悉是否具有刑法上可归责的判断意义。〔1〕参见余振华《刑法总论》(修订二版),台北:三民书局,2013年,第118页以下。
既存的行为理论异常繁复,花样转换、目不暇接。在异彩纷呈的观点之中,笔者倾向于新进的控制行为说。“根据控制行为说,一般意义上的行为是指主体控制或应该控制的客观条件作用于一定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过程。它是人类所特有的,是有理智的、有责任的人的活动”〔2〕陈忠林、徐文转:《犯罪客观要件中“行为”的实质及认定》,《现代法学》2013年第5期,第114页。。但是,笔者进行了小小的修正,行为是指主体控制或可以控制的某种状态。根据这一定义,首先,解决了“有意性”问题,因为过失行为及原因自由行为很难说是有意为之的;其次,解决了“不作为”问题,因为不作为犯缺乏刑法意义上的身体的动静;最后,将“应该”置换成“可以”更显中立的立场,淡化规范的意义。〔3〕在其后与陈忠林老师的交流中,他认为笔者的修改不妥,笔者以为,“可以”是事实的描述,“应该”是价值的描述,在行为人“可以”之后才谈得上“应不应该”的问题,既然行为概念是中性的,就不应含有价值判断,“能力不济,谈何义务”?只是说,犯罪是主体不应控制而予以控制(作为犯)或应该控制而不控制(不作为犯)的客观条件作用于一定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过程。
犯罪是行为,对犯罪成立条件的分析实际上是对一种特殊行为成立条件的分析。正确的行为概念是建立正确的犯罪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是整个犯罪论体系的出发点。作为现行犯罪理论的基础的行为概念都有错误,必然导致整个体系的错误。〔1〕参见陈忠林《中、德、日现行犯罪论体系的重构》,载梁根林主编《犯罪论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0页。“危害行为实际上是个综合性的概念,将实施行为的主体(人)、行为主体的主观意识、行为的自然和社会性质都概括进来,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犯罪构成的前提性因素。而这些因素也只有与危害行为相结合,才能与犯罪发生联系,具备刑法上的意义。”〔2〕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2页。
犯罪是主体控制或者应该控制的客观要件作用于一定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的过程。反过来说,犯罪是在行为人可以控制或者可以不控制之下的某种状态的改变。行为是主体运用自己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结果,也是行为人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表现形式。行为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就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控制或者应该控制的标准,具体到犯罪行为过程中,就是刑事责任能力,因此,行为应当是主体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进行的活动,是主体的存在和表现形式。〔3〕参见陈忠林《刑法散得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41页。
笔者以为,我国行为理论乃至大陆刑法理论存在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认为行为是人的单纯的身体动静,脱离主体与对象去观察行为,这不能说明构成要素与“犯罪是行为”这一格言的关系;二是认为行为仅仅止于行为人本身,将行为局促于行为人的外部表现,割裂了主观方面,无法确定行为个数、起点与终点。从而,行为论的错误结论蔓延到其他刑法理论,造成了当下犯罪理论中的不少问题。
二、行为个数的规范化诠释
(一)个数标准应当规范化
刑法学所解决的是“已知”的犯罪事实在刑法上如何评价的问题。〔4〕参见熊秋红《程序法上的犯罪定义及相关问题》,《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57页。在现实生活中犯罪总是具体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事实,认定犯罪,就是把某一种社会事实用法律来评价为犯罪,是一个从社会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的过程。〔1〕参见陈兴良《走向规范的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90页。一旦在刑法学上确立了一个相对科学的“行为”范畴,毫无疑问就开辟了通往犯罪论体系化的坦途。当刑法学将不作为包容进行为概念的时候,我们就建立起了有别于一般生活意义上的行为概念。过去,我们在刑法学理上提出了“行为”概念,但是我们忘记了“行为”在法律上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显而易见,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具有刑法意义。因此,需要对一般意义上的“行为”的概念进行层层分类,以确定哪些行为能够产生法律效果。
既然存在论上的行为,不必然等同于规范论上行为,所以,即使是存在论上的一个行为,未必不能作多个评价;即使是存在论上的数个行为,未必不能作一个评价。〔2〕参见庄劲《想象的数罪还是实质的数罪——论想象竞合犯应当数罪并罚》,《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第109页。例如,为杀死一个人,砍某人一百刀的现象应当作为一个犯罪行为来处理。又如,一个扳道工,在应该扳道的时候持刀去杀人了,不扳道是不作为,杀人是作为,既然不作为是行为,作为也是行为,那么就应该有两个行为,而不是一个行为。〔3〕这种情形要与某些学者那里的“一个行为从一个角度来看是作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不作为”相区分开来,因为这位学者无视了我国刑法中故意犯罪的概念。对于故意犯罪,我国刑法要求的是其对于结果的危害(而不是行为的危害),以他所说的闯红灯撞人的事例来说,应当是作为。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遗憾的是,我国有的学者居然认为,刑法中的行为既是一种事实判断,也是一种价值判断。〔4〕参见熊选国《刑法中行为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第26页。有人就说,“甲开一枪击中被害人心脏造成死亡的,无疑只是一个行为。但是,乙开三枪才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是一个行为还是三个行为?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行为的数量既可能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判断,也可能根据构成要件判断”〔5〕张明楷:《罪数论与竞合论探究》,《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7页。。并且,该学者还表示,“用数十刀捅死一个人,可以成为增加责任刑的情节,但这并不是因为手段残忍或者手段具有重大的反伦理性,或者手段具有行为无价值,而是因为用数十刀捅死一个人时,同时产生了数十个伤害结果”。〔6〕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张明楷《论影响责任刑的情节》,《清华法学》2015年第2期,第8页。显然,这些说法明显牵强,究其根本,这是论者一方面为了一如既往地维护结果无价值,反对将行为方式作为衡量法益侵害严重程度的标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行为方式是犯罪社会危害之高低的一个要素的逻辑怪胎。
诚然,就德国刑法理论和判例而言,竞合论中所称的行为单数实际上包括一般观念的多数与构成要件的单数〔1〕参见张明楷《罪数论与竞合论探究》,《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第117页。,即如果不同的行为部分是基于同一的意志决定,且时间和空间又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它被一个与之无关的观察者认为是一个行为,那么,一个事件过程表面上可分离的数个组成部分应当视为一个单一的行为。〔2〕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l年,第862页。
但是,学术研究不宜盲从,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只能有一个,如果存在多个彼此相冲突的标准的话,最后可能愈发混乱。目前行为个数的判断中,将生活世界的标准不加深思的植入刑法体系,变成体系中的异质因素,造成体系紊乱。刑法学人必须要知道我们从行为论的研究中要得到什么,“同一个术语或同一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语境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3〕[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虽然刑法学也在使用“行为”这一概念,但是我们的“行为”与一般的“行为”有共性也有特性,不可以简单套用生活意义上行为个数的判断标准。
如欲圆满解答这一难题,必须进一步探究刑法规范意义上的行为个数的认定标准。结合规范论的观点至少包含两个特色:作为判断的标准包含评价的要素,作为评价的标准是从特定的目的引申出来的。〔4〕参见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行为个数的认定标准,本文以为,从主观方面看,存在一罪责则为一犯罪行为,存在数罪责则为数犯罪行为;从客观方面看,侵害一法益则为一犯罪行为,侵害数法益则为数犯罪行为。详言之,日本学者指出,“行为——刑法上的行为——必须是意志的客观化、行为化和实现”〔5〕[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2页。。我国学者认为,“刑法中的行为不仅系客观的存在也系主观的存在”〔6〕熊选国:《刑法中行为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第26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行为理解为包含主观意志内容及其客观外部表现的统一体。既然犯罪是行为,犯罪的成立要求主客观要素,那么行为的成立也必然要求主客观要素,如果成立数个犯罪,就应当是数个行为,有着数个主观要素,也有着数个客观要素。值得说明的是,犯罪行为是主客观的统一,因此,无论是运用主观要素的个数还是运用客观要素的个数去认定犯罪行为的个数,不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犯罪客体重合性说,法益侵害的个数或者说是罪责的个数,本质上都是一样的。〔1〕参见庄劲《犯罪客体重合性罪数标准的倡导》,《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2期,第27页以下。
(二)行为个数的主观标准
“行为是主观意志的外在表现,是主观在客观上的转化(将主观转化为客观),换言之,主观和客观在此已结合在一起。”〔2〕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79页。姜伟先生认为,“我国刑法学者对犯罪构成理论的认识,似乎过于强调客观方面,事实上罪过心理才是犯罪构成的核心”〔3〕姜伟:《罪过形式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7—48页。值得说明的是,罪过,这一刑法术语源自苏联刑法理论,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大陆法系是罪责或责任,海洋法系是犯意,因此,本文对于罪过与罪责或责任等语词未加区分,换言之,笔者认为罪过与罪责或责任具有相同的概念内涵与体系定位。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第3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2页。。陈忠林先生也表示,犯罪行为之所以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不仅是因为其在客观上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价值,更是由于这种对刑法所保护的价值的侵害是在一定意志状态实现的。〔4〕参见陈忠林《刑法的界限——刑法第1~12条的理解、适用与立法完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68页。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作为产生罪过心理的载体的行为人必须达到相应的刑事责任年龄、具备一定的精神智力状态,这是产生罪过心理的前提;罪过心理决定着犯罪客体的性质,在具体的犯罪中,其犯罪客体是行为人的罪过心理所指向的那种法益,而不是纯粹的客观上被侵害的法益;罪过心理支配着客观行为,没有意志因素也就没有罪过,也就没有客观行为,罪过心理决定了客观方面的性质。其他构成要件从属于罪过心理,并以罪过心理作为存在根据;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差别,集中反映在罪过心理的不同上;罪过心理全面反映了犯罪的基本特征。〔5〕参见姜伟《罪过形式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页以下。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是行为人在认识自己行为性质的基础上,用这种认识来控制自己行为性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犯罪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具体化为具备一定内容的心理状况——行为人对于自己行为性质的认识状况和控制状况。在实施具体行为时,由于行为人运用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状况有所差异,体现在犯罪行为中的心理状况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故意和过失,即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1〕参见陈忠林《刑法散得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56页。我国有学者认为,将主观罪过视为犯罪构成的核心,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的观点,是主观主义。(参见周光权《“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之理解——兼与刘明祥教授商榷》,《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87页。)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分野,在于是否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或者说,犯罪的成立是不是由于彰显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如果认为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并由此建构犯罪论体系,那就是客观主义的犯罪论体系。
于域外而言,在目的行为论之后,犯罪,并非唯恶意莫属,实际上是行为所实现的恶意,所以,客观构成要件作为意志见之于客观的外在行为,实际上也是“客观的行为情状”,亦即是说,客观不法要素既为意志见于客观之物,客观不法要素之客观,并非行为人主体陌生之物,而是意志通过构成要件以客观表现于外的东西。所谓的客观构成要件,既然是意志的客观化的表现,就不可能是完全剔除主体精神要素的纯粹客观的外在物,必须在整体中予以考察。〔2〕参见王安异《穿越价值哲学——威尔策尔之人本刑法思想研究》,《政大法学评论》2009年第108期,第34页。在阶层犯罪论体系中,如果行为人具备了罪责,就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同样的,在我国,如果行为人具备了罪过,就应当受到刑罚处罚。
德国法儒耶林曾说,“使人负担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3〕转引自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具有主观罪过,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不存在主观罪过,就无须承担刑事责任。”〔4〕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1页。在我国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中,行为是否是在与刑法所保护价值相对立的意志状态下支配实施的,行为中是否包含与刑法所保护价值相对立的意志因素,包含何种与刑法所保护价值相对立的意志因素,以及这种意志因素在现实中的实现程度,决定一个行为是否成立犯罪、成立何种犯罪、成立何种形态的犯罪等说明犯罪严重程度的本质因素。〔5〕参见陈忠林《刑法的界限——刑法第1~12条的理解、适用与立法完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68页。主观罪过是犯罪构成的核心,主观要件代表犯罪行为的本质,犯罪主观要件是犯罪构成要件的集中体现,是唯一和刑事责任有必然联系的构成要件。换言之,犯罪行为中包含的主观要件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1〕参见陈忠林《刑法散得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以下。
罪责具有相反相成的价值功能,在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基础上为国家行使刑罚权确定合法性依据。罪责原则是刑法文化的核心,能正视人类自由与责任,能正视人类尊严,基于这个理由,不会有比罪责刑法更符合人道及自由的刑法。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刑罚是基于罪责而正当化的,行为人具备罪责,刑罚即可以施加于他。〔2〕参见[德]Ulrich Schroth《刑法总论:导论》,王效文译,载[德]Neumann/Hassemer/Schroth主编《自我负责人格之法律——Arthur Kaufmann的法律哲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300页。“如果科处刑罚的目的是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那么只有在受到禁止的事实是行为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或者至少是他通过合理审慎能够避免的情形下,才可能实现这种预期的激励效果:意图通过刑罚威胁使相对人排除不在其控制范围内的行为,这是没有意义的。”〔3〕[意]艾米利奥·多尔契尼:《意大利法律制度中犯罪的概念及其体系化》,吴沈括译,载赵秉志主编:《走向科学的刑事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99页。
一个罪责支配下的身体一系列举止,应当被认定为一个犯罪行为,负一个刑事责任,反之亦然。可惜的是,通说在因果关系错误的处理中,又背离了这一原理。详言之,在我国,罪责的成立采取了因果关系认识必要说,以犯罪故意为例,明知的范围涵盖了“会发生”,这就要求故意犯罪中行为人必须明知作为行为手段与行为对象间的关系而存在的因果关系。〔4〕一般认为,只有在结果犯的场合才存在因果关系认定的问题,不过,本文在使用该词时也包含了行为犯的场合,当然,此时将“因果关系”称为“发展进程”或“行为进程”,可能更好,所以本文交替使用这两个语词。这种“明知”,也就是对自己所应该控制的行为是如何作用于犯罪对象存在状态的过程的认识(需要认识到因果关系)。考虑到刑法上因果关系中的结果。所以,因果关系认识不要说及因果关系错误无用论并不妥当。〔5〕参见柏浪涛《狭义的因果错误与故意归责的实现》,《法学》2016年第3期。通说中的概括故意,或者计划理论、事前计划理论学说、故意危险理论等,违反了故意与行为同在的原则,混淆了计划实现与故意归责,忽视了故意行为危险与过失行为危险的差别。〔6〕参见柏浪涛《结果的推迟发生与既遂结论的质疑》,《法学家》2016年第1期。
我国不少刑法学者,一方面认为,在图谋枪杀仇人的预备行为中,由于揩拭枪支不慎击中仇人的行为不是故意杀人行为,另一方面又认为,嘴中默念杀死仇人的行为人具备了犯罪故意。不少学者,在论述客观归属理论中雷雨击人案时,认为“虽然杀人的故意可以得到承认,但是由于没有未被允许的危险发生,因而其结果不能为客观归属”〔1〕[韩]李在祥:《韩国刑法学总论》,[韩]韩相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其实,这位学者还犯了一个错误,不是一个人想着杀人,就具备了犯罪故意,其举动就可以评价为故意杀人之行为,否则迷信犯都具备了犯罪故意。。
构成要件性故意要求故意存在于行为时即实现构成要件的时候,因此,虽然行为人在行为之前具有实现意思但行为时未认识到的事前故意,不属于犯罪故意。在构成要件性结果发生之后才对事实有认识的事后故意也在刑法上不具有任何意义。〔2〕参见[韩]李在祥《韩国刑法学总论》,[韩]韩相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0—141页;[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1—192页。所以,甲决意打猎时枪杀妻子,但是在打猎前一晚上因擦拭枪支而走火致使妻子死亡,又如,甲自以为杀死了乙,在丢弃“尸体”于水中才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场合,都不具备犯罪故意。
与此相关,在打击错误的场合,具体符合说主张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法定符合说主张犯罪既遂。后者认为,前者难以做到罪刑均衡。〔3〕参见张明楷《论具体的方法错误》,《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法定符合说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想象竞合犯的一般情况中,其可能承认存在故意A+过失B的场合,但是如果未击中A,对B却可能成立故意犯罪。正是基于此,张先生指出,这种场合,都成立故意犯罪,进而指出,“倘若在量刑实践上对于故意杀害二人以上的,判处死刑,那么,对于基于方法错误而导致二人以上死亡的想象竞合犯,则不宜判处死刑”。[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52页。]这种观点就更值得商榷了。当然,具体符合说也有不少的问题,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暂不展开。对此,前者解释道,“因为,按照我国《刑法》第23条第2款的规定,对未遂犯只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不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未遂犯处与既遂犯同样的刑罚。这样,也就不会出现对犯罪分子处刑过轻的不合理现象”〔4〕刘明祥:《刑法中错误论》,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但这种说法明显牵强,因为如后者所述,这种情况我们应当数罪并罚,而不是在“可以”两个字上下功夫。
(三)行为个数的客观标准
结合前文所述行为与结果的关系,不难看出一个行为只会产生一个结果,行为的性质取决于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在普遍承认“犯罪是行为”这一格言的同时,又将结果纳入犯罪的构成要素之中——这反映为犯罪客体与违法性。基于这一原因,行为个数的客观标准是行为所侵害法益的个数。
“刑法的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国民自由。对任何一个案件的不法内容,只有既充分评价又不重复评价,才能既保护法益又保障国民自由”〔1〕张明楷:《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4页。。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荣坚认为,“从刑法保护法益的基本观念出发,在一行为的情况下,作为判断是否评价过多或评价不足的对象,应该是法益”〔2〕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5页。。“双重评价之禁止,所要禁止的是一行为侵害一法益而触犯数罪名的情形。除此以外,行为侵害数法益的情况,不管是一行为或数行为,不禁止双重评价。”〔3〕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5页。庄劲先生也认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要确定行为的可罚性的大小,关键在于确定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又集中体现在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上。因此,犯罪行为个数的判断,应当观察行为所实现的多个犯罪构成在犯罪客体上的关系,判断标准应当是法益的个数。〔4〕参见庄劲《犯罪客体重合性罪数标准的倡导》,《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2期,第27页以下。申言之,行为所侵害的法益,能够被一个构成要件所包容,没有超过一个罪名所保护法益的范围,就没有成立数个犯罪行为的余地。〔5〕参见王彦强《犯罪竞合中的法益同一性判断》,《法学家》2016年第2期。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在这里所谓的客观,是行为人主观已经认识到的客观,是已为主观所反映的客观。意思的内容,不仅不应自行为概念中分离,而且,还是行为概念的重要构成要素。所以,在故意杀人中,行为人杀一个人不见得就比杀两个人的社会危害更重,所应负刑事责任更重。因为,行为人杀两个人可能是在对方寻衅滋事中临时慌乱之中故意杀害的,而杀一个人是蓄谋已久、手段极其残忍的呢?其实,不论行为的社会危害有多大,刑法只能要求行为人在自己应当承受的范围内负担刑事责任。如果非得说行为客观危害的程度是量刑情节,那也是经过主观罪责这个筛子筛选之后的客观危害,或者说有些客观危害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客观危害。犯罪的客观危害是犯罪的主观罪责的外化与载体,犯罪的主观罪责是犯罪的客观危害的本原。没有客观危害,也就无所谓犯罪,因而也就无所谓犯罪的主观罪责。〔1〕参见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92页。美国学者赫希认为,主观罪责对于界定犯罪的客观危害具有制约作用,不体现主观罪责的客观危害不应被视为犯罪的客观危害,即不可以被纳入犯罪的严重性的评价范围。〔2〕参见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95页。另外,法律保护法益,但是其只调整人的行为,因此,即使动物自发袭击等自然事件对社会造成了不利影响,但不能就此说存在法益侵害。“从归责的角度而言,只有存在于行为无价值之中的结果无价值,才应成为刑法评价的对象。脱离行为无价值的结果无价值,对刑法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一种从行为无价值中流出的结果,才是无价值的结果,与行为无价值没有任何关联的结果,只是一种法益受损的自然状态,不应对行为人的归责产生任何影响。”〔3〕冯军:《未遂行为的刑法评价——李圣杰教授和劳东燕教授论文之评释》,载李圣杰、许恒达编《犯罪实行理论》,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215页。
三、新行为理论下犯罪竞合论之反思
(一)犯罪常态与真假竞合
我们刑法学中,罪数问题是很多刑法制度的交合点,涉及刑法制度和刑法理论的不同领域。〔4〕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9页。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区分。有人认为,“在想象竞合犯的讨论中,最为复杂的还是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之间的区分”〔5〕陈兴良:《刑法竞合论》,《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第108页。。有人也指出,“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标准,是刑法理论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6〕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4页。。令人欣慰的是,张明楷先生提出了不少应对之策,他认为,不借助具体案件事实的联结,仅通过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就能够肯定两个法条之间存在包容或交叉关系,是法条竞合的形式标准。实质标准之一是法益的同一性,即一个行为侵害了两个以上犯罪的保护法益时,就不可能是法条竞合,而只能认定为想象竞合。实质标准之二是不法的包容性,即在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法条,只适用其中一个法条就能够充分、全面评价行为的所有不法内容时,两个法条才可能是法条竞合;倘若适用任何一个法条都不能充分、全面评价行为的不法内容,即使符合形式标准与法益的同一性标准,也只能认定为想象竞合。〔1〕参见张明楷《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7页。
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引入“犯罪常态”这一概念。顾名思义,犯罪常态就是犯罪的一般状态与通常情况。例如,故意杀人中毁坏了被害人数额较大的衣服,是不是构成想象竞合犯呢?诚然,的确存在故意杀人时,被害人尚未穿衣服的场合,但这不是犯罪常态,因而不成立想象竞合。又如,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中毁坏了被害人家数额较大的门窗,是不是构成想象竞合犯呢?诚然,也的确存在侵入他人住宅时,被害人门窗完好无损的场合,但这不是犯罪常态,因而不成立想象竞合。如出一辙,所谓的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如盗窃枪支之后进而持有,也只能评价为一罪。
(二)行为个数与数罪并罚
“所谓禁止重复评价,并非绝对禁止对存在论上的同一行为或同一情节要素进行重复使用,其所针对的是对本质上反映同一不法内涵和同一罪责内涵的同一行为或者同一情节要素的重复考量。”〔2〕王明辉、唐煜枫:《论刑法中重复评价的本质及其禁止》,《当代法学》2007年第3期,第15页。它是充分而不过度的评价。行为如果满足数个构成要件,除非法条竞合时——严格意义上法条竞合时行为不满足数个构成要件,应当进行犯罪复数评价,否则便是不充分。
我们司法实践中,将大量本可以成立想象竞合犯的情形,作为一个行为处理,只成立一个罪名,从而导致案件的处理不能实现罪刑均衡。例如,在拆迁补偿中,一个住户给相关人员行贿,要求其在测量建筑面积时增加一些,该工作人员也应允了,事情办成功了。该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诈骗罪(共犯)的想象竞合犯,但是实务中多不是这么处理的。笔者认为,这三个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各不相包容,并且考虑犯罪常态,不是大多数受贿行为人都会附带着滥用职权与诈骗,不是大多数滥用职权行为人都会附带着受贿与诈骗,不是大多数诈骗行为人都会附带着受贿与滥用职权,所以不存在重合部分,理应评价为数罪。又如,甲以抢劫故意并准备了相关抢劫工具,在侵入他人住宅后发现住宅内没有人,于是实施了盗窃行为,这种情况也应评价为数罪。还如,丈夫有了外遇,意图下毒杀害妻子,便在饭菜中投毒,虽然意识到妻子经常会给儿子喂食,一起用餐,但是认为是否也会毒死儿子无所谓,最后妻子在给儿子喂食的过程中,发现食物有问题,及时将已经吃了半碗饭的儿子送到医院,所幸医治及时,终无大碍,由于间接故意行为中,没有犯罪未遂存在的余地,司法人员可能会将其作为不作为犯罪处理,正确的做法是故意杀人(妻子)的未遂,而对于儿子则是间接故意犯罪未遂的不能犯。
但是,晚近有力的观点又将大量法条竞合的情形,认为成立数个罪名(只是不予以数罪并罚而已),从而导致案件的处理评价过度。其认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与交通肇事罪的保护法益分别为人的生命与公共安全,盗窃罪与盗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分别为财产与森林资源,等等。〔1〕参见丁慧敏《论刑法中的法条竞合》,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07页以下。笔者以为,这些学者之所以要“明目张胆”地将特别法条与一般法条解说为想象竞合,根本在于他们在特殊法条为轻法条时要将行为人入罪,而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尤其是法律已经明确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时候),私见以为,这种学术研究的理念可能有一定问题。虽然这些学者认为想象竞合犯不宜数罪并罚,法条竞合中如无刑法分则明文规定则应适用重法条的话,最终刑罚并无太大差异,但是难以令人认同。
因为这是令人疑惑的,其一方面认为,一罪与数罪的区分,与对数罪是否并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数罪不必然并罚,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要满怀正义,实现评价充分。〔2〕参见张明楷《罪数论与竞合论探究》,《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8页;张明楷《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4页。如果评价为数罪之后,又转头只科处一罚的话,那么评价为数罪又有何意义呢?目前,想象竞合犯与牵连犯等处罚方式,“不但使得其他构成要件的法定刑,无由共同参与法律效果的决定,更因法律效果的吸收关系,使得反映实现复数规范的一行为,其可罚性之具体内容,变得格外模糊不清,连带也使得复数构成要件所共同决定的不法内涵,丧失其非价判断的意义”〔3〕柯耀程:《刑法竞合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
而且,在这种做法下,还会产生更多困惑:“对于想象竞合犯究竟是从一重罪论处(仅认定为一个重罪),还是认定为数罪但仅按一个重罪的法定刑处罚?抑或认定为数罪按一个重罪的法定刑从重处罚?在按照一个重罪的法定刑处罚时,所科处的刑罚是否不得低于轻罪的法定最低刑?是否应当科处轻罪的附加刑?在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财产犯罪时,是否需要累计犯罪数额?”〔1〕张明楷:《罪数论与竞合论探究》,《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7页。笔者着实不解,为什么“行为被评价为数罪并不意味着必须并罚”“当适用一个重法定刑可以全面清算数罪的不法与责任时,就可以仅适用一个重法定刑”?〔2〕参见张明楷《罪数论与竞合论探究》,《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8页。
如前所述,“当一个自然行为蕴含多个危害行为的意义时,构成多个危害行为的竞合,其实质是危害行为的复数”〔3〕庄劲:《想象的数罪还是实质的数罪——论想象竞合犯应当数罪并罚》,《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第107页。。所谓的想象竞合犯中的一个行为,“是在自然观察上,为社会观念所认同的一个行为”〔4〕[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62页。,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一个行为。
一罪责则为一罪,数罪责则为数罪。推而言之,在锯齿现象、钩环行为、想象竞合、牵连行为等之中,我们常常将自然意义上行为的个数作为刑法意义上行为的个数的前提,一方面将一罪责支配下的砍某人一百刀的现象作一行为处理,另一方面又将二罪责支配下的一箭多雕之想象竞合犯作一行为处理;将牵连犯中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统合起来视为一行为,此种做法无疑是荒诞不经的。
更深层次,“所谓行为构成犯罪,就是行为逾越刑法所能容忍的限度,当特定行为逾越刑法所能容忍的限度时,刑法必须有所回应,否则刑法就无法自保,刑法如果无法自保,又如何保护法益?刑法对犯罪行为的回应,就是动用刑罚”〔5〕许玉秀:《刑罚规范的违宪审查标准》,载国际刑法学会台湾分会主编《民主·人权·正义——苏俊雄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389页以下。。如果刑罚的恶害无法与犯罪的恶害相匹配,刑法便可能是在自取灭亡、放纵犯罪。践行罪刑均衡原则的关键是责任与刑罚均衡,即有几个罪责,就应该科处数个刑罚。
四、新行为理论下犯罪参与论之检讨
(一)从犯从属性说之疑问
惩罚一个无法左右结果出现的行为——例如事故受害人所处的医院起火,在刑事政策上毫无意义。这也就是说,以一般预防为目的的禁令根本上只关系到行为方式,而与实害结果无关。一个刑法规范只能要求公民不准以刀捅人。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有这些都已经摆脱了行为人的影响,所以既不能成为一个行为规范的内容,也不能作为立法者或法官一般预防考虑的对象”。〔1〕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客观归责——不只是口号?》,王静译,载梁根林、[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主编《刑法体系与客观归责: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0页。德国学者指出,“禁止或要求一个人去做一个他根本无法避免或根本无法实现的行为是没有意义与不合理的,因此理性的批判仅会针对自由地被实施的行为”,“只有当行为人对于行为具有选择空间时,才会存在一个自由的行为(也因此才是一个行为)”。〔2〕参见[德]扬·C.约尔登《对人因其行为所为之批判——对于梁根林教授报告之评论》,林信铭译,载梁根林、[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主编《刑法体系与客观归责: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1页。
行为概念中,居于核心的思想是支配性。行为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可以支配的客观条件改变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状态。不作为之所以属于刑法上的行为,是由于“法秩序期待着一个特定的行为”〔3〕[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l年,第247页。,而且这也是他能够办到的。所有人类的责任都与支配这一概念相勾连,刑法上的归责判断,也奠定在支配的观点之上。“每个人都只需要对其所能够支配的事物负担刑法上的责任。所谓的归责判断,就是从众多的因果事实中,找出能够算是行为主体之‘作品’的事物。透过‘可支配性’这样的概念,表明行为人在事件流程中所具有的优势地位。”〔4〕蔡圣伟:《重新检视因果关系偏离之难题》,《东吴法律学报》2008年第1期(第 20卷),第139—140页。进而言之,能够部分左右结果的出现,就能够负一定的责任,如果完全左右结果的发生,就应当完全负责。完全不能左右结果发生时,一定不能负责。这正是作用分类法的合理性,分工分类法将分工与作用混为一谈,从而忽视了构成要件实现的支配力的高低,只关注于“谁是最后一刀捅进了被害人的身体”。
“仅有当一种生物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在思想上能够理解刑法的意义是针对具有罪责内涵之恶行所加诸的痛苦时,我们才能对之施以刑罚,这种生物不外乎就是人类。”〔1〕[日]山中敬一:《以人格体的权利作为刑法的界限——亚图·考夫曼对于父权式刑罚决定的评论》,李圣杰译,载[德]Neumann/Hassemer/Schroth主编《自我负责人格之法律——Arthur Kaufmann的法律哲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409页。刑罚的成立前提,必须建构于行为人的罪责之上,“所谓多数人参与犯罪,其刑事责任的认定,还是应该回归到犯罪的基本定义,针对个人行为做个别的判断。在犯罪构成的认定上,没有所谓的共同,也没有所谓的从属”〔2〕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共犯现象是数人所实施(各自的固有的)的数罪,而不是数人实施一罪。〔3〕参见钱叶六《共犯论的基础及其展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反观从属性论者,瑞士学者特若乐教授所言——我们应当避免不切实用的法学理论或方法的复杂化与精致化〔4〕Troller,Haftungsprobleme aus Schweizer Sicht,Karlsruhe Forum 1959,S.65。转引自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侵权责任法疑难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419页。,这或许是对共犯从属性论者最好的忠告。不过,在追求复杂化与精致化的同时,他们又对于某些问题粗枝大叶、不予理睬,正是由于其一般认为,共犯在犯罪参与中只存在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这无视行为概念在适用刑法上的指导意义,无视罪责理论在犯罪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因此存在不少疑问,这主要表现为:一个行为数个责任与一个行为两种状态。〔5〕论点“一个行为几个责任”与“一个行为两种状态”,系笔者在2014年5月27日陈忠林教授于西南政法大学毓才楼三楼学术报告厅所作“刑法中的行为概念及其展开”之讲座上所听说的,首见于马克昌、莫洪宪主编《中日共同犯罪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第289页。
首先,无法解释一个行为数个责任的难题——采取实行从属性的话,一个正犯行为将导致数人同时被评价为犯罪,如果没有正犯行为没有一个人犯罪。何以一个行为转瞬之间使得数人具备了罪责进而肩负起严苛的刑事责任?例如,有论者认为,“在正犯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只要能认定正犯的行为是由教唆犯的行为所引起,就能肯定教唆行为的成立;同样,只要能认定某人的行为对正犯的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就能肯定帮助行为的成立”〔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60页。。
其次,无法解释一个行为两种状态的根据。例如,正犯犯罪未遂,教唆犯随之未遂,正犯犯罪中止,教唆犯却还可能成立未遂。区分制之下,对此种一个行为影响他人的论说语焉不详,更没有说明“为什么正犯犯罪过程中的未遂可以影响共犯,但中止行为可能不影响”的原因。单一正犯体系,完全抛弃连带违法之论,真正实现违法性之个别判断。共犯从属性原理意味着共犯的无价值内容是从正犯行为那里借用而来的,却忽视了共犯行为本身即侵害了法益,尤其是在具体情景中,共犯行为利用他人的行为之后还有演变为区分论者所谓的“实行行为”的可能性。
(二)改造共犯行为理论
现代刑法摒除了团体责任理念,确立了个人责任原则。从刑法发展史来看,现代刑法的原则是建立在个人责任的理念之上,共犯人因各自的行为而产生各自的责任,绝不可因为其他人的行为而承受不利于自己的责任。一个人只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人的行为举止于己无涉,既不能令一个人对他人的行为负责,也不能让他人影响自己的行为状态。“犯罪永远是一个人在犯罪”,一个人之所以构成犯罪,全在于自己的行为具备了不法与有责,符合了犯罪构成。所有行为人,都是因为自己的责任而受到惩罚,而责任的基础当然是建立在自己行为的不法性和有责性的基础之上,不可能建立在刑法对他人行为的评价之上。〔2〕参见许泽天《共犯之处罚基础与从属性》,载《罪与刑:林山田教授六十岁生日祝贺论文集》,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73页。
单一正犯概念将所有对犯罪有贡献的人都一视同仁地当作正犯,至于这些主体各自对整个犯罪过程和结果的重要性、影响力,在定罪上都在所不问。不法的判断永远是就个人的情形独立判断,不法的判断根本无法从属,因此,在单一正犯概念之下,不会有共犯从属性问题。〔3〕参见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相对的,共犯从属性说无法解释共犯为正犯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责任的根据。当然,晚近有学说将因果共犯论、惹起说作为共犯的处罚根据,较好地解决了责任主义的困扰,但是,如果以其作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很难说还与单一制有什么差别。〔1〕参见[日]高桥则夫《共犯体系和共犯理论》,冯军、毛乃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3页以下。申言之,以惹起说中通说“折中惹起说”为例,其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共犯不实行构成要件的行为,而是透过正犯间接侵害构成要件上要保护的法益,如此这般,单一正犯体系论者也认为共犯透过正犯间接侵害了构成要件上要保护的法益,而且更进一步地说,共犯行为本身也侵害了法益。即使正犯没有侵害法益(没有犯罪预备),也可以处罚教唆人、帮助人。而且,从属性导向的惹起理论,在虚假教唆与对向犯的问题中,必须提出矛盾的见解,徒增烦恼。
只要坚持行为刑法与罪责刑法,树立规范意识,就必须承认任何人都是独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独立地符合构成要件。犯罪的成立取决于客观不法与主观罪责,行为人也只对自己罪过支配下的行为和结果负责。二人共同开枪射击一个,在受害人由于一枪毙命死亡而无法查明是由谁导致时,存在共同决意与不存在共同决意,处理结果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各自行为的支配范围(主观罪责的支配范围)不同。行为人之间相互利用、互相补充,自己的犯罪是他人的,他人的犯罪也是自己的,正所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2〕我国共犯从属性论者,也认可了这一结论,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总论精释》(第三版),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第501页。,行为人的罪责所支配的范围得到了拓展。一言以蔽之,“任何犯罪都是人的主观意志表现于外在的行为而对他人利益造成侵害的现象”〔3〕刘明祥:《我国大陆不宜采取共犯从属性说》,载林维主编《共犯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8页。。
有学者认为,按照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逻辑,要认定某一行为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犯罪成立的全部要件,并以此批判我国犯罪构成体系。〔4〕参见钱叶六《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阶层化及共同犯罪的认定》,《法商研究》2015年第2期,第148页以下。但是,笔者的疑问是:难道按照域外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逻辑,要认定某一行为成立犯罪,不需要具备犯罪成立的全部要件吗?既然认定任何一个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合乎构成要件、具备违法性与有责性,正犯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共犯行为也符合构成要件。
共同犯罪中,行为人总是通过控制某些客观条件作用于特定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来实现自己行为的目的,在共同犯罪中,他人的行为,对行为人而言,就是自己行为所利用的客观条件之一。各个共同犯罪人也只能对自己独立实施的行为负责,而不可能是对“行为的一个部分”独立承担刑事责任,这是罪责自负的个人责任原则的必然结果。共同犯罪也是数个人共同犯数个罪,每一个人至少具备一个罪过。〔1〕参见陈世伟《论共犯的二重性》,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第2页。“在共同犯罪与犯罪构成的相互关系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共同犯罪构成,共同犯罪构成不但受一般犯罪构成理论和规格的制约,而且其构成要件不过是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结合。”〔2〕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9页。这可谓是大鹏虽大,五脏俱与麻雀相同。
江溯教授即指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利用他人的客观不法构成要件来实行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间接行为人从属于直接行为人,因为任何行为人之所以构成犯罪,都只可能立足于自己的行为具备不法与罪责。教唆犯在犯罪参与中,就不可能只存在教唆行为,还存在一个利用行为,其行为构造是教唆行为+利用行为。〔3〕参见江溯《犯罪参与体系研究——以单一正犯体系为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6页以下;江溯《超越共犯独立性与共犯从属性之争——刑法第29条第2款的再解释》,《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2期。共犯行为的利用部分,就好比物理学中的“场”,虽然日常生活中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同理,帮助犯在犯罪参与中,其行为构造也是帮助行为+利用行为。共犯在犯罪参与中,其犯罪行为绝对不止步于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只是其参与行为的组成部分,其完整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是共犯行为+利用行为,只是说,共犯行为与利用行为只在一个罪责支配下侵害了一种法益,应当在刑法体系中视为一个行为。
五、余论
一方面,刑法乃规范之学,必须在规范中思考概念。生活世界关注的是自然意义,意义世界关注的是规范意义。自然事实与法律事实并不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当法律对自然事实施以评价时,系根据事先确定的规范命令所为。一项行为完全可能违背数项规范命令,从而有着相当不同的规范意义,并因此与之对应数个犯罪构成。事实世界看似性质单一的行为,在沿着模态逻辑进入规范世界后,又如光线透过三棱镜,将呈现出纷繁各异却又系出同源的面向。自然事实不过是宿主,意义在于为规范事实提供栖居之所。同一自然事实进入规范世界后,可能表现为性质迥异的数项规范事实。〔1〕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4页以下。
另一方面,诚如德国波恩大学教授Puppe所言,刑罚系取决于罪责之轻重,而罪责对外表现于行为、对内则反射出行为人之非难可能性与人格特质,故刑法对具有可责性行为赋予刑罚之效果,并非即表示刑法为行为刑法或是行为人刑法。〔2〕参见柯耀程《刑法的思与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罪责作为刑法理论的缩图,主观状态不是一个神经活动的过程,而是有意义的规范化的透过知觉而后决定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学者指出,“整个刑法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将定罪的标准组建从违法行为移向行为者的历史”〔3〕[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罪责在我国乃至域外刑法学理与审判实践上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普遍确立了罪责原则或曰责任主义,但是尚未充分利用罪责在认定疑难案件、破解复杂问题时的独到作用,以至于人们对不少问题感到无望的恐惧。虽然,质疑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笔者十分谨慎地在进行质疑。因为如果这些质疑并非基于对该概念的真正了解,而是建立在各种先入之见与误解的基础之上,那么,不仅会阻碍刑法学本身的发展,而且会妨碍我们在智识上的进步。笔者由衷地希望本文是一个开端,利用对话和交流,纾解已经形成并在不断放大的相互之间的疏远、误解乃至对立。“我们身处的,是一个确定性丧失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们转而寻求相互理解并力图达成共识的时代。”〔4〕王轶:《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32页。毕竟,问题之解决,不应仅由体系架构与公理化来求得,也需要透过与其他学者的论题进行具体之争论来寻得。尤其是针对实质问题,只有透过论证与否证,方能求着主体间性。〔5〕参见[德]Ulrich Schroth《刑法总论:导论》,王效文译,载[德]Neumann/Hassemer/Schroth主编《自我负责人格之法律——Arthur Kaufmann的法律哲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