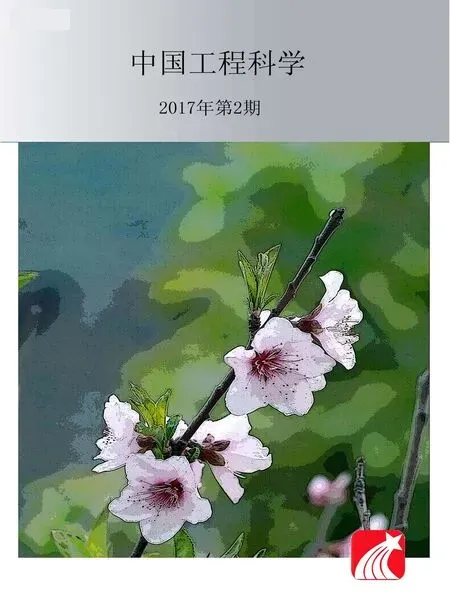建立新型国家预防医学体系战略研究
徐建国,刘开泰,陈博文,贾光,邵瑞太,尹德卢,殷继永,薛冬梅,胡贵平,马军,孙长颢,何燕玲,何耀,李丽萍0,杨克敌,梁鸿,郭有德,温春梅,阚飙,武阳丰,戴政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北京102206;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北京100050;3. 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北京100020;4.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100191;5. 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1121;6. 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100020;7.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哈尔滨 150081;8.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 200025;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北京100853;10. 汕头大学医学院,广东汕头 515063;11.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武汉 430074;12.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13.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北京 100600;14.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北京100191;1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育培训处,北京 102206)
建立新型国家预防医学体系战略研究
徐建国1,刘开泰2,陈博文3,贾光4,邵瑞太5,尹德卢6,殷继永2,薛冬梅1,胡贵平4,马军4,孙长颢7,何燕玲8,何耀9,李丽萍10,杨克敌11,梁鸿12,郭有德12,温春梅13,阚飙1,武阳丰14,戴政15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北京102206;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北京100050;3. 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北京100020;4.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100191;5. 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1121;6. 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100020;7.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哈尔滨 150081;8.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 200025;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北京100853;10. 汕头大学医学院,广东汕头 515063;11.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武汉 430074;12.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13.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北京 100600;14.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北京100191;1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育培训处,北京 102206)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劳动生活方式的改变,影响我国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谱以及危险因素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有的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教育体系已不再适应疾病预防控制、保障人民健康的实际需求。未来的卫生方针和政策、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工作能否及时调整以应对这些变化和需求,是摆在我国卫生决策者面前的重大挑战。探讨建立适应实际需求的新型国家预防医学体系,并制定相应的卫生战略、战术和相关政策,从而实现有效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获取最大的健康保障效果。
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疾病预防与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健康危险因素;策略
DOI 10.15302/J-SSCAE-2017.02.009
一、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提出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把控制严重影响人民生命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作为卫生工作重点。经过60多年艰苦奋斗,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妇幼卫生保健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孕产妇、新生儿死亡率显著下降;环境卫生、职业卫生、放射卫生、学校卫生以及营养卫生等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不断拓展;埃博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地震灾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得到有效防控。基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不仅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日常卫生服务,也为落实疾病预防和控制的具体措施提供了保障[1,2]。
伴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影响我国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谱、危险因素以及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不仅面临新发、突发、再发传染病等的威胁,同时慢性病的发生也进入失控阶段。现有的卫生服务机构和公共卫生教育体系源于对传染病、急性病的防控,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保障和促进人民健康的需要。未来的卫生方针和政策、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战略能否及时调整以应对这些变化和需要,如何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念”,关注生命全周期和健康全过程,是摆在我国卫生决策者面前的重大挑战[3~5]。2016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贯彻“大健康”观念要全面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本文为实现高效利用有限卫生资源,达到最大程度地促进和保障人民健康的目的,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尝试性地分析了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可防可控的重大疾病和公共卫生问题,提出了能满足实际需求的新型国家预防医学体系框架,为制定卫生战略和相关政策提供了相关依据。
二、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取得的成就
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值得认真总结、继承和发扬光大。其主要表现为:依法实施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设立重大传染病管理项目,并在相应的政策和经费上予以支持;建立遍布全国城乡的三级医疗卫生网络与覆盖全国的传染病应急反应机制相互配合;将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使绝大多数弱势群体得到了有效保护;针对孕产妇、儿童和老年人等重点保护人群,开展了营养干预、免疫规划、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性病)管理;对职业场所,实施了行之有效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八字方针;实施了针对儿童肺炎、乙肝、结核、血吸虫病以及重点地方病的防控,效果显著[1,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促进了药物和医疗技术更合理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区居民对常见病就诊和治疗的需求。全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发病率由1970年的7000/100 000下降到2013年的473.9/100 000,降幅达93.2 %。1950—2010年,我国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从35岁增长至76岁[6]。
三、当前我国重大疾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以及发展趋势
认真梳理、分析疾病流行趋势及危险因素,并通过有效手段加以预防和控制,进一步提高、改善、促进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是我国目前卫生工作的重点。
(一)新发传染病肆虐,传统重大传染病如肝炎、结核病等未得到完全控制
由于国际经贸发展和人员来往大幅度增加,导致新发和不明原因传染病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重大挑战,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和安全。同时,曾被控制的传染病死灰复燃,新型传染性疾病时有发生,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反弹趋势。SARS、埃博拉的暴发流行,曾严重威胁全球人类健康与生存,引起民众恐慌及社会不安,全球不得不全面动员并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以控制这些疾病的蔓延[7]。
(二)慢性病成为我国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
随着环境质量的恶化,人们饮食结构和行为因素的改变,较低的健康素养和不合理的体育运动,加上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缺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以及肿瘤等迅速上升为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占全部死亡原因的80 %以上,每年大约有300万人过早死亡[8,9]。分析其主要原因:现行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不再适应新时期慢性病的防控需求。从专业上看,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相互割裂,渐行渐远;从管理上看,政府各部门缺乏疾病防控的整体观,管理各行其道,执行力低下,比如,目前开展各类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比例不到30 % [10]。
(三)精神、心理问题日益严重
患精神性疾病的人数急剧上升,与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型带来的工作、生活压力和日益严酷的竞争有关。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计到2020年,我国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至全国疾病总负担的1/4 [11,12]。而我国目前相应专业的医护人员、医疗机构和心理健康干预人员却十分匮乏。
(四)职业危害、环境污染等公共卫生问题不容忽视
当前,我国职业性危害尚未得到根本控制[13],影响我国职业人群的职业有害因素种类繁多,所致疾病类型也多种多样,传统因素如粉尘、有毒化学物、物理因素等尚没完全有效控制,新的职业有害因素不断涌现,如不加以有效防控,将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4]。同时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空气、土壤等环境要素质量持续恶化,大气灰霾的污染也逐渐成常态化的趋势,人们面临多重污染暴露[15,16]。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如吸烟、过量饮酒、体育运动不足等危险因素广泛存在,我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亿,每年因烟草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17,18]。如果影响疾病流行的职业与生活环境、行为因素得不到根本改变,我们将很难完成健康中国的重任。
(五)人口老龄化加重疾病负担
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相应的医疗卫生负担将持续增加。如果不及早实施有效的医养结合的疾病预防与控制策略,维护老龄人群健康,慢性病和老龄社会卫生服务的双重压力必将成为我国社会及家庭的沉重负担[19]。
综上所述,我国正面临着传染病、慢性病、精神性疾病、不良生活习惯以及职业危害、环境恶化等多重挑战[20]。在新形势下,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相应的卫生战略。
四、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一)决策者和公众对新时期疾病和健康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且缺乏足够的应对策略
健康和富有活力的人群是一个文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长期以来我国重视发展经济,以确保人民群众实现基本小康生活。应当认识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方面保证了基本生活需求,同时也带来了对健康不利的负面因素,如生活和职业的环境恶化、疾病传播加速、不健康生活方式等,造成了本来“可防、可控”疾病的流行。加上我国民众健康素养水平较低,长期以来将自己的健康寄托于医生和医院,而不是从自身出发,建立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现有的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教育体系不能满足应对疾病和重要公众健康问题的需要
我国现有的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教育体系是基于生物医学模式的传染病流行和急性疾病治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当前以生物因素、职业(环境)因素、行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共同作用引起的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需要的专业技能、知识和基础设施差距巨大,难以满足预防控制慢性病流行所需的早期筛查、健康咨询和长期随访、治疗的需要,也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21]。
(三)医疗卫生领域投入不当,医疗资源布局极其不合理
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缺乏严格的技术审核和相应法规、政策支持及限制,医疗卫生投资和人群健康水平缺乏关联,导致医疗卫生投资集中在医院建设,而且多数都在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由于交通、经济能力等因素限制,只有部分人能够使用这些高技术设施,而社区和基层的群众难以获得相应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政府巨额投资大医院,反过来又大大增加了医疗服务的费用,客观上造成与基层和社区卫生服务竞争有限的卫生资源,使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需求更难以得到基本保障,形成周而复始、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
(四)医疗和预防之间的裂痕加大
在医学教育中出现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教育互不交叉,实际工作中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互不来往,特别是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中存在“防治”分离现象。虽然注重健康教育和危险因素控制,但不能有效发挥临床医学在疾病早发现、早治疗中的作用;而临床治疗专注的是个体疾病,忽略了人群疾病流行模式的变化,如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从根本上减少疾病;二者的渐行渐远不仅不能互补发挥作用,而且导致鸿沟和裂痕不断加大,导致居民健康得不到保障,不利于疾病的“源头治理”[22]。
(五)现有的卫生信息系统无法全面反映我国居民的健康状况
医学科技的快速发展、卫生行业分工的细化、业务流程日益复杂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卫生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卫生统计信息尤其是人群死因等生命统计信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尚不能完全掌握居民的生命全过程信息,卫生信息不准确、不及时、不完整,不利于政府做出正确的卫生决策。
(六)卫生决策机制不健全
当前,我国卫生决策机制仍然以应急性、临时性、部门性决策为主,决策方法和手段落后,知识更新不及时,缺乏科学、透明、综合和宏观长远的卫生决策制定程序和调整机制。健康是群众的基本需求,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水平,需要适时调整颁布切实可行的针对性强的卫生决策。
(七)缺乏监督和长期追踪评估机制,政绩和健康效果脱钩
卫生投入于硬件建设(如医院建设、设备更新)在短期内能立竿见影,客观造成行政管理者为出政绩而热衷短期投资,需要较长时间显效的投资如基层社区卫生服务则缺乏足够投入。有些医疗卫生项目投资产生不良后果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显现,由于缺乏长期追踪评估机制,造成投资过大、低效益的恶性循环。
五、发展目标
我国未来预防和公共卫生领域发展的总目标:增强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早期检测、监测和应急反应能力,降低人群因慢性疾病引起的早死和提高健康预期寿命,促进和谐、健康老龄社会的建设。
具体目标是:①建立功能配置合理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和人才培养的预防医学体系;②完善新发、突发传染病反应灵敏、迅速和控制措施落实有力的网络和体系;③强化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和能力建设,控制影响慢性病和精神性疾病等卫生问题的危险因素,及早发现和诊疗疾病,全面实施符合成本效益的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将主要健康问题在基层解决。
未来的预防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展战略应立足国情、放眼全球,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将“末端治理”变为“源头治理”。继续坚持“预防为主和防治结合”方针,加强国际合作和国内协调,强化部门协调和合作等基本原则。
六、政策和措施建议
(一)确定重大疾病和影响公众健康的主要问题
对于我们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管理层次多、发展不平衡、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双重负担、贫穷和富裕相关疾病并存、未富先老的国家,难以在国家层面将所有疾病和健康问题系统管理,而应参照国际上通行的确定重大疾病和健康问题的方法,根据疾病对生命和健康、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卫生安全等指标的影响,确定国家必须重点控制的重大疾病和公众健康问题,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进行预防和控制,推动绿色清洁生产,改善作业环境,严格控制健康危险因素,强化职业病防治,优化生活环境,营造健康环境,实现重大疾病的一级预防。
(二)将重大疾病控制纳入国家发展议事日程,并实施有力的保障措施
重大疾病的控制工作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内容,需要强化政策法律和经济手段,以保证控制措施的落实。
1. 将重大疾病和公共卫生问题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重大疾病和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公众的健康,而且这些疾病与大环境密切相关,也和多个政府部门工作有关,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控制重大疾病必须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要作为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全面小康和健康老龄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相应的政策、经费等方面予以支持。
2. 完善有关卫生法律和法规,保障公众健康
做好顶层设计,加快出台能够指导其他政策法规实施的健康基本法,梳理现有的卫生政策法规,使得各项政策、法规界定清晰,互不矛盾,废除不合理的或落伍的卫生政策法规,修订不完善的政策、法规,注入新的更加有效的政策、法规制度。
3. 建立中央负责基层社区、省地县负责本级预防保健经费的分级负责制
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动员社会、全民参与的慢性病综合防治机制,建立中央负责基层社区、省地县负责本级预防保健经费的分级负责制。中央政府完全负责基层社区(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委会))的预防保健费用,省、市、县级政府负责省、市、区(县)级的专门预防保健经费。明确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个人等各方在健康管理方面的责任。统筹社会资源,完善社会保险购买预防保健服务的支付模式,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捐资、捐赠疾病预防事业,鼓励市场创新驱动健康服务业发展、社会各自发挥自身专业化优势,互为补充,以进一步提高健康服务的效率和覆盖面。
4. 设立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专项经费
继续坚持“设立国家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专项经费”,增加用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肺癌为主的重大慢性病预防控制专项经费,逐渐增加其他可预防重大疾病专项经费,用于引导和指导全国各地对重大疾病的预防控制;建立实验示范点,探索更有效的预防控制方法和途径,以达到迅速控制这些疾病的目的。
5. 营造健康环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广泛宣传关于维护促进人民健康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普及健康科学知识,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引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教育居民树立正确健康观,增强社会对慢性病防治的普遍认知。增加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开展早期人群筛查和疾病早期检测,实现一级、二级预防工作的关口前移。加强正面宣传、舆论监督、科学引导,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慢性病预防控制。同时,系统加强慢性病防治科研布局,推进相关科研项目及科技成果转化和适宜技术应用。
(三)建设适应疾病控制需要的公共卫生体系
实施控制重大疾病和公众健康问题需要技术水平高、覆盖面广、反应迅速、执行有力,并能够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公共卫生网络和体系。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强化国际合作和国内协调,全面提高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反应和控制能力
新的传染病控制策略应当提高技术检测和流行病学分析调查能力,及早预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走出国门,与国际同行一起,共同控制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这点已经成为传染病控制的共识和行之有效的重要策略。同时,还要加强卫生、交通、海关、旅游、商务、公安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依法实施控制措施,切断传播途径。
2.我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功能、作用需要重新定位和发展,实现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
为能适应当今复杂的防治形势,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需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部门的角色定位。我国未来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更需关注两端,一端是统筹管理和科学研究,主要在国家、省级专门预防机构,定位于疾病的一、二级预防,指导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提供卫生服务技术指导;另一端是服务的具体提供和实施者,主要包含各级医院和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需要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衔接、功能整合,提高传染病的早期发现能力和慢性病的早期诊断、防治、技术指导和监测能力。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需要调整功能,重在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快速协调和反应能力、开发处理慢性病和其他公众健康问题的适宜技术和提供技术指导能力,促进预防与医疗协同,实现全流程健康管理。
3. 以需求为导向培养符合实际需要的预防和公共卫生人才
建议合理培养公共卫生专业人才队伍,从具有专门训练的临床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专业人才中招生,用于培养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高级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培养具有处方权的公共卫生医师或者全科公共卫生医师和专科公共卫生医师,从事与疾病诊治有关的公共卫生人员,需要培养临床医学诊断和治疗能力,并纳入医师考核管理系统。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预防医学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顺应居民对健康的需求,促进健康,降低疾病负担,推进预防医学体系改革、建立国家新型预防体系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和必然。建立健康中国,迫切需要功能完善并能发挥作用的充满活力的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体系作为支撑,我们需要抓住机会、顺势而上,更好地保障、促进公众健康,为建成中国全民健康和全面小康做贡献。
[1]李立明,姜庆五. 中国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Li L M, Jiang Q W.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health in China [M]. Be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5.
[2]李立明. 新中国公共卫生六十年的成就与展望 [J].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14, 30(1): I0001–I0002. Li L M.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of public health in sixty years in New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2014, 30(1): I0001–I0002.
[3]Meng Q Y, Yang H W, Chen W, et a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alth system review [J]. Health Systems in Transition, 2015, 5(7): 1–142.
[4]韩启德.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 [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0(05): 41. Han Q D. China’s health development is still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J]. Chinese Health Policy Research, 2010(05): 41.
[5]李滔, 王秀峰. 健康中国的内涵与实现路径 [J]. 卫生经济研究, 2016, 345(1): 4–9. Li T, Wang X F. Connotation and realizing route of healthy China [J]. Health Economics Research, 2016, 345(1): 4–9.
[6]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2013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Z].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3. Ministry of Health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Center. China health statistics yearbook in 2013 [Z]. Beijing: Pec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ress, 2013.
[7]龚磊, 张进, 陈国平, 等. 新发传染病的流行与早期识别预警研究综述 [J]. 安徽预防医学杂志, 2015, 21(2): 117–121. Gong L, Zhang J, Chen G P, et al. A review on epidemic and early recognition and warning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J]. Anhui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15, 21(2): 117–121.
[8]Listed N. China’s major health challenge: Control of chronic diseases[J]. Lancet, 2011, 378(9790): 457.
[9]卫文. 我国每年300万人因慢病过早死亡 [J]. 家庭医学, 2015(2): 32. Wei W. 3 million people die prematurely each year in China due to chronic diseases [J]. Family Medicine, 2015(2): 32.
[10] 司向,翟屹,施小明.中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能力评估 [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4, 35(6): 675–679. Si X, Zhai Y, Shi X M. Assessment on the capacity for programs regarding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4, 35(6): 675-679.
[11] Alonso J, Chatterji S, He Y. The burden of mental disorders: Glob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WHO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 Phillips M R, Zhang J, Shi Q, et al. Prevalence, treatment, and associated disability of mental disorders in four provinces in China during 2001—05: An epidemiological survey [J]. Lancet, 2009, 373(9680): 2041–2053.
[13] 张幸. 消除矽肺病任重而道远 [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12, 30(1): 1–2. Zhang X. Elimination of silicosis has a long way to go [J]. Chinese Journal of Industrial Hygiene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 2012, 30(1): 1–2.
[14] 贾光. 健康中国, 职业现行 [J].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6, 48 (3): 389–391. Jia G. Healthy China, occupational health first [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s), 2016, 48 (3): 389–391.
[15] 潘小川. 关注中国大气灰霾( PM2.5) 对人群健康影响的新常态 [J].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5, 47 (3): 377–379. Pan X C. Pay attention to Chinese atmospheric haze (PM2.5) new normalization effects on human health [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s), 2015, 47 (3): 377–379.
[16] 杜刚. 新时期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 资源节约与环保, 2015(4): 136–148. Du G.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analysi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new period [J]. Resource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5(4): 136–148.
[17] Li S, Meng L, Chiolero A, et al. Trends in smoking prevalence and attributable mortality in China, 1991–2011 [J]. Preventive Medicine, 2016(93): 82–87.
[18] Gu D, Kelly T N, Wu X, et al. Mortality attributable to smoking in China [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mdicine, 2009, 360(2): 150–159.
[19] 杜鹏, 翟振武, 陈卫. 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 人口研究, 2005, 29(6): 92-95. Du P, Zhai Z W, Chen W. The elderly population of China: A century-long projection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05, 29(6): 92–95.
[20] 陈新石, 高润霖. 坚持改革创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J]. 中华医学杂志, 2017, 97(1): 1–2 Chen X S, Gao R L. Persevere in reform and innov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China [J].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2017, 97(1): 1–2.
[21] 司向, 翟屹, 施小明. 中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能力评估[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4, 35(6): 675–679. Si X, Zhai Y, Shi X M. Assessment on the capacity for programs regarding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4, 35(6): 675–679.
[22] 黄建华. 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关系发展探讨[J]. 中外医学研究, 2012, 10(5): 154. Huang J H. To explore the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clinical medicine development [J].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Research, 2012, 10(5): 154.
Establishing an Innovation-Oriented National Preventive Medicine System in China
Xu Jianguo1, Liu Kaitai2, Chen Bowen3, Jia Guang4, Shao Ruitai5, Yin Delu6, Yin Jiyong2, Xue Dongmei1, Hu Guiping4, Ma Jun4, Sun Changhao7, He Yanling8, He Yao9, Li Liping10, Yang Kedi11, Liang Hong12, Guo Youde12, Wen Chunmei13, Han Biao1, Wu Yangfeng14, Dai Zheng15
(1.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2206, China; 2. National Institute for Nutrition and Health,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50, China; 3. Community Health Associ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20, China; 4.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1121, Switzerland; 6.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Beijing 100020, China; 7. Public Health College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1, China; 8.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 9.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100853, China; 10.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Shantou 515063, Guangdong, China; 1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ongji Medical College,Wuhan 430074, China; 12.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13. WHO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China, Beijing 100600, China; 14. Peking University Clinical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191, China; 15.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ivision,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ife-style changes, the spectrum of diseases and risk factors affecting our people’s health has drastically changed. The current systems, including health laws and decrees, education about clinical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health service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so forth, do not meet the real dema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health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China’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curr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healthcare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strategy, and discuss how to establish an innovation-oriented national preventive medicine system in order to make efficient and ultimate use of limited resources to control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prevalence of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to protect and promote maximum public health across the nation.
public health; preventive medicin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health risk factors; strategy
R1
A
2017-01-10;
2017-02-10
徐建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微生物学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E-mail: xujianguo@icdc.cn
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我国全民健康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战略研究”(2014-ZD-06)
本刊网址:www.engins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