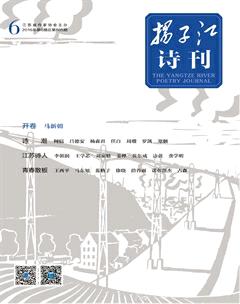大辽河(组诗)
罗凯
祖母的西佛
在辽河以西,这个叫西佛的乡土,就在河坝下
它只需安静地躺在平原上,不用站起来,足以让天空低垂目光。
她是西佛女人中的一条河,她使用一身
岸上的良田,拔节过十二个子女,她的天空下是无边的粮食。
在这块祖母地上,她曾经的活动范围,比火炕
要辽阔得很多,但是她从没有越过祖国的一寸疆土。
我的祖母活着的时候,辽河的波涛,跟着她身后落了一生的雪
她总能按住,一个比她内心还要苍白的辽西平原。
西沙岗子的反光
西沙岗子祖坟头上会有反光,风搅动阳光的碎片,还有火焰
就在西佛镇上空,我看见,有一道闪电的裂缝填充纸灰。
我的祖先重叠的白骨之上,一朝又一朝,覆盖着黄土黄沙,荒草荒花
整个辽西平原,他们抬着辽河,在庄稼地底下暗处给根补充着水。
他还在那条饥饿的路上
他,是我的祖父
他,有一身辽河的悲凉。
坝下那条路,他腰上的一根比命还长的麻绳
而平原,飘摇在绳下。
他比遥远的路,还瘦
更早地倒在饥饿的路上。
手上,始终没有抓到一粒安稳天下的粮
手里,抓住了路边一根野草。
他身体里,还有辽河的激流
放进去太厚埋骨的泥沙。
以后,每年收走他的那条路的
两边,再也不生长野草,除了种粮,就是收粮。
老宅
祖母的老宅,已是一堆阳光和月色的瓦片。
我曾经站在屋顶上,看得见辽河与她的身影。现在重叠的那一部分还在流浪。
她的坚韧,善良和忍耐,足以肥沃辽河西岸的平原。我翻出世道的风声
我阅读,一本放进氏族风雨的家谱。
想故乡
想故乡
就是想那个北方以北的辽西平原。
想平原,就是想那一条总在分割清浊的辽河。
想辽河
就是想坐在火炕上,很像思想者的祖母。
想祖母,就是想那个村西头埋着她的坟,想坟里头还活着多少根
一笔辽河
一画平原
留守着故乡的白骨。
一块蓝花布
我的祖母,曾经有一块白底蓝花布
总裹在头上。 很像落下的天,从村东头走过西头的几朵云。
在乡间的黄昏尽头
一个装着风雨的青花瓷器,而裂纹里有她一生无法蹚过的辽河。
在河坝下,那块布,还在埋着她。
这布纹里的平原,已是一块糊口交粮的好田。
大辽河
有一片平原,生生息息在天空下
来自乡间的目光
必须放在辽河的源头,更能让我看得清,多少事都搁浅在岸边。
我捧起一捧河水,很想看到它的全部骨骼
总是有响动的液流
进入,一湾蓝得很的肉体。
在海边
我看见我的先祖,用一身生命里的水和盐,抬着这条
分不开清与浊的大水,从未停止在海上。
那盏煤油灯还亮着
祖母,用过的那盏煤油灯,仿佛远在故乡亮着。
我曾经在黑暗里
很想看清,它晃动辽河的影子。
它照亮的窗户
能让夜,在窗纸上走出星光。
总是祖母的身影,连接着比一扇窗户,要辽阔很多很多的平原。
她在夜里,孤独的一个人
占有她屋檐下的范围,堆放着安静的粮食
抽着一锅,能听到辽河涛声的烟袋。
那盏灯
让她在长夜的中央,能有多么的灿烂。而她看过风雨的势力
都先于她熄灭了。
那九株很红的高粱跟着她也走了
我的故乡
有一片高粱地,那种红的根,在坝下能够得到辽河的根。
祖母活着时,她的根
也是很深地扎向平原内部。
她用一生喂养了十二子女,有九个花草一样夭折
她总是乘着黑夜
在那片高粱地,挖个坑埋下。
总会有一场夜雨 ,很想冲出她的平原
含在她的眼里的苦难
流向一身的辽河。
之后,那一片红高粱
一年比一年红。
她的眼里
总能摇晃着那种红
照亮着辽河。
那一年,她走了
九株红高粱,一夜之间,也跟着她走红了
整个平原。
从辽河往西走
从辽河往西走
坝下,往西再走十五里地,就是祖母的家。
一条进村的路,扭着腰往西哼唱着走。
一片玉米地,在风里,往西晃荡阳光金黄的叫声。
一条小河,弯来弯去地往西流,流不出氏族在辽河流域的命和运。
往西走,几代人不停地走
走进一座西沙岗子,一座坟地长满了野芝麻。
那一年的清明
我和弟弟、妹妹在坟前,向西烧了几张盖红戳的黄纸。
一群乌鸦在飞,是几代的乌鸦往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