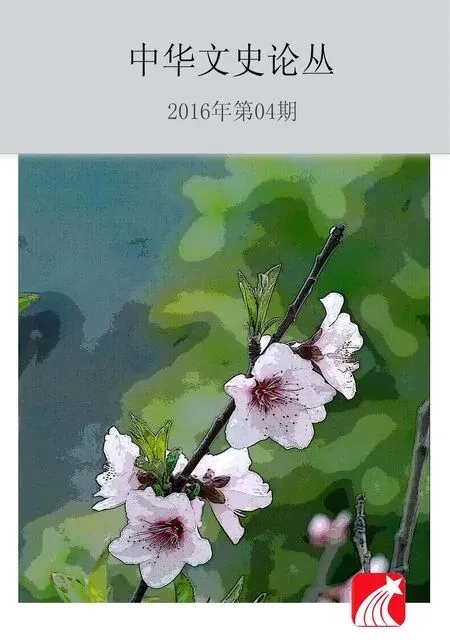徐謂禮文書簽押附注詞考
石聲偉
徐謂禮文書簽押附注詞考
石聲偉
《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的整理出版爲研究宋代官文書提供了非常好的範例。簽押是官文書生效的必經程式,本文考釋了“免書”、“分書”、“都督”、“督視”、“奉使”、“未上”這六種較爲少見的簽押附注詞,它們與“假”、“闕”一樣,都是任責官員未能簽押的特殊情況說明。
關鍵詞: 徐謂禮文書 簽押 簽押附注詞
中華書局2012年出版的《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下簡稱“徐謂禮文書”)幾乎完整地記錄了南宋武義(今屬浙江)人徐謂禮一生的任官歷程,包括告身十一道,敕黃十道,印紙八十則。宋代的任官文書有真本與錄白本之別,真本即原本,錄白本錄自真本,且需經由書鋪對讀、繫書。徐謂禮文書爲錄白本之抄件,雖無真本之畫押與用印,亦無錄白本之書鋪繫書,但其文字内容與格式(包括提行、空格、字體大小等),應是嚴格按照錄白本抄錄,爲我們研究宋代官文書的内容與格式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在這批文書當中,簽押附注詞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宋代的官文書需由任責官員簽押和用印方能生效,而在徐謂禮文書中的官員簽押之下,不少還有附注說明。這些附注詞有的透露了文書製作的流程,有的則說明了任責官員未能簽押的特殊情況,從中亦可窺探當時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往石刻史料中雖然也出現過此類附注詞,但因爲材料分散,尚未引起學界關注,而在徐謂禮文書中,簽押附注詞比較集中地出現,爲我們研究宋代官文書的簽押提供了很好的契機。本文擬對這些附注詞進行分類和考釋,希望能對徐謂禮文書的進一步整理、解讀有所幫助,不當之處,還請前輩學者批評指正。
一 徐謂禮文書簽押附注詞分類
徐謂禮文書中的簽押附注詞大概可以分爲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文書處理的程序說明詞,包括讀、省、審、受、付吏部、言、上、下、批等。這一類的說明詞比較常見,也較易理解。*包偉民在《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前言中對這類附注詞已有說明,可參看。
第二類是“押”字。宋代官文書需要經過任責官員畫押後方能生效,各官員的畫押難以模仿,於是抄錄者便以“押”字代替。
第三類是任責官員未能簽押的特殊情況說明,包括假、闕、免書、分書、都督、督視、奉使、未上。假與闕不難理解,假表示該官員正在休假,闕則意味該官職當時並未除人。後六種比較少見,據筆者考察,免書當指“免簽書”,都督、督視、奉使是指中央朝官帶相應的職銜出外任職,未上則是已除授而未到任。至於分書,徐謂禮文書中僅一例,筆者推測其涵義應與“免書”類似。下文即對這後六種較少見的簽押附注詞略作考釋。
二 免書: 常程文字,特免簽書
“免書”只出現在徐謂禮文書中的錄白告身部分,共十一次。這些免書的官員級別,均爲宰相以及位居宰相之上的平章軍國重事。

此外,元人陸文圭在《跋黃子高先(黃待聘)誥·再跋》中曾提到:“後五十年,至淳熙間,選人敕黃左右相皆免書,不知始於何人建明,當考。”*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一〇《跋黃子高先誥·再跋》,《叢書集成續編》,108册,上海書店,1994年,頁566。可惜未見實例。
至於分書,徐謂禮文書中僅出現一例,即錄白告身第三則《紹定二年(1229)七月二十六日轉宣義郎告》,其第7行爲“參知政事臣(葛)洪 分書”。宋代官文書中未見同例。該告身中還有“少師右丞相魯國公臣(史)彌遠 免書”的簽押,參知政事葛洪之“分書”與右丞相史彌遠之“免書”應是同種性質的附注,此處“分書”内涵應與“免書”類似。在《宋會要輯稿》職官·官告院部分中出現的兩處“分書”,可爲旁證。《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七一載:
孝宗隆興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官告院言:“契勘本院應出給功賞轉官等告命,宰執、侍從、左司都事郎,官告院官依昨出給空名官告例代行簽書,續承指揮除宰執分書與院官親書外,其餘官並代書。竊緣賞告代書數多,又恐日後無以稽考,欲乞將大使臣修武郎以上官親書吏部尚書、小使臣從義郎以下親書吏部侍郎外,其餘官並乞代書施行。”從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七一,頁3359上。
《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七三另載:“淳熙元年六月七日:
詔“諸軍功賞轉官告命,令依舊簽書宰執、侍從等官,隆興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指揮更不施行。”以中書、門下省言“諸軍功賞轉官告命昨因擁并,除力分書外,餘並代書,恐無所稽考”,故有是命。*《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七三,頁3361上。
《宋會要輯稿》這兩條記載涉及諸軍功賞轉官等告命中宰執的簽書問題,隆興元年(1163)官告院上言中提到當時“除宰執分書與院官親書外,其餘官並代書”,而淳熙元年(1174)六月七日詔令“依舊簽書宰執、侍從等官”,說明宰執之前是不用簽書的,則上文“宰執分書”中“分書”應是“免書”之意,即免簽書。淳熙元年新詔令的發佈背景是中書、門下省上言此類告身“除力分書外,餘並代書,恐無所稽考”,此“力分書”也應該與前詔中的分書意思一致。
三 都督、督視、奉使: 南宋宰執出督軍政
在徐謂禮文書中,附注詞“都督”共出現三次,分別是錄白告身第八則《嘉熙四年(1240)正月十一日轉奉議郎告》第6行“右丞相臣嵩之 都督”、錄白敕黃第四則《嘉熙三年四月 日差主管官告院牒》第8行“右丞相 都督”以及錄白敕黃第五則《嘉熙三年八月 日添差通判建昌軍牒》第11行“右丞相 都督”。這三例中,都督均是時任右丞相的史嵩之的簽押附注詞。據《玉海》記載:“嘉熙二年二月辛卯,史嵩之以參政督視京湖、江西。三年正月癸酉,爲右相,都督兩淮、京湖。二月丙寅,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四年四月癸卯,結局。”*王應麟《玉海》卷一三二,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1987年,頁2440下。徐謂禮這三份告身、敕黃簽發的時間,正好是史嵩之以右丞相都督在外,無法親自簽押,故以附注詞“都督”說明。
“督視”亦出現三次,分別是錄白告身第十則《淳祐七年(1247)十月四日轉朝請郎告》第6行“樞密使兼參知政事臣葵 督視”、第17行“樞密使兼參知政事臣趙葵 督視”以及錄白敕黃第十則《淳祐八年二月 日差權知信州牒》第11行“樞密使兼參知政事趙 督視”。這三例中,督視均是時任樞密使兼參知政事趙葵的簽押附注詞。與史嵩之都督類似,當時趙葵也是督視在外。《宋史·理宗紀三》載: 淳祐七年四月辛丑“趙葵爲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甲辰,趙葵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應軍行調度並聽便宜行事”。*《宋史》卷四三,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37。《景定建康志》載:“淳祐七年六月,趙葵開督視府,省制置司。淳祐九年正月,督府結局,復沿江制置司。”*馬光祖修,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二五,《宋元方志叢刊》(2),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0年,頁1735上。淳祐七年四月,趙葵被命以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六月開督視府,到淳祐九年正月督府結局。徐謂禮這三份告身、敕黃恰好是在趙葵督視在外時簽發,故而以“督視”附注說明。
“奉使”僅出現一次,即錄白印紙第七十則《淳祐七年十月 日將作監主簿在任歷過月日》第31行“奉議郎新除宗正丞兼權郎官督視行府參議官方 奉使”。此人當爲方岳。據《南宋館閣續錄》卷八“秘書郎·淳祐以後”載:“方岳字巨山,貫新安,習《周禮》,壬辰進士。(淳祐)七年四月以宗學博士除秘書郎,是月除宗正丞兼督視行府參議官。”*《南宋館閣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306。元人洪焱祖所撰《方吏部岳傳》亦云淳祐七年,方岳“除秘書郎,方掃革省中舊弊,適趙葵以元樞出督,辟充參議官,遂以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在行”。*《新安文獻志》卷七九,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頁1934。可見,淳祐七年十月,方岳作爲權工部郎官,他本該在徐謂禮任將作監主簿的在任歷過印紙上簽押,但當時他受趙葵辟差,擔任督視行府參議官,奉使在外,無法簽押,故以“奉使”二字附注說明。
南宋常以宰執出督軍政,以便統和一方之軍事勢力。朝中官文書雖保留他們的銜名,但因本人任職在外,無法簽押,故附注說明。在高宗、孝宗兩朝的文書中,常是附注“出使”二字。如陸文圭在《跋黃子高先誥》中提到: 去年(指紹興二年)八月,“孟庾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移屯金陵。今誥中所書‘參知政事出使’……此也”。*《牆東類稿》卷一〇《跋黃子高先誥》,頁566。又,《嘉惠廟額牒》(紹興二年十一月)與《靈濟廟龍母牒》(紹興三年八月)的簽押部分均有“參知政事孟 出使”的字樣,此參知政事孟即孟庾。*《嘉惠廟額牒》,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43),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0;《靈濟廟龍母牒》,見繆荃孫等《江蘇金石記》卷一五,《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13),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頁9820上。在《宋陳少陽先生文集》附錄的《加贈陳東朝請郎誥》(乾道七年)中,時任四川宣撫使的參知政事王炎銜名下也是附注“出使”二字。*陳東《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七附錄《加贈陳東朝請郎誥》,《宋集珍本叢刊》(39),頁168。在徐謂禮文書中,至晚到理宗嘉熙時,則是注明“都督”、“督視”,以兼帶之具體官名附注。
四 未上: 淳祐間政局之變動
徐謂禮文書中“未上”共出現七次,分別是: 錄白告身第四則《淳祐五年正月十九日轉承議郎告》第5行“右丞相臣(杜)範 未上”,第6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臣(游)佀未上”,第16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臣游佀 未上”,第23行“吏部侍郎(王)伯大 未上”;第十則《淳祐七年十月四日轉朝請郎告》第13行“郎官臣鄭逢臣 未上”;錄白印紙第六十五則《淳祐七年三月 日行將作監簿到任》第18行“朝奉郎新除郎官陳 未上”;第七十則《淳祐七年十月 日將作監主簿在任歷過月日》第30行“朝散郎新除郎官曹 未上”。鄭逢臣與後兩位只得其姓的郎官均事迹無徵,而杜範、游佀、王伯大因仕宦顯著,史籍多有記載。
所謂“未上”,是指該官員已授官而未到任。下面即以錄白告身第四則《淳祐五年正月十九日轉承議郎告》第5行“右丞相臣(杜)範 未上”爲例加以驗證。根據該告身第12行所載,“右丞相臣(杜)範 未上”的簽押時間應是淳祐四年十二月,具體日期不明。據《宋史·理宗紀三》記載: 淳祐四年“十二月庚午(四日),以范鍾爲左丞相兼樞密使,杜範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五年春正月丙午(十日),“杜範辭免右丞相,不允”。*《宋史》卷四三,頁831,832。又據《戊辰修史傳·丞相杜範》所載,杜範薨於淳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爲相纔八十日。*黃震《戊辰修史傳》,《宋代傳記資料叢刊》(2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頁41。則杜範正式接任右丞相必在淳祐五年,淳祐四年十二月時杜範已授右丞相而尚未到任,故在徐謂禮轉承議郎的告身中附注爲“未上”。
關於簽押附注詞“未上”,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八月朱巨川轉朝議郎告身中即有。*《金石萃編》卷一〇二《顏魯公書朱巨川告身》,頁214下。而石刻史料中宋代官文書簽押中附注“未上”的還有數例。如《宋吴芾賜謚敕牒》中列有“新除侍郎朱 未上”;*黃瑞《台州金石錄》(3)卷七《宋吴芾賜謚敕牒》,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1982年,葉27B。《宋理宗賜繼一處士告詞》官告院官員簽押中則有“員外郎□自然 未上”。*《台州金石錄》(4)卷一〇《宋理宗賜繼一處士告詞》,葉2B。又,崔與之端平二年(1235)拜參知政事,三年拜右丞相,皆力辭不赴任。碑刻中所保留的這期間的多份敕牒都在其銜名下附注“未上”二字,如《宋封太學靈通廟敕牒碑》、《宋永靈廟加封顯佑通應侯敕牒碑》、《永靈廟協惠夫人加封昭慶敕牒碑》。*《宋封太學靈通廟敕牒碑》,見阮元《兩浙金石志》卷一一,《續修四庫全書》,911册,頁72下;《宋永靈廟加封顯佑通應侯敕牒碑》,頁74上。該敕牒中尚有官告院“主事徐元未上”的記載;《永靈廟協惠夫人加封昭慶敕牒碑》,見陸心源《吴興金石記》卷一一,《續修四庫全書》,911册,頁569下,570下。陸心源在跋文中對“未上”注解云“與之始終未到右丞相之任,故云未上也”,甚確。
宋人仕宦經歷中“未上”是相當常見的,被授予差遣或職事官,常需數月甚至數年纔到任,在此期間,又常改除他官或因故(如辭免、丁憂等)没有上任。而在徐謂禮《淳祐五年正月十九日轉承議郎告》中,竟出現三位重臣(宰相、執政、吏部侍郎)同時“未上”的特殊情況,其政治背景則是當時朝中正進行大規模的高層人事調動。史嵩之在淳祐元年至四年期間獨相四年,因其主和議,不爲當時聲勢浩大之理學官員所喜。*何忠禮《南宋全史(二)·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15—116。淳祐四年九月史嵩之丁父憂,不久即起復,引發了大規模的學潮,三學生(太學、武學、宗學)及京學生皆上書論史嵩之不當起復。*《宋史》卷四一四《史嵩之傳》,頁12425—12426。理宗雖諭嵩之赴闕,但“嵩之控詞,不允”,爲主持朝中政局,“十一月辛丑,詔趣游佀、杜範赴闕。……庚戌,詔陳韡、李性傳赴闕。十二月庚午,以范鍾爲左丞相兼樞密使,杜範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游佀知樞密院事,劉伯正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宋史》卷四三《理宗紀三》,頁831。而王伯大亦在“淳祐四年,召至闕,授權吏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尋爲吏部侍郎仍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宋史》卷四二〇《王伯大傳》,頁12569。因政局之變動,於是便出現了三位重臣同時都“未上”的情況。未上任官員的銜名仍列入官文書的簽押之中,宋代文書行政重名不重實亦可見一斑。
(本文作者係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