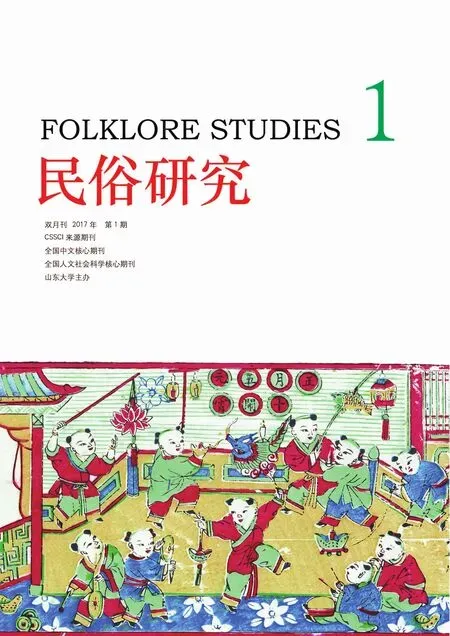《苗族史诗》中民俗事象翻译的民族志阐释
王治国
《苗族史诗》中民俗事象翻译的民族志阐释
王治国
《苗族史诗》以口传文本的形式在苗族跨地域、跨方言的文化共同体内传播。史诗承载着苗族远古历史的文化记忆,其中所包含的民俗事象铸就了苗族独特的文化世界。苗汉英三语对照、民族志深度翻译、置换补偿为史诗民俗事象翻译提供了可能途径与可行策略。只有将口承人、接受者和具体说唱场景构成的生态文化环境三者同时呈现和保存,活态史诗才能从文化标本的保护过渡到文化现实的动态传播。
苗族史诗;民俗事象;民族志;置换补偿
苗族是聚居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与历史上其他无文字的民族一样,文化传承以口耳相传为主,拥有特别丰富的口传文化。其中《苗族史诗》,又称“苗族古歌”和“古史歌”,是苗族最古老的口头语言艺术形式,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以民族身份命名的南方创世史诗。史诗记载了苗族起源、古代社会状况和风俗人情,是苗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具有很高的历史、民族、语言、民俗研究价值。不仅如此,史诗以问答式的盘歌体,以及古今对照的吟唱方式,将远古的记忆与现在的生活经验相互映照,形成了苗族古歌所特有的表达形式。作为苗族最古老的口头语言艺术形式,史诗承载着苗族远古历史的文化记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符号铸就了苗族独特的文化世界。史诗经历了口头传承和文本传播阶段,形成了跨方言、跨地域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目前,苗族史诗正经历着由口传文本向书面文本的过渡,并出现了通过英文译本对外传播的新气象。学术界对苗族史诗的流传地区、史诗生成、演述方式、押调韵律等都进行了相应的介绍和论述,然而,鲜有成果介绍研究史诗的外译与传播。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华文化“走出去”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下,对《苗族史诗》的民俗事象翻译与传播展开研究,成为了民俗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由歌而诗:苗族史诗的翻译梳理
史诗从民间口头传唱到现代书面文本传播,经历了数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据吴一文、覃东平考证,至迟在唐代(618-907)以前,苗族史诗主体部分业已定型,但一直未为外界所知。*吴一文、覃东平:《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8页。苗族史诗的最早记录是1896年由英国传教士克拉克与苗族人潘寿山合作记载的《洪水滔天》《兄妹结婚》和《开天辟地》中的一些史诗篇章。*李炳泽:《口传诗歌中的非口语问题——苗族古歌的语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7页。史诗最早的翻译是上世纪40年代陈国钧记录的三则苗族“人祖神话”,其中第三则是488句的汉译诗体史诗,是现代“洪水滔天”“兄弟分居”的合编,当属最早的苗族史诗诗体译文。*吴泽霖、陈国钧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11-118页。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中央民族大学马学良教授率队进入黔东南苗族地区,开始对苗族史诗资料进行第一次系统搜集,并指导随后的翻译、整理和研究工作。1956年马学良和苗族学者邰昌厚、今旦共同刊文《关于苗族古歌》,对史诗的分类、内容、篇章构成与逻辑关系、五言体句式、格律以及歌花对唱方式等作了最早且比较全面的论述和介绍。*吴一文、今旦:《苗族史诗通解》,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唐春芳较早地对苗族史诗进行了翻译和研究。1958年他在《苗族古歌》一文中将苗族古歌分成叙述天地来源、万物来源、人类来源与民族迁徙、反映古代社会历史变革、古代生活、古人事迹、古代发明等七类古歌。*唐春芳:《苗族古歌》,《民间文学资料》第四集,中国作协贵州分会筹备组编印,1958年,第4页。对史诗作了内容上的分类,但还没有将史诗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和整体来进行研究。1978年,田兵主编的《苗族古歌》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也掀起了研究史诗的热潮。该书前言写道:苗族古歌习惯上呼为“古歌”,因为苗族人民把它看成历史,所以也称为“古史歌”。同时该书对苗族史诗的构成,五言、盘歌对唱、押调等进行了介绍,指出:“这些古歌,在研究苗族族源、风俗习惯、古代社会、迁徙等都有一定用处的。它的价值,还可能远远超过文学价值。”*田兵:《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前言》第1-11页。
1983年,马学良、今旦又出版了《苗族史诗》。马学良认为苗族史诗是“苗族古代文化的光辉结晶”,“堪称古代苗族的百科全书”。苗族史诗在学术界的汉语译名也是从马学良先生开始的:“如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苗族群众向来以歌唱的形式来颂扬祖先的丰功伟绩,因此过去习惯地称之为《古歌》或《古史歌》。这些诗歌详尽地记载了苗族族源,古代社会状况及风俗人情等等,苗族人民把这些诗歌看成自己形象的历史,所以我们认为称之为《苗族史诗》更为恰当。”*马学良、今旦译注:《苗族史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代序》第1-12页。
新世纪以来的2012年,吴一文先生在总结前人及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对苗族史诗有过如下界定:
苗族古歌又称苗族史诗,黔东方言苗语称为“HxakLulHxakGhot(古歌老歌)”、“HxakLul(古歌)”、“HxakGhot(老歌)”或“HxakHlieb(大歌)”等。它是流传于苗语黔东方言区,以五言为基本句式,以穿插有歌花的问答式对唱(盘歌)为主要演唱形式,叙述开天辟地、铸日造月、人类万物产生、洪水滔天、民族迁徙等内容,内部篇章之间有着紧密逻辑联系,具备史诗性质的苗族民间“活形态”押调口头传统。*吴一文:《苗族古歌的演唱方式》,《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新中国对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高度重视,陆续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开展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活动。这一时期,除了由苗族地区的学者搜集以前记录的一些歌谣,并将其翻译为汉语外,还有其他民族地区学者和苗族学者合作进行的记录和翻译,开始了为编写民族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史而有计划地记录和翻译的学术活动。期间,经过各族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悉心搜集,还发现了不少异文,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注意。
正是基于史诗的文本传播,国外同行对《苗族史诗》开始了翻译研究活动。早在1988年,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就发表了HxakHmub:AnAntiphonalEpicofTheMiaoofSoutheastGuizhou,China对苗族史诗进行了翻译研究。2006年,马克将马学良、今旦的《苗族史诗》翻译为英文并出版,书名为ButterflyMother:Miao(Hmong)CreationEpicsfromGuizhou,China。两部译作均译作“epic”,前者重点突出其演述形式:对唱史诗;后者重点突出其性质:创世史诗。随后,马克又继续与国内苗族学者吴一方合作将《苗族史诗》翻译为英语。最新的英译本是由贵州民族出版社于2012年9月正式出版的《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全书约80万字,原文是吴一文的原著《苗族古歌通解》。苗、汉文译注部分由今旦、吴一文负责,英文译注由Mark Bender教授和吴一方、葛融合作翻译。*吴一文、今旦汉译,[美]马克·本德尔、吴一方、[美]葛融英译:《苗族史诗苗文·汉文·英文对照》,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年。译本贵在中外译者合作翻译,而且吴一方是唯一通晓苗、汉、英文者,开创了本土人士与海外学者通力合作、共同翻译的合作翻译模式,在史诗海外传播实践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多语对照的民族志翻译
译本的合作者之一吴一方曾撰文就苗族史诗的英译作了介绍,探讨了在苗、汉、英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苗族诗歌跨文化传译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吴一方:《苗族口传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传译——〈苗族史诗〉三语翻译刍论》,《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下文重点是就英文译注本的三语对照模式、民族志翻译策略、民俗事象置换补偿翻译方法展开探讨,以期对其他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翻译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一)多语对照:苗汉译注、英文译注
三语对照是英文译注本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外译中仅有的多语对照翻译。苗汉英三语对照本内容包括:16页提供丰富苗族文化知识的民族志图片、三语对照的注解、三语对照目录、汉英双语前言、汉英双语英译者自序、三语对照序歌、金银歌、古枫歌、蝴蝶歌、洪水滔天、溯河西迁与附录等,共729页,近80万字。全书全部按照[苗文·汉文·英文对照]排列,并且以苗、汉、英三种语言顺序排列。书名为三种语言对照:第一行为:苗文Hxak Hlieb;第二行为汉语苗族史诗;第三行为英语Hmong Oral Epics。编译者署名均以三语对照形式出现:第一部分为苗文,共两行,其中第一行:Qet Hfaid/ Wenf Jenb, Jenb Dangk,第二行Hfaid Leix Yenb/ Xongt Mal, Bangx Jenb,Gof Yongf;第二部分为汉语,共两行,其中第一行:苗汉译注/吴一文 今旦,第二行:英文译注/马克·本德尔 吴一方 葛融;第三部分为英语,相应也为两行,其中第一行:Han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and Notes by Wu Yiwen and Jin Dan,第二行:English Translation by Mark Bender, with Wu Yifang and Levi Gibbs。
此外,前言和英译者自序,每一部分歌后,附有本部分注释,汉语在左侧,英语在右侧,又形成三语对照的布局格式。目录也是三语对照,其中附录中包括,《苗族史诗歌骨歌花对唱实例》《半个世纪的耕耘(代后记)》和《苗文声韵母表》。兹引述史诗中开篇序歌,以观其貌。

可见,苗族史诗以五言为主,讲究押调,即每句歌词末字声调相同或相近,构成苗语诗歌的韵律美。汉译诗歌为七言,尽量讲究平仄和押韵,比苗语原文多了两个字,这样既符合汉语民间诗歌多为七言的特点,又拓展了翻译阐释空间以更加完整地表达原诗内容。英译文诗句没有统一的字数要求,一般是由五个或七个单词构成,通过音步来实现诗歌的韵律美。实际上,不强求字数的统一是英文诗歌的自身特点之一。尽管汉英译文无法再现由规范的押调和整齐的五言形成的史诗独特的艺术美感,但是译者还是尽可能顺应汉、英两种语言各自的诗歌韵律,力求传达苗族史诗的原生态艺术特色。
(二)深度翻译:人类学民族志通解
《苗族史诗》三语对照本中附有大量的注释,呈现出人类学民族志特有的学术气息。这些注释本身就是对苗族民俗事象的生动注解,为读者展示出一幅幅活态的古代苗族生活全景图。对于苗族民俗事象的注释和注解,在史诗中随处可见。上述诗行中就有八处注解。苗族文化是活态的,根本还在民间,需要研究者拥有搜集整理的经验,深入生活切身体悟。史诗的注解者和翻译者都是多年来持续关注、深入田野调查的苗族学者和美国人类学家。对史诗的注解是“思路开阔,苗典与汉典,苗俗与汉俗,古与今,物与典,歌与俗都能融会贯通”。*韦文扬:《苗族史诗观止——读吴一文、今旦〈苗族史诗通解〉》,《贵阳文史》2015年第2期。他们熟谙苗族史诗的原生态文化,通过在原生态土地上不断地体悟、理解,对苗族文化进行了深度阐释,从而使该译注本呈现出人类学民族志翻译的独特视角。
所谓民族志翻译是指民族志学者从事的翻译工作。通常采取两步走的工作模式:首先是将当地人的口头话语口译成自己民族志书写的语言;其次是将口译本加以改编成为书面文本,或是口头资料文本化以后的书面文本,以供在主流文化中进行消费。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借鉴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深度描写”说,提出“深度翻译”概念,并著专文加以阐释。
所谓深度翻译是指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按语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尽力去重构源语文本产生时的历史氛围,以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段峰:《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显然,作为一种翻译方法,深度翻译通过在译文本中列举各种注释和评注,尽力重构源语文本产生时的历史氛围,还原源语生成时的话语历史背景,以便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文化,并由此产生对它族文化的应有尊敬,即便该文化是弱小民族的文化。关于在书写文化中进行口头艺术文本记录和翻译的观点和方法,如杨利慧所言:
民族志诗学实际上是表演理论大阵营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中主要探讨口头文本转写和翻译方法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的学术追求,不仅仅是为了分析和阐释口头文本,而且也在于使它们能够经由文字的转写和翻译之后仍然能直接展示和把握口头表演的艺术性,即在书面写定的口头文本中完整地再现文本所具有的表演特性。*杨利慧:《民族志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
民族志诗学在努力寻求一种更好地翻译和转写口头诗歌的手段,这一点就与当前《苗族史诗》史诗英译相契合。正如深度描写和深度翻译所阐释的一样,史诗用较大篇幅提供了诸如题解、古语词解释、人物注解、古今地名考注、动植物注解、重要风俗解释、句子解意、段意解读、异文对比、关系词考证等各种注释,凡3000多条。如史诗《制天造地》一节中关于五倍子的注释:五倍子木来撑地:苗族常用刺楸树、五倍子树、麻栗、芭茅等的根、叶、果等混合在一起,挂在门上以驱鬼避邪。五倍子树在苗族传统观念中被视为神木,在大多数与敬鬼神有关的活动中都少不了,如卦卜、敬尕哈神时的幡杆等都须用。译注者进行了深度翻译:The Hmong Language for this line is “Ghab nix pab nil nangl”. It refers to various types of leaves, cogon grass roots, and gallnut of the Chinese gallnut (Rhuschinensis) tree, known aspabin Hmong andwubeiziin Han; prickly castor-oil tree (Kalopanax), known asdetbeltongdin Hmong; saw-tooth oak (Querusacutissima), known asdetyelin Hmong; and cogon grass are bundled and hung over doorways of Hmong homes to ward off negative spiritual forces. Chinese gallnut is regarded as a numinous tree that links the human world with that of the spirits. The tree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virtually all rites honoring the spirits. Its wood is used to make blocks cast in divination rites. In offering such as to the spirit Ghab Hvib, the poles used to support streamers are also made of gallnut.*吴一文、今旦汉译,[美]马克·本德尔、吴一方、[美]葛融英译:《苗族史诗苗文·汉文·英文对照》,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15-116页。
通读译注本发现,无论是民俗事象还是文化典故,通解都正本溯源,逐字逐句考察词语的始源与流变,力求打通古代与现代、辨析不同方言间的音意之别,为读者欣赏史诗诗歌、体验史诗口语押调与韵律变化清除各种障碍。译注本为此而进行的文化人类学深度描写,旨在达到苗、汉、英三语背后文化背景的阐释通解,不愧为人类学深度描写的典型译注。
(三)置换补偿:民俗事象的英译
史诗包含着大量的苗族民俗事象,这些事象在汉族文化和英语文化中有的彼此皆有,但更多的是此有彼无或是此无彼有,形成单项缺失。汉英译注中采用了同类置换、异类补偿,通过意译和直译加注的方式,以期让英文读者对苗族文化有所了解。另外,史诗翻译涉及到语言转换、民俗事象传播、读者期待等相关问题,因此译注本适当地在译文中保留了苗文,以保持史诗语言及文化内涵的原汁原味,让读者更好地体会其中意味。对于大多数的民俗事象词汇,译文则是采用了补偿策略。
典型的民俗事象如“芦笙”“十二地支”,这类苗汉皆有,而英语缺失。在《洪水滔天》“leik hxongb gix jus jil, Xit baib max bas bil”(一副芦笙剩一根,人手一份也难分)一节中,英译为“a single gix pipe left from an ensemble. That can’t be divided among many players”,保留“芦笙”的苗文“gix”,再加上种属类词“pipe”,既限定了“gix”的语义范畴,又传达了苗族演唱习俗:芦笙乐手或成对演奏或多人对奏。同理,“十二地支”苗汉文化皆有,而英语文化中缺失这一事象。英译直接将苗文十二地支保留,在地支“Earthly Branch”之前增加各种生肖动物,将十二地支转译为十二生肖,并作了尾注,对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进行阐释。如此译文和注释遥相呼应,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苗族文化。再如,在《铸日造月》“dail hlieb mais bit Said”(老大的名字叫做子)一节中,英译为“the first was called Said, the rat Earthly Branch”,即保留苗语Said,增加同位语“the rat Earthly Branch”对“Said”进行补充阐释。
对于彼此皆有,但不完全等同的民俗事象词汇,以及此有彼无的民俗事象词汇,英文译注进行了恰当转换,适当补偿。由于民间文本的多重性质,对图像的阐释和理解无法确定,在故事的讲述者和民族志工作者之间会发生改变。如《古枫歌》中“det dod”(一种枫树)一词的理解和阐释,就颇为复杂。在不同史诗讲述者和编辑者的各种版本中,这种树或是被识别为是一种树皮光滑而色浅的树,或是比较粗糙而色深的树,甚至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品种。然而,在已版的史诗中,关于该树的阐释只代表一种树种。译者将其翻译为“枫树”(sweet gum tree)。如果能在随后的增修本中附上枫树详细的照片以及可能的其他树种,增加文化和植物学的解释,则会为类似民俗事象词汇的隐喻阐释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苗族史诗》的通解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志实践,译注者需要了解史诗的文化生态语境,以便翻译时采用多种符号系统进行表征,从而最大化地保持原作品的力量与美。
三、语境再现:民俗事象传播的思考
马克·本德尔作为美国表演理论研究的研究者之一,具备学养的高度和深入民间的深度,他将史诗的文本分析和田野作业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创作中的表演”的重大学术命题。将史诗的创作者,传承者、接受者置于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中进行宏观的综合考察,同时兼顾口传文学翻译中众多因素的各自作用和地位,从多维层面保存史诗民族志文化语境,是马克·本德尔译本为我们带来的重要翻译启示,这对其他民族口传文学的对外传播具有借鉴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在编写民间文学史的学术宗旨下,学者们把不同民间“版本”糅杂在一起进行汉译,史诗的传播媒介发生了嬗变:即从口耳相传的媒介过渡到书面文本媒介,从听觉的聆听过渡到视觉的文本阅读。毋庸置疑,这会扩大史诗的阅读受众群,提高苗族族人的文化保护意识,引发全社会对苗族传统文化的关注,是非常有意义的文学翻译活动,在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甚至在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今天,有学者认为现代媒体的发展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提供了极好的技术支持:“在当今传媒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口述和传媒结合,形成音像多媒体,以大大超越旧时文本的方式扩展时空,并以高度可塑性与文字结合,成为音像字的‘三位一体’。”*朱伟华、刘心一:《活在传媒时代的苗族史诗〈亚鲁王〉》,《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但是也有学者在研究苗族史诗《亚鲁王》文化生态保护问题时指出:
通过多媒体的呈现方式将纸质文本的《亚鲁王》立体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亚鲁王》的存在状态,无论是纸质的文本还是多媒体的影像资料,这都是对一种文化的静态的保存,是一种文化标本的保存,虽然这种行为对保存一种文化现象而言是很有意义的,它甚至是可以让这种文化现象以纸质的或者是音像的方式与人类历史共存,但是,这种记载对苗族史诗的传承而言却意义不大。*何圣伦:《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与苗族史诗的当代传承——以〈亚鲁王〉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前者主张通过文字记录整理苗族口传文献,用现代数字音像技术来收集苗族仪式,以保护日渐消失的文化现象。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而言,经过多媒体档案化数字管理后,成为了活态的文化标本。后者认为经文字记录翻译后,史诗独立于作为叙述者的说唱者和接受者,脱离了史诗咏唱的语境,以纯文本的方式进行文本解读,只是更多地关注了文本内容,脱离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缺少深度的田野考察和活态民间生态环境的保护,变异成为一种作为认识对象的文化标本。
实际上,上述两种观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涉及到口传文化保护的核心宗旨,体现出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符合学科发展的正常认识论逻辑,所以二者是渐次发展、并行不悖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尽管活态史诗抢救整理出来的是一种叙事文本而已,与活在民间的活态史诗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将搜集整理的文本存档,这对于一种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人类社会尝试对即将消失的文化现象所做的最后保护,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和继续保护活态遗产的学术动力。在民族口头传统保护的初级阶段,离不开文字的记载和不同语言间的翻译。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口头传统的传承不只是其文本内容,而是连同其生存的生态文化语境。只有将活态史诗口承人、接受者和具体说唱场景构成的生态文化环境三者同时呈现和保存,才能从文化标本的保护层面过渡到文化现实的活态传播阶段。
作为苗族史诗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以苗、汉、英三语平行对照形式,辅以大量民族志背景知识的通解,为弥补文本整理翻译与生态语境再现之间的隔阂进行了一次异语传播的尝试。翻译与研究并重的深度翻译,值得苗学研究者和翻译界继续给予相应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如何借助于数字媒介、数字化的综合文本将史诗表演的开场白、旁白及观众的赞叹等表演中的生态文化语境通过数字科技以音频、视频、图像等形式传播,应是今后学界共同探讨的学术话题之一。
[责任编辑 龙 圣]
王治国,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基地兼职研究员(天津 30038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域外传播与翻译转换研究”(项目编号:16BYY02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