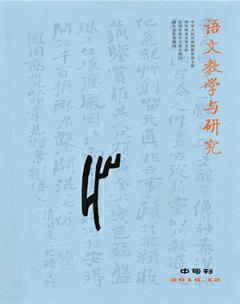语文课堂问题的设置
一堂课,应该教什么,不应该教什么,应该用什么方法教,不应该用什么方法教,得益于教学内容的确定。问题的设计直接体现着所要教授的教学内容,不言而喻,问题是否有“含金量”直接影响着教学内容的合适与否,教学目的的达成与否。如要提高“含金量”,则应足够地重视与全方位地考量问题的设置。
新课标把阅读教学定义为学生,教师,文本三者之间多重对话的过程,课堂模式由传授型模式转为对话型。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课堂对话流于形式、碎片化、空泛化,游戏化的对话充斥于课堂,倍受诟病。伪对话的“泛滥”偏离了语文课堂所追求的“真”。何以“纠偏”,科学、高效的问题设置“当之无愧”成了剔除诟病的关键。
斯滕伯格设计了三种提问策略:第一个是以讲课为基础的,称之为照本宣科式策略;第二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问答式策略;第三种是以训练思维为基础的问答式策略。如何训练思维,“苗头”直指问题的设置。
主问题的设置契合了在思维理论指导下设计问题的要求,把学生的思维与文本内容紧密地粘合在了一起,使课堂对话紧贴文本内容,带动学生深层次地理解文本,避免流于表面的肤浅的课堂教学。学生的发言虽不乏精彩之语,但比较零散,如果能够娴熟地设计出高质量的主问题,关注学生的思维训练,让教学过程至始至终处于思维的“流”中,那么,课堂对话的效率则有望大幅提高。
主问题的设计是教师文本解读功力的彰显,是追求高效课堂实现的保障,是学生学习兴趣提高的关键,是教学方法得以确定的基础。
有论者指出,主问题设计可从“文章的核心句,留白处,语言特色,思想感情,结构脉络方面入手”,也有论者指出可从“文章的标题,关键词句,中心事件,文本类型处入手”。为主问题的设置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抓手”,但了解了“抓手”不代表就具备了“万能钥匙”,主问题的设置要根据所确定的教学内容,所要达成的教学目标而选择恰当的切入点,本文仅以《孔乙己》一文为例来谈谈教学中所应具备的设置主问题的理念。
《孔乙己》是一幕悲剧,然而,文中没有一个“悲”字出现。叶圣陶在1924年5月15日发表在《国文杂志》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孔乙己〉中的一句话》,认为《孔乙己》的主题在于“表现旧式教育的不易发展人的才能,潦倒的读书人的意识和姿态,以及社会对于不幸的人的冷淡——除了随便的当作取笑的资料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关心”。纵观全文,不难发现,一个细节——“笑”贯穿全文。“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这里的笑声,不是一般的描述,而是整篇小说情绪的逻辑起点和整篇小说的结构支点。整篇课文中,笑声伴随着孔乙己的活动全程,孔乙己在人们的笑声中迂腐地走来,又在人们的笑声中难堪地离去,最后,在人们的笑声中孤寂悄然地死去。小说立意的焦点,显然就在这种“笑”上。因此,笔者以“笑”为切入点,统领全文,进行主问题的设置,即“谁在笑?笑什么?为什么要笑?这些笑又说明了什么?”
一、笑者为谁?
阅读课文,不难找出这样的两句话,“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甚至“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丁举人的狂笑,掌柜的奸笑,众人的哄笑、取笑,孩子们凑热闹的笑以及我附和着的笑。总之,所有喝酒的人都看着他笑。
二、笑什么?为何要笑?
1.孔乙己的可笑首先在于他是一个“站着喝酒的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既穿长衫,又站着喝酒。
一个被时代抛弃了的穷困潦倒的书生,就在这站着的与坐着的夹缝里艰难地生存着,作为这矛盾结合体的孔乙己一出现在人们中间,自然就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
2.孔乙己的可笑还在于他的言谈举止,热衷于科举的孔乙己,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那些喝酒的嘲笑他又偷了书,又挨了打,而且有人指出是亲眼所见,“吊着打”的。这是确确凿凿的事实。
而孔乙己否认的态度又是十分坚决的,“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但是,否认的论据却是十分薄弱的,甚至是不能成立的:“窃书不能算偷”。显而易见,这不过是把偷窃的概念从白话变成了文言,并没有改变偷窃的实质。
3.教小伙计识字,孔乙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回”字的四种写法。
但他所教的却是毫无用处的“回”字的四种写法,也无怨小伙计表现出鄙夷的笑。
4.即使对孩子们讲话,孔乙己也是满口的之乎者也,“多乎哉,不多也”。
文白夹杂,语体不辩,也无怨孩子们都笑出了声。
5.“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以及后文的“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
从“排”时的得意炫耀到“摸”时的倾其所有,他骨子里的穷酸相就跃然纸上。
三、“笑”说明了什么?
也即是鲁迅在这笑里挖掘了怎样深刻的含义呢?
从掌柜的冷漠无情的笑,到长衫主顾的轻蔑的笑,再到短衣帮的取笑,嘲笑,哄笑,孩子们凑热闹的笑,从上层到下层构成一个鲁迅惯用的小说结构模式,即看与被看的模式,不单是《孔乙己》存在着一群看客,在鲁迅的其他小说里如《明天》里的单四嫂子,《祝福》里的祥林嫂,《阿Q正传》里的阿Q,《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他们周围都有一群看客存在着,这些看客是一群“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无时无刻地制造着吃人的悲剧。我们从这些笑声中听出了看客们的冷漠,无情与精神麻木,同时,也从侧面认识到了科举的罪恶。
牵一“笑”字而动全文,即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所揭示的社会意义。四个问题的设置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由表到里。
传统的文学理论形成了传统的文学解读模式: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作品内容——艺术特色。这一模式被应用到文学教学中,直接转变成为机械的程序化模式:时代——作者——社会内容——艺术特点。这一固定的程序化模式长期“统领”语文教学实践,根深蒂固于语文教师的心目中,已然形成了教学思维定势,但是,若教学中一味地循着固定模式进行教学消解的不仅仅是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更是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忌讳一种模式一统天下,当然,主问题的设置能否适合于每一篇课文,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而定。而语文教师需要逐渐培养“窥一斑而知全貌”的能力,走出长期“统治”语文教学的固化模式,着力于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美】斯滕伯格.《思维教学》[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2]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2页。
[3]余虹.《文学作品解读与教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符晓云,山西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