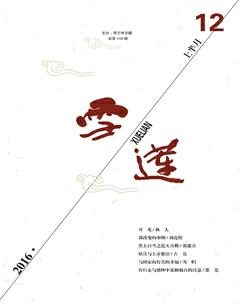姑且与上帝絮语
古岳
我从未像2015年冬天这样,感觉到自己与死神离得这么近,它仿佛时刻都在我身边。这倒并不是因为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而是因为父亲每隔一两天都会谈到死亡。而且,每次谈到都是极其渴望的样子,仿佛死神已经在他身边等候多时,他不想再耽误它的时间和行程。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环顾左右,好像死神就坐在那里,或者,就站在我身旁,向父亲张开双臂,正等待他起身离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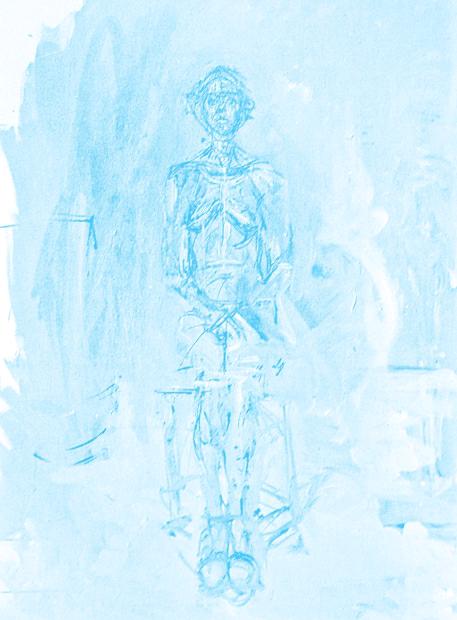
回想起来,在我有限的人生旅程中,至少也有一两次曾与死神擦肩而过,其中一次,我甚至以为自己肯定是要在那个时间和地点了。那是20年前的事,我深入一片森林去采访,因为遭遇风雨,在森林里迷路,本想抄近道绕过一座山头回到住的地方——我事先已经在林区找好了一个可以住下来过夜的房间——可是没想到那个山头到处都是悬崖峭壁,根本无法翻越。便在深夜的密林中不断左突右拐,而雨却一直在倾盆而下。直到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之后,才决定在山上宿营。好在我还有一位同伴,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他是我的一个姑祖父,在去往这片森林的途中,我与他巧遇,觉得这是缘分,便相伴而行。那是一个夏天,此前我从未想到过高原夏天的雨夜会那么寒冷。因为衣衫单薄,当雨水不停地浇到身上时,仿佛一下就渗进了骨髓里,奇寒无比。那时,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像一缕微弱的火苗,随时都有可能被浇灭。虽然,我们最终燃起了一堆篝火温暖着自己越来越冰凉的身体,但是,过了午夜之后,我们已经无法继续找到可以燃烧的柴火,而雨却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那个时候,我无数次想到过,我们肯定要死在那里了。那个时候,我感觉死神就站在那雨夜里,就在我们身边,向我们微笑,仿佛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它的脸庞。假如那雨,再下大一点点,或者再持续个把时辰,我就不会还坐在这里写这些文字了。也许,那一次死神只是跟我们开了个玩笑,而并非真跟我们过不去,或者,它只是碰巧路经那片森林也说不定。总之,雨并没有下得更大,持续的时间也没有更长,所以,次日早晨,我们才得以活着走出了那片森林。所谓命不该绝,这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
即便有过这种与死神非常切近的体验,与这个冬天刻骨铭心的记忆相比,那甚至算不上是一种记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个冬天,每时每刻,我都处在一种毛骨悚然的状态,好像一转身投足之间就可能与死神撞个满怀。我甚至设想过,假如我被它撞倒在地,自己还能不能重新站起身来,接着还进一步设想,假如我再也爬不起来,那是否就意味着已经死亡了呢?
有一次在飞机上,我正在读尼尔·唐纳德·沃尔什的《与神对话》。我旁边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衣着朴素,感觉像是一位某家工厂的老工人。他歪过头来,看了一眼封面,用浓郁的东北口音自言自语:《与上帝唠嗑》,我知道,这是他对这本书封面上英文书名的另一种译法,不禁侧目。后来,我好像问过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依稀记得,他是一位地质工程师什么的,又或者是别的什么工程师,比如灵魂工程师。后来,他没再说什么,因为我什么也没问。后来想起那一幕时,我总觉得他曾经跟上帝唠过嗑,说不定,他还是一位神的使者。从表面看,一位圣徒可能更像是一个乞丐,他们的高贵和圣洁永远隐藏在灵魂深处。于是,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多问几个问题。可是,我与他已经错过,他已隐于茫茫人海,无从寻觅。我与他的短暂邂逅永远留在了八千米的高空。这便是缘分。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在接受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的采访时,曾谈到过《与神对话》的缘起。1992年前后,陷入人生谷底的沃尔什愤怒地给上帝写信,问了许多关于他的生活为何如此悲惨的问题。写下问题之后,他听到有个来自右边的声音说:“你真的想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吗?或者只是在发泄而已?” 沃尔什转过头,却看不到人影。他感到脑海中充满了那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决定将它们写出来。因为母亲的离去,因为病危的父亲总是在谈论死亡,在这个冬天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起那次航班上的那一幕,好像受到了某种启示,觉得自己应该写一部与死神对话的作品,甚至也学着沃尔什的样子拟好了很多要向死神提出的问题。
比如,一个人是否可以自己决定死亡的时间和地点?一个人是否可以在死亡时自己选择有谁陪伴在身边?一个人临近死亡的时候,能否做到从容愉快地离去?如果能或不能,那么又是谁决定着这个结果?谁给他(或它)赋予了这样一种权利?还有,一个人的死亡是人生的彻底结束还是一次全新旅程的再次开始?如果是再次开始,那么他会去往哪里?往生何处?谁将决定他的去向?他是否有自己选择的余地?如果有,自己该做什么样的抉择?还有,父亲问过我的那些问题:究竟有没有死亡这回事?要是有,为什么一个人想死的时候却死不了呢?……等等,等等。
可是,无论是我的右边还是左边,都没有一个声音说:“你真的想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吗?或者只是在发泄而已?”——也许,我应该对这句话的后半句稍稍做些改动,因为,我并不是要发泄什么,而是在追问。而后,我转过头去——不停地转过头去,也没有看到人影,我的脑海中更没有充满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惶恐而疑惑。也许死神与神或者上帝还是有所区别,如果愿意,神或者上帝有时候可能会跟人对话(或唠嗑),而死神不会,它沉默不语。虽然,有很多时候,我好像确曾听到过死神在耳边絮语的声音,但那不是真的声音,它是以沉默的方式传递声音的。于无声处才有死神的絮语。它仿佛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而我却什么也听不明白。
很多人临近死亡的那一刻,某个意想不到的人恰巧悄然来到他的身边,而很多本该在身边的人却都离开了,像是被谁给支开了一样。我曾祖母临走之前的那个午后,她一直在我家院墙根里剥蚕豆。回到老宅租屋之后,晚饭后,很多人都在身边陪着说话,看她好好地在炕上端坐着,像是有点困了,就让她早点睡,便都离开了。可是,她并没有睡,她像是在等一个人。这时,我在外地工作的伯父回来了,在自己家稍事休息之后,等不得天亮就想去看看奶奶。他走近我曾祖母的房间时,她还那么坐着,看到他回来了,很高兴,说了几句话。过了一会儿,伯父看见我曾祖母已经闭上双眼,他还以为她睡着了,想把她喊醒来,让她睡。可是,她没有反应。把声音放大点了,再喊,还是没有反应。她已经离开了。我母亲弥留之际,我几乎日夜守护在身边,须臾不曾离开。那天清晨,我看她睡着了,呼吸均匀,便回到自己屋里眯了一会儿。离开她身边之前,我还摸了摸她的脉象,很微弱,却平稳。我就对几个妹妹说,母亲没事儿,让她们也眯一会儿。可是,没几分钟,我听见动静不对,赶紧跑过去时,她老人家已经离开了。我岳母走的时候也这样,那天晚上,在她医院的病床前,我和妻子看到她似乎好多了,连气色也比以往要好一些。她还说了很多话,有一会儿,脸上还挂着微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有微笑过了。便觉得,她不会有事,我就回了一趟家。刚到家,妻子就打电话来,声音不大对劲儿。赶忙跑到医院时,她老人家也已经走了……
不仅是死,生似乎也充满了这种悬念。我老家有一种习俗,一个人出生时,第一个走进家门的人,叫踏生者,说这个人身上的很多习性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新生儿一生的性格。所以,一个孩子降生后,一家人总希望第一个走进家门的人是一个心慈面善之人,而不希望一个口是心非之人,更不希望一个满身坏毛病的人突然闯入。为了慎重起见,有的人家还会在宅门外面煨上一堆火,或者在门上系上一溜儿红布条,谓之忌门,以防不速之客的擅自闯入。而结果往往是,你最不希望到来的那个人总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不期而至,不早也不晚,好像一切都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无法更改。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都具有神秘的仪式感,庄严神圣。
我觉得,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这更像是一种有意的安排。那么,谁在安排着这一切呢?谁可以事先注定这一切?谁在界定生与死的界限?死亡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死亡对生命又意味着什么?死亡之后,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就烟消云散了吗?那么,灵魂呢?灵魂又去了哪里?这又是一连串的问题。虽然,我们谁都清楚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却无法给出答案。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个现象是,一个人死亡之后,其实,他还在那里,很平静,甚至很安详,所不同的只是他已经没有了气息,呼吸停止,脉象消失,心脏也不再跳动。而我们并未看到这些生命的气息去了哪里?它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一下子就那么没有了,消失了,消失在了自己的生命深处,好像那里有一个我们无法感知的秘密通道,通向一个未知的时空。现代医学把这些气息特征的消失确定为正式死亡,可很多从事灵魂工程——科学界称之为内在科学——的人坚信,那个时候,人的意识还在,包括记忆和听觉,他们能听见你说话的声音,也能记住你说的话。而对这一切,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是无从体验的,至少普通人做不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永远无法证实自己的死亡。任何有关死亡的消息都是由活着的人来宣告的,包括讣告,包括葬礼的时间和地点。尤其是那些千篇一律的追悼词,把任何一个人都说得完美无缺,听了,你都会替亡人感到耻辱。在做这些事情时,我们无须征询亡者的意见,尽管他才是真正的当事人,好像那只是生者的事情,与亡者无关。那么,谁会知道死亡以后的事呢?我想,假如真有知情者,除了死神就是亡者本人——也许还有那些灵魂师。亡者不会开口说话,死神则可能不想跟活人谈论这些——它只对亡者谈论死亡的秘密,你要非得找它理论,它可能会说:别着急,等你死的时候,我们再谈论不迟。而那些灵魂师,当非常人,一个普通肉身之人,他即使乐意跟你倾心交谈,你也未必能听得明白。原因很简单,那是死亡以后的事,而你还活着。即便你听到的句句都是真理,也无从证实。据此,你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无从证实的真理就是谎言。
于是,我们就陷入了死亡的困惑,被死神所困扰。我们谁都清楚,迟早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好像那扇门随时为我们敞开着。可是,它又将我们拒之门外,以致死到临头,我们对死亡本身还是一无所知,直到你踏进那扇门里面,看到那扇门在你身后再次紧紧关闭。想必那时,你肯定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了,你终于看到了它的真相,也许你曾想把那真相告诉外面的人,可是,你无法回头,你回不了头了。你可以从那扇门进去,却不能从那扇门回到过去。如果你还能继续生与死的轮回,那么,在别的什么地方也许还有一扇门通往下一次轮回,但绝不是从你曾进入的那扇门里原路返回。
而此时,死神也许正站在我们身旁,絮絮叨叨地谈论着我们的死亡,所有的细节都不曾遗漏,好像很早以前就已经设计好了,却跟很久以后——也许没那么久——才会发生的那一幕丝毫不差。我们是当事人和主人公,那一切都确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可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成了自己的一个秘密。那么,是谁把我们锁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它好像掌管着我们的生,生和死应该是对立的,它为何又让死神掌管着解锁的钥匙或密码呢?一个人的生命旅程设计得如此精妙,而旅行者自己只记得中间这一段旅途,却不知起点和终点,更不知道开始之前和结束以后的事。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生最大的局限。那么,又是谁预先设置了这样一个前定,它在限制什么?或者说,它在担心和害怕什么呢?是人的智慧?还是人的贪婪和欲望?也许都有。试想,有了这样的限定,人类都已经不可一世,凌驾于万物之上了,要是没有了这样一个限定,还不知道它会怎样肆意妄为、祸害万物?毕竟,人类只是造物之一,而非造物主。
如此想来,又觉得这是一大幸事。你只管好好活着,考虑到,你死后还有可能以另一种生命形态继续存在于某处,继续你生命的轮回,而你前世的孽缘和功德,说不定能折算成某种苦役或福报偿还给来世的你,你就不得不善待自己,更不得不善待他人乃至万物,先利他,而后利己。且不论其它,就理而言,人能做到这点,善莫大焉,因为,这符合万物的利益。如此想来,死神可能只是把守一道关口,并严守最后的秘密,无论你是谁,最终都会听到它的召唤,而一经听到召唤,片刻也不敢耽搁,便匆匆赶到它门前报到。如此,天下万物方能消长有度,生死有致,这便是生命的秩序,是永恒的自然规律,是定数,也是劫数,你纵使有再大的能耐也会甘愿就范。
如此想来,我所听到的死神的絮语,并非真的是它说话的声音,而是切身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而它的确是存在的,否则,我们就会像西比尔那样永远活着,而不会死去了。西比尔是希腊神话中的女先知,因为阿波罗爱上了她,赋予她预言的能力,而且,答应给她一件她想要的东西,她要的是永远活着。阿波罗满足了她的要求,只要她手中有尘土,她就能一直活着。然而,她忘了跟太阳神要永恒的青春,所以日渐憔悴,最后老得只剩下了一层皱巴巴的皮囊,只好吊在一只空瓶子里,整日哭泣,却依然求死不得。她像一片早已干枯的树叶,却无法凋零。艾略特在他不朽《荒原》的引言中写到:“因为我亲眼看到大名鼎鼎的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只瓶子里。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她回答说,我要死。”如此想来,能活着固然好,但是,如果青春不再、行将就木,依然不会死去,或无法死去,也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情。我等并非西比尔,但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不会早一天,也不会晚一天,就在要死去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