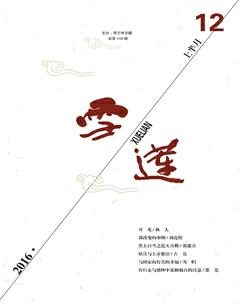古城又飘槐花香
进入八月,西宁街头的花渐渐稀落起来。早春里给高原人带来春的气息的丁香、榆叶梅和连翘,只剩下一身的绿叶,安慰着高原人对绿色的期盼和挽留之心。杨树、柳树和榆树依然用单调的绿色映衬着灰色的建筑。周末的早晨,卸下一周的劳累走出家门,穿过地下通道来到十字路口,突然,一股淡淡的清甜的香味飘散了过来,是熟悉的槐花。停下脚步往旁边的树上看,马路边一溜槐树组成的行道树上开满了淡黄色的花。碗口粗的树干上,许多长长的树枝如同一支支手臂伸向了天空和四周,槐树特有的宽阔的树冠上椭圆形的小圆叶缀满了枝头。绿色的树冠,如同一顶硕大的碧伞,给来往的行人遮风挡雨。在绿色的树叶中,看到不少淡黄色、一串串、一簇簇的蝴蝶一样的花,花朵烂漫妖娆地开满枝头,一挂一挂地压弯小枝,一种久违的亲切油然而生!那柠檬般泛着绿意的淡黄色,使人悦目,心静,乃至忧伤。
我又深深吸了一口气,那槐花特有的清香直渗心脾。每天都从这个十字路口经过,我却从来都没有注意过这排树。今天,不经意间又闻到了久违的熟悉的清甜的槐花香,而且是在高原古城西宁。在这个用杨树、柳树和榆树作为行道主要绿化树种,以柳树为市树的高原高寒城市,竟然能看到一排依稀只有在记忆中才能见到的槐树,且还能闻到清甜的槐花香,无不让人感到惊喜和意外。
整个八月里,一有空闲时间,就走出家门,怀着对槐花的深深留恋,在西宁的许多街头巷尾、公园和游园中去看正在飘散着芳香的槐花。不知不觉间,槐花已成为八月西宁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
最早知道槐树是在故乡打麦场上看的露天电影《天仙配》中,老槐树能开口讲话,促成董永与七仙女的一段美好姻缘,还有电影《地道战》中,日本鬼子夜里进村偷袭高家庄时,发现鬼子的老忠叔在急促的音乐声中一路小跑,毅然来到村中的老槐树下,解开绳索,拉响了那口报警的大钟。就在钟声回荡在高家庄的上空时,山田的枪声也响了,忠诚的老钟叔从怀里掏出一枚手榴弹扔向鬼子后倒在了老槐树下。再后来我到关中平原的陕西杨凌求学,学习林学,每天和树木打交道,对槐树有了亲近和更深的了解。绿树成荫的校园里,布满了青海高原不能生长的槐树、雪松、龙柏、水杉、玉兰、棕榈、合欢等树。校园里的第一个中秋节,我和同宿舍的同学带着学校分发的槐花做的月饼,来到渭河边的槐树下,一边赏月,一边品尝槐花月饼,那是我有生以来有过的最激动、最难忘的中秋节,槐花的清香就是在那个秋日进入我的记忆。
在纷繁复杂的植物界,一朵像蝴蝶一样的花把地球上一万八千多种植物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植物大科,称为豆科,是植物界中继菊科和兰科后的第三大科。那蝴蝶一样的花最后都长成一个扁平的豆荚,这是豆科植物共有的特性。一朵同样形状的蝶形花,开在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上,它在丰富植物世界的同时,也是人类食品中淀粉、蛋白质、油和蔬菜的重要来源之一,使人们的饭桌上多了许多豆制品。高原人日常生活中的豌豆和蚕豆,还有那种在庭院和菜园中的刀豆、用来做花卷的香豆,作为牲畜饲料的苜蓿,无不来自豆科植物。在地球上,只要有绿色植物的地方,就会有豆科植物存在。而在高寒的青海高原,那些喜湿暖环境的高大的豆科乔木树已无法生存。而豆科灌木却以耐寒、耐瘠薄的习性呵护着高原大地。被青海人亲切地称呼为“猫儿刺”的短叶锦鸡儿,几乎分布在高原大地的每条山坡荒地,那鲜黄的蝶形花成为高原大山里最早开放的野花。全身布满像猫的指甲一样的叶刺,使牲畜和人类都敬而远之,使之得以繁衍生息。还有那满身长满长棘刺的“浪麻”,被植物学家给了一个“鬼箭锦鸡儿”的雅称,以其发达的根系和繁茂的枝叶,柔韧细长的叶刺成为防风、护坡和水土保持的优良灌木。
槐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古时多栽于宫庭,唐时称宫槐,后来多见于城乡的庭前院后,故又称家槐。自从美国引入洋槐,家槐又称为中槐、国槐。槐树原生于温带,在我国华北最常见,以人工栽培为主,目前天然林已十分罕见。长期的人工栽培,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槐树文化和传说。
《周礼·朝土》载:在外朝树槐棘以分朝臣品位。大臣朝见帝王之前,要先在外朝列队等候,就是常说的“五更待漏”,外朝排列着槐树和枣树,称为“槐棘”。文武官员按官职品位依次分列于槐棘之下,三公列槐下,公卿列棘下。最前面的三棵槐树是三公的位置,三公是指太师、太傅、太保,是周代三种最高官职的合称,因此“三槐”便成了三公的代称。由于三公为国家重臣,举足轻重,因而三公之位又叫作“槐鼎”或“槐铉”之职。如某人位列三公,即说他“越登槐鼎之任”或“越登槐铉之任”。“槐棘”也就成了大臣的代名词,南朝文学家任昉(460年~508年)在《桓宣城碑》中就有“将登槐棘,宏振纲网”的句子。
在长江以北,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槐树常常长成千年古树,古树古朴苍劲,多遗存在古村落或寺庙院内,人们爱奉之为神树,并由此产生了很多民间传说。《因话录》说古槐之上常有仙人出游,每于夜间会传出丝竹音乐之声;河北《唐县志》记载:“古槐在县署二堂东,大数围,高耸旁阴,无一枯枝,下有槐神祠”;山西《汾阳县志》记载:“仙槐观在城煌庙之北,相传其地有槐,枯朽如刳舟。金皇统中,遇异人投药其中,倏长茂如初。故州人饰观以仙槐名”。
在周朝时期,槐树被视为吉祥的树种。古人种槐除了获得绿荫之外,还在于讨取吉兆、寄托希冀,民间有“门前一棵槐,不是招宝就是进财”的俗语。古代不少地方有冬天烧槐枝、烤槐火以避邪的习俗。清河北《文安县志》载:“古槐,在戟门西,清同治十年东南一枝怒发,生色宛然,观者皆以为科第之兆。”于是槐树就成了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偶像、科举吉兆的象征,并常以槐指代科考,考试的年头称槐秋,举子赴考称踏槐,考试的月份称作槐黄。
古时候官道上每隔一里设置一个土台,作为里程碑,西魏时期京兆杜陵人韦孝宽(公元508年~580年)于公元552年任雍州刺史时,发现土台经日晒雨淋极易崩塌,需要经常加以维护,便将雍州境内所有官道上的土台废除,改种槐树,既不失原有的计程作用,还能让过往行人遮阳避雨,更可以减轻官民的负担。西魏大丞相宇文泰(公元507年~556年)在巡视京畿时大加赞赏,他认为:“如此好的作法不能仅在一州实行,应在全国各地推广”。于是宇文泰命令西魏全国一律用槐树替代官道上原有的土台,并且规定:每隔一里种槐一棵,隔十里种三棵,隔百里种五棵,还规定凡新开拓的疆域,新修的官道都必须照此制度栽种树木,此举开启了我国历史上“行道树”的先例。后来西魏的疆域不断扩大,官道植树的制度一直沿续下来,并为其后历朝历代所沿用,路旁的树木越种越多,品种也越来越多样,虽然失去了里程碑的作用,确使植树事业得到了发展。
槐树是被高原人从内地引进栽培的最早的豆科乔木树种。在槐树还没有引种到青海时,有关青海王姓的故乡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故事早已传遍高原。“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首歌谣几百年来一直传唱。“大槐树”成为祖先居住之地的一种象征。史载明朝初期,因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全国各地“生民减半”,唯独山西少受战乱之苦,且连年丰稔,人口大增,于是朝廷下令从山西向各地移民,老百姓不愿离乡背井,官府便强行将其反绑双手押送出境,先行押送到洪洞县的交通要道处集中,那儿有一棵大槐树,人便在树下等候分遣。至今许多高原老人喜好背叉双手,据说就是不忘其祖先被反绑着双手,从大槐树下来到青海的。
从30年前在关中平原第一次看到槐花起,我就盼望着故乡青海也能生长槐树。如今槐花已飘满西宁街头,不久槐树将从西宁古城走向乡村,青海也将出现用槐树命名的槐树庄。浓密的槐树荫下走来背叉双手的高原人。
一阵微风再一次吹过古城街头,空中飘落许多细碎的淡黄色槐花,散发着让人陶醉的香味,如同一层黄色的雾霭洒在身上,我缓缓扬起手臂,却舍不得弹落那一身黄色槐花。一股幽幽的清香再次弥漫在空中,宛如飘渺的歌声,袅袅娜娜,悄悄缭绕着,在初秋的微风里,在碧绿的叶片间飘荡。
【作者简介】董得红,汉族,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高级工程师,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青海省湿地保护协会秘书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发表散文200余篇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青海日报》《青海湖》《雪莲》和《中国土族》等。出版散文集《行走在江河源》《江河源拾韵》《绿意柴达木(柴达木文史丛书)》和《三江源随笔》。现供职于青海省林业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