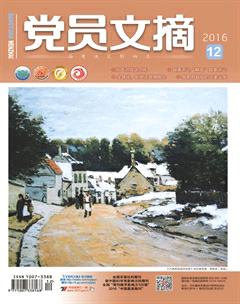我那有缺陷的完美父亲
莎伦·戴维斯+董晨晨
我知道父亲是不完美的。他打我屁股的时候,往往是我没犯错的时候,而我该被“修理”的时候,他又将我“缓刑”处理了。他性情温和,偶尔发起脾气来却令人不寒而栗。我知道父亲所有的缺点,却没告诉他,因为我想,告诉他他也听不进去。
他不完美,但是他真的很聪明。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想,所有真正聪明的男人都会成为总统。我希望他成为总统的时候,我正好到了可以恋爱的年纪,我想这样我就能以总统女儿的身份出嫁了。但是父亲自有他的计划,“你结婚的时候正好可以用上这个”,他指的是那把为了刷房子才买来的铝制伸缩梯子。我十分没好气,我可不认为这架梯子能让我从自家卧室攀上白宫的房顶。
我的弟弟们参加了童子军,父亲是童子军的教练。男孩和家人们会在小学礼堂开一次大会,进行授徽章一类的仪式。终于等到父亲上台演讲了,我很奇怪,他并没感冒,怎么就咳个不停呢。他的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衣领下面。他到底在每个词之间说了多少个“啊”?中途甚至还当众吐了一口痰,就更不要提那满脸的汗水有多损形象了。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为什么会表现成那样,母亲从身后拉了我一把。父亲则像没听到我的问题一样,只是又清了清喉咙。
唉,看来父亲是当不了总统了,因为演讲可是总统的必备技能啊,他们不就是一天到晚讲来讲去的嘛。后来肯尼迪遇刺身亡,我才变得释然了,有个怯场的老爸也不错啊。
父亲是我们家的“户长”,是老妈眼里的绝对权威,但是我可不买账。我会就某一问题跟他辩论个没完,因为他是绝不会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父亲有那么多的观点和理想,不止一次,我在心里呐喊:“你还要想多久才去实现?你究竟要你的孩子等多久?”每次还没争论出个结果,他就扭身进了书房,继续读他的报纸去了。
父亲曾是一名专门从事动物营养研究的研究员,他把科学方法也应用在了家庭生活中。作为子女,我们得合理解释自己的每个行为。可是我不具备很好的逻辑性,做任何事情都随心所欲,所以我最怕跟他交代我的动机。
买漂亮衣服,跟朋友们去游泳,去别人家过夜……这些要求即使无法满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我的心中深植了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我曾经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可是不巧我的作品被母亲发现了,于是我的作品集里多了一张她写的小纸条:“莎伦,你可快给我清醒清醒吧!”一想到把本子放到哪里都会被母亲翻出来,我就没有了写下去的欲望,于是我有了新的梦想——成为一名演员。这个想法我没告诉任何人,甚至连我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
我可以选修我们高中的戏剧课,但是我没有,那样谁都能猜到我的小心思了。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是的,我没有一刻忘记自己的梦想,我想在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之前,更多地接触社会,培养一颗易感的心,并且掌握在人群中说话的能力。
我从来没想过把自己的梦想分享给父亲,我实在说不出要成为演员的理由。毕业典礼上,父亲问我未来有什么打算,我没说。父亲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时间一晃而过,我离开大学,没有成为演员,而是做了一名家庭主妇。结婚第三年,我的丈夫离开了我。我想我的表演技能第一次发挥得那么好,在一双儿女面前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在父母面前也装得很轻松。
找工作是如此困难,毫无社会经验的我处处碰壁。有一天,父亲过来看我,他说路过一家小剧院,看见门口张贴着招聘演员的广告,要我去试一试。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我的梦想,我也不想贸然跑去丢脸,父亲怎么会想到让我去面试?一种心里最隐秘的部分突然被人触碰的痛感包围了我,这些天来的所有委屈涌上心头,我高喊着“开什么玩笑!”摔门跑了出去。
边跑边哭,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跑了多久,只知道停下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景物都是陌生的,除了不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父亲的脸涨得通红,满脸的汗水浸湿了衣领。我们的目光相遇,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让我想起了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他。我并不知道不善言辞的父亲为我联系过多少个剧院,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说服剧院经理为我争取到面试机会的,只知道在那个夕阳浸染的傍晚,我和他肩并肩地走了好久。从那一刻起,我终于了解原来父女之间无须言语,父亲其实一直都懂我。
如今,作为一名成功的哑剧演员,我已退休,家里堆满了父亲的笔记本,那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父亲对我表演的感受和建议。在儿子进入伊利诺伊大学戏剧表演专业后,我把这些宝贝转赠给了我的儿子。
有天父亲在读报纸,突然笑得喘不过气来,我跑过去一看,是马克·吐温写的一段话:“14岁的时候,我觉得父亲极其无知,我几乎不能忍受和他在一起。但是,等我长到21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在过去7年里,他已经学到了那么多东西。”
我和父亲笑着对视了一眼,是的,我的父亲有缺陷,但他比我想象的更懂得梦想的意义、生活的真谛。他,永远是最爱我的完美父亲。
(摘自《读天下》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