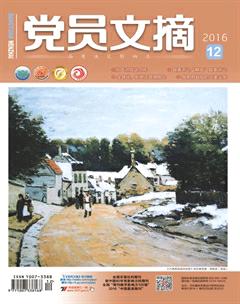唯有风知道
丁立梅
长得好好的文竹,一些日子后,竟莫名其妙枯死。我去请教花农,花农扫了一眼枯死的文竹,说,它不是缺水,也不是缺肥,它是缺风了。
缺风?我怔怔。这新鲜的提法,我是第一次听到。花农解释,你一定是把它放在室内,很少通风,它是被闷死的。我看到花农的小屋门前,一盆盆凤仙花,在风中盛开着,精神抖擞,喜笑颜开。万物生长,都离不开风的。这个常识,却被我们天长日久地忽略着。
我站在一座桥上,等风。夜晚,风捎来太多的好意。草木的清香,露珠的清凉,虫子们的欢唱,还有幽深幽深的静谧。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女孩时,住在乡下。夏夜,我们早早搬出纳凉的凳子,坐在门口的晒场上,等风来。不远处,稻田里的水稻,已沸沸扬扬开着碎粉的花。蛙们齐齐演奏,如吹萨克斯。
风来,步子迈得碎碎的,摇落一些花朵、露珠和虫子的叫声,轻且温柔地。
乡亲们手把蒲扇,眼望着繁星密布的夜空,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聊着天。风拂过他们黝黑的脸庞、胳膊和腿,他们很感激地轻叹一声,多好的风啊。白天再多的劳累和不堪,也被那样的风抚平了。夜过半,他们满足地拍拍被风吹凉的身子,道声别,各回各的家。一片风,也跟着他们走进屋子去。真怀念那样的夏夜,风自在,人安好,岁月不惊。
多年后,我从海南带回一只贝壳风铃,把它挂在屋门口。一阵风来,风铃发出欢快的鸣唱。我出门时,它在欢唱。我进门时,它在欢唱。风不停,它的歌声就不会停。我走过它身边,会不知不觉地抬头看看它,看着看着,就微笑起来。那日的沙滩、海浪、椰子道,和邂逅到的陌生人,一一涌现。
没有谁的记忆比风的记忆更长久。我们以为许多的经过,经过就经过了,了无痕迹。其实,风都给细细收着呢。受伤了,不妨去风里走走。风知道一个人的疼痛有多深。眼泪掉进风里面,风默默接纳、倾听,并一一替你拭干。哦,只要天不塌下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在风里静静呆一会儿吧,哭一哭,就好了。风同样知道一座山、一块石头、一堵墙、一幢老房子的秘密。我们说,是时间削平了所有。我们在“消失”面前,惆怅,悲伤,不能自已。这个时候,风躲在一旁窃笑。哦,这世上,哪里有真正的消失呢?所有的秘密,都悉数被它带走了。风最后也会把我们带走。我们从风里来,最终,都将回到风里去。
风把一粒种子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风把岁月从远古的洪荒年代,带到今天,且带向无限去。
岁月再久,哪里久得过风?世界再大,哪里大得过风?
(吕丽妮荐自《哲思》2016年第10期 图:项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