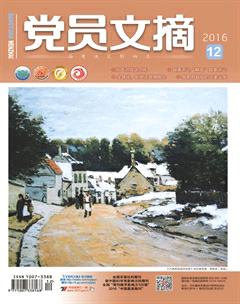陈云治家
陈伟华+朱东君
陈云与妻子于若木共育有五名子女,他们的二女儿陈伟华今年69岁,仍满头黑发,步伐矫健。在她的点滴回忆之中,陈云的另一面呈现出来——作为父亲,他是如何严于治家的。
婚礼只花一块钱
1938年初,父亲和母亲于若木结婚了。婚礼在中央组织部的一间平房里举行,而婚礼的所有花费只有一块钱。父亲用这一块钱买了花生、瓜子和糖果。事后,消息传开,有些同志见到他,就说你得请客啊,父亲当时手上虽然有点钱,但是他不愿意摆场面,所以就没有请。
父亲一直奉行粗茶淡饭,中午两菜一汤,菜谱每周一轮,都是一些家常菜,晚饭常年是青菜豆腐,甚至过春节时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去外地,接待的宾馆不知道他的规矩,第一顿饭为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就不高兴,无论如何不肯入座,人家没办法,只好重新做了两菜一汤。
上世纪50年代末,父亲参加郑州会议后,当地负责接待的人员给他那节车厢上装了几只鸡。等火车到下一站停下来加煤加水,他就让人把这几只鸡拿下去,让省里领导收回。为了这件事,他整整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觉得这是腐败作风。
父亲读小学时,学校对面有两家书场,做完功课,父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去那里听评弹。这个爱好陪伴了他一辈子。有一年,上海评弹团在进京演出前,通过父亲秘书请示他可不可以到我们家里演出一次。父亲说:“见见他们可以,但不必演出。我每天听录音不是很好吗?在这种事(指设专场)上,还是要严肃一些。”
父亲八十大寿时,有人提议召集一些老同志和他在一起吃顿便饭,庆祝一下。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于是母亲和我们同他协商,决定全家人照张合影,就用这种方式为他过了80岁的生日。
“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
父亲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他也是这样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
解放初期,父亲担任中财委主任,母亲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两个人虽然都在同一个单位,但母亲总是自己骑车上班,从没有搭过父亲的专车。后来,母亲调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地点在香山,平时住单位,周六晚上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车才能到家。有记者就这件事采访过她,她说:“我们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的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1959年,父亲去杭州、苏州休息。母亲陪了他一年多。他就跟母亲说,你陪我休息期间不能拿工资。所以母亲就没有领工资,不过母亲的单位还是帮她把工资存了起来。她回到单位后,领到了2200多元工资,但母亲按照父亲的要求,把这笔钱全部退给了单位。
上海刚解放时,父亲就给家乡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写信,叮嘱他“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为”;“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们通信,就写了这一大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有责任告诫你们”。
子女都没因为他“沾光”
对于自己的子女,父亲更是严格要求。
大姐伟力上小学前,父亲很严肃地把她叫到办公室,把她当成大人一样跟她谈话。他说,你马上就要上学了,学校跟家里不一样,那是个集体,有很多同学,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那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
大哥陈元的婚礼则像是父亲婚礼的翻版。那是1972年春节,当时父亲正在江西“蹲点”,大哥带着新娘去探望父亲并举行婚礼。父亲就从住所腾出一间房做新房,还借了几床军用被子、褥子,新房唯一的装饰就是墙上贴的红双喜字。大哥结婚那天,由于事前没有声张,大家一点都不知道。参加婚礼的客人只有六位,其中多数还是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是婚礼,其实就是一次简单的聚会。父亲说:“今天,我儿子结婚,他们新事新办,没有酒席,我只是买点烟、水果糖,大家一起玩玩。大家不会有意见吧?来,一起吃糖、抽烟、喝茶。”
妹妹伟兰1968年被分配到西藏,当时她只有18岁。有人给她出主意,说你可以让你父亲跟领导同志讲一讲,留在成都,别去西藏了。她回家就跟父亲说了。父亲说,我不能给你讲这个情,别人能去,你也应该能去。等到她离开时,父亲站在门口,让家里人都去送她。父亲对伟兰说,再大的困难你也不要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
对于小弟陈方,父亲也是谆谆教诲。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父亲正在洗手准备吃饭,看到小弟下班回来,就把他叫进办公室,对他说,现在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参与了,影响很不好。这方面你得注意,绝对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管好自己。记住了没有?小弟说记住了,父亲才让他回去。
我1966年从北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北京郊区的怀柔县当小学教师。我们分配的地方有靠近县城的,也有在半山区、深山区的。我跟父亲说了,他就说你要准备到最艰苦的地区去。后来,我被分配到了长城脚下的一个公社。
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非常想家。有一次工作日,我没有向学校请假,就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父亲看到我,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在知道我没有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立即回去,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让我安心教好书,育好人。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80年代中期,父亲从报纸上了解到师范学校招生难,就让秘书朱佳木转告有关领导,应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在那次谈话中,父亲还提到了我,说我过去当教师,后来上了师范大学,但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对此他是不赞成的,今后应当“归队”。朱佳木向我转达了父亲的意思,而我也正有此意,父亲的话让我下定决心。不久,我就调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当了一名中学教师,直到退休。
父亲曾说:“希望所有党的高级干部,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殷欣奎荐自2016年9月28日《科技信息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