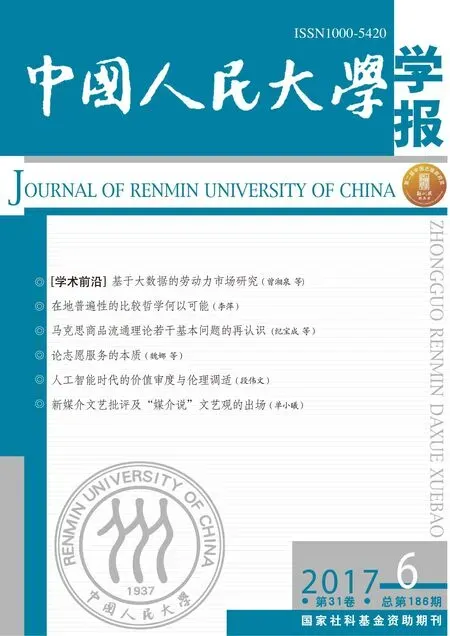在地普遍性的比较哲学何以可能
李 萍
在地普遍性的比较哲学何以可能
李 萍
比较哲学不同于比较文化,也非哲学比较。作为专门的研究,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比较哲学的问题意识是如何回答哲学研究中的“一”与“多”的关系。中国近代哲学是在择取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产生的,早期中国学人持有明确的他者与自身的二分意识,并以此确认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当代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是全球共在、互通,另一方面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地方性知识的张扬,比较哲学将定位于追求在地普遍性的哲学之真。
比较哲学;在地普遍性;方法论;世界哲学
每一种具体哲学体系都只是哲学家族成员的“多”。相对于其他哲学体系而言,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是他者,都不是哲学的全部,只是哲学的个别。比较哲学将哲学研究中的“一”与“多”的问题以十分尖锐的方式呈现出来,换句话说,比较哲学的基本立场就是要打破某种哲学体系的独尊地位。比较哲学是对不同哲学体系进行的对比性研究,是在肯定哲学基本实体或者说基本哲学问题的前提下对哲学进行的实质性研究,要在“多”中寻找“一”。就此意义而言,比较哲学的研究性质具有“之间”的特点,它触及的是“哲学间性”的问题。[1] (P3-39)“哲学间性”关注不同哲学体系之间的共相,即“哲学家族相似性”,这也解释了比较哲学兴起的内在根源。在今日中国,比较哲学研究除了上述视角外还有一个视角,那就是中国哲学不仅要融入哲学家族,成为普遍哲学的一个成员,同时还要确认自身,完成中国哲学的身份认定。因此,开展在地普遍性的比较哲学研究,对于打破哲学下属的八个二级学科的壁垒,推动中国哲学为世界哲学的生成做出自身的独特贡献大有裨益。
一、比较哲学及其问题意识
首先,需要澄清“比较哲学”与“哲学比较”的不同。哲学比较是指将不同的哲学家或不同的哲学流派的观点予以对比,加以说明。这是一种解释,无新思想的产生,所有讲授哲学的人或学习哲学的人都会使用哲学比较。比较哲学则指将两个相似或相关的不同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观点用以讨论某个常规哲学问题。这是一种阐述,通常会有新思想的产生。进行哲学比较十分容易,因为它只是交代、说明已经存在者的不同或相同,增加可辨识性。比较哲学是一种有意识的理论建构尝试,它不同于哲学比较,其目的不在于简单说明两个或多个不同哲学文本之间的异同,而是在于促进哲学文本的“视域融合”,最终完成不同哲学体系之间交互生成新的哲学知识这一比较哲学的初衷。
在学界,人们对“比较哲学”这一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理解。广义上,它可以包括一切形式的哲学比较,狭义的比较哲学则仅仅指跨文化或文化际的哲学比较。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接触催生了比较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哲学的最初努力始于两千多年前。例如,佛教典籍《米兰达王问经》就记载了古希腊思想和印度文化接触后产生的冲突、碰撞,这本佛教典籍显然包含了教化、传教的使命,它将印度文化作为主动的评判者,审视一位异域的国王如何从怀疑到接受佛教的过程,作者为此围绕有关地方性民族文化传统与普遍性人类思想意识如何对应、承接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同样,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原地区以后,也激发了许多中国学者对于外来文化和固有本土文化的比较,唐代出现的《华严原人论》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力图站在中立的立场对外来的佛教与本土原生的儒学、道教予以对照阐述,在此过程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中国本土自古以来的若干根本性的传统哲学观念的批判性态度。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上述比较哲学大多是广义性的,主要提供的是比较哲学产生的思想条件,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哲学是迟至19世纪末才形成的,因为它是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一些跨越东西方两个文明的学者成为无畏的先行者: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 1823—1900)所开启的宗教学研究突破了西方神学哲学对东方民族及其文化的刻板印象,力图融合全部现存的人类信仰现象做出学理性考察,宗教学其实成为狭义比较哲学的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和初期形态。不仅如此,缪勒还组织各类专业人士将大量东方文明典籍翻译为主要西方文字,东方文明典籍在西方知识界得到阅读和评述,才有了以后广泛而且持续进行哲学思考和批判的可能。与此同时,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启蒙学者也把许多欧洲学术名著译为中文,中国部分知识人和士大夫们可以自如地接触到西方思想的核心内容,从而使得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成为可能。在这之前有印度人将英文文献译成本国文字,在这之后有日本人将西方哲学文献译成日语,这些精心选择并被组织翻译的东西方传统思想原典,使得那个时代的各国哲学家进行较为严肃的比较哲学研究成为可能。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比较哲学仍以西方学者的研究为主,对他们来说是主动做出的内生性激励,而对东方学者来说则是受到西方哲学的刺激,以此观照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而予以回应,更为主要的目的是在整理故旧国学的过程中完成创造性转换或自我更新。从一定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比较哲学既扩大了西方人的哲学视野,增加了哲学研究的素材,也促成了东方人的哲学再现。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可知,以比较哲学命名的专著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法国哲学家马松·乌尔塞勒于1923年出版的《比较哲学》成为开山之作,被视为哲学研究的划时代作品,因为它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马松·乌尔塞勒在此书中指出,所有哲学判断(judgment)都是比较,只有放到不同文明视域下得到充分检验,才是可靠的实证化研究,而这样的研究一定是比较哲学。[2](P36)换句话说,比较越是广泛,独断性也就越少。我们可以合理推断:由于哲学研究是要说理,以往西方传统哲学的说理以命题或概念分析为主,形成了内在自洽的闭环。引入文化传统这一变量,哲学研究越来越转向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事实、事物、理性的检视,比较哲学就将自己置于所处的历史进化的链条之中,这也决定了从事比较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向过去,根据历史事实(民族文化传统)来解释人类思想发展(哲学萃取),更确切地说,由跨越文化的历史事实来总结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这一方面促成了哲学研究的动态性和立体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哲学研究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即置身诸多文化传统且不断流变的文化传统之中的哲学研究如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这个难题也成为影响比较哲学推进的极大障碍。
应当承认,马松·乌尔塞勒的努力是十分了不起的。因为当时的东西方在经济发展、政治地位上相差悬殊,很少有西方人能够将东西方文化置于同等地位,更不屑于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哲学研究。马松·乌尔塞勒为此还提出了“中间类型”的概念。他认为,尽管把非西方的文化传统引入哲学研究的视野有助于催醒西方学者的教条主义迷梦,但将当代西方哲学同最不发达地区的人群之思想意识进行比较显然未必适宜,应当选择可以将拟比较的东西方置于某个中间状态,这样得出的结论不仅是可信的,而且具有启示意义。[3](P38)马松·乌尔塞勒指出,在已知的东西方各个民族中,能够发现显见的平行性的只有三个:欧洲、印度与中国。其中,欧洲思想是比较哲学的基点,但它仅仅是哲学一般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在此前提下进行欧、印、中三地的比较哲学研究。
美国哲学家巴姆的《比较哲学》(1977年)一书也对比较哲学做出了独特的解释。巴姆断言,最广义的比较哲学比任何其他哲学分支都更为古老,因为哲学就是在不同思想传统的刺激下才得以获得自身的素材和养料,就此而言,任何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都无法离开比较这一视角。[4](P175)巴姆由此认为比较哲学是高于其他哲学分支的哲学研究领域。比较哲学应是世界所有文明的所有观点的比较,但在现阶段却难以实现,退而求其次,至少应是对世界三大主要文明,即西方、印度和中国,做出整体比较,才有望构成现代比较哲学的主体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过分的简化势必会严重影响最终结论的准确性。巴姆所谓欧、印、中三大文明的哲学体系,如果要做出比较研究,很可能只是蜻蜓点水略及极少数哲学家而已。众所周知,三大文明传统的内容极其丰富,任何一种过于概略性的研究都可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分清主流和支流固然十分必要,但“省略”不宜过分,也不能完全不考虑支流。
比较哲学涉及不同的文化传统,那么,文化传统研究是比较哲学的背景式知识还是其组成部分?从已有的比较哲学的成果来看,这二者很难厘清,确实有不少比较哲学的论者未能很好地体现哲学本身的问题意识,故而比较哲学有比较文化或比较思想之说。例如,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就将比较哲学称之为比较思想,他认为,无论是国外还是日本,目前比较思想的研究尚处于混沌状态。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日本知识界开始广泛关心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作为日本文化背景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比较考察问题,但很难说这些关注就是哲学性的,或者构成了哲学问题。中村元甚至预言比较思想将来大致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特殊化方向。或者着眼于某一地区或某一社会,去解释某一民族的哲学思维的传统和特征;或者着眼于某一时代,去揭示相同时代的东西方文化或民族所具有的哲学思维特征。二是普遍化方向,即超越了时代和民族的差异,把各种不同的思想或思维放在一起,互相批判,以此来寻找他们的共同点。[5](P134)
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的倪培民认为,比较哲学扩展了哲学本身的“数据库”, 从而身处当代哲学的中心课题——“他者”问题的最前沿。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比较哲学中“他者”问题的集中体现,是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有力挑战。但他同时指出,比较哲学的可能性问题与科学哲学中的可比性、可兼容性、可通约性问题,语言哲学中的可翻译性问题,以及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中的相对主义问题密切相关。[6](P67)这意味着比较哲学研究可能涉及诸多未解的难题,这些难题的存在使得比较哲学尚处于不成熟阶段,仍然需要投入巨大力量予以构建。*不得不承认,比较哲学自产生至今进展非常缓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研究人员的老化现象十分严重。例如,日本“比较思想学会”曾于2010年举行过一次专题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如何使比较哲学研究者年轻化。这样的话题之所以成为一场专门哲学会议的主题,是因为要深刻理解、把握两到三个以上的不同哲学体系或文化传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长期研究多个异文化的学者才有可能涉足比较哲学研究,而这样的学者通常都已经步入中老年阶段。
从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比较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工作来看,他们都认可比较哲学不仅为一般哲学研究提供了素材,同时也具有方法论意义,比较哲学促使哲学将文化(地方性知识)融入哲学问题的讨论之中。比较哲学最初是为了解决跨文化情境下哲学的传承、转述、移植等方面的问题,它不仅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学形态所呈现出来的同一性或差异性等表象,还更关注哲学存在本身。这无疑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扩展和哲学方法的应用等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中国近代哲学(比较哲学)的兴起
在中国,中西文化比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明末的启蒙运动时期。方以智在《物理小识·自序》中曾断言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他所做的中西比较所得出的结论简直令今人难以置信,因为他居然认为西方学问忽略了对根本道理亦即哲学问题的探讨(“通几”),而中国传统思想之所长是对政治学或统治学(“宰理”)的重视。囿于当时尚未全面认识西学,中国士大夫相信中国思想的长处恰恰在于思辨性及对根本性学问的追究上。正因为如此,中国文人曾经有足够的自信提出“中体西用”的学说,“中体”的核心是“道德文章”“心性天命”“性理学”。
哲学或者更具体地说中国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产生并确立的。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哲学思想被陆续引入中国并产生重大影响,比较哲学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当西方哲学作为“他者”出现时,相关研究集中于在比较中总结各自的特征、寻找中西哲学的异同、讨论中国哲学何以自立等问题,比较哲学逐渐形成。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比较哲学在中国的制度化建构紧密相连、互为影响。
作为官费生留学过欧洲的严复比当时的绝大多数国人对西学了解更多,正因为如此,他不遗余力地译介西学名著,传播西学,并试图以西学之长来弥补中学之不足。例如,他区分了政界自由与伦界自由,认为前者“乃与管束太深为反对”,后者则是“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7](P1284),只有个人独立于社会,现代伦理才可建立。现代性的职业伦理、公共伦理都由此而来。严复还明确提出过改造中国的三大纲领:“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8](P35)所谓“民力”、“民智”、“民德”都是就全体国民而言的,是从确立转型期国家新意识形态角度立论的。
一些思想家表现出了独特的“本土问题意识”,梁启超便是一例。梁启超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国家富强与国民意识的现代化有关,故倡导新民,对中国道德的转型问题给出的回答是兴公德。在他看来,“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导致“中国数千年来之束身寡过主义”。这就需要兴公德,因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9](P12)。公德与私德的二分引发了国人在道德问题上的深入思考。实际上,梁启超的这一思想来自于日本明治思想家福泽谕吉。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本书籍,“思想为之一变”。可见,梁启超的思想包含了非常明确的引西入中、借日援中的比较立场。
1903年,张之洞等人主持制订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获得清政府恩准。该章程规定大学堂分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其中大学专门分科又分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此方案一公开,王国维就撰文予以激烈的批评,认为独缺哲学是该《章程》的一大败笔。哲学是一切人类思想的根基,“《易》不言太极,则无以明其生生之旨;周子不言无极,则无以固其主静之说;伊川、晦庵若不言理与气,则其存养省察之说为无根柢。故欲离其形而上学而研究其道德之哲学,全不可能之事也”[10](P38)。王国维非常明确地将哲学作为一门独特的且基础性学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也在于拥有了哲学之本。
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学东渐已经成为许多中国开明人士的共识,其中不少人并不想简单拿来或移入,希望做中和或融通,因此,出现了中西思想比较的一个高潮,为数不少的思想家投身其中,试图全面总结中西文化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例如,李大钊就曾在他的多篇时文政论中指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差别。他把东方文明称为“南道文明”,而将西方文明称为“北道文明”。他说:“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11](P128)早期从事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的很多中国学者大都通过比较的方法与视角进行相关研究。时人常常将这样的学者称为“学贯中西”“通览古今”,这种赞誉确实反映了当时哲学界的总体倾向:只有以中国思想文化为参照才能理解西方哲学,只有将西方哲学转换成中国概念才能被接受,这是第一代乃至第二代中国哲学学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比较哲学的第一部代表作。梁先生在此著作中对西洋、中国、印度三种哲学体系从形而上之部、知识之部、人生之部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比较。他认为,形而上之部西洋与印度为同物,但研究动机不同,中国则自成一种;知识之部是西洋哲学的中心问题,中国几乎没有,印度有研究但不兴盛;人生之部西洋粗浅,中国最盛,印度此方面归入宗教。[12](P76)梁先生的比较哲学研究所选取的三个维度基本上参照西方哲学,在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之下进行分析,但他的宗旨是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以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体系。这一比较哲学的研究立意深入到中西哲学的核心,并由此揭示和探究中国哲学之本质,这也成为现代新儒家群体(包括港台和海外的一些著名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相当流行的做法。
牟宗三在多个场合指出,从西方哲学的观点来看,哲学的精髓在于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在于超越的观念。中国哲学的超越观念有其特性,即“内在性”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之处。[13](P190-191)方东美所展开的比较哲学研究同样是在中西交汇的背景下,以形而上学为中心,直探中西哲学的内涵与底蕴。他将处于不同时代之不同民族的形上学分为三种形态,即超自然形态、超越形态和内在形态。西方形上学为“超绝”形态,这种形态的弊端在于视世界为二分状态,认为整个世界呈现为二元对立,它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严重困难;中国形上学为“内在超越”形态,“全部现实,无论作为某种实有、某种存在形式、某种生命形态或某种价值类型,一方面不能被为涤除所有自然实物与过程后悄然享受彻底自我封闭之特权的独立先验客体;另一方面也决不能严格限定于去除了真正活力后的实际或幸福领域。中国人的理论拒绝两分的方法,否认二元的真理,据其视角,人和宇宙乃被视为一体建构,其中所有相关的事实构成了建造由低到高不同层次‘上层建筑’的牢固基础。”[14](P15)。方东美认为这种形态是唯一正确与合理的形态。方东美的比较哲学研究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承认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优越性,但又难免陷入“东方中心论”的偏执之中。
西化运动开始一百多年来,比较哲学一直是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方法,用西方哲学的立场、流派、思维或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解析和批判,最终的结果是以西方哲学框架体系剪裁和定性中国思想。例如,胡适以西方实验主义哲学为指导撰写了第一部中国哲学史专著,冯友兰以西方新实在论哲学为指导写中国哲学史,李石岑、范寿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中国哲学史。笔者认为,比较研究的方法虽然使中国哲学获得了“合法性”存在,却是以忽视自身原创思想为代价,遏制了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原动力,这种方法如不反思,将影响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语境下的发展。
三、比较哲学的可能路径:在地普遍性
印度当代哲学家拉著在《比较哲学导论》一书中指出,哲学应当从人开始,比较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人。哲学是人的生活指南,哲学应该阐明人的本质,给人提供一幅描绘他自身的图景,说明人的思想、行为是怎样的。人是理解和评价哲学传统的裁判者。[15](P92-93)拉著反对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人们的好奇心的观点,指出哲学的真正起源在于人类对于高于现实的存在的追求,无论人们所追求的是宇宙、社会还是国家。中、西、印三大哲学传统也基于此而各显特色。西方哲学强调控制自然和注重社会改革;中国哲学强调改造自我以适应国家与社会并改革之,却未能将问题的触角延伸到任何物质的或精神的终极基础;印度哲学也强调自我控制,但所控制的只是人的内在精神,并且它一直推延到终极的精神本源。比较哲学要通过揭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们如何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为人类更完美的生活提供启示,同时应提供人类一统的意识,帮助人们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有各自的片面性,所以特别需要互补。中国、印度、西方三大哲学传统都有扩展、补充的必要。印度哲学需要的是恢复早期吠陀和弥曼差派的原初的行动主义。从纯粹的神我主义出发并不能培养出崇尚生活的思想,但是从崇尚生活出发却可以发展出健康的神我主义。印度哲学还需要建立社会意识的形而上学基础。西方哲学需要对人的存在的内在精神注入热情,没有它,哲学就不能从既定的物质中正确区分灵性和精神的自由。西方虽然有伟大的圣人、伟大的道德和精神领袖,但总的说来,内在精神的自我肯定与信仰混淆在一起,因此它无法在哲学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中国哲学需要不懈地对内在精神和外在物质的终极做系统思考,以发现在这两个方向上的人类存在之根。人是这两个方向的平衡点,中国人保持了平衡。他们从来不迷恋于任何终极的追求。拉著主张,东西方结合的目的就是打破“东方”、“西方”的观念,去除“文化块状领域”的误解。[16](P69-99)换句话说,比较哲学的目的就是实现不同哲学的融合。
另一位同样盛名卓著的印度哲学家达亚·克里希纳(Daya Krishna,1989)通过对印度哲学梵语术语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印度哲学的研究,都是在用西方的概念和范畴来理解梵文,依然是如何把一种概念结构翻译成另一种概念结构的问题,此语境下的比较哲学乃是把西方模式悄悄强加于人的做法。他指出,比较哲学的理想范式应该采纳解放者的定位,即通过比较研究促成每一种哲学传统实现共同的解放,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哲学是将每一种哲学传统从过去的固有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也实现了每一种哲学传统放弃支配地位及其标准, 并最终达成每一种哲学传统在平等对话中的共在。[17]
比较哲学研究不仅在印度,而且在日本也有持续的关注和令人欣喜的成果。早在1927年,铃木大拙的《禅佛教论集》所阐发的禅之悟性就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西方人意识到东方思想也包含心灵哲学、认知哲学、人生哲学、逻辑学等丰富内容,这促使东西方思想的交融在更深层次的心智领域中进行。几乎与此同时,西田几多郎开创的“京都学派”致力于东西方思想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并试图使佛教“无”的观念融入西方的“存在”、“实践”等理智化哲学结构当中。阿部正雄在《禅与西方思想》一书中重点论述了禅、佛教以及和西方思想(基督教思想)的比较研究,通过剖析西方人与佛教徒在思维方式上的结构性差异,考察了西方几位代表性的思想家与基督神学家对禅的吸收和改造。松尾宝作也从佛教的角度进行比较哲学的研究,他在《比较哲学与十二缘起的解释》一书中,对十二“缘起”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了十二缘起新的解释方法的线索。[18]川田熊太郎的《佛教的思想形态论——比较哲学的研究》也从佛教的角度进行比较哲学的研究。
在日本,比较哲学专门性的著作以峰岛旭雄等人撰写的《比较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为代表,该书对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做了开创性的专门工作。全书的重点是通过比较哲学而突出“心源”研究的问题。峰岛旭雄等人明确主张比较哲学的目的是探寻人类思维的结构,东西方哲学所具有的思维逻辑是比较哲学方法论得以成立的根据,比较哲学在本质上属于实证性、结构式的研究,通过实证和结构方法的使用,探寻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精神源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种可以包容东西方哲学的“普遍哲学”,所以该书所肯定的“对比”、“实证”方法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方法,而主要是带有阐释性、论证式的哲学方法。
在英语世界里,美国的比较哲学研究相对成熟。1939年夏天,夏威夷大学主持召开的首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标志着比较哲学从此成为一门受国际学术界认可的独立学科。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东西哲学都不是自足的,都不具备全面整体的哲学特征,都只能作为新的世界哲学的组成部分。为了推动比较哲学的发展,夏威夷大学于1951年创办了专业学术刊物《东西方哲学》,对比较哲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该杂志至今仍然是比较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为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良性互动的平台。1960年,美国国会设立“东西方文化与技术交流中心”,并与夏威夷大学密切合作,开展国内外的比较哲学研究工作,使得夏威夷大学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比较哲学研究重镇之一,也形成了今日比较哲学研究领域内著名的“夏威夷学派”。此外,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西弗吉尼亚州马歇尔大学的“世界哲学史研究所”等都是国际公认的比较哲学研究的重要机构。[19](P79-80)
毫无疑问,当代比较哲学领域“夏威夷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安乐哲,他一直致力于从语言比较——比如对于翻译效应的思想自觉,对比不同语言的语法、语义和语用——入手,在对关键词的相关分析中,逐步达到哲理比较,这样的路径取得了一些显见的成果:通过浸入跨文化的语言及其语境,从而获得概念、命题层次上的哲学比较所身处其间的比较情境,概念与命题之间的同异得以自然呈现。[20](P58-64)比如,用“Focusing the Familiar”代替“Doctrine of the Mean”来翻译“中庸”,关于《中庸》的译文是他运用上述研究视角翻译中国哲学经典的成果。[21]在翻译《老子》时,他对道家关于“无” 的一系列概念如“无为”、“无知”、“无欲” 做了辨析。[22]他认为,“无为”不是“non-action”,而是“nonassertive actions”(自然而然的非武断的行为);“无知”不是“no-knowledge”,而是“unprincipled knowing”(非规定或准则性的认知);“无欲”不是停止或没有欲望,而是“objectless desire”(非目标性欲望)。[23](P30)安乐哲的翻译方法有效地避免了不同哲学体系间在概念理解上的“格义”与“附会”,但未免有使译文的可读性与可理解性大幅降低之嫌。[24](P18)牟博通过对现代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中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的反思,进入到元哲学和元方法论的层次,提出了“建设性交锋—交融”的方法论策略。牟博指出,该策略旨在去探索那些来自各种哲学传统(或者来自同一传统中的不同风格/取向)的不同思想方式、方法论途径、洞察、概念性/解释性资源,比较它们如何通过反思性批判和自身批判而相互学习,从而为共同的哲学事业(对一系列通过哲学解释而共同关注的问题或论题)做出贡献。[25](P65-70)
与传统西方哲学相比,比较哲学在国际学术界并非主流。即便如此,至少在从事比较哲学的学术圈子中人们已经大体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共识:第一,比较哲学要摆脱文化比较、思想比较的空泛性,进入到哲学基本问题层面。换句话说,比较哲学要达到哲学研究的深化和质性提升。“在‘哲学’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知识体系,‘科学’成为一种有力的价值尺度的现代社会里,我们需要做的是努力改变西方人对‘哲学’与‘科学’的地方性定义,使它们摆脱西方文化狭隘的地方性、经验性的内容,从而扩展为一种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新概念。”[26](P358)第二,比较哲学起始于对他者的观照,引入异域文明中的不同哲学体系是必要的,同时自我检视也是必不可少的,本土哲学的自主性并非故步自封、唯我独尊,相反,只有在开放的语境下才能得到终极辩护。第三,比较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世界哲学,以融汇东西方不同哲学传统。其实,“世界哲学”反映的是从古至今中外思想家们的最大公约数,如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中国先贤的大同世界、今人提倡的“普世伦理”等等。“世界哲学”并非存在论意义上的实体,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论意义上的开放、宽容精神,其中包含了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对哲学研究者而言,就是放弃画地为牢、排外主义的观念,参与全世界范围内的哲学问题论争。
然而,比较视域本身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关涉被比较者的显现/隐匿,另一方面也关涉比较自身的显现/隐匿,由于实际存在四种可能的关系形态,因而任何特定的比较研究难免挂一漏万。这也是比较研究的一个先天不足。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比较视域和比较哲学研究的必要性。由揭示本土的时代精神(本地的重大时代问题)出发,自如地兼及自身哲学传统和其他各种哲学资源,在逻辑自洽、言说得意中做出合理论证,这不仅应该成为比较哲学的常态,也应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主要表达形式。保护各国哲学体系的多元性与扩大人类的共识基础,二者同样重要。笔者将这样的尝试解读为建构具有“在地普遍性”的世界哲学之努力。“普遍性”反映的是哲学本真,是哲学的共相,同时也是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的基调。但我们总是以自身的方式诠释哲学之共相,文化传统、国民性、社会—国家关系等具体条件既提供了我们进行哲学运思的资源,又形成了我们只能如此思考的阈限。因此,我们所做的比较哲学研究一定是在地化的。“在地普遍性”世界哲学促使我们在不失哲学理念、学术理想的前提下,关切吾国吾民,此时此地,从而提供复调、立体的共在图景。
[1] 张志伟:《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关于比较哲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载《学术月刊》,2008(5)。
[2][3][4][15][16] 冯禹、邢东风主编:《宏观比较哲学名著评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5] 中村元:《比较思想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6] 倪培民:《探涉比较哲学的疆域》,载《学术月刊》,2006(6)。
[7] 严复:《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严复:《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11]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12]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3] 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
[14] 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上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17] 达亚·克里希纳:《比较哲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载《第欧根尼》,1989(1)。
[18] 松尾宝作:《比較哲学と十二縁起の解釈》,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网站,www.jstage.jst.go.jp/article/ibk1952/23/1/23_1.../_。
[19] 彭越:《西方比较哲学发展概述》,载《广东社会科学》,1995(4)。
[20] 张祥龙:《比较悖论与比较情景——哲学比较的方法论反思》,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9)。
[21] Roger T.Ames,and David L.Hall(eds.).FocusingtheFamiliar:ATranslationandPhilosophicalInterpretationoftheZhongyong.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22] Roger T.Ames,Laozi, and David L.Hall.Daodejing:APhilosophicalTranslation.NewYork: Ballantine Books,2003.
[23] 温海明:《比较哲学方法论简论》,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24] 李明辉:《中西比较哲学方法论省思》,载《中国哲学史》,2006(2)。
[25] 牟博:《论比较哲学中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的方法论策略》,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9)。
[26] 吴根友:《求道·求真·求通——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HowtoTestifyComparativePhilosophyofLocal-universality
LI P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Comparative philosophy is different from comparative culture or philosophical comparison. As a special study,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ame into being in the 1920s. The core question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is how to justify the relationship of “One” and “Multiple” in philosophy.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was brought about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so most Chinese philosophers at the times explicitly held the binary ideas of other/myself, which made them rationalize philosophy in China. We are now in a new historical stage. On the one hand globally people are co-being and interconnected, on the other hand national spirits and local-knowledge are being waken up.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ies, comparative philosophy should pursue philosophical truth of local-universality.
comparative philosophy; local-universality; methodology; world-approach philosophy
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15XNGL08)
李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