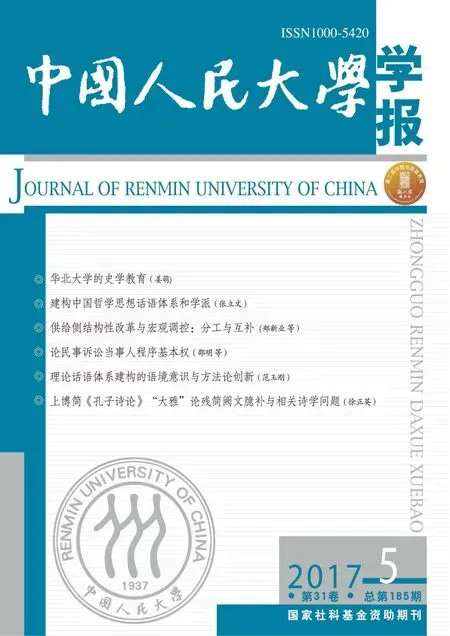伦理信任何以可能的本体性思考
唐代兴
伦理信任何以可能的本体性思考
唐代兴
伦理信任的实践形态,表征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信任和美德信任;伦理信任的社会功能,抽象为统摄制度规训与人文精神、历史情感与生存想望、个性自由与生存担责的社会精神秩序内稳器。伦理信任解构的深层机制是人成为人的神性消解、人性扭曲,其社会运作机制是“财富—权力”社会结构对“平等—公正”分配机制的解除。伦理信任的社会化建构之成为可能,需要人性觉醒与神性守望的有机统一、信仰与哲学的共生性融通、“权利—权力”相博弈的社会结构与“平等—公正”分配的社会机制互为规范。
伦理信任;人性觉醒;神性守望;权利—权力博弈;平等—公正分配
凡研究,无论是纯粹理性知识论研究,还是实践理性方法论研究,都源于问题并围绕问题而展开,伦理信任研究同样是迫于伦理信任解构这一实际社会状况。要从根本上解决伦理信任解构及其社会化重构问题,其重要前提是拷问伦理信任何以可能。
一、伦理信任概念的双重内涵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人类已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其突出标志是全球性财富驱动、贫困驱动和非理性军备竞赛导致了生态危机的立体化。尽管贝克以独特的视角描述和分析了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风险,但最终仍停留在现象层面。透过现象而审察世界风险社会的生成可以发现,伦理信任的加速解构才是其本体性根源,因为伦理信任是支撑社会秩序的本体性精神结构的内稳器。
在风险社会,尽管伦理信任的解构早已成为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但并没有引发普遍的社会关注和应有的学理讨论。当然,在此之前已出现了类似的提法,这就是道德信任。对“道德信任”的关注和思考始于2011年,时至2017年初,其可见的也仅有《新医改背景下医患信任的主导:道德信任与制度信任》(刘俊香等,2011)、《对当前企业道德信任危机的思考》(李春英,2011)、《统一考量道德信任和制度信任》(李志昌,2012)、《道德信任:现代高职教育的典型性缺失》(陈云涛,2012)和《论道德信任和制度信任的辩证关系》(李志昌,2015)等文献,分别从企业、临床医学、教育、制度等不同方面提出了道德信任丧失的问题,表明道德信任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基本伦理问题。
笼统而言,道德信任问题就是伦理信任问题,对道德信任危机的思考就是对伦理信任解构问题的具体反思。但伦理信任并不等于道德信任:从构成角度看,道德信任只是伦理信任的具体构成,除此之外,伦理信任还涉及美德信任,比如老人跌倒“扶”与“不扶”的问题,就是一个美德信任问题。不仅如此,伦理信任与道德信任还存在着功能方面的区别:伦理信任指向社会精神秩序的构建,道德信任意指个体精神生活的实现。
伦理信任与道德信任的如上区别,有其词源学源头。在西语中,ethics源于希腊语ethos;morality源于拉丁文moralis,二者语义相通:“在日常语言中,我们说某人是ethical还是moral,说某行为是unethical还是immoral,实际上没有任何差别。不过,在哲学领域,ethics一词还用以指称特殊的研究领域——伦理学,即集中关注人的行为和人的价值的道德领域。”[1](P5)如此区别仅仅是指涉范围的大小,伦理与道德还存在如下根本区别:人们对“伦理”、“道德”的通见,表现为赋予它们以品性、气禀、习惯、风俗等含义。但实际上,品性、气禀、习惯均呈个体指涉性:气禀更多地指个人的天赋因素;品性侧重强调个人后天修养的内化状态及其取向;习惯却主要指个体行为对某种群体性规范的自觉。与此不同,风俗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指特定地域共同体中人人须遵守的行为模式和规范。以此观之,气禀、品性、习惯更多地为道德概念所统摄;风俗却主要为伦理概念所统摄。这种区分的依据应该是伦理和道德本身的构成性及其指涉范围的限定性。
客观地讲,道德相对个人才获得意义的指涉性,伦理却相对关系才获得意义的指涉性。比如,我们可以说此人道德或不道德,但不能说此人伦理或不伦理。因为道德是对具体行为及其结果状态、取向的判断和评价,由此使道德概念获得了三重功能:首先,道德意指具体行为的合善性。所谓行为的合善性,即是行为追求合法期待。其次,道德意指其合善性的行为所达及的最终结果,真实地避免了恶而实现了善,即道德是行为达及的良好结果状态。所谓良好结果状态,是指其行为结果实现了行为主体与行为相关者的俱得或共赢,这种俱得或共赢在本质上是善的自由的真正实现。再次,道德意指行为的合善性因其最终实现了善的自由的效果而可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指涉功能的判断方式,即道德是对行为善恶的判断依据、标准、尺度。
然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使用道德概念,都涉及一个支撑性的前提,即道德始终是建立在某种可具体定义的情境关系上的,离开了这种可具体定义的情境关系,道德无从产生。
这种支撑道德的可具体定义的情境关系,是指充满利害取向的人际关系。对这种性质取向的人际关系予以理性权衡和选择并建构起不损或共赢的生存关系,就是伦理关系。道德,就是建立在可具体定义的人际关系基础上的,这个可具体定义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利害”,道德就是对人际关系中的利害内容予以权衡和取舍的行为、方法、依据、尺度。
对人际关系中的利害内容予以权衡和取舍,客观地存在两种基本方式,即功利论方式和道义论方式。前者是以不损他的方式或均利、共赢的方式对具体人际关系中的利害内容予以权衡和取舍,其行为展开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就是道德;后者是以损己的方式或单纯利他的方式对具体人际关系中的利害内容予以权衡和取舍,其行为展开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美德。因而,伦理关系蕴含两种可能性,伦理体现两种德行取向,并展现两种德性境界,即道德和美德,前者是基本的德,后者是卓越的德。
德始终是相对人与他者的实际关系而论,这是德产生的前提。人与他者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实际地构成了三种发散性类型,即我→你关系、我→他关系和我→它关系。如进一步归类,这三种类型可以归纳为两类,即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前一种关系要获得德,必须以诚为价值取向;后一种关系要获得德,必须以信为价值取向。所以,对待物或生命,要诚,才可做到利用(即物尽其用)和厚生;待人,必信才可生德。从后者观,无论道德还是美德,都必须建立在人对人的信任基础上:道德作为基于道德信任;美德追求基于美德信任。
由于道德与美德乃伦理的基本构成,所以,伦理信任实际上是指道德信任和美德信任,是道德信任和美德信任的整体表述。但这仅仅是伦理信任的基本方面,即伦理信任必须要通过道德信任和美德信任而得到实现与呈现。更为根本的方面是,道德信任和美德信任并不建构伦理信任,相反,道德信任和美德信任的生成建构需要以伦理信任为规训和引导。因为无论是道德信任还是美德信任,都是具体情境定义中人与人之间以互为理解的善意所形成的对利害的权衡与取舍方式,它需要一个具有自生张力的社会平台的保证,需要一个充满自由想望的社会精神结构的支撑。前者是以人性法则为坐标所形成的以人道→平等→公正为根本指南的制度平台,后者却是以传承→鼎新为双重动力的人文精神框架,将此二者联结起来形成一种生成性建构的整体力量的那个抽象而稳定的东西,就是伦理信任。
概括地讲,伦理信任就是统摄制度规训与人文精神、历史情感与生存想望、个性自由与生存担责的心灵—情感化的精神认同机制(或精神秩序),它蕴含社会心理认同的利爱情感动力和社会精神秩序创构的价值导向。伦理信任植根于民族国家地域化生存的历史土壤之中,其自我展开始终以境域化存在困境为舞台回应未来对现实的召唤。伦理信任既朝形而上方向敞开自我构建,又朝形而下方向展开自我实践:前者彰显为社会精神秩序、社会心理认同、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后者落实为道德信任和美德信任,具体到实际的生活情境定义中,就是个体的道德作为和美德追求。
二、伦理信任生成的双重土壤
伦理信任作为社会心理认同和精神秩序建构的价值意向和情感动力,其生成运作何以可能,既涉及人性问题,更涉及神性问题。
伦理信任相对于人才有实际意义。从存在论角度讲,人既是一个个体存在者,也是一个个体生命存在者;从发生学和生存论角度观,人既来源于他者,又必存在于他者之中并通过他者而获得继续存在的全部可能性与现实性。
人作为个体存在者,决定了他必须自由:自由天赋于人,并构成人的天赋权利能力。
人作为个体生命存在者,既决定了他必须因生而意愿于活,并为活而谋求新生,且生生不息;更决定了他必不可自由,因为生命需要资源才可获得滋养,滋养生命的资源却并非现成,必须谋取才可获得,而谋取资源的过程既需要付出,更要接受限制或承受阻碍。付出和限制之于人,始终表征为代价,包括付出时间、精神、体力、智能、才华以及金钱或物质财富,但其所付出的本质内容却是自由和生命:人必须以不自由和生命为代价而换取生存资源的保障。比如,哪怕你今天不高兴或从根本上讨厌自己的工作,但你还得打起精神上班,因为只有上班,明天才有生活的保障。为了明天有饭吃或者有更好的饭吃,你必须每天牺牲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甚至还要加上一到两个小时的乘车(或开车)时间,但时间永远是生命的刻度,更是自由的标志,所以每个人都是在以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为代价来换取生存的最低保证。人的这一存在状况导致了人的两种生存取向:一是求利取向。人是求利的存在者,为了生存而必须求利。求利是生命存在的动力,是人成为人甚至人成为神的动力。二是趋利避害甚至投机取巧的本能冲动。任何人都本能地追求利益而避免损害,并本能地渴求少付出、多获得。如上两种生存取向为伦理的产生、伦理信任的生成提供了反面的动力,即人人都想少付出、多获得这种冲动一旦化为行为,则相互之间必然发生矛盾、冲突、斗争甚至流血,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人们不得不寻求其行为的边界,并在行为上予以恪守和兑现,对这种恪守和兑现的行为方式的普遍遵守,就构成伦理信任这种社会精神秩序和利爱情感方式。
但是,人如果仅限于此,伦理将不会产生,也不可能产生伦理信任。伦理的产生,伦理信任形成的可能性,完全是因为人不仅是个体的和独立的存在者,同时也是非个体性和非独立性的存在者。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272)。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不能自生。人的非自生性敞开为两个方面:首先,人人都由他者所生。每个人的生命都得之于天,受之于地,承之于血缘,最终才形之于父母,天地神人共铸了个体生命。每个生命都诞生于具体的家庭,获得家族、民族、物种的基因,具有地域特征,打上国家的烙印。其次,任何人从生到死既不能独立存在,更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解决所有的生计问题。人要活下去,只能走向他者,走进群,构建起互助的共同体,才可求得安全存在和生存。因而,求群、适群、合群,既是人的现实存在要求,也是人的实际生存冲动,更是天性与本能。个人孤立无能的现实境况推动他必须充分释放如上天性与本能,由此使伦理成为现实。伦理的现实本质就是人对人的信任:欲求共同生存的伦理冲动,使伦理信任获得了可能性;将共同生存的伦理冲动化为行动,促进伦理信任成为现实。
人从动物进化为人,不仅将动物的生之本性提升为有意识地谋求以利爱为基本取向的人性,而且有意识地追求将以利爱为基本取向的人性提升为神性,这是人成为人的根基性需要。
人从动物进化为人的过程,是获得人质意识并创造人的文化和精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创造的奠基工作,就是为原本仅是一物的生命创造不凡的出身,为原本没有目的、没有归宿的生命创设明确的目的和归宿。这一工作就是创造宗教,建构信仰体系,为平庸而弱小、自卑而无望的自己解决如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存在问题,赋予人获得神性存在的自觉、自信、自强:第一,人是从哪儿来的?第二,人应该到哪儿去?第三,人必须怎样走才能够到达那儿?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人的出身:人由上帝所创造,人是神的子民。这种高贵的出身,使人获得了神性的自信和做人的光荣,一无所有和苦难的现实因此而变得不那样重要。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人的归宿:人最终能回归于上帝,获得与上帝同在的永生,赋予了人承受苦难、努力生存、超越自我的动力。
第三个问题解决了人解救自己、实现神性存在的正确方向与途径:真诚生活、努力工作、创造财富、成就他人,这是人解救自己、重新回归上帝、达向永生的必由之路。
概括地讲,人成为人,必须实现双重的超越,第一重超越是人由动物变成人,必须接受群己权界,必须利爱行为的相关者,必须爱人,这是伦理信任得以社会化建构的人性基石。在此基础上,人致力于第二重超越,将自己从人提升为神。这需要人从两个方面努力追求至善:一是向上努力,把自己交给上帝,聆听上帝的教诲、接受上帝的引导,即让上帝成就自己;二是向下努力,把自己交给人间的苦难与磨砺,以工作和创造为天职,以博爱为基本要求,以成就他人为自我成就的实质体现。换言之,让上帝成就自己的基本方式,就是成就自己周围的他人:成就他人,成为成就自己的实际路径,这是伦理信任得以社会化建构的神性动力。
伦理信任问题,表面上看是社会文明精神和秩序的建构问题,本质上却是人成为人和人成为神的问题,是人如何具备人性和怎样获得神性的问题。人一旦获得了人性和神性,就会内生出两个至诚的东西:一是做人的尊严与光荣;二是待人的尊重和敬爱。这两个至诚的东西构成人对人的信任的主体前提和内在动力。这种至诚的成人尊严与光荣、待人的尊重和敬爱情感一旦普遍化,伦理信任作为社会精神的内稳器就会得到良性建构。
伦理信任何以可能的双重精神土壤,就是人的双重超越,这就是人性觉醒与神性守望:人性觉醒,因生生而平等地利爱;神性守望,因永生而无私地博爱。因生生而平等地利爱,人与人之间可以达成信任,但因这种信任是以权衡和取舍利害为前提的,所以往往会因利害及其权衡与取舍的变化而生变,由此使伦理信任既可因人性觉醒而获得实现,也可因利害权衡与取舍的境遇性而消解。伦理信任的社会化建构要获得完全的实现和持续的稳定,须由人性觉醒与神性守望共同打造,因为缺乏神性守望的人性觉醒,始终把目光锁定在利爱的大地上,难以有勇气和力量昂扬起头颅仰望天空。如果人从根本上缺乏一种来自于天空的牵引力,就很难摆脱生存利害的羁绊,人对人的信任就很难达致至诚之境,并且往往会因此而蒙受解构之难。这种情况在没有宗教文化的国家社会里经常出现。宗教是一种大众文化,在没有宗教这一大众文化哺育的国度里,人从根本上缺乏超拔利爱的信仰和神性守望,没有一以贯之的心灵坚守。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中,人既没有“高贵”的出身,也没有“全有”的归宿,从根本上缺乏做人的高贵感、神性的自信意识和永生的超拔意愿。人最终只能龟缩在血缘与世俗权利之中,为财富和权力而争斗不息。所以,在没有神性守望的文化环境里,人性觉醒最终会被财富—权力结构所绑架,伦理信任总是被迫处于自我瓦解之中。
三、伦理信任生成的两维基石
人性觉醒和神性守望为伦理信任的社会化建构提供了可能性。但比较论之,前者为之提供的可能性是或然的,后者为之提供的可能性是必然的。在这种或然与必然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一种不可逆的生成性关系:神性守望必源于人性觉醒的激励并最终达向对人性觉醒的超越;人性觉醒可能生成神性守望但并不必然产生神性守望。这表明,从人性觉醒达向神性守望,必有其条件的要求,而使之实现的根本条件就是宗教和哲学。
伦理信任能获得普遍必然的首要文化条件,就是人文宗教,简称为宗教。宗教之所以构成人性觉醒达向神性守望所必需的文化条件,是因为宗教本身的内在要求使它为伦理信任成为必然的社会精神内稳器提供了不竭的源头活水。
首先,宗教是一种大众文化,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张扬大众文化的品质,发挥大众文化的功能。所谓大众文化,就是愿意相信它的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文化,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普遍平等的价值诉求。宗教对人没有任何的比如阶级、身份、地位、血缘、出身等方面的特定要求,它使每一个享有这种文化的人都平等,并且总是平等地面对所有的人,平等地接纳所有的人。二是全面开放的文化品格。宗教超越种族、民族、阶级、政治、宗族、家庭的局限而向世界上所有人开放,即凡是愿意接受这种文化者,不管你来自于何方,其身份、地位、家庭如何,都将获得平等地信仰这种文化的资格权利。从本质上讲,宗教这种平等主义的大众文化为伦理信任的社会化建构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次,宗教作为大众文化是一种信仰文化,而不是一种知识(比如科学)文化,也不是一种技术(比如政治)文化,更不是一种(比如哲学)方法的文化。梁漱溟曾这样定义宗教:“所谓宗教,都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在他看来,“(一)宗教必以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为他的事务;(二)宗教必以对于知识之超外背反,立他的依据”。宗教的作用就是通过信仰的崇拜而“不外使一个人的生活得以维持而不致溃裂横断,这是一要宗教之通点”[3](P96-97)。宗教即信仰,它是生命对神圣的投入,是心灵、意志、情感、身体的整体化领悟。宗教的行为本质是对信仰的崇拜,它使人获得一种存在的终极意识、尊严、情感,产生一种生存的终极关怀胸怀和博爱慈悲精神,并成为激发人从生命底部喷涌出反抗不幸、包容苦难、开辟新生、达向幸福和永生的希望之光和力量之源。这种以生命对神圣投入的信仰崇拜构成伦理信任得以社会化建构的最终心灵基石和情感原动力。
从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看,每个民族都有丰富的自然宗教,却只有少数的民族才将自然宗教转换提升为人文宗教。对于没有本土宗教的文化,其伦理信任就面临根基的缺乏,能够予以补救的方式就是哲学,因为“哲学是人类科学即理性之自然照明来认识事物的科学中之最高者”[4](P135)。相比之下,虽然对宗教和信仰予以专门研究的神学比哲学更高,但“哲学既不是在它的前提上,也不是在它的方法上,而是在它的结论上臣属于神学。神学对于这些结论行使着一种控制,因此它自身便成为哲学的一种消极规律”[5](P142-143)。哲学是关注人的世界性存在的学问,它借助人类的超验理性之慧光而追问人的存在,探求人的存在方式,从而为人类提供如何存在的态度和视野。神学是关注生命存在和世界存在的学问,它凭借人类的先验理性之慧光而直观人,探求人类存在的神圣世界,为人类提供完整的心灵信仰和终极目标。将哲学和神学联系起来的纽带是对存在的形而上学沉思,因为形而上学既是超验理性的,又是先验理性的,既追求本体知识的构建,又超越知识的努力而达向神性领悟之域进而获得整体直观的方法。正是因为形而上学,哲学获得了向神学领域进发的全部可能性。[6](P116)进一步讲,哲学在结论上“臣属于神学”蕴含两层语义:
首先,哲学必须走向神学。雅克·蒂洛和基思·克拉斯曼在论及伦理学与哲学的关系时说:“哲学一般关注三大领域,即认识论(关于知识的研究)、形而上学(关于实在之本性的研究)和伦理学(关于道德的研究)。”[7](P4)这应该是对复杂的开放性的哲学系统的最简洁的归纳,它突显出哲学的基本部分:认识论是哲学的主体部分,它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全部领域,自然科学探讨创建自然知识,社会科学探讨创建社会知识,人文艺术探讨创建人的知识。知识论则是对如上各种知识的生成何以可能的问题和其个性背后的共性问题予以系统性解答的学问。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基础部分,它不仅要探讨知识生成的依据,更要为哲学的探讨——包括知识论探讨和伦理学探讨提供方法论。伦理学是哲学的论,或可说是哲学达向普遍社会实践的方法论,它要着力解决的是哲学如何走向社会、走进人的生活,引导人并导航社会使其更善美地存在。所以,哲学是伦理学的方法论,伦理学是哲学达向普遍实践的生成论方式。但是,无论是知识论、形而上学,还是伦理学,都需要人性这个共同的土壤和原动力,因而人性论构成了哲学的基石。
其次,哲学必须以神学为归宿。哲学以人性为起步,从纯粹理性(知识论)和实践理性(伦理学)两个方面展开审视人的世界性存在,必然踏上形而上学道路而通向神学。只有当通过形而上学而打通通达神学的道路时,人类的精神探究才可由地而天并由天及地:由地而天,这是哲学的上升之路;由天及地,这是神学的下降之路。正是哲学与神学之间的这种升降循环的融通,构成伦理信任的社会化建构的内在文化机制。
宗教始终是人的宗教,它是人对完美想象的自我完整的对象化定格。宗教的主体化方式是信仰,神学就是以信仰为对象,探讨信仰的神性本质,其最终目的是提升人性,使人性神性化,但其前提却是用信仰纯化人性,用神性引领人性。哲学站立在大地之上,用坚实的臂膀将人性往上托;神学则假借上帝伸出信仰之手,努力将人性往上拉。这一拉一托,使人性与神性相向走进对方,使世俗的利爱与信仰的慈悲互为体用。因此,缺乏宗教这一大众文化土壤,哲学同样可以担当大任而通向空寂的神学殿堂,体悟人的世界性存在的神性慧光,打通人性的利爱与神性的慈悲之通道,构筑伦理信任的社会化建构的文化机制。
但是,当一个在本原上缺乏人文宗教的民族国家,又从根本上丧失时代性的哲学创构的能力时,伦理信任必然因信仰与哲学的双重缺失而自我消解。这或许是当今中国社会伦理信任面临解构危机的认知根源。
四、伦理信任建构的基本社会条件
综上所述,风险社会的实质是伦理的,是人类伦理信任解构的形式呈现。以现实社会为例,无论是市场的畸形垄断,还是社会贫富的巨大差距,或者腐败的权力化、职业化,都源于伦理信任之社会精神的丧失。最典型也是最普遍的三个例子或许是最好的说明:第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是老人跌倒无人扶而且也不敢扶,表明美德风尚的缺乏,但其根本前提却是伦理信任之社会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解构。第二个是近年来在反腐过程中不断暴露出来的比比皆是的贪官现象,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伦理信任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解构,抑或更准确地讲,是政治伦理信任之精神结构的解构,才导致了贪腐普遍化。贪官们为何要成千上万亿地贪,并不是因为缺钱花,而是对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职业缺乏根本的伦理信任,当其伦理信任丧失后,需要寻求一种替代品,而在一个以财富—权力为深层结构的社会里,金钱、财富恰恰成为伦理信任的替代品。第三个是近些年出现的海外移民潮,上千万人席卷数万亿人民币永久性移居海外,其根本社会冲动有三:一是谋求生存安全;二是谋求财富保障;三是追求健康生活环境,即远离污染和获得食品安全。形成这三大冲动的最终动因却是人们对社会未来丧失了基本的伦理信任。
上述三个实例展示出当前社会伦理信任危机的广度与深度。一个社会的伦理信任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呈现出如此严重的危机,至少从反面表明:伦理信任的社会化建构,除了应具备人性与神性的双重土壤和信仰与哲学的体认基石外,还应该具备基本的社会条件。这一基本的社会条件有二:一是权利—权力相博弈的社会结构和平等—公正分配的社会机制。
伦理是对充满利害取向的人际关系予以合德的权衡与取舍方式,而伦理信任则为这种合德的权衡与取舍方式的社会化运用提供普遍的精神框架和共享的利爱情感动力。伦理信任的社会化建构首先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的支撑。这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必须是合利爱的人性和合慈悲的神性。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伦理信任所需要的社会结构,只能是权利—权力相博弈的结构。权利与权力相博弈的社会结构,就是权利限制权力、权利监约权力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生成构建的前提,是确立权力来源于权利,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权力服务于权利,或者说权力保障权利。权利与权力相博弈的社会结构必须具备一个人权政体的基石,即个人构建社会,公民是国家的缔造者。概括如上内容,首先,权利与权力相博弈的社会结构,必须遵循人权政体原则,这是政体健康的基本体现:“政体的原则一旦腐化,最好的法律也要变坏,反而对国家有害。但是在原则健全的时候,就是坏的法律也会发生好的法律的效果;原则的力量带动一切。”[8](P142)其次,权利与权力相博弈的社会结构必须规范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力,使国家权力只能是有限度的强权,政府权力必须是有限度的绝对权力。这需要三个方面的制衡: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9](P184)。二是确立人权边界原则,即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官员权力的边界就是公民权利。三是权利与权力相博弈的社会结构必须具备群己权界的制度机制,才能发挥权利博弈权力的社会功能。
权利博弈权力的社会结构必以“平等—公正”分配的社会机制为规范方式和推动力。在人们的习惯性认知模式中,分配所涉及的仅仅是社会劳动和财富,其实,这仅是分配的末端内容。分配的开端内容或者说根本内容却是权利和权力。首先是权利分配:只有当权利分配普遍平等和完全公正时,权力分配才有限度,被分配的权力——无论横向分配的权力还是纵向分配的权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限绝对权力。对国家、社会来讲,任何形式的无限绝对权力的形成或泛滥,都是基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权力分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真正根源,恰恰是权利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权利分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前提性预设,是权力优先并优越于权利。客观论之,以普遍平等和全面公正为准则而分配权利,这是权力分配平等和公正的根本前提与保证。权利分配平等公正和权力分配平等公正,才是劳动分配和财富分配普遍平等公正的双重基础。换言之,权利和权力分配平等公正的原则,才是社会劳动和财富分配普遍平等公正的保障。
权利—权力相博弈的社会结构和平等—公正分配的社会机制之所以构成伦理信任之社会精神建构的基本条件,是因为伦理信任的存在本质是利益权利的平等和公正。在实际的社会生存中,利益权利的不平等、不公正是导致社会伦理信任机制瓦解和社会伦理信任基石崩溃的直接动因。反观当前社会生活中三个领域的伦理信任状况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市场领域最缺乏的恰恰是诚信。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普遍缺乏诚信,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的垄断性结构,这种垄断性结构实质上是一种财富—权力结构,即以谋取财富为动机和目的,并以权力为实现其谋取的手段这一深层的市场结构,恰恰又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的市场化呈现。由这样一种财富—权力社会结构支撑的市场,要讲诚信,要诚信地经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其次,日常生活领域的道德沦丧和美德消隐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追根溯源,同样源于平等—公正分配的社会机制的缺乏,权利不仅始终未形成对权力的博弈机制,更没有获得对公权的博弈功能。在一个公权无限度的社会里,日常生活必然充满权利与权力的倒错,导致道德沉沦与美德消隐,形成伦理信任之社会精神的萎缩和消解。再次,政府公信力状况和官员道德美誉度状况,表明政治伦理信任这一基本的社会精神被立体消解的深广程度,如果追溯其形成的最终社会机制,财富—权力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权利的社会机制,才是其根本诱因。所以,在财富—权力社会结构和权力—权利分配社会机制的双重规训下,伦理信任之社会精神秩序的时代性建构何以可能的问题,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
[1][7] 雅克·蒂洛、基思·克拉斯曼:《伦理学与生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5] 马里旦:《哲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6] 唐代兴:《生境伦理的知识论构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8][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Abstract: The practical form of ethical trust is characterized as moral trust and virtual trust between peopl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ethical trust is abstracted as the internal stabilizer of social spiritual orders governing system discipline & humanistic spirit, historical emotion & existential longing, and individual freedom & survival responsibility. The deep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ethical trust is disenchantment of divinity, and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among human being; while the social operation mechanism is the release of the “equality and justic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b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wealth and pow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trust may be possible with the norms such as the harmony of humanity awareness & divine guarding, the symbiosis commutation of beliefs & philosophy, the social structure with the game of “rights vs power” , and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f “equality & justice”.
Keywords: ethical trust; humanity awakening; divine guarding; game of rights vs power; social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f equality & justice
(责任编辑李理)
OntologicalThinkinguponWhytheEthicalTrustisPossible
TANG Dai-xing
(Institute of Ethic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唐代兴: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二级教授,特聘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