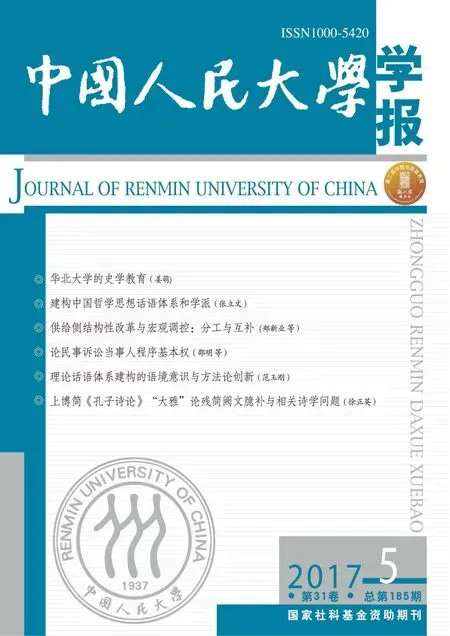何其芳与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
杨 伟
何其芳与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
杨 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文艺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不仅对当时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为新时期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培养了一批领军性人才。研究“十七年”文学史,就要关注“文研班”现象。在首届“文研班”学员开学典礼上,周扬正式宣布何其芳为“文研班”班主任。在“文研班”,何其芳以“广而专”的教学理念要求学员。何其芳以学者的大度与执着体现了特殊背景下政治与学术的共时存在。
何其芳;人大“文研班”;十七年文学;文艺理论史;马克思主义文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两个“文艺理论研究班”曾对当时的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产生重大影响。一个是1954—1957年北京大学举办、主要由苏联专家毕达可夫讲授的“文艺理论研究班”[1](P100-102)*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班”1954年4月开办,1957年结业。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曾为研究班开课一年,主要讲“文艺学引论”和“俄苏文学史”两门课。研究班学生从北大中、英、俄三系挑选。听课的还有来自全国主要高校的文艺学教师,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理论家的蒋孔阳、霍松林、王文生等。,另一个就是1959—196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文艺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中国人民大学的“文研班”不同于一般的研究生班,它是在周扬倡导下、中宣部委托举办的特别培训机构,培养过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骨干,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当时的文艺理论与批评走向。
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于1959年9月成立,1964年结束,共培养过3个班,大约111名学员。关于“文研班”成立的动因,值得用另文做专门的探讨,这里作为背景简略提及的是,“文研班”成立的1959年,在当代文学史上是很特殊的年份,“反修”与“反右倾”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词,辐射到文艺界,则是思想的混乱:既想“两条腿走路”,在纠正“大跃进”虚浮病的同时兼顾一点文学创作的艺术质量同时,又不能不顾忌当时日趋紧张的“路线斗争”。虽然难于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局,不过当时很多有关文艺理论的讨论(如“两结合”创作方法、如何对待古代遗产、文学的民族形式、创作是否需要才能,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等等),却也表现出对理论的渴求,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渴求。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 1958年年底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报告》, 20世纪60年代初又主持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都显示了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雄心”,举办人大“文研班”正是这个“雄心”的一部分。
这个“文研班”的班主任就是著名诗人何其芳。要梳理研究“十七年”的文学史,特别是这一段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就不能绕开“文研班”,那么自然也要关注对“文研班”贡献较大的何其芳。笔者通过查阅档案和大量的调查,意在弄清楚“文研班”的始末,研究当年活跃于文坛的这一文学理论批评“准流派”。这里提供的是有关何其芳与“文研班”关系的一些史料,希望能由此进入所要探讨的问题,并进一步引发研究者的思考。
一、何其芳与“文研班”的筹备
现有的几种何其芳传记,对何其芳参与人大“文研班”筹建并出任班主任的这段经历都语焉不详,甚至忽略不提*例如,何其芳任“文研班”班主任之事在严在勤的《何其芳评传》并未提及,虽此事在卓如的《何其芳传》、贺仲明的《何其芳评传》,以及蒋勤国的文章《何其芳传略》等中有提及,但都未对具体细节展开论述。,其实这是何其芳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
据参与过筹备的王平凡回忆:“5月—10月,何其芳、毛星、蔡仪、王平凡、何洛(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商讨,在人民大学建立文学研究班。”[2]王平凡回忆商讨筹办“文研班”的时间比较笼统,最早似乎是1959年5月。但何、毛、蔡等五人既然开始讨论建立“文研班”,显然已经是在落实中宣部、教育部的相关指示,那么实际筹备时间应当早于这个时间。笔者从人大档案馆查到一则最早与“文研班”有关的报告,即中国人民大学1959年4月4日的《关于我校1959年招收研究生问题向教育部的报告》,在该报告中提到:“文学研究班招收研究生30名,其中应届大学毕业生20名,请教育部统一分配,其余10名招收在职干部。”[3]而这份报告是回应3月14日教育部向各高等学校发送的一份通知,即《关于报送你校1959年招收研究生计划和征求有关招收和培养研究生问题的意见的通知》[4]。这样看来,早在3月中旬之前,人大就已经拟定并向上级报告“文研班”的招生计划,那么筹建的时间应在3月中旬之前,早于王平凡所说的5月份。以此推测何其芳知晓创办“文研班”的时间应当是在此时或在这之前。因为“文研班”是人民大学与文研所合办的,所以创办“文研班”之事必先通知时任文研所所长的何其芳。只是何其芳参与“文研班”最早的确切时间尚无资料确证。
“文研班”正式下文举办,是在1959年8月5日。当时中宣部发布《关于人大、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合办文学研究班招生办法》,要求“在人民大学合办一个文学研究班,以帮助各地培养文学理论批评干部”[5]。这是中宣部从官方层面宣布这个举措。
而在此之前,“文研班”显然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筹备,其招生计划就多次变化。如在人民大学1959年5月上报的招生简章中,文学研究班计划招收50人。但是6月公布的招生简章中,却又将“文研班”的信息删去,等等。由此可以设想“文研班”的创办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这里面涉及中宣部、教育部,以及人民大学、人大新闻系、人大文学教研室、文研所之间的协调。班主任的人选和任命、教师的选择也几经商讨请示。其中 1959年5月25日人民大学向教育部请示“与科学院协议,增设历史专业和文学研究班”[6]。教育部于6月13日回复意见为同意增设,并且指出“文学研究班设班主任,由文学研究所派人担任,并且很多课程由文学研究所派人担任”[7]。至此还未有明确任命何其芳为“文研班”班主任的文件。尽管如此,这一事实却早已被大家知晓。比如,新闻系文学教研室的同志在1959年5月20日的《关于文学研究班的组织机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该班因与科学院文研所合办,主任又是何其芳同志担任,为了尊重对方,若×该班独立,更能取得他们的支持和指导”[8]*因为资料中的字看不清楚,所以用“×”来代替。。何其芳被任命为“文研班”班主任,那是中宣部的决定。据相关回忆,此事的定夺在周扬:“经中宣部周扬批准,7月8日回信:任命何其芳、何洛为‘文研班’正副主任”[9]。
但何其芳被正式任命,是在“文研班”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上,时间是1959年9月21日。典礼上,周扬正式宣布何其芳为“文研班”班主任,何洛为副班主任。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直接宣布任命“文研班”班主任,也可见“文研班”的“规格”之高——这是中央委托组建的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一般的研究生班。
有名望的文艺理论家大有人在,为何选何其芳作为班主任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文研班”由人民大学与文研所合办,而且师资以文研所为主,所以选时任文研所所长的何其芳做班主任,是很自然的。另外,中央也可能考虑到何其芳有办学经验,何其芳曾于1940年11月任鲁艺文学系系主任,任职期间,他不但管理学生的大小事务,还给学生讲创作实习。因此,他在如何管理学生、如何安排教学内容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何其芳在鲁艺工作时,为人真诚,做事认真,周扬对何其芳是熟悉而且有好印象的。据相关回忆,周扬曾这样评价何其芳:“以他的文学素养和负责精神,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十分适当而又称职的人选”[10](P1)。当然,选择何其芳出任班主任,也可能考虑到他的学养,何其芳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诗歌理论、“典型共名说”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有史料表明,何其芳对于“文研班”是主动介入的。他在正式出任“文研班”班主任之前,就已积极地参与准备工作了。据人大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在筹备阶段,何其芳与何洛等人对教学计划进行了不止一次的研究。诸如,“本月二十五日何其芳同志与何洛同志约集文研所与人大文学教研室的部分同志,对文学研究班教学计划草案第二遍稿进行了研究”[11]。“本月二十五日”即1959年5月25日。那是他被任命班主任之前。何其芳在着手“文研班”的准备工作时,便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显然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教学任务,而是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一项大工程——培养党的文艺理论干部,他是带着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去从事这项工作的。
二、何其芳“广而专”的教学理念
“文研班”是中央直接指示举办的,不同于一般的研究生班,它的“规格”很高,培养目标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骨干,多少带有“干训班”性质。“文研班”放在人民大学来办,显然也是有过考虑的:当时的人大有些类似于党校,学员很多是调干生,政治要求是很高的。在那个特别强调政治化的年代,按照中央的要求来举办这样一个高规格的研究班,应当如何制定安排教学内容,这就要看何其芳的办学思路了。
何其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除了政治上的坚定,特别要求知识的“广而专”。他在“文研班”一班的开学典礼上强调:“文研班学员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正如金字塔必须建立在宽广坚实的地基上。”[12](P61)这便是何其芳对学员的要求:知识的广博和专业的精湛相结合。“广而专”的教学要求是为了更好地培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学好这门专业,必须注意到广泛钻研文学艺术的著作(古今中外),特别是现代文艺著作。”[13]可以说,何其芳“广而专”的教学理念一直贯穿“文研班”的始末。
据目前资料来看,何其芳在“文研班”期间并未明确阐述过“广而专”这一说法,只是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提及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在“文研班”开班之前,何其芳就把“广而专”的思路渗透到教学计划中了。从档案材料来看,无论是教学计划的初稿还是第二稿,都明确了“文研班”的专题讲授形式,规定讲授内容多样化,体现“广而专”的教学思路。教学计划的初稿把授课内容分为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三大部分。这时,专题安排还较为笼统,但这已经确定成为“文研班”主要的教学形式。具体办法是,在上课之前,学员先根据书目自学,课上老师根据专题内容及学员的问题进行报告和答疑。在第二稿中,何其芳等人又对“文研班”专题讲授教学计划做了修改,使之更加具体:在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三个教学板块之内,又分设若干专题,何其芳自己设定要讲授的专题就包括“文艺的典型问题”、“诗歌”、“话本和拟话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尽管在后来的实际教学中何其芳并未讲这么多,但这个“面”还是很“广”的。比较前后两份教学计划,发现何其芳“广而专”的教学理念一步步成型,并得到落实。
何其芳“广而专”教学理念还表现在“专门组”教学上。从1961年暑假开始,何其芳参与制定新的教学计划,即学员分组计划,把二、三年级学员分为文艺理论基础、美学、文学批评史三个专门组。教学计划表明:“根据意见,系行政初步进行了研究,并由何洛同志与何其芳同志交换了意见。现将进一步改进研究班教学的计划提出。”[14]学员的学习情况以及学员毕业后工作的需要成为1961年10月13日“修订教学计划方案草案的修订意见”出台的原因。有材料证明,何其芳参与了此次修订,“以上的修订教学方案和过渡教学计划及其他问题,是根据十月七日语文系系务会议和十月十日文研班班务会议(文研所何其芳、唐弢、蔡仪等负责同志都出席了会议)的讨论意见整理出来的”[15]。何其芳参与1961年10月的“专门组”教学计划,其结果是从二年级开始,分为文学理论基础、美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西洋文学六个专门组,也就是当时所谓“专门化”教学体制:“我校和文研所合办的文学研究班……同班主任何其芳同志商量,决定二、三年级由本学期起分专门化进行学习”[16]。“专门化”的分组实际上是分“研究方向”,让学员“学有专攻”,这自然是日后从事教学与研究事业的需要。在这之上形成的“专门化”教学模式并非让学员一头扎进狭小的某个课题中,无论哪个组,都还要打好共同的学术基础、有广博的学识视野。
何其芳“广而专”的教学理念还在其他事情上反映出来。比如他给学员开列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民间文学、中国文艺理论、外国文艺理论、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东方文学、西方文学的300本必读书目。*参见何西来:《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附录,即“由班主任何其芳所开具的必读书目三百部”。这份书单数量大、涉及面广,可以说囊括了古今中外最重要的文学名作和理论经典。何其芳修改过的教学计划有这样的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专业教学,不是单纯文学知识的传授,它是具有强烈的党性和战斗性的科学,要真正掌握它,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参加实际斗争。其次要认真钻研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的文艺著作(包括理论和作品)。为此,要拟定一个研究生在三年之内必须阅读的书目(书目见附件)。”[17]书目中外国文学及文艺理论的书目比重接近三分之二,涉及18个国家的经典作品,另外三分之一是中国文学及文艺理论。虽然也有“政治标准”和所谓现实主义优先的考虑,但涉及面仍然是相当宽的。
此外,在邀请专家授课方面也力图体现“广而专”。“文研班”汇聚了当时文学理论界顶级的学者和许多“大作家”,毫不夸张地说,是大师林立。授课者名单如下:蔡仪、钱钟书、余冠英、毛星、王燎荧、陈友琴、叶水夫、季羡林、李健吾、罗念生、冯至、朱光潜、宗白华、游国恩、杨周翰、吴组缃、赵澧、马奇、王朝闻、周来详、李泽厚、萧涤非、周振甫、黄肃秋,等等。他们讲述在各自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方法或体会,如朱光潜讲“西方美学史”、钱钟书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几个问题”、王燎荧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杨周翰讲“中世纪文学”、周贻白讲“中国戏剧发展概况”、马可讲“音乐界的创作与争论”等等,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文研班”培养的是“又红又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干部和高等院校的文艺理论教师”[18]。为此,学员学习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好这门专业,必须注意到广泛钻研文学艺术的著作(古今中外),特别是现代文艺著作”[19]。这样看来,何其芳提倡的“广而专”,这个“广”是有鲜明的指向性的,是为了给“专”一个宽阔坚实的基础。大概何其芳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论若要坚实有力,就要吸收中外文论的智慧,能够和不同的流派观点“对话”,提高自身的学理性,只有知识结构的“广”,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
这和他几年前对于“专”的想法相比较,是有变化的。1950年他写过《随笔四篇》,其中对专家的“专”是有微词的。他认为:“一个专门家,如果他不和人民群众结合,如果他不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及其所创造的新鲜事物学习,如果除了他的专门而外既不通晓一般的革命理论,又不了解一般的革命实际,那么他就不但对于他所专门以外的事情没有发言权,就是议论他所专门的事情也是可能悖谬的。”[20]当时何其芳不满于“专门家”脱离政治的“专”,希望专家更多关注现实。而现在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要“广而专”,这个“广”不只是现实,还包括相关的学科知识,这也是何其芳对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又红又专”要求的一种阐释吧。
“文研班”开办之时,文艺界正在“反右倾”和批判“修正主义”,诸如李何林的“生活真实论”、巴人和蒋孔阳的“人性论”、钱谷融的“文学即人学论”、张庚的“戏剧遗产中人民性”等观点,这时都遭到批判。何其芳强调“广而专”,似乎和当时的“风向”有点相逆,但他又为何这样做呢?有种解释是,他对当时只强调政治正确的“大批判”有些不满,希望文学批评能“以理服人”;同时,培养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也需要眼光开阔一点,写文章多一些学理性。
回顾“文研班”的历史,我们感到何其芳提出“广而专”的教学理念是很有前瞻性的。“文研班”的课程设置如此开放,要求学生阅读面相当广,就是把当年“文研班”的教学计划以及阅读书目和当下许多大学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培养方案比较也毫不逊色。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当年政治化背景下的“文研班”仍然如此注重打好学员宽广的知识基础。
何其芳“广而专”的教学理念,其实是他自己做学问的经验,他把这个经验带入“文研班”的教学中。何西来曾这样说过:“其芳师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自己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来要求和培养他的学生们的,因此必读书目和课程设置,都注意到了古今中外的兼收与包容。”[21](P13)虽然因各种“运动”不断干扰或中断学业,使得“文研班”“广而专”的教学计划并未能得到很好的全面实施,但即使那样,“文研班”的学员读书还是比较多,知识面也比较宽的,他们中不少人在“文研班”“广而专”的训练下获益甚多,打下较厚实的基础,这在那个特定时代是尤为可贵的。所以新时期到来,不少“文研班”出身的学者都能迅速跟上时代,成为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中坚。
三、何其芳与写作班子“马文兵”
“文研班”的目标是要培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但碰到那个特定的政治化年代,“反修”、“反右倾”以及“路线斗争”对文学的介入,“文研班”不能不受影响,而且很自然就顺乎这个时潮,强调在“实战”中培养评论家。周扬就曾指示学员:“你们除了读书,还要实践,要参加战斗。我们要高举反帝反修旗帜,与修正主义进行论战,在文艺战线,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在文艺战线反帝防修的任务也很重。你们要边学习边实践,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22](P24)这样,“文研班”学员便担负起“大批判”的任务,组成写作班子,经常以“马文兵”、“文效东”为笔名在报刊上撰文批判“资产阶级”或者“修正主义”文艺观。其中,“马文兵”的文章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马文兵”的写作是有组织的,属于集体写作,选题往往来自“上边”的指令,或者由揣摩时局的变化而得,总之是紧贴“大批判”的需要来选题,基本上是“听将令”的“命题”作文。一般是题目拟定后,集体讨论出提纲与观点,再根据文章重要程度或长度选择一个或几个人执笔,学员王春元、谭霈生、缪俊杰等人都执笔写过文章。初稿出来,大家讨论、修改。“文研班”的副班主任何洛还经常负责审查文章,他“要求一定要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时他还要求把原典带去,认真查对,力求做到准确无误”[23](P70)。
从1960到1961年,以“马文兵”、“文效东”笔名发表的文章不下22篇。其中如《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人性”问题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就“人性的异化”、“人性的复归”同巴人辩论》《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的艺术遗产—为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五十周年而作》等等,当时都曾经被当作体现“时事动向”的权威文章甚至是“风向标”。“马文兵”的文章文笔犀利,战斗性极强,几乎形成一种“大批判文体”。其特点是收罗归纳“论敌”的某一作品或某些言论,“提炼”出某些“要害”,放到特定的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的环境中去考察检讨,揭露其隐含的“阶级意识”、“立场”,然后判定其性质,这也就是所谓“上纲上线”和“揭露实质”。这类大批判文章讲究气势,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中找观点作依据,文笔犀利。
虽然没有资料显示何其芳直接参与过“马文兵”的写作组织或者策划,但可以肯定他是了解此事的,也知道“马文兵”在当时文坛已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他的态度如何呢?可能他的心情很复杂。作为班主任,何其芳默许“马文兵”写批判文章,在“场面”上,何其芳是支持这种“大批判”的。他在第二届“文研班”开学典礼上,就明确要求学员批判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文研班’的学风即‘战斗,革命,谦虚,刻苦,实事求是’”[24]。然而,对于“马文兵”,何其芳更多的是置身事外,让别人去管,他不愿多插手。他对“马文兵”的“大批判”文风是有些不满的,还找机会告诫学员,应尊重学者,包括当时被批判的学者。有学员回忆说:“何其芳看了我们发表的几篇文章后,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参加了学术批判,搞活了学习,有一股朝气;忧的是批判面过宽,一些观点有失公允。为此,他找班上几个干部谈话,提醒大家对专家学者要尊重,要学习,批判时要注意分寸,要科学,用商量的态度,不要盛气凌人。”[25](P60-61)在政治斗争的风暴中何其芳有些迷惘、无奈,他并不乐于让学生去写那种动不动扣帽子、盛气凌人的文章。
何其芳毕竟比较实事求是,尊重文艺规律,自觉不自觉地在和教条主义或文坛上的“左倾”思潮拉开一些距离。比如,当时何其芳和蔡仪等参与组织编写“毛泽东文艺理论大纲”,讨论怎么写时,有些同学的观点比较“左”,和老师发生分歧争论。那种“极左”思潮兴盛的情势下,一般是很难坚持正确的观点、去说服激进的年轻人的。但蔡仪和何其芳还是坚持认为不要简单套用毛泽东某些言论去解释那些具体的文艺理论问题。[26]有些学员的印象十分深刻:“何先生还总是嘱咐我们一些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话,比如说你们不要跟风,不要写那些时过境迁后没有价值的文章,要写就写打不倒的有学术价值的书和文章。”*2016年5月23日采访滕咸惠。
四、学者的无奈、大度与执着
有学者认为“文学何其芳”中有政治,“政治何其芳”中有文学,“何其芳只有一个,根本不存在‘两个何其芳’!”[27]“何其芳”只有一个,他身上体现的是政治与学术的共时存在。在政治与学术的纠缠中,何其芳有时也表现出他的无奈。
何其芳在“文研班”上课不多,但讲得有特色,不是系统的知识讲授,主要是答疑,围绕一些理论问题启发学员思考和讨论,何其芳回答疑问并做小结,他曾就如下一些问题给学员上课和“答疑”:关于“继承与革新”( 1962年3月22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红楼梦〉》和“典型共名说”、如何治学,等等*除“继承与革新”答疑有确切的时间外,其他何其芳答疑只有大致时间,所以笔者没有在文章中写出来。。根据学员的记录和回忆,何其芳作关于继承与革新的报告时,回答了三方面内容。*李思孝在“文研班”上课的笔记。首先,他就“古典文学思想内容是否有助于我们创造新文化”、“高尔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能培养社会主义个性”、“是不是古代遗产随时代发展越来越失去价值”等几个问题进行回答;其次,他总结说明应批判地继承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性,继承的标准是马列主义和人民需要,等等;最后,他引导学员进行“案例分析”,包括如何评价欧洲18、19世纪作品,如何看待历史上所谓“政治反动人物”(如李后主、苏轼、阮大成等)的作品,以及如何用历史的观点分析某些比较复杂的时代(如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等等。这些讲述和讨论,努力做到既有理论,又有实例,学员很受益。
但根据学员当时的笔记与回忆,也可以看到何其芳授课时的“理论紧张”,比如他对李煜词的评价。何其芳这位曾写过《画梦录》那样“悲哀的独语”的感伤诗人,不可能不欣赏李煜的词,即使后来变得“感情粗起来了”,也不见得不会和李煜词中那种感伤落寞的情调产生共鸣。李煜词历经千年能持续拨动不同时代读者的某根心弦,总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但何其芳在讲课时却特意要指出李煜词因写宫廷生活、男女生活、亡国恨等而“思想性”不高,甚至还生硬地拿“现实主义”为试金石,检验李煜的词,自然也就得出“虽然有现实主义特点,但是很狭窄”的结论。他进一步强调:“人民性绝不是李煜词的特色。”[28]“理由”非常简单:李煜词并不能完全反映人民最本质的生活面貌。“思想性”、“人民性”是当时用得最多的标签,何其芳顺手就拿来评说李煜了,现在看来是那样的机械和肤浅。这也可见一个时代对于诗人、评论家的巨大约束力,有时真是很难超越。
显然,这正是何其芳在政治与学术纠缠中犹疑与无奈的表现。如果只是看到何其芳的“无奈”,并把它看作其主要的精神特质,其实是减弱了其作为学者的形象意义,应当看到无奈之中,何其芳还有学者的大度与执着。
在那个虚浮的年代,面对“文研班”日益卷进“大批判”,何其芳是无奈与焦虑的,他尽己所能,让“文研班”正常运转,让学员真正得到学业的提升。当时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文研班”的教学秩序被打乱,计划老是完不成。当有人反映“文研班”一班学员学习专业课的时间过短,其他课和政治活动占用的时间过多时,何其芳便亲自给学校打报告,表明他的担忧。他认为:“1959级的业务课应当开始,不宜再拖了。”[29]然而,教务处却不予以批准,理由是“文研班”只学习了一个学期的政治课,不符合相关规定。何其芳等人还是坚持要求增加业务课的时间,最终校方只好同意这一届“文研班”延长一年学习。当时申请延长学习时间的报告上是这样写的:“为了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毕业后能担任教学和编辑工作,和弥补我们在执行计划上的缺点,我校与文研所何其芳同志都认为这个年级需要延长一年学习期限,以便补课和从事毕业论文的写作。”[30]又比如,在指导学员的毕业论文写作时,何其芳针对空泛的大批判文风,建议学生多注意从作品实际和文学史链条出发,去研究人物性格和环境的关系、人物形象的意义、思想和艺术成就,等等*这可以通过何其芳辅导黄泽新的四次谈话资料予以说明,参见何西来:《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84—8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何其芳曾担任1962—1963学年文艺理论专业毕业考试委员会主席,何洛任副主席,缪朗山、纪怀民、冯其庸为委员。何其芳并指导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李希贤等人的毕业论文写作。1963—1964学年毕业考试委员会主席改为何洛,何其芳不再担任主席,委员是马奇、缪朗山、赵澧、郑国铨,秘书是郑国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1962—1963学年各专业毕业考试委员会委员名单和1963—1964学年各专业毕业考试委员会委员名单。。更为重要的是,他敢请朱光潜、周贻白、李泽厚等当时正在被批判的专家来讲课。在请朱光潜来讲课这件事上,陈传才回忆:“何其芳、何洛说朱光潜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批评,但朱光潜的学问不可否认”*2016年10月21日采访陈传才。。在这样一系列小事之中,何其芳复杂的心理变化被如实反映出来,表达出何其芳在政治压抑之下学者的一面。
受“大批判”风气的影响,当时学生批判老师是常见的,有时还对老师缺少起码的尊重。而何其芳总是以学者的大度来对待学员。何其芳大概作过三次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答疑,其中讲过“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讲文学高于生活的原因,毛主席在讲话时候如何说的,后来发表时怎么改的,应该怎么理解”*2017年4月9日采访夏之放。。对此问题,何其芳认为艺术可以高于“普通的实际生活”,而不能高于如革命英雄、革命领袖之类者的“特殊的实际生活”[31]。现在看来,何其芳的所言确实有失当之处。当时还是学员的夏之放就指出:“这种认识不仅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这种看法会导致艺术家在处理革命英雄、革命领袖等重要题材时,放松甚至放弃典型化的努力,导致照搬具人其事的不良倾向。”[32]夏之放把其观点写成一封约五、六千字的长信寄给兼任《文学评论》主编的何其芳,结果,何其芳便把它发表在《文学评论》上,即《关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署名夏放。这便是何其芳作为学者的大度。也可见当时“文研班”虽然非常政治化,但在何其芳等人的努力营造下,还是有讨论和思考的空间的。
对于何其芳的“大度”和学术民主,其他学员也有回忆。在“文研班”,何其芳在他的答疑中夹杂对《红楼梦》的讲解,“讲他如何研究《红楼梦》”*2016年7月19日采访李思孝。;讲他研究此书花的时间很久,“有一次,他讲到写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个月时间,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驳他、超越他,起码在时间上得花八个月以上”[33](P105)。意思是要批判别人,自己总得先有较高的学养和准备,其中是含有告诫的。又有一次谈到“典型共名说”,何其芳认为:“文学作品就要创造典型的人物,而衡量典型的标准就是使典型成为一种‘共名’。比如像诸葛亮就是‘智慧’的共名,贾宝玉就是乖戾的‘共名’。”[34](P99)对此,学员王先霈并不同意。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觉得何老师反对庸俗社会学很对,但他的这种说法也未免带有另外一种简单化,便写了六七千字的作业交上去,说了不同的想法”[35](P188)。后来,何其芳还专门约王先霈到他家中讨论,结果是彼此谁也未能说服谁。在谈话结束王先霈准备走时,何其芳说:“王先霈,今天晚上我没有说服你,但是你也没有说服我。”[36](P188)这令王先霈感动不已,“一个身居要位的大师级学者,能如此平等地与一个不知名的青年教师对话,在他的眼里,只有纯粹的学术,没有所谓身份、地位的世俗之见,足见其赤子之心”[37](P189)。
在主持“文研班”时期,何其芳一方面要完成“任务”,他显然认为这项任务是有价值、值得去做的。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与人才培养也有信心,但受制于当时政治化的环境,他的“理想”又往往被挤压,学者的责任与习惯也有变形,难免经常陷于矛盾的境地,产生诸多精神的困扰。他的学生缪俊杰说:“我觉得何其芳先生兼有诗人和学者的两种气质。”*2016年7月27日采访缪俊杰。尽管在创办“文研班”的过程中受到很多现实情况的制约,有许多无奈,但何其芳始终保持有学者和诗人的气息,这显得尤其可贵。
何其芳在人大“文研班”的组建和运行中做过大量工作,“文研班”倾注了何其芳的心血。时过境迁,学术界对“十七年”文学有各种不同的评价,同样,如果评说“文研班”得失,也会调动各种不一样的感情,有不一样的结论。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何其芳主持的“文研班”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这几乎是一个“准流派”,对当时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产生过巨大影响。“文研班”的学员毕业后或者从事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美学的教学,或者到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或者进入宣传部门等,大多数都成为所在院校、单位文艺理论等学科的领衔角色,有不少是著名的批评家,如评论家何西来、缪俊杰,戏剧理论家谭霈生,批评家刘建军,美学家李思孝,古典文学家张锡厚,古文论学家马成生,文艺理论家李衍柱,等等,这些骨干对于文艺理论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他们中许多人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仍然活跃于文坛。“文研班”打造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豪华阵容,其多数学员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这其中,饱含有班主任何其芳所付出的心血。如今,“文研班”已成为历史,而探析何其芳在“文研班”的经历,也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这段历史,从而给予其一个客观的评价。
[1] 温儒敏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9] 王平凡口述,王素蓉整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大事记(中)——郑振铎、何其芳领导时期的文学所》,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11(1)。
[3] 《关于我校1959年招收研究生问题向教育部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9-JX13-A-3.0014。
[4] 《关于报送你校1959年招收研究生计划和征求有关招收和培养研究生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60-JX13-B-2.0011。
[5] 《关于人大、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合办文学研究班招生办法》,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9-JX13-A-3.0002。
[6] 《请示教育部党组关于各系学制及招生对象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9-JX13-A-1.0007。
[7] 《关于我校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学制和增加师资等四个问题向教育部党组请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9-JX13-A-1.0008。
[8] 《关于文学研究班的组织机构问题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59-XZ12-10.0010。
[10] 何其芳:《何其芳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1][13][14][15][16][17][18][19][29] 《文学研究班教学计划》,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61-JX13-A-7.0002。
[12][21][22][23][25][33] 何西来:《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0] 何其芳:《随笔四篇》,载《人民文学》,1950 (1)。
[24] 康丹:《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文研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6] 《新闻系批判修正主义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60-JX13-C-6.0007。
[27] 李杨:《“只有一个何其芳”——“何其芳现象”的一种解读方式》,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1)。
[28] 何其芳:《如何评价李煜的词(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集体讨论)》,载《文学遗产》,1956(105)。
[30] 《文学研究班延长学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1961-JX13-A-7.0001。
[31][32] 夏放:《关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载《文学评论》,1964(3)。
[34]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校友散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7。
[35][36][37] 王先霈:《王先霈演讲访谈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Abstract: A Graduate Class for Literary Theory Studies was jointly held b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Literary Research Department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Class not only influenced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at that time,but also cultivated many leading talents of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for the new period.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 requires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about“the Graduate Class for Literary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ith He Qi-fang announced as the head teacher by Zhou Yang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irst batch of students. He Qi-fang advocated the teaching concept that students should have extensive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ntangled in politics and academic, he showed helplessness,generosity and persistence.
Keywords: He Qi-fang;the Graduate Class for Literary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the history of literary theory ; Marxist theories of literature
(责任编辑张静)
HeQi-fangandaClassofGraduateStudentinRenminUniversityofChinaforLiteraryStudies
YANG Wei
(School of Litera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100)
杨伟: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 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