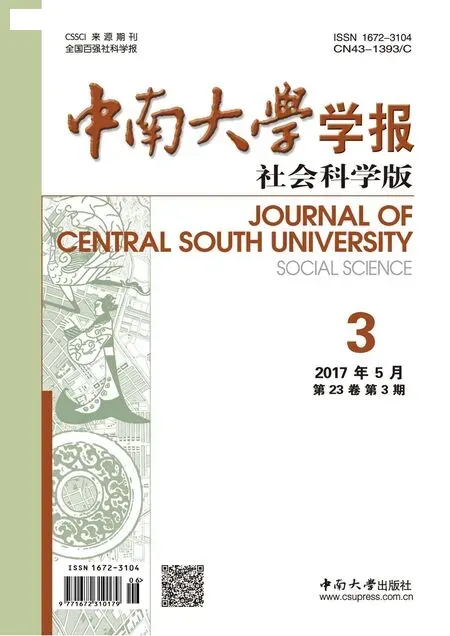生命拯救是可能的吗?——论米歇尔·亨利生命拯救理论的困境
刘少明
生命拯救是可能的吗?——论米歇尔·亨利生命拯救理论的困境
刘少明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当代法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认为生命已经在形式主义、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中被异化。为了回归本真的生命,对生命进行拯救,就必须对这三者进行批判和抛弃。但形式主义中的科学技术虽然从理论形式上脱离了生命的先验地位,但是仍然在不断地释放着生命的能量。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最终仍将给个体生命以间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信息传播在让主体的体验形式化与虚无化的同时,也让主体生命的感受能力在提升。整体主体虽然在叙述上抛弃了个体生命,但生命主体仍然吸收着它的有利成果在继续扩大和延伸自己的感受能力。历史主义表面上将历史形式化,抛弃了个体生命的内在历史,但其目的往往带有更深刻的对于主体生命的关注。因此,简单地对三者进行批判和抛弃并不能拯救生命本身,反而有可能是一种对生命的反对,进入生命拯救的困境。
米歇尔·亨利;生命;拯救;形式主义;整体主义;历史主义
米歇尔·亨利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现象学家,构建了其著名的生命现象学。在此理论的基础上,亨利又对以当代科学技术为代表的文化野蛮主义进行了批判。阐述了作为主体的生命如何自我否定,陷入异化的僵局,同时又将通过何种方式回归生命主体,提升生命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亨利阐述生命自身所包含的要素:能量,在自我否定中的作用。又强调了艺术、道德和宗教作为生命延伸的真正的文化,在拯救(这里提到的拯救,就是亨利提到的生命本身的回归,其含义将会在后面谈到)生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亨利在批判形式主义、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障碍时,却忘记了这三者本身也是生命的拯救所需要的东西。那么抛弃了它们,生命真正的拯救是可能的吗?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世泉的译文《法国哲学家米歇尔·亨利》中,指出了亨利所认为的生命现象为经济现象学提供基础的说法,并认为活的劳动是所有价值的基础。这一点在探讨生命与整体主义的关系时有很大的作用。杨大春在《文化与生命——米歇尔·亨利与科学批判的物质现象学之维》中认为“现代科学的极度发展导致了新的野蛮”[1]。本文将从形式主义、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三个方面来分析亨利对于主体拯救理论将要面对的困难。而在这之前,需要对主体拯救,也即主体回归本身所具有的含义进行详细的说明,以便后面的追问。
一、主体回归的三重含义
(一) 主体的本体性的回归
因为生命主体的本体性代表的是主体本身的地位,回归主体应有的地位是拯救主体的应有之意。
亨利所说的主体就是生命本身。“绝对的现象学生命,它的本质由自我感知和自我体验组成的事实——我们所说的主体性构成。”[2](6)而绝对生命,是一切显现的先验条件,所以在亨利那里,生命作为主体,具有很强的本体论意义,具体有以下几个表现。首先,“对自身的体验的知识是深刻的知识形式,因此作为活着的生命,是这个源初的知识”[2](6)。其次,作为生命的身体与自然互相属于对方。“身体与大地通过互属(Copropriation)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我们称这种源初的互属(Copropriation)为属身性(Corpspropriation)”[2](45)。这就是说,生命是自然显现的自然条件。不仅如此,生命还通过身体转化自然,“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个转化的历史”[2](46)。最后,在生命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制度、文化都可以归结为生命。比如当亨利在谈到技术时就说“源初的techne的本质就是一个通过我的身体的运动和努力所形成的系统”[2](45)。那么,亨利的主体的本体性就可以归纳为,生命作为一切存在现象的先验条件,不仅显示了存在,而且改造了存在,并在改造中创造文化,延伸自己。但是科学技术本身“通过将自然还原为理念的规定性,从而不再将感性生命或生命总体理论化”[2](62),并且认为“真理是外在于生命主体的领域,是单独属于客观的领 域”[2](62)。所以,回归生命本身,拯救被异化了的生命,就需要让生命重新占据这种地位,让自然、科学技术和各种制度都在感性生命的基础上得以解释。
(二) 感受力的延伸与增强
上面已经提到,生命主要表现为一种自我的感知,自我的体验。那么,假如这种自我的感知和体验被阻断,生命也就会在所谓真理、制度、实践中被排除掉,因此也就需要被重新释放出来。亨利提到了几个主要的手段,主要表现为生命从事艺术、道德和宗教活动。
首先,从艺术方面来看,“艺术是一种感性活动,是感性活动的满足”[2](23),“在艺术中,可以被体验到的是艺术的创作者的生命中的壮丽,是对生命感知的加强”[2](71)。也即是,艺术不仅仅是生命自我的感知,而且是对生命感知自身的发展和加强。无论是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从艺术中体验到的才是生命本身的壮丽,而非单调和空洞的知识,也非无生命的材料。
其次,从道德方面来看,“道德是生命各种样式的集合,它展现了与生命同样的强度和它的充分的满 足”[2](96)。在亨利看来,道德中所谈到的各种结果、规范和价值本身仅仅来源于生命。“生命在每一刻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适合做什么……生命不是先于或‘规定’行为,准确地说是等同于它。”[2](96−97)很显然,亨利的这种道德理论是一种以生命作为支撑的个体化的道德,是生命规定自身的行动理论。在道德中,生命实现了自身,满足了自身。回归真正的道德,才能拯救沦落的生命。
再次,从宗教来看,“宗教的根源在于,生命作为一种自我体验的,从来不是自身存在的基础。对与神圣的体验是这个终极的本体论处境的体验,和对于死亡的畏惧的体验”[2](126)。不同于前两种生命的自我延伸与满足,宗教是更为终极的体验。所以,亨利认为在每一种文化中,死亡的沟壑总与宗教相联系。而宗教的衰落也将导致艺术的衰落,因为“艺术是神圣 的”[2](126),这一点也可以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神秘主义绘画的兴起中看出端倪。
(三) 能量的释放
能量在亨利的生命现象学中,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假如我们称‘能量’为在与存在物的感受性的联系中,作为现象化的实现中出现的东西——作为通过自身生长而使自身向外的不可表达的经验——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的文化都是能量的释放,同时文化的形式是这个具体的释放的样式。”[2](200)从这里可以看出,能量本身是与创造力和向外表达有关的。也因此,能量这个概念本身与感受性是有关的,它表现的是感受性的自我发展的一面。“如我们所说,每一只眼睛都想看到更多……能量就在这个视觉之中。”[2](100−101)每一种感受力都有自身的能量,它追寻的是是感受到更多,但从根本上对追寻的对于自身的感受。生命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感受到自身感受力的释放。
那么所谓的野蛮主义(barbarism)就是一种能量的未被开发的状态。但是,即使是在能量被压抑的状态下,“能量会被持续的作为生命自身被产生出来。现在未被开发的能量就会被体验为忧虑(unhappiness)”[2](106)。 在这个过程中,忧郁(malaise)会不断增加,生命主体想要逃离却不可得,只会在这条道路上不断重复着。在能量未被开发的情况下,主体又不能逃离自身,就会产生无聊(boredom)。在无聊的情况下,主体“不知道做什么”[2](109)。生命就只会沿着它平常被教化的方式那样生活,于是“在生命自身的生长中,外在性进入了自身”[2](109)。这样生命就完全在这种无聊的状况下被外在的东西所抓住,丢失了自身。这样的情况也被亨利称作异化。
因此,克服这种野蛮主义,就是回到源头上让生命得以释放自身所具有的能量,让生命自身去感受、审美、理解和实践。具体的方式包括上面所提到的艺术、道德和宗教的实践,当然也包括本真意义上的教育、科学和技术(未被理念化的)。但是要实现主体生命的回归,仅仅靠这些手段足够吗?要克服哪些主要的障碍呢?
二、生命拯救理论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主体需要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需要物质的极大丰富,需要人的充分发展之后才能达到自由人联合体的状态。与实现主体的拯救一样,生命的拯救需要抛弃和扬弃很多障碍,去克服异化。根据亨利的文本,本文将这些障碍分成三个类别:形式主义的、整体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障碍。这三种生命的异化形式让生命失去了上面所提到的本真的生命的内涵,那么克服这三种形式本身是可能的吗?克服这三者会有什么后果?
(一) 形式主义的障碍
所谓的形式主义就是亨利经常提到的它对于生命的抽象化、理念化和排除。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对于主体生命的理论抽象化和对于自然的抽象化。而对于形式主义的批判,亨利主要提到三个值得最引人注意,也是统治力最强的领域: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学和新闻传播。那么这三个障碍是如何阻碍生命回归自身的呢?亨利在此又是如何陷入困境的?
1. 从科学技术来看
对于这一点,亨利继承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以来的现象学传统,批判了自伽利略以来的科学的数学化和完全的理念化,并且将他们对于这一点的批判推向了前进。胡塞尔对于科学的批判点在于——“被理念化的自然不断地代替前科学化的直观自然”[3]。符号化的科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应用技术将自然和人都当作“物体”,使本源的生活世界被形式化、被遗忘。海德格尔的批判点在于——“数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能够且只能作为数学性筹划而起作用”[4]。所谓的数学性筹划就是数学性视域,也即存在性视域。就是自身存在性的视域决定了数学作为一门定量的学问贯彻了整个现代性视域。亨利立足于主体的自我感发的特质,认为理念化的科学是对生命的否定。“科 学——数学性的自然科学——排除了自然的感觉特质,也就是排除了生命世界和生命自身。”[2](62)而技术的自我繁殖将对生命造成极大的危害。“技术像疾病一样传染,它缺乏任何规则,仅仅在在其完全的冷漠中朝向不是它自身——生命的东西。”[2](52)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人员都成为了科学技术研究的工具,忘记了自身的起源。
那么亨利对此克服的方式在哪里呢?“源初的科学作为生命总是持续地达到自身,作为不断的对自身的感觉和体验,同时作为以某种方式体验着的某物和以作为源初的是其他一切体验基础变化着。”[2](68)这就是说,要克服生命技术本身的纯粹形式的挑战,就必须回到科学技术的起源,让真正的生命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实践中起主导作用。
但是这种对于回到生命自身的感受力的科学技术与符号化、形式化和数学化的科学技术之间的冲突有看起来的那么严重吗?实际上是没有的。首先,就如亨利自己所说:“在科学研究中有一种特殊的喜悦,它属于观察本身。”[2](112)因此,即使科学研究所处理的对象离我们生命直接的感受已经十分遥远,但是科学发现本身对于研究人员的生命来说仍然是一种直接的喜悦。其次,遥远的科学研究对象本身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表面的感受不能抹杀这种生命的特殊形式——生命面对吸引力时的冲动与渴望。或者更进一步说,它背后所包含的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命保存的渴望和对于恐惧的排斥,与直接的吃、喝、住、穿是一致的。最后,离直接的生命感受力遥远的科学技术仍能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中形成有利于直接的生命感受的物品。就如曾经看起来那么遥远的无线电波的研究,如今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每个人的手机、电视、电脑等的生活中,补充和增强着我们的感受力。也即是,用拯救生命的三个标准来衡量形式化的科学技术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科学技术虽然从理论形式上脱离了生命的先验地位,但是从其起源和功用上来说仍然是服务于生命的感受力,并加强着感受力,因此也仍然是在不断地释放着生命的能量。 “正是在生命的最深处,我们看到了科学最深刻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也正是在生命的最深处,我们看到了科学的生命和科学家的生命的融合。”[5] 科学技术正在磨灭生命,也能拯救生命。抛弃形式主义的科学将会带来科学的停滞,对生命本身的损害会更大。
2. 从政治经济学来看
对于亨利来说,“活的劳动及其与其相适合的身体都是不可衡量的”[2](88)。但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为了让交换和分配得以可能,价值必须被规定,因此价值的尺度——客观劳动——也必须被规 定”[2](88)。而这个所谓客观劳动只不过是时间的持续,并且这个时间本身也是被形式化了的时间,是时间的表象。这样,政治经济学里面的劳动和时间都只不过是生命的劳动和生命的时间的表象。政治经济学就完全被形式化了。
与之相对应,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肤浅的批判。它们仅仅是纠正某些概念(比如资本周期的概念),但永远是在生命劳动和生命时间的表象中运作,没有回到生命劳动和生命时间本身。第二个方面的批判就是根本性的批判。它的目的在于追寻政治经济学为何会以表象性的形式代替其起源,并致力于回到这个起源。“在源初的自然的属身性(Corpspropriation)的自然中,集体中的个体为了将自己现实化,每一个生命为了获得总体产品中属于他自身的那部分,都要评估和衡量他在所有人劳动中自己的那部分劳动。”[2](90)这也就是亨利所提到的政治经济学的先验起源。在其中,生命的劳动得到了肯定。在政治经济学的生命拯救中,也就是要让政治经济学回到这个起源,回到“经济作为生命的价值……整个经济的实体仅仅有其指向生命的价值”[2](88)这个出发点。
然而,即使如亨利所说,政治经济学回到其先验的本源,但是没有经过量化的交换如何可能呢?也即是,作为主体的生命如何能够衡量他在总体劳动中自己所应得的部分呢?因为毕竟“将要将换的产品和将要成为商品的产品在量上是不同的。这个量可以从质料的本质和使用价值两个方面来考虑”[6](192)。如果按照亨利所说“存在是不可交换的,它们是不可比较的。同时真正的劳动是主观的时间性,在每一个特殊的情况下都拥有一种特殊的现实性,它也是不可交换 的”[6](194),那么回到起源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劳动都没法知道自己所应得的部分。在这一点上同时会产生三个问题。首先,交换不可能,回到源头也就不可能。也即是,政治经济学的先验起源也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条件达到。回到每个概念都直接与生命相关也不可能。因为交换本身必须要让物被量化、客观化。其次,即使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源头,这种回归是否能带给生命以更多的感受性、扩大生命的感受性?是否更能促进艺术、宗教和道德的增加?是否更加能够释放主体的能量?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历史来看,失去了客观主义公平原则的社会往往会让更多的人遭受奴役,生命的感受性和能量都会收到压制,也只有少数人能在艺术中得到感受力的延伸。而罗尔斯的“在无知之幕的基础上用一个纯粹形式的正义作为理论的基础”的观点[7](118),更能消除由于暴力和权利的压制导致的这些问题。所以“正义才是政治制度的第一优点”[7](3)。最后,形式化政治经济学是否真的是完全反生命的?表面上来看是。但如上面所说,分配的公平最终仍将给个体生命以间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人们将会有自由的时间去欣赏艺术,至少有基本的物质去保证生命的存续。抛弃形式主义的经济学,将给人类带来公平和物质上的退步,将给生命带来基本存续上的威胁,因此扩大感受力和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都得不到保障。
当然,我们也必须破除在完全形式化中生存的个体,他们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将交换价值的逻辑完全内化于心,以至于当一件东西仅仅被提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对它产生欲望。”[8]这种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的两面性始终存在。如何消除纯粹符号形式的控制呢?这一点将在历史主义的障碍中探讨。
3. 从新闻传播来看
亨利认为,电视节目的“审美”是对一切审美的否定。首先,电视节目取消了真正的感性生活。电视节目对于人的眼球的吸引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美元和石油的上升或下降,黄金的上涨或下跌,被强奸女孩的最近大厦的门卫的采访,驾驶帆船跨越大西洋……”[2](112),每一个孤立的时间如走马观花般出现在眼前,一时激起涟漪,很快又会被遗忘。生命放弃了感官,放弃了理解和爱的实践。其次,“新闻(actualité)规定了什么是现实”[2](111)。这让个体生命自身对于现实的体验变得被可操控。这就决定了所有的现实都进入了符号的阶段。“到处都以相同的方式出现的仿像:时尚中美与丑的互换、政治中左派与右派的互换、一切传媒信息中真与假的互换、物体层面上有用与无用的互换、一切意指层面上自然与文化的互换。”[9] 可以说,新闻传播达到了形式化对于生命宰制的高峰。
但新闻传播不仅仅是负面的。从生命的先验地位回归来看,新闻传播在异化着生命的同时,在量上提高着生命揭示世界的能力,扩大了在信息传播不发达时代的有限的生命体验。但同时在质上并没有缩减。无聊仅仅是众多生命的一个状态。其次,在提升生命的感受力方面,新闻传播让生命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欣赏绘画、戏剧、音乐等艺术,去释放生命的能量,而不仅仅是走马观花般打发无聊。所以最关键的是如何提高主体的感受能力、辨别能力,而非单纯否定新闻传播。王晓升在评价劳动时说,“对于一个人来说究竟具有象征意义、满足需求的意义还是自我实现的意义,这是由个人的自我理解来决定的”[10](80),任何被传播的信息也都需要主体生命的过滤。马克思说:“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11](87)而恰恰现在能欣赏音乐的耳朵越来越多。信息传播在让主体的体验形式化与虚无化的同时,也让主体生命的感受能力在提升。因此,抛开信息的扩张,主体本身的感受能力未必能够进步,主体也未必能体会到真正的事实,生命也未必能够被拯救。
(二) 整体主义的障碍
所谓的整体主义就是忽略生命的个体特性,将所有的生命当作某个工程中的小小一员来对待,生命停止作为社会的基础。“政治上的从属性意味着整体主义。”[2](134)亨利对此的批判具体表现为对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整体性的批判。
在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的批判上,亨利借助了上面提到的对于媒体宣传的批判。“社会存在的贫困被一种修饰过的和歪曲的形式从媒体中展示出来”[2](134),“那些能以‘事件’的标题所宣称并存在的东西,肯定是能够被播放的东西;它是且肯定是被创造的、剪辑的,并且是被不可逃脱的需要所限制的东西。这个需要本身的本质就是我们早已认识到的东西:新闻(actualité)”[2](136)。也即是,人们对于政治事件的认识,早已经被政客所控制。人们所以为的民主,只不过是被操控的民主。因为人们的意识已经在每天的新闻媒体的轰炸下被操控了。同时,亨利更是认为所谓的民主投票是一种真实的虚无。“客观的‘公共观点’是被一种调查的虚构所创造出来的,在其中仅仅能发现数学和数学化的坐标的应用”[2](78),这是因为所谓的调查和投票只不过是一种对人进行了抽象化之后的结果,真正的生命并没有在民主投票中被活生生地表达出来。具体来说,因为每个人获得的信息量有限,并且内心做出的判断是复杂、不确定和易变的,那么一时的投票并不能说明结果真的代替了每一个人的判断。英国人自己投票脱离欧盟后,接着又有很多人站出来要求重新投票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亨利在对民主政治的反对上太过于扩大化。首先在宣传上,民主社会的新闻媒体的宣传诚然有控制成分,但是仍然扩大了人们的信息量。信息量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反控制力量的增大。当今网络的发展为各种谣言提供了温床,也为辟谣提供了方便。应该说,信息量的扩大好过信息不畅,也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另外,民主投票所形成的契约仍然在正义制度上有一定的贡献。罗尔斯就认为个体之间“达成协议的基础在于协议化的处境和对于善物的追求”[7](118)。而协议化的结果促进了善物的公平获得,公平的获得更有利于生命的保存的发展。生命的感受力仍在这种整体主义带来的物质丰富和制度安全中获得了保障。最后,尽管政治上的政策往往带有政治家的目的、各种主义的情绪和不周全的考虑,但是逃脱开这种整体的民主制度,个人如何完全享受主体生命自身呢?“在成熟的社会里,公民已培养出一种妥协精神,能够并希望在既有制度范围内通过协商、谈判与互谅互让解决分歧。否则,大量涌现的政治冲突与拒绝妥协的斗争精神足以摧毁任何民主政体。”[12]显然,资本主义民主作为生命复归的障碍,仍然不能直接被否定。
亨利也批判了社会主义的整体性。首先一点就在于他对阶级观点的批判。他认为,社会主义里面的阶级理论将阶级中的生命整体化看待,没有看到个体化的生命的差别。其次,“马克思主义……有其自身的规则,但是它呈现了一个对于伽利略计划的混乱的模仿……因为假如历史和社会仅仅是有着自身运动的存在者的话,就没有对于个体的拯救,而只有对于将这些个体混合在整体之中,这个整体规定着个体,并为了与他们和他们的命运相符合而走出个体”[2](92)。亨利这里对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就在于其整体的计划性,仿佛个体完全为了某一个目的被牺牲掉。
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首先,“当马克思提出同质性工人的时候,马克思是从雇佣劳动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工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人构成了一个阶级,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否定了工人在生产中的差异”[10](301)。这说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实际上并没有抹杀对于个体生命差别的区分。而且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与亨利具有同样的旨趣:“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是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1](85)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对于主体生命自身总体性的一种肯定,对于个体之间的差别是不可能被否定的。其次,社会主义的计划性是否完全是对生命的否定和排除。“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计划经济,在当时起码适应了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13],这说明计划在一定时间内是有巨大作用的。经济体系的建立尽管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也有粗放浪费之嫌疑,但是毕竟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建立了工业的基础。工业发展本身不是对生命需要的满足吗?工业发展不是为生命的存续保驾护航的吗?当代工业的符号化和形式化的发展本身尽管已经离具体的生命有点遥远,但是生命本身仍然可以利用这些成果为自身服务。同时,计划的根本还在对于人的生命的关注(比如生产多少粮食,建立多强大的国防等),并不是为了否定人而设定的,尽管这种总体化的操作造成了对于生命主体的相当程度的漠视。
所以,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整体性虽然有很多脱离生命基础的地方,并且看起来离主体生命的基础越来越遥远,但实际上其根本仍然在生命处。生命主体仍然吸收着二者的有利成果在继续扩大和延伸自己的感受能力。消除整体主义的亨利将以何种形式来替代它?生命的伦理、艺术和宗教的要求需要在集体中实现,批判集体主义本身并不意味这个人生命在能量上的释放,反而是对能量释放的条件的否定。
(三) 历史主义的障碍
在亨利那里,有三种历史。第一种历史是绝对主体的历史,这是一切历史和历史性的发端处。“作为绝对的自我感发(Auto-affection),生命的主体以一种个体唯我性的形式在每一时刻被历史化和本质化。”[2](37)个体生命的历史是源初性的历史,是生命内部的痛苦与欢乐的交替。第二种历史是一种衍生性的历史。“我们不断转化着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个转化的历史……但是这种转换仅仅是属身性(Corpspropriation)的使用和现实化,这种属身性让我们以主人的身份栖居在大地上。”[2](45)这种历史是内在的外在化,生命的历史变成了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就是生命不断转化世界,进行实践的历史。第三种历史就是完全客观化和时钟化时间上的历史。这种时间“是真正时间的表象:也就是宇宙的客观时间,时钟和世界的时 间”[2](89)。而亨利所要批判的历史观就是第三种历史。但是第三种历史本身并不是要被批判的唯一原因。
亨利所要反对的历史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首先,他在对存在的解释时说,“当感性存在不再受到关注,它的表象仅仅在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和语言的给予物的基础上得到解释”[2](92),即一切存在物都可以被解释为历史的产物,主观的感性体验,生命自身的苦乐被抹杀。其次,与上述亨利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历史主义表现了一种历史的计划,在历史的过程中将人类进行拯救。这种拯救理论所使用的是第三种历史观,它本身已经忽略了个体生命,而将历史社会当作一个主体来看待。所以这一点对于亨利来说,历史性和整体性的错误是同样的。要使生命得以回归到其本身的历史性,就必须消除这种历史观的障碍。
但是这种批判仍然是片面的。首先,对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的批判并不代表历史主义本身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关注生命。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例:“主体性是历史主体在改造客体的对象性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特性,表现为人总是从自己出发,即从自己的内在需要、利益、爱好、愿望出发。”[14]这说明尽管在历史主义那里,历史表现为一个不受单个个体掌控的形式,但是主体自身仍有着自身行动的能力,并不是完全听任摆布的棋子。并且主体生命都参与了这场历史的变迁。其次,历史主义的目的往往带有更深刻的对于主体生命的关注。就如亨利在研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时说的那样,“它参加生产仅仅是为了实现其主体的实践潜能”[6](306)。这里的历史主义虽然预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同时以一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外在方式来表述这个过程,但是这种历史主义往往承载的是对于现实的人所受处境的不满和对于未来历史的推测和向往。而这个推测和向往的基础就在于对于人的生命主体的深深关怀。不然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描述的时候,也不会把个人潜能的实现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一点,对于消除政治经济学中的符号形式控制也至关重要。
所以,尽管历史主义存在着不以绝对主体的生命来进行阐述历史的毛病,也存在着忽略真正主体历史的风险,但是历史主义本身仍然与亨利的生命主体有着相同旨趣的一面。那就是,历史主义就是为了扩大生命自身的感受能力,开发主体的潜能,释放主体的能量而设定的。反而,如果没有历史主义带有痛苦性的挣扎和努力,亨利的生命如何通过自身,回到自身和拯救自身呢?所以,亨利仅仅能在实际的历史表述上否定历史主义的疏忽,但在实际操作上,却仍要倚重历史主义的实效。
三、结语
总体来说,亨利的生命拯救理论对三大障碍的批判和克服是片面的。形式主义中的科学技术虽然从理论形式上脱离了生命的先验地位,但是从其起源和功用上来说仍然是服务于生命的感受力,并加强着感受力,因此也仍然是在不断地释放着生命的能量。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最终仍将给个体生命以间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人们将会有自由的时间去欣赏艺术,至少有基本的物质去保证生命的存续。信息传播在让主体的体验形式化与虚无化的同时,也让主体生命的感受素养在提升。而所谓的整体主体虽然在叙述上抛弃了个体生命,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本身虽然有很多脱离生命基础的地方,并且看起来离主体生命的基础越来越遥远,但实际上其根本仍然在生命处。生命主体仍然吸收着二者的有利成果在继续扩大和延伸自己的感受能力。最后历史主义虽然表面上将历史形式化,抛弃个体生命的内在历史,但其目的往往带有更深刻的对于主体生命的关注。所以,简单地对三者进行批判和抛弃并不能拯救生命本身,反而有可能是一种对生命的反对。亨利在大力批判三者的同时,未曾注意到自己已经陷入了悖论之中:自己所要抛弃的东西也正是自己所要借助的东西。忽视了这三者,人类的文明可能会回到另外一种野蛮,一种完全不同于亨利谈到的生命的自我否定的野蛮,而是人否定人、自然否定人的野蛮和人深深体会到自身的无力与渺小的野蛮。那样的拯救是真正的拯救吗?
[1] 杨大春. 文化与生命——米歇尔·亨利与科学批判的物质现象学之维[J]. 求是学刊, 2009(4): 5−10.
[2] Michel Henry. Barbarism[M].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3]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M]. Trans by David Car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50.
[4] David Farrell Krell. Basic writing: from being and time to the task of thinking[C]. San Francisco: Harper Collins, 1993: 293.
[5] 孟建伟. 科学·文化·生命——论科学生活的人文复归[J]. 社会科学战线, 2008(5): 15−22.
[6] Michel Henry. Marx——A philosophy of human reality[M]. Trans by Tom Rockmo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7]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M].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8] 让·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 夏莹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11.
[9] 让·鲍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M]. 车槿山译. 南京: 译文出版社, 2012: 7.
[10] 王晓升.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构[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2] 龙太江. 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妥协精神[J]. 文史哲, 2005(2): 156−161.
[13] 武力. 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3(4): 37−46.
[14] 杨耕.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33.
Is saving life possible?——On the dilemma of Michel Henry’s theory of saving life
LIU Shaom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s the modern French phenomenologist Michel Henry believes, life has been alienated in the formalism, collectivism and historicism. To go back to the authenticity of life and save life, we should criticize and discard the three, which are obstacles of saving life. However, as one of the formalism, science and the technology break away from the transcendental position in view of the form, but they still constantly release the energy of the life. As another formalism, political economy will at last give indirectly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At the same time,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has been criticized in that it has caused the formalizing and nihilism of the experience, but it has still enhanced the ability of the auto-affection of the life. Even though collectivism throws the individual away in terms of the narrative,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life still absorbs the good result of it and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extend its ability of the auto-affection. At last, historicism seemingly formalizes the history and throws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life away, but its aim always pays some intentions to the life. All in all, simply criticizing and discarding the three obstacles not onlyfail to save life, but also may cause the result of negation of life, and at last lead into a dilemma.
Michel Henry; life; saving; formalism; collectivism; historicism
[编辑: 颜关明]
B565.59
A
1672-3104(2017)03−0020−07
2016−11−14;
2017−03−12
刘少明(1988−),男,重庆奉节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现象学,法国哲学